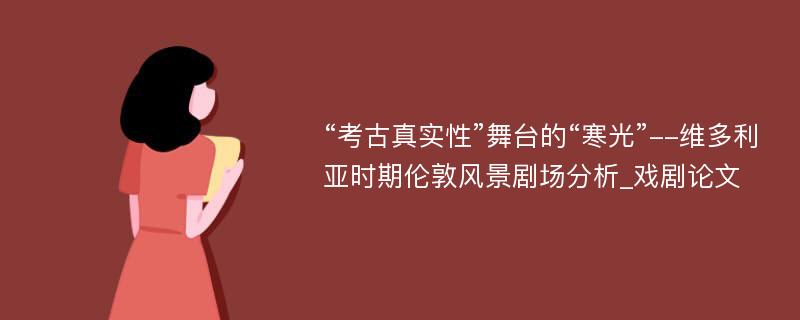
“考古真实性”舞台的“冷辉煌”——试析维多利亚时期伦敦景观剧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多利亚论文,伦敦论文,剧场论文,景观论文,真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1-0045-09
在英国戏剧史上,19世纪一直被看作是戏剧衰落的时期,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少数学者的质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戏剧批评家迈克尔·R·布斯(Michael R.Booth)。在1969年出版的《19世纪英国戏剧》第一卷的绪论中,布斯指出:“与其说戏剧‘衰落’,不如说戏剧已经在新的社会文化中激烈地改头换面。”(Booth:6)20世纪70年代以降,大量有关19世纪戏剧的论著相继出现,许多学者开始纠正以往戏剧评价体系只关注戏剧文学而忽略舞台艺术的做法。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衡量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戏剧的成就时,剧场艺术至关重要,戏剧文学倒在其次。(Booth,1974:7; Woodfield:2; Taylor:8)最近几年,维多利亚戏剧史的专家们更是从舞台艺术、观众接受、女权主义、东方主义、市场文化等多种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剧场文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①
在这些研究成果所引征的大量史料文献中,“考古真实性”舞台(the stage of archaeological authenticity)这一在维多利亚时期盛极一时,继而渐趋无闻的舞台艺术创举,逐渐浮出水面。西方学界已经出版了几本相关的论著,主要从舞台艺术效果以及剧场社会地位的角度进行分析。②在国内,何其莘教授在《英国戏剧史》中对19世纪剧场进行了一般性介绍;吴光耀先生在《西方演剧史论稿》(上)中对“考古真实性”舞台的历史形成、舞台技术特点也有过简单评介,此外鲜有详尽的研究论述。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世纪三位剧场艺术家的舞台实践来对“考古真实性”舞台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特点进行简要的梳理,并进一步结合社会文本以阐释维多利亚时期剧场与同时代新兴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更深层次上说明了当时社会景观化形象展示体系的确立以及公众历史真实体验的缺失。
一、“考古真实性”舞台的发展历程
“考古真实性”舞台盛行于19世纪中后期,主要指剧场利用当时刚刚兴起的考古学方法,在舞台布景和服装方面追求历史准确性,并结合各种复杂的技术手段创造出华丽壮观而又颇具真实幻觉效应的舞台。这种风格在英国始于1823年查尔斯·肯伯(Charles Kemble)排演的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③在古文物研究者塞缪尔·迈瑞克(Samuel Meyrick)和弗朗西斯·杜斯(Francis Douce)的协助下,该剧的舞台设计师布朗佩(J.R.Planché)成功再现了莎士比亚时期戏剧舞台的服装风格。这种力求精确复制的突破性设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轰动效应。在日记中布朗佩写道:
幕启之时,穿着打扮酷似其肖像画的约翰王出现在伍斯特大教堂,围绕在他身边的男爵们身穿梭子盔甲,头戴圆柱形盔帽,手持刻有纹章的盾牌;他的众多朝臣穿着13世纪的束腰长衣和斗篷。当观众们发现这一切时,剧院里响起一阵赞叹的欢呼声,接着是四轮清晰可辨的掌声。掌声如此普遍热烈,演员们甚至都有些惊恐。我深感工作中所经历过的困难、焦虑和烦恼终有回报。(Jackson:164—65)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布朗佩的考古展示一方面在于根据肖像画设计人物形象,另一方面,无论是剧中主角还是众多陪衬人物,其服装都无一例外包括在考古细察的范围中。前者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英国戏剧舞台,形成了包括人物在内的“舞台似画”风格。后者极大地增加了舞台设计的难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世纪后半期剧场演出从保留剧目轮演体制(the repertoire system)到同一剧目长期演出体制(the long run system)的改革。而观众热烈即时的反馈则说明当时的戏剧观演开始注重“形象展示”本身的魅力。“考古真实性”舞台的最初尝试所引起的这三方面特性在随后的发展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19世纪中期是“考古真实性”舞台设计的发展成熟阶段,最杰出的代表是有着“剧场古文物研究王子”之称的查尔斯·凯恩(Charles Kean)。任公主剧院(the Princess's Theatre)经理期间(1850—1859),凯恩以考古展示的方式全面复兴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麦克白》的演出海报中,凯恩首次围绕该剧的历史背景对自己搜集史料的考古勘查过程大篇幅予以说明。(Schoch:37)在《亨利八世》中,为了逼真再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伦敦街景,凯恩竟利用当时盛行的活动全景画技术(moving panorama),在舞台上复制了安东尼·梵·戴尔·维尼利德(Anthony Van Der Wynyrede)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幅历史画作品。根据凯恩的说明,画面开始于“布莱德威尔宫,经由舰队渠——黑衣修士修道院——圣保罗教堂——伦敦大桥——伦敦塔——莱姆豪斯区……终止于格林尼治宫”。(Schoch:43)这一规模宏大的街景在“考古真实性”舞台设计方面颇具代表性:一方面,所选取的画面均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风景名胜,舞台效果因此不同于普通的“写实主义”,华丽壮观的效果才是其突出的重点;另一方面,依据绘画作品所设计的舞台具有鲜明的“图画”特色,并且这一“舞台似画”的风格也延伸至戏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舞台上,穿着具有历史准确性服装的演员仿佛是“画”中的一部分,表演往往强调身体展示而不是语言动作。和肯伯与布朗佩单纯的服装展示相比,考古学方法已经成为凯恩全部舞台设计的核心。在感受历史真实的同时,凯恩热衷于引导观众注意从舞台整体效果到服装设计细节的考古研究的显著成果,这一做法实际上与提升剧场社会地位的意图密切相关。在凯恩的努力下,公主剧院借助“如此明显的文化蕴涵,如此明白无误”的演出风范,扭转了19世纪初以来剧院在公众心目中“低级粗俗”的形象,重新成为社交名流和富裕中产阶级的娱乐场所。(Taylor:25)由于在考察历史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凯恩本人也在1857年被选为伦敦“古文物研究者协会”的成员。
尽管凯恩在舞台设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考古展示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商业利润。与同一时期的德国和法国的国家资助剧院截然不同,英国剧院长期以来一直是自主经营的机构,票房收入对于剧院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新的演出风格和当时普遍采用的剧场运营模式间存在很大矛盾:“考古真实性”舞台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均消耗巨大。演出前需要遍访博物馆、艺术画廊,甚至实地考察历史原址来保证所依据的材料的真实可靠;设计舞台时要对每一件演员服装、每一个舞台道具精选细制;舞台空间十分有限,需要动用灯光、平面绘画布景、组合布景、全景图、透视画等各种技术手段营造真实效果;而当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时还要雇用几十甚至上百个临时工人在后台各个部门工作,以保证舞台“真实幻觉”的完美再现。这样一来,每一个剧作的排演时间也就相对较长。但在原有保留剧目轮演体制下,剧院习惯于上演常备剧目,剧目演出更换频繁,具备“考古真实性”的精雕细刻之作无法收回预支的大量成本,勿论盈利;而新的剧作缺乏足够的准备时间,演员们更没有精力去认真揣摩排练角色。因此,随着考古式真实风格的盛行,剧院经营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1860年,伦敦艾德菲剧院(the Adelphi Theatre)首次以长期演出体制上演了剧作《玻恩姑娘》(The Colleen Bawn)。该剧连续上演230场,票房收入相当可观。该剧院经理迪恩·布希科(Dion Boucicault)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创造了剧院经营的新秩序”,并以高达20万英镑的净利润开创了伦敦剧院商业收入的新局面。(Taylor:8—9)长期演出体制的确立为剧院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也在各个方面为考古展示提供了保障。正如布斯所言:“只有一种方式能够承担花费如此巨大的演出并从中获利:长期演出体制。”无论是艺术上的成熟,还是商业意义上的成功,“考古真实性”舞台的高潮终于在19世纪后半期到来。
亨利·欧文(Henry Irving)是19世纪后期英国最富盛名的演员——经理④。从与他同一时代的批评家珀西·菲茨杰拉德(Percy Fitzgerald)引述的一段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文在当时伦敦戏剧界无人能及的显赫地位:
欧文先生将会声名卓著,流芳百世,后世的戏剧年鉴将会在所有有关戏剧的场合,对欧文先生的名字倍加赞颂。与宴诸位的子孙后代读到此时,他们将会因为自己的先辈曾参加我们今天的晚宴而感到自豪。(Fitzgerald:152)
欧文也是英国戏剧史上第一位获得皇室加封爵位的演员。1888年,欧文重新排演了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麦克白》,为了在服装和道具方面达到考古准确,舞台设计师查尔斯·凯特穆尔(Charles Cattermole)搜遍了英国和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的博物馆,“为每一件戏服、武器、设备以及家用器具寻找权威参考,细致程度达至每一个钉子、纽扣和刀片”。最后,凯特穆尔总共设计了“408套服装,其中包括165套士兵服装……还有80套传统女巫的服装”。(Spielman:98—99)《麦克白》一共上演151场,取得很大成功。法国著名戏剧导演安德烈·安托万(André Antoine)看过演出后,对欧文“无与伦比”的舞台设计感触颇深,尤其是舞台灯光,自愧“法国还没有这样的设想”。(Hughes:89)欧文对考古真实风格的热衷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但和将考古真实性奉若圭臬的凯恩有所不同,除了真实,欧文更加注重舞台的艺术美感。他说:“任何人排演剧作的首要职责都是生成美的、愉悦人心的效果。”(Finkel:83)从其任兰沁剧院(the Lyceum Theatre)经理期间(1878—1902)排演剧作的具体实践可以看出,欧文致力于在真实与美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他执导的莎翁名剧《亨利八世》即为此中典型。在这出剧作的排演中,与欧文合作的两位舞台设计师均为英国皇家艺术院的著名画家。布景师劳伦斯·阿尔玛-泰德玛爵士以考古式布景设计著称于世,他为该戏设计的布景严格仿制罗马帝国时期;服装设计师翰·西摩·卢卡斯则擅长表现传统英式服装,忠实于历史原貌而又富于美感。两位设计师娴熟驾驭舞台表现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亨利八世》的巨大成功。舞台上的场景使人身临其境,服装更是美奂美仑,再加上欧文搭配灯光、颜色、演员姿态等各个要素的高超水准,其综合效果正如《每日邮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评论所言:这一切“使得一个有才干的经理[在舞台上]美上加美,让剧院贴近自然的程度达到了人能想象的极限”。(Finkel:89)虽然欧文在创造舞台真实之美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但当真实与美发生冲突时,欧文倾向于后者。他曾声称,“考古学必须让位于美感。”(Booth,1981:98)欧文的“美感”更多来自于“图画之美”,他习惯于将舞台比作画布,创作的灵感也因此常常源于绘画作品的构图技巧和颜色搭配,他曾形象地说过:“每一个布景就如同画作之于画家,必须将各种颜色和人物组合融为一体,并且安排好衬托背景。”(Finkel:98)与凯恩的“舞台似画”风格相比,欧文更进一步,他的舞台不是对某幅画作的单纯模仿,而是本身就是一幅画,所包含的各个要素也是根据绘画作品的尺度进行架构。考古展示舞台发展至亨利·欧文时期,历史真实不再是一个衡量的单一标准,而是降至为一种舞台表现技巧。在欧文看来,戏剧舞台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体,如画般和谐完美才是最重要的。亨利·欧文的艺术观点和剧场实践都暗示着一个势将到来的发展趋势:“考古真实性”舞台在19世纪后期已经开始走向衰落。
二、“考古真实性”舞台的“景观化”
综观英国戏剧演出史,“考古真实性”舞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构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从上文的例证中可以看出,这一舞台风格与当时复兴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紧密相联。⑤批评家沃森认为,19世纪的莎剧演出不以当时的社会品味作为衡量准绳,而有意追随剧本原作。(Worthen:32)本文则试图说明,以考古细察为基础的历史真实性舞台是以具体形象取代戏剧文本,而对于景观化视觉形象(the spectacularization of visual image)的追求恰恰是维多利亚新兴消费社会生成的一种体验艺术与生活的模式。
这是一个颇具悖论色彩的现象:在排演莎剧的过程中,设计师们一方面严格求证于考古史料,另一方面却毫无顾忌地大肆修改莎剧原作中的文字。很多时候,许多幕被整体删除,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新的场景又被添加进来。《文学公报》(The Literary Gazette)就曾评论查尔斯·凯恩《冬天的故事》的演出是让“一系列惊人的戏剧舞台场面排列在莎士比亚原作之上”。(Schoch:99)而在《亨利五世》中,凯恩添加了亨利五世凯旋归来进入伦敦城的情景,这一场景在莎士比亚原作中并不存在。由此可见,“考古真实性”舞台的设计初衷与戏剧原作并无多大关联,正如麦克里迪(William Charles Macready)⑥所言:“场景设置不是文本的说明,被言说的文本倒更像是舞台展示的连续评述。”(Booth,1981:52)那么,剧场艺术家们又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实现富有考古真实色彩的舞台布景呢?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考古展示舞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历史宏大场面的真实再现。舞台画面带有明显的选择性,设计师们只选取那些有助于制造华丽壮观效果的历史画面。无论是凯恩的一系列“伦敦街景”,还是欧文的几百套服装展示,都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它们是在对现实经过放大夸张处理之后制造出的历史景观。在《亨利五世》中,凯恩添加亨利五世凯旋归来进入伦敦城一幕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这一幕中,共有135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如此盛况空前的群众场面,与其说是出于剧情的需要,不如说是凯恩在展示19世纪剧场所具有的巨大舞台包容力。针对这一现象,布斯使用了“景观剧场”这一概念。在其专著《维多利亚时期的景观剧场:1850—1910》中,布斯指出,维多利亚人对“景观效应”(the spectacular effect)即舞台上绚烂的灯光效果、迷幻的颜色混合以及历史宏大场面的热切追逐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Booth,1981:160)在景观剧场里,服装和布景第一次成为舞台的主角,而演员不过是表现这两个要素的有形载体而已。舞台上的历史景观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形象展示本身,为观众提供的是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单纯的形象展示往往浮于表面,缺乏真实感,考古细察则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众所周知,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实地考察获得“物证”(the testimony of things)。(Greene:xii)剧场艺术家们将这一方法应用于舞台设计上,他们不仅在搜寻“物证”的过程中获得了“真实”的体验,并且将这种体验通过舞台形象传递给观众。面对舞台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画面,观众们一次次难以遏制的惊呼认可了景观形象与考古学相结合所创造的真实幻觉。
事实上,维多利亚人对这种景观化的形象展示并不陌生。19世纪中期以来,伦敦逐渐成为“丰裕社会的中心,在那里人们享受着炫耀性消费”。(Lee:450)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从1851年开始举办的世博会展览。水晶宫内琳琅满目的展品除了让伦敦市民大开眼界之外,还在更深层次上达到了规约的效果。人们开始习惯于用眼睛去直接“消费”所视之物,景观(spectacle)作为一种新的规模化的商品象征体系开始形成。研究19世纪英国商品文化的社会学者托马斯·理查兹(Thomas Richards)指出,“如果说短时期内世博会展览带来了商品的膜拜,那是因为它成功地综合并改进了象征机器制成品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景观。”(Richards:54)从世博会展览开始的视觉景观热潮迅速在维多利亚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报纸上大幅的人物形象广告、各种各样的图画期刊、制作精美的维多利亚女皇头像饰品,以及新兴百货商店别具一格的橱窗布置——所有这些都在讲述着整个社会对于“景观化”形象展示的普遍奢好。
作为当时大众娱乐业的核心场所,剧场对这一需求的呼应体现在服装和布景的重要性上。亨利·欧文曾感叹道:“布景和服装所附带的价值已经不再是可以凭主观意见判断的问题,而已成为必需。它们受公众品味的支配,并非仅仅源于剧院经理进行场景展示的愿望。”(Finkel:88)与水晶宫内精心安排的展品一样,舞台上的一切要素都是从展示本身的景观化效果出发。⑦场景设计的负荷不断膨胀,设计师们极尽雕琢之能事,利用考古学的方法放大了舞台上任何一个可以表现真实效果的细节。追求“历史真实”的舞台终以“舞台似画”的景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场景道具的安排都可以直接与博物馆中被参考的巨幅历史画或人物肖像画对应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舞台上的历史景观甚至可以被称作是装饰艺术的完美典范,它具有人工制造的商品特性,是商品景观化在剧场中的变形。观众们购票进入剧场,不再单纯为了欣赏舞台艺术,更希望见到为视觉表象的炫示所垄断的戏剧演出。正如布斯所言,“炫耀性展示以其自身的魅力成为吸引票房收入的真正来源。”(Booth,1981:27)在景观娱乐的美妙体验中,一类新的戏剧欣赏群体逐渐形成。他们在有限的休闲时光里沉浸在各种舞台技术手段所创造的形象幻觉之中,享受着单纯的视觉感官上的刺激。
三、“行动中的消费主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见出,景观展示是独立于戏剧舞台的一种社会化力量,那么,又该如何评价剧场艺术家们对考古勘察近乎偏执的喜好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细节的过分关注呢?他们对各种历史文献所进行的孜孜以求的考察行为与舞台上的形象展示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呢?本文将进一步指出,考古勘察过程本身创造了“考古真实性”舞台赖以存在的客观依据,而基于纯粹行动之上的主体意识恰恰说明了消费社会中历史真实体验的缺失。
“历史真实”(historical authenticity)概念是19世纪各学科领域研究的核心观念,这一在知识史上得到充分确立的事实在此毋需赘述。⑧“考古真实性”舞台正是在这一观念影响下于剧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趋向中出现的一种舞台演出风格。但值得注意的是,体现在考古展示中的历史真实,借用戴尔的说法,“不在于其对[以往]经验的充分阐释,而在于它是通向这一阐释的最为可能的路径。”(Dale:4)换言之,对于剧场艺术家们来说,考古展示不仅是获取准确历史知识的手段,它更是架构当下现实存在的最重要原则。可举一例证之。亨利·欧文排演《麦克白》时,曾有评论者询问欧文,服装和道具上的历史准确性如何与语言的事实达成一致:一个11世纪的麦克白说着17世纪的无韵诗?——即穿着11世纪风格服装的麦克白说着莎士比亚在17世纪初创作的无韵体戏剧独白。欧文和他的设计师们对这样明显的年代混乱不置可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热衷于考古展示舞台的创造。(Booth,1981:43)在这些剧场艺术家们眼中,“考古真实性”舞台的“真实”之处并不与具体的历史内容直接相关。尽管他们的舞台设计是建立在严格的“物证”基础之上,但和考古学者考证历史的出发点不同,剧场艺术家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将对某一历史情境的抽象理解转变成具体可见的舞台形象,并使这些形象具有真实的效果。对于那些已经厌倦依靠自己想象力参与戏剧情节、痴迷于景观展示的维多利亚公众来说,舞台上的一切细节都必须一览无遗地表现出来,一切因素都要直接针对眼睛而不是激发内心的情感。1855年,戏剧监察官唐讷(W.B.Donne)撰文写道:
就剧场的所有方面而言,我们这一代富于教养却冷漠而无个性。若要打动我们,无须符合想象中的真实,只要物质上的逼真。祖先们用心灵领悟到的景象如今必须以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必须是视觉上可触知的,感受上亦如此。(Booth,1981:2)
面对缺乏想象力的观众,景观展示必须在视觉欣赏的瞬间代理完成真实体验的参与——这正是景观剧场“细节阐释”(an interpretation in detail)所遵循的潜在规则。舞台上无所不在的、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景观场面除了提供视觉的愉悦之外,还为“真实”设定了评价的标准。设计师们按着这个标准从历史连续体中剥离出一个个具体的片段,然后针对这些片段的所有细节展开考古式的“搜寻”。他们将“历史真实”的体验与信仰置于对博物馆、艺术画廊的不知疲倦的考察中,置于数不尽的舞台构图草稿中,置于历史图画的重复复制中。换言之,考古勘察式的反复“搜寻”行为本身成了生成“真实性”的唯一来源,这也解释了为何剧院经理们总是要在演出海报和广告中详细陈述考古勘察的过程——脱离了具体的研究对象,考古实践本身成为舞台剧作炫耀其“真实”面向的依据。就如司考慈(Richard w.Schoch)所作出的概念化阐释那样,维多利亚剧场的考古追求是一种“行动中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 in action)。(Schoch:8)
司考慈形象地概括了剧场的考古实践本身,但并未阐明暗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根由。事实上,以行动本身作为“真实性”的基准恰恰说明了剧场艺术家们的考古行为并不指向任何历史性真实,正如奥斯卡·G·布罗凯特和罗伯特·R·范德雷所言:“添加讲求历史准确的服装、逼真的音响效果以及精致的背景并不能使[剧作]充满现实感,它们只不过是一部非现实主义剧作的幻象性的装饰而已。”(Brockett and Findlay:13)舞台上的景观因此成为波德里亚所称的“超现实”的存在,它自我指涉,不依赖于任何来源,是一系列幻象的集合体,而幻象之下空无一物是其唯一的真实之维。此外,仍值得一提的是,剧场艺术家们并不是单纯地信奉行动,他们的“行动中的历史主义”是和考古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他们的行动依赖于新兴科学方法,并且乐此不疲,这体现在舞台设计的很多方面。⑨梳理这一内在联系,对理解风靡维多利亚剧场的考古研究同样至关重要。法国20世纪后半期杰出的文化理论家居伊·德波在其影响深远的论著《景观的社会》中明确指出,“认为可以通过当前的科学知识掌握历史,这一观念无法剔除其本身的资产者特性。”(Debord:53)即是说,正是这种对新技术的顶礼膜拜体现了消费社会中量化手段的无所不能以及信仰者典型的商业化思维模式。很明显,舞台上以考古细察为前提创造的历史景观在迎合观众喜好的同时,也给其制造者们带来了极大的快感。他们不厌其烦地处理各种琐碎细节,正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新兴的考古手段,自己比任何人都更直接、更具体地体验了所谓的“历史真实”。然而,也正是对这种体验的认同显现出瓦尔特·本雅明所言的“自我异化”(self-alienation)的征兆。在本雅明那里,机器复制时代下的现代人将“自我毁灭看作是最高级的审美享受”,(Benjamin:242)而在景观剧场中,演员和经理都以自我欺骗的方式实现对艺术成就的追求。考古勘查为戏剧排演的真实经历提供的只是幻象性的“客观”支持,它驱使设计师们远离戏剧想象的园地,疯狂地追寻各种可能表现“真实”的细节和表面化的效果,其直接的结果不过是物质建构下的历史幻象,掩盖的则是艺术心灵的迷狂。正如波德莱尔形容的那样:“艺术家越是不偏不倚地注重细节,混乱状态就越发严重。”(波德莱尔:488—89)
维多利亚后期的一位名叫约翰·赖德(John Ryder)的演员曾向当时有名的女演员艾伦·特里抱怨他的剧场经理:“你以为他雇佣我是因为我有演员的潜力吗?完全不是!他雇佣我是因为我有着符合考古展示的身材(an archaeological figure)。”(Taylor:25)赖德的抱怨不无道理,但他无从知晓,责任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剧场经理。在景观形象统治的舞台上,无论设计师还是演员都已经抽象化为一种媒介。通过他们,一个个历史场景片段从戏剧文本的故纸堆中蜂拥而至,将自己直接展露于公众的凝视之下,成为视觉消费的对象。历史就这样未经心灵的想象参与,迫不及待地走入人们的视野,“从一个奢侈的罕见之物转变成了大众消费品”。(Debord:105)在景观包围的世界里,人们不再“真实地”经历历史,“考古真实性”舞台所显现的实际上是真实体验的缺失,是现实感的不可能性。正如詹明信所言,这个时代最终“在对过去时代的丰富形象的痴迷催眠中记录下其自身历史感的缺乏”。(Jameson:296)
在发表于2001年6月的《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的一篇文章中,史蒂夫·狄龙(Steve Dillon)指出,包括米歇尔·福柯和乔纳森·克莱里(Jonathan Crary)在内的研究19世纪视觉文化的学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德法两国。(Dillon:86—87)近年来,随着《英国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 in Britain)杂志的出版,人们逐渐对19世纪英国视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兴趣。但是,鲜有论者将这一时期的剧场与视觉文化相互引证。在本文的研究思路中,“考古真实性”舞台不仅是作为一类视觉艺术的表现手法,更代表着某种“视觉性的呈现”。(罗岗、顾铮:13)它以形象揭示意义,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复杂的彼此交织的世界。在这里,剧场艺术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结构性特征,它们共同指向存在于维多利亚社会中的视觉景观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古真实性”舞台是一个充满悖论性的能指:在其虚假幻想的支配下,剧场艺术家们将消费社会的景观自律机制看作是自我对行动的主观选择。这一选择因而体现的不是人的主动性而是一种充分物化了的世界观,是商品价值体系侵入个体无意识领域的佐证。在视觉景观的无深度的“震惊体验”之下,人的本真的、感性的生命体验已经被排除在外。考古展示曾经为英国戏剧舞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但其辉煌——借用托马斯·卡莱尔在其他场合使用的一句评语——“既无生命又不真实,不似自然界夏日多彩柔和的光辉,而是像抛光的金属一般,是一种冷辉煌。”(Carlyle:452)
注释:
①主要包括:Kerry Powell,Women and Victorian Theatre(Cambridge:Cambridge UP,1997).Gail Marshall,Actress on the Victorian Stage(Cambridge:Cambridge UP,1998).Edward Ziter,The Orient on the Victorian Stage(Cambridge:Cambridge UP,2003).Kerry Powel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ctorian and Edwrdian Theatre(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Lynn M Voskuil,Acting Naturally:Victorian Theatricality and Authenticity(Charlottesville;London:U of Virginia P,2004).
②主要包括:Michael R.Booth,Victorian Spectacular Theatre 1850—1910(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Alan Hughes,Henry Irving,Shakespearean (Cambridge:Cambridge UP,1981).Richard W.Schoch,Shakespeare's Victorian Stage:Performing History in the Theatre of Charles Kean (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P 1998)
③“考古真实性”舞台最早出现在德国剧场,在19世纪的法国剧场也有着广泛的应用。1801年席勒在宫廷剧院上演自己的名作《奥尔良的姑娘》,该剧的服装以精确细致的历史准确性闻名,为“考古真实性”舞台技巧的首次亮相。
④演员—经理体系是19世纪英国剧场的主导管理体制,剧院中的明星演员既是戏剧演出的核心人物又是剧场经营管理的负责人。
⑤参见R.Foulles,ed.,Shakespeare and the Victorian Stage(Cambridge:Cambridge UP,1986).W.B.
Worthen,Shakespeare and the Authority of Perform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P,1997).Gail Marshall and Adrian Poole,eds.,Victorian Shakespeare.2 vols (Hampshir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
⑥威廉·查尔斯·麦克里迪:英国19世纪中期考文特花园剧院和特鲁里雷恩剧院著名经理,一些学者称其为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导演。
⑦值得一提的是,凯恩的公主剧院和水晶宫位于同一街区,水晶宫展览的风靡也带动了公主剧院演出收入的增加。
⑧参见Peter Allan Dale,The Victorian Critic and the Idea of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P,1977).V.F Storr,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he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Longmans,1913).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Longmans,1952).
⑨例如舞台上频繁使用的全景画就和当时照相技术的发明有关,而照明设备的不断更新,从煤气灯、钙光灯到炭质灯,以及后来的白炽灯,都源于灯具的改进发明。
标签:戏剧论文; 维多利亚时代论文; 剧场论文; 艺术论文; 考古论文; 服装风格论文; 文化论文; 麦克白论文; 演出服装论文; 亨利八世论文; 欧文论文; 剧院论文; 舞台设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