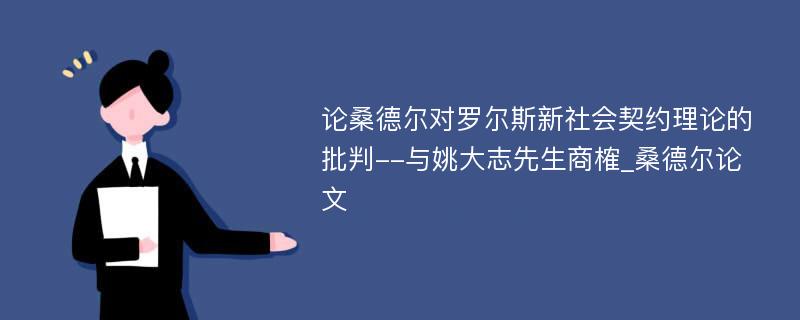
论桑德尔对罗尔斯新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兼与姚大志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约论文,德尔论文,新社会论文,罗尔斯论文,姚大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罗尔斯在当代复兴社会契约论模式以来,赞美、模仿、发扬光大者有之,由疑惑不满而发为批判者亦有之。除了自由主义内部阵营的批评外,在社群主义对新契约论的批判中,桑德尔的论述以系统全面、逻辑清晰、直逼主题而独树一帜。姚大志先生在2001年夏中美学者伦理讨论会上所提交的文章中,已经提到桑德尔批评罗尔斯契约论中蕴含着自由与互惠的矛盾。姚大志先生反驳桑德尔,认为可以通过把自由排在互惠前面的“优先性”排序来解开这一矛盾,因为“自由”当然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我们也认为社群主义对于新契约论的正当性的批评有失偏颇,但是我们同时觉得“自由”高于“互惠”的优先性排序的办法并不能反映罗尔斯新契约论的特点。
一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也就是他设计的“原初状态”,其特点是资源的中等程度匮乏使人们之间的合作成为必要;合作者对彼此的利益促进不感兴趣;订约各方都处于“无知之幕”之后,也就是“首先,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阶级出身,也不知道他的天生资质和自然能力的程度,不知道他的理智和力量等情形。其次,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特殊性,甚至不知道他的心理特征”[1](p.131)。总之,凡是影响选择的公平的一切信息都不知道。这样,原初状态的各方就一定会选择侧重平等的“正义原则”,即要求社会按照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构建。
不难看出,社会契约是一定的“我们”通过共识订约而形成新的“我们”。桑德尔层层剥笋,一一敲打和瓦解罗尔斯契约论中的这些观念。大致说来,可以把桑德尔的批评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点是从对订立契约主体的质疑得出原初状态中根本不会发生订立契约的活动。桑德尔认为:“原初状态中达成的任何契约之所以公正,不是因为程序保证任何结果公正,而是因为情境只保证一种特殊的结果……原初状态中的人的行动毫无自愿可言,处境的设计使他们没有可能选择任何其他的原则。”换句话讲,在订约前不存在真正分立的当事人。在“无知之幕”下,只存在一些未分化的(undifferentiated)当事人,他们是被同一地设定的(identically situated)。从逻辑上讲,原初状态中的人只有一个。所达成的任何契约都不可能是不同个人之间相互达成的契约。这里至多只有“一个隐喻意义上的协议,那是我与我自己所达成的协议”[2](p.127)。
桑德尔区分了“契约”的两种不同意义,第一种指的是就一个命题主张达成一致,第二种意义是指同意一个命题主张。前者是一种“共同选择”,要求多个人,这是典型的契约,它涉及到形成一种意图。桑德尔把它称为唯意志论意义上的契约。后者不涉及意志行为。同意一个命题就等于承认它的有效性,既不要求其他人的介入,也不要求依该命题的有效性作一种选择[2](p.129)。桑德尔称之为认知意义上的契约,并认为罗尔斯的“契约”就是最初的唯意志论意义上的契约让位给了认知意义上的契约。
桑德尔批评的第二个方面是从契约论引发开去,深挖罗尔斯自由主义自我观和社会观的错误。他指出罗尔斯预设的自我独立于它所拥有的价值观,它已经先行个体化了,这使它成为一个不受影响的性质不变的个体。这个自我实际上毫无内容,从而根本不可能产生相互情感和共识,更谈不上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排除了所有善或恶的概念;排除了任何能够超越我们的价值观以保证我们的同一性构成的可能性;排除了一种公众生活的可能性;排除了共同目标能够或多或少激励自我理解的可能性。”[2](p.62)与此相反,社群主义认为“我们”或社团不能被仅仅描述成一种情感形式,或可以供人自由追求的附加成分;社团本身就是构成自我本质的一种自我理解和认同的方式:“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的核心抱负及其伴随的特征所构成的,我们作为主体,总是根据我们的自我理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和成长。只要我们的构成性自我理解包含着比单纯的个体更广泛的主体,无论是家庭、种族、城市、阶级、国家、民族,那么,这种自我理解就规定了一种构成性意义上的共同体。”[2](p.172)
实际上,罗尔斯为了提出他的实质性的主张(差别原则),不得不依赖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观念。桑德尔从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判思路中找出了这一条线索。诺齐克反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认为它实际上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资产,一种共享的分配的利益。在诺齐克看来,这就是不尊重人之为目的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对此罗尔斯的回应是:“不是通过声称,是我的资产而不是作为我的那个人被用作了其他人的目的的手段,而是通过反问,在何种意义上,那些分享着‘我的’资产的人才能恰当地被描述为‘其他人’。”[2](p.79)可以看出,为了反驳诺齐克的论证,罗尔斯只能放弃他自己提出来的自我观念,设定某种共同体的存在。桑德尔说,这种辩解“把共同资产观念与一个同占有主体的存在可能性联在起了”,从而求助于“一个关于自我的主体间观念”(intersubjective conception of self)[2](p.80)。也就是说,占有主体是一个“我们”而不是“我”。
二
我们认为,桑德尔的批评虽然很犀利,很聪明,但是并不成功,它反映的毋宁说是社群主义在政治上的天真,以及契约论的思想的深刻。
首先,社群主义立足于和谐一致的构成性的“我们”。但是,纵观历史,什么时候存在过这种一体化的“我们”?不错,人们必须构成一定的联合体,才能够超出自然界的局限,但是联合体中的冲突与斗争从来也无法避免。因此,契约论才是构成“我们”的可取模式。罗尔斯之所以提出契约论,正是试图把握利益一致与利益冲突之间的平衡。罗尔斯看到:“虽然一个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1](p.2)
马克思也强调人是社会的动物,但是他也看到历史上普遍存在利益的冲突,它主要表现为两大阶级的对抗。只有消除阶级对立、消除人类社会的一切对立与压迫,才能使利益的冲突最后被利益一致所取代。当代不少学者也很关注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层面的诸多冲突。像美国的基督教伦理学教授阿伦(Joseph L.Allen)在《爱和冲突》一书谈到,我们生活在诸多道德要求中,处在义务的复杂网络中,问题是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因此冲突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3](p.82)。他还提到,近二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西方人大多认为利益冲突的克服与和谐的取得是容易的,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作为20世纪认真对待冲突现象的神学家之一,他却认为“不管在小范围的人际关系中,还是在民族、国家等其他大团体中,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2](p.88)。尼布尔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人的自私,由于人的罪性骄傲及其对我们局限的否定,人不可避免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其他人。
罗尔斯不企求彻底消灭利益冲突以建立理想一体化的“我们”,而是寻求利益一致与利益冲突之间的张力平衡。“无知之幕”社会契约得出的“平等”的正义原则——又具体化为政治平等和经济补偿——就是使冲突的社会利益达到一定的和谐。这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罗尔斯的契约论属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在整个社会的水平上不讲目的论,不诉诸某一种完备性学说,从西方传统说,也就是不援引基督教作为自己的合法性根据。这种契约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水平契约,而非传统的神与人的垂直契约。它的出发点是个体,而不是整体或圣约所订立的整体(“选民”)。但是灵性的丰盛也必须以长治久安的民主自由社会为基础。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意义就在于保障这样的社会的建立。正如多伦多大学的诺维克在研究犹太人的政治理论时所指出的:“在我们这个脆弱的历史转折时期,犹太人应该认识到,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甚至在宗教上,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我们才能存在下去,更不必说获得繁荣。”[4](p.28)社会公共生活的层面非常复杂,利益纵横交错,要建立共识的正义社会,首先要使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变得简洁可行。
桑德尔反映的是美国共和主义传统,这是清教之约。对于清教徒,约是内在之约。上帝与整个选民团体立约,这样的团体因此是先于个体的“我们”,是可以进行统一的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的。用贝拉的话说:
在当时新英格兰的政治思想中,对社会的、社团的或集体性的因素十分强调。这种强调集体,把人理解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思想,来自旧约中上帝与对自己的行为集体负责的人民之间订约的观念,来自新约的建立在爱之上并在同一个共同体中的兄弟之情谊和同胞之感中表达出的共同体观念[5](p.17)。
但是,美国殖民时代后期,风气骤转,现代性的个体、宽容、多元的精神从欧洲传入美国。在一个主体已经觉醒的时代里,在一个对于不同的终极价值——完备性学说——必须宽容而不能强求统一的时代里,如果不愿意陷入相对主义或强者为王的境地,“社会契约”模式不失为建构道德基础的一种方式。
三
另一方面,罗尔斯与其他自由主义者不相同的是他同时强调个体与他人、社会团体的密切关系。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既反对整体型功利主义的大有机体、非契约论式的“我们”,也反对个体功利主义的交易式契约的相互利用式、临时协定式的“我们”。在《政治自由主义》里,罗尔斯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己的任务是“在被看作是自由而平等的、并在整个生活中世世代代都能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之间,具体规定其社会合作之公平项目的最适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6](p.3)罗尔斯认为民主社会的这一正义观念一定不会只是工具性的,而是要服从道德的原则。一般认为最大最小值之避灾心理是在无知之幕后订立契约的人们的主要心理,而在我们看来,无知之幕的视角是道德的视角。不错,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确实讲过依靠“最大最小值”的理性(rationality)订立契约,但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指出是“公正”的理性或合情合理性(reasonableness)在契约制定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6](P.35)。
关于罗尔斯这种超出私利者之上的、以互惠式公正为原则所构造的“我们”的讨论,把我们导向契约论中“自由”与“互惠”的关系以及我们和姚大志先生在这一点上的分歧。
桑德尔指出,当人们达成一种契约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估它的公正性。其一,可以探讨他们达成契约的条件,双方是自由地还是强迫地达成此契约的。其二,可以考察该契约的具体条款,看双方是否公平地获得各自的份额。如果一种契约实现了第一种观点,或者说实现了自律的理想,它就接近于纯粹程序正义。而按照第二种观点,契约属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它试图接近一个独立存在的正义标准。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同意本身就意味着契约条款是公正的,但在实践中并非全是如此,因为契约即使是在同意情况下签订的,一方也可能是被强迫签订契约,或者在讨价还价时处于不利地位,或者被欺骗,抑或不清楚正在交换的东西的价值,或者不清楚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所在。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契约论中蕴含着两种正当标准——自主订立与平等互惠——之间矛盾的可能性。姚大志先生指出,可以通过设定“自由先于互惠”来避免这一矛盾。他说:
即使当契约论的自律性与互惠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罗尔斯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之间规定了优先性一样,我们也应该在契约论的两个道德理想之间规定一种优先性,即自律性优先于互惠性。也就是说,一份契约首先应该满足它的自愿要求,然后才能够满足它的功利要求。契约论最重要的道德基础是它的自愿性质。如果契约是我们自愿达成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履行这份契约,无论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对于契约论来说,自律性是至高无上的,它体现了契约精神的本质。没有自律的观念,没有自愿性和选择性的观念,也就没有契约论。而互惠性必须服从自律性,它是对自律性的补充[7](pp.41-42)。
我们认为,姚大志先生的看法很有启发意义,但是可能不会为罗尔斯所接受。罗尔斯自称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确实看重自由。但是也正因为此,在保障方式上它并不一定讲自由或积极自由。程序不过是设计出来保证自由的,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用来“表达”自由主义的那些基本信念——平等、自由人的合作等等的。所以,原则上我们可以设想罗尔斯不取“社会契约论”的程序,而采取由专家代为计算,然后,再由各种完备性学说各自独立地去“交叉共识”它。桑德尔和哈贝马斯式的共和主义坚持程序是本质性的,人们的商谈—民主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罗尔斯会认为,共和主义主张的那种“只讲程序(商谈),结果开放”的思路事实上潜伏着危险:凭什么可以“先验地”保证大众民主在集体商谈中不会得出侵犯自由、平等等限度的结果?而根据“商谈伦理学”,只要这样的结果是经过充分的、无压抑的商谈后得出的,就是合法的。当然,共和主义可以指责罗尔斯的思想为“精英”倾向或“反民主”,近于哲学王思想。哈贝马斯确实对罗尔斯提出了这样的批判。他认为罗尔斯这么做危害了“自主”(自律)。(注:参见:Habermas.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 Remarks on JohnRawls's Politicai Liberalism[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XCII,Number 3,March 1995,p.129.)
然而,罗尔斯并不让步。契约论的主要因素是自愿和兼顾。罗尔斯使用“社会契约论”看重的与其说是自愿不如说是兼顾,“契约一词暗示着这种个人或团体的复数,暗示必须按照所有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原则来划分利益才算恰当”[1](p.14)。为了“兼顾”这一面,罗尔斯有时不惜牺牲一般人看来更应该是契约的本质特征的“自愿选择”要素。罗尔斯讲,“好”是允许多种多样,允许每个人随时自由选择,“正当”或社会政治的基本结构只能一义,必须要在生活的入口处一次性地先确定下来。罗尔斯的“幕后之约”并不存在契约谈判中的讨价还价,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在为所有的人作选择。一个人——只要他进入了理想的道德境界或“公共理性”的境界——的选择,就是在为所有人立法。这也是自由或自主,但它是康德式的自由,而不是一般讲“合同”的意思自治时的那种自由。“根据公平正义的观点,不能说每个人的良心判断都应当绝对地受到尊重”[1](p.505),并非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决断,就是道德的。真正重要的不是意志,而是“公平性”即立约时环境结构有利于各方——是“恰当地规定的”最初状态[1](p.116)。正因为如此,可以设想是专家通过“合理的慎思”先验地为人民所计算好的“共识—真理”。罗尔斯后来强调“少数专家”或公共理性的最佳代表者是最高法院,它中立无立场,能够防范大众民主之弊端[6](p.244)。桑德尔其实看到了罗尔斯的契约论这一本质特点,他说:
原初状态的秘密——以及正当合理性证明力量的关键,不在于人们在那里做什么,而在于人们在那里理解了什么。关键不是他们选择了,而是他们看到了什么;不是他们决定了什么,而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在原初状态中所发生的首先不是一个契约,而是逐渐自我意识到一种交互主体的存在[2](p.132)。
所以,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并不是市场型的契约,它的基础不在自由意志,而在于先于、高于个体意志的某种共同存在(交互性)。罗尔斯与社群主义并非看上去的那么对立,实际上,一个讲“反思的平衡”的罗尔斯与社群主义在本体论与人论上有不少暗中契合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