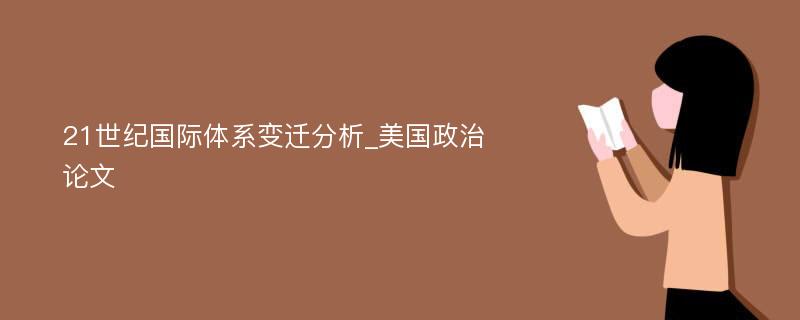
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4月2日,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及主要新兴国家在内的20国集团(G20)会议在伦敦开锣。会议的首要议题是如何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但它更深层的国际政治内涵则在于拉开了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的帷幕。21世纪国际体系将向什么方向、以什么方式转型?新的国际体系将表现出什么样的形态、特点?这已不仅是学者们探讨的学术问题,更是政治家们议事日程中的现实议题。本文将在探讨国际体系转型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探索国际体系转型的一般规律与启示,并就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式与方向及其内涵发表管窥之见。
一
国际体系(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r system of states,interstate system)是一个界限相对宽泛的概念,与之内涵相近的概念很多,如“国际社会、国际系统、世界、世界系统、地球、地球社会,等等”①。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国际体系概念取其广义。如没有特例,本文中的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the World System)、国际结构(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全球政治体系(the Global Political System)等概念,甚至与国际社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国际政治(the World Politics)等概念不作严格区分。
按照日本研究国际体系的学者田中明彦的观点,国际体系(世界系统)似可定义为“存在于地球上的社会系统中、自身不带上位社会系统的最上位系统”②。詹姆斯·多尔蒂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则把国际体系定义为“既是国家构成的系统(System),也是国家组成的社会(Society)”③。如参考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定义,国际体系则可作如下延展性理解:第一,它是一个“社会体系”,“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第二,它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而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根据该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不同时期该体系结构的强弱;第三,它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结合在一起,而当其内部各种力量不断试图把它改造得对己有利时,又会造成体系分裂。④本文论及的国际体系转型,则指近代以来,作为有机体的国际体系从一个所谓“生命期”向另一个所谓“生命期”的转变。
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转型大体起始于公元16世纪前后(沃勒斯坦选定的时间点是公元1492年;《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一书中则笼而统之地提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大约于5个世纪以前才开始”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体完成,历时约4个世纪。第一次转型的基本内容表现为国际体系由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化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
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还处在各大洲、各大区域分散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能囊括全球的国际体系。如按沃勒斯坦的观点,当时仅欧亚大陆就至少有五大区域型体系,除了欧洲-地中海体系外,还有“印度洋-红海混合区”、波罗的海地区、“从蒙古到俄国的大片陆地”以及实行“朝贡体制”的“中华帝国”。除此之外,南北美洲还有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非洲还有一些小的体系。⑥也就是说,1500年前后,按某种方式划分,世界上大约有七八个区域型国际体系,这些区域型体系或相互间相对独立(如欧亚大陆的几个区域型体系之间)、或者相互间绝对隔离(如南北美的区域型体系与欧亚各区域型体系之间),其相互关系更类似于田中明彦创立的一个概念,即所谓相互间并列的“针叶林”状态。
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契机,海洋真正成为人类活动的大舞台和大通道,东、西半球相对隔绝发展的格局以及“旧大陆”各区域之间孤立、平行发展的格局被打破,“人类社会由区域文明向全球文明过渡,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⑦在此过程中,分散、孤立发展的区域型国际体系开始朝整体发展的全球型国际体系转型。这一转型过程起步阶段较慢,但随着航海技术以及以枪炮舰船改进为主的军事革命的推进而不断加快,到19世纪达于高潮。在此期间,先是南北美洲、而后是欧亚大陆的其他几个“区域型体系”以及非洲相继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所谓“近代世界体系”。⑧
最能显示全球型国际体系到19世纪末基本形成的指标莫过于欧洲人对世界陆地的控制程度。根据保罗·肯尼迪的统计,“1800年,欧洲人控制了世界陆地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1914年超过了84%”。⑨另一个有意义的指标是到19世纪末,作为完整统一、囊括全球的国际体系经济基础的、统一的“世界经济体”大体形成,这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除囊括被沃勒斯坦称为“中心区”的欧美以外,还囊括被称为“边缘区”或“半边缘区”的广大亚、非、拉地区。⑩
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第二次转型大体以1900年前后为起点,到2000年前后,亦即大体以所谓“后冷战时期”(Post-cold war)的终结、“后后冷战时期”(Post-post-cold war)的启动为终点,历时约一个世纪。这次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内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型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型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在国际体系第二次转型的大约百年期间,世界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如果沃勒斯坦有关两次世界大战是同一次战争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观点(11)有其合理性,那么,从大历史观看,把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视为同一次战争,即美国为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而进行的百年斗争的三个不同阶段,也有很强的解释力。经过这三阶段跨越百年时空的激烈争斗,美国相继替代主导原有国际体系的英国、战胜与美争夺新国际体系主导权的德国和前苏联,最终成为20世纪国际体系的主导者。
二
综合近代以来历时约500年的两次国际体系转型过程,可以归纳出不少有助于我们观察未来国际体系转型趋势与前景的启示性结论。
第一,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渐变、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转型结局通常寓于转型过程之中,转型过程之动态时段不但比转型结局达成后的相对稳定时段更长,而且在全部历史进程中也许更重要。第一次国际体系转型耗时约400年,其中转型过程占据了300多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都不过是欧洲体系而非全球体系,拿破仑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全球体系的最后形成以及英国全球主导权的最终实现。真正的全球体系形成和英国全球主导权的确立是在19世纪中后期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威尔士大学卡尔教授(E.H.Carr)在《回归霸权:美国与国际秩序》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从1815-1855年,英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欧洲领导者的角色”,这一时期因而是英国的“半霸权”时代。随后20年,即1855-1875年,英国经济实力达于顶峰,“其对欧洲的影响力及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力也达到了英国历史(1688-1945)的顶峰”。(12)如果需要一个历史里程碑的话,历史学家可能会把这个标志英国全球主导权确立的历史里程碑划在1858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及其被英国殖民军残酷镇压。总起来看,英国在第一次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斗争了3个多世纪,最后享用全球主导权不到半个世纪。到19世纪末,随着美国和德国的崛起,其主导权就受到挑战,国际体系开始向下一个“生命期”过渡。1897年阿诺德·汤因比在伦敦舰队街观看维多利亚女王60周年大典的盛况,其实是英国对全球型国际体系主导权的“历史终结”。(13)第二次国际体系转型历时百年,其中转型过程占据了大约90年。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英国向美国“禅让”国际体系主导权并不意味着国际体系第二次转型的完成,因为继之而来的是美苏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展开了新的角逐。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才确立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真正实现了对英国主导权的替代。然而,美国对全球主导权的“享用期”为时不过10年左右,比英国“享用”全球主导权的时间短得多。此后不久,亦即大体上以新世纪开局为起点(尤其是以“9·11”事件为起点),国际体系就进入了新的“生命期”,开始了第三次转型。(14)
第二,已经发生的两次国际体系转型在转型性质方面连续性大于非连续性。尽管美国替代英国成为20世纪国际体系的主导国,从而促成了国际体系第二次转型,但是,美国是主要由欧洲移民建立的新国家,甚至被认为是欧洲的“女儿国”,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与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虽有所不同,但依然是一种所谓“泛欧体系”(亦即所谓“西方体系”)。从“非泛欧”民族和“非泛欧”国家的视角看,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白肤碧眼、腿长多毛、鹰视狼顾”,没有什么区别,更何况他们还同属于英国老牌政治家丘吉尔曾一再以非常自豪的口吻强调的“英语民族”,信奉同一种宗教、文化,具有同一种饮食习惯、同一种审美标准;国际体系无论是“美治”还是“英治”,都是“泛欧国家”(亦即所谓“西方国家”)(15)主宰世界。从第一转型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到第二转型期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及美国追求的所谓“单极体系”等,皆无一不由“泛欧大国”主导。所谓“西方的冲击”,更是贯穿于前两个转型期始终。在此500年间,“泛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至基督教文化向非泛欧国家迅猛扩张,非泛欧国家则承受着持续不断的“欧化”、“西化”、“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基督教化”压力和“刀叉文化”以及“领带西装”压力,而这些又基本上等同于某些西方政论家及政客观念中的“全球化”,也与他们主张和主导的“全球秩序”及“全球秩序观”并行不悖。
第三,已发生的两次国际体系转型过程充斥着由大国主宰世界的大国政治和“霸权主义”,中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基本没有发言权,其间霸权国走马灯似的起起落落,竞相更替,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也是“泛欧”大国不断争霸的过程。在此期间,相继兴衰的大国,16世纪有葡萄牙和西班牙,17世纪有荷兰,18世纪有法国,19世纪有英国,20世纪则有美国。莫德尔斯基、汤因比、沃勒斯坦等人并据此提出了大国争霸“周期律”,认为大国兴衰周期大体“以一世纪为单位”。(16)沃勒斯坦甚至具体提出一国霸权通常经历勃兴(A1)、胜利(B1)、成熟(A2)、衰退(B2)四个发展阶段,并论证荷、英、美等霸权国都经历过或将经历这样四个发展阶段,从兴到衰的周期也大体皆为一世纪左右。(17)
第四,已发生的两次国际体系转型过程皆充斥着争霸战争和长期国际动荡。根据汤因比、莫德尔斯基等人的大跨度研究,在两次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也存在一个“以一世纪为周期”、或者说以“100年多一点”为周期,反复出现大国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的“战争和平周期”或者说“世界战争”,这包括1494-1516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意大利以及在太平洋上的战争”、1580-1609年西班牙对荷兰的战争、1688-1713年“路易十四的战争”、1792-1815年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914-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等。(18)据加拿大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更详尽的考证,从1648年到1989年的341年间,全世界共发生各类战争187次,(19)平均每隔不到两年就有一次战争。这些战争或者是大国之间直接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的战争,或者与大国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有关联。而按其他一些学者依据不同的战争标准进行的研究,在此期间的战争频率甚至更高。如英国学者理查森认为从1820-1949年共发生了317场战争,几乎每隔半年就摊得上一次战争。(20)总之,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也是战争与动荡持续不断的过程,其间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世界处在战争中的时光大大多于世界处于和平中的时光。
第五,这两次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还是“泛欧国家”的国际观、国际秩序观、国际政治理论从形成到实践并强行向全世界推而广之的过程。在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的数百年间,“泛欧国家”产生了众多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和形形色色的国际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理论流派,其集大成者莫过于摩根索等人,其始终居于主流地位的理论则莫过于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各类变种。综合起来看,“泛欧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理论,其理论基石和“理论高峰”(21)是摩根索所主张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包括以“人性恶”作为国际政治的起点;以“权力界定的利益”为国家的最高政策追求;以实力征服、控制对手;在追求国家利益时不受“普遍的道义原则”限制,等等。(22)简言之,这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是把“人性恶”、“理性决定的国家利益、权力、均势,以及无政府世界中权力的运用”等视为国际政治的普遍法则。(23)正是在这些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秩序观的引导下,相继兴衰的各“泛欧”强国在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的过程中,不断扩军备战,不断争霸,不断以武力贯彻国家意志,搞“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尤其是向“非泛欧”地区进行全方位侵略扩张,追求无限的权力和利益,以至在国际体系两次转型的500年间战乱不止,血流成河,“非泛欧国家”大部分沦为“泛欧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从第一次国际体系转型期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到第二次国际体系转型期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美国追求的“单极体系”,皆无不浸透了各“泛欧国家”的权力政治观,而这些“泛欧”体系的形成又使“泛欧国家”的权力政治观,包括实力原则、崇尚武力和战争、均势、弱肉强食、大国主宰世界等等,皆合法化、制度化,并一度风行全世界。
三
21世纪国际体系将朝什么方向转型?将以什么方式转型?又将表现出什么样的形态?所有这些问题,不但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在“象牙塔”中关心的问题,也是政治家们议事日程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历史表明,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既漫长,又非常曲折、复杂,有很大的反复性,它如何完成主要受历史法则控制而不能简单地服从于人的主观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体系本质上是历史的产物、时势的产物,而非人力所能主观构建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于追随历史潮流,顺水推舟,顺势而为,而不在于主观拍脑子拍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来。前两次国际体系的转型与形成过程莫不如此。
现在就预测未来国际体系的演变方向及其形态,确实言之过早,甚至近乎不可能。然而,依据此前两次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也依据变化中的世界潮流,包括依据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消费、从器物到观念的、亘古未有的全面转型,以及依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等新现象,我们仍然有可能对未来国际体系的转型方向及其基本轮廓与特征作一个简单素描。
第一,未来国际体系将更多地反映“非泛欧”国家的观念和利益诉求、愈来愈接近“全球共主”型的、真正的全球体系。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泛欧国家”的主导权将不断弱化,这意味着“泛欧国家”、尤其是“泛欧”大国对国际体系持续500年之久的垄断性主导权中断、甚至一去不复返,“非泛欧”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将出现质的跃升,而这也正是我们理解未来国际体系转型模式及方向的钥匙。
一般说来,决定国际体系主导权归属及国际体系形态、性质的首要因素是国际力量对比。过去500年,“泛欧国家”之所以能主导国际体系,主要是由于它们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享有压倒性优势。单以经济指标而论,1800年,“泛欧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尚不到30%,包括中、印在内的“非泛欧国家”则占近70%。但到了1880年,因科技和工业革命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泛欧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急剧上升到近80%,其中英国一国占22.9%,而“非泛欧国家”所占份额降至1/5左右。(24)正是这种新获取的经济优势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实力优势,使“泛欧国家”、尤其是英国掌控了国际体系主导权,也支配着“非泛欧国家”的命运。(25)
1945年,虽然欧洲国家普遍衰落,但欧洲的“堂兄弟”美国继欧洲而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泛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对世界享有综合实力优势,只不过国际“权力”在“泛欧国家”内部进行了一次向美国倾斜的再分配而已。就在1945年,美国几乎占有世界黄金储备的2/3、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出口份额1/3以上、拥有世界一半的造船业,还拥有1200万军队、1200艘大型战舰以及拥有原子弹,其权势之强盛“无与伦比”。(26)美国之强大,不但保障了美国足以替代英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也保障了“泛欧国家”继续居于国际主导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虽因朝战、越战等因素影响而实力下滑,但欧洲、日本的实力回升,“泛欧国家”的总实力仍然处于超强地位。如,1955年,“泛欧”核心国家美日及当时的欧共体9国GNP之和占世界同比的56%;20年后的1975年,美国的GNP占世界比重从1955年的36.3%降至24.5%,但由于欧日力量回升,“泛欧”核心国家美日及欧共体9国的GNP所占世界比重仍达到支配性的53.5%。(27)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解体及第三世界一度陷入所谓“大失控”和“大混乱”,美国实力再度回升,其经济一度创造过长达113个月的连续增长期。1999年,美国GDP达91904亿美元,接近世界GDP总量30万亿美元的31%。(28)在其他领域,美国也处于傲视全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能反映“泛欧国家”总体实力的经合组织29国的GDP之和在1999年达到24.8万亿美元,占全球同比的5/6左右,较之20世纪70年代有了新的回升。(29)美国的一超优势及“泛欧国家”相对实力的逆势上扬,不仅保障美国实现了对20世纪国际体系的主导权,也使“泛欧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点。也正因为如此,反映“泛欧国家”国际观和利益观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扩展民主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断层论”、“欧亚黑洞论”、“文明冲突论”、“民主改造论”、“国家转型论”等西方意识形态一时甚嚣尘上。
但是,以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为契机,美国及“泛欧国家”力量逆势上扬的势头被打断,历史开始回归常态,即回归到“非泛欧国家”力量上升,“泛欧国家”力量从峰顶衰退的常态。这一回归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受反恐及其他因素牵制,硬实力与软实力双双衰退;二是欧日等重要“泛欧国家”的综合实力一直呈下滑态势,且它们、尤其是欧洲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与作为“泛欧国家”“领头羊”的美国之间,有渐行渐远之势;三是俄罗斯停止了战略摇摆,从冷战后初期的向“泛欧体系”回归再次转向脱离“泛欧体系”,寻求“走自己的路”;而最重要的是第四,以“金砖四国”为首的“非泛欧国家”呈普遍崛起态势。其结果是不到10年时间,世界力量图谱发生了重大调整。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推动这种世界力量图谱的调整大大加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年,“泛欧体系”核心国家的美欧(原欧共体9国)及日本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为292020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689969亿美元的42.4%,这一比重比冷战结束时低得多,也较20世纪70年代低了约10个百分点。如按汇率计价,美欧(原欧共体9国)及日本GDP总量为324827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606898亿美元的53.3%,这一比重虽然与20世纪70年代相当,但比冷战结束时仍低了不少。(30)美国的GDP总量所占比重更是从30%这一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数”(31)跌至不到1/4。与此相对照,“非泛欧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和重要性则大幅提升。冷战结束以来,这些“非泛欧国家”加快发展,形成群雄并起之势,扎卡里亚(Farred Zakaria)称之为“它者的崛起”和“后美国时代”来临。(32)这些“非泛欧国家”人口之和相当于“泛欧国家”人口之和的6倍,GDP总量占全球比重已从2000年的36%上升至2008年的41%。(3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及全球后,“泛欧国家”面对危机不是按以往经验求助于G7/G8集团,而是主动发起两次“G20”会议,求助于“非泛欧国家”共同参与救市,生动地说明“非泛欧国家”国际经济地位和影响确实在上升,也说明世界结构不一样了,过去数百年反映“泛欧国家”实力优势、由“泛欧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体系已难以为继,国际体系转型由此提上日程。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非泛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增长率长期高于“泛欧国家”,后者对前者所享有的经济优势还将进一步削弱,直至基本平衡。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表的最新全球趋势研究报告《转型的世界:2025年全球大趋势》分析说,世界财富和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规模、速度史无前例,这将导致“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体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34)在这里,美国战略界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国际体系“转型”将构成未来“世界转型”的主要内容。但是,这种转型远不止是改变“二战以来”的国际体系,而是要改变自十五六世纪以来一直由“泛欧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局面,使国际权力在“泛欧国家”和“非泛欧国家”间进行相对平衡的再分配。
第二,未来国际体系中大国的地位与作用将呈下降趋势。近代以来500年的国际关系史证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大国政治、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大国关系。在21世纪新的国际体系中,这种大国主宰局面很可能会有大幅改变。一方面,大国圈子在扩大。历史上的维也纳体系主要由英、俄、普、奥四大国操纵;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主要由英、法、美、日、意五大国操纵;雅尔塔体系仅由美、苏、英三大国操纵;冷战后初期美国甚至谋求建立由一个大国操纵的“单极世界”。但在21世纪,除了美国继续保持超强地位、中国开始从“多强”中出线外,印度、巴西、印尼、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韩国,都愈益开始具有大国的实力、也具有挤入大国圈子的心态。欧洲的英、法、德、意等则愈益回归到以独立大国身份处理国际事务,从而架空欧盟。这意味着大国的“门槛”和“标准”在降低,大国格局以“单极”、“两超”、“五大力量中心”、“一超多强”、“G2+X”等概念都不足以描述。21世纪的大国圈子除既有的美、中、俄、日、英、法、德、印等国外,很可能还将纳入澳、加、韩、墨、印尼、巴西、南非、尼日利亚,甚至纳入伊朗、土耳其等人口过亿或近亿、GDP过万亿美元或接近万亿美元的国家。此次“G20”会议很可能是未来新的大国圈子的一次“彩排”。这种大国标准泛化、大国“门槛”降低现象,恰恰说明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下降而不是在提高。另一方面,大国圈子的性质也在变化。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到维也纳时代,再从凡尔赛-华盛顿时代到雅尔塔时代,所有的大国圈子基本上都以“泛欧大国”为核心,只有20世纪下半叶中国加入大国圈子是个例外。但在21世纪的新大国圈子中,“非泛欧大国”的数量和影响将明显增大,这其中不但包括中、印、巴、墨、印(尼)、尼、南非等,也包括开始脱离“泛欧”体系的俄罗斯。而“非泛欧国家”影响的扩大,又可能吸引日、澳这样的“泛欧”外围大国“变脸”、“变身”,靠向“非泛欧国家”。很有可能,在21世纪中叶以前,大国圈子中“泛欧大国”与“非泛欧大国”的实力与影响将势均力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转型的世界:2025年全球大趋势》预测,到2025年,中、印两个“非泛欧”大国将超过日、德等,跃居世界“最大经济体”排行榜的前三甲;而到2040-2050年间,中、俄、印、巴等四个“非泛欧大国”GDP的“全球份额”将超过“G7”的份额。(35)到2050年,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泛欧大国”将从目前的6席降为2席;世界前10个人口大国中,“泛欧大国”将只保持1席。(36)“非泛欧大国”的崛起及影响的扩大,势必改变数百年来由“泛欧大国”确立的国际政治思维及相关法律、制度和国际游戏规则、改变大国的行为模式以及国际体系的性质、构架与相关的游戏规则。此外,还要考虑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及世界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等因素的影响。前者使各大国愈益主动积极地融入各自的区域,与各区域内中小国家相互依存、同进同退,对此,英国积极融入欧盟、中国积极推动东亚“10+1”、“10+3”、美国屈就拉美一体化,皆可为证;后者使大国更难按过去500年来经久不衰的“大国主宰”模式行事,更难对中小国家予取予求,对此,美、中、俄、日、韩未能迫朝鲜弃核,美、欧、俄未能迫伊朗弃核,而以美国与北约之强大,迄今仍未能制服“塔利班”、“摆平”伊拉克,也皆可为证。
第三,未来国际体系将建立在国际权力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太平洋地区的新地缘政治图谱的基础上,这将从地缘政治上保障新的国际体系更多地带有“非泛欧国家”的印记。“泛欧国家”之所以能主导国际体系500年之久,是由于以大西洋为依托的“泛欧”核心国家美国及欧洲各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长期享有对“非泛欧”地区的全面优势。如,1900年,以大西洋为中心的欧洲与北美占有世界制造业总值的85%以上。(37)整个20世纪,大西洋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份额一直在3/4左右波动,从未低于60%,正是这一点为以大西洋为地缘政治依托的“泛欧国家”主导国际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然而,由于世界经济中心加速从“西方向东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一情况正在改变。目前,世界经济中心主要分布于并驾齐驱的欧洲、北美和亚太三大区域,其中北美横跨两洋,太平洋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进程一方面取决于亚太与欧洲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时也取决于北美在亚太与欧洲二者间进行什么样的战略选择。近代以来亚太在经济上长期落后于欧洲,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1999年,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22个)的GDP总量为9.3万亿美元,而亚太GDP总量约略超过8万亿美元,稍逊于欧洲。(38)2007年,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23国)的GDP总量增至105042亿美元,而亚太仅中日韩与东盟的GDP总量就超过10万亿美元,与前者不相上下。(39)如加上港澳台、蒙古、朝鲜以及印度等地区和国家的相关数据,则亚太GDP总量与整个欧洲不相上下。由于中、印、东盟等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欧洲各国,今后10-15年间,亚太经济规模将大大超过欧洲。届时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将决定性地从大西洋沿岸转移至太平洋沿岸,美国的大西洋国家属性将弱化、其太平洋国家属性将增强,并将最终完成从大西洋国家或两洋国家向太平洋国家的转型。同时,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也可能蜕去“泛欧”属性,完成从“泛欧国家”向亚太国家的“变脸”、“变身”。简言之,一旦亚太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国际体系的“泛欧”属性也必然淡化,其全球性特征也会相应强化。
第四,未来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虽然也将充满艰难、曲折,充斥着竞争与冲突,但不会像前两次国际体系转型那样处处充斥着战争血腥,更不太可能发生类似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战争。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几百年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浩劫留下的历史记忆影响外,更是由于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全球化造成各国俱损俱荣的相互依存关系等,导致大国战争成本与收益之间出现倒挂关系。任何大国、在任何条件下发动大国战争,不论是胜是败,都将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中印等“非泛欧大国”的崛起将有助于把和平竞争因素引入大国机制和国际体系,有助于抑制大国战争的再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新政府提出不以崛起大国为主要战略防范对象、提出“无核世界”理念,(40)以及调整军事力量结构、包括放弃采购进攻性很强的F-22、代之以采购进攻性较弱的F-35等,的确有顺应“世界转型”和“21世纪全球大趋势”的一面。
最后,新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即其基本构成“单位”将发生重大变化。近代以来数百年间,国际体系一直以所谓“民族国家”为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但是,在21世纪的新型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只是国际体系构成中的基本单位之一。除民族国家外,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还将包括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区域集团等。这不但导致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独占性地位下降,也是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环保组织、禁雷组织等,较之一些中小国家更敢于就一些“低位政治”问题直接向美、俄、中、日这样的大国施加种种压力。在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构成变化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因素、世界转型、相互依存等因素作用下,国际体系的运行规则、游戏规则、人们的国际政治观念和行为方式等都将出现不同以往的新变化。国际社会有关战争与政治、战争与和平,有关合作与竞争、安全与发展,以及有关各种涉及“高位政治”、“低位政治”的种种重大国际问题的思考、解读及政策反应,都会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现实主义及其各类变种的国际政治观将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和平、和谐、依存、共赢的理念将持续增长,战争、零和、尤其是恶性竞争和大国战争因素将不断削弱。
余论
在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大潮中,中国已成为促成并推动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之一。中国崛起的规模、速度和方向以及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将对这一轮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速度、方向、性质产生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对这一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西方都已了然在胸,我们自己也要心中有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大国、“非泛欧大国”和亚太大国等多重身份以及中国的加速崛起,是推动国际体系由“泛欧体系”向“非泛欧体系”转型、由以大西洋为中心向以太平洋为中心转型的重要因素。2008年,中国初步核算的GDP总量为300670亿元人民币,折合约44000亿美元,(41)已大大超过德国,紧紧咬住日本,进入“坐三望二”位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研究报告《转型的世界:2025年全球大趋势》有关2025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2)的预测结论是相对保守的。虽然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小,但对美欧日等“泛欧国家”影响更大。因此,从相对力量对比看,这场金融危机很可能将加快而不是延滞中国“赶超”“泛欧大国”的历史进程。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降到6.1%,但美国同期却降到-5.7%,日本甚至更糟。IMF预测日本经济2009年可能收缩5%-6%,而中国可望实现“保八”目标。若果如此,中国有可能在2009年、最迟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越过一道重要的国际政治“分水岭”。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的时间也很可能切合高盛公司及林毅夫的预测时间表而提前。(43)届时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还将进一步提升,而这一点也正是中国能对国际体系转型施以影响的根源。
在前两次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中国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是牺牲品。在第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后期,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在第二次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中国在其前期由列强予取予求,在后期、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全球参与,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时下步步展开的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为中国真正成长为世界大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并获得与中国的历史地位、国家规模相称的国际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声誉和威望提供了难得一遇的时机。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有种种期待以及种种猜测。中国自己,无论是决策精英还是学术精英甚至普通大众,都应以中国文化特有的谦谨态度面对这一时刻,都应严肃思考:中国应如何继续坚持“咬住发展不放松”?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承诺?如何在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推进“和谐世界”建设,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注释:
①[日]田中明彦著,杨晶译:《世界系统》,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4月,第8页。
②[日]田中明彦著:《世界系统》,第10页。
③[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④[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0页。
⑤[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谭荣根译:《美国实力的衰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8页;《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4页。
⑥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14页;[日]田中明彦著:《世界系统》,第93页。
⑦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第三版,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
⑧[日]田中明彦著:《世界系统》,第95-99页。
⑨[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⑩[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492-465页。
(1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美国实力的衰落》,第4页。
(12)IAN CLARK (E.H.Carr),"Brining hegemony back in: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Affairs,January 2009,p.33.
(13)参阅Arnold J.Toynbee,Civilization on Trial,NY,Oxford U.S.,1948.
(14)沃勒斯坦在划定“现代世界体系”转型历程时选定了四个时间点,即:1492年、1945年、1989年、2000年。本文划分法与沃勒斯坦的观点有所区别,但在第一次转型起点(1492年)和新一轮转型点(2000年)的时间定位上,本文汲取了沃勒斯坦的观点。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58页。
(15)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表的报告《转型的世界:2025年全球大趋势》中,西方国家被明确界定为“包括欧洲、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见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p.1,19,http://www.dni.gov/nic_2025_project.html.(上网时间:2008年12月25日)
(16)[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5页。
(17)[日]田中明彦著:《世界系统》,第75-84页。
(18)《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32-333页;《世界系统》,第75-76页。
(19)[加]卡列维·霍尔斯蒂著,王浦劬等译:《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44、75-78、122-125、187-189、237-243页。
(20)《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32页。
(21)王缉思:“摩根索理论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美]汉斯·J·摩根索著,肯尼思·W·汤普森修订,徐听等译,王缉思校:《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序言,第1页。
(22)[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第4-21页。
(23)《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81-86页。
(24)[美]保罗·肯尼迪著:《没有永久的霸权》,第10页。
(2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下)》,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5-630页。
(26)《没有永久的霸权》,第304-307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编辑组编辑:《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三联书店,1979年,第60页。
(28)OECD,Main Economic Indicators,June 2000,p.263.
(29)OECD,Main Economic Indicators,June 2000,p.263.
(30)"List of countries by GDP (nominal)",http://en.wikipedia.org/wiki.(上网时间:2009年4月28日)
(3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32)Farr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43.
(33)Chris Bryant,"China in second place in purchasing power table",Financial Times,April 12/13,2008.
(34)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p.1,7.
(35)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p.7,28.
(36)"Births of a nation",Financial Times,March 1/2,2008.
(37)[美]保罗·肯尼迪著:《没有永久的霸权》,第10页。
(38)OECD,Main Economic Indicators,June 2000,p.263.
(39)OECD,Main Economic Indicators,2009/1,p.283; Emily Kaiser,"Grim news is expected in export number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pril 6,2009.
(40)Merle D.Kellerhals Jr.,"Obama Seeks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Washington File,Public Affairs Secti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pril 6,2009,p.2.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09年2月27日。
(42)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p.28-29.
(43)关于中国GDP总量何时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的预测,经合组织经济情报局、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统括部研究员小峰隆夫分别预测为2020年;原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预测为2030年;高盛公司预测为2041年。参见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8,p.36;林毅夫:“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展望”,《外交评论》,2007年6月,第9页;[日]小峰隆夫:“世界经济长期预测”,《越洋聚焦——日本论坛》,2007年11月号,第17期,第29页;高盛公司报告:“BRICS——通往2050年之路”。
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沃勒斯坦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