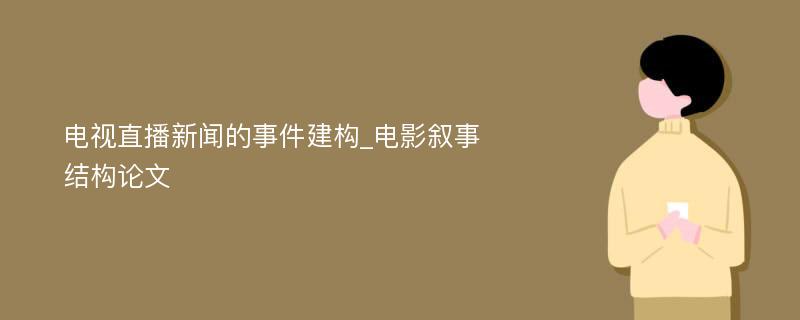
电视现场新闻的事件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场论文,事件论文,电视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4-0014-08
在叙事理论的视野中,叙述的法则存在于一切用符号建构的世界中。它包含了神话、寓言、童话、小说、历史、戏剧、绘画、电影和社会新闻。探讨作品的叙事形式,就是在透视作品的架构,它不仅使我们知道作品说了什么,而且知道作品是怎么说的,进而了解叙事作品的真实价值。尽管大部分叙事理论将视线投放到文学作品上,对于广泛传播的社会新闻论及较少。但是,社会新闻尤其是电视现场新闻(简称现场新闻)为我们展示出了故事文本对现实的最直接和最有可能的忠实形式,它也是叙事与真实之间的一种最接近理想的状态,所以,它可以成为分析其他社会新闻的可信性、忠实性的一种范式。
一、现场新闻的故事文本
叙事学家雷·肯南(Shlomith Rimmon.kenan)给故事下了这样的定义:故事是由“行为者所引起的或经历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故事是“依时序安排的一连串事件”[1]。鉴于此说,现场新闻作为故事,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新闻作为故事与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是有区别的,电视现场新闻更是如此。
故事是叙事理论首先涉及的问题,故事构成有两个主要因素:情节和场景。在故事中情节和场景是分不开的,但两者仍有区别。一连串的情节可能在一个场景中出现,也可能在多个场景中出现,这就为我们将其分开论述提供了可能。为了描述的方便和准确,需要将故事分为真实故事和说的故事。因为本文研究的是说的故事,行文中的故事一词即指此。有没有真实故事作为叙述对象,也是本文研究现场新闻故事文本与其他故事文本区别的基础。
(一)现场新闻故事的情节
1.故事情节的一般叙述。故事情节作为故事的主要构成因素,因其存在样态的不同,对叙述的要求也不同。在文学作品中,故事的发展是可以预料的(当然,这种预料符合情节和人物的发展逻辑),包括悬念也可以安排,情节便也有了灵活的串联方法:时序法(A、B、C依次发生)、因果法(A发生了,便有了B)[1]。不同的串联方法,把情节安置在一种时间顺序上,便构造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叙事作品中的情节是在叙述行为发生之后才面世的,情节自然随着叙述活动的展开才产生。叙述活动停止时,情节可以中断,待叙述再次开始,情节又在中断处继续,直至叙述完毕,故事才与叙述行为本身分开。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也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在整个叙述过程中,情节犹如语言选择轴上成千上万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它们被挑选和认定,并且按照人们接受的某些共同规则进行组合,只要在叙述的组合轴上符合故事的逻辑即可(注:言语行为采用两个基本操作方法:选择和组合。如果话语的主题是“孩子”,说话人就要在他掌握的比较接近的名词中选择一个,如孩子、儿童、小家伙和小鬼等,这些名词在意义上都是互等的……选择是在对应、类似,相异、同义以及反义的基础上继续的;组合则以连接为基础。)。因此,人们在阅读故事时对情节真实性的认定,是从故事本身获得结论的,并非在现实中一一对应。
2.非现场社会新闻情节的叙述。社会新闻中的故事是对现实中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叙述,这类故事都有一个叙述对象——真实故事。真实故事在叙述开始之前已经发生,它的存在与叙述行为(新闻报道)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完全是一个自在的完整的主体。真实故事用自己的时间将情节串联起来,由场景承载,它并不在乎有没有叙述行为出现,也不会受任何说法的影响。事情的发生、过程、结果都是无法预料,不可逆转的。因此,社会新闻故事必须以五个W(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都与真实故事相同为前提,这五个W就是新闻故事的真实性特征,也是情节中的主要构成因素。社会新闻故事必须排除任何情节的虚构,才能够保证其真实性、可信性。社会新闻故事与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尽管如此,非现场的社会新闻仍不能保证将被报道对象的原本状态和变化完整地给以展示。对此,用肯尼斯·博克提出的戏剧五要素(Pentadic Analysis)进行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博克说:“这五个术语将是我们研究的总原则:他们是行动、场景、人物、工具和目的(按:这五个要素与新闻的五个W基本相同)。要用一句话来说明动机,你必须用一个词来指称行动(指称在思想中或在行为中发生了什么),另一个词来指称场景(行动的背景,行动发生的环境);还有,你必须指明什么或什么样的人(人物)完成了这一行动,他运用了什么方式或手段(工具),为了达到什么目的。”[2]虽然,这五个要素决定了基本事实的不可改变,但它不能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出于不同的动机,人们在演讲和话语中搭配这五个因素的关系时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从而折射出不同的态度,进而引起截然不同的行动。”[2]因此,非现场电视新闻故事情节在叙述时仍有一定的选择余地。我们先来分析一个事例: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以后,美国的许多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但是,这种报道在主要画面的选择和搭配方面却是不同的。电视台给美国观众播放的是使馆在未遭轰炸之前和轰炸以后正面的图像,做这种对比意在表明轰炸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而使馆的另一面(坍塌的墙和破损的房屋)却不给观众看。虽然这两个画面都是现实的,但却折射出对这个事件完全不同的态度,并且引起不同的反映来。这样的搭配似乎给人们造成使馆轰炸的情况不严重的感觉。这就是画面符号选择和搭配的结果。因为只要新闻故事是被说出来的,而且是事后说的,它只能做到所说情节都是真实发生的,并不能证明说的故事就等于真实的故事。特别是怎么说,会导致不同的效果。再说,真实故事一旦存在于一种话语符号中(无论是用文字,还是用口头话语、画面说),符号就成了读者与现实之间的遮蔽物(当然画面符号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对此将在后面详述)。这时,符号本身的各种功能在故事的线性变化过程中开始起作用,接受故事者直接与符号——叙述行为而不是真实故事接触。
3.现场新闻情节的叙述。在描述此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分析画面符号的特点。画面作为一种符号,与其他文字符号、口头语言符号的区别在于其能指和所指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而为一的[3]。所谓的某种程度,是指映现事物全部或部分外在形象时,画面既是符号,又是被符号指称的物本身的影像。画面作为符号与被摄物合而为一,画面的存在就是现实本身的存在状态。这样一来,即使故事在叙述中出现,我们不仅感觉不到符号的遮蔽,而且还获得部分直接与其接触的机会。电视画面符号的这种透明性,与我们在现实中对事物外在形象的把握情形极为相似。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指出,电视新闻故事并不能等同于真实故事,选择、搭配、叙述等言语行为不可避免地折射着叙事的态度,并将它渗透到情节中。所以,仅依次为据还不能证明现场新闻故事对事实的忠实性是大于其他故事文本的。
现场新闻故事对故事的忠实是建立在叙述与真实故事同时展开的基础上的,它使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叙事作品的结构样式,即故事本身与真实故事在时间和现场上的重合。这不仅保证了故事情节串联的自然结构,并且使其“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始终有真实故事的验证。当这种新闻故事在屏幕上被叙述时,画面的连接也是在事件的时间系列中才形成顺序的,因此,故事的搭配方式也被严格地限制在真实的情节架构之中了,这样才保证了五种因素的结构[3]所在位置的自然性和不容置换。由此,电视现场新闻故事作为叙事作品,能够把真实故事中的全部情节及其展开顺序再现于屏幕上,并且将故事的悬念保持始终,在故事未完成之前,谁也不能肯定其结果,包括叙事者在内。这才从操作方面有效地保证着叙述对事实的忠实态度。正如罗兰·巴尔特在《S/Z》中指出的那样“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出无数种发展的可能:读者和观众一直在紧张与期待中猜想,接下去会如何?”[1]在紧张与期待中的猜想不仅在观众那儿,在叙述者身上也同样发生。这样的叙述不仅保持了故事自己原始的整体结构,而且映现出故事的变化状态。同时,还使观众获得了和现实中同样的“紧张与期待”。
(二)现场新闻故事的场景
1.场景的一般叙述。场景是指叙事文中故事的情节、人物活动的场所。有了场景,人物、实物、一切行为才不会被悬置起来。在文字符号构成的叙事作品中,场景并不是直接诉诸视觉的“视像”。事实上,读者什么也看不见,“所有的激情都是由一种意义引发的,它是一种更高的秩序或者关系(文字符号包容了的一切)引发的激情,而这种秩序或关系有自身的情感、希望、危险和胜利”[2]。与现实相比较,“在文学叙事作品中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语言而已,只是语言的历险”[2],只有语言的到来才构筑起场景。它的真实程度在于合理与可信。由于场景是承载故事中的所有存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发展与变化远比它更有吸引力,因此,对场景的感觉实际上成了对语言的一种感觉,场景是在这些语言唤起的思维中才逐渐明朗清晰起来的。语言的线性特征使场景从面的展示变成线的叙事。一旦人们熟悉了这种叙述,他们根据各自的经验再将线变成面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2.非现场新闻场景的叙述。用文字符号系统构筑的新闻作品对场景的叙述与上面所讲的基本相同,人们对于场景的感觉也是通过语言的“历险”,在语言的召唤中产生历历在目的感觉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叙述可以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叙述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因此,语言的指称功能在叙述过程中产生着主要作用,故事的场景——行为发生的环境基本上都是由那些有指称功能的语词构筑。非现场电视新闻的场景虽说在每个独立的画面中都有映现,但是在整个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却常常因为组接的关系,无法保证对真实场景的忠实。从表面看,画面符号作为场面的影像,将场面或局部、或完整地映现出来。但是,这种映现是根据叙述故事的需要进行的,尤其是画面符号的组接可以完全按照叙述的要求进行,加上画面符号可中断性及片断性的规则(杰姆逊认为当人们在观看电视时,他们首先要接受电视的规则,他们是按照电视规则看电视的。因此,电视的可中断性对于他们来说是正常现象。电视剧播放过程广告的插入是最典型的),非现场新闻中,场景与真实故事的场景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重新决定观众的观看顺序,在规则的允许下甚至颠倒原来的顺序。也可以利用组接法,用两个不同的场景承接故事的进展。例如,在一则关于卢旺达内战时期埋设地雷炸伤平民的新闻报道中,场景是由这样三个画面符号叙述的:一个小镇出现五六个被炸伤腿或胳臂的人;一片到处可见地雷端倪的草地;一个在草地上飞快奔跑的小男孩。这三个画面符号承载着发生在卢旺达地雷爆炸的真实故事。第二和第三个画面完全有可能本不是同一个场景,但当它们在电视新闻故事中被如此叙述时,人们将它视为一处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主要情节合理,场景自然会被视为真实的存在,并且成为情节展开的场所。这种规则的应用,同时也意味着对非现场新闻忠实于真实故事的约束是极有限的。
3.现场新闻场景的叙述。电视现场新闻与非现场新闻的主要区别有三个方面:一是现场新闻故事的叙述与被叙述对象——真实故事处在同一个场景中,它不仅利用画面符号将观众的兴趣从故事的结构转移到视像上,把事件的串联和事件转移到实物、人物的呈现上,而且把上述一切都放置在真实的场景中,以突出现场感。二是叙述与叙述对象的同时态,即现在进行时。两个行为同时发生,同时结束(关于时间的问题后面将会详细描述)。三是画面的组接受到现场的严格限制。以上三个方面使得现场新闻场景的叙述在最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叙述对真实场景的忠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忠实是叙述本身的要求和受到现场的限制的。当摄像机和记者开始叙述时,面对的是正在发生事件的现场,这时候他所要做的就是直面事件的现场,及时地将这个场景中最近的状态摄录下来。摄像机不停地工作,忠实地记录着它面对的现实情景。即使是同时使用多台摄像机进行拍摄,现场有主控室编辑画面,只要所有的镜头对准的是一个场景,编辑、摄像、事件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他们都会受到现场场景的控制。这种控制决定了镜头只能够变换拍摄角度和移动机位,也就是说在场景的横端面上进行选择,并且完成画面的组接。可以说,现场新闻场景的叙述是由场景本身调控的,它因此保证了场景叙述与真实的相符相成。另外,我们还看到现场的限制减少了画面组接的规则——可中断性、片断性介入叙述的程度,使观众通过媒介了解真实情况的权利得到了足够的尊重。
二、现场新闻的叙事者
任何一个叙事作品都是说出来的故事。因此,叙述就成为叙事作品分析的中心问题。对叙述者的研究,往往从分类开始,分类的过程就是对叙述者在故事中承担的具体任务、作用进行描述。叙事理论首先区分叙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还是故事外的人物。故事内的叙述被称作“同质叙述”(Homodiegetic),故事外的叙述称为“异质叙述”(Heterodiegetic),即“镜头叙述者”[1]。“同质叙述”由于是作为故事中的角色在说故事,故被认为缺乏客观性和权威感。异质叙述者置身于故事之外,可以全面地看待事实,叙述故事,因此被称作“铁面无私”的叙述者。
电视现场新闻故事的叙述者主要可以分为:镜头(画面)叙述;同期声叙述;现场记者叙述。三种叙述如果互相吻合,形成一体,便产生理想的叙事效果——忠实、可信的叙述。在叙述进行过程中,真实故事会对镜头和现场记者的叙述进行纠正。这种纠正是依赖于观众辨别和分析的能力自然进行的。
在非现场新闻故事中,镜头叙述是将叙述者隐藏于画面之后的,它没有暴露透视点,镜头似乎是一个飘忽不定的观察者。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画面的动态使观众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它在表面上造成的真实感使观众认为事实就是镜头上正在演示的,完全放松了对镜头编排的警惕,将编排意图也视为事实一同接受过来,这正是镜头的冷漠和平静导致的。它用单个画面的真实,遮蔽了选择和搭配的行为。同期声也可以被剪成几个片断配置给画面,以满足编辑的需要。同期声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另外,从接受的角度讲,这种冷漠也会因为缺少人际交往时的认同感,减少观众的兴趣。
电视现场新闻故事是由记者面对观众叙述的,与其他叙事作品的主要区别有二:一是叙事的非虚构性和对叙述行为本身的敞开;二是叙述者要进入故事的场景,保证叙述的时间与被叙述事件在时间上的一致。这种区别决定了叙述者与故事的如下关系。
(一)镜头叙述
现场新闻故事与其他叙事作品的主要区别是:其一,它使观众能够接触到真实故事,这种故事虽然靠镜头的摄录,但是镜头并不能将其遮蔽或改变其基本形态,这也是镜头的机器本性所致。其二,它必须在自己的叙述中保证事件的时间及其顺序不变,无法进行跳跃式叙述。镜头叙述由于其本身的单义性(镜头适合表现具体、单独的事物的面貌),在面对现场时对同期的音响(故事本身的声音)、话语叙述有强烈的要求。因此,镜头跟着话筒一起面向现场,记者的叙述既是镜头叙述的一部分,也成了镜头叙述的对象。其三,由于镜头叙述依事件顺序进行,画面的组合能够将事件的原过程映现出来,使故事的自然叙述与镜头的叙述基本一致。
(二)同期声叙述
同期声是真实故事的一部分,与画面同样具有证据的价值。同期声的出现是自然现象,它有时就是故事本身,有时也兼作故事的注释。在现场新闻故事中,声音和形象的同时出现才保存了事件较全面的状态(现实中的许多事物的存在或部分存在以及质的表示,就是由声音来显示的)。
(三)记者的叙述
记者在现场叙述故事时充任两种角色:同质叙述者和异质叙述者。作为异质叙述者,记者是以旁观者语气说故事的。“各位观众,我是小力,我现在在维多利亚港向您作现场报道……”(这句话证明记者不是当事人,只是旁观者),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的开始语。接下来,记者和镜头同时开始叙述。通过画面,观众得知记者已在现场,记者就等于获得了叙述的特权,即被观众认可的目击者或见证人。以“眼见为实”的理由,记者这时得到观众的信任了。对于社会新闻故事来说,得到观众的认可和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当作为“证人”的叙述进行时,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直觉而不是理性,这样才能保证故事的真实性。同时,在镜头机械式叙述的相伴下,如果记者的叙述出现了偏差,观众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他们总是认同画面(相信镜头叙述),以画面为依据对记者的叙述进行批评。
作为同质叙述者,记者身不由己地充当着当事人的角色。尽管记者的话语可以表示自己是一位冷静、客观的叙述者(这是对记者的要求,以此保证故事的公正),只要他在场,他的一举一动都具有叙述的功能。例如,担任战地现场报道的记者,会对现场爆炸声的强烈程度、火光的照射作出本能的反映:当记者在一个火灾现场进行叙述时,他身后一座仓库突然爆炸,爆炸产生的热浪和浓烟都会对他产生影响。他或被热浪冲得踉跄几步,或被浓烟呛得咳嗽,或直流眼泪。他的这些反应在画面中出现,使观众知道场景的危险程度。又如,在五月的雪域高原叙述现场新闻故事时,人们可以从记者被晒黑的脸上、干裂的嘴唇上了解到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的严酷。尤其是画面作为一种被扫描的电子信号,它在传递信息时只保留了事物的形状和运动状态,事物的某些性质(冷热程度、质地的优劣等)无法通过画面表现。记者在现场的直觉反应能准确提供这些信息。人类学家戴斯蒙·莫里斯把人体的行为表现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无意识型姿态(传达信息的机械动作。如用手试水温的时候,过冷或过热都会本能地缩手);表现型姿态(高兴时的笑容,悲伤时的眼泪);象征型姿态(通过模仿表达信息)等。新闻现场既是记者叙述的对象,也是记者的叙述环境。记者在这个环境中的种种无意识姿态和表现型姿态就是对现场的无言叙述,它的出现为观众提供了感觉现实的路径。因此,在其他叙事文中同质叙述者丢失的客观与权威性,在现场新闻故事中却能够获得。
我们看到,当记者进入当事人的角色时,他还可以把两种角色融为一体。两种角色的合一,是由记者的行动和角色化的采访完成的。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一个关于四川麻风病医院的故事(记者在现场讲述故事时出现的一个情节):记者主动伸出手与已经痊愈的麻风病人握手,对方脸上先露出迟疑的表情,然后激动地紧紧握住记者的手。记者的这个行为有两种作用:一是记者出于对采访对象当下处境的同情(因为麻风病人即使痊愈后,也难以被家人接纳),做出愿意与他接触、不嫌弃他的姿态(此时记者充当着同质叙述者)。二是继续叙述内容。在这个故事中,记者要告诉观众麻风病人痊愈后不会传染,他们应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拒绝他们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异质叙述)。记者在这两种角度的转换过程中,成功地完成了叙述。
三、现场新闻的叙述时间
关于叙事作品的时况问题,叙事理论做如下描述:叙事作品是一个双重时间性的序列,也即所讲述事情的时况和叙述的时况(所指的时况和能指的时况)。这个二元性不仅可以造成时况上的扭曲——这在叙事作品中司空见惯,例如主人公三年的生活,用小说中的两句话或者电影中几个“反复”剪接的镜头即可概括,而且更为根本的是,我们由此注意到,叙事作品的功能之一即是把一个时况兑现在另一个时况当中[4]。在作为叙事文的现场新闻叙述中我们发现,普遍存在的双重时间性的序列由于现场的存在而合二为一。时间只有一个,即真实故事的时况。这个时况承接故事的每一个环节,不受叙述的影响,前面讨论过的场景的真实顺序也是由这个时况保证的。与此相同,记者的叙述(能指的时况)不是把一种时况兑现到另一个时况当中,而是极力保证它们的一致。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所指的时况以自己的顺序流动,能指的时况像它的影子一样紧随其后,这在其他叙述作品中不可能存在。
(一)等时性
在现场新闻叙事过程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事件的时长与叙述的时长保持着均衡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们的时长是相等的。这种等时的叙述,不仅保持了事件的原本长度,在事件进展的每一个环节上也使观众充分感受到时间的本来意义。任何一个事件的时间不仅仅是对过程的一种限制,或者是对其规模的表示,时间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以画面为符号的叙事文中,画面的单义性使得抽象的、概括性的、内心感受的内容很难被表现。但是,在这种等时的叙述中(尽管这是不得已的),事件的类似意义却能在时间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让我们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先来体会一下观众是如何在时间的流逝中感受“等待”的意义的:当帷幕拉开时,观众看到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像是在等人(等戈多)。时间在流逝,场面依旧。观众在期待变化的心情的驱使下也在等待。终于有另一个人走了上来,告诉他戈多不来了。在这出戏中,作者用时间的流逝表现等待的意义,获得了成功。现场新闻的叙述也体现出了这个特点。现场新闻对类似“等待”这种意义给以充足的时间,使其得以在体验中获得对意义的理解。例如,在柯受良先生驾车飞跃黄河瀑布的现场新闻中,柯先生第一次驾车冲到起点,没有越起,汽车便退了下来。第二次再冲上去,汽车越起,跨过黄河壶口瀑布。从第一次到第二次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的意义是飞跃的艰险、成功的可能性等。上述意义只有在时间的给予中,观众才能够直接获得。
(二)顺时性
记者在现场进行叙述时只有一个顺序——事件本来的顺序,在下一个情节未出现时,记者和观众都处在对未来的期待中,或者是对结果的等待中。由于面对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等待的时间较长,观众也不会因此产生抱怨。当我们面对真实时,都懂得直面是最理智的选择,这就是真实的力量所在。即使中途有背景插入,故事的时间依旧。如果背景是语言符号的话,它犹如画面的旁白,与画面同在一个故事时间中展开。这时,画面作为事件的映现,对语言提出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如果是作为背景的画面插入进来,原来的时间依旧在流动,画面便被限制在故事的时间的线上,它并未扯断这根线,也无法让故事倒叙。当画面(背景)淡出后,故事再次出现。尽管背景画面的出现消耗了故事的部分时间,但是故事的时间顺序并没有被打乱,时长也没有缩短。
(三)不能省略
省略是叙事作品在处理时间时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法,我们熟悉的语句有:“过了一年”、“几年过去了”、“三天以后”等等。这些语句将故事的时长变成一种描述,这种描述所需的时间,是由阅读者给与的。阅读者一般不会真正用诸如三天的时间来阅读“三天”这句话。如果在三天中发生的事情也被省略,只要故事从三天以后又开始了,其中的情节没有中断,读者一般不会追问三天内的事情。即使叙述者在叙述三天内发生的事情,读者也不会用三天时间去读它,故事的时长在这里只是一个说法而已。省略使得故事的时长与作品的时长形成不等的关系,这是因为故事对叙事的过程没有时间上的要求。叙述开始了,故事便出现了。叙述中断,故事可以隐去。著名作家金庸曾告诉记者,他写社论时不想小说的事情,写小说时也不去想社论。因此,他能够做到一边写小说,一边写社论。叙述可以中断,叙述本身就获得了时间上的相对独立。再说阅读的时间基本上是由读者自己掌握的,甚至打乱阅读顺序、跳跃式阅读都是允许的。现场新闻的叙述与文学叙述作品相反,它不能够省略时间,也无法使叙述故事的时间顺序与故事本身的顺序相左。如果在叙述过程中需要背景介绍,作为叙述的一部分的背景出现时,依然是由故事的时间轴承载着,不可能有新的时间轴出现。虽然现场新闻叙述允许背景或其他相关内容的切入,但这种切入不允许也无法改变故事的时间轴,只是占据这个轴上的某个时间段,因为故事的时间一直在流逝。另外,当切入的内容结束、叙述回到现场时,本来与这段时间同时存在的内容也被抹去了。这就要求在叙述过程中任何一种切入都必须保证故事的进展不被破坏,避免造成观看的遗憾,因为这种遗憾是无法弥补的。一般情况下,切入是故事情节在较长的时间内没有变化或进展的情况下(例如: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现场新闻在叙述开始不久,主会场在较长的时间内等待中英双方的首脑进入会场,时间在流逝,事件没有进展,无事可言)进行的。这样,既保证了叙述与故事的一致,也避免了由于故事的滞留产生出来的叙述空白。
电视现场新闻依靠技术的力量将我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活灵活现地映现在屏幕上,并且自始至终保持住我们日常接触各类事物时的感觉——视觉与听觉的同时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现场新闻是最接近真实存在的故事文本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关注点放置于新闻报道(包括各种新闻文本在内)是否等同于事实上,回答既简单,也无意义。因为,即使电视现场新闻报道也不是事实的自然存在面貌,电视现场新闻并不等同于事实本身。即新闻中的事件并不等同于作为事实的事件。我们之所以创造并使用各种符号系统,并且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用这些符号的指称功能达到叙事的目的,因为我们别无选择。研究符号如何构筑事实,即真实性的真实情形的意义也在于此。
[收稿日期]1999-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