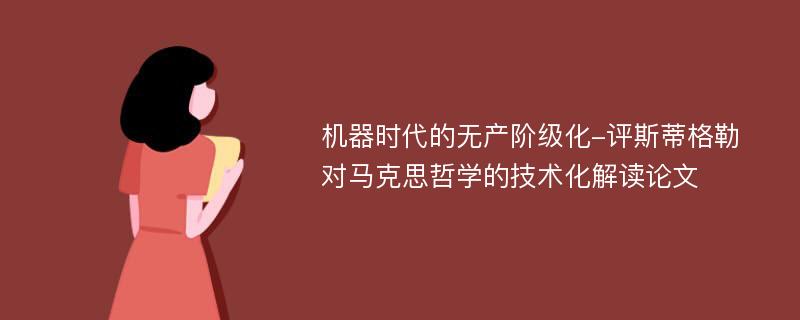
机器时代的无产阶级化
——评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哲学的技术化解读
□张福公
(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当代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他把由技术变革导致的劳动与知识的分离现象称作无产阶级化,并将诊断这一现代性症候的批判理论追溯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从无产阶级化的逻辑视域出发重新诠释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着重分析了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与无产阶级化问题,最终走向基于技术自反性的自治解放之路。这一解读思路为我们推进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真实语境和科学方法论,以致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存在严重缺陷。
[关键词] 无产阶级化;机器论片断;一般智力;工艺学
当代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是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重要弟子,当今欧洲最重要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之一。近年来,他沿着在《技术与时间》中开辟的技术哲学批判理路,进一步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问题症候及其解放路径进行了创新性探索。“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就是其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斯蒂格勒将工业革命以来由技术变革带来的劳动与知识(技术)的分离及由此造成的总体性知识短路与系统性愚昧现象称为“无产阶级化”,并将针对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批判理论追溯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不过,回到马克思的真实文本语境就会发现,斯蒂格勒不仅没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而且同维尔诺、奈格里等人的社会批判理路具有同质性的理论缺陷。对斯蒂格勒的观点进行辨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与批判。
一、重读黑格尔和马克思:无产阶级化视域下的主奴辩证法与机器大生产
斯蒂格勒指出,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化现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工业革命导致的技能知识的丧失;第二阶段是20世纪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导致的生存知识的丧失;第三阶段是21世纪数字化技术导致的理论知识的丧失① 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张福公译,杨乔喻校,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另参见张福公:《重读马克思恩格斯:一种人类纪的视角—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短期研究生课程综述》,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19日第版。 。其中第一阶段的无产阶级化正是马克思所遭遇的时代症候,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构成了无产阶级化思想的理论源头,而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又是以颠倒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为前提的。
斯蒂格勒认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是一种追求承认的辩证法。我们通常所说的“奴隶”(slave)实际上是雇工(Knecht,servant)或工匠(craftsman),而主奴关系的颠倒恰恰来自“奴隶对知识的追求”,即奴隶“通过工作、运用技巧而使自己获得技能、知识、个体化形式和财产”[1](p125),并最终成为未来的主人即有产者(bourgeois)。在这一过程中,奴隶获得承认的革命性力量就源自奴隶在工作(work)中获得的知识。而这里的“工作”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labor)”:工作是最典型的外化(即知识的获得),而劳动则是知识的丧失。因此,如果黑格尔描述的是从工匠向有产者的转变,那么,马克思描述的则是从工人向无产者的转变[1](p126),即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丧失知识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也就是说,黑格尔正确揭示了工作与知识的肯定性关系,但却严重忽视了技术和知识对工人的疏离与控制[1](p126)。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要揭示和批判的内容。
在斯蒂格勒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首次遭遇无产阶级化问题。首先,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外化(exteriorization)颠倒为物化(materialization),即人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人“一旦开始生产自己的生存工具,他们就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2](p519),也就是说人自为地通过生产资料进行技术性自我生产,从而与动物的本能行为彻底界划开来[1](p130-131)。这同时也是一种人为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的过程,即“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p520)。其次,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引出人的无产阶级化问题,即人的物质生产过程同时就是知识的外化过程,而知识的外化既是知识建立的条件,又是知识丧失的原因——这正是对苏格拉底的记忆药理学(Pharmacology)(记忆的外化亦即记忆的丧失)的翻版[1](p107)。随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进一步推进了他的无产阶级化思想:一方面,他更详细地描述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明确将雇佣工人的无产阶级化描述为工人丧失知识的过程,因为知识被转入了机器中[1](p127);另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这种无产阶级化将逐步扩展到所有阶层[1](p126)。
斯蒂格勒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机器论片断”(即《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中真正确立了机器时代的无产阶级化思想。马克思准确指认了从工具到机器体系的外化发展过程[1](p131),即“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3](p90)机器体系的产生标志着人的外化过程进入新的阶段,并使无产阶级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具体来说,因为机器“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3](p102),因此,机器是人的智力经验的编程化(grammatization)① “编程化”概念来自法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席凡·欧胡(Sylvain Auroux)。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拼写文字(alphabetic writing)是如何出现的。而斯蒂格勒则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切人类运动和行为是如何被分析、离散和再生产出来的。 和人工再生产(artificial reproduction)的结果:一方面,机器产生于人的姿势(即手和脚)的分离和再生产;另一方面,机器又是知识物化的产物。于是,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便凸显出来。斯蒂格勒认为,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蕴含着一种“知识器官学(organology of knowledge)”[1](p135),即“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3](p102)。也就是说,科学知识作为一般智力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并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方式。然而,一般智力及其技术器官却导致无产阶级化不断扩展与深化,越来越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力量。马克思指出:“知识、技能和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都被资本所吸纳,而反对劳动,表现为资本的属性……”[3](p92-93)这种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就是通过知识的物化(编程化)而实现的,并导致知识本身的变化:工人的技能知识被机器的物化了的知识所代替,同时,理论知识变成一种合理化的技术知识而导致大众的系统性愚昧(systematic stupidity)[1](p133)。这是无产阶级化在机器大生产时代的显要症候。
尽管斯蒂格勒在这里同样没有引述原文,但马克思的确提到工人丧失技能知识的现象,即“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7](p38)。而且,马克思也看到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而导致所有社会阶级都将被划入两大阶级,亦即同资产阶级对立的其他阶级都将沦为无产阶级。因此,斯蒂格勒说马克思描述了无产阶级化的扩展趋势是有一定依据的,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的理论关联。因为:第一,斯蒂格勒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得益于马克思自身的工艺学研究。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集中摘录了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关于机器大生产的工艺学著作,并在《哲学的贫困》中积极利用了这些材料[8](p165-169),这促使他开始从机器大工业的视角来理解资产阶级社会[9]。这意味着此时马克思对机器大生产及其“无产阶级化”的认识具有特定的历史—理论语境。第二,马克思的论述似乎的确蕴含了斯蒂格勒所说的无产阶级化,但这并不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本质认识。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产物。它在本质上反映了特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经济剥削关系。因而,“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或文化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因此,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普及化趋势是在机器大工业推动资本关系扩张的意义上而言的,而不是斯蒂格勒所说的技能知识的丧失。这其实是斯蒂格勒的技术逻辑从一开始就缺乏历史社会关系视域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主成分分析也称主分量分析,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在用统计方法研究多变量问题时,变量太多会增加计算量和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希望在进行定量分析的过程中,涉及的变量较少,得到的信息量较多。希望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数据中的大部分变量,将许多相关性很高的变量转化成彼此相互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数据中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并用以解释数据的综合性指标。本文应用SPSS软件针对表1所列15个指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以找出15个指标中的内在联系,并加以总结归纳。
总之,斯蒂格勒沿着无产阶级化线索对马克思思想文本的重构是独树一帜的,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马克思没有展开或遭遇的问题。不过,他的解读又往往遮蔽了马克思的真实思想语境和科学方法论。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世界重新审视斯蒂格勒的另类解读。
二、斯蒂格勒重读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与内在缺陷
一方面,从技术史角度来看,技术分工的确是机器产生的现实路径之一,但从技术分工角度理解机器发明的合理性仅在于它真实反映了工场手工业及其向机器大工业过渡阶段中机器形成的主导路径,而绝不是唯一的路径。因为即使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机器发明也包含科学的因素,只不过它还主要是以技艺—经验形式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尚未成为独立的力量。只是到了大工业充分发展的阶段,机器发明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技术分工的范畴,而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一般智力)。这是拘泥于分工逻辑的斯密和拜比吉等人所忽视的方面,也是尤尔等人重新揭示的理论质点。
(一)《形态》: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物质生产理论的误读
上述是对斯蒂格勒沿着无产阶级化线索重读马克思思想文本的基本理路、原初语境与内在缺陷的梳理与剖析。而斯蒂格勒重新激活马克思的最终目的在于探求超越无产阶级化的解放路径。对此,马克思《大纲》中的一般智力概念实际构成了斯蒂格勒酝酿去无产阶级化(de-proletarianization)方案的灵感源泉。
(二)《宣言》: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无产阶级概念的误读
在《宣言》中,马克思已经走出一般历史观层面而转向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科学剖析,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初步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现实境遇与历史使命。这成为斯蒂格勒重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的重要基础。
在他看来,虽然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一般智力导致无产阶级化不断加剧,但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技术)本身具有自反性和治愈性,并为克服无产阶级化现象提供了现实基础,即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建立一种共享性的力比多经济体系,从而使每个人重获知识,重新实现个体化[1](p130)。由此,斯蒂格勒批评马克思只是基于无产阶级的否定革命原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方案,甚至在《资本论》中不仅“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而且“将无产阶级状况的否定性看作一种无法超越的界限”[1](p127)。总之,斯蒂格勒基于技术的积极药理学提出了一种超越无产阶级化的客体解放方案。对此,斯蒂格勒承认自己受了维尔诺、奈格里等人的影响,但又强调自己的方案与他们有着质性区别[14]。为了辨明其中的学术关系,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维尔诺的一般智力思想。
利用稻草秸秆为主料的内置式反应堆技术能有效的提高棚内温度、地温和二氧化碳浓度,从而加快植株的生长发育,提高作物品质,亩产量提高10%以上,是设施农业生产值得推广应用的一项好技术。
(三)《大纲》:斯蒂格勒对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机器大生产理论的误读
在《大纲》中,马克思真正深入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内部,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建构起科学的机器大生产理论。而这恰恰构成了斯蒂格勒阐发机器时代的无产阶级化问题的重要理论源泉。
1978年~1993年为改革调整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为起点,农民获得了购买使用农业机械的自主权,从而改变了只有国家、集体经营农机的格局,逐步形成了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和联合、合作多种形式并存的新局面,形成了以小型机械为主的发展新格局。到1993年,河南省农机总动力达2624万千瓦,较1978年增长1.75倍,农户拥有的农机资产占社会农机总资产的92%,农户经营农机的收入占农机经营总收入的90%以上。
不过,由于斯蒂格勒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固定资本概念的双重维度(即物质存在形式[机器体系]和社会存在形式[资本关系])[10],因此,他对固定资本和一般智力的理解严重脱离了其具体历史语境和深刻理论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斯蒂格勒只从线性技术逻辑出发强调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从工具到机器体系的发展构成了理解无产阶级化问题的基础。其实在同一段文字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3](p92)这表明,马克思绝不是单从技术角度来理解机器体系,而是深刻指出机器体系作为适应资本要求的劳动资料在本质上是由特定的资本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它是资本的特定存在形式即固定资本。第二,斯蒂格勒从“编程化”角度解读机器大生产的思路只是对上述那条技术逻辑的延伸,其中的人类姿势的分离与再生产对应于技术—身体维度,而智力知识的分析与综合则对应于技术—知识维度。在笔者看来,前者正是从斯密到拜比吉的技术分工逻辑的继续,同时也是马克思在《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受斯密和拜比吉的影响而持有的主导思路[11]。后者则代表了科学知识(一般智力)对机器发明所起的突出作用。这是此时马克思受尤尔的影响在理解机器大工业方面所获得的重要认识,也是斯蒂格勒得以重释马克思的隐性理论支点。但实际上,斯蒂格勒并没有对这两个层面做出严格区分,而是笼统地划归为人的编程化。这种抽象理解使他严重偏离了真实的历史现实:
为了真正辨识斯蒂格勒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我们在深度耕犁马克思的核心文本过程中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斯蒂格勒得以遭遇和重读马克思的理论依据和原初语境是什么?二是斯蒂格勒在何种意义上遮蔽和误读了马克思的本真思想与科学方法?实际上,由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理论视域和研究主题有所不同,因此,斯蒂格勒重读马克思的思想语境和关注内容也随之不同。而这恰恰是斯蒂格勒在解读过程中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潜在问题。
围绕提升行业能力,水利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稳定增长的水利投入机制初步建立,省级安排水利财政专项资金37.75亿元,比2010年增长78.07%。大中型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进入收官阶段,省重点调度的212个大中型水管单位人员经费落实率达99%。在研水利科技项目150项,24项先进实用技术(产品)得到宣传推广。“金水工程”一期项目基本完成,省级水利数据中心一期和联网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即将上线试运行。县级专职水政监察队伍全面建立,90%以上市县实行了水利综合执法。
三、超越无产阶级化:斯蒂格勒、维尔诺与马克思的不同方案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形态》中基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首次科学阐发了他的物质生产理论。这也实际构成了斯蒂格勒从一般层面将人的外化与物质生产进行创造性嫁接的内在逻辑支撑。具体来说,斯蒂格勒从外化角度解读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的着眼点就在于“人创造自己的生产工具”。因为它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又是人的个体化生存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他将物质生产直接看作人为选择过程,以表明人的主体活动不同于自然选择。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2](p540)。他只关注了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生产力维度,却严重忽视了与生产力构成内在矛盾的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其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就基于科学实践观确立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到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交往形式,而现实的个人则受一定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的制约;在根本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构成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可见,马克思深刻阐明了个人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关系[4](p439),而斯蒂格勒却对此视而不见。譬如,在他援引的同一段文字中明确写着:“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2](p520)而他却只摘取了“个人与他们的生产相一致”[1](p131)的词句。这表明斯蒂格勒还看不到人的主体性外化过程是在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具体地历史地展开的。而这种线性技术逻辑同样体现在他对《形态》的无产阶级化解读中,即人在物质生产(外化)过程中丧失了知识。不过,斯蒂格勒没有给出明确的文本引证,唯一可能的文本依据应该是马克思关于分工和机器造成工人片面发展的描述。但马克思对分工和机器的这种否定理解只是基于斯密的分工理论而确立的暂时性认识[5],只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表征的阶段性认识[6]。总之,斯蒂格勒基于线性技术逻辑对《形态》的重构在一般历史观层面上遮蔽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的双重维度及其内在矛盾特性,这也决定了他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的科学视域。
还有哪个,是宝玉和香娭毑。二狗伢接着说,我看见他们两个偷偷进了这碾屋,就把门从外面搭上了,他们谁也跑不了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单纯的技术史线索并没有完整展现真实的历史过程,作为英国工业革命亲历者的尤尔早在1835年就清楚认识到,科学的工业应用并不来自科学本身,而是资本招募科学镇压工人、提高生产率的结果[12](p368)。这一认识要比斯蒂格勒单从科学知识外化角度理解机器发明来得更为深刻,也构成了马克思从资本关系角度理解科学知识的社会历史作用的重要依据。由此,马克思深刻指出:“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3](p99)这里,马克思明确将机器体系的技术逻辑和生产关系逻辑有机统一起来。显然,斯蒂格勒并不能理解这一点,而只是着眼于机器体系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他通过马克思看到了一般智力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但他只是从知识对劳动的疏离、对立和统治角度来理解这一状况,即工人的技能知识的丧失、理论知识的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系统性愚昧。如果撇开斯蒂格勒的独创术语而从内容来看,他的观点的确依循了马克思此时关于一般智力与劳动关系的描述。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此时的观点还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思想实验。如前所述,这是马克思受尤尔影响而从机器大工业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分析,但尚未深入研究工艺史,甚至认为“这里无须详细地研究机器体系的发展;而只要求从一般的方面考察”[3](p93)。但对照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工艺史的详细研究就会发现,他在那里获得了两个重要认识:一是科学、劳动和资本的历史辩证关系——在资本关系尚不发达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技能知识与劳动是相统一的,只是随着资本关系推动的劳动资料的发展,工具才被机器取代,科学知识才逐渐成为一种统治力量[13](p541-590);二是不仅工人不了解科学知识,而且资本家也对科学知识一无所知[13](p541)。而后者是马克思从尤尔那里获得的。这似乎确证了斯蒂格勒关于无产阶级化逐渐扩大的观点,其实不然。因为资本家不掌握科学却能招募科学为之服务的事实恰恰印证了资本关系的本质地位。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看到了经理、技术专家等新兴阶级的诞生,这意味着科学知识的独立外观不是来自技术外化的神秘力量,而是现实社会分工和资本关系共同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大纲》中对机器—工人关系的描述的确还只是居于机器大工业的视角,而这恰好适应了斯蒂格勒的技术逻辑。但由于斯蒂格勒抛弃了本质性的资本关系视角,将一般智力与劳动的关系抽象化,从而彻底偏离了真实的历史过程,同样远离了马克思的整体思想语境。
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指出,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马克思描述的一般智力控制社会生活过程的趋势已得到全面实现,但他所预言的危机和解放却没有到来[15](p100-101)。这是因为一般智力和劳动方式本身在新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智力已经越出机器体系领域进入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同时体力劳动也被非物质劳动所取代,因此一般智力对社会生活过程的控制更多地表现为它对新型活劳动(非物质劳动)的权力建构:“一般智力中的一部分必然不再体现在固定资本中,而是通过认识范式、对话展示及语言游戏等伪装而在交往互动中展现自己。”[15](p65)由此,维尔诺强调,马克思所说的基于经济危机的解放路径已经过时了,人类潜力的分享或非物质劳动的自主能力发挥将成为活劳动走向自治解放的通途。可见,维尔诺是基于一般智力的当代延伸而提出一种建立在非物质劳动之上的主体自治方案。
当今的时代是多元化的,各种思潮都在相互影响、相互碰撞,这也给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重视学生的思想和道德建设,引导他们健康成长。而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想精华,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结合新时代的特征,古为今用,找到更多的结合点,让青年学生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培养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健全完善的人格,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勇敢地承担起建设祖国的重任,真正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
表面来看,斯蒂格勒与维尔诺的确基于一般智力概念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去无产阶级化方案。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在本质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沿着单一的技术—知识逻辑走向乌托邦式的激进解放,却忽视了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之内在矛盾而提出的社会历史性解放方案。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为斯蒂格勒和维尔诺的解放思路提供理论支撑?又是在何种层面上超越他们的呢?
马克思的确认为,随着一般智力(机器体系)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就能瓦解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而为工人阶级重新占有自由时间提供坚实基础[3](p103)。这显然是一条依循技术—知识本身来寻求人类解放的逻辑。就此而言,斯蒂格勒和维尔诺的解放思路与此时的马克思有着深层的逻辑同构性。但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很快认识到只要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机器体系创造的自由时间就会转变为剩余劳动,而当资本无法在内部消化剩余劳动时,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和经济危
机[3](p103-104)。于是,上述依赖技术本身的解放思路在此后的手稿和《资本论》中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规律的探索,这正是维尔诺摒弃的那条经济危机线索,也是斯蒂格勒批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放弃去无产阶级化的原因。这表明,斯蒂格勒和维尔诺都没有理解马克思在探索资本主义客观规律与无产阶级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虽然斯蒂格勒在解读“机器论片断”时也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观点,但他只是从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使“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3](p92)的表述直接过渡到上述观点的[1](p133-134)。因此,斯蒂格勒的理解过于表面化了。一方面,马克思的这段表述本身并不够准确,因为他混淆了机器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此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劳动资料只是转移价值,劳动力创造价值。但在看到机器排斥劳动的现象之后,马克思却得出了单个劳动力创造价值的能力趋于消失的结论。这表明此时马克思还没有正确理解这种矛盾。到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劳动是全部进入生产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而机器虽然全部进入生产过程,但只有它的磨损部分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而且单件商品中机器的价值部分必然小于劳动力的价值部分[16](p366-368)。这是斯蒂格勒无法看到的层面。另一方面,斯蒂格勒看到机器对劳动的排斥造成一般利润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这只是导致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随着机器应用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将不断减少,从而在根本上减少了总资本的可变资本量。因此,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结果[17](p236-237)。这自然是斯蒂格勒所忽视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这一客观规律的分析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规律[17](p278-279),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客观的现实支撑和科学论证。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规律的探索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路径是内在统一的[11]。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又回到了阶级问题,虽然只有几段文字,但从中可以看到,他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来谈论阶级问题的[17](p1001-1002)。而这是斯蒂格勒又忽视的一个文本细节。到此为止,斯蒂格勒对马克思的批判就显得破绽百出了。
四、结语
总之,尽管斯蒂格勒力图从马克思那里汲取思想资源,但其技术哲学的构境基础却并非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在《技术与时间》中就建构起来的他性思想镜像(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基于个人本位的新人本主义、德里达的延异与药理学、胡塞尔对科学理性的现象学批判、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等)[18]。这决定了他的总体解读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真实思想语境和科学方法论视域:一方面,斯蒂格勒从人类外在化角度对技术的本体论设定将传统视域中客体性的技术与主体性的人紧密勾连在一起,从而使技术获得一种充满内在张力的主客体同构性——技术发展过程即是人的个体化过程,而外在化了的技术同时意味着人类知识的丧失(即无产阶级化)。可见,虽然斯蒂格勒是以宏大的人类历史为背景,但其实质却是一种技术人本主义。因此,他只抓住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线索,却忽视了与生产力构成内在矛盾的生产关系线索。换句话说,斯蒂格勒眼中只有技术和人,而没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尽管斯蒂格勒在其理论逻辑中忽视了生产关系,但在最终的替代性方案上却又回到生产关系上来,即劳动主体借助现代技术来建立共享性的自治组织。然而,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并不是来自社会生产总体的内在矛盾性重构,而是来自个体主体在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局部自主实践,因此,这种数字共产主义实验是无法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之,虽然斯蒂格勒的激进理论与实践隐含着根本性的逻辑纰漏和实践忧患,但他的努力却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我们必须深入挖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意蕴和当代价值,为深刻反思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时代症候提供更有效的诊断与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1]B.Stiegler.States ofShock: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M].Cambridge and Malden:Policy Press,201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5]杨乔喻.生产力概念:从斯密到马克思的思想谱系[J].哲学动态,2013(8).
[6]张福公.青年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及其哲学意义再探[J].哲学动态,2016(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张福公.论尤尔的工厂哲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J].东吴学术,2017(3).
[10]唐正东.“一般智力”的历史作用:马克思的解读视角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
[11]孙乐强.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效应[J].哲学研究,2014(3).
[12]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M].London:Charles Knight,183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张一兵,贝尔纳·斯蒂格勒,杨乔喻.技术、知识与批判——张一兵与斯蒂格勒的对话[J].江苏社会科学,2016(4).
[15]Paolo Virno.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M].New York and Los Angeles:Semiotext(e),2004.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8]张一兵.雅努斯神的双面: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构境基础——《技术与时间》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17(6).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7.005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7-0033-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度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江苏省社科基金2018年度项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工艺学笔记的翻译与研究”(18ZXC002)。
作者简介: 张福公(1990—),男,山东邹平人,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
标签:无产阶级化论文; 机器论片断论文; 一般智力论文; 工艺学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