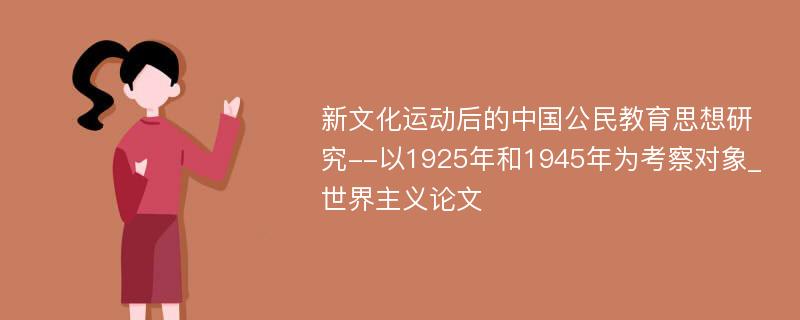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公民教育思想研究——限于1925—1945时段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时段论文,中国公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6-0094-06
1925年是中国公民教育思想发展历程的转折之年,促成这一转变发生的就是英日帝国主义无端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事件。五卅事件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列强的强权本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所希望的公理世界、大同世界等远未到来。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是中国公民教育思想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继五卅事件后,日本接连制造“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国人重新思考中国公民教育的宗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倡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开始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尚武精神、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一、尚武精神的重新提倡
甲午战后,近代思想界有感于中国积弱不振,极力倡导尚武精神。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一宗旨得到各方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被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的例证。在此情况下,中国思想界和平主义思潮兴起,尚武教育被认为不合时宜。1919年,教育调查会的建议案说:“现在欧战之后,军国民教育不合民主本意,已为世界所公认。我国教育宗旨,亦应顺应潮流有所变更。”[1](P333)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2](P92)鲁迅先生也认为德国战败是军国主义的失败,人类将从此逐步迈向人道世界。他说:“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芽滋长。我们如果问问良心,觉得一样滋长,便什么都不必忧愁;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3](P359)1925年的五卅事件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美梦,五卅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个世界仍是一个强权世界。鲁迅说:“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压迫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4](P88)五卅运动后重新兴起的尚武精神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对武德、武力的重视,对软弱无力的痛恨。著名学者雷海宗认为缺乏武德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中国自秦以后就是无兵的文化。所谓无兵的文化,并不是说没有兵,而是人们不肯当兵,当兵不被当做荣耀的事。雷海宗说:“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的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5](P101)这样就造成了民族文化中重文轻武的习尚,造成了文弱为尚的国民人格。因此,中国人的人格应由士大夫人格向大大士人格转化,也就是由重文向尚武的转化。罗家伦更提出:“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所谓强就是要有野蛮的体魄、聪明的头脑、不屈的精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尚武教育也非常重视。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时,一度以党义教育代替公民教育。济南惨案发生后,尚武教育重新被确立为教育宗旨。中华民国大学院发布公告:“以外侮日亟,非尚武不足以救国,经饬令全国专门以上学校加授军事教育,中等以下学校特别注重体育。”[6](P1239)九·一八事变后,教育部颁布命令:“全国高中以上各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初中以下各学校,一律组织童子义勇军”[7](P1267),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1938年,教育部制定的战时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建国之要素有三。一曰武力,二曰经济,三曰文化。有充备之武力而后自立自强之基础立,国家之生存得以保障。”[8](P17)为达到充备武力之目的,必须实行文武合一之教育,使人们改变观念,“认军事知能为人生应具之知能,而无歧视,造成全国军国民之精神”[8](P21)。
2.深沉勇敢之精神。崇尚勇敢是尚武精神的另一重要内容。实际上,甲午战后思想界就提出培养国人勇之精神。此时所谓的勇,主要含义有两方面:知耻、无畏。所谓知耻就是认识到中华民族所处的地位,耻而振之。中国自古就有“知耻近乎勇”的格言。所谓无畏就是无畏生死、无畏艰险。应该说,五卅事件后,国人对勇的论述既继承了早期知耻、无畏的精神,又有新的发展。相较于勇之外在形迹,人们此时更注重勇之内在精神。文学家鲁迅对勇作了当时最深刻、最好的论述。那么鲁迅对勇敢是如何理解的呢?(1)勇气与理性的结合。鲁迅说:“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的‘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3](P225-226)(2)敢于正视现实,而不沉湎于精神胜利。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3](P240)真正勇敢的民族,应该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3)韧性的战斗。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特性。这“五分热”的病态,不是仅为哪一个阶层所独有,而是中国的地方病,是全国民的耻辱。之所以有这样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五分热”病,就在于没有韧性。鲁迅说:“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4](P142-143)
3.对生命活力的崇尚。宋明理学主张静以修身。在宋明理学的强大影响下,主静戒动成为国人的信条。虽然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对其发出挑战,但影响也是昙花一现。自中日甲午战后,这种主静的观念就受到思想界的一再质疑。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就热烈呼吁:“愿中国的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3](P325)1925年,鲁迅再次抨击了这种尚静不尚动的生活态度。“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下去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4](P52)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要求焕发民族活力的愿望就更强烈。最能集中体现这一愿望的,就是这一时期人们倡导呼吁的“力的生活”。罗家伦说:“宇宙没有力如何存在?人生没有力如何生存?萎靡柔懦是人生的大敌。力是生机的表现,是自强不息的活动,是一种向上的欲望,你愿意人叫你软骨动物吗?做人不但要有物质的力,而且要有精神的力。有力方才站得住,行得开。”[9](P7)把这种力的生活阐述得最完整、提高到一种哲学审美高度的是战国策派的林同济。林同济从四个层面阐释“力”。第一,力是生命的表征,也就是说无力也就无生命。“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天地间没有‘无力’之生:无力便是死。诅力咒力的思想,危险就在这里。……诅咒愈烈愈久,其反响到生理的健康,也愈大愈深。到了最后阶段,不是不能再生,便是虽生若死。此所以人类历史上诅力的文化,命运若出一辙:不被人家格杀,自家也要僵化若尸。”[10](P114)第二,力就是动。“中国‘动’字从力,是大有意义的。一切的‘生’都要‘动’,一切的‘动’都由于‘力’。……动是力的运用,就好像力是生的本体一样。生、力、动三字可说是三位一体的宇宙神秘连环。”[10](P115)第三,力就是战斗。林同济说:“我们回想先民筚路蓝缕、启发山林的当年,每一个‘动’都是一个‘战’,一个‘斗’——与天时斗、与地利斗、与猛兽斗、与四邻的民族斗。在这种不断的战斗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想像得出,最重大可歌可泣的事情就是胜利、成功;最必须最可贵的本领就是勇敢。而我们的功字、胜字、勇字都是从力,我们便大可以看出先民对‘力’的态度如何了。反而观之,劣字从少从力。‘少力为劣’——是一个直截了当不枝不节的‘训词’,十足地流露出我们先民在当年‘如日初升’时代所抱有的一种天然的焕发襟怀。”[10](P115-116)第四,力是客观存在,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林同济说:“德是价值论上的一个‘应当有’。力是宇宙间万有所‘必定有’、‘必须有’!只要大家不太顽固,大家便不难恍然会悟:‘美之为美,不在其为大家公认的经典式。即使惹人怒、刺人眼,美还是美。’”[10](P119)
二、民族主义的高涨
甲午战后,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有否民族主义被视做是民族能否生存的关键。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民族主义被当做狭隘过时的主张,世界主义一时被思想界崇奉为圭臬。所谓世界主义,也就是认为人认同的目标不应该是国家、民族,而是人类。鲁迅曾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11](P192)周作人也是世界主义的热烈提倡者。周作人说:“如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都不过是一种偶像。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人类里边有皮色不同、习俗不同的支派,正与国家地方家族里有生理、心理不同的分子一样,不是可以认为异类的铁证。我想这各种界线的起因,是由于利害的关系,与神秘的生命上的联络的感情,从前的人认为非损人不能利己,所以连合关系密切的人组织一个攻守同盟;现在知道了人类原是利害相共的,并不限定一族一国,而且利已利人,原只是一件事情,这个攻守同盟便变成了人类对自然的问题了。从前的人从部落时代的‘图腾’思想,引伸到近代的民族观念,这中间都含有血脉的关系;现在又推上去,认定大家都是从‘人’这一个图腾出来的,虽然后来住在各处,异言异服,觉得有点隔膜,其实原是同宗。这样的大人类主义,正是感情与理性的调和的出产物。”[12](P22)
对于这种世界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有人提出异议。孙中山先生就对世界主义不以为然。孙中山认为处在当时的时代,民族主义仍是民族求生存的基础。世界主义是列强变相的侵略主义。“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13](P223)即使世界主义价值上有可取之处,也必须先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再谈世界主义。然而由于风尚所至,孙中山的这种主张在当时的思想界处于边缘地位。五卅事件后,中国的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更是达到高潮。张君劢说:“世界是否有大同之一日之不可得而知也。在今日言之,民族国家实为各民族之最高组织,有之则存,无之则亡。”[14](P68)相较于此前的民族主义,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有显著特点:
1.强调民族的自尊自信。近代中国,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由于国家对外屡次失败,所以很多人思想上即觉得中国万事不如人,丧失民族自尊自信,形成民族虚无主义。九·一八事变后,要求树立民族自尊自信的呼声高涨,连一贯以揭露国民精神病态为己任的鲁迅,也强调树立民族的自信力。鲁迅认为,中国人虽有他信、自欺等弱点,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失去自信。“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15](P118)这一时期,人们之所以异常重视树立民族自尊自信心是因为民族自尊自信是民族生存意志的基础,是民族自救振兴的基础。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在《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一文中说:“一个人,如果倒了志,失掉了自信力,自己看不起自己,觉得前途绝对没有希望,必定自暴自弃,萎靡不振……反之立志向上,自尊自重,认为前途不可限量的人,他的人生观必定是积极的,他的精神必定是奋发的……一个民族也复如此。请看长久的人类历史,哪个国家不经过强弱?哪个民族没有过盛衰?但是有些国家可以转弱为强,有些民族可以转衰为盛,当然也有些国家或民族,终至于受淘汰。这其中,人家‘虽曰天命’,我说‘岂非人事哉!’。所谓人事,即是要看该民族是否奋发有为,百折不挠地力求上进;换言之,也就是要看该民族有否自信力。有了自信力,亡可以复兴,弱可以转强,衰可以转盛;否则,只有开始于萎靡,沦落于奴隶,终至于灭亡。”[16](P158-159)
虽然在树立民族自信心上,思想界有一致的意见。但对如何树立民族自信心,思想界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民族自信心,应该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张君劢说:“凡为一国之人民,应当尊重其祖国固有之文化……要知一国之人,不尊重本国文化,不相信自己的思想家,便等于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不相信自己,则不能为人。岂有一国人民,不尊重自己文化而可以立国的。”[17](P97)一种意见认为,民族自信心应该建立在民族自省的基础上。这一派仍认为传统文化罪孽深重,必须反省。胡适说:“可靠的民族自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的祖宗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18](P269)
2.重塑民族新精神。无人能够否认新文化运动对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五卅事件后,理性评估传统文化的声音逐渐高涨起来。在抗战前夕,更兴起所谓的新启蒙运动。总之,人们希望在重新评估传统文化和吸收其他优秀文明的基础上,重建新文化,塑造民族新精神,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其特点主要有二:(1)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源。如果全部舍弃传统文化,重塑民族新精神便无从谈起。其实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就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19](P211)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只是当时梁启超并没有指出哪些传统文化需要继承与发扬。这一时期,思想界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提到传统文化,首当其冲的就是宋明的心性之学。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心性之学就被很多人作为民族积弱的罪魁。对此,有人指出心性之学不是宋朝以来民族积弱的罪魁,政治措施才是根源所在。心性之学不仅不能承担民族积弱的责任,而且其存在有坚固的基础。张君劢说:“吾以为吾国之心性学自有其至强之根据而不易动摇者矣。治此学者,修之于一身,一身有心安理得之乐。施之于一方,则一方之学者受其熏陶而社会风尚为之丕变。及夫国运凌替,则必有忠义愤发之士,或奔走国事,或隐居高蹈,以存士可杀不可辱之精神。如是,心性之学非空谈,盖亦明矣。”[17](P31-32)
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对一些传统道德观念的继承与发扬。因此,忠、孝、节、三纲之观念都被重新阐释。忠历来被解释为忠君,因而自甲午战争以后,就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事实上,孙中山早就提出以忠于国家、民族来解释忠。也有人以忠于人、忠于事来解释忠。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忠的观念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林同济指出,在以全体化国力为竞争单位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国家有机体的一分子,个个人民都要成为公民。大政治世界上公德比私德更重要。公德中最重要的就是忠。“一切的政治德行之中,忠为第一。所谓忠者,不是古代忠于君或忠于朋友的忠。忠于君或忠于朋友的忠不免含有五分私德意。大政治时代的忠,绝对忠于国。唯其人人能绝对忠,然后可化个个国民之力而成为全体化的国力。忠是国力形成的基础,形成的先决条件。……现代国家的组织,就是根基于此纯政治的德行——忠——而建立,而运用,而维持,而发展的。换言之,就是忠为百行先。”[10](P71)
因为提倡忠,所以就不得不非孝。因为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孝为百行先”。这一时期的非孝与五四时期的非孝不同。五四时期非孝主要是以个人解放、个性解放为目的。这一时期的非孝主要着眼于孝与忠的冲突,也就是孝于父母与忠于国家的冲突。这一时期的思想界认为孝与忠的冲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对小团体的忠,有碍于对大团体的忠。张荫麟说:“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有一条可立的定律:对于一个团体的专心,可使这个团体的分子对于别个团体的同情之扩张成为不可能。当国命垂危、要塞迭失的时候,绾兵符的要人可以不赴疆场而回故乡省墓——这种现象,非有‘百行孝为先’和‘以孝治天下’的道德观念是不容易解释的。”[20](P34)其次,孝为百行先的观念与现代国家的价值不符。“孝为百行先,便是以孝为国民伦理的基础。……它不但以孝为百行先,它还要把孝字来解说一切人生的价值。……此于现代各国的趋向,要把一切价值纳于忠一样。孰优孰劣,是玄理上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谈。我们所要穷究的,哪一个适应于现代的生存?分明时代要求是公德,是政治德行,是忠为第一。”[10](P74)再次,以孝为百行先的结果,可能是以孝破忠。“中国重孝轻忠,便是说它以孝为先,以忠为后。孝为百行先之说,自汉以后,坚牢不拔的深入民间。而忠之一字,无形中成为次要之次要。结果,大家的心目中总认得不孝之罪大于不忠。所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逆父母者乡党不齿,而卖国者反可取得一般亲友的优容。”[10](P76)
重视气节,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新文化运动时,气节的观念也受到人们的抨击。程颐的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知被多少人当做吃人礼教的铁证。九·一八事变后,气节问题再次被提到一个新高度。曹聚仁说:“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却并不是儒家之道……‘哀莫大于心死’,假使人人以偷巧躲避为得计,那么,中国读书人都要个个变成‘汉奸’了!‘礼义廉耻’之说方兴,我愿国人注重‘耻’字,就该把‘节操’比一切都看得重些。”[21](P259-260)贺麟从哲理的高度,说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一种伦理原则,是四海皆准、百世不惑。贺麟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有普遍性的原则,并不只限于贞操一事,若单就其为伦理原则而论,恐怕是四海皆准、百世不惑的原则,我们似乎仍不能根本否认。因为人人都有其立身处世而不可夺的大节,大节一亏,人格扫地。故凡忠臣义士、烈女贞夫、英雄豪杰、矢志不二的学者,大都愿牺牲性命以保持节操,亦即所以保其人格。伊川此语之意,亦不过是孟子‘舍生取义,贫贱不能移’的另一说法。因为‘舍生取义’实即‘舍生守节’,‘贫贱不能移’实即‘贫贱或饿死不能移其节操’之意。今日很多爱国志士,宁饿死甚至宁被敌人迫害死而不失其爱国之节,可以说是都在有意无意间遵循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遗训。”[22](P192-193)
自甲午战争后,三纲观念就被人所痛批。这一时期,贺麟对三纲作出了新解释。贺麟认为,中国的道德观念由五伦发展到三纲,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因为五伦是相对的,三纲是绝对的。“相对关系可以造成社会基础不稳,变乱随时发生。”[22](P59)另外,三纲不是要人做君主、丈夫、父亲个人的奴隶。“完全是对名分,对理尽忠。”[22](P59)它背后的道德内涵是:“不论对方的生死离合,不管对方的智愚贤不肖,我总是应绝对守我自己的位分,履行我自己的常德,尽我自己应尽的单方面义务。不随环境而改变,不随对方为转移。”[22](P59)
重新解释过去,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这一时期,思想界之所以重新阐释忠、孝、节、三纲之观念,当然与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空前生存危机息息相关。他们绝不是在重新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而是希望把这种绝对的道德观念转移到民族、国家身上。
这一时期,思想界虽然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教条主义、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合理主张,也予以继承。这主要表现在对西洋优秀文明的吸收。当时思想界最看重的西洋精神有三:一是自由精神。张君劢说:“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民族今后政治学艺术之方向。”[14](P2)“自由学说之最大价值,在其能养成独立人格与健全公民。这一点不可磨灭之价值,可以垂诸千百年而不变。”[23](P149)二是理性。张申府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一文中说:“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24](P189)三是西方人对信仰的坚贞、热忱。当时的思想界都对中国人缺乏确信因而做事缺乏热忱表示忧虑。鲁迅说,中国人对信仰只有利用,没有确信。张君劢说:“由于平日言天事不离乎人事,因而缺少事天之诚敬,陷于信仰上之不专一。彻底言之,吾国人之心灵中有真正确信与真正诚意者,实不可多见。因其念念不忘人事之故,而所希望于宗教者,不外乎‘益寿延年’、‘有求必应’之要求;以视西方人对于上帝但求悔罪赦免者,大不同矣。西方人有此信心,故处事有诚意,社交上率直而不失其真,政治上有百折不挠之气概,视吾国人专以敷衍应酬为生者,不可同日而语。”[14](P116)正因如此,所以当时思想界有不少人希望在儒家人文精神中注入宗教精神。
3.民族主义的教育内容更加充实。中国虽然自中日甲午战争后,即大力倡导民族主义,但如何在教育中加以体现,就显得比较空洞。应该说对民族主义的提倡更多注重精神意识。九·一八事变后,就更注重在平常的教育内容中落实民族教育。一是注重民族历史教育。“灌输儿童中华民族过去伟大之事迹及伟大人物之言行,以坚定其自信力,及爱国家、爱民族之观念。”[7](P400)二是注重国难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教育部就要求各校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教育部令文说:“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横加侵略,欲雪奇耻,自非从教育入手不为功,惟各级学校课程及授课时间均有规定,若中途增加实有未便。为应目前需要起见,于课外另加临时讲演,专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6](P1266)
三、国家主义伦理观的重新兴起
所谓国家主义伦理观也就是认同国家为人类最高之团体,国家有其自身之目的,爱国是人应尽之义务与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中国有近代国家观念与爱国主义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但不同时期人们对国家的认知不同。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国家主义思潮是主流,梁启超即是国家主义的热烈提倡者。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家主义受到人们的批判,认为它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由于要求个人权利与个性解放,所以这一时期思想界主流认为国家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和实现个人权利,而不是人生之归宿。正是因为反对把国家当作最高目的,所以他们认为国家主义的爱国观是片面、绝对的。要人爱国,首先国家要可爱。“国家者,保障人民权利,谋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25](P71)九·一八事变后,国家主义伦理观重新兴起。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恐非张君劢莫属。张君劢说:“国家为民族生死与共之体,非保护个人权力之机关。”[17](P143)“国家本身,乃目的而非手段。”[18](P143)正因如此,张君劢提出:“(一)国家之存在理由在一切之上;(二)个人利益应因国家之利益而牺牲。”[17](P121)
正是把国家当作最高目的,爱国就不能是有条件的,它是一种本能、是真情的流露。王造时在《泛论爱国心》一文中说:“的确,爱国心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强有力的感情,并且是出乎人类本性的一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比较其他情绪高尚一等,因为它根本上是利他的,不是自私自利的。一个人爱国,并没有想到于自己有什么好处;若因为于自己有好处而爱国,便不是真爱国。”[16](P198)王造时认为,爱国是无条件的,不论其强弱贫富大小。“爱国心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比爱你的情人更是无条件的。你爱你的情人,有时还因为她长得好看。你爱国便不管本国是强、是弱、是富、是贫、是大、是小、是新、是旧,富强如现在的美国固有人爱,亡国如现在的高丽、印度也有人爱,恐怕爱得更厉害!同时,爱国心,在这些爱国志士看来是一种自觉的责任,不得不爱,不能不爱。”[16](P198-199)
爱国之表现就是为国尽责。相较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强调个人权利,此时人们更注重责任。罗家伦说:“从最高的道德意识来讲,责任就是权利。只有从尽责任的过程里面,才能得到充分权利的实现。”[9](P111)他又说:“一个人能够替大我尽责任,才能够实现自我。能够创造新的价值,才能够享受和扩大新的权利。权利的享受,只是尽责任的结果;若是不负责任,而固守个人权利,则保守愈久,权利的范围愈小。所以我们惟有投身于大我之中,尽人生所应尽的责任,充实自我以扩张大我,乃有真正的权利可言。不然的话,只谈人权,不尽己责,国家灭亡、民族灭亡、自己也就灭亡!”[9](P11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思想,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公民教育思想的反思,又继承了其合理部分。这表现在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空想色彩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以及民族虚无主义予以批判或抛弃,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倡导的自由与理性精神加以继承。这一时期,对公民教育思想最有益的探索,就是对树立民族自信以及重塑民族精神的提倡与探索。总之,培养造就既具民族自信又有开放精神,既有深厚民族、国家意识又不失个人自尊与独立的公民,是这一时期公民教育思想的宗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公民教育宗旨必将更显示出其意义。
收稿日期:2006-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