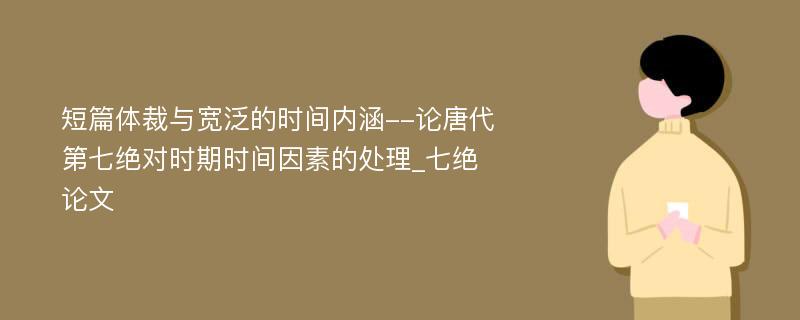
短小的体裁与较广的时间内涵——浅论唐人七绝中时间因素的处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体裁论文,短小论文,唐人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空间与时间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也是一种存在,它和一切物质形态的东西一样,同样离不开与时间、空间的联系。而诗歌,尤其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以语言、声音为媒介,诉诸听觉,擅长表现持续于时间中的全部或部分事物的运动。因此对于时间因素的处理,无疑是创造诗歌艺术境界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就七绝这种诗歌体裁而言,由于其篇幅短小,在截取时间的长度上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如何在有限的框架中,对时间因素进行艺术的处理,从而暗示、诱导读者去发现比作者给定的时间更长的一个时间过程,体验出其中所容纳的丰富的情感和生活内容,便成了七绝创作无法回避的课题。唐代的许多诗人围绕着这一课题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本文试图就此做一简要的综述和分析。
一、利用时值对比扩充时间体验的内涵。
时值就是时间的长短。对于时间的长短,人们既能够采取客观的标准去度量,也可以凭借主观的感知来体验。前者所度量的是一个表示数量概念的“物理时间”,它的标尺是恒定的;后者所体验的则是一个表示质量概念的“心理时间”,测量它的标尺,乃是人们对某一顷刻或某一时间段的延续或停顿的感觉,正如生活中所常见的那样,同样一段时间,对有些人来说是瞬息而过,而对另一些人则会觉得度之如年。如前所述,七绝能够容纳的物理时间较为有限,然而作者可以在所截取的有限的物理时间中引入人物对它的心理体验,并通过这两种不同时值的尖锐对比,使读者感到眼前的每日每时竟是如此的漫长和沉重,从而达到扩展绝句容量的目的。杜审言《赠苏书记》云:
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容赴朔边?
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
这是一首赠别诗。作者希望他的朋友苏某不要在朔边耽搁得太久,以致超过一年,完全任务后就应早点回家,因为家中的妻子每天都在怀念他。从诗中可知,对于苏某及其妻来说,分离的时间的长短是相同的,而且即使相别一年,也不能算是太长。然而诗人将这一时间分成了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两种不同的时间,苏某在朔边的燕支山下所要度过的是一段完整的物理时间,但对其妻来说,这一段完整的时间却因思恋其夫而被计日分割,所谓“红粉楼中应计日”,好似没完没了,这就造成了时值长短的对比。有意思的是,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因思恋情人而不得见面,就发出过“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感叹(见《王凤·采葛》和《郑风·子衿》),短暂一日竟如同三月之久,这当然是心理时间的一种反映。和它们相比,杜诗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其将某一特定时间分割成许许多多更小的单位来表达诗中人物的主观感知,这样,心理时间在杜诗中就不是明显地表现为好像超过物理时间的长度,而是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可感知的密度,诗人通过这种密度来引导读者去体验苏某之妻将来的那种度日如年的漫长和沉重的感觉。简言之,杜诗是以密度来表现长度,并进而以心理时间之长来和物理时间之短构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比单纯地抒发“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感叹更具艺术魅力。
唐人七绝中时值的对比,既有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对比,也有不同的物理时间的对比,究其目的,也同样是为了引导读者通过对一段较长时间的联想和体验,更深入地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这方面,可举王翰《凉州词》为例: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此诗描绘的是战士们在紧张动荡的征戍生活中开怀痛饮、尽情酣醉的一个片断。唐代的戍边战士,往往终身不调,他们长年累月地出生入死,许多与性命攸关的危险便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的心情受着压抑。而一个人遭受这种压抑越久,内心便越痛苦,越难受,便越是渴望宣泄,一旦遇到这种机会,哪怕只是片刻的工夫,也会纵性放情,将内心压抑已久的情绪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以求得一种精神上的平衡。俞陛云评曰:此“诗言玉杯盛琥珀之光,檀柱拨伊凉之调,拚取今宵沉醉,君莫笑其放浪形骸,战场高卧,但观能玉关生入者,古来有几人耶!于百死中姑纵片时之乐,语尤沉痛”。(《诗境浅说续编》)此说很有见地。因“纵片时之乐”而“醉卧沙场”的举动,正是在“百死之中”经过的人那种独特的内心宣泄。所谓“片时之乐”,言其时间极短,诗人已将其明确地标示出来,至于战士们出生入死的那些漫长的岁月,虽然没有正面言及,但在诗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暗示,明眼人不难看出。作品有意识地将这两种长短不同的时间进行明暗对照,既使“片时之乐”这一主体时间表现得更其鲜明,又能唤起读者对于另外一种漫长时间的相关联想,并通过二者的对比,从总体上揭示出长年征战的艰难危险和战士们醉卧沙场时的独特的心理状态。
二、以动态开放的结尾将短暂的过程转化为延续性状态。
七绝短小,其框架所能容纳的时间相当有限,但七绝的艺术特征又在于借有限表无限,这就要求作者设法在一个大于作品本身规定的时间段的规模上展现生活,并能为读者在阅读时造成一种诗里所容纳的时间正在不断延续的心理——艺术效果,使读者的感情在读完诗之后仍然会延续发展下去。例如鱼玄机《江陵愁望有寄》:
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
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此诗截取的是江陵愁望的一段时间,诗人言其伫立江岸,忧愁满杯,眺望远方,只见江桥掩映于枫林之中,虽然已是暮色时分,却仍不见那人乘船归来。事情再往后发展,其逻辑结果应是诗人失望而归,随之江陵愁望的过程便告以终结。然而,就在这事情的发展快到限度的临界点时,诗人却将这一有限的过程转换成一种时间的延续:“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这就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眼前的事件引向了对于一种永无休歇的相思之情的关注,并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时间被无限延长了的体验。
对于时间的这种处理方式,还可举王维的《送沈子福归江东》一诗说明之: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诗人送客江边,当友人离去之际,自己顺流远望,惟两岸芳草萋萋,一片碧绿,向前不断伸展,而自己对于友人的深情厚意,也就像这遍布两岸的春色一般,紧紧伴随着他,渐行渐远……不难看出,此诗也是在送别的过程快要终结之时,从眼前的春色展开联想,将其转换成一种延续性状态的。稍有不同的是,此处对于时间延续的表现,是借助于视察空间的拓展来暗示的。
综观上面二诗,它们都成功地将一个短暂的即将终结的过程转换成了一种时间的延续,显示出七绝诗体善于以有限表无限的艺术特征。这种效果的取得,一个重要的原因,乃在于诗歌的末端均以一种动态式的开放形态出现,这就给时间的延续提供了一个不受阻拦的通道。像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刘长卿的“江春不肯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马蹄”(《送李判官之润州行营》)等,均属此类构思。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与此不同类型的诗作。岑参有《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一诗,这首七言名篇共十六句,其中第一至十二句描写热海奇景,渲染送别的环境;十三、十四两句“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写相送于天山城外,举杯痛饮,不觉酣醉,待到酒醒时分,已见夕阳落于热海之边,勾勒了送别过程中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情事;结尾二句“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说被送的崔侍御是那么威严、冷峻,连热海的炎威都要为之消减。诗人于此不再言及崔侍御是如何离开的,自己又是如何依依不舍的,而是以赞叹收结全诗,将此前延续的时间之流拦腰截断,使其仅仅限于诗歌的框架之内而无法溢出。所以读者从此诗中所感受到的时间之流是短暂的,尽管诗的篇幅要比以上几首七绝长得多。又如韩愈的七言古诗《山石》,移步换景,详记游踪,从第一天诗人“黄昏到寺”时写起,经由“夜深静卧”,直到第二天“天明独去”,漫步于山林涧水之中,搜奇览胜,其篇幅和所容纳的时间的长度,较之一般的诗歌要长得多。但此诗的结尾四句是对这段时间的游览加以概括,并就此抒发感慨,这就等于明白地宣告,这次游历的过程该结束了,对于诗中不断向前运动着的时间之流来说,它好像构成了一个阻拦外溢的堤坝,因此,读者从诗中所能体验到的时间长度,并不比诗中实际所容纳的更长一点。这两个例子从一个相反的方面启示我们,一个动态式的开放形态的结尾,对于七绝中时间延续性状态的生成,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三、选择最富于包孕性的时刻,诱导读者延长内心的时间意识。
七绝体裁短小,和长诗比起来,难以在章法上张驰相间、波澜起伏、纵横变化,但却更适宜于表现一个片断时间内的动作、情节和内心活动。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一个片刻都不是单纯的、孤立的,它无不是由过去演进而来,又向着未来发展而去,可谓“怀着未来的胚胎,压着过去的负担”(莱伯尼兹语,转引自钱钟书《读〈拉奥孔〉》),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诗人就是要根据需要,在事件和情节的演进中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时刻来进行表现。所谓最恰当,指的是它最富于包孕性,可以使读者在面对这一时刻的同时,能够借助想象,将视线投向过去或未来,延长内心的时间意识,达到对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最清楚最充分的理解。如王建《赠李愬仆射二首》(其一):
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
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
这是歌颂中唐历史上有名的淮西大捷的一首诗。诗人从雪夜长途奔袭入手,在大部队遥看火号映空、推知先锋已攻上城头这一片刻落幕,如同神龙出没,见首不见尾。所谓“火号连营赤”,“先锋已上城”,并不是战斗的最终胜利,而是趋向胜利的时刻,此时的战场气氛动人心魄,后续部队如弦上之箭,脱手即发,称得上是笔所未到而气势已吞。诗歌本身虽划然而止,但因其收尾处实际上包孕着一个从当下的酣战直到胜利终结这一未来的发展过程,可以诱导读者通过联想和想象,在自己的心中完满地实现它的未来的可能性,所以虽是短章,却仍显得悠然而长。
上面的这首诗算是“怀着未来的胚胎”,下面再看一个“压着过去的负担”的例子。元稹《得乐天书》云: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知?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此为诗人贬谪通州(今四川省达县)期间一个片断情景的描绘。瘴乡独处,孤寂凄凉,忽接远方友人来信,顿时潸然泪下,这一不同寻常的表现使妻子惊诧不已,女儿也因害怕而跟着哭了起来,妻子不禁猜测道,能够引起这种情感波澜的书信,一定是挚友白居易寄来的。此诗起得突兀,结得干脆,除了从诗题上说明妻子的猜侧是对的,作者丝毫没有涉及到这个片断情景之外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然而读者的思绪却可以超出作者的笔墨范围去追溯既往,因为诗中当下的这一刻并非是孤零零的存在,它和过去活生生地情事密不可分,并包容了从过去到现在的所有内容。如果白居易和元稹过去不曾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如果元稹夫妻俩在通州贬所不曾经常地念叨白居易,那么元稹怎么会“远信入门先有泪”,他的妻子又怎么会猜得着其中的原因呢?与其说此诗表现的是元白之间的情谊,还不如说是这种源远流长的情谊的又一次复现。通过当下这一片断中的复现,读者体会到了源远流长的过去,体会到了凡是人间真挚的情谊总是联系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包孕性时刻的选择,使得七绝诗在事实上扩大了时间的容量,获得了以少胜多的效果。试比较一组题材相似而体裁不同的作品: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廓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唐)张泌《寄人》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
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宋)晏几道《鹧鸪天》
张诗篇幅较短,晏词篇幅较长,张诗所选择的片刻,与晏词的末二句略同,但其时间的容量则等于甚至大于晏词,因为张诗所描绘的梦魂萦绕的情事,成功地暗示了过去一段较长时间内的两情相悦和别后相思,而这些大体相同的内容在晏词中却花费了较多的笔墨。当然,晏词自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本文在此只是就包孕性时刻的选择这一特定问题进行比较,并非是从整体上评价二者的优劣高下。
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人类对时间的把握从一个重要方面标志着对世界认识的深度,诗歌创作是人类对世界审美认识的一个领域,所以,对时间因素的处理技巧,在诗歌创作中是非常重要的。唐代七绝诗人就此而做的成功探索,无疑给我们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