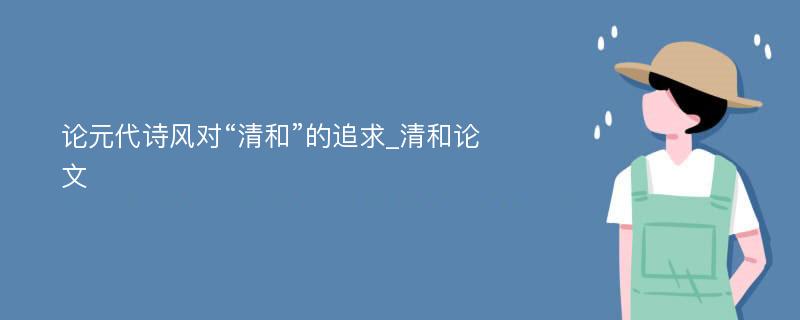
元人诗风追求“清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清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人的诗风追求是多元的。但在多元之中,也有主导性的追求与崇尚。其主导性的诗风,即一代代表性诗人的风格取向和代表性诗论家的理论主张,且在当时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元代代表性的诗人,历代论者一致认可的是元中期虞集等所谓“元诗四大家”和他们的同好,如欧阳玄等人,及其影响下的部分诗人。以他们为基点,向上追溯元代诗风的开创者,如赵孟頫、袁桷等人,向下则有他们诗风的继承者,如后期的傅若金等人。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里,诗歌史与批评史,是双线发展的,诗人与批评家是两个群体,以至于形成“作者不必善论,论者不必善作”①(清人史念祖语)的认识。但元代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元代诗人大多同时也是批评家。代表性的诗人,同时也是代表性的诗论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和诗论家,其创作风格和理论主张,影响着诗坛风气。由于元后期诗坛转向比较明显,所以本文所论涉及前、中期比较多。 20世纪研究者认为,元诗的特点是“雅正”。但略加考查就会发现,“雅正”在中国诗学中,有时用作风格概念,但却常常被作为论诗的规范、标准的概念来使用,诗求“雅正”,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诗学数千年一以贯之的追求。《诗大序》言:“雅者,正也。”郑玄《周礼·大师》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在这个意义上说,“雅正”就是典则纯正,由典则纯正而垂为后世法则。直到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在讨论选录标准时仍使用“雅正”一词,其依然有规范、标准,或合乎规范、标准之义。如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圣谕:“该总裁等,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副朕鉴古斥邪之意。”归于“雅正”则“鉴古斥邪”,雅即可鉴古,正则可斥邪。雅正虽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风格概念,但古人论诗,特别是在儒家的诗论中,不管是“雅即正”还是“雅且正”,都首先是一种定性判断,或者说是一种规范性、标准性的要求,雅则美,不雅则不美,正则善,不正则不善。于是“雅正”也就成为儒家诗论中一个千古不变的追求。这样一个概念,显然不能用来概括一个时代的诗风特点。在古代诗学风格概念中,能够代表元诗风格取向的,是清和、恬淡、平易等。而这些概念,都与雅正有密切的联系,有时候可以说表达了近似的风格取向。如果要给元代主导性诗风一个高度的概括的话,我们认为应该是“清和”。 元人论诗,尚“清”尚“和”,元人的诗美学理想,则是“至清至和”。元人追求的“清和”诗风,是“清”与“和”的融合。“清”与“和”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清”是自然的,“和”是社会的。元人的所谓“清和”,是二者的谐和统一。以下分论之。 一 尚“清”诗论 “清”是中国史诗一以贯之的追求,并非有元一代独特之崇尚。蒋寅有《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一文②,专论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清”,指出“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六朝时,其已成为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如此说来,元人尚清,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在尚深致、重才学的宋代诗学之后,元人的尚清,就给人较强烈的印象。而元人之尚清,又不是回到六朝之清。元代诗论家对“清”意趣展开性的论述,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在中国史诗上,元代对清的崇尚,是较为突出的。要说明这一点很容易。元人辛文房一部十卷本的《唐才子传》,“清”竟出现130次。“清”代表了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如果从深层次上分析元代诗学尚清的原因,一是由于元代文人与政权的关系相对比较疏离,对政治的依附关系较弱,如此倒使他们拥有充分的空间,去自由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情趣,表达自己的审美追求,于是“清”便在他们的诗文和诗文理论中强有力地反映出来。二是元代文人在失去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后,富与贵已经不属于他们,为了抗衡富与贵,展示自己的个人价值,就要充分张扬自身的文化优势,突出其人格高致,于是不管是从情趣说,还是从人格说,抑或从为人气象说,高扬文人和文化之“清”,以区别并抗衡“东华尘土”所代表的富与贵之“尘”之“俗”之“浊”,就成为文人们获取人格自尊和心理平和的必然。 (一)“清”:文人清雅离俗之格调 屈原自我人格标榜“举世皆浊我独清”(《渔父》),在古代文人中影响很大,以清洁人格抗拒浊世,成为很多文人的自觉意识。在元代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在宋元易代之初的南方,清洁自守成为由宋人元许多文人的自觉意识。元代文人普遍推崇陶渊明,多以陶渊明为人格榜样,贫困中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精神自我激励,失意与迷茫中以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适性任运相期许。诗人白珽有《山居怀林处士》诗,其中“饱看贵人面,不若饥看天”两句,颇能体现这种孤高而清洁自守的人格精神。白诗所怀林处士,即宋代著名隐士、以写梅花诗著称的“西湖居士”林逋。他所追慕的,就是林逋之“清”:人格清,情趣清,诗风也清。而诗风之清,正是其人格与情趣之清的体现。元代诗人赵文有《诗人堂记》一文,文中提出了一个“诗人”的标准,他拿这一标准评量当时诗坛,得出了一个让人颇感新异的结论:“今世诗多而人甚少。”原因就是符合诗人“清”格的人太少,只有那些“萧然山水间,无求于世,研朱点《易》,扫地焚香,庶几不失其所以为人者。”这样的人,坚守为“人”之清洁标格,“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山林介然自守之士,忍饥而长哦,抱膝而苦调”③,清洁远俗,所作诗歌,清气满纸。李存称这样的人为“清修君子”,“清修”的标准,就是摆脱世俗欲望,保持诗人所应有的灵明:“何以谓之清,又若何而修?曰:无欲为之宗。”④他们以清贫对抗富贵:贵不如官,富不如商,但“清”(清才、情趣)却唯我独有,有此信念支撑其甘居山间林下,相伴风云月露、花竹草树、琴鹤舟笻,“枯槁介特,绝不与世相婴……而独得其一绪之清思,终日累月,吟哦讽咏于泉石几榻之间”,其所作诗,如“春冰结花,尘滓都尽;秋空卓秀,一色空青”⑤。宋元之际的牟巘说,这样的诗人,其人其诗,都如山间白云,“脱鞅掌超尘坱,以与莽苍鸿蒙游方之外矣”,作诗也是“自乐其乐,内足于己,不以己徇人”。所以“其辞隽,其思清,其兴寄远,读之殊使人有凌云意”⑥。富有自然清趣。 (二)“清才”:文人自身价值的重新发现 宋元易代,文人在宋代所拥有的政治与经济优势,随天地之变一去不复返。宋代社会以文人政治为突出特色。宋代几乎所有的职位都被文人占据:“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⑦元代则是一个极度尚武轻文的时代,由宋人元,文人社会地位突然跌落,自我人生价值的认定也陷入困惑。在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人生价值观成为虚幻之后,在迷茫之中的文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生存的价值,以支撑其生活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自身价值的重新发现。当他们重新审视自身时发现,能够寻找到的可以抗衡福与贵的优势,只有才与学。于是,富有“清才”,就成了支撑文人自尊,且据以傲视无学无才的王侯贵种的最大资本。赵文就很自负地说:“宰物轻与人以富贵,重与人以清才。”⑧富贵得来易,清才得来难。按照难得者贵的逻辑,文人自然比高官、富商更有价值。 在诗人戴表元看来,诗歌“清言”,得自诗人“清能灵识”,而此“清能灵识”,与“世俗膏粱声色富贵豪华”相排斥,“使有一毫昏惫眩惑之气干之,则百骸九窍,将皆不为吾用,而何清言之有乎”?⑨人无“昏惫眩惑”,上天“纳之以清能灵识”,如此方有“清才”,能“清言”,是为诗人。既然“清才”比富贵更有价值,富有清才的文人们就自可傲视王侯。戴表元有时又称之为“清能灵解”,此“清能灵解”得自山水自然,人从山水清气中获得,“山巉水驶,风气疏爽,士大夫得之而为清能灵解”,诗人要保持这种“清能灵解”,就要排除功利之心、势利之想,作诗的目的不能是换取功名富贵,不“挟之以资身华世”,而仅仅“自适其不遇”,这是“古仁人君子隐居求志之事”⑩。 好诗要清,好的诗人一定要有“清”的精神、“清”的灵魂。其“清才”得自天地“清气”。天地“气清”如何变成“清意”之诗?诗论家刘将孙说:“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11)如此,诗就应该如风之清、雪之白、梅之洁。具体的风格容或不同(或简远,或古雅,或轻盈等),“清”则不可无。这就是所谓清气为诗说。清气为诗的观念不是元人发明,但元代诗论多有阐发。 (三)“清气”为诗说 唐代诗僧贯休说:“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12)是诗人得乾坤清气,而后发而为诗,诗成于乾坤清气。元好问引此以论诗,元氏又有诗云:“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13)乾坤清气难得,故世间真诗少,真诗人少。而宋遗民林景熙则说:“天地间唯正气不挠,故清气不浑。清气与正气合而为文,可以化今,可以传后。而诗其一也。”(14)诗是天地间正气与清气的一种体现,一种表现。一般人认为,文章(包括诗)由气而成。气有正邪清浊,文也就有正邪清浊。林景熙强调的是,只有正气、清气为诗为文,才是可以化今传后的好诗好文。清气为诗,在元代逐渐成为一代诗论家的共识。 大儒吴澄论诗,强调“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其《萧独清诗序》,是一篇古今罕见的清气为诗说专论: 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屈子《离骚》、《九歌》、《九章》、《远游》等作,可追十五国风,何哉?盖其蝉蜕污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不滓于楚俗为独清故也。陈拾遗《感寓》三十八,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超然为唐诗人第一;李翰林仙风道骨,神游八极,其诗清新俊逸,继拾遗而勃兴,未能或之先者,非以其清故?朱子论作诗,亦欲净洗肠胃间荤血腥膻而漱芳润,故曰: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万安道士萧独清诗)莹莹如冬冰,瀼瀼如秋露,湛湛如石井之泉,泠泠如松林之风。岂意道流中之有是诗也?……噫!不有是人,何以有是诗哉?故曰: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15) 文章以“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开篇,中间重申,后又强调,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开篇以“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立论,而后在历数了代表性诗人,验证其“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之认识。本文是为道士萧独清诗作序,回归本题,道士名“独清”,其诗也独清。而其诗之所以清,当然也是因为其禀赋了乾坤气清。于是做出结论:“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如此一篇之中三致意,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此“乾坤清气”,戴表元称之为“宇宙间清华奇秀之气”(16),学者黄溍称之为“宇宙间清灵秀淑之气”(17)。戴表元、吴澄、黄溍,他们的学术观点和诗学观点有诸多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使用近似的语言,表达了大致相同的主张。但细品三人的语言,还是有些差别。戴表元之“清华奇秀”,华、奇、秀,可以分别与清组成“清华”、“清奇”、“清秀”,显示了他与清有关的诗风主张;黄溍之“清灵秀淑”,灵、秀、淑也可以分别与清组成“清灵”、“清秀”、“清淑”。黄溍的“清灵”与戴表元的“清华”不同,在于虚灵与高华之别,而“清奇”与“清淑”的区别就更大:“清淑”即清和,其风格取向与“清奇”相对。吴澄只说“清气”,但从上引文字看,他有“清逸”、“清洁”等义。刘诜也以“清淑”论诗,他认为,诗人清气得自自然,“寒夜月高,万里一白,乾坤之清气,沁入肌骨”,诗人得此清气则气清、思清。要保持清淑之气,就应蝉蜕于世事之外,保持清静的心境。所以,在元人看来,方外之士往往得清气,其诗亦清。 (四)“清新”诗论 由“清”组合而成的各种风格,如清和、清远、清澹、清旷、清奇、清雄、清峭、清新、清雅、清巧、清丽、清秀、清润、清朗、清婉、清浅等等,这其中,元人最为推崇的是清和,其次则是清新。 文学史家以“清新”评六朝诗,六朝也是清新观念形成时期。唐代杜甫评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以为李白诗有庾信之清新。但盛唐诗坛,并不以清新为尚。清新成为诗坛普遍风气,是在晚唐。韦庄《题许浑诗卷》诗云:“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18)是晚唐人以“清新”评晚唐诗(这里“奇”非奇崛,乃不同凡俗之意)。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给予“清新”评价的,也基本上是晚唐诗人。方回《瀛奎律髓》评以“清新”的,也多中唐以后诗人,如说:“贾浪仙诗幽奥而清新,姚少监诗浅近而清新,张文昌诗平易而清新。”(19)宋人诗论中,“清新”使用频率已较高,但清新并非宋诗的主要特色。至元代,诗求清新,以“清新”评诗论诗,就比较普遍了。 方回的《冯伯田诗集序》,是中国诗学史上难得一见的清新专论。文章先论“清”,用博喻的方式从自然和人事等多方面对“清”做充分描述:“天无云谓之清,水无泥谓之清,风凉谓之清,月皎谓之清。一日之气夜清,四时之气秋清。空山大泽,鹤唳龙吟为清;长松茂竹,雪积露凝为清;荒迥之野笛清;寂静之室琴清。”在让人对“清”有强烈印象后接一句:“而诗人之诗,亦有所谓清焉。”这些比喻,都不是论诗,但通过联想,可以增强或丰富人们对诗“清”风韵的感受。而后转向论“新”:“清矣,又有所谓新焉。”论新,全从人生经验说:“新沐者必弹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此以旧而为新者也;古尝黍稻麻麦皆贵新,此名旧而实新者也……”这些生活经验中对“新”的认识,都可以迁移到诗学上来。上述文字,可以说是不言诗而不离诗,使人们对诗之“清”与“新”有感悟和认识。归到论诗之清新的话并不多,说: 然则诗人之诗,清而后能新,即新而后能清耶?老杜谓“清新庾开府”,并言之,未尝别言之也。非清不新,非新不清。同出而异名,此非可以体用言也。……才力之使然者为俊逸,意味之自然者为清新。可无彼,不可无此。故不同也。或又问清新之所自来,得之学乎?得之思乎?世未尝无苦学精思之士,而或不能为诗,或能为之而不能清新。(20) 方回对“清新”与“俊逸”的辨析也很有意义:“才力之使然者为俊逸,意味之自然者为清新。”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方回此文推崇“清新”,又认为“清新”与才力、苦学精思无关。这与他前期诗论的一贯主张不同。他之“清新”论,对我们从精神上把握“清新”的意义,很有参考价值。 清新诗风的倡导和实践,在元代诗史和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是元人告别宋、金遗风,形成时代诗风的转关。苏天爵评卢挚对元代诗文发展的贡献说:元初,诗坛尚沿“金、宋馀习”,诗风或粗豪(北方)或衰苶(南方)。“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21)以清新飘逸荡涤金之粗豪、宋之衰苶,是诗风转变之始。 前人批评“元诗浅”(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浅”与“清”利弊相连,浅是元诗求清带来的负面影响。诗如何才能得“清”之长避“浅”之失,元代诗论家没有理论的阐述,但他们在提倡“清”时,往往同时提倡淳、古等。清而淳,清而古,就不会流于浅,即以“淳”、“古”、“奇”救“清”之失。 二 尚“和”诗论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命题,《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能“致中和”,则天地万物各得其所,达于和谐境界。道家也主和,《老子》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和”也是贯穿中国文学史数千年的基本精神并且都对中国诗歌和诗学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 “和”的观念体现在元典注释中,有不少与我们的论题直接相关。如《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郑玄笺:“穆,和也。”即言其诗有清和之风。又《论语·八佾》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安国注:“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22)乐与哀都适度而不过分,即适中,恰到好处,是为“和”。这些经学的阐释,体现着也影响着中国的学术精神和诗学精神。“和”的精神,在中国学术史和诗学史中,无处不在。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献中,历代都有关于“和”的论述,这里不必详述。但在诗学领域,元人对“和”观念的展开论述,多是前所未有的。 (一)“贵天和”,合诗教 元代诗人曹伯启有诗云:“画名无言诗,所贵存天和。……画水有清意,凉风皱微波。”(23)所谓“天和”,即自然和顺之理,体现的是道家的主张,在《庄子》一书中累见。宋代理学家标榜“定性”,所谓定性就是定心,使心不动。理学家吸收了《庄子》的精神,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24)元代文人推崇这样的心性修养,主张不因境遇的改变破坏自己内心之“和”。按唐人韩愈“物不得其平则鸣”说,诗人处艰难困苦之中,必以诗抒其抑郁不平之气。但元代诗论家多不赞成,他们主张,诗人不管处在什么境况中,都应该心平气和(25),如此才能得诗之天趣,才能表现诗人性情之正,不失诗人之风度与雅趣,要像陶渊明那样生活,享受自己天趣之乐:“爨尾三尺,云根一泓,日陶写得天趣。宜其诗和平无暴气,清醇无险语。”(26)如此作诗,才合陶谢韦柳之正声。元末画家诗人倪瓒在《谢仲野诗序》充分阐发了这一主张,他说:“《诗》亡而为《骚》,至汉为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渊明乎?韦柳冲淡萧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则王摩诘矣。何则?富丽穷苦之词易工,幽深闲远之语难造。”他赞赏“家无瓶粟,歌诗不为愁苦无聊之言”的诗人,这样的诗,好在使读者“讽咏永日,饭瓦釜之粥麋,曝茅檐之初日,怡然不知有甲兵之尘,形骸之累也……其得于义熙者多矣。”(27)道家贵天和,与儒家诗教中正和平、温柔敦厚之宗旨相通。儒家诗教有“温柔敦厚”之旨,又有“兴观群怨”之用,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关系,两者是否矛盾呢?唐人孔颖达对“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的解释,为元代诗论家所重视,所借鉴。孔颖达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其核心意思是,讽谏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色温性和,“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依违”者不直言,“不指切”,即不指责,用委婉的方式,让听者感悟且乐于接受,这就是所谓“温柔敦厚”。许有壬说:“诗人为教,则主于温柔而敦厚也,故必婉其意而微其辞,奖其善以辅其不及,使告者无失言之累,听者有悦怿之美。”(28)“诗人为教”,是就诗的功用而言。这种理论,关注的是教化效果,而非诗的抒情本质。 (二)“太和”之气发于声而为诗 元人以为,诗之所以“清”,是乾坤清气所成。同样,诗之所以“和”,是由于天地之气太和,人禀太和之气,发而为诗,声和诗和,是为极盛之诗。所谓太和之气,乃天地间冲和之气。“太和”是最高的和谐。《周易·乾卦》之用九《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体现了《乾》卦元、亨、利、贞的德行。太和之气,成太和之乐。按古人的理解,“天地之气太和”只在盛世,故由此推论,“太和之气”所发,是盛世之音。正如虞集所言:“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29)大儒吴澄为著名道士、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作《吴闲闲宗师诗序》,说:“天地之气太和,而声寓于器,是为极盛之乐。人之气太和而声发乎情,是为极盛之诗。”他形容道教大宗师吴全节之诗“如风雷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特别是当此大元盛世,“遭逢圣时,涵泳变化,其气益昌,太和磅礴”,“固非寒陋困悴、拂郁愤闷者之所可同也”(30)。吴澄连用四个比喻形容吴全节之诗,需要注意的是,四个比喻,体现的并不全是温润柔和的风格,“风雷振荡”之烈,“长江大河”之壮,也都被纳入“和”的风格范畴。这提示我们,元人所说的“和”,不仅仅是平和、温和,“和”应作更本质的理解。学者任士林则以“元气”之“和”称元代之诗,说在宋、金南北分裂而后,“今天下一家,元气浑合,大声洋洋,朝廷之上,躬行古人,而右文之治,四海风被。山林之远,时及睹播告之修,纪载之作,咏歌之章,浑然典谟之温润,风雅之清扬。”不管朝廷之上还是山林之远,诗文都体现了“元气之合”带来的“浑厚以和”,体现在他的朋友邓文原(字善之),其诗“浑厚以和,沉潜以润,如清球在县,明珠在乘。信涵养之深而持守之纯也。……盛古之风,躬行之治,历数千百年而后振乎?”(31) (三)“充养有道”则诗和 宋代理学家重人格修养,在他们看来,人之为学,就是学为圣人。士希贤,贤希圣,以圣人之学涵养成圣贤气象。所谓“圣贤气象”,如程颐对其兄程颢形象的描述:“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32)这样的大儒,因“充养有道”而和气充盈。如此有道之士,诗也“和而不流”。到元代,这种人格修养论对诗学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影响。元代诗论家认为,有道者诗“和”,有德者诗“和”,“和”与人格修养的关系极其密切。元人陈旅认为,上古之诗,世德淳,故风雅颂都体现了“和”的精神。后世德衰,诗味薄调下,不“和”。大元有“淳庞大雅之风”,为恢复“和”提供了时代条件,而他的友人周权(号此山)充养有道,故“其言之蔼如也”。一般人的诗,随其所遇而变化,但总有一偏之失,不能归之于“和”:“夫志得意满者,其辞骄以淫;穷而无所遇者,其辞郁以愤;高蹈而长往者,其辞放以傲。”只有那些充养有道,德盛仁熟者,养成圣贤气象,其诗才能“简澹和平,无郁愤放傲之色”。这样的诗人“可谓有温柔敦厚之德矣”(33)。有德者,其诗永远不失其和平,个人的穷通、荣辱都不碍于诗之和。元人尽管多敬仰欧阳修,但对他“诗穷而后工”的说法极不赞成,许有壬就说:“穷而工者,多怨悴无聊之语。虽强自宽释,犹贱丈夫忍怒,形色有不可揜者。”他赞赏的是“萤窗雪屋,残釭独坐。山庄野馆,风晨雨夜,他人有不胜荒寒凄楚之态”,充养有道者“目之所遇,心之所触,形之歌咏,冲融萧散,无一毫抑郁不平之气”。(34)如此才可钦可敬。今人对这样理论不会赞同,甚至难以理解。今人一般认为,诗歌是诗人真实感情的自然抒发,诗贵情真。但元人的理论自有其合理处,宋元之际的刘辰翁说:“夫阴阳寒暑,雷霆风雨,以致于沸腾压溺之变,何所不有?而不足以易吾性之所存。是谓彼乱而我治。由其治,则虽天地待我而正,万物待我而生。”(35)“我”的人格力量,“我”之“治”而不乱,可以影响自然,可以影响社会,可以影响天地。“我”正则天地正。照此理解,这种不随世变而改其“中和”,倒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诗学主张。 (四)“气完”则诗和 孟子的养气说在宋元时期影响很大。在元代,养气说也是通过人格修养论进而影响诗学理论的。如果说“充养有道”是以圣学之理养其心,“气完”说则是养其浩然之气,志定气完,气完而后声和,声和诗和。理论上虽有理、气之别,但殊途可以同归,不管是因“理充”而诗和,还是因“气完”而诗和,最后达到诗之“和”,其归则一。元释圆至《庐山游集序》就说:“夫所谓言者,气志之形容尔。浩然溢乎中,沛然发于外,不可欺也。孟子善养气,故其言铿横磬辨,肆出不慑。而《礼》称:风之哀乐,亦由其志和怨。”人之言(诗文),是其气与志的表现。释圆至在这篇序中,介绍他两位朋友的经历,以此验证气完诗和的理论。两位朋友从钱塘到庐山来游,道途作诗数十篇,这些诗“宽恬清平,壮浪豪快,泰然如得意者。”但他见到这两个人时,两人却十分狼狈,“柴肩木项,穴衣苞屦,貌服丧其常度。”圆至感到很奇怪,也很意外。原来两人遇到了强盗,脱难而来:“舟覆于盗,仅脱者身耳”。身狼狈而言泰然,全得力于两人善养其气,“冲涛波,犯寇敚,漂沈颠陨,濒死而后济,其困且劳如是。使无所养者居之,方戚戚相叹泣不暇,何暇为赋咏谈笑,取无憀之乐?而二君曾不少动其志,有哀思怗懘悔沮之言,则其所养又可知矣。”(36)与释园至此说极其近似的,还有文章家袁桷《题闵思齐诗卷》,袁桷表彰闵思齐诗“冲澹流丽,亹亹仿唐人风度。寄兴整雅,将骎骎乎陶韦之畦町矣。”之所以能如此,关键在于闵思齐“气完体充,不以沮折为可挠”,故其诗“和平多而凄怨少”(37)。 (五)“当怒而怒,怒亦和也” 上文所引吴澄《吴闲闲宗师诗序》,将“如风雷振荡”、“如长江大河”之诗,都纳入“和”的风格范畴。这提示我们,“和”并不等于温润柔婉。而诗学批评家刘辰翁则有“当怒而怒,怒亦和也”之论,他说: 人知喜与乐之为和,而不知当怒而怒,怒亦和也。非怒之为和,而和者未尝不在也。犹当哀而哀,必哀尽而后无馀憾也。……故夫大寒大暑,烈风雷雨,人知其过,不知其和。彼其倡导湮郁,开辟变化,不若是不足以有为。故在当日为过,在一岁言之亦适和耳。(38) 刘辰翁对“和”的解释,决不是他个人的臆想,这既是对《中庸》“中和”说的正确解读,也符合理学家以物付物而各得其当的精神。《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节”者,即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此即“和”。当怒不怒,不中节,便非“和”。20世纪部分研究者说元诗没有价值,认为元诗缺乏社会批判精神,没有激荡的感情。这也可能与元诗追求“和”有关。但元代诗人并非一味求温和,他们也追求诗歌感天地、动鬼神的效果,只是力求将强烈的感情藏于和易的文字与和缓的音节之下,黄溍就主张,诗文应“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藏奇于平中。宋濂描述黄溍诗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鼋鼍蛟龙,潜伏而不动,渊然之色,自不可犯。”(39)可见在元人的观念中,奇与和并不矛盾。 三 “至清至和”之诗美理想 元人的诗风追求是清和,理想的境界是“至清至和”。所谓“至”,并非极,如《大学》之“至善”,即完美境界。清不空寂,和而不流,至清至和,臻于完美理想境界,如月到中天,风来水面。元代诗论家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和描述。 (一)关于“清和” “清和”一词,首先指清和天气,即清明和暖。曹丕《槐赋》:“天清和而温润,气恬淡以安治。”白居易《朝归书寄元八》诗有句:“况当好时节,雨后清和天。”司马光《居洛初夏作》诗也用“清和”描述初夏雨后天气:“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由形容天气,迁移到形容风景风物的清新和美,如独孤及《水西馆泛舟送王员外》诗:“剧谈增惠爱,美景借清和。”苏轼《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一:“一枝风物便清和,看尽千林未觉多。”(40)由形容天气、风景风物再到形容人的性情清静平和,如《晋书·郑袤传》说郑袤“退有清和之风,进有素丝之节”。一个人神清气和,决不仅仅是性情、性格问题,还涉及到人的智慧、品行等等方面。说一个人“清和”,应该是对此人极高的赞誉,《南史·武帝上》说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外甚清和,而内怀英气”。由形容天气,到风景风物,到用于人的品藻,都与对艺术的描述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和”用于对艺术的描述,可形容声音的清越和谐,扬雄《剧秦美新》:“镜纯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声。”音乐之清和与诗文之清和,其意义应该是很接近的。所有这些,都能帮助我们体会和感悟诗学“清和”风格的意义。 “清和”出现在文学理论文献中,应以《文心雕龙》为早,其《养气》篇云:“清和其心,调畅其气。(41)此处“清和”用作动词,使神情清明和爽,与风格论无关。宋苏轼《邵茂诚诗集叙》说:“其文清和妙丽如晋、宋间人。”(42)言邵氏之文,风格清新和顺,是风格论。南宋张戒分别以韵、味、才力、义气论诗。论韵推曹植,赞美其诗“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43)苏轼、张戒使用的“清和”,与元人论诗的“清和”概念,含义已大体相同。检点元以前的文献,用“清和”论诗文者并不多。但清和之精神,在文学批评理论中是有体现的。如前已述,《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清穆即清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清奇”一品,其描述如下: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屧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这里与“清”组合的是“奇”。但品读其文,感到清气满纸,却并无“奇”的感觉。按一般的理解,诗文风格之“奇”,有瑰奇、雄奇、奇崛、奇险,以及奇逸等。但在这段文字中,绝对读不出这些义项。品其文究其义,“奇”应该是“非常”之义。文中所描述的,都是超凡出俗的非常之境,有幽,有澹,有静,这些都与“清”为同一取向。而在清幽恬淡中,显然包含着静穆之和气。也就是说,“清奇”一品所描述的,不是一般诗歌风格意义上的清奇,“清”是确定的,在“清”的总体风格之下,具体的风格感受是多样的,除清幽、清淡、清静之外,还应该有清和的境界。 总之,在宋之前,中国诗学理论中少见“清和”之论,但“清和”却一直是中国诗学追求的一种境界。 (二)“至清至和” 元代诗学“至清至和”论的代表性论者是虞集,其《天心水面亭记》以水月之至清至和,论诗之至清至和: “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风来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则不足于东,既亏则不足于西,非在天心,则何以见其全体?譬诸人心,有丝毫物欲之蔽,则无以为清;堕乎空寂则绝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趋下而不争,渟而为渊,注而为海,何意于冲突?一旦有风鼓之,则横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则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动之风,其感也微,其应也溥,涣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诸人心,拂婴于物则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过,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于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44) 古代文论中以水喻诗文者颇多,就人们印象最为深刻者说,唐代有韩愈“物不得其平则鸣”说(45),宋代则有苏轼“随物赋形”说(46)。虞集之论,与韩愈、苏轼,分别出现在唐、宋、元三代,三人又分别是三代代表性的人物,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窥得三代文学主张的变化。“不平则鸣”、“随物赋形”、“至清至和”,同以水喻文(诗),却体现了不同的文学精神,文学主张。 对于虞集的主张,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不仅主“清”主“和”,并且强调“清之至”“和之至”。如上所言,“至”并非极之义,“至”乃“理之当”,即恰到好处。月未盈与已亏,非在天心,光不满,或有所遮蔽,如人心之有物欲遮蔽而非光明澄澈,非“清之至”。“清之至”并非对清的无限追求,“堕乎空寂”是清之过而非“清之至”。“和”也如此。《周易·系辞上》言:“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圣人感而天下应,如此则天下和。虞集用此思维论诗,主张“其感也微,其应也普”,不“拂性而害物”,则诗和。但若一味求和,无所抵止,“流而忘返”,过犹不及,也非“和之至”,此为《中庸》“和而不流”之意。程颐在为其兄程颢所作行状中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之语,“宽而有制”,有利于我们理解“和而不流”:和顺而不失去节制,不随物迁移,体现为不失自我的主体精神和有节制的抒情。 “至清至和”之说并非虞集最早提出,首先使用“至清至和”者倒是宋元之际的方回。方回被认为是“江西诗派”后劲,在他集诗选、诗格、诗话为一体的诗学著作《瀛奎律髓》中,有“至清洁而无埃,至和平而不怨”之论:在该书卷二十张道洽《梅花二十首》诗后的评语中,首先阐发其“格高”“圆熟”之论,说:“夫诗莫贵于格高,不以格高为贵而专尚风韵,则必以熟为贵。”然后对张道洽梅花诗作具体评论,认为张诗是尚“风韵”的“左右逢源”圆熟一路,说:“此二十首梅诗,他人有竭气尽力而不能为之者,公谈笑而道之,如天生成,自然有此对偶,自然有此声调者,至清洁而无埃,至和平而不怨。放翁、后村亦当敛衽也。”(47)他的具体表述是“至清洁”、“至和平”,与后来的虞集稍有不同。由此我们知道,“清和”追求和表现的,不是力度美,而是风韵美。巧合的是,方回也有一篇文字,以水与月之“清”为喻论人格修养,虽未涉及诗文,但仍可作为我们理解他诗学理论的参考。他说:“泉出于地,天一生之;月出于天,日光所为。月之照物,明发于外;泉之照物,清在于内。人之方寸,其内至清,至清无欲,其外至明,则兼有夫月与水之光精者也。故月之与水,能照万物之形而已。而心之在我,则能照万物之理焉。是故君子之学,莫大于养心。”(48)诗之清之和,来自人之清之和。从这一意义上说,诗人要达到“清和”境界,其关键也“莫大于养心”,需要诗人具有不以利害得失易其心的君子人格。诗人的境遇有各种不同,就天下国家说,或盛世或乱世或衰世,个人际遇也有顺有逆,这些都会影响诗人的情感,使其心动荡。不管处逆境还是处顺境,都难以保持心之平和,于是诗也就失去其“清和”。只有修养成君子人格,才能介然自守,心不随外物所感而动。如虞集所言:“气之所禀也有盈歉,时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丧利害,休戚吉凶,有顿不相似者焉。于是处顺者则流连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婴拂,饥寒之迫,忧患之感,死丧疾威之至,则嗟痛号呼,随其意之所存,言之所发,盖有不能自揜者矣。”先儒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而“和”乃“天下之达道”(《中庸》)。那么,诗人就要力求使自己感情的表达,发而中节,不失中和,就需要控制情感,即所谓“持情”。虞集认为,控制情感的方法,有人会选择“外其身以遗世,不与物接,求生息于彝伦之外,庶几以无累焉。”也就是佛、老的出世间法。但如此就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故“亦人之所难者矣”。不具备普遍的可行性。儒家的主张,不离人之正常生活,在日用常行中修养君子人格,行于义,安于命,其心不动,就能胜外物之感: 事变之来,视乎义命而安之,则忧患利泽,举无足以动其心。则其为言也,舒迟而澹泊,暗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贵之。……澹然有馀而不堕于空寂,悠然自适而无或出于伤怛,乃若蝉蜕污浊,与世略不相干,而时和气清。即凡见闻而自足,几乎古人君子之遗意也哉!(49) 无论世事如何,更不论个人的遭际如何,仁者以义制命,私欲尽去,穷通得失,举不足以动其心,永远可以保持一身的“时和气清”。而在揭傒斯看来,“清”“和”还不仅仅是后天修养问题,“和”是“气”,“清”属“才”,“气”可后天养之,“才”则得自天份。他所表彰的诗人,是“貌粹而气和,才清而志锐”(50)。刘壎则欣赏“和平无暴气,清醇无险语”(51)的诗作;辛文房也将“清”与“和”分论,其评灵一道人诗“气质淳和,格律清畅”(52),辛文房所谓的“和”,是诗人精神风貌在诗中的表现,而“清”,则是语言声韵问题,这可能与虞集等人的“清和”论寓意不大相同。 “至清至和”是虞集为代表的元代部分诗人的诗风理想,但要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并不容易。“清和”诗风主张,在创作实践中的实际效果如何,也未必能为所有人肯定。 (三)关于“清和”的其他论述 虞集以人心和人格论“清”论“和”,他以水与月之清之和为喻,在他的观念里,“清”与“和”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清”与“和”是一致的。这是他个人的理解。但就本质而言,“清”是自然属性,“和”是社会属性。要使诗歌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完全一致,那只是诗论家的美好愿望。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虞集的老师、大儒吴澄论诗的两句话:“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53)希望情之“天真”与性之“世教”和谐地完美统一起来。这恐怕是永远都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虞集追求“至清”与“至和”的统一,从本质上说,与吴澄表达的是相同的愿望。也就是说,不管诗论家主观上如何希望“清”与“和”统一和谐,但其矛盾是客观的存在。正是体会到这种矛盾性,诗人甘复认为,就一个诗人来说,“清”与“和”很难兼得,他说: 天赋人以才,虽万亿有不同,圣人之道同也,而才不能无异焉。能清者鲜于和,和者恒不足于清也。孔子弟子游于圣人之门一也,能政事者不能言语,能言语未必能政事也。至于文章,古今作者何多也?才有不同,故各伸所长以名家。岂道之不同,识见有浅深而然哉?(54) 尽管他不明白“清”与“和”不能兼得的真正原因,但他确实认识到了这样的文学史现象和诗人各具特色的事实,也可以说,他认识到了“清”与“和”之间存在着难以兼得的矛盾性。《世说新语·文学》载:“谢公因弟子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55)谢玄(遏)所欣赏者清,谢安(谢公)所欣赏者和。这则故事从欣赏角度告诉我们,“清”与“和”是很难统一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细加分析。就创作角度说就更是如此。 宋元之际的牟巇没有运用“清和”观念,他论诗推崇“和平恬淡”。无需辨析,他所谓“和平恬淡”与“清和”的含义是极其接近的,只是“恬淡”是宋人论诗用得较多的词语,他这里其实是沿用了宋人之说。如果说“清”与“恬淡”的区别,则“恬淡”多就人的性情说,而“清”与自然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不过人恬淡之性情,多合乎自然。牟巘论诗,以和平恬淡为“诗之极致”,我们不妨认为,其论乃“清和”诗论的先声。牟巇说:“《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又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予读书至此,然后知和平者物之极致,不但声之与味为然,虽诗亦然。夫和平之词恬淡而难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声外之声,味外之味,而造夫《诗·颂》之所谓和且平者乎?故精能之至,及造和平,此乃诗之极致也。”(56) 虞集的弟子赵汸是“清和”论的支持者。他论“清和”为我们提供了两点认识:其一,揭示不清不和之病,即从反面论证诗求“清和”之必要。其二,指出“清和”乃治世之音。他先转述虞集的观点说:“大抵世有治乱,人品风俗不同,极才情则淫伤而无节,尚词藻则绮靡而失真”。“淫伤而无节”是不和,“绮靡而失真”是不清。这是不清不和之病。然后借杜甫对阴、何等的推崇,说阴、何诗清醇,符合清和诗风的要求,进一步让读者具体认识清和诗风。他对清和诗风的描述是:“和而有庄,思而有止,华不至靡,约不至陋,浅而不浮,深而能著,其音清以醇,其节舒以亮,有承平之遗风焉。”(57)从多个角度描述“和”与“清”,让读者多方面认识清和诗风。最后指出,清和是“承平遗风”。 元代主“清和”的诗人和诗论家是比较多的,只不过他们并不一定使用“清和”的概念。如黄玠论诗诗有云:“佳诗如饮泉,一寒乃清真。妙趣欲无我,宁复有袭因?……多忤言可忘,薄奉气乃醇。羲黄复何心,适当天地春。”(58)主清主和,表现了对“清和”诗风的追求,但没有出现“清和”一词。 “清和”以及“清”、“和”都有一些近似概念,其含义互有交叉互有渗透,比如清与恬淡,和与平易等等。要真正了解元人“清和”论,这些相关概念的元人论述,也必须加以梳理和讨论。元人认为,人得天地间清气则淡泊,人清诗味淡,“清”属韵而“淡”属味。元人论和还多与“平”相连,或说“和平”,或说“平和”。明清人论诗论文都力戒平,平是平板而乏波澜与曲致。元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平”是大气象,“平”是正气充实。“平”与“和”,不管指人的性情还是指诗的风格,“平”是很难达到了境界。“清和”与恬淡,与平易,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无法展开。 “清和”是元代代表性诗风,也是元代代表性诗论家的诗风追求。它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客观存在,其自身也有利弊得失。作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对于元人的主张,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赞同甚至反对,但必须了解它认识它,进而以历史的眼光客观评价它。 ①史念祖:《俞俞斋文集初集》卷二《文心雕龙书后》,台湾文海出版公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辑,影印清光绪本。 ②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③赵文:《诗人堂记》,《青山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李存:《清修斋路》,《俟庵集》卷二十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永乐刻本。 ⑤虞集:《会上人诗序》,《道园学古录》卷四十五,《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本。 ⑥牟巘:《跋厉白云诗》,《陵阳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蔡襄:《国论要目·四曰赏功实·任材》,《蔡襄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83~384页。 ⑧赵文:《王奕诗序》,《青山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戴表元:《吴僧崇古师诗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⑩戴表元:《千峰酬倡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48页。 (11)刘将孙:《彭宏济诗序》,《养吾斋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释贯休:《乾坤有清气》,《禅月集》卷二《古风杂言二十首》之四,《四部丛刊》影印宋写本。 (13)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其三,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8页。 (14)林景熙:《王修竹诗集序》,陈增杰校注《林景熙诗集校注》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3页。 (15)吴澄:《萧独清诗序》,《吴文正集》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戴表元:《送王子庆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75页。 (17)黄溍:《雪峰文集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八,《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18)韦庄:《题许浑诗卷》,《浣花集》卷三,《四部丛刊》影印明江阴朱氏刊本。 (19)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三张籍《过贾岛野居》诗后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3页。 (20)方回:《冯伯田诗集序》,《桐江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 (21)苏天爵:《书吴子高诗稿后》,《滋溪文稿》卷二十九,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495页。 (22)何晏集解、陆德明音义、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三,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68页。 (23)曹伯启:《题胡府判赵生山水卷》,《曹文贞公诗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二程文集》卷二,《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06页。 (25)揭傒斯《萧孚有诗序》:“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三,李梦生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2页) (26)刘壎:《琴泉诗稿跋》,《水云村稿》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倪瓒:《秋水轩诗序》,《清閟阁遗稿》卷十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按,义熙指陶渊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彭泽令,挂冠归隐。 (28)许有壬:《送苏伯修赴湖广参政序》,《至正集》卷三十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本,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 (29)虞集:《李仲渊诗稿序》,《道园学古录》卷六,《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本。 (30)吴澄:《吴闲闲宗师诗序》,《吴文正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任士林:《送邓善之修撰序》,《松乡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程颐:《明道先生行狀》,《二程文集》卷十二,《二程集》,第637页。 (33)陈旅:《周此山集序》,《安雅堂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许有壬:《玉渊集序》,《至正集》卷三十一,《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本。 (35)刘辰翁:《中和堂记》,《须溪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释圆至:《庐山游集序》,《牧潜集》卷四,清光绪《武林往哲遗著》本。 (37)袁桷:《题闵思齐诗卷》,《袁桷集》,李军等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714页。 (38)刘辰翁:《中和堂记》,《须溪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宋濂《金华黄先生行状》,《金华黄先生文集》附,《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40)分别见曹丕:《槐赋》,《艺文类聚》卷八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18页);白居易:《朝归书寄元八》,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38页);李之亮:《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附录卷一(巴蜀书社,2009年,第六册第77页);独孤及:《水西馆泛舟送王员外》,《毘陵集》卷三(《四部丛刊》影印亦有生斋校勘本);苏轼:《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一,《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746页)。 (41)刘勰:《文心雕龙·养气》,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370页。 (42)苏轼:《邵茂诚诗集叙》,《苏轼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页。 (43)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44)虞集:《天心水面亭记》,《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二,《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本。按“天心”、“水面”之语,有理学背景,从邵雍《清夜吟》来。邵诗云:“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45)韩愈:《送孟东野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二十,《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46)苏轼:《自论文》,《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2069页。 (47)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张道洽《梅花二十首》,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850页。 (48)方回:《月泉铭》,《桐江续集》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虞集:《杨叔能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一,《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本。 (50)揭傒斯:《送也速答儿赤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四,第311页。 (51)刘壎:《琴泉诗稿跋》,《水云村稿》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周绍良笺证《唐才子传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第483页。 (53)吴澄:《萧养蒙诗序》,《吴文正集》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甘复:《山窗馀稿·读东坡文》,《豫章丛书》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 (5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235页。 (56)牟巘:《高景仁诗稿序》,《陵阳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赵汸:《郭子章望云集序》《东山存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黄玠:《次韵孙尤实言诗》,《弁山小隐吟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