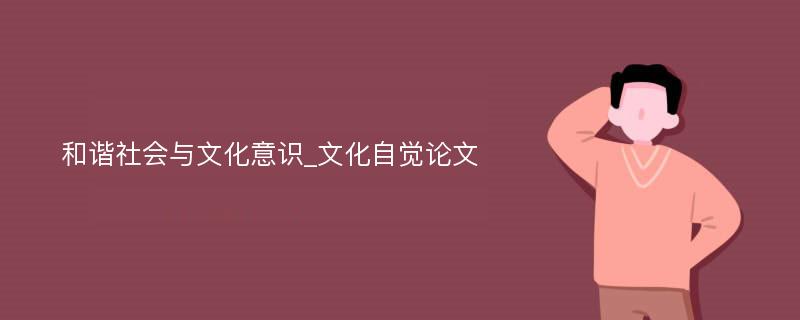
和谐社会与文化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自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6-0048-05
我们正面临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和谐社会是当今人类的普遍追求。过去大规模的社会转型都是通过战争(包括宗教战争)、暴力革命、血腥镇压来完成的,这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苦难;再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在科学高度发展,权力空前集中的今天,人类的前途只有毁灭。正如莱切尔·卡逊所指出的:今天,人类正处在走向毁灭或者美好生存的“十字路口”!
一、西方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从西方来看,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到了21世纪,这种自觉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的死亡①。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②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在这个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人类需要的是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这是对另一种全球化的期待。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
新出版的J.里夫金的《欧洲梦——欧洲梦是如何悄悄地使美国梦黯然失色的》③一书提出:我们正处在后现代与正在浮现的全球时代交叉的十字路口,处在衔接这两个时代之间断层的中间地带。他认为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帝国霸权的出现,世界已显示出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建设一个全球多极均衡,多元共生的世界。J.里夫金所谓的“美国梦”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祉;“欧洲梦”则是强调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在里夫金看来,“欧洲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持续的、保持稳定的经济的状态下,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在各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解毒剂,它承认每个人的经历和愿望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并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而地球本身最值得关怀,这就是可以将力量凝聚起来的未来的蓝图。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一切远非欧洲的现实,而只不过是一些不满现状的美国人对于欧洲想象的乌托邦,但它却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和路向,一种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这种思想和路向与我国最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正好相合。
二、和谐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指天和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易经》认为“天道”,“地道”,“人道”,三者的道理是统一的,都是乾坤的表现。“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也,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张载)。既然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天”和“人”就有一个相通的、共同的道理,所以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就是“知天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贺》),“天”的道理要由“人”来彰显。如朱熹所说:“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也就是说“人”对“天”有一种内在的责任,人不仅要“知天命”,还要“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按照“天命”行事。例如“天”有“盎然生物之心”,人就要体证“天道”,也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朱熹)。总之,“天人一体”,“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有其实现“天道”的责任,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故“天”、“人”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这样一种思维路径,不仅可以使我们走出“天人二分”(天人对立)的困境,而且也为人类走向和谐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道路。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也很重要。当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仅涉及“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而且也涉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冲突。儒家的“仁学”对于缓解冲突,造就“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孔子“仁学”的出发点,首先是亲亲、爱人,并推己及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由情感出发的,“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孝之放,爱天下之民。”“仁学”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要“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实现“仁”的准则。
其次是克己复礼。把“仁”推广到社会(全人类社会),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克服私欲)和“复礼”(复兴礼制)不是平行的两个方面,费孝通先生解释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一个人进入社会,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礼);一个国家要进入世界,也必须遵守世界的最基本的“公约”。这就是说,要克服自己的私欲,以使做人行事能符合礼仪制度规范。“仁”(爱人),是人所具有的内在品德(“性生仁”);“礼”是规范人的行为所必需的外在的礼仪制度,也包括含有强制性的权力、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等统治模式。“礼”的严苛可以用“乐”来“协调”,这就是“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春秋繁露》)。总之,“礼”的作用是以共同的规范和秩序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
“仁”和“礼”的根本价值取向都是“和”。“天地之气,莫大于和”(《淮南子》):“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以相同的事物叠加,不能得到发展,只能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归根结底,都要靠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来实现。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知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认为做人首先要“修德”(修养道德)要有关怀人类社会福祉的胸襟。“讲学”(讲究学问)不但要求自己提高智慧,而且要负起对社会进行人文教化的责任。“改过”,要能勇于改正错误,才可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以至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提倡的做人的道理,也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路径。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寿天不惑,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如果一个人能修养他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就能达到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
三、文化自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目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和谐社会都还只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梦想,一个前进的方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中,文化自觉是至为关键的一环。特别是现在,世界面临两大思潮。一种思潮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也就是要依靠美国的强大力量来统治世界,并在这个基础上,听任他们占领全球资源,覆盖多元文化,推广单一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思潮是世界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他们看到事实已证明美国的单边统治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和更多的死亡。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一种多极均衡、文化多元共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全球化,也就是中国当前提出的建设“和平世界”、“和睦邻邦”、“和谐社会”的主张。
建设“和平世界”、“和睦邻邦”、“和谐社会”,其核心是一个文化自觉问题。没有文化自觉,就谈不上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就没有“和谐社会”。什么是文化自觉呢?文化自觉指的是深刻认识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最根本的种子或基因,并为这个基因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同时将这个文化传播于世界,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建;没有文化自觉就不会有多元文化的共生,也不会有世界社会的和谐。事实已多次证明,任何想要依靠霸权覆盖或绝灭他种文化的企图都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只有各民族充分的文化自觉,才能共同建立一个和平共处,各抒所长,共同发展的世界。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主动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
要延续并发扬光大,只有种子还不行,还要创造条件,让种子开花、结果。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费孝通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机械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两个在西方分阶段发展的文明,在我们这里,却重叠在一起了。我们必须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变化。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还应该走自己的路。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面对的。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我们不能对这些秩序和准则置若罔闻,而应该自觉地精通掌握它,并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当前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
总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换句话说,文化自觉提出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展开未来,找到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任何民族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显然,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才有可能建设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的和谐社会。如果用这个坐标来衡量,我们在文化自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传统和现代的创造结合很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展开未来。文化自觉并不是“文化复归”,但是,目前这种完全‘复归’的倾向很严重,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甚至认为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路。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其次是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的取向,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此类更深层、更难解决的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成为进一步推动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再者,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以建立“和平世界”、“和睦邻邦”、“和谐社会”。只有理解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世界共同体。唯我独尊,蔑视他族文化的“大国心态”是做到这一点的最大障碍。当国家贫弱时,它会演变成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国家逐渐强盛时,它就滋生为企图覆盖他族文化的东方中心主义。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东方中心主义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覆辙,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只有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找到在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及其对世界的未来可能做出的贡献,才有可能向“和平世界”、“和睦邻邦”、“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
四、文化自觉与人类未来
如果说当前中国的文化自觉,始于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备受压抑之后,因而带有强烈的文化复兴的愿望;那么西方的文化自觉则是在数百年来作为强势文化,充分发展之后,势必更强调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和问题。这种不同是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不同的处境使然。以德、法为代表的西方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使他们对非西方文化采取了和过去迥然不同的态度。
西方学者经过深刻的审视,提出人类需要的是一个“社会世界”,即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的另一种全球化,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坚持的“和能生物,同则不继”,“少则得,多则惑”的精神是相一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期待在这样的语境中通过沟通、互补、协调、合作,也就是有些学者总结的4C精神(Communication,Complementary,Coordination,Cooperation,即沟通、互补、协调、合作)和全世界一起,开创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
注释:
①参见埃德加·莫兰:《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第1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②[英]鲍曼著,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
③Jeremy Rifkin:The European Dream-How Europe's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Quietly Eclipsing The American Dream Tarcher/Penguin,USA,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