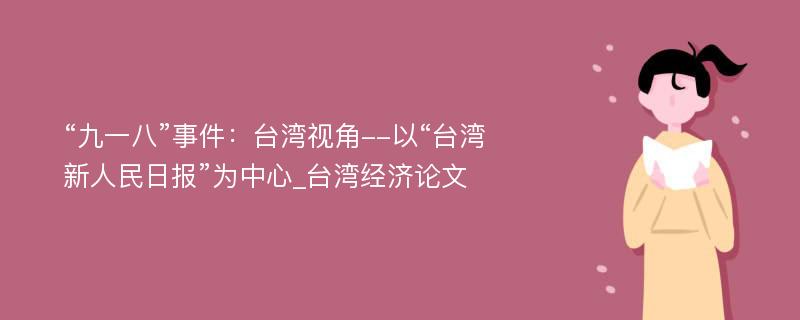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一个台湾的视角——以《台湾新民报》记事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事变论文,视角论文,九一八论文,民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举国上下愤怒声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反抗日本侵略扩张、要求收复东三省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在名份上属于“日本国民”,同时又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其对“九一八事变”如何反应?颇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在以《台南新闻》为代表的所谓“台日纸”(日人报纸)的一片“惩罚暴支”的叫嚣声中,《台湾新民报》的声音却有着相当的不同。《台湾新民报》是由台湾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报纸,被称为台湾民族运动的喉舌,它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台湾人的声音。分析《台湾新民报》对“九一八事变”的相关记事,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台湾民众心态,并提供从台湾看这一问题的新的视角。
《台湾新民报》对事变原因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当时的舆论中普遍关注的是日本军部及关东军是否违背政府的政策独断行事,以及事变的发生究竟是中国军队的挑衅抑或是日本军队之蓄谋而为;日本政府即宣称他们的行动“纯属自卫”,1931年10月26日,若摫阁发表的《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则诬陷中国“收回国权运动渐趋极端”,破坏了日本国民的“生存权益”。(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事实究竟如何?《台湾新民报》在有关“九一八事变”的首篇报道《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中就揭示说,事变是由日本军部势力一手策划的(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9月26日,第2版。),并且对军人势力的恶性膨胀及其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代天征伐暴虐无道的口号,在日俄战争当时听过一次了。”“对这回的满州事件,军人们口中仍唱卖着三十年前一样的旧东西。”“原来新时代的思潮,还奔流不到超然乎时势的老军阀社会里头!”他们紧接着就此发表评论说:“国际间有两位始终对方着的权威者,一名强权,一名公理。”“公里是以抑强扶弱为信条,可是力量不足,徒被强权笑为迂腐!”对日本军阀的肆意妄为表示极大的愤慨。(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9月26日,第2版。)
然而,《台湾新民报》的分析并不只浮于表面现象,它更注重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面来看问题。题为《满蒙的特殊权益是什么?》一文以大量翔实的资料披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事实,指出所谓“满洲事件”的爆发其实是日本在华经济利益驱使使然。
日本之进出于满蒙,系自日俄战争起,迄今凡二十六年。以铁道政策为中心,实行开矿山,采原料,积极移民。现时在满蒙日侨日本人二十二万余,朝鲜人八十余万。其总投资额十四亿元,约占全总额(二十亿)百分之七十五。据日本所指满蒙的范围,包括辽宁,吉林,黑龙,热河四省。总面积七万四十余方里,约有日本国土的三倍。现人口仅三千万,尚有收容七千五百万人的余地。工业要素的铁,煤等殆近于无尽藏。日本人所经营的抚顺煤矿,埋藏量有九万万吨。鞍山铁矿的埋藏量三万万吨,占全中国铁的埋藏最三分之一,日人投下二千八百万元的资本在经营的。主要农产物的大豆仅大连一地每年约输出二百七十五万吨以上,利权为三井财阀所独占。凑上其他农产物和蓄产物的输出,每年达二万万海关两。如上所述地大物博的满蒙特殊权益的内容,继承俄国的有关东州租借权,长春以南的干支线及其附属财产诸权,属于铁道及为便利铁道经营之煤矿,一“基罗米突”得屯驻铁道守备兵十五名,中立地带的设定等。其他如满铁的营口支线敷设权,抚顺及烟台煤炭的采矿权,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等地开设商阜地置日本领事馆,定间岛为什居区域,铁道敷设商议权,等不遑一一枚举。尚有当欧战时日本与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所关的关东州及南满路租借期限延长为九十九年,或土地商租权,或自由居住权等是中国向来所不承认的。后来东北交通委员会成立,定来满铁包围铁道网的计划,以致南满路营业不振。综合以上情形,也可以明白这回的满洲事件,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24日,第7版。)
已有的研究表明,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基本确立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优势地位,东三省成为日本重要的原料来源地,商品倾销地及资本输出场所。1930年,日本64%的煤炭,46%的铁及76%的大豆均来自中国东三省,其70%的对外投资也集中在中国东北。(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日本还将中国东北视作日本解决人口问题实施移民的理想地。为此,军国主义分子、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即积极鼓吹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日本国会议员松冈洋右更抛出满蒙生命线论,他叫嚣:“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存亡的问题,(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想到在满蒙有许多同胞侨居和巨额的投资,还有用鲜血写成的历史关系”,日本对满蒙生命线“要牢牢确保和死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正是看到这一点,《台湾新民报》在《经济界周间情势》一栏中,即明确指出:“日华两军冲突形势不稳,波及财界的影响激(极)大,同种的东洋人为什么原因而起冲突。不消说是为着经济的关系,利害冲突为其动机。”(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9月26日,第6版。)显然,《台湾新民报》刊载的分析文章正是把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经济利益实质之所在,切中了要害,这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性思考“九一八事变”成因的方向。
《台湾新民报》对“九一八事变”影响台湾的相关记述
“九一八事变”前的台湾,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岛内经济亦陷入了一片低迷之中,《台湾新民报》曾经在一篇社论中描述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情形:“米价贱落,税金及其他费用无从节省,业户佃家所入不供所出,农村疲弊渐次趋于深刻了,民众消费力大减,各工场呈出生产过剩的现象。事业缩小,惹起大批劳工的失业。商人们顾客日稀,经营困难,市况陷入萧条不振的状态。智识阶级的青年学子,一出校门,即被编入失职队里。徘徊流浪,终是找不见有谋生的出路。如上所述农工商学无论那一界,都已经到壅壅不通的穷境。”(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10日,第2版。)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无疑给本来就陷于困境的台湾经济雪上加霜,《台湾新民报》指出:“此(按指“九一八事变”)对台湾经济界定是不能免其打击的,例如米谷价,芭蕉价,株价以及地价都跌落到底。勿论农工商各界都受了很大的打击,就中最深刻的不消说是农村经济界,不论大小地主都莫不受着很大的打击。”(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3日,第2版。)米价低落是当时困扰着台湾农村经济的重大问题,以台北地区的米价为例,1930年蓬莱米价为每公斗1.40元台币(战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处统计数字),到了“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骤然跌落到每公斗0.95元,跌幅近30%,这也是台北米价自19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农民及中小地主的利益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处编:《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第916页。)就“九一八事变”前后米价问题带给台湾农村的窘境,《台湾新民报》作了详尽披露:“三年前的米价,在来米每千斤五十元左右,所以若是年一千石收入的地主,其收入就有五千元,然而税金一石大约一元,结局要千元的税金;然而一到现时在来米已经贱到二十五元,故其收入仅有二千五百元而已,就中税金依然是要扣除一千元,其余所残剩的仅仅一千五百元而已。在这阶级的人们,假使有一万元的借金,便断不能支持其生活了。”(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处编:《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第916页。)米价的暴跌虽有其他因素在内,如1929年以来的经济萧条余波等,但“九一八事变”的冲击不可否认也是一大原因,由于战时经济管制的加强,台湾米谷外销大受冲击,输日大米数额在1930、1931连续两年创下台湾自1922年来的最低水平,1931年输往其他地区的大米量更是锐减至仅为1927年的13%,比次低年份的1930年还要少50%以上,这对高度外向型的台湾农业不免影响至深。《台湾新民报》在一篇短评中论及台湾农村经济状况时即写道:“台湾的经济困难之程度,已无须赘言,就中尤其是以农产物的收入为生活资源的台湾人的苦况最为厉害。一年所收除纳公课税金而外,所剩的已不足维持寻常的生活……这回无端又遇日华的时局激变,本在低廉的米价又再惨跌,而既陷在营最低限度的生活的同胞们,似乎已经无从再努力把生活程度降低,所以此后对此困穷的经济生活,须要用心考虑其对策了。”(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9月26日,第2版。)农民收入水平的降低,一方面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另一方面由于农民们无法投入扩大再生产,更加剧了农村经济的凋蔽,此一状况直至1935年方见改观。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活动,日本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受到极大的打击,这就势必波及同样被视为日货的台湾商品。《台湾新民报》称:“台湾与对岸因有种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其影响的表现比较的迟钝而且轻微,然而倘再经过时日,排日运动更进于深刻化的时候,虽是台湾亦难免其影响之浩大了。”(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24日,第6版。)果然不出所料,台湾对外贸易很快就受到了影响,该报援引台湾税关报告云:“至(1931)十月末的台湾对外贸易,受着景气不佳和满洲问题影响不少”,预计当年对外贸易总额将“减少五千万元以上”。(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1月7日,第6版。)事实表明,在此期间台湾对大陆贸易额便从1929年的5062万日元,降至1930年的3419万日元,“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剧减到2561万日元,仅仅是三年前的一半。(注:林仁川,黄福才:《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2页。)1931年11月7日的《台湾新民报》以《满洲纷纠问题影响到台湾来了》的大标题报道了新竹大批依赖制作纸帽为生的台湾人,因“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对日经济制裁导致外销受阻,外销商不愿收购而引出“大批的女工失职,彷徨在饥寒线上”,《台湾新民报》为此忧心忡忡地说:“新竹市内(制帽女工)至少也有六七千人。在中产以下的家庭,对纸帽工金要算是总收入中的一重要部分,甚至有全家生计赖此维持的。今后如果长久继续这种状态,当然是会惹起社会上的重大问题,断不是能够轻轻和商况之盛衰一样看过的。”(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1月7日,第5版。)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虽然发生在中国的东北,但给远在东南海上的台湾也带来波澜,台湾社会经济无论从对外贸易到农村经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外贸的阻滞,米价的惨跌,开始波及台湾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台湾人民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牺牲品。
《台湾新民报》对台湾民众祖国向心力的揭示
如所周知,随着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签定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台湾被迫割让给了日本,台湾人民在条约规定的两年选择期后名份上已属“日本国民”。但是,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人民始终不懈地开展着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从初期的武装斗争到后期的非暴力政治抵抗运动,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就是图谋以直接(如初期武装斗争时期)或间接(如后期民族运动时期)的方式,保持与祖国血脉相联的紧密关系乃至要求归返祖国。(注:参阅拙作:《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4期;《日据时期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湾研究》1993年第1期;《“七七事变”与台湾》,《台湾研究》1998年第3期。)故而日本殖民者说:“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是汉民族的系统。”“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注: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年,第14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殖民者意识到这是与台湾人的祖国发生的战争,因此对台湾民众的态度相当关注。那么,台湾民众对九一八事变的心态究竟怎样?他们都作出了什么反应呢?由于殖民者的新闻管制,日据时代留下的相关资料并不多,但《台湾新民报》记事却为我们披露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弥足珍贵。
台湾民众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毋须说是以和平解决为最高期待。《台湾新民报》第一次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即说:“日华两国军队在满冲突,两国舆论沸腾,势将陷入国交断绝,时局能够扩大与否,尚暂不容逆料,以后的推移如何,殊堪注目。然而日华本属邻邦,对于维持东洋的和平,互相有责,所以一旦两国龃龉,不但有碍两国的邦交,甚至东洋和平的基础为此破坏。俗语有云:打架两成败,所以当此时候,双方均要以冷静的态度,顾虑大局的前途,促进其从速移入和平的解决才是。”(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6月26日,第2版。)但很明显的,台湾民众在事变中还是站到了自己的祖国中国的一边,譬如在抨击国联调停软弱无力时就写道:“自日华纷争问题的发生,在识者早就对其能力怀疑了”,“对于纷争国的调停方法,给强国能得满足承诺,然后欲说服感着不利的弱国屈伏,这也可称为和事老的老练外交家之辛辣的手腕了。”(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24日,第2版。)给予弱者祖国中国很大的同情心。并对国内掀起的反日浪潮拍手叫好,《台湾新民报》称:“各国有各自特有的国魂,现时全中国之浓厚反X的空气,是不是中国魂的反映?”(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24日,第3版。)另一方面,他们对日本殖民者封锁消息的做法表示不满,“中日间的关系,日趋纷纠,但我们台湾,仅可从内台各报纸探得消息而已,故所知的范围可谓狭隘极了。因为台湾当局,对于从国外寄来的报纸,多数没收,所以难得确知消息,很多表示遗憾云。”(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17日,第4版。)为此,他们一面揭露日本在台御用报纸的歪曲报导,同时尝试以各种办法让台湾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如1931年11月14日的《台湾新民报》便提醒台湾民众:“对于日华纠纷问题,在内地的新闻比较的是用冷静的态度去批判,但在台湾的日刊纸则用感情的煽动的,谩骂的笔法来对付这回的问题,尤其台南新闻的笔法最为露骨,请诸位注意于每夕刊的羊头语便知。”(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1月14日,第9版。)更有人自己翻译九一八事变的相关新闻告知民众,如台北文化公司的林俊卿将有关新闻译成汉文贴于店前,却遭日本警察拘捕,控其“故意宣传日本不利,要将他稍加以警戒”(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3日,第8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的人心向背。
除此之外,台湾民众还以各种方式抵制日本殖民当局发起的所谓“慰劳满洲日军”的活动,如台北帝国大学学生以经济萧条为借口反对高额募集所谓“慰问金”,这当中还包含日本学生在内。(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2月5日,第3版。)台北日人发起的募集“军人慰问袋”活动,更是闹出不少笑话,比如就有人把妇女的“腰卷”和“足袋”放在慰问袋里,引起日本人“大为愤慨”,“以为是没有诚意”。《台湾新民报》嘲讽道:“人家既然肯置物品于慰问袋,自然是出自诚意,听说腰卷的意思是传说可以防御子弹。”(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17日,第4版。)“九一八事变”也激发了《台湾新民报》社全体同仁的强烈爱国心,据杨肇嘉的回忆:“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挑衅,开始侵略我国东北。本人亲眼看到新民报编辑同人,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是支那都改为中国,为不侮蔑祖国,轻视自己,常常与日本警察发生争执。”(注:杨肇嘉:《台湾新民报小史》,收入《台湾新民报》景印本第2册,东方文化书局,1974年。)正是由于《台湾新民报》鲜明的倾向性,引发日本殖民者的严厉打压,如龙潭警察分室巡查部长佐佐木荣龟即在保甲会议上公然要求辖区内民众不要购阅《台湾新民报》,被该报斥为“真是无理的干涉”(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1月7日,第8版。)。最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台湾新民报》的一段记事,它反映了台湾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所表现出的义愤难抑的心态,特摘录如下:(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1月7日,第4版。)
最近每在亲朋聚会谈天的当儿,话柄都由满洲事件与经济苦的二大时事发生出来。论到公理无从发扬之处,热血青年所谓纯真的人们,都要兴奋至于极点,甚至有气得眼眶全红,热泪往下直流的。语云哀莫大于心死,在青年体中能够有这种热血,聊堪自慰!
限期撤兵,直接交涉,经济封锁,国交绝绝,宣战,开火……许多国家大事,在弹丸之地而且孤悬在海中的台湾,由不出息的台湾人任是如何呼喊,也不过是一种的还愿,于大局自是没有反应。但青年的意气即所谓憨气是不可被客观的认识抑制下去,变为虚伪的腐化青年,于台湾的前途才能有点向上的曙光。
概而言之,“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民众在这场战争中显然是站在了自卫的、反侵略的、正义的祖国人民一边,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战、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台湾民众对祖国的向心力。
《台湾新民报》与1931年的台湾
日本占据台湾后,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殖民统治斗争,一方面动用国家机器及警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持续开展同化运动,以“内(日)台如一”,“一视同仁”为幌子,企图将原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人同化为崎型的日本人,从而改变台湾人的民族性。(注:参阅拙作:《日本据台时期的同化政策及其失败》,收入《同祖同根源远流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日本殖民者更体认到同化台湾人民以消弥其“汉民族”意识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日益膨胀的法西斯势力影响也波及到了台湾,随着日本本土右翼活动的猖獗,台湾岛内右翼团体纷纷成立,如“台湾社会问题研究会”,“维新会”,“东亚共荣会”等等。台湾民众的反日民族运动则受到镇压,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被诬为“含有民族独立主义的要素”而倍受打击,最后被迫停止。(注:周婉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1989年,第147,152页。)台湾总督府更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又掀起所谓治安维持法行动风潮,搜捕左翼及进步人士,日人自称:“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满洲事变发生以降”,日本“内外情势”发生“大变迁”,台湾岛内亦对社会运动进行了“全般检举镇压”。于是,台湾社会陷入动辄触禁的紧张气氛之中。(注:黄昭堂:《台湾总督府》,自由时代出版社,1989年,第336页。)
《台湾新民报》的前身是《台湾民报》,它是台湾民族运动的喉舌,经常刊载抨击日本在台殖民统治,号召开展民族运动的文章,或引进大陆白话文,刊登大陆作家的作品,介绍祖国的情况,或展开台湾乡土文学,台湾话文等的论争,或向民众传播新知识新文化动态,深受台湾民众的欢迎,被称为“台胞忠实的喇叭手”。(注:杨肇嘉:《台湾新民报小史》,收入《台湾新民报》景印本第2册,东方文化书局,1974年。)然而,《台湾新民报》乃诞生于1930年,这一时期的台湾民族运动已经发生很大的变迁,1927年文化协会分裂为新旧文协两派。左翼的新文协被镇压后不久,1931年2月台湾民众党遭日人以“绝对反对总督府政治和民族自决主义”的罪名而禁止。(注:黄昭堂:《台湾总督府》,自由时代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6月台湾共产党组织亦被破坏。杨肇嘉回忆道:“九月十八日夜,日军突袭我东北,占据沈阳,惹起历史上的九一八事件。因此,他们(按指日本殖民者)里外紧张,再由于日本国内法西斯思想的抬头,台胞的汉民族及以民族思想为中心的各种活动,从此面临重大的阻力。”(注:杨肇嘉:《台湾新民报小史》,收入《台湾新民报》景印本第2册,东方文化书局,1974年。)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台湾人的心境则有如当时民族运动的干将之一叶荣钟所说:“国人对于日人,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精神上并无苦闷。但台胞则身心相剋,情理矛盾。包羞忍辱,草间偷活的心情,和装聋作痴,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得到。”(注:叶荣钟:《一段暴风雨时期的生活记录》,收入氏著:《台湾人物群像》,时报文化出版社,1995年。)因此,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台湾新民报》的记事便不能不相当谨慎从事。譬如,我们上面的引文中就看到“反日”不得不写作“反X”,针对日本殖民者限制言论自由的横暴行径,在报纸上也只得以委婉的语气发表声讨文章,以下文字就很能反映当时《台湾新民报》的处境和无奈的行文风格:
现在因日华关系,愈形紧张的缘故,警察当局竟在锐意取缔流言蜚语的传播。当此重要时机民众要慎其言是当然的事,然而新闻的报道,总也不可过于不确,对此警察当局亦要注意才是。(注:《台湾新民报》昭和7年2月6日,第3版。)
曾经在《台湾新民报》担任通信部长兼论说委员在叶荣钟在回忆录中记载了报社工作人员对付日人的做法,就是“以其矛攻其盾”。他说:“日本在东北制造满洲国,标榜王道乐士,大同世界。我们就说大同的理想是使人各得其所,王道政治更须以仁义为依据,使满洲国人得其所,自然也需使台人得其所。侵略中国大陆,日人自称为圣战,我们的说法是皇军在支那大陆攻城略地,并不是要把支那人斩尽杀绝,目的在乎使日本和中国人和平相处,进而协力提协,那末台人全是由大陆移住过来的,而且做日本国民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倘若对台人不好,中国人必望而却步,不敢跟日人走,因为做了四十多年的台人尚且如此,何以叫支那人心悦诚服。不过主张不妨强硬,措辞必须力求婉转就是。”(注:黄昭堂:《台湾总督府》,自由时代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上述情形应当说是《台湾新民报》在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这样,我们但能够理解《台湾新民报》在刊载“九一八事变”相关记事时所表现出来的谨慎,含蓄的表达方式,同时也对《台湾新民报》敢于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报道事变当时台湾人民真实心态的勇气而感佩。毕竟它为我们揭示了台湾民众对祖国的同情与支持,让人们知晓日本同化政策下生活了30多年后的台湾人仍然有着对祖国的向心力。当我们看到《台湾新民报》痛斥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为大陆同胞的反日行动叫好且称其为“中国魂”的时候,还有必要再说更多的语言吗?台湾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左翼新文协负责人连温卿曾批评《台湾新民报》相对于早先的《台湾民报》而言民族主义色彩有所减淡,攻击性不强。(注: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稻乡出版社,1988年,第261页。)我们认为,这虽与《台湾新民报》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多为台湾民族运动中的稳健自治派或改良主义者有关,但也应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判,而不是去苛求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