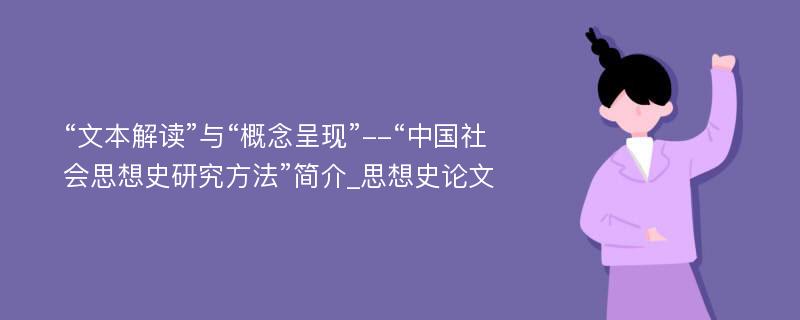
“文本的诠释”与“观念的呈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史研究论文,观念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思想是古典思想资源在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的发明和再生成,从理论视野来看属于社会学,而从理论中心来看则属于思想史。虽然社会学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得以发生、展开的触媒,但模拟自然科学的实证社会学方法并不是发掘思想的得力工具。社会思想作为隐含在资料文本中的主观存在,需要有与其主观性相匹配的研究方法。因此,必须立足社会学的特点,结合思想史的要求,探索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恰切方法,确立从古典资源中呈现观念的有效方式。
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视野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立足社会学理论方法发掘古典思想资源的学术创造,不论是“发现”社会思想,还是“发明”社会思想,都有一个关注中心或逻辑起点,这个中心或起点构成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视野。综合考察社会学的宗旨和使命、历代知识精英的主张和实践以及生活世界的日常行动逻辑,可以说秩序是三者的中心或起点,因而秩序也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视野。
第一,社会学的秩序论范式。
按照孔德重建社会秩序的设计,秩序与进步是社会学的两大主题。要确保社会持续进步,就必须按照实证主义对社会自然法则的正确认识来恢复社会秩序。人类自然拥有博爱的倾向,扩充这种倾向,甚而把人的情感宗教化,就可以引导人类迈向有序与和谐。社会秩序也需要劳动分工和经济合作,同时建立开明政府,确立政治权威,扩大政府的管理权限,对社会实施普遍的调节和改造。这些方面既是社会秩序的生成要素,也是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
孔德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些近代思想家对社会秩序的思考。霍布斯在论述“利维坦(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只有通过放弃某些个人权力才有可能形成和平统一的市民社会,即以某种契约义务把个人同某个主权国家联结起来,由国家以成文法的规定保障秩序与和谐①。帕森斯深入检讨了霍布斯的假设之后指出,如果按照最严格的功利主义假设,在社会的条件下,一个完整的行动体系将会成为霍布斯所说的“战争状态”②。霍布斯以功利主义逻辑思维进行的实验,并未真正解答秩序的建构问题。在帕森斯看来,全部理论社会学的核心必须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而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则是回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初步尝试。而吉登斯认为,经由帕森斯之手,秩序问题成为社会学最突出的四个神话之一,他决意破除这四个神话,秩序问题当然也在其解构之列③。不过,可能让吉登斯始料未及的是,他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却被贝尔特称为在时间中“社会秩序的巧妙实现”④。
此外,迪尔凯姆、韦伯、库利、鲍曼、布迪厄、亚历山大等大批社会学家,都从不同角度阐发了社会秩序的本质和原理,因而秩序论是社会学的一种主要范式。而在当代中国,郑杭生的社会运行理论结合经典社会学理论命题和中国历代王朝治乱盛衰实际,认为社会秩序就是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生成机制。
第二,传统思想文化的秩序关怀。
秩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在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关于秩序的成熟想象和周密安排。天道是世道、人道的价值根源,人道、世道和天道同源同构、相互关联,日月星辰的排列格局和运行轨迹就成为人世的秩序模版,即以“天秩”构造“人秩”,按自然秩序构造人类社会的秩序⑤。而从宇宙天地中领悟到的人间秩序,又在礼仪中被固定下来,仪式通过一套一套的象征确认并强调秩序的天然合理与不可质疑。象征的反复使用,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意识,即象征的秩序就是人世的秩序,象征秩序的崩溃就是人世秩序的崩溃⑥。
知识精英对秩序问题格外敏感,在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重建秩序是知识精英的永恒话题和终极关怀,并由此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有学者指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蕴藏着一个因动乱创伤而造成的向往秩序的情结,从春秋战国时代哲人的言论中,可以觉察到他们视社会动乱为最大威胁,并且致力于秩序的重建。建立秩序凌驾一切,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心智所系的中心课题。以儒学为例,孔子的终极关怀是建立社会秩序,这压根儿是个社会学的课题。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线索虽多,大抵还是沿着秩序这条主脉而铺开⑦。
秩序追求不仅是历代知识精英和官方的主流价值,也是生活世界的行动逻辑。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也要郑重其事地排一排座次,清整一个长幼尊卑的人伦秩序。这种情形投射在生活世界中,就是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结构位置,都必须遵行特定的角色规范,上下长幼、尊卑贵贱,各安其位、各行其是,不能有丝毫错乱,而且生活世界具备自觉的纠错机制,确保生活秩序良性运行。传统的家族、乡族、会社、会馆等,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思想深处对人们实施有效管理,因而在官方秩序出现纰漏的时候,民间社会有时还能运转正常⑧。
第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秩序主线。
正是基于对社会学的秩序主题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秩序情结的深入把握,王处辉在其研究和著作中始终贯穿着秩序这一主线。从《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书早期版本的逻辑结构来看,社会秩序一直是其未曾言明的理论关怀。特别是《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一书,从人性、人的欲望、社会化、人际互动、社会规范、社会控制、社会理想等主题入手,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的认识、观念与规划,而且各个研究主题之间环环相扣,逐步递进,建构起一个以秩序为终极关怀的逻辑体系⑨。
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修订版中,王处辉明确提出,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构建、管理及理想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理想等几个方面。关于社会生活的思想之核心是社会群体生活秩序如何构建和运行管理的问题,而社会问题则属群体生活秩序运行中出现的障碍性问题,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及解决方案均属社会生活秩序管理的范畴⑩。在最近召开的第八届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术研讨会上,王处辉再次强调,社会思想研究要眼光向下,服务生活、服务草根、服务现实,注重从生活世界中的行动和事实中发现秩序的生成逻辑和表达机制。
以秩序统筹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等内容,开创了社会思想研究的新视野,即从描述性解读演进为诠释性理解。描述性解读在于通过陈述被纳入社会思想范畴中的不同要素,由此呈现“社会思想为何”;而诠释性理解在于通过揭示文本的内涵,诠释不同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追问各要素的终极关怀,并发现作者的真实意图,即“社会思想何为”,重在阐明社会思想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高超目标。
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整体性规则
有学者担心,以“秩序”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会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最终写成了政治思想史?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资料共享、内容交叉、手法趋同等,再加上经史传统中的知识精英们向来以求治去乱、解天下于倒悬为己任,因此很难说中国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的界限必定一目了然。不独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社会思想与其他专门思想史之间也存在内容交叉与边界重叠的问题。那么,如何确保呈现出来的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别的什么思想?
其实,无论社会思想抑或政治思想,都有其仰仗生成的学科背景,学科背景的区别和差异,是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或其他专科思想之间边界的关键。在探寻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差异时,鲍曼发现,如果以研究对象来区分学科边界,一块块领地已经被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割据,社会学只能捡拾这些学科剩余的领地。这种以研究对象判别学科差异的方式,只会导致社会学是“剩余学科”。鲍曼并不认可这种判别方式,更不认同这个结果,他指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并成为独一无二的知识体系,本质上在于社会学将人类行为看作是广泛的整体结构的要素(11)。在鲍曼看来,研究规则才是学科之间的本质差别,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就是从综合的、整体的结构化角度研究人类行为。因此,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的独特研究规则,就标明了社会思想研究的方法立场——综合的、整体的规则。不仅要关注思想观念的元素,也要关注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终极关怀,即将“思想”看作一个整体事实,无论是一种思想观念,还是一个人的思想主张,抑或是一个学派、一本著作的思想内涵,进而寻求文本所叙述的各义涵要素之间的关系,即整体意义。
在孔德那里,从整体性角度研究社会事实和人类行为,已经成为社会学的基本准则。孔德指出:“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而分别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条件和社会的运动进行科学的研究。”某一特定的社会现象都与时代、文明、人类这些整体有关,如果不是放在整体社会之中,那么就无法理解与解释,即不能孤立地考察个别事实,必须把所有事实放到它们组成的整体中才能加以正确认识,如果撇开整体就不可能个别地正确解释任何社会现象与事实。这一整体性规则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理念,新功能主义者亚历山大指出:“个别部分本身的意义只有在把它们看作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时才能被理解。如果我们要使某些部分具有意义,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是更为广泛的论题的代表和例证……整体是从对有意义的部分之间的关系思考中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只有假定已经有某些整体的存在才去探讨部分的意义。”(12)
古代知识精英的思想主张多以感想和体悟的形式表达出来,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和观念也多是含蕴在人情世相之中,大都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龙冠海曾指出:“社会思想的范围较广,不一定有系统、合逻辑,或以社会事实为根据;而社会学思想则否,其范围较狭,必须有系统、合逻辑,并以社会事实为依据。”(13) 因此,无论是知识精英的思想和主张,还是生活世界中的观念与行为,如果只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些内容,那么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思想或观念就仅仅是一个个片段。这些被分离出来的片段,可能是伦理关怀、政治倾向,也可能是经济主张、管理经验,还可能是军事理论、科技思想,结果也就是现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视野中的所谓“某某思想”。不过,不同学科视野中的某某思想研究,深入专精而不及其余,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实际上,包含在精英话语和日常行动中的各种思想要素不是一盘散沙,也并非如研究者从不同学科立场发现的各种界限分明、孤立寡与的思想片段,而是有着共同的意向性和意义指向——社会秩序。研究者以不同学科视角强行切割下来的片段,割断了各思想要素内在的有机联系,因而也就无法揭示其话语和行动背后的真实意图。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不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各种思想要素的终极关怀,而仅仅纠缠于某一或某些片段,将其不断放大,结果只能是以偏概全,遮蔽了思想者和行动者思想的全貌,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消解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自性。因此,无论是立足社会学的方法立场,还是基于传统思想本身的特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坚持整体性规则,综合、全面地考察知识精英的观念和主张,以及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承载的不同观念要素,探寻话语、观念、实践表象之下到底意欲何为。
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超越就事论事的局限,而应在更为广阔的情境中寻求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关联,因而宏观的、综合的整体性建构立场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规则。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不必纠缠于某一思想片段,除了发掘思想要素,更要以整体的立场、宏观的视野,将片段的、零散的、感悟的思想,纳入以秩序为中心的框架之中,综合探寻各思想要素的内在关联及终极指向。因此,立足社会学的整体性规则,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术语、范畴和方法,从而使中国社会思想史以秩序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具备独特自性而与其他思想史区别开来。
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诠释进路
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原材料主要是从过去流传至今的典籍文献,在文本解读和诠释的基础上,达成对前人智力活动的再发现。这个以文本为中介领会前人意义、意向的过程,不仅仅是呈现事实或事件的资料排比、统计描述,而且是将言说者、行动者隐而不宣的言外之意揭示出来,呈现的不仅是“事”而且是“思”。因此,必须运用恰切的方法将文本、行动蕴含的思想观念呈现出来,即通过对文本意义的发现、阐明和译解,把过去世界存在的意义转换到现在的世界之中,最终达成文本、作者、阅读者共同的意义体验。
第一,社会思想的文本。
大体而言,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类:第一类是十三经、诸子书、二十五史以及各种文集,属于立言者、立功者直接陈述观念主张的文字材料,这也是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一贯应用的常规文本;第二类是文诰、政令、类书、善书、历书、蒙书、契约等对生活世界具有指导性质的文字材料,这些文本不是对思想观念的直接阐述,而是思想观念的应用形式,已逐渐受到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的关注;第三类是各种形式的非文字材料,包括绘画、地图、雕塑、建筑、历史遗迹,甚至物事的排列布局等都可以看作以图像符号表达“意义”的文本。以上资料类型大多是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原材料,同样也可以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分析文本。
不过,如果要拓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视界,还必须拓展文本的范围,才能真正发现生活秩序的逻辑,真正做到关注生活、服务现实。葛兆光认为,话本、小说和唱词等也应当成为思想史研究的资料,可以用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观念的世俗化过程(14)。近年来,这些材料也受到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高度重视。话本、小说和戏曲通过类似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迎合民众的理想诉求,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民众的价值观念,是发掘生活世界中价值观念和行动逻辑的重要材料。目前,以小说、话本和戏曲为分析文本,无论是思想史还是社会思想史,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除了长久以来研究者习惯于以经典文本为解读材料之外,也与在小说、话本和戏曲中发现“符合规格”的思想的操作难度有关。
丸山真男将思想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高度抽象化的体系性理论、学说、教义等;第二是具有总括性的世界观或世界像;第三是意见和态度;第四是生活感情、生活气氛等实际感觉。一般而言,层次越高,体系性、抽象性越高,层次越低,片面性、经验性即与生活结合的密切度越大(15)。这些思想层次不一定与思想史的资料类型形成一一对应,不过丸山所说的三、四层次却是小说、戏曲和话本等文本的主打内容。小说、话本和戏曲不是思想观念的直接陈述,也不是思想主张的间接应用,而是生活世界中人情世相与日常行动的描绘和呈现。善恶忠奸、是非美丑,不是直白的说教,而是借助人与事、情与理,通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将是非判断、善恶因果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受众的道德意识和行动准则,真正成为整齐人道、规范秩序的教科书。
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原材料,小说、戏曲和话本等文本含蕴的思想与生活紧密切合,片段零散而不成体系,并不能直接将其提炼、归纳、总结出来,这与以经史子集等经典文本为原材料的社会思想研究不太一样。经典文本的作者们运用多种论证手段,或摆事实,或讲道理,竭力阐明自己的观念和主张,文本的直接指向对象就是思想本身,所以研究者可以直接将“思想”提取出来。但小说、戏曲和话本等文本并不直接指向思想,所以必须再造文本,将这些文本还原为“可理解”的行动,探测文本中的行动者——而不是文本的书写者——的行动意义及思想动机。
如何从话本、小说和戏曲等文本中有效“提取”出其含蕴的社会思想,需要重新构造出适合于呈现思想的文本。小说、戏曲和话本,甚至俚歌、谣谚和笑话,无不展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的生活世界,各色人等或崇高、或卑微、或苦涩、或得意的行动,以及行动造就的人情世相,是这个生活世界的主旋律。无疑,此一生活世界是有意义的。不过,表达意义、呈现观念的载体不是文字编织的人情世相,而是人情世相背后的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就是文本的构成,但文本只是行动寄居的载体和背景,并非社会思想研究的文本本身。这些行动是虚拟的行动,是被书写者创作的行动,但却是书写者价值观念的投射,也是大众思想意识的集结。社会思想的理解和诠释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和情境,但社会思想的核心问题不是语境和情境,而是在语境和情境中生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所以必须将表达思想观念的行动从作为语境和情境的人情世相中分离出来,作为考掘社会思想的文本对象。借用格拉肖的观点,这个从文本中分离出来的行动,在存在形态上是一个理想文本,是研究者重新建构的文本(16)。
在不少学者看来,富有意义的行动就是一个文本,利科认为:“人类的行动在许多方面皆是一种准文本,行动被外在化的方式犹如书写文字特有的裁夺方式一般。行动在脱离行动的人时,取得一种与文本的自律相似的自律;它留下一种痕迹,一个标志;它被记录在事物的进程中,成为档案和文件。”(17) 与利科的说法相反,斯金纳的论点是:“文本即行动,因此,与其他一切自发行动一样,理解过程要求我们复原文本作者行动所体现的意图。但这并非陈旧的解释学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种神秘兮兮的移情过程。”(18)
一方面,我们将行动与其寄居的文本分离,另一方面,我们又将从寄居载体中分离的行动视作一种文本。也就是说,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文本,文本是具有意图的行动的文字化。文本的作者即是行动者,行动者也就是文本的“作者”。因此,无论是利科还是斯金纳,将文本与行动等价互换,于是社会思想研究对文本的诠释就转换为对行动的理解。
第二,文本的理解与诠释。
斯金纳指出,思想史研究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文本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作者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思想史研究不仅要理解文本的意涵,追问文本说了什么,而且也要探究文本作者的意向和意图,诠释其话语的背后意欲何为。尽管这两个问题主要针对思想史研究的常规经典文本,但研究者从小说、话本和戏曲等文本展现的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的行动,同样可以追问行动/文本的意义,同样可以探究行动者/文本作者行动的动机和意图。
追问文本在说什么,也即理解文本的意涵。展现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者面前的文本,是以过去的语言、过去的言说方式表达过去的所思和所想,如《论语》倡导克己复礼、仁者爱人,《墨子》号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韩非子》主张峻刑酷法、权谋阴术,《抱朴子》宣扬内修外养、积善升仙,《水浒传》书写啸聚山林、快意恩仇,《金瓶梅》描摹猎酒渔色、弄财使气,等等。不过,研究者理解诠释过去文本的意义,并不能真的回归过去,而是以当下的话语系统和理解方式审视过去的文本,不论如何坚持原汁原味,终究难免皴染现在的时代气息或价值色彩。况且,社会学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背景学科,其理论立场、方法视角和概念框架作为研究者“理解的前结构”或“前理解”,已经事先规制了文本诠释的方向,其结果即是以社会学的语言、社会学的言说方式再造文本之后呈现的信息与意涵。当然,运用专业术语诠释文本的意涵,是所有思想史研究的常规工作,这与用现代白话文转译古代文言文在机理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这种语言是特定学科的专用语言。
思想史研究不仅只是解读文本在说什么,而且要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发现文本的言外之意,即解释作者为什么说这些,意欲何为?不过,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复杂,而中国古典文献的作者问题尤为复杂,特别是小说、戏曲和话本等文本,有的是累代集结多人智慧而成,有的根本无法确知作者,因此,所谓作者的意图或言外之意也就无法落在实处。但这些文本是生活世界普遍的、一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文本的作者就是生活世界的所有普通行动者。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生活世界中的普通行动者与知识精英之间没什么两样,知识精英用书面语言、学术语言表述思想,而普通行动者用行动践行思想(19)。所以,知识精英那些高妙的、超越的思想主张,在生活世界中普通行动者以日用而不知的行动实践、重现那些思想主张。
如何才能捕获作者/行动者的言外之意,斯金纳的方法是,努力穿透文字意义的表象,深入考察作者书写的情境以及作者表达意涵时运用的修辞策略,以发现作者的真实意图或文本的言外之意。因为文本作者的意图是隐而不彰的,只有通过对文本的语境和作者的修辞作出解释才能使其显现出来。斯金纳指出,必须将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研究者识别文本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因此在解读文本时,必须注意作者的修辞策略,通过揭示如何说的问题达到准确理解为什么说和说什么的问题(20)。
斯金纳强调,理解文本作者的真实意图并不是移情过程。而给斯金纳深刻理论影响的柯林伍德,却要求以移情的方式“重演”行动者的所思所想。柯林伍德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他看来,历史过程就是行动过程,行动包含着思想过程,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求证思想过程。如何求证?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就是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行思想”行动,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考、去洞察行动者的思想。由此,思想史甚至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21)。历史通过文本而再现,但柯林伍德并未驻足文本,而是直接进入文字塑造的历史时空,要求历史学家以移情的方式将自己代入行动者的角色情境,以同情的理解重温行动者的思想。马丁并不完全赞同柯林伍德的重演理论,在修正柯林伍德理论的基础上,他发展出新的行动解释模型——实践推断,“它指的是一个具体的解释样式,在这个样式中,通过参照行动者的处境动机、目的、手段/目标信念等等来说明一个行动”(22)。如果说柯林伍德的重演近似于将心比心、换位思考,那么马丁则侧重于根据行动者的动机、目的和手段等推断其思想观念。
虽然柯林伍德的重演、马丁的实践推断在于呈现历史行动者的思想观念,但实质上与韦伯对一般行动的诠释性理解异曲同工。在韦伯看来,行动是有意义的,作为表象的意义源自行动者内在的目的、动机和意图,有效把握行动者意图、动机和目的的可靠方法,就是对行动附着的意义作出诠释性理解。而对行动意义的诠释,可以有两种特质:理性的确证和拟情式的再体验(23)。想象性地处于行动者的位置并拟情式地体验行动者的情感,可以把握别人的行动和动机。不过,这种理解只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体验,还必须对主观体验作出因果说明才能揭示行动的真相。理解基础不在于狄尔泰强调的“移情作用”,理解方法不是靠“直觉”或“同情的了解”,而须由观察者本着可靠的经验,运用推理能力,才能获致对行动的动机和意义关联的“客观可能性”判断(24)。因此,对行动者思想的理解,虽然不排除直观的想象,但更重要的是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演绎。
第三,秩序观念的逻辑呈现。
社会科学有两个认识论传统: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求事物内在的一种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弄懂一些人类活动在一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要试图寻找一个具体事物或事件中的因果联系(25)。如果说理解文本的意涵属于解读传统,而作者/行动者的意图来自于对文本意涵的整体性关联的因果推断,那么探究作者/行动者的意图就属于解释传统。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希望通过这两种认识传统,有效呈现出知识精英的秩序关怀以及生活世界的秩序逻辑。
一方面,无论是直接陈述思想观念的经典文本,还是展现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小说、戏曲和话本等“民间”文本,都没有将秩序作为明确的呈现对象,而是作为一种意在言外的深层存在。知识精英将对秩序的诉求、规划和实践隐含在各种论题和话语之中,生活世界中的行动也没有明确以秩序为旨归,而是隐含在各种行动要素的因果链条之中。另一方面,秩序本身是抽象的,超越了直观感性经验,需要借助理性的反思才能把握。有学者指出:“社会秩序本质上是社会的稳定与协调状态,而社会范畴是对人类整体性存在方式的概括,稳定与协调范畴则是对社会活动的一致性、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和社会规则的约束性状态的总体性把握。这些范畴所指涉的对象及其属性都超越了感性经验的范围和层次,只有以理性反思的方式才能把握得到。”(26)
如前文所言,秩序论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范式,不同的学者对社会秩序的生成建构有着不同的见解。这些理论观点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据以解读文本的理论工具,对于研究者提纲挈领地把握传统社会思想的秩序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在孔德看来,人在理性的指引下,通过遵守共同的行动规则,形成协作关系,并辅之以外在的权威协调机制,从而建构起社会秩序。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是在行动中自发演生而成的,任何理性的控制都是致命的自负。而鲍曼指出,社会秩序却是以理性为招牌的权力集团剪除异己、强制纳入统一规则的后果(27)。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理论提供的思想和视角来解读文本的意涵,类比发现文本意涵的秩序指向和生成理路,最终建立这些理论观点与文本意涵的同一性,如秩序的理性建构论与儒墨社会思想的类比、秩序的自发生成论与道家社会思想的类比、秩序的强制规范论与法家社会思想的类比。
不过,类比解读只是建立一种表象的相似性,而且极易出现误读或过度诠释,因而必须综合作者/行动者的言外之意和行动意图,整体地作出因果推论,逻辑地发现文本意涵和作者意图二者共同的秩序诉求。基于文本(作者)说了什么,发现隐含在文本背后的作者意图,即不仅要理解知识精英有什么样的思想主张,还要了解他们怎样建构或论证其社会思想,其话语、行动是如何逻辑地指向社会秩序。秩序作为一种未曾言明的终极关怀,需要研究者立足社会学的整体性规则,理解文本的意涵,呈现文本在说什么,将这些片段的、零散的感悟、观念、主张或动机、目的等,综合联接在一个意义框架内,由此合乎逻辑地推理作者/行动者的言外之意或行动意图,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思想要素整体地措置在一个因果序列之中,从而发现这些要素如何有机地共同指向秩序,揭示其如何达成秩序的意义框架。
也就是说,通过理解文本的意涵、诠释作者/行动者未曾言明的意图,综合二者才能从整体上最终呈现出秩序关怀。例如,作为生活化的社会思想的研究文本,《水浒传》描写了梁山好汉们各种各样的行动,打家劫舍、搬运财物,兄弟聚义、排座次序长幼,分管不同生活职能部门的头领各司其职,等等。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内容,则只是铺陈故事的不同情节要素,但如果将这些内容措置在一个逻辑结构之中,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共同的意义指向,即日常生活的秩序。
四、余论
随着“三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在史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材料、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资料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原料,思想史研究也开始突破传统界限而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拓展。针对目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以经典文本诠释为主导形式,有学者提出,社会思想研究应该进入田野,而不是蜷缩在文献里阐释(28)。
进入田野、走向实证,是否就会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就与哲学史、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有所区别?答案并不乐观。社会调查、田野工作早已不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看家本领了,在社会思想史研究进入田野还处在设想阶段时,社会史研究已经在实践通过田野工作走进历史现场了。走进田野的社会史研究被形象地概括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29),所谓“找碑”,就是搜罗碑刻铭文,仍旧是收集资料的工作。基于碑刻铭文的社会史研究,实质上仍旧没有离开文本的解读与诠释。那么,进入田野、走向实证的社会思想又能走出一条怎样与众不同的道路呢?因而,拓展资料文本的范围并不能当作社会思想的独门暗器,收集资料的方法也不能代替将思想从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的方法和视角多是别人思考过的,或者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我们的工作就是将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的智慧,按照特定的目标和思考方式,重新整合建构为“诠释文本、呈现思想”的恰切方法。当然,望文生义的解读、无根无据的演绎,极易使思想研究落入空疏和偏颇,甚至变成文本游戏(30)。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要注意避免过度诠释,既要避免“时代误置”,将现代学术概念强行加诸古人,更要避免“唯秩序论”,将任何观念都视为秩序问题。
收稿日期:2011-04-23
注释:
① 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陈玮、冯克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页。
②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③ 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1-145页。
④ 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03-104页。
⑤ 吴鹏森:《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特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⑥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
⑦ 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⑧ 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绪论。
⑨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⑩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
(11) 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12) 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13) 龙冠海、张承汉:《西洋社会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第14-15页。
(14) 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15)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7-88页。
(16) 格拉肖:《文本的形态分类》,汪信砚等译,《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美国学者格拉肖将文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现实文本、意向文本和理想文本。现实文本是当前或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本;意向文本是作者关于文本及其意义的模糊观念和意向;理想文本是诠释者在理解现实文本的基础上,对原有文本进行微妙加工改造基础上的文本重建再造。
(17) 蒙甘:《从文本到行动——保尔·利科传》,刘自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18) 昆廷·斯金纳:《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19) 金小红:《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0) 李宏图:《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21)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1-213页。
(22) 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王晓红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23)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24) 顾忠华:《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导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 赵鼎新:《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出路何在》,《社会观察》2004年第6期。
(26) 高峰:《社会秩序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5页。
(27) 刘少杰主编:《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108页。
(28) 杜靖:《走向田野罩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对现有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人类学反思》,《创新》2010年第1期。
(29) 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0) 刘泽华、张分田等:《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前言。
标签:思想史论文; 社会学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