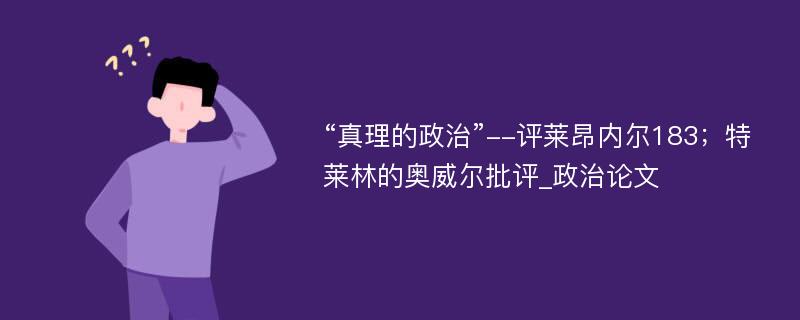
“真相的政治”——论莱昂内尔#183;特里林的奥威尔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里论文,威尔论文,内尔论文,真相论文,莱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美国的经典化与美国批评家、纽约知识分子①重要成员菜昂内尔·特里林的大力推介和经典评论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其影响深远的一篇评论《乔治·奥威尔与真相的政治》。②该文首先于1952年在《评论》杂志发表,后成为1952年美国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③的序言,并收入特里林1955年出版的关于19、20世纪重要作家的文学批评文集《反抗的自我》。本文将从批评文本入手,对特里林的奥威尔批评及其批评动机进行层层分析,并揭示这个批评文本的重要思想史意义。 一、《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序言 特里林在这篇序言中提出了奥威尔的文学声望在美国最终确立的重要论点:“他[奥威尔]是一位有德性的人”(he is a virtuous man);“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位天才”,“他所做的一切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做到”。④这里,特里林对奥威尔作出了与英国文学批评家普里切特的“一代人冷峻的良心”、“一位圣人”⑤一样最为经典的评论:他是一位有德性的人,因此他是“我们”生活中值得尊重的人物,这个人物并不是高不可攀,难以企及,而是“我们”每个人通过反思和效仿就完全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时代人物。 特里林首先对“他是一位有德性的人”进行了解释。“有德性”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词,指的是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以此界定他是一位时代人物似乎有些奇怪。但是,特里林认为其不寻常之处正在于这种“老套”的描述:“这是一个古语,特指过去对情感的勇敢执著以及过去所具有的简单朴实。”(Opposing:154)“古语”意味着现在不再使用了,特里林这里所说的“德性”具有深刻含义:一是以前寻常的品质现在变得不寻常了,这说明现在“我们”丢失了这种品质,因此“我们”应该效仿仍然拥有这种品质的“时代人物”;二是奥威尔的“德性”是来源于过去的道德传统,具有简单和朴实的特征,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欠缺的。特里林详细说道:“通过语言的某种双关内涵,这个句子的形式带来‘有德性’一词的最初意义——这并不只是道德意义上的善良,而且是在善良中还具有坚毅和力量的意义。”(Opposing:155)特里林对“善良”和“德性”作了区分,甚至“他是一位有德性的人”这句话与“有德性”这一修饰语也是不一样的。这句话表明奥威尔的“德性”是“善良中的坚毅和力量”,继承的是过去朴素的道德传统。 正是基于这样的评价,特里林认为:“奥威尔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位天才,而这正是他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使我称之为人物所具备的一种品德要素。”(Oppsing:155)特里林列举了美国的马克·吐温、梭罗、惠特曼和英国的劳伦斯、艾略特和福斯特等时代人物,他们是“天才”,“我们钦佩天才,爱戴他们,但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沮丧”,因为“天才”遥不可及,并非常人可以达到,而奥威尔不是“天才”,“这是多么大的宽慰,多么大的鼓励啊”,“他解放了我们”:“他的影响在于他能够使我们相信自己也能成为有思想的社会成员。这就是他成为我们时代人物的原因。”(Opposing:158)也就是说,奥威尔的“德性”是“我们”已经忽视或丧失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效仿“这位时代人物”而重获“德性”,成为有思想的人。 那么为什么特里林把奥威尔当作是“有德性”的人呢?显然,他认为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揭示了历史的真相。由此可见,“德性”和“真相”密切相关。特里林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样评论道:“[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要文献之一”(Opposing:151),“现在,我相信他书中的记录已被每位判断力值得关注的人接受为本质的真相”(Opposing:170)。特里林对奥威尔的西班牙内战经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他没有刻意表明他是支持右派还是左派……他只对讲述真相有兴趣。”(Opposing:172)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官方的报道深信不疑,一致认为是马党(POUM)挑起了内战,背叛了革命。因此,特里林认为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既说明了现代政治生态的本质,也是作者[为我们]演示了应对这一政治生态的其中一种正确方式,这对当前和未来都很重要”(Opposing:151-152)。特里林由此提出了“真相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uth)这一关键问题。 要理解奥威尔代表的“真相的政治”,需要区分与之相对的“观念的政治”。“观念的政治”中的“政治”是指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设计”,支撑这种政治的精神动力是把政治当作田园诗,是“观念和理想”(ideas and ideals)。显然,特里林这里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信仰”。但是和斯彭德一样,“上帝”失败后⑥是理想的幻灭,由此产生了许多类似特里林所说的“忏悔文学”(confession literature)。但是特里林认为奥威尔并没有“转变态度”或者“丧失信仰”。他没有“忏悔”,而是坚持自己的政治方向,这是因为他在思考,他关注的是客观真相。这表明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具有现在十分稀缺的头脑和心灵”(Opposing:153),他坚守的是“真相的政治”。这里“政治”的意义有较大的拓展。特里林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序言中对“政治”解释说:“我们现在需要应对的是该词的广义,这是因为现在我们一提到‘政治’很清楚的是指‘文化的政治’,它是指把人类的生活组织起来,一是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标,二是为了调整情感,即人类的生活质量。”⑦可以看出,特里林并不是号召知识分子去效仿奥威尔出生入死地参加西班牙内战这样激进的政治斗争,他强调的“真相的政治”是一种“文化的政治”,它指向的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和人类情感,坚持“真相的政治”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向和质量。 那么,为什么奥威尔具有这种讲述真相的能力呢?特里林特别强调了奥威尔对“公共规范”和道德传统的重视: 他针对的真理并不限于一种:他既对早期和简单的真理作出了反应,也对现代痛苦和复杂的真理作出了反应……他所关注的是生存,他将之与以前简单的观念相联系,这些观念其实并不算是观念而只是一些信仰、偏好和偏见。在现代社会中,他把这些当作是新发现的真理,这是魅力和胆量的召唤。我们许多人至少是在文学生涯中卷入了对人性痛苦的、形而上的探索,但是当奥威尔赞扬一些诸如责任、个人生活的有序、公平和勇气甚至是势利和虚伪时——因为它们有时可以帮助支撑摇摇欲坠的道德生活堡垒,这让我们既吃惊又沮丧。(Opposing:158-159) 这段话清晰地说明了“真相的政治”与“观念的政治”的区别。“观念的政治”是“痛苦的形而上”,而“真相的政治”的基础是“生存”和“简单的观念”。“简单的观念”是与“抽象的观念”相对的,它指的是基本的道德品质:责任、秩序、公平、勇气甚至一些道德缺陷(它们是真实的,并非“观念政治”中的“人的完美”)。这些品质如果用奥威尔的话来讲就属于“公共规范”⑧,如果用哲学意义来阐释的话就是指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特里林认为奥威尔之所以能够坚持“真相的政治”是因为他保留了他中产阶级出身的一些品质(责任、公平等),并对中下阶级的品质(生存)加以吸收。相反,其他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对前者完全抛弃,要么对后者又很鄙视。因此,他认为奥威尔正是基于这些品质对热衷于抽象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厉批评:“当代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去思考,没有真正地去热爱真理。”(Opposing:166)他最后指出奥威尔揭示的真相其实是一种普遍真理,这种真理以及揭示这种真理的人对“我们”现在和未来都十分重要(Opposing:172)。十分明显,特里林提出的“真相的政治”是一种“普遍的真理”,是对存在本质的探求。奥威尔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批评其实也是特里林对美国5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告诫:要思考,不要盲从;要真理,不要迷信神话。不过,要理解特里林批评的动机必须对他50年代两部重要文集《反抗的自我》和《自由主义的想象》进行分析,考察这些文本背后的思想语境。 二、反抗的自我 特里林在《反抗的自我》中指出批评文集的主题是“自我的观念”(idea of the self)。自我是人类自我反省的行为,在哲学中也有主体、意识、身份等衍生概念,不同时期对此有着不同的阐述。自我与文学关系紧密,也与社会关系紧密,文学是联系自我与社会的纽带。哈桑说:“文学是自我的文学,是栖息在世界中的自我的文学,是自我与世界被写成文字的文学。”⑨特里林对“自我”和“现代自我”进行了分析。他在文集序言中提到“自我对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进行着强烈而又反抗的想象”,而文化“不仅是指一个民族关于知识和想象的杰作,而且也包括他们一些假想和未成形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的习惯、行为和迷信”。那么,“现代自我”的特征是“[他]具有表达某种榜怒感受的力量,能够对准文化的潜意识部分,并使其成为有意识的思想”(Opposing:X)。特里林这里所分析的“现代自我”和《自由主义的想象》所说的“文化的政治”是一致的,他认为“现代自我”可以感受到文化之下的不文明因素,通过与之对抗,使其成为公众意识,而文学则是表现“反抗自我”的舞台,可以承担拯救文化的使命。特里林引用阿诺德的“文学就是对生活的批评”,目的也在于此。 特里林用“囚笼”意象来形容“现代自我”的处境。在现代社会,“囚笼”不只来自社会的外力,更来自个体对强制力的默认,这种强制力让“囚犯”不得不给自己签署“秘密逮捕令”(lettere de cachet)。家庭、职业、体面、信仰和责任甚至语言本身都是这样的“囚笼”,“‘现代自我’如何看待、指明和谴责他的压迫者将决定自身的本质和命运”(Opposing:x-xi)。奥威尔的作品也突出表现了“现代自我”身处“囚笼”的困境,比如《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所谓“流浪汉是可怕的魔鬼”、《缅甸岁月》中的“上等白人条例”、《牧师的女儿》中的“宗教清规”、《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金钱崇拜”、《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的“工人阶级身上有味道”、《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马党与法西斯主义勾结”、《上来透口气》中的“日常生活的琐碎”、《动物庄园》中的“苏联神话”以及《一九八四》中的“英社”和“新话”。这些“谎言”充斥在社会生活当中,构成强大的话语网络体系,如同“禁忌”桎梏着“现代自我”的思想,“现代自我”反抗着这些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囚笼”,但多以失败告终。但是,奥威尔运用反讽策略揭示了“现代自我”的困境,将对“囚笼”的“无意识”认识以“像窗户玻璃一样透明的”语言转换成“公众意识”,以警示世人。奥威尔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些“谎言”⑩,与这些“现代文化”的“囚笼”现象对抗。因此,特里林所说的“真相的政治”就是依靠文学中的“现代自我”去揭露“谎言”,与“囚笼”的压迫者进行对抗的文化政治。奥威尔以其“德性”品质和“反抗”的作品拯救现代文化,这就是特里林号召知识分子效仿他的原因。当然,对特里林而言,“文化的政治”是对30年代“激进的政治”的扬弃,他也在为战后的知识分子指明思想方向。 三、自由主义的想象 欧文·豪明确地指出特里林以上评论的受众是“自由主义者”,他把奥威尔当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效仿的坚毅和真诚的榜样”。同时,豪认为特里林在50年代特别关注“美国自由主义者在对待左右两派的极权主义上应该持有什么样的道德和政治立场时所面临的问题”(11)。另外,特里林还特别提到他在答应出版商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写序时碰巧与他的一位研究生讨论奥威尔,这位研究生与他不约而同地认为“奥威尔是一位有德性的人”。这些证据以及特里林批评文本中的诸多细节表明,特里林以一种公认的文学批评家权威身份告诫战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年轻一代应该效仿奥威尔这样“有德性的人”,摆脱“观念的政治”,追求“真相的政治”。特里林这种告诫实质上是想说明自由主义者应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修正,确立新的自由主义方向。他的重要著作《自由主义的想象》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写的。(12) 特里林指出《自由主义的想象》的主题是“自由主义观念”,特别是这些观念与文学的关系(“preface”:xv)。前面讲到《反抗的自我》主题是“自我观念”,探讨的是文学中具有反抗意识的“现代自我”,文学是“现代自我”与社会文化相联系的纽带。因此,文学把“自由主义”、反抗的“现代自我”和社会与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有理由推测文学将在特里林所说“自由主义的想象”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奥威尔一样,通过“反抗的自我”的文学想象来改造社会和文化。特里林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在美国这个时期,自由主义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也是唯一的思想传统。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在保守主义和反动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得到传播。”(“preface”:xv)(13)结合这一判断的上下文语境,特里林的暗含之意是说,当今保守主义和反动主义虽然还没有形成观念气候,但是具有很强大的思想暗流,认为其“观念破产”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要防止坠入“保守和反动”的暗流,始终坚持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美国唯一的思想传统。这里关键是如何解决好当下的思想困境问题,而特里林提出自由主义应该根据时代和自身的需要而被修正。 首先,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确自由主义的总体趋势是正确的,但其个别表达却可能有错误,因此可以通过加深对对手(如保守主义和反动主义)的了解,知彼而知己,才能给己方施加思想压力,产生修正自身的动力。对此特里林特举自由主义的奠基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为例予以说明。密尔认为应该对保守主义者柯勒律治的思想加以了解,因为“像柯勒律治这样的对手施加思想压力可以使自由主义者反省自身立场的弱点和自满”(“preface”:xvi)。 第二,既然情感和观念是相互影响的,那么文学与政治也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前面讲到“文化的政治”是关注人类的生活质量,自由主义原则与此是一致的,因此自由主义者应该以文学想象的方式介入政治。特里林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凡是有创见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都把他们批判的激情投入到政治,比如文学中的“反抗的自我”便是典型。他还指出密尔重视柯勒律治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诗人身份。密尔认为诗人之见“可以修正自由主义总是以一种他称为‘散文’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错误,提醒自由主义者应该感受到多样性和可能性”,而且这种修正“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必须的”(“preface”:xix)。特里林对密尔的上述阐释意在告诉自由主义者应该走文学想象和批判之路,因为文学是必然性和或然性的统一,文学可以认识到个人和社会存在的本质,也可以把握现实中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这与纯粹的抽象观念截然不同,抽象的现实是单一的,真实的现实是多样的,文学中的“反抗的自我”揭示的是无意识的“囚笼”,是“真实中的真实”。文学无疑是自由主义、“现代自我”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平台。 第三,自由主义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悖论:自由主义关注情感,人的幸福是其中心议题,但在以自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情感时又往往会排斥情感。当今自由主义也存在这个悖论:当它在朝扩大化、自由和人生的理性方向想象时,它就会排斥情感的想象;当它对思维能力越有信心时,它就越会使思维机械化。这就是说,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理性主义的,对人的前途是乐观的,在以进步观念实现最大自由的时候往往会与情感产生矛盾。这是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特里林主张以一种均衡的批判精神来对待这个矛盾,对待自由主义想象: 当我们以一种批判的精神来分析自由主义时,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其朝组织化发展的冲动是必须的,也是有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批判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同样必须理解组织意味着团体、机构、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那些能在团体中保留下来的观念以及那些能传递到机构、部门和技术专业人员的观念通常都是某种类型的,具有某种简单性。这些观念要能保留的话通常会失去一些整体(largeness)、调节(modulation)和复杂性。偶然、可能性以及那些有可能使规律走向终结的例外等所带来的鲜活感受并不能与组织化的冲动协调一致。因此当我们以批判精神看待自由主义时,我们要考虑到在我所称的自由主义的最重要想象与它现在特定的显现是存在差异的。(“preface”:xx-xxi) 特里林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想象”中的“想象”一词有一语双关之意,既表示对自由主义的设想和看法,也突出“想象”在以“理性”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中的重要反拨作用。“自由主义的最重要想象”,即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暗示文学可以抵达真正的自由主义。因此,特里林在序言的最后强调了文学在自由主义想象中的重要作用: 批判的任务就是提醒自由主义最为本质的想象是它自身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这就是要使其意识到复杂性和困难性。在对自由主义想象进行批评时,文学具有独特的关联性(unique relevance)。这不仅是因为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向政治,更重要的是因为文学是最完整、最准确地记录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的人类活动。(“preface”:xxi) 特里林通过分析自由主义的外在动力、内在悖论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了文学与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完全吻合,自由主义者可以投身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来达到改造社会和文化的目的,这一“文化政治”策略既不偏激,又不保守,理智与情感均衡协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有可为。特里林均衡的文化发展观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与他在奥威尔批评中提出的“真相的政治”精神实质是一样的。特里林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将奥威尔“真相的政治”中激进的政治介入成分去掉,将之改造成一种“文化政治”,成为修正自由主义的有力工具。 《自由主义的想象》收录特里林在30、40年代所写的16篇文学评论,后依“自由主义观念”主题进行了统一修改。这些评论是他阐发文学(包括文学批评)在修正自由主义想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和实践,尤以其中一篇《美国的现实》最为重要。该文的批评对象是自由主义进步论的代表帕林顿(14),其代表作《美国思想的主流》是一部以经济和社会决定论介绍美国自殖民时期以来作家的“教科书”,被几代人尊奉为美国思想文化的“标准和指导”而占据中心地位。帕林顿在书中试图说明“美国长期存在的信念是现实和观念的二元对立,但一个人必须加入现实这一方”(15)。然而,特里林毫不留情地指出,帕林顿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他对现实的态度。在帕林顿眼中,现实是唯一的、可靠的且只是外部的,因此作家应该像一面透明的镜子将现实记录在案,这样他就把想象力和创造力当作民主的天敌。比如,霍桑的作品以探索人的内心阴暗面为主,而帕林顿认为这于实现民主毫无益处,与美国现实严重脱离。特里林针锋相对地说: 阴暗面也是现实的一部分……霍桑在完美地处理现实,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能够对自然和道德完美提出种种精彩而又严肃质疑的人,一个能够与“美国现实”保持距离的人,一个能够在异议的正统中保持着异议(dissent from the orthodoxies of dissent)并告诉我们许多关于道德狂热本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在处理真正的现实。(New:169) 特里林受到弗洛伊德很大影响,比如他关于“自我”和“无意识”的观点,这里的“阴暗面”也是如此。帕林顿推崇的美国现实是以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为评判标准,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在异议的正统中保持着异议”、“告诉我们道德狂热的本质”无疑也是奥威尔的写照,他正是批判地继承了英国的异议传统。“道德狂热的本质”是与奥威尔“真相的政治”相对的“观念的政治”。30年代许多左派自由主义者都陷入这种“道德狂热”。 特里林还把矛头指向该书标题“主流”一词的错误。他说:“文化不只是一条主流,甚至也不是合流。其存在的形式是斗争或者至少是辩论——如果不是辩证则什么都不是。”(New:169)特里林曾在《反抗的自我》中详细分析到黑格尔,特别是他的“异化”理论。这里他以正题-反题-合题的动态逻辑来分析文化不是一家独大,也不是思想相安无事的交汇,而是一种思想与其针锋相对的思想进行论辩,促进自身的完善。这种斗争不是暴力的镇压,而是智力的交锋。他进一步阐述道: 在任何文化都会有某些艺术家充满了辩证思想,他们表达的意思和力量就存在于矛盾之中。可以说他们触及的正是文化的实质,其标志是他们不会顺从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团体或者趋势。正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环境,一种需要经常作出解释的环境,使得多得出奇的19世纪著名作家成为他们时代辩证的宝库,他们对其文化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他们因此能够预言未来。(New:169) 阿诺德认为民主文化的健康平稳发展需要最优秀思想的发现和保留,而文学及其对生活的批评是发掘闪光思想、鉴定良莠的最佳工具。特里林深受阿诺德的影响,主张文化的均衡发展,对文化需要辩证地看待,而非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狂热。在这个问题上,特里林特意将西奥多·德莱塞和亨利·詹姆斯进行对照,指出自由主义者对前者是“教条般的沉迷”,而对后者则很苛刻。两者的对照会“立即让我们处在文学与政治相遇的黑暗而又血雨腥风的交叉路口”(New:170)。在帕林顿描述的美国人思维里,德莱塞关注工人阶级,是现实和进步的;詹姆斯关注人的内心,讲究小说叙事技巧,但却不实用。德莱塞是美国20、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受到美国共产党的推崇,而以拉夫为代表的纽约知识分子推崇的是像詹姆斯这样的现代主义文学。文学是政治的宣传工具还是具有自足性,这是战前纽约知识分子在其主办的刊物《党派评论》与听从斯大林指令的美国共产党展开的重要争论。特里林通过这篇文学评论对帕林顿与德莱塞的批评旨在告诫战后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反思历史,认识到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倡导利用文学批评唤醒公众意识,改变社会方向。 四、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在特里林看来,自由主义者既要放弃30、40年代左倾的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狂热,也要反对战后出现的右倾冷战思维,他们只能坚持一种新自由主义,即修正后的自由主义。那么战后美国社会出现了哪些显著变化促使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呢?特里林认为自由主义是美国占主导的思想传统。但从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到20世纪初,以“进步”为特征的工业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日益突出。此时出现的“进步主义”运动是为了控制垄断,对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进行干预,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次修正,其代表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新国家主义”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新自由”则试图恢复自由竞争,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抑制垄断,促进公平,这为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奠定了基础。“新政”是新的社会变化所导致的对自由主义的重大修正,标志着美国从古典自由主义进入现代自由主义。 “新政”不仅使美国安全度过了经济危机,也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使美国战后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也使美国文化充满活力,不少著名欧洲知识分子纷纷来到美国。经济的繁荣使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迅速提高,他们在高校教书之余可以安心著书立说,或在政府部门担任智囊。也是这个时候,纽约知识分子开始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在政治方面,战后美国国内的和平时期有利于知识分子对左倾激进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反思。但是,战后国际形势并不太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盟友变成争霸世界的对手,冷战取代了热战,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战争威胁和紧张气氛。在美国国内,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政策和麦卡锡主义掀起反共主义高潮,名单事件、指控诽谤、调查迫害等反共活动刺激着美国知识分子的神经,仿佛莫斯科审判的历史将会在美国重演,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遭到严重挑战。面对战后美国社会的新变化,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成为重要议题:是走左倾激进主义的老路,还是跟随抬头的右倾保守主义,或者还是走非党派的中间路线?《党派评论》在1952年发起的“吾国与吾国文化研讨会”(16)正是要解决这个路线问题。与拉夫和欧文·豪继续坚持激进路线不同,特里林走的是均衡的中间路线,即以了解保守主义为动力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修正,以文学批评干预社会生活,以文化政治取代激进政治。 战后的纽约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要想取代不合适的自由主义,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必须要建立起来。一是打铁需要自身硬,足以抵御传统自由主义常常暴露的自身弱点;二要能够经受得住极权主义的激进分子和歇斯底里的反动分子发起的攻击”(Prodigal:180)。这也是特里林在《反抗的自我》和《自由主义的想象》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乐观,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他们想在激情的“革命岁月”和多灾的“战乱年代”中“独善其身”,被不少激进主义者斥为“过于幼稚”。特里林还敏锐地发现自由主义自身的“悖论”会造成人的理性的简单化和机械化。不少自由主义者陷入了“观念政治”的狂热。特里林指出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的理性光环之下存在着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的恶。他从历史的教训得出结论,无论是左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无助于解决美国现实问题,意识形态的神话只能导致极权主义,“修正需要替代革命成为时代精神”(Prodigal:184)。美国知识分子只能走均衡的非党派路线,建立新的自由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战后美国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使许多纽约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从批判走向接受。虽然仍有拉夫等人将妥协顺从美国的态度斥为“美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化”,但是不少人已放弃以前的激进主义政治,转向了重新界定的自由主义。他们立足于现实,以自己渊博的知识特长分析美国社会问题。由此,社会科学取代了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美国开始兴盛。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学者开始考虑如何将这些致力于拓展人对自身认识的研究发展成为一种应对自由社会出现的问题的解决之策(Prodigal:185)。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是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贝尔说:“摆在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对他而言,“通向天国城市的梯子不再是一个‘信仰之梯’(a ‘faith ladder’),而是经验之梯”(Prodigal:187),因此他信奉“今天属于活着的人”。(17)贝尔在1949年1月25日《新领导者》发表的评论《一九八四》的文章贯彻了这种思想。他说:“当我们可能总是在探求最终结果的时候,我们却是活在这里和当下。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经验的判断(empirical judgments),它们能够对一个行动的后果作出肯定的回答。”(18)《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一部以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当代美国社会的论著,贝尔还称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9)。特里林的《反抗的自我》和《自由主义的想象》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背景下产生。 如果说贝尔论证走自由主义之路的理论基础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具体操作之法是社会学的话,特里林的理论基础则是自由主义的“想象”——文学的想象,他的具体方法是文学批评。正如贝尔利用奥威尔表达了他“活在这里和当下”、“在矛盾中生活”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特里林则利用奥威尔来强调“有德性”的自由主义品质和“真相的政治”中真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这是特里林所定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20)只有“有德性的人”才能追求“真相的政治”,奥威尔就是这样的人。这不仅是特里林想向美国自由主义者(包括他的学生)传递的重要信息,也是他对自己思想道路的历史抉择。 ①“纽约知识分子”又称“纽约文人圈”,大致分为老、中、青三代。第一代在1900-1910年出生,主要有菜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拉夫(Philip Rahv)、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胡克(Sidney Hook)、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等;第二代在1915-1925年出生,主要有欧文·豪(Irving Howe)、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卡赞(Alfred Kazin)等;第三代则更为年轻,主要有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桑塔格(Susan Sontag)等。纽约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经历了从激进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历程。在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奥威尔的影响不可低估,大多数纽约知识分子都著有重要的奥威尔批评文本。除特里林将奥威尔当作应该效仿的榜样外,豪也把他视为“知识分子的英雄”,波德霍雷茨则把他称为“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和先驱”。纽约知识分子团体是推动奥威尔在美国经典化的重要力量。 ②威廉斯认为该文“标志着奥威尔文学声望的形成”(Raymond Williams,ed.,George Orwell: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74,p.6)。特里林还在1949年6月18日《纽约客》发表对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书评,他认为小说并非完全是攻击苏联共产主义,而是警告一种纯粹以权力为中心的统治制度对人的自由造成了最大的威胁。奥威尔作为批评者也对已沦为教条的激进思想进行了批评(see Jeffrey Meyers and Valerie Meyers,George Orwell: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New York &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77,p.111)。另外,与纽约知识分子关系紧密的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是奥威尔在美国经典化的积极推动者,他在《纽约客》系列书评中称其为“最有才能、最具有吸引力的作家”、“具有良好意志的人”和当代文化研究“唯一的大家”。 ③奥威尔这部长篇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揭露西班牙内战真相。新婚不久的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五个月后奔赴西班牙前线。实属偶然,他参加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而不是共产党组织。共产党的方针是先打败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再进行革命,而马党则认为先建立革命政府才能打败弗朗哥。奥威尔支持共产党的策略,想参加共产党控制的国际纵队,但是他对政治内部争斗毫无兴趣和准备,因为他来西班牙参战的目的只是为了打败法西斯。然而,苏联的大清洗波及西班牙,受苏共支持的政府军开始对持有不同政见的马党及其他组织进行镇压,不少和他在前线浴血奋战的马党成员被当作托派分子和叛徒而受到清洗。奥威尔在一次战斗中喉咙被子弹击中差点丧命,但是真正让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是清洗运动,他最后九死一生逃到法国边境。奥威尔回到英国后发现当地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惊天谎言,莫须有地攻击马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同谋。奥威尔的西班牙经历是他继缅甸经历之后第二次人生重大转折,从此他写作的政治目的是“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诺姆·乔姆斯基等都曾赞扬奥威尔在这部记录西班牙内战的长篇报道中具有揭穿谎言、说出真相的勇气。 ④Lionel Trilling,The Opposing Self:Nine Essays in Criticis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55,p.154,p.155,p.15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⑤Jeffrey Meyers,George Orwell:G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1975,p.294. ⑥See Richard Crossman,ed.,The God That Failed,New Yorker:Bantam Books,Inc.,1959.《失败的“上帝”》主要讲述柯斯勒(Arthur Koestler)、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路易斯·费希尔(Luis Fischer)和斯蒂芬·斯彭德这六位前共产党作家从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到最后脱党的心路历程。 ⑦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8,"preface",p.xvii.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prefac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⑧奥威尔所说的“共同规范”核心原则是:“只要每个普通人行为得体,世界就会变得公平美好。”(George Orwell,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vol.12,London:Secker & Warburg,1998,p.23) ⑨Ihab Hassan,"Quest for the Subject:The Self in Literatur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29,No.3(Autumn,1988),p.420. ⑩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一文提出其创作目的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既要揭露政治谎言,又要把写作当作是审美活动(George Orwell,The Complete Works of Gorge Orwell,vol.18,p.319)。 (11)Irving Howe,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Text,Sources,Criticism,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3,p.217. (12)奥威尔是西方不同政治派别“争夺”的对象,正如波德霍雷茨所说,“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作家争夺到自方阵营可不是一件小事。这会给我们的政治立场带来自信、权威和力量”(see Norman Podhoretz,The Bloody Crossroads:Wher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Meet,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6,p.51),因此,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对奥威尔的政治利用主要表达的是自身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诉求。 (13)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是现状最忠实的支持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现状,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现状是此时此刻所能达成的最好状态。反动主义者(reactionary)主张倒退变革,支持将社会带回先前的状态甚至是先前的价值体系。 (14)帕林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为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创始人之一,他对美国历史的进步主义阐释在20世纪20-40年代具有重要的影响力。1908年,帕林顿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思想开始左倾。 (15)Neil Jumonville,ed.,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7,p.170.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6)《党派评论》编委会提出研讨的问题是:1.美国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对美国及其机构的态度?2.是不是美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一定要去适应大众文化?如果是一定的话,那么将以什么形式去适应?或者说,你是否相信一个民主社会必须使文化拉平与大众文化一致(a leveling of culture to a mass culture),并让这种大众文化凌驾于西方文明传统的思想和美学价值之上?3.当艺术家不能再依靠欧洲作为文化的榜样和活力的源泉时,他们可以从美国生活的什么地方找到力量、更新和认知的基础?4.如果重新发现和认同美国势在必行,那么批判的异议传统(tradition of critical non-conformism)——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梭罗和梅尔维尔并在美国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能够一直保持强劲的势头吗?(see Alexander Bloom,Prodigal Sons: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 Their World,New York:Oxford UP,1986,p.19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这些问题是针对美国战后出现的新变化提出的。拉夫的文章《美国战后的知识分子》(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Postwar Situation)即是按照以上问题进行回答,强调知识分子在地位和环境发生变化后不能安于现状、缺乏危机意识,而应该自始至终保持批判和创新精神。 (17)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7页。 (18)Jeffrey Meyers,George Orwell:Critical Heritage,p.265.贝尔提供的具体建议是:第一,既要承认没有固定的答案,也不要过激地怀疑任何答案;第二,认识到人类境况是有限的;第三,任何社会行为都应该受到实证的检验(be tested pragmatically)。他在评论的最后说道:“一个人只能有意识地或有自我意识地生活在长期存在的双重意象之中,如介入与隔离、忠诚与质疑、爱与批判地赞同等,没有它们,我们就会迷失。最好的情况是,我们能在矛盾中生活(At best we can live in paradox)。”(Jeffrey Meyers,George Orwell:Critical Heritage,p.266) (1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1页。 (20)英国新左派威廉斯对特里林这篇评论发表了看法,并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并没有像《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那样广为流传有一种怀疑,即“奥威尔的讲述真相是在多大程度上被官方文化收编用来反对革命社会主义”。例如,特里林在评论中对后期巴塞罗那幻灭的讲述就要多于早期充满革命精神的巴塞罗那(see Raymond Williams,ed.,George Orwell: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p.6),这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对奥威尔的政治利用。标签:政治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奥威尔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特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