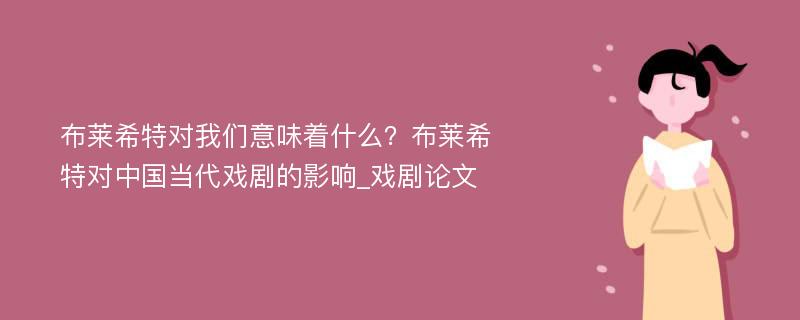
布莱希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莱论文,意味着什么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影响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西方戏剧家中,有三个人物影响深远。首先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西方话剧东渐伊始,就开始了他那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戏剧界的好几代人都是在易卜生的影响下成长的,这对造就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潮流具有决定作用;其次是俄国戏剧表演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为“体验派”的一代宗师,他的影响进一步从表演和导演方面强化了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戏剧潮流;第三个必须提及的人物则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如果说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潮流起到了奠基作用,斯坦尼则起了促进和强化作用,那么,布莱希特在中国戏剧文化中,则是作为一种与前者相对抗的力量出现的,因此,其影响不可小觑。本文就是对布莱希特在中国当代戏剧发展中的复杂影响的一种尝试性分析。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作两个工作性的界说。
第一,要讨论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首先必须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只有把握了这种语境,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作用一种话语,是如何被谈论和运用的,以及这种话语的特别意味。在我看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矛盾始终体现为三个方面:传统—发展—社会主义。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和转变,都体现为这三极的不同关系。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者的关系处于迥然异趣的状态。布莱希特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戏剧界的热门话题,与中国文化的这种三极关系密切相关。比如,布莱希特是一个重要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西方戏剧家,这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就获得了某种被谈论的“合法性”;再比如,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赞赏和褒奖,以及他的最重要的戏剧理论“间离效果”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关系等,使得他成为在现代西方戏剧家中难得的对中国戏剧界有亲和力和认同感的人物,他无疑是一个与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有复杂联系的西方戏剧家【1】;再者,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作为西方现代戏剧潮流中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尝试,虽然在西方现代戏剧史上并不是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其中所包含的某种新的戏剧观,在中国特定的戏剧文化背景中,却被当作打破偏狭的现实主义戏剧的强有力武器。再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对布莱希特理论和实践的认同甚至批判,构成了中国戏剧界注意更多其他西方现代戏剧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中介环节。即是说,对布莱希特式的戏剧的发现、认同和倡导,在客观上为中国戏剧界拓宽视野,变革观念,更广泛地理解和接受“荒诞戏剧”、“残酷戏剧”、“质朴戏剧”等现代西方的戏剧观念,起到了中介作用。【2】
第二,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除了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外部原因以外,还有内部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概括成中国当代“戏剧共同体”。这里,我是借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说法,他认为,科学的进步有赖于科学共同体,所谓共同体是指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有相似或相同观念的科学家群体,他们中构成了一定的科学范式,而科学的革命实际上就是这种范式的革命。显而易见,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内部动力是这样的戏剧共同体,即戏剧界各种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包括剧作家,导演,演员,舞美,批评家等。相当于社会学上所说的“内集团”。更进一步,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演变,事实上是戏剧共同体的戏剧观念(戏剧本体论等)发展演变的过程,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每当一种知识体系被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一致接受时,在共同体中便形成了一种“收敛思维”,这样的思维倾向导致了该共同体保守性的形成。换言之,一种知识的“精神定势”(库恩语)构成了。这时,一方面需要变革,但另一方面变革又是相当困难的,在一些情况下,某种外部力量常常是实现变革重要因素。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布莱希特正是充当了这样的外部因素,作为特定意识形态环境中具有被谈论“合法性”的少数西方戏剧家,布莱希特令人意外地作为与易卜生和斯坦尼相对立的戏剧思潮出现了。布莱希特的理论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戏剧家(共同体),从而导致了中国戏剧舞台上“范式”的巨大转变。布莱希特作为一个尖利的矛,打破了由狭隘的沉闷的甚至教条化的“现实主义”戏剧观一统天下的局面,对构成新时期戏剧蔚为大观的缤纷景观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将集中在中国当代戏剧共同体的戏剧“范式”转变上。
二
中国戏剧界译介布莱希特始于三十年代,【3】但系统地介绍和翻译甚至上演布莱希特的剧目则显然是建国以后的事,而布莱希特对中国戏剧界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在新时期。针对这个事实,我们有理由把布莱希特的影响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建国到文革的17年,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以及后新时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
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化始终处在社会主义、发展和传统三者的复杂关系中。在从建国到文革的第一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始终处于不可动摇的首要核心地位,发展则相对说来处于第二地位,而且不停地受到前者的制约和干扰,至于传统则显然被排斥在边缘地位,被曲解成封建糟粕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大变革激情和期望的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教条化,使得极左政治—文化路线的逐步形成,导致了一个越来越具有封闭和排他特征的文化,发展遇到了巨大的阻碍,而传统变成了一个必须谨慎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文化语境里,说什么和怎么说是有特定限制的。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布莱希特现象作为戏剧话语出现了。
1951年黄佐临编导了具有布莱希特风格的《抗美援朝大活报》,也许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第一次对布莱希特戏剧模式的尝试。但直到1959年,戏剧界谈论他的文章著作才较多出现,而布莱希特的理论和戏剧甚至诗歌著作开始在中国出版,如剧本《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布莱希特选集》等。特别是这一年在中国戏剧舞台上,上演了布莱希特的代表作《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我们知道,解放以来,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下,前苏联的戏剧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话剧,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氏的表演体系作为一种“制造幻觉”(布莱希特语)的理论,与半世纪以来的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的主流是一脉相承的。这无疑强化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戏剧模式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主导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话剧逐渐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尽管人们不时还称之为“现实主义”,当然这种“现实主义”实际上已与斯坦尼的精髓相去甚远了。我们注意到,在17年里,真正的现实主义也许根本不存在,盛行的倒是带有这样那样“浪漫主义”特征的戏剧,而且这种戏剧不可避免地趋向于政治、道德性的说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戏剧倒在某些方面是和布莱希特式的戏剧接近的,特别是他的戏剧观中那些强烈的革命思想,改造社会和人们的理想,以及教育民众,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张等,实际上是和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相当合拍的。换言之,这段时期应该是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最容易发生作用的时期。但历史的复杂性恰恰表现在这里。在中国戏剧共同体最容易接受布莱希特戏剧主张的时候,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与布莱希特的世界观一致的情况下,布莱希特实际上反倒没有发生什么深刻的影响。中国戏剧共同体在这种语境中至少在理论上是选择是斯坦尼而不是布莱希特。当然,以斯坦尼为楷模的并不意味着一丝不苟地照搬斯坦尼,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在一种复杂的变形状态中来造就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对斯坦尼体系的曲解和实用主义态度,加上各种政治上的压力和作用,名义上追求斯坦尼式的戏剧,实际上却是非斯坦尼的。在一定程度上看,这种倾向到是与布莱希特式的戏剧有些接近,但却又不是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性的“错位”,这种“错位”不但表现在17年中,而且还进一步体现在新时期的戏剧实践中(详后)。
17年中,中国戏剧的道路越走越窄,越来越片面化、极端化和贫困化,越来越服务于某种非戏剧的政治的或伦理的目标,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在有限条件下可以谈论的话语,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舞台”上的出现。它的出现是耐人寻味的。首先,它不是一般的外来戏剧思潮的翻译介绍,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入中国戏剧舞台,意义是重大的。其次,在与斯坦尼体系相比较的意义上说,当时中国的戏剧实践和倾向,应该说是和布莱希特而不是斯坦尼更接近,但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布莱希特的理论一俟进入中国戏剧共同体的视野,就是作为一种和斯坦尼体系相对立的批判力量。换言之,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舞台上,被演变成为一种用以抗拒带有自身特征的一种戏剧思潮,尽管名义上是被戏剧共同体当做一种用以对抗偏狭的“现实主义教条”的有力武器,一种改变当时戏剧现状的外来力量。这不防看作是布莱希特的戏剧话语在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中;历史性“错位”的另一含义。
在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可以称之为“黄佐临现象”。黄先生属于中国现代话剧的前辈,早年留洋,熟悉西方戏剧的各种流派,同时对中国古典戏曲也有较深入的理解。在这17年间,大力宣传倡导布莱希特戏剧的莫过于黄佐临了。对他来说,倡导布莱希特的戏剧观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突破当时已经变得越来越教条的话剧模式。照他看来,中国戏剧民族化的努力很容易转向传统戏曲的直接借鉴和挪用;而斯坦尼的影响又极易导致自然主义的倾向,所以,中国戏剧共同体需要一种新的观念,在这种条件下,布莱希特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黄佐临在五十年代末就提出了“向布莱希特吸取什么?”的问题。在他看来,斯坦尼和梅兰芳是对立的两极:“一个讲究内心体验,生活化,一个讲究程式化;而布莱希特似乎站在两者的中间。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学不到家,可能产生自然主义倾向(对生活化误解);学习民族戏曲传统倘只发展加锣鼓点、说韵白,再好也好不过传统戏曲,这使我想到布莱希特,从他这里是否可能得到启发”【4】到了62年广州“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时,黄佐临关于戏剧观的发言,明确提出了:“中国话剧创作好象还受到这个戏剧观(指狭隘的现实主义的戏剧观——引者按)的残余所约束,认为这是话剧唯一的表现方法,突破一下我们狭隘的戏剧观,从我们祖国‘江山如此多娇’的澎湃气势出发,放胆尝试多种多样的戏剧手段,创造民族的演剧体系,该是繁荣话剧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5】从表面上看,这篇发言旨在比较斯坦尼、梅兰芳和布莱希特“三大体系”的区别,但文章的主旨则显然在于倡导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并以这种“破除生活幻觉的”“写意的戏剧观”来冲击一下已日渐僵化的“造成生活幻觉的”“写实的戏剧观”。值得注意的是,在黄佐临的这个发言中,布莱希特理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同中国戏曲,特别是作为民族艺术瑰宝的梅兰芳表演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布莱希特的戏剧观所以有其合理性,它的引进和尝试所以具有“合法化”,原因之一是它有别于我们所熟悉的易卜生和斯坦尼式的“写实的戏剧观”,而原因之二则是这种理论同中国古典戏曲的美学思想的血脉有着一致之处。布莱希特不但作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戏剧家值得注意,他同时还作为一个弘扬中国戏曲艺术的西方戏剧家值得钦佩。这里,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或有意的“误解”,那就是以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来反抗当时已经变得日益狭窄、贫困和庸俗的戏剧现状,名义上的根源是所谓斯坦尼体系,即是说,要以布莱希特来对抗斯坦尼,但中国戏剧的困境实际上又不是斯坦尼的“余毒”所造成的,这无异于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从而构成了一个假想的“敌人”。这是“黄佐临现象”中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方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一下,由于某种无法直言的原因,黄佐临不得不把当时戏剧的困境原因有意归结为一种可以被合理化并被戏剧共同认可的原因,即是由于斯坦尼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了中国戏剧的贫困化。这里的“误解”是巨大的,在我们并未真正学会和掌握斯坦尼戏剧理论的精髓时,我们便迫不急待地以另一种戏剧理论取而代之,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而构置一个假想的“敌人”,归结为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原因加以克服,不过是一种为戏剧变革所找出来的借口而已。于是,历史性的“错位”在这里又一次呈现出来。
“黄佐临现象”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点,是黄佐临在倡导布莱希特理论方面并非始终如一,而是有些前后矛盾和摇摆。而这些矛盾和摇摆恰恰体现了中国戏剧共同体接受布莱希特戏剧的内在矛盾。其实,照黄佐临自己的看法,他1959年导演《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实际上是一次挫折。虽然他六十年代就提出了“三大体系”的观点,可20年后他却从原来的立场大大地后退了,他撰文说:“他(指布莱希特)没成为一个体系,他只有些理论和一些剧本。他的剧本也没能按照他的理论写出来。他的《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一剧,是我导演的八十八个戏中最大的失败,我归罪于‘间离效果’,把观众都间离到剧场外头去了。事实上他写戏是一回事,理论又是一回事,还没有成为体系。所以我认为斯坦尼是话剧中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在于我们怎么用。”【6】如果说62年黄佐临大谈布莱希特尚有“机会主义之嫌”的话,那么,78年的这番话恐怕是肺腑之言。到了79年,当他导演《伽利略》时,他吸取了59年的教训,注意到中国观众的特有欣赏习惯,走了一条“一半是斯坦尼,一半是布莱希特”的道路。【7】黄佐临的这种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正好反映了“戏剧共同体”对布莱希特的分歧,也反映了布莱希特式的戏剧在中国舞台上可能的抵牾和困境。“黄佐临现象”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一方面,他是布莱希特戏剧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倡导者(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另一方面,他又是这一倡导及其实践成功甘苦的体会最深切者。他的摇摆和矛盾事实上正好反映出一个悖论式的困境:一方面,他(以及戏剧共同体)期望以一种新的戏剧理论和观念来冲击和改变一下当时已经日渐僵化贫困的戏剧舞台,在有限的可选择的范围内,布莱希特充当了这种角色,尽管他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当时的中国戏剧实践有着令人惊异的一致;另一方面,布莱希特的戏剧在表现形式等方面的确又和中国观众已经习惯了的欣赏方式有距离有矛盾,这在黄佐临导演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时,已经初见端倪。但这个矛盾只有到了新时期,才能明确地显现出来,并被有识之士们探索性地加以解决。文化史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每当一个文化领域的发展达到停滞状态时,总会出现一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激进对抗和极端的倾向,从而打破原有的平衡,实现局部的或整体的变革,这就是所谓的矫往过正。不过,在这种矫往过正过程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种较为中庸较为温和同时也较为成熟的理论,而且这样的理论常常占据着主流。或许我们可以把黄佐临的退却和摇摆视为这样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新时期的某些成熟的戏剧家,他们在关注戏剧突破传统范式的同时,更强调必须遵循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放弃完全套用布莱希特的方法,注意情与理、幻觉与反幻觉、叙述剧和戏剧性戏剧相结合的理论,等等。
我们注意到,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在西方戏剧理论的历史脉中,其实并不是和斯坦尼体系截然对立的,【8】然而,在中国特定的戏剧发展背景中,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则被用来抗拒斯坦尼体系,事实上扮演了“突破者”和“沟通者”的双重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发展和传统的复杂关系中,就戏剧而言,布莱希特一方面打通了中国戏剧和西方现代戏剧的联系,这是因为他的理论具有在有限条件下可供选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还因为他的理论本身又是现代西方戏剧主流(打碎“第四堵墙”和反抗造成生活幻觉的写实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为突破中国话剧中许多实际上存在的“禁忌”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布莱希特理论还扮演了双重的“沟通者”角色,一方面,他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某种联系,无论他理解中国戏曲是否正确(“正确”这个词在这里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任何外来的理解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他者”的意识形态。不过,历史证明,“误解”往往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和契机。),他都在客观上造成了我们重新反省传统戏曲的价值,进一步激发了戏剧共同体走戏剧民族化道路的自觉意识。而布莱希特的理论正好打通了这个关节点,使古老的中国戏曲不但未过时,反而显得有点“前卫”了。这就是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和实践的“沟通者”功能的一个方面。黄佐临在60年代提出的“写意的戏剧观”,就包含了布莱希特的动力因素。另一方面,作为西方现代戏剧潮流中的一部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又打通了我们进一步关注其他西方现代戏剧派别的通道,把戏剧共同体的视野扩展到更为广大的戏剧革新空间。布莱希特之于中国当代戏剧共同体的意义,不只在于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制造幻觉的“叙事剧模式”,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戏剧共同体思考戏剧本性提供了无限的可以革新的理由和根据。换言之,对布莱希特的戏剧观的逐渐认可和接受,是中国戏剧界更广泛和那些不具备或暂时不具备“合法性”西方其他戏剧理论交流的一个中介。
三
粉碎“四人帮”,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和传统的三个方面依然存在。不同于文革前的17年,发展的主题转而变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经济上的发展极为紧迫,而且文化上的发展也同样迫切。对中国当代戏剧来说,打碎旧的桎梏,获得新的发展无疑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保持“爆炸性扩张”,又使戏剧面临着新的危机。传统不再是一个被压制的角色,从边缘走向中心,激发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戏剧民族化的探索热情。它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景观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在这样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的复杂影响,在新时期戏剧的实践中体现得尤其彰明较著。新时期这中国戏剧共同体内谈论得最多的也许就是布莱希特。戏剧观念上迥然异趣的人,却都可以在布莱希特思想中找到用以支持自己实践的理论根据。激进的戏剧改革派从他的理论中寻找的“打破第四堵墙”的创新根据,并由此打通了通向西方现代戏剧诸派别的通道;而期望从传统戏曲中吸取养料来民族化的“保守主义者”,也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中得到启发和灵感;最后,对于那些不偏不倚坚持走“辩证综合道路”的人来说,布莱希特无疑是一个有待“结合”的不可或缺的方面。
我们有理由认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对中国戏剧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在新时期。如果说17年是初步介绍和理解布莱希特戏剧的阶段,只有少数戏剧家(从剧作家到导演再到舞美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间接或直接地受到布莱希特戏剧观的影响。
经过十年文化浩劫,在中国戏剧重建和复兴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当务之急是清算极左的戏剧观念和偏狭的现实主义。在这种条件下,布莱希特不仅又一次充当了批判性的理论武器,而且同时变成了老一代戏剧家(如黄佐临等)和新一代戏剧家(如高行健等)共同的实践要求。对新时期戏剧界的热门话题稍加翻检,便会发现,诸如“戏剧观念的论争”、“开放的现实主义”、“假定性”、“打碎第四堵墙”、“戏剧的哲理性”、“情与理的关系”、以及“写意戏剧”等重要问题,几乎都和布莱希特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联系。不仅如此,更多的布莱希特戏剧在中国的舞台上演,更多的布莱希特理论著作和剧本被翻译介绍,研究评论他戏剧观的论集也编撰出版,越来越多的中国戏剧家开始认真地思考布莱希特及其对中国戏剧的涵义。这时,在中国戏剧共同体内,可以说形成了自“易卜生热”、“斯坦尼热”以来的第三股“热潮”,即“布莱希特热”。
新时期伊始,中国戏剧界座谈的最多的议题,是如何突破创新,更新戏剧观念。而“向布莱希特学习”似乎变成了戏剧界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这方面,胡伟民的说法颇有代表性。
怎么搞戏?能不能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去制造一批戏剧?谁都会说这是可笑的,可惜,长期以来我们正是这样主张的。我们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时,往往对世界上其他戏剧流派持贬斥态度。我们赞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同时,对其他演剧方法不屑一顾。这种独尊一家,罢黜百家的作法使我们患了艺术贫血症。……布莱希特毕生的艺术实践都在追求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有效、更为合理”的现实主义概念。他坚持现实主义宝贵传统,也不拒绝现代主义艺术提供的新经验。他是位广阔的现实主义者,可以认为,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美学新经验、古老的东方戏剧经验的结晶体。【9】更新和拓展戏剧观,实际上是黄佐临62年提出的问题的重提,所不同的是,这次布莱希特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根据,更是一种实践上的迫切要求和强大动力。布莱希特“旧话重提”,不再是谈玄说理,而是真正的实践。黄佐临继59年导演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之后,又一次执导(和陈合作)布莱希特的代表作《伽利略》,这次他吸取了59年照搬布莱希特的教训,有意识地尝试着“三结合”,演出的空前成功除了当时特定的文化氛围外,的确和强调“一半是斯坦尼,一半是布莱希特”有关。而像高行健这样的年轻一辈戏剧家,已不满足于上演布莱希特的戏剧来改造舞台,而是要写出新剧本,身体力行地尝试运用布莱希特式的叙述手法来打碎过去已变成为戏剧共同体的“范式”和传统的“易卜生式和斯坦尼式的话剧”,如他所言:“现代戏剧一旦捡回这门艺术本身就曾经具有的而一度被丢失了的叙述手段,便会面临一个新的广阔天地,原本属于小说或诗歌的那些领域便将进入戏剧艺术中来。我的那些戏,诸如《车站》、《野人》以及我的那些《现代折子戏》都找寻不同的叙述——表演方式。”“我在找寻别的叙述方式的时候,应该说确实受到过他(指布莱希特)的启发。”【10】
布莱希特对中国新时期戏剧发展的影响作用,首先体现在更新戏剧本体论观念上。中国话剧完全是一个“舶来品”,这种艺术形式的引进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近代以来,传统戏曲已逐渐演变成失去社会批判性的艺术形式,在面临着启蒙和教育民众的巨大历史重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必然选择了现代话剧作为武器,而且这种选择又是以“易卜生模式”为主流,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鲁迅语)。“易卜生模式”造就了中国现代戏剧对这种特定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崇拜,而斯坦尼的表演理论则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戏剧观念,即“制造生活幻觉”和导致观众共鸣的戏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虽然在17年中,真正的现实主义戏剧已经被种种“伪现实主义”戏剧所取代,但在中国戏剧共同体内部,现实主义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和永恒的理想。新时期到来时,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已经被歪曲甚至被摈弃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确乎如此,恢复现实主义乃是新时期初期的一个重要任务。然而,中国戏剧是否只有这样一条必经之途而另无他途呢?在业已恢复了严肃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后,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新的探索和突破。于是,布莱希特式戏剧及其理论又一次旧话重提,出现在新时期的中国戏剧文化语境之中。不同于17年那种封闭的政治文化环境,新时期宽松的环境,使人们不再有必要把布莱希特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作为谈论的合法性依据,而是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上来思考和讨论布莱希特。这里又一次出现了历史性的“错位”。从某种意义上看,清算17年中国戏剧的偏误,总结历史的教训,本应该对布莱希特那种带有明显政治意味和说教特征的戏剧保持警惕。但是,正象17年布莱希特的理论本应有所作为但却没有发生实际形象一样,新时期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非但没有被排斥,反而成了一种批判的武器和突破的途径。在新时期,布莱希特戏剧观中的激进的革命思想和倾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影响中国戏剧共同体,反倒是他戏剧理论中那些作为实现这些思想倾向的手段,亦即他理论中较为技术性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戏剧。我们发现,在新时期戏剧实践中,无论是导演、编剧还是评论家,都对布莱希特的那种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的“叙事剧”(又译作“史诗剧”)概念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并不象布莱希特那样是为了以戏剧来促进革命或教育民众,更多的是着眼于纯粹的戏剧美学意义上对中国戏剧的启迪和借鉴作用。换言之,布莱希特的戏剧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戏剧观念。高行健说得很明白:从布莱希特的实践中,“我发现从剧作法到表导演方法可以是全然另外一种样子,不同于易卜生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那种样子。……布莱希特便提供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戏剧。”【11】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表述,也是一种中国戏剧家面对布莱希特戏剧时所产生的典型感受。我想,在中国戏剧共同体内,布莱希特戏剧所制造的“惊讶”或“不适应”,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在西方的反应。因为西方戏剧共同体内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在轰轰烈烈地不停变革,而中国戏剧却是在走着一条和西方戏剧发展全然不同的道路。当中国戏剧家们已熟悉了易卜生和斯坦尼式的戏剧,并亲身经历了17年中国戏剧艰难困境之后,不从政治上和伦理上而是从纯粹的戏剧美学意义上来看待布莱希特的戏剧时,自然会产生一种“惊讶”。也正是这种“惊讶”和“不适应”使中国当代戏剧共同体中的大多灵敏人,自然而然地把布莱希特式的戏剧当做新的突破点和探索途径。
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念对中国戏剧界的冲击,不只是改变了人们对戏剧本体论的看法,而且更进一步打通了注意西方现代其他各种流派的通道。正象布莱希特是西方不少戏剧派别的先驱一样,当中国戏剧界已经充分理解了布莱希特之后,那么,更广泛地注意和接受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布鲁克、谢克纳等人的戏剧主张,便不再有那样的“惊讶”和“不适应”了,这不妨看作是一种布莱希特“副效应”。新时期中国戏剧舞台上的丰富景观,全然有别于以前那种不敢越“现实主义”雷池的单调贫乏的状况。演员不再是单纯的角色,他即是角色,同时还承担了叙述人的功能(空政话剧团《周郎拜师》中的孙权,或中央实验话剧院《思凡》中的诸多角色)【13】;演出空间不再局限于镜框式的舞台,有的甚至扩大到观众席或休息厅,或者让观众坐到舞台上看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挂在墙上的老B》);布景不再单一地追求写实的再现风格,具有抽象性和象征性的舞美设计越来越被重视(薛殿杰设计的《阿Q正传》的布景);导演不再局限于制造“生活幻觉”的藩篱,而是大胆地运用“非幻觉主义手法”(如徐晓钟执导的《桑树坪纪事》中“围猎耕牛”的场面,具体的麦客队伍演变成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中国农民,或青女受辱后变成了“美女石”等。)。布莱希特戏剧观念对新时期戏剧本体论认识的影响,进一步转化为对“假定性”的深刻思考。新时期“是中国戏剧界思想活跃、创造力解放的十年。西方现代各种戏剧流派被介绍进来,尤其是梅耶荷德、布莱希特的观念论说和创作实践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戏剧演出中的‘写实主义’独尊剧坛数十年的至高无上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无数的话剧导演们热衷于利用舞台假定性手段对演出中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灵活处理,切割取舍,跳跃交错……”【14】虽然假定性的概念早就引入了中国戏剧界,但由于斯坦尼体系的主导地位,这个问题事实上进入了“文化遗忘状态”。随着布莱希特史诗剧特有的“间离效果”被中国戏剧界广泛采用,戏剧的假定性本质也就随之提上了戏剧美学和实践的议事日程。可以说,布莱希特的戏剧实践是促使中国戏剧共同体深入认识和理解戏剧“假定性”本性的一个催化剂。如果说西方现代戏剧的主导趋势是这种假定性风格的话,那么,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在中国戏剧界被广泛接受,并被诉诸实践,无疑具有使中国当代戏剧和西方戏剧沟通的作用。假定性被视为戏剧的本质,这表明中国戏剧跳出了偏狭的“制造生活幻觉的写实主义窠臼,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新时期戏剧舞台上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布莱希特式的戏剧(即使是演出他的剧本),但布莱希特精神却随处可见,它渗透在各个角落之中。
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和实践影响中国当代戏剧的第二个方面,是加强了中国戏剧的哲理化倾向。我们知道,布莱希特戏剧的一大特点就在于他对戏剧理性或内在的哲理化的追求。他的几部主要的戏剧作品及其对表演和导演的要求,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倾向,如《第三帝国的恐惧和灾难》,《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川好人》或《伽利略》等。实践上,布莱希特戏剧的这个特点,也可以视为西方现代戏剧的一个主流,如表现主义戏剧,残酷戏剧,荒诞派戏剧等,都具有这种追求哲理化和理性深度的倾向。而对中国戏剧来说,经过文革式的“假、大、空”模式,重建中国戏剧的思想理性深度,无疑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新时期以来,这种重建从问题剧开始,然后转向更加深刻的社会剧的哲理追求,这显然和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密切关系。问题剧的“应时性”和“时事性”弊端显然为戏剧家所不满,戏剧家在深入思考社会矛盾和普遍性时,日益重视深刻的哲理和人性的剖析。有的戏剧家早在60年代就指出:“关于哲理性,我认为这是我们戏剧创作中最缺乏的一面。”【15】在这方面,布莱希特显然是一个现成的榜样和典范。虽然不能把新时期戏剧在追求哲理深度的所有实践都看作是布莱希特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确存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像《车站》,《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桑树坪纪事》等戏剧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哲理性,是第一阶段(17年)中非常少见的。尤其是被誉为“中国新时期话剧十年‘形式革新’的总汇合”的《桑树坪纪事》,堪称这一努力之典范。该剧所表达出来的深沉历史感和哲理的深度,代表了新时期话剧舞台上的卓越成就。导演徐晓钟在剧中追求的是“诗化的意象”,他不是通过传统的制造“生活幻觉”来实现的,而是相反,“不在舞台上创造现实生活的幻觉,而是通过某种象征形象的催化,在观众的心理联觉和艺术通感中创造出再生的胞含哲理的诗化形象;一个诗化形象的完整语汇,应该是一个哲理的形象并体现为一个形象的哲理。”【16】这种历史感和哲理深度最突出地体现在具有“间离效果”的几个不同含义“围猎”场面中。
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他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戏剧界对“民族化”戏剧的种种尝试。在新时期,传统不再是一个边缘角色,它走到了前台。发展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而是在传统中发展。在西方文化又一次空前“东渐”的局面中,如何保持我们戏剧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本性,是一个不可推诿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深入地分析布莱希特在中国当代戏剧中的影响,就不难发现一些复杂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他的理论和实践打开了通向西方现代戏剧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戏剧共同体思考传统戏曲的本性并汲取营养,对中国戏剧的民族化,又有某种促进作用。在一些人把布莱希特模式作为冲击斯坦尼模式的动力时,另一些人则开始注意并有意探索是否有可能把布莱希特的戏剧和其他戏剧倾向结合起来。如果说我们在易卜生和斯坦尼的戏剧中很难发现中西合壁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在布莱希特那里,这种可能性就大多了。一些戏剧界的有识之士注意到,斯坦尼和布莱希特其实并非截然对立和相互矛盾。他们认为存在着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新时期有相当一部分戏剧空持这样的观点。自黄佐临60年代提出“三大体系”的看法以来,在新时期的中国戏剧界,出现了不少探求话剧民族化的尝试,在这种方面,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深刻的反思,有选择地融合传统戏曲中的某些表现形式,看来与布莱希特不无关系。虽然自40年代张庚等人提出话剧应该向传统戏曲学习以来,中国戏剧共同体内部已经数次出现过向戏曲学习的倾向,但象新时期这样深入思考中国传统戏曲本性,并有机地结合进话剧创作,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方面,以黄佐临为代表的将布莱希特、斯坦尼和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三结合”的“写意戏剧”,以及以徐晓钟为代表的融和“情与理”、“表现与再现”、“叙述剧体戏剧与戏剧性戏剧”的尝试,尤为值得注意。
四
从中国现代文化的三个维向——社会主义、发展和传统——来看,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似乎有一种多重功能,首先,他的戏剧观是明显倾向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他的戏剧观中的平民思想、革命性和战斗性,显然是适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其次,他的戏剧理论和实践又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反传统”和创新性,特别是他提出的“叙事剧”理论是和“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相对立,这就为当时的中国戏剧界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合理的武器来突破僵化模式并获得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对中国戏剧的发展是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更有趣的是,布莱希特的戏剧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解释和褒奖,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戏剧界追求民族化戏剧的自觉努力,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黄佐临提倡的“写意戏剧观”之中。
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吸取不同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布莱希特效应”的复杂状态。这种复杂的影响对未来中国戏剧的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现在论断还为时过早。布莱希特影响的复杂性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主动选择是相当重要的。比如,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具有明显的说教特征,这一局限曾经受到西方戏剧界的尖锐批判。【17】不过有趣的是,在他的戏剧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说教性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片面观念却未在中国戏剧界流传,这倒不是因为中国戏剧界对此有所觉悟,而是因为,第一,中国历来有“文以载道”传统,戏曲在中国古代历来被当做道德教化的工具;第二,五四以来,中国话剧的现实功用一直被许多戏剧家大力强调,建国以后,这种倾向发展得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在文革时期戏剧完全演变成一种“非审美的政治说教”。所以,当新时期中国戏剧变革的曙光出现时,布莱希特戏剧观中的这一局限性在记忆犹新的中国戏剧共同体内部,自然不会有强烈反响。值得思考的倒是,在追求哲理化或理性深度的同时,一些戏剧家走上了片面极端的道路,在加强戏剧哲理性的同时,削弱了戏剧的审美感性魅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中国新时期戏剧的发展历程中,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实践上并未得到“全面公正的传播”,而是有所选择和有所歪曲地被解释和被传播,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有密切关系。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庞杂,中国戏剧共同体总是依据特定的文化走势来取舍布莱希特。我发现,布莱希特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没有被戏剧共同体完整地辩证地加以译介和解脱,而是被必然地极端化和片面化了,因而构成了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特有的布莱希特影响。最典型的现象莫过于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中间离效果、破除生活幻觉以及诉诸理性等方面的强调,用以冲击多少已被教条化和理想化了的易卜生—斯坦尼式的戏剧观。这就构成了中国戏剧共同体内对待布莱希特戏剧遗产不可避免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我们知道,布莱希特虽有时突出地强调这些方面,但从整体上说,他还是警惕片面化和极端化,多次强调辩证统一和反对过于偏激,特别是他四十年代以后的理论中,明显地具有一种辩证综合的倾向。【18】比如注重情与理、叙述性和戏剧性、娱乐与教育、间离与共鸣等方面的统一,反对偏废。为什么中国戏剧共同体会强调布莱希特理论的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这是由中国特定的戏剧文化语境决定的。在“易卜生—斯坦尼模式”强有力的教条化和模式化的背景下,要打破现有规范和教条,使用一些偏锋和激进的做法,矫枉过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往往也是必不可免的。这样一来,布莱希特的戏剧观也就在一种歪曲和片面的形态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影响了戏剧共同体。诚然,布莱希特的理论对于扩展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空间,开阔视野和变革戏剧观,的确有不可轻视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偏激的甚至片面的理解布莱希特,也对中国当代戏剧发生了不可忽略的消极作用,例如抑制情感偏重理性,结构松散而缺乏吸引力,随意中断剧情,任意使用间离效果,演员角色经常交换,过于哲理化而流于晦玄奥等,这些的确削弱了新时期戏剧本身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我觉得,肯定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和实践对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无须赘言的。然而,当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已经成为我们戏剧传统和范式的一部分时,当各种比布莱希特式的戏剧更加激进的实验在中国舞台上频繁出现时,当我们从易卜生—斯坦尼模式的一个极端中摆脱出来,又可能落入布莱希特或被曲解了的布莱希特另一极端时,要深入地思考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其中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中国戏剧观众和中国舞台?换言之,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对中国戏剧会有负面效应吗?我们有必要超越布莱希特吗?这一系列问题是我们思考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意义时无法回避的。黄佐临59年导演的《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时,恪守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结果使得演出不那么成功。而79年导演《伽利略》,他坚持“一半是斯坦尼,一半是布莱希特”结果大获成功。这种修正和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在这方面,徐晓钟的看法和实践,也许是继黄佐临之后的又一次成功的尝试,他提出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他认为,中国戏剧文化的特殊历史和现实,使得直接照搬布莱希特是不恰当的。他指出:
我揣摩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是,创造生活幻觉与破除生活幻觉的原则兼用,以创造为生活幻觉为主。【19】
在剧场艺术实践中我观察到,运用布莱希特的理论时,如果割烈了“情”“理”的辩证关系,造成对“情”的忽视,往往使观众对剧场力的一切产生冷淡,不仅是感情的冷漠,也导致理性思考的冷漠。导演对观众欣赏戏剧时的情理自然逻辑过分生硬的干预,会给观众的欣赏带来困难,降低观剧审美的愉悦。我以为,仔细研究中国传统戏曲情理交融的美学观,可能有助于我们加强戏剧思索品格的追求。【20】这种解答有两个要点:第一是提出易卜生—斯坦尼模式为主,而布莱希特模式为辅;第二是指出中国戏剧观众的欣赏习惯决定了以上“配方”或“结合”的必然性,即离开了舞台上“生活幻觉”,戏剧必将失去吸引力。不过,这里的难题在于我们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难以摆脱的循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描述这种循环:正是多年来“易卜生—斯坦尼模式”的一统天下,导致了戏剧观众对戏剧共鸣的依赖和迷恋,而反过来,我们坚持这种模式又必将强化观众的这种欣赏习惯,使之变成一种不可变更的“审美惯例”,以至于一旦出现打破共鸣的间离效果,观众便认为这不是戏剧或不是道地的戏剧。所以说,突破这种模式的阻力其实不在观众,而正是这种模式本身。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布莱希特式的戏剧在中国舞台上难地演出,最终不但改变了戏剧共同体的戏剧观,而且也慢慢改变着普通观众的戏剧理解。如果只有作为戏剧专业人士的共同体的观念变革,而普通观众的戏剧观念一成不变,这样的变革是不彻底不全面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变革是前者在先。反过来说,在比较的意义上看,戏剧共同体的观念变革,要比一般戏剧观众的变革相对容易一些。而戏剧观众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甚至反复的过程。
我觉得,当我们沉溺于易卜生和斯坦尼模式而越走越窄时,的确需要一种具有对抗性和冲击力的对立理论来作为武器,这时,我们选择了布莱希特。但是,当我们着迷于布莱希特,并把布莱希特模式化教条化时,最要紧的是有必要超越布莱希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又必然回到易卜生和斯坦尼。正像解释学在讨论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时提出了“视界的融合”的设想一样,今天我们思考布莱希特对中国戏剧的意义时,有必要超越布莱希特,寻找一种更广阔的诸种视野“新的融合”。历史地看,作为布莱希特理论渊源之一的俄国形式主义者,曾创造了一种看似简单化却非常有用的历史模式,即他们认为文学史上的陌生化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其中之一就是在历史已经不再占据文学中心的那些样式,在被人们遗忘了许久之后,被后来的作家重新拣起来,并加以运用,这就对当时的读者构成了一种“陌生化”。【21】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观点来分析布莱希特的影响,就会发现,以倡导“间离效果”(又译作陌生化)而闻名布莱希特,与其说是在“创新”,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在“复旧”。换言之,在易卜生和斯坦尼模式占据着戏剧主流和中心的格局中,在这样的戏剧观已变成为戏剧共同体的传统规范的条件下,布莱希特提出了一种与此判然有别的戏剧主张,似乎有某种强烈的“现代派”的创新和反传统味道。然而,只要我们稍作历史分析,就不难发现,布莱希特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回到易卜生之前的古典戏剧观念上的一种努力,只不过易卜生—斯坦尼的戏剧观已经变成了我们约定的范式和惯例,所以尽管布莱希特式的戏剧是一种回到古典的努力,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戏剧主张却显得“前卫”了。【22】不过,这个有趣的是探讨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题旨。
注释:
【1】布莱希特本身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非常关心,研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并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古诗也颇有研究,他的几部重要剧作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据说,他的个人艺术品收藏中,中国艺术品占有很大的比重。他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褒奖和分析,对西方戏剧界认识中国传统戏曲具有重要作用。
【2】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戏剧中的现代主义明显地迟于造型艺术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者通常认为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而戏剧中的现代主义作始俑者正是布莱希特,他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不仅影响了叙事剧,而且广泛地影响了其他现代主义派别。参见Connor,S.,Postmodernist Culture.Oxford:Blackwell.1989.P.132.
【3】据张黎考证,最早在中国介绍布莱希特的是1930年上海书局出版的赵景深先生翻译的《现代世界文坛鸟瞰》;而布莱希特作品最早的译文是,由蓝天翻译的《第三帝国的恐怖和灾难》,1941年8月24日载于《解放日报》。
【4】黄佐临《关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载《论布莱希特的戏剧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第19页。
【5】《戏剧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25页。
【6】黄佐临,《导演的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第291-292页。
【7】这是当时黄佐临对扮演伽利略的演员杜澎的要求。见郑雪莱《略论布莱希特演剧理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异同》,同【4】,第296页。
【8】尽管布莱希特曾谈到他和斯坦尼的区别,但必须看到,他也经常提到两者的一致性。他曾撰文《可以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些什么》,提出了9点建议。布莱希特夫人魏格尔也说过:“我们还证实了,在我们的工作方法当中,许多都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工作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详见张黎编,《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36-248页。
【9】胡伟民,《开放的戏剧》,《文艺研究》,1985,第2期。
【10】高行健,《我与布莱希特》,载《当代文艺思潮》,1986,第4期。
【11】同【10】。
【12】其实,在诸如苏州评弹等传统表演样式中,演员的这种角色和叙述人的双重形态,是常见的。有趣的是,中国当代戏剧家们对这种双重形态的发现,却是由布莱希特的戏剧引发的。经由这样的启发,于是不少戏剧家开始举动入地研究中国传统表演方式的原理和变化,并把它们应用到话剧中来。
【13】王晓鹰,《舞台上的“假定性”与“环境”》,《文艺研究》,1995,第2期。
【14】同【5】,第15页。
【15】林荫宇编,《徐晓钟导演艺术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第413页。
【16】卢卡契批判了布莱希特戏剧的说教性,指出这样的戏剧是违反艺术的审美本性的;阿多诺也指出,布莱希特是典型的“御用戏剧家”,赋予艺术太多的“承诺”,因而是不成功的。(Adorno,T.W.Aesthetic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汉德克则尖锐指出,布莱希特的作品是“平庸的”,他最大的失误在于把政治行动的特性和戏剧的特性混为一谈。(Handke,P.″Strassenthester undtheatertheater,″Theater Heute 9,4,[Apr.1968]:27)
【17】布莱希特多次指出他被人们所误解:“我在戏剧方面的许多论述都被误解了。”所以他反复指出:“丢弃共鸣作用,决不是意味着抛弃情感。”“我清楚地意识到,须摆脱‘这是理性,那是情感’的对立口号。……史诗性的原则保证观众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是很有感情色彩的。”引自《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41,36,197页。他在1941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从不能忘记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只是一种形式;它进一步发展了某些特殊的社会目标,但不能说它可以垄断戏剧一般所关心的东西,在某些戏剧创作中,我既可以运用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又可以运用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见Bentley E.(Ed.)The Theory oftheModern Stage.Haemondsworth:Penguin.1968.P.104.
【18】同【16】,第402页。
【19】同【16】,第410页。
【20】详见俄国形式主义者梯里亚诺夫的论文,他深刻地指出:“任一时期的文学运动,都是在以前的系统中寻找支撑点。”Richter,D.H.(Ed.)Critical Tradition.New York:St.Martins.1989.PP.748-755.
【21】艾思林认为,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的出现代表了欧洲古典传统主流的回归;泰兰指出,布莱希特的戏剧是一种接近古典戏剧的尝试。以上参见施叔青:《西方人看中国戏剧》,台湾经联出版公司,1976,第65-66页。本特利也有相似的看法:“布莱希特的方法如果说不总是,那么也经常是在超越现代戏剧的同时恢复了那些较古老的传统。”“张黎选编,《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