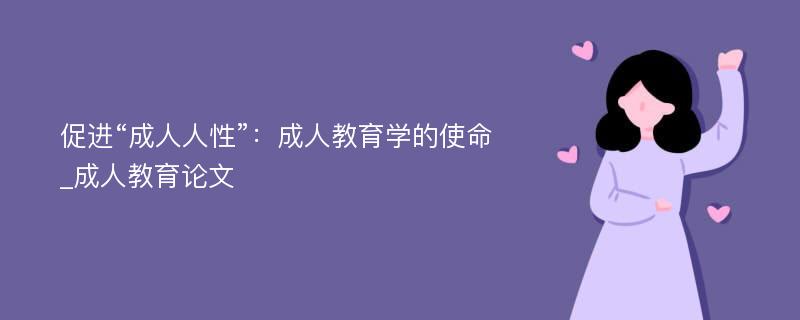
提升“成人性”:成人教育学肩负的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使命论文,成人论文,成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6)03-0102-04
关注成人教育学的发展是成人教育学者的普遍心向,而成人教育学者的思考和探索,无疑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促进着成人教育学的发展。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当前我国多数教育研究者,包括成人教育的研究者都认为,尽管1992年“成人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被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但不可否认的是,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合法性还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承认,成人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还远未成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境和发展难题。
那么中国的成人教育学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无疑是每一位成人教育研究者不得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一、“成人性”的缺失:一种源自成人教育合法性的让渡
德国波库大学教授黑克豪森认为,判定一门学科合乎标准与规范,获得合法性与成熟度的标准有7项:(1)学科的“材料域”,即根据常识可以理解的一组研究对象;(2)学科的“题材”,即从材料域中划分出来的可观察现象的范围;(3)学科的“理论一体化水平”,即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树,这是衡量学科的最重要标准;(4)学科的独特方法;(5)学科的“分析工具”;(6)学科在实验领域中的应用;(7)学科的“历史偶然性。”[1] (P34-38)比利时跟特大学教授阿玻斯特尔认为建立学科要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1)一群人;(2)这些人进行一系列的活动(观测、实验、思考等);(3)这些活动导致某些相互作用,并在这些人内部、外部进行交流;(4)通过教育、交流使这些人的知识不断更新;(5)这种活动通过历史性的学习方法代代传递。同时,他认为一门学科绝不仅仅是一系列论题、文章或教科书,而是一系列行动、目的、组织和发展[1] (P52-53)。
我国学者认为,一门新学科合法性的建立有赖于整个科学共同体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又基于以下现实的标准。概括地说,这种新学科已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体系;一定数量有固定收入的职业研究人员,以及相对稳定的研究机构;学科本身独特的出版物,如杂志、期刊及书籍;正规的培养计划如规范的博士、硕士及本科教育,它们为该学科提供可靠的后备力量。在这些要素当中,一定数量的职业研究人员最为重要。通过他们的工作,该学科在理论建构及经验材料方面累积研究成果。与之相关,他们具备完善的学术自信心及学科自我意识[2]。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个学科要想取得学科共同体的认可,要想真正独立为一门学科,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既有物质层面的,如图书、期刊、资料等;也有建制层面的,如相应的系科、研究人员、培养体系等;还有理论层面的,如经典的著作、规范的体系等。换言之,一个新学科的合法性可以分为学科的行政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及学术合法性三个部分。学科的行政合法性主要指该学科获得了国家行政审批,有相应的国家批准承认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和刊物;学科的社会合法性是指该学科运用自身关于研究的范式、逻辑起点、学科文化、学科建制,以及学科核心课程等方面获得的成果为公众服务,在此基础上获得的社会理解、认同和支持度。学科的学术合法性主要是指该学科的研究者在学科研究成果上所表现出来的学科理论化、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度与广度。这三种合法性既是相互促进又是相互制约的,但究其根本,学术合法性应是学科合法性的核心和基础,加强学科的“学术性”是提升学科合法性的关键。
然而在成人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由于受认识深度和广度的限制,人们对于成人教育和成人教育学不能做出必要的区别,反而将二者混为一谈。我国学者瞿葆奎教授等在《西方教育学史略》一文中曾评析道,在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似乎将作为一门学科的‘成人教育学’(Andragogy)与作为一种教育活动、过程、事业的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混为一谈了。”[3] (P355)在中国,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成人教育学是一门以成人教育为研究对象,探讨成人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在这种定义下,成人教育学与成人教育的关系显得十分暧昧。事实上,也正因为这种暧昧的关系,最初的成人教育学才获得了作为一门学科的行政合法性,即政府部门以为成人教育学就是研究成人教育如何发展的科学,因此,在建制层面确保了成人教育学的合法存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合法性是一种让渡的合法性,即成人教育学的合法性是通过成人教育的合法性让渡而来的,而非学科本身的合法性。因此,政府部门可以将成人教育学列为学科,而学术共同体却难以认同。究其原因,那就是成人教育学获得的是学科的行政合法性,而非学科的学术合法性。学科的行政合法性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合法性”,即成人教育学的合法性是通过人们,尤其是成人教育决策和主管部门的行政人员的“非理性决策”获得的,这种决策使得成人教育获得了合法性,而不是成人教育学本身足够挣得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事实是:一旦成人教育失去了政府的强力支持和保护(如1998年国家教育部成人教育司的撤并,以及随后各省市教育厅成教处的消失),成人教育学的发展似乎就失去了方向,陷入了低谷。这种依赖政府对成人教育强力保护的做法,在成人教育发展的初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很大程度上又削弱了成人教育本身探索成教特色的紧迫性,抑制了成人教育实践对成人教育理论的需求。比如,成人高等教育中不断出现的“替代论”、“取消论”、“合并论”等错误观点,就直接地反映了人们对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忽视与冷漠。因为能否探索出成教特色和有无科学规范的成人教育理论指导,对成人教育的生存与否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恐怕是中国成人教育学尚未得到重视和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成人教育学研究的本质所在应是“成人性”,而不是笼统的“成人教育”。因为以“成人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一定仅是成人教育学。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个性并真正独立于其他学科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特别的学科,是因为它研究的现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4] (P120)成人教育学的合法性之基础在于对“成人性”的科学诠释,这是成人教育学发展的逻辑起点。成人教育学离开了“成人性”的研究,而其研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学科的立足点和存在的基本理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我国的成人教育需求非常强烈,实践样式也是纷繁复杂,然而我国成人教育学在“成人性”研究上的缺失,却导致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步履维艰,屡遭诟病。我国学者高志敏教授曾分析说,翻开我国当代的成人教育理论期刊和成人教育理论著作,我们就会发现我国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表现出三种取向:政策诠释、经验总结和理论演绎[5]。这三种研究取向都不利于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因为政策诠释将导致理论的政策化,偏离了理论的学术精神,用各种政策口号取代学理分析,容易走向理论的俗化,不利于成人教育知识的积累;经验总结往往会导致理论的粗糙和板结,不利于成人教育学话语的独立、发展和完善;而理论演绎,则使得成人教育学成为普通教育学的翻版。这三种研究取向,形成的后果是,当我们过于依附政府时,必然会使研究成果等同于国家政策的注释;而当我们过于依附实践人员时,我们不得不在作经验总结工作;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过于依附其他学科的知识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失去“理论研究者”的研究主体性和自主性,成人教育理论变成了其他学科的附庸。这三种研究取向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实质都在于“成人性”研究的缺失和肤浅,导致成人教育学学术合法性的低下,最终造成整个学科的合法性的危机。
二、提升“成人性”: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呼唤
(一)西方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西方成人教育学如果以1921年,世界第一个成人教育系在英国的诺丁汉大学成立为标志,至今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西方的成人教育学研究中,曾存在两种主要的研究价值取向,一是彰显“成人”与“儿童”不同的“成人的教育学”;二是更多地从教育过程而不是从成人本身来研究,试图融入现代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成人教育的科学”。这两种研究取向对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都存在不足,如“成人的教育学”表现出在理论整合和学术深入上的力不从心,无法跨越缺乏系统知识和实证支持的沟壑。而“成人教育的科学”却遭到了来自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内部的质疑,像沦陷区一样,时时受到外来的威胁和控制[6]。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不断的争论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何在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上重新发现“成人”,重建学科的“成人”意识,加强成人教育学科的特殊性和完整性研究,已经成为成人教育学科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研究课题。事实业已表明,在西方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建构上留名的往往都是突出了“成人性”研究的著作。如1926年美国人林德曼发表的《成人教育的意义》,是世界上最早以“成人教育”命名的,为成人教育奠定理论基础的著作。他借鉴进步主义哲学思想,对成人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作了系统而全新的哲学阐释。1928年美国人桑代克发表了《成人的学习》,他从心理学的视角,廓清了过去一般人对成人学习能力的误解,科学地指出:“学习之能量永不停止,成人的可塑性或可教性仍大,25岁后仍可继续学习”。1935年桑代克又发表了《成人兴趣》一书,更为具体集中地研究了成人学习的问题,为成人教育学奠定了心理学依据。
在此基础上,1970年美国著名成人教育家诺尔斯出版了《现代成人教育的实践:成人教育学和儿童教育学的对照》一书,具体分析和阐述了作为学习者的成人与作为学习者的儿童之间的不同特征,由此指出了成人教育的使命、功能、形式以及促进成人教育和学习的一系列方法和途径。该书在世界成人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凸显了成人教育学的独特性质,捍卫了成人教育学研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尊严。诺尔斯本人由此被国际成人教育界尊崇为“成人教育学的大主教”[7] (P64)。
(二)教育学科的争论和反思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众所周知,随着人们理性的自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面临着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强烈的挑战。从1989年陈桂生发表《教育学的迷惘和迷惘的教育学》[8],到1995年吴刚发表《论教育学的终结》[9],再到2001年赵蒙成发表《教育学的迷惘》[10],教育学在学界众人面前越来越处于尴尬的境地。教育学的迷惘,实际上表达了人们对于教育学存在和发展状况的种种困惑。教育学是不会迷惘的,迷惘的只能是教育学者。通过持续的争论,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学的存在是合理的,种种困惑多源于人们对于教育学及其发展的个性缺乏深刻的洞察,在于教育学知识缺乏生命意识,缺乏实践意蕴,缺乏个性色彩。这种来自母体学科的持续讨论,同样也在锻炼、激励和启迪着成人教育研究者,对中国成人教育学研究有着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伴随着成人教育研究者理论素养的逐步提高和学科反思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成人教育学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和反思,成人教育学必须体现成人特色,要有自己的“学科意识”,以成人教育学独特的研究范式建立其课程核心地位,提炼其学科的主干,构建独特的学科文化,体现出学科的“成人性”和“反思性”,最终以学科建制的合法性攻破“总学科圈”中其他学科的“学科壁垒”,使得成人教育学从经验水平的学科,上升到科学水平的学科。
(三)当今中国成人教育的转型也深切呼唤成人教育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成人教育一直沿袭着“普教化”的发展模式,因而对成人教育学的理论指导需求不大。而现在成人教育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当今中国成人高等教育凸显出来的招生人数急剧下滑,考试舞弊现象严重,承受着不断加大的“成人教育穷途末路,走向黄昏”的訾议和诘问,究其原因就在于成人高等教育脱离甚至丧失了“成人性”。因为当今的成人高等教育已不再是为工作的成年人提供一个继续教育的平台,而更多是为普通高考落榜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在,是成人教育回归本位的时候了,其振兴之路就在摆脱以往成人教育“非成人性”的教育发展模式,关注成人生活,回归成人的生活世界,不断满足成人受教育的主体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成人教育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除了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努力获得成人教育的行政和社会合法性外,还必然会从根本上要求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在理论上提升成人教育的学术合法性。因此,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不断进取,回应实践的召唤,相信成人教育学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