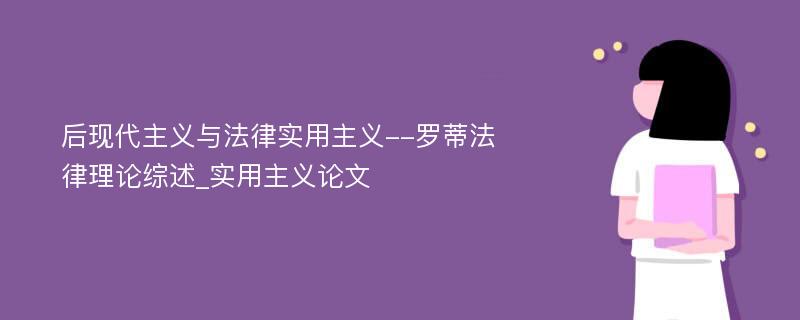
后现代与法律实用主义——理查德#183;罗蒂法律理论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查德论文,概观论文,法律论文,实用主义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实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后现代主义“最近的堂兄弟姊妹。”新实用主义酷似后现代主义是因为它与后现代一样坚信真理和知识是文化的、语言的和生成的。另一方面,新实用主义又不象后现代主义,因为它很少关心于揭露现代性的弊端,更多的是为解决手边的问题提供一种工具、方法。新实用主义的先锋人物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撰写法律方面的文章不多,然而其作品被众多法律评论文章所讨论,并且在法律研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 反基础主义:法律实用主义者的立场
罗蒂认为,“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是同义语,都认为偶然性不可避免,对理论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反对法律形式主义,特别是兰德尔的“法律科学”理论——“作为科学的法律是由原则和原理构成的。”[1] 而罗蒂认为, 兰德尔的法律理论已经遭到来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女权主义、种族主义等激进思潮全面、无情的质疑,法律人现在愿意以更开放的态度思考法律。这些倾向表明人们开始拥抱实用主义。
林恩·贝克教授指出,“一个作为进化论的反基础主义的、社会变革的观念可能既冲淡预言者本身洞察力的信心,又可能冲淡其实现社会变革的动机。”[2] 作为对林恩·贝克教授的回答,罗蒂指出,如果结果确实如此,那么这种预言者就是那种糟糕的预言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本身就是某种权威性的声音,而从不顾及其思想应用的后果如何。”[3] 罗蒂将预言家分为“糟糕的预言家”和“好的预言家”,预言家在法律界指律师和法官。“糟糕的预言家”将他们自己本身作为某种神秘物事(如真理、理性、法律的精神等等)的权威性使者,并且以它们的名义布道。他们用来辩护其主张的方式更多地诉诸于其权威性,而非其主张所带来的变化结果。而“好的预言家”将他或她本身视为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或者是类似于一种新的和有用产品的发明者。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具有“合法性”或“权威性”,好的预言家从不宣称他或她的建议是基于某种神秘物事。对未来来说,好的预言家以结果来衡量他的或她的建议的价值,而不是通过是否建构在观念的完美性和体系性上。
因此,罗蒂认为,对预言家们来说,使“他们所支持的社会变革作为巨大的、无穷的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予以概念化非常有用,因为这帮助他们摆脱了关于寻找权威典据的困境。将它们的观点概念化为一个长期进化过程的一部分,恰恰表明了他们对最后事物的偏爱。这最终导致他们采取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方法”——“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4] 这种“好的预言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实用主义者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罗蒂的答案是,“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中,如果我们实用主义者对任何事都有益,这是因为我们讽刺那种复兴权威的雄心壮志。”[3] 换言之,只要你认为“哲学”具有内在的赎回权威的名义,你将发现实用主义非常令人失望。 罗蒂承认实用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平庸的,因为它并没有为解决案件提供指南,也没有提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关于法律或正义性质的法律理论。但是罗蒂认为,实用主义可能对那些仅仅需要从理论的激战中挣脱出来的智识预言者有用,因为他们很少陷入此类的争论中。罗蒂指出,实用主义的一个益处是,“很难说某人拥有的东西是巨大和强有力的。”[5] 因为大多数实用主义者是否定的,即不认为能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而仅仅是关于促进对话的建议。
这种实用主义立场的一个显著命题就是“理论(广义上解释为与行动相分离的活动)在法理学中不是非常重要。”[6] 罗蒂主张,根本不存在能辨别判决的正确与错误之普适的法律理论,不存在能预先告知法官如何做出正确判决的公理。他同意格雷(Thomas C.Grey)的观点,“……实用主义拒绝这样的格言,即你能用一个更好的理论击败另一种理论,不存在理性的神的预先保证:重要的实际活动的领域将由美好的理论统治着。”[7] 正确的理论必然导致正确的判决或者关于疑难法律问题存在正确答案只是法律哲学家的一种幻想。这意味着由德沃金所实践的那种法律哲学对富有想象力的法官来说作用不大,因为他为法官描述了一系列复杂的规则,以供法官在寻找正确答案时使用。相反,对罗蒂来说,在决定案件时,人们只能构造一个观点,然后去实践它。
从罗蒂的这种粗线条的、写意式的法律理论中,人们依稀可以察觉,罗蒂支持一种后现代的、实用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经验的、讽刺的法理学。他不能为法律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例如,法官应该如何做出裁判——提供确定的答案。他所提供的只是这样一种答案:“任何人,谁相信存在关于这些问题的有充分根据的理论答案——解决这些道德困境的运算法则,那么他在本质上仍然是个形而上学论者。”[8]
二 种族中心主义:法律知识的语境论
罗蒂主张种族中心主义的真理观,种族中心主义者认为,根本不存在独立于我们之外的普适标准,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出发,从我们自己的种族出发,而不是从某个不可比的绝对命令和范畴体系出发。罗蒂不否认世界是自在存在的,在时空中的绝大多数事物都具有因果律,因为它不是我们的创造物。但是当论及真理问题时,他总是要将其置于特定的语境中,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真理,而语言是人类的创造物。世界不语,语者惟人。[8] 种族中心主义主张,真理标准是在一定背景下约定俗成的东西。因此,“真理”是由具体而历史的群体约定的,与实在无关;真理的基本属性不再是客观性,而是协同性(主体间性)。
然则我们如何获得这种真理呢?就是要不断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对罗蒂来说,所有语境都是平等的,应该消除那些与“硬”事实相对应并具有特权、成为范式的语境,倡导平等对话的权利。种族中心主义并不拒绝与其它共同体对话,相反与其它共同体对话恰恰是种族中心主义一个值得称道的德性,“我们与其他共同体和文化的交流,不应当被看作是在来自不可比较的第一前提和不可调和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9] 为此,我们要做的正是不断地与别人、别的共同体和别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从而超越自我,使“我们”不断地扩大其范围,使“种族”之间不断地融合。最终,罗蒂以政治问题取代了认识论问题,真理不是认识的集合,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受种族中心主义真理观的影响,罗蒂主张语境性的法律知识论。他认为,法律理论、正义和道德观念嵌入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语境)中,由此我们必须着眼于我们文化中的传统和习惯。寻觅超文化的、非历史的正义和道德的所有企图最终都已经失败了,失败使我们强烈地认识到,寻找完整的、普适的道德原则或法律理论的计划是拙劣的幻想。正如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言,“不包括任何特定社会道德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四世纪雅典的道德是存在的,十三世纪西欧的道德是存在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道德,但是它们都是各具特色的、毫不一样的。”[10] 沃尔泽(Michael Walzer)也认为,正义是相对于特定社会而言的。如果大多数人以某种方式生存,而这种方式对其成员的共享的理解力是可靠的,那么这一个给定的社会就是正义的。[11] 同这些思想家一样,罗蒂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合理性”的追求,因为每一个合理性的观念都是存在于一定的传统中:“我们不应该过多的使用象‘客观价值’和‘客观真理’这样的观念。我想,在大多数对传统哲学谈论‘理性的批评中,后现代主义者是正确的。”[12] 客观性的丢失意味着哲学(包括伦理学和法学)必然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我们将从我们之所在的地方出发。”[8] 罗蒂认为,虽然德沃金批评实用主义,并且坚持疑难法律案件中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德沃金也不再试图谈论什么“客观性”了。而且,德沃金对“作为整体性的法律”描述,与卡多佐在对“作为立法者的法官”的论述,并无二致,似乎仅仅在苦心经营的程度上存在区别。
实用主义者在解决疑难案件时,通常趋向于最佳选择,而这种选择必定是依据背景因素的一个有水准的猜测。罗蒂举例说明,当法院被问及为什么“人不可侵犯”时,假使法院的答案是:这个原则体现在大多数美国人的信念中,它是我们道德和法律传统的中心,并且法院不可能在它之后寻找到其它前提。这种回答就类似于罗尔斯在回答他的正义观念是政治的,不是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罗尔斯指出,“作为正义的观念是物质的,在一定意义上,它来自并隶属于自由思想的传统以及民主社会政治文化中最大的共同体,它不是普适的,通过交流行为理论建立起来,因此成为准先验的前提。”[13]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实现了从形而上的、道德的向现实的、政治的转变,抛弃了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正义观念,强调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合理多元主义事实,现代民主社会的统一和稳定不再可能建立一种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全整性和一般性的正义理论,社会统一依赖于各种全整性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总之,罗蒂法律知识语境论的必然结果就是,法律理论不能建构在坚实的阿基米德式的基础上,而必须建构在特定文化场域中的原则和实践上,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法律理论明显地带有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的特点。罗蒂指出,“我们必须从我们之所在出发”,其含义是指,我们追求正义的努力要构筑在已经深深嵌入在语境——我们的偶然制度和实践中的正义观念的基础上。
三 反对方法:“创新精神”的工具主义
罗蒂认为,古典实用主义具有一种信奉科学主义的倾向,而罗蒂扯起了“没有方法的实用主义”的大旗,而其实质就是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认为,古典实用主义的“科学主义”无非是反对墨守陈规,打破陈规陋习的禁锢,主张创新精神。要达到此目的,并非离了科学就寸步难行,现代先锋艺术的大胆创新、不断追求的精神,丝毫也不让于科学。因此,强调大胆探索、不断实践与拘泥僵硬的‘科学’方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恰恰说明实用主义“没有方法”的一面。昔日的同盟军现在成了危险的敌人,过去的解放力量现在变成了压迫与统治的势力,而实用主义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一贯价值取向却始终不渝。[14] 实用主义今天的主要对手是科学主义,它应该去除“方法”,涤清传统实用主义中的科学主义色彩。
对于科学的态度,一方面,罗蒂承认科学在认识、改造自然、改善人类生活和提高人类文明水平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反对对科学主义的盲目崇拜,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不存在任何独特的标准和方法,科学活动与艺术、政治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罗蒂的科学定义是宽泛的,“如果在信仰改变上运用了强力……(或者是)我们辨认……(不了)我们的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关联,”我们就不能称这种信念形成方法为科学。[15] 实际上,罗蒂主张“科学家的形象将不是把事情搞清楚,而是使事物创新。”[16] 显然,罗蒂的这种科学观与实用主义的向前看的、创新的工具主义进路是一致的。
罗蒂明确承认这种“没有方法的实用主义”特别受到费耶阿本德的影响,变得开始怀疑“科学方法”。他指出,这种“没有方法的实用主义”对法律理论非常重要。罗蒂追随杜威的信仰,即实用主义支持社会实验高于理论,具体来说,这种思想实质就是律师和法官应该提出一种关于法律问题的新观点,检验标准是其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如何。实用主义的一个益处就是脱离了关于某物的科学性的焦虑。[7] 这些观点有没有得到哲学的支持,对它们来说,并不重要。罗蒂认为,提出一种观点实质上类似于在“黑暗中跳跃”,这种跳跃是一种浪漫的行动,它试图通过创造性的、诗一般的想象锻造一种新的法律范式。在罗蒂看来,一个法官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试图成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能认真考虑到我们共有的传统和渴望。[6]
当然,罗蒂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实用主义者在解决疑难案件时,必须采取一种无原则的跳跃的方法。相反主体的立场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就界定了理论的范围。他认为,一个好的法官不能通过遵循先例以霍姆斯法官的“坏人的信念”为标准来行动,他或她也不能像一个随心所欲的哲学王那样行动来实施个人的道德观点。法官们必须应围绕案件,试图成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当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时,结果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要求,要求法官为了美好的民主社会发现新的方法,承担改造社会的任务,将法律理论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
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罗蒂审视了美国的一些著名案例。他认为,一些被认为是20世纪最好的法律判决,如果从传统的法律观点来说,可能是失常的和混乱的,因为它们绕过了法律已经确定的领域,或者说固有的模式。罗蒂认为,我们偶尔需要富有想象力的范式转换来打破一个不合时宜的先例之链。例如Brown v.Broad of Education和Roe v.Wade案件的判决就是最高法院司法激进主义的结果,在判决中,最高法院拒绝服从先例或者等待国会立法。面临难题,最高法院没有逃避,相反通过扩大基本权利的范围,它跳跃了一下,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实验。虽然法官们不可能预先知道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判决,然而罗蒂将这些判决当作是富有想象力的一种实验,一种“黑暗中的跳跃”,并且这种跳跃最终创造了一个经结果证实,行之有效、好的实验。
总之,对罗蒂来说,不存在专门预先告诉法官如何裁决案件的方法,人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建议一种关于未来的更好方法,并且期望它在实践中能够成功。虽然,法官应遵循先例,但是遵循先例可能导致不公正,如Bowers v.Hardwick案件;同时也存在必须遵循先例的案件,如Roe v.Wade案件。即使如此,也不可能预先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公理来决定何时应推翻先例,并确立一种新的法律原则。我们所能做是要求法官朝着一个美好的社会工作,然而这不能依靠一个法理学的公理以一种系统的方法来完成。[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