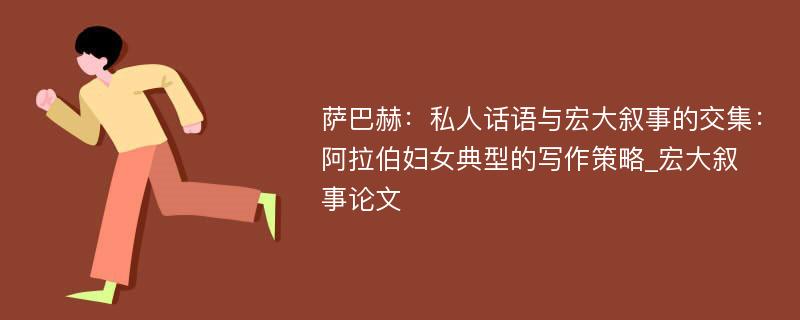
苏阿德#183;萨巴赫:私人性话语与宏大叙事的交叉层叠——阿拉伯妇女写作策略的一个典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宏大论文,阿德论文,话语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阿德·萨巴赫(1942—)是科威特著名的女诗人,不仅在海湾各国声名远扬,而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她的诗歌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总体上是属于抒情诗而非叙事诗。但这里所说的私人性话语与宏大叙事不是从叙事诗的概念出发的,而是从文学作品对时代、环境和社会真实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注:专门研究叙事学领域里具体的对话理论的董小英指出:叙事的本质是信息的传递,是交流过程中一个单方面的发射过程,叙事文本是一个被发射的信息集,叙事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途径进行。绘画、雕塑、服饰和建筑等都包括在广义的叙事之中。而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则是指诗歌辞赋、小说故事或数理逻辑符号、电报密码等以文字符号记录的语言所叙述、描绘事物的方式。叙事是语言表达的内容,是语言产生的目的,同时是语言产生的原因,叙事是语言的母亲,也是语言的儿子,正如罗兰·巴特所言:“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参见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1页。 )角度来考察的,把它看作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映照。
在历史叙述中以私人生活和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 )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构成了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宏大叙事”似乎总是居于强势地位,具有一种强迫性,常常对“私人性话语”进行涂抹、覆盖、清除或侵犯,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结果是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注:参见雷颐:《“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读书》1997年第6期,98页。)苏阿德·萨巴赫作为一位女诗人, 和其它的阿拉伯女作家女诗人一样重视对女性个人经历和个体经验的叙述,反映阿拉伯女性作为一个边缘群体所受到的主流文化的挤对。苏阿德·萨巴赫看到构建主流文化的“宏大叙事”的压迫性,作为一位有强烈使命感的女性诗人,她不顾重重阻力,试图以其私人性话语对抗主流文化,并努力使其私人性话语汇入宏大叙事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女性诗人,她不满于男性对宏大叙事的支配权力,不时走出私人叙事的圈子,直接运用宏大叙事参与总体文化的建设。于是,我们在她的诗中看到了私人性话语与宏大叙事的交叉、层叠,造成私人性话语与宏大叙事的双重效应。
苏阿德·萨巴赫诗歌的抒情性质决定了她的创作必然倚重私人叙事。黑格尔在论述抒情诗时谈到伊斯兰教系统的诗。他认为阿拉伯——伊斯兰的抒情诗中,“诗人把他们的内心世界及其活动,特别是欢乐的情绪和情境,坦率地随便地表现出来,这样就会把凡是在他内心里出现过的东西尽情吐露出来。”而诗人所最常用以表现的形式主要是显喻、隐喻和意象。“这种显喻、隐喻和意象虽然使始终力求表现的内心生活有外在事物可凭依,毕竟不是所要表现的情感和对象本身,而只是一种由诗人主观臆造的用来暗示情感和对象的表现方式。”(注: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981年第1版〉, 第三卷下册,224、230页。)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秉承了阿拉伯抒情诗的主观性,凸现了诗人的个体意识,从而使其大多数的诗作成为一种私人性话语。
苏阿德·萨巴赫的私人性话语是从个体作为一个人的独立存在延伸到作为女性的个体与自我,再延伸到个人在家庭、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描述个体的生活经历与经验。所以,我们看到她在诗中描述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描述自己作为一个女儿、一个恋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阅历和感受。她满足于运用极平凡的内容表现心灵本身和单纯的主体性格,表现情感的波动和灵魂的震撼。那闪电似的无忧无虑的笑声,内心的欢呼,一纵即逝的愁伤、哀怨、怅惘和悲叹……等等情感生活的全部浓淡色调,无论是瞬息万变的动态或是凝滞不动的静态,无论是对宇宙的总体把握,还是由极不相同的对象所引起的零星的飘忽的感想,都通过主体的内心运动凝定于其诗篇之中。
在大男子主义思想仍然盛行、一夫多妻制仍有市场的阿拉伯社会,在部落意识仍有残余的海湾社会里,作为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知识分子和女诗人,萨巴赫希望男人成为女人的朋友,而不是女人的敌人、女人的压迫者,希望可以“同你一道漫步在草地”,“与你共读一本诗集”,希望得到男性在感情上的真正投入。她并不稀罕男人为爱她而提供各种物质享受:“不!/我不要你为我买一只游艇,/也不要你送一座宫殿。/不!/我不要你似雨般地为我喷酒法国香水,/也不要你交给我月亮上的钥匙串……”这些东西不能让她感到欢快感到满足,她只是希望男性作为一个朋友在她的情感生活中甘苦与共,同欢乐共患难:“我向往几小时同你一起漫步/共听小雨淅淅沥沥/当悲伤让我沉寂/当烦恼令我哭泣/我向往能在电话中听到你的话语……”(注:《做我的朋友》,见《本来就是女性》集(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men),London,Riad El-Rayyes Books Ltd.,1988,pp.9-14.)
在另一首较多地体现其私人叙事特征的诗中,萨巴赫吟道:
小姑娘的时候,
我曾以为
树是世上最高的地方。
及至长大成人,
爬在你的肩上,
我才知道你比所有的树都高。
睡在你的怀里,
又甜……又香,
像覆盖着月光……(注:《世上最高的树》,《本来就是女性》集,54页。)
这些简简单单的句子经过诗人萨巴赫的组合以后,具有了深刻的内涵,使普普通通的话语充满了浓浓的诗意。头一句说“我曾以为树是世上最高的地方”,显得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等到吟出第二句“及至长大成人,爬在你的肩上,我才知道你比所有的树都高”,那违反生活逻辑的话语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并产生疑问:“为什么人会比树还要高?”如果说一个人比刚刚长起来的小树高,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诗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是比“所有的”树都高,也就是说,无论多高的树,都没有诗人心目中的“你”高大,这就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了,这个世界上的大个子、超常的巨人身高超过2 米亦属罕见,连普通的树都比不过,更不用说参天大树了,可是诗人偏偏要那么说,显然是在表面的文字底下还隐藏着另外的意图,于是读者产生了赶紧继续读下去以便搞清真相的急切心情;等到读完最后一句“睡在你的怀里,又甜……又香,像覆盖着月光……”诗人的“言外之意”才渐渐显示出来,“覆盖”一词画龙点睛地暗示了诗人的情感隐秘,我们从这一词语才知道诗人是如何比兴的;树能供人遮荫,“你”能给“我”提供庇护,“你”那坚实的肩膀和宽广的胸怀给“我”以极大的安全感,使“我”睡在“你”的怀中有如覆盖着柔美的月光,感到安稳、甜蜜、美妙。回过头来,重读前面的诗句,我们又有了新的感受和体悟:爬到树上,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但毕竟有限得很;而站在“你”的肩上,借助“你”的知识、阅历、见识和“你”的支持帮助,我能够认识广阔的世界,所涉猎的范围之广,是站在一棵树上所无法比拟的。而这一点,在“我”幼小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认识到的,只有当“我”长大成人,具备了一定的思想和认识水平以后,才能有所体悟。像这种具有私人叙事特征的诗作在萨巴赫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在建构私人性话语的同时,苏阿德·萨巴赫还不时运用宏大叙事参与主流文化的建设。她认为在阿拉伯共同的事业上,不应把阿拉伯女性排除在外。特别是要让知识女性参与进来,发挥其积极作用。她说:“作为一位有文化的阿拉伯女性和科威特女性,我不能站在历史运动的边缘,我不能对阿拉伯大祖国的土地上发生的各种事情袖手旁观。我们周围尽是废墟。我们针对落后、暴虐和新旧殖民主义者而投入的一场场战斗,不能将男女截然区分开来。性别不能豁免任何一个人参加到保卫行动中去——保卫阿拉伯大家庭,保卫阿拉伯的未来,保卫阿拉伯的根基及其宝贵品质。”(注:参见拙文《诗人与学者的情怀》,《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4期。 )正是因为执着于加入到阿拉伯历史运动中的信念,诗人能够从表现女性自我、女性意识和宣泄自我的女性话语中走出来,进入宏大叙事的历史叙述。我们从苏阿德·萨巴赫的诗中可以读到她对阿拉伯主义的赞扬,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大一统的热情讴歌,对阿拉伯光荣历史和科威特祖先业绩的缅怀,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对阿拉伯大祖国四分五裂的叹息,对科威特祖国的深情思恋,对阿拉伯社会仍然落后、愚昧状况的忧患意识,还有她对以色列人侵占巴勒斯坦人家园的切齿痛恨,对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批判,对西方腐朽文化渗透的抗拒,对阿拉伯社会专制、暴虐现象的鞭挞,……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苏阿德·萨巴赫对宏大叙事的成功驾驭,使她摆脱了女性诗人角色而成为一位可以与男性诗人并驾齐驱的杰出文学家。她在文学领域的成功运作,使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从而为自己树立了强大的自信心和作为一个人的自尊(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女人的自尊)。
对阿拉伯的历史和文化深厚的感情是诗人萨巴赫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根基。近古以降,阿拉伯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渐趋衰微,盛况不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渐落于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犯与压迫,则无异于雪上加霜,在阿拉伯文化的复兴道路上设置障碍。对此,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阿拉伯女性诗人,萨巴赫无法缄默不语。她大声喊道:
兄弟,燃烈你们的仇恨,
我们血管中的自尊并未亡身
荣耀吸吮的营养
正是我阿拉伯主义之心的底蕴。
昔日是优越,
是勇于牺牲和献身。
法特梅·宰哈拉是我高贵的母亲。
我伟大的姐妹韩莎与我情深。
我尊严的阿拉伯之父
使大地遍是吉祥,
在他的保护之下,
众先知出现来临。
我的兄弟击败了十字军。
但愿那些残肢断臂张口语真。
我的家乡贡献出无数牺牲,
我的孩子们或是英雄,
或是烈士捐躯牺牲。(注:《希冀》集,苏阿德·萨巴赫出版社,1996年版,18—19页)
(《阿拉伯的呐喊》)
在诗人萨巴赫的眼里,阿拉伯主义是和阿拉伯的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既有历史人物如法特梅·宰哈拉、韩莎等的英雄事迹,又有全民同心同德抗击外来侵略(如十字军)的光辉历史;既包含着宗教(伊斯兰教)给阿拉伯人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又包含着阿拉伯传统所积淀下来的一整套价值(如勇于牺牲和贡献的精神)。
在历史上,阿拉伯曾拥有光荣的过去,有过辉煌的文化,有过统一的大帝国。但现实无情地粉碎了诗人萨巴赫及其同胞的阿拉伯之梦。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不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近代以来阿拉伯民族落后于时代,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强权凌辱下软弱无力,使诗人深感阿拉伯民族自尊地丧失,昔日荣耀已春光不再。贫穷、愚昧、落后,抱残守缺,因循守旧,泥古不化。……这就是阿拉伯社会自近代以来毫无生气的生活写照,法国旅行家福尔尼在18世纪末游历埃及时,对阿拉伯社会的恶劣状况深表诧异:“愚昧是普遍的……遍及所有阶层,表现在一切精神的和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表现在艺术上,甚至手工业生产也极为原始。”(注:转引自[黎巴嫩]汉纳·法胡里:《阿拉伯文学史》,郅溥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537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直到苏阿德·萨巴赫的青年时代(20世纪50—60年代)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尤其是诗人的祖国科威特和周围的海湾社会仍处于极端落后的封闭状态。即便在六、七十年代海湾各国发掘、开采石油,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换取了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大男子主义观念,一夫多妻的思想等各种传统观念仍大量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
尽管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使诗人萨巴赫感到失望,但她对阿拉伯的前途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对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民族性格光辉的一面深感骄傲与自豪:
“他们的剑囊中,
饱藏精良的装备:
那是优良的传统、高尚的道德
舍身奋战的激情和勇力。……”(注:《希冀》集,苏阿德·萨巴赫出版社,1996年版,8页)
(《珍珠时代》)
那优良的传统、高尚的道德统摄于“豪侠”的最高标准之中。在宗教或部落之间发生冲突、战斗时,敢于冲锋陷阵,即便赴汤蹈火,牺牲性命亦在所不辞;在宰牲待客、济困扶危帮助他人时,即使倾其所有亦在所不惜。(注:参见[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纳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一册(黎明时期),10页。)总之,慷慨大方、豪迈仗义,勇敢善战,扶危济困……等各种美德仍然存在于阿拉伯社会中,这种善的根源正是阿拉伯未来前途的基础。
因此,苏阿德·萨巴赫紧紧地抓住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不愿放弃之。她在诗中吟道:
“难道可以取消我的阿拉伯身份?
我的身躯是一棵枣椰树,
吸收的水分来自阿拉伯的大海
在我的心扉上刻画了
阿拉伯所有的希望、过错和悲哀……”
(《我是科威特的女儿》(注:《急电致祖国》,苏阿德·萨巴赫出版社1994年版,10页。))
无论阿拉伯主义带给她的是希望还是失望,是欢乐还是痛苦,诗人萨巴赫都愿把它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中,时时刻刻与之相伴相随。
在成功地运用宏大叙事进行历史叙述并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以后,苏阿德·萨巴赫才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感觉,才有了蔑视男性权力话语的资本。90年代中期,她在接受采访时曾发表自己的观点,说道:“在我们的国家,只有男人独自在政治舞台、经济舞台和文化舞台上戏耍。当前发生的事件全都证明了男人的失败,在政治上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同样在文学和艺术等领域也是失败的。女人为什么不介入她可以做到的拯救(活动)中去?”(注:《这就是埃及——我青年时代的游乐场》,埃及《大家》杂志,总第372期,1996年7月2日,49页。 )特别是在诗人从事的文学领域,她更是怀着一种傲视文坛的心态。在被问及科威特文学与思想运动中男性文学家是否比女性文学家进步得多时,苏阿德·萨巴赫答道:“科威特男性文学家中并没有超常的巨人,拉开我们和他之间的距离。”(注:《对哈黛·萨曼和马吉黛·鲁米的看法》,《大家》杂志,总第376期,1996年7月30日,32页。)对于那些操纵主流文化话语权的“御用文人”所写的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诗歌,她视之为“乞丐时代”的产物,认为“这些卖诗为生的诗人模式在诗歌的地图上没有它的位置,其命运常常是归于废纸篓中。”(注:《对哈黛·萨曼和马吉黛·鲁米的看法》,《大家》杂志,总第376期, 1996年7月30日,32页。)
在某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看来,向宏大叙事和主流文化的靠拢似乎是偏离了女性的道路,是对妇女解放事业的背离。但阿拉伯当代女性文坛正滋长着这样的一种倾向:一些较为杰出的女作家(如苏阿德·萨巴赫、哈黛·萨曼等)不满足于表现女性自我和过多地沉溺于自我渲泄,而从私人性话语走向宏大叙事。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倾向是女性作家对自我的隐匿:“由关注女性自身命运和生存状态起步,逐步转向其它题材或写作角度,由对自我的大胆、直率的剖露而转向对自我乃至女性经历和感受的隐匿和回避。”(注: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173页。)无论是隐匿也罢, 回避也罢,对于许多阿拉伯女性作家来说,那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相反地,能够突破题材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她们非凡的叙事能力。在小说领域,叙利亚女作家哈黛·萨曼的《贝鲁特梦魇》、《亿万富翁之夜》,巴林女作家法姬娅·拉希德的《阿拉伯怪骑士的嬗变》(1990),黎巴嫩女作家哈娜·谢赫的《宰哈拉的故事》,以历史的高度和哲学的深度探讨了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社会急剧变革、动荡的时代中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表现出她们驾驭宏大叙事杰出的艺术才华。
苏阿德·萨巴赫和这些杰出的阿拉伯女性作家从私人性话语走向宏大叙事获得的成功,使她们藉此而问鼎阿拉伯文化话语权力。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阿德·萨巴赫和一些阿拉伯女性作家有时候并不赞成妇女文学(或女性文学)的提法,在她们看来,文学就是文学,不应有什么性别之分。
私人性话语和宏大叙事的交叉层叠体现在苏阿德·萨巴赫诗歌创作的各个层面。她早期的创作中多以私人性话语为主,而后期则趋向于更多地运用宏大叙事;在有的诗集中以私人性话语为主如《女人的悄悄话》,在另外的作品中则以宏大叙事为主如诗集《玫瑰与枪的对话》、散文集《难道不许我爱国?》,而更多的是在同一本诗集中既有私人性话语,也有宏大叙事,两者交叉层叠而汇成了较为真实的历史记忆。
即便在最细小的层面上,苏阿德·萨巴赫也以其独特的诗之思完成对某种“真理”的叙述,在同一首诗中造成私人性话语和宏大叙事的双重效应,从细微处见出大道理。一些特殊具体的情境经过诗人的处理,变成了带有诗意的和普遍性的东西,就像歌德所说的,“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注: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外国文艺理论丛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6页。)
苏阿德·萨巴赫深知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把握,所以她选取许多琐细的事情作为写作的题材。有的人担心个别特殊引不起共鸣,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每种人物性格,不管多么个别特殊,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从顽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因此各种现象都经常复现,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只出现一次。”(注: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朱光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10页。)
苏阿德·萨巴赫的诗作中出现的特殊事物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如诗人从陪伴爱子的成长到丧子之痛的经历虽很琐细,她却从中领悟人生,通过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个人经历表达她对人生的思考。如“送子上学”不止是一位“家庭妇女”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的简单描述,而是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性认识。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能因为社会的喧嚷而长久躲在没有风吹雨打的、静谧安宁的家庭,不能因为社会的复杂而长久依赖父母的荫庇,而要努力去适应社会,适应周围的人和环境,最终完全溶入社会。(《送子上学》)(注:《希冀》集,苏阿德·萨巴赫出版社,1996年版,32—34页)在“死亡的飞机”里,诗人眼看心爱的儿子遭受病魔的折磨,听着那“窒息般的痛苦呻吟时断时续”,为之心痛神伤。诗人一直把儿子视为“日月的瑰宝”、“眩目的豆蔻年华”、璀璨的梦想,把他看作自己痛苦黑夜中的“光明和安慰”,是自己的希望和财富。然而这一条鲜活的生命正处在死亡的飞机里向死亡之路走去,在年轻母亲诗人的注视下如一朵鲜花般渐渐地干涸枯萎,失去活力,终至离开了尘世。但诗人在这里不只是为了说明儿子临终的状态,渲泄失子的苦痛,而是同时借此私人性话语表现诗人面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从而汇入了宏大叙事的范畴:爱子的弃世是对她信仰稳固性的一次严峻考验。(《在死亡的飞机里》)(注:《献给你,我的儿子》,苏阿德·萨巴赫出版社1994年版,19—22页。)
又如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读报的经历,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了,但诗人却在短短的几个诗行中向我们揭示出东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在欧洲的咖啡馆里,
我独自读我的报纸;
在阿拉伯咖啡馆里,
所有在座的人却同我一起读我的报纸
(《咖啡馆文化》(注:中文版中易名为《好奇》,原载《本来就是女性》集,108页。)
我们从诗人在诗行中留下的想像空白中可以体会到她所要言说的东西:西方是个尊重个人稳秘、充分享受个人自由的社会,而相比之下,阿拉伯社会(甚至整个东方社会)却没有给个人留下多少私人的空间。虽然东方人能更多地感受到集体生活的意义,但对于越来越重视人的个性的时代里,人们毕竟渴望多少拥有一片只属于自己的空间,在这个独立的空间里自由自在,不受一丝一毫外界的干扰,即便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空间,如能暂时拥有,也是一种享受。诗人在接受穆菲德·法齐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正好可以用来诠释她的这首诗。她说:“我并不以旅游者的眼光去看待各个城市。有些城市美极了,但它不会对我言说什么。而另外有些城市很小,很不起眼,但我在那里却能感受到我的人性,感到我自身的和平,以及与他人的和平。我喜欢那些尊重我的沉默、我的自由,不把鼻子放在我的私事上的城市;我讨厌那些干预我的小问题,冲破我的安详,像秘密警察似地跟踪我去餐馆、咖啡厅和电梯的城市。我喜欢尊重我本人的城市,逃离那些喜好监视人和咀嚼他人身上肉的城市。”(注:《男人是阿拉伯生活舞台的唯一歌手》,《大家》杂志,总第379期,1996年8月20日,34页。)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不一一赘述。
私人性话语和宏大叙事在苏阿德·萨巴赫诗歌创作中的交叉层叠使历史的记忆趋向完整。特别是她的私人性话语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以往阿拉伯男性知识分子所把持的宏大叙事在局部历史真实上的“缺失”,摆脱了阿拉伯文化建构只有男性声音的局面,使之逐渐趋向男女声合唱的真正完整的“交响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