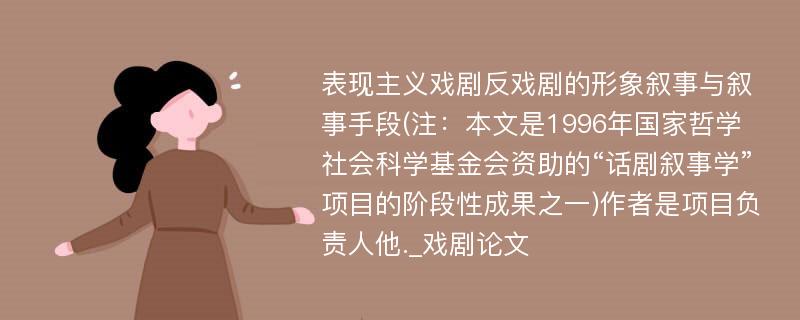
试论表现主义戏剧反戏剧式的意象性叙述方式和叙述手段——(注:本文是199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戏剧叙事学》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系课题负责人。全文共由七个部分组成。由于篇幅较长,本期先推出前三个部分,其余部分我刊将陆续刊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表现主义论文,意象论文,篇幅论文,较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表现主义戏剧对反戏剧式意象性叙述方式的成功铸就和艺术开掘
传统的戏剧叙述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显在戏剧叙述与潜在戏剧叙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戏剧的崛起,戏剧的叙述方式很快又产生了第三个品类:那就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情节结构剧的反戏剧式的意象性叙述(注:见拙文《戏剧叙事学刍议》,《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33页。)。它不注重叙述戏剧情节(无论潜在还是显在),而重在叙述各种复杂的心理情绪和内在意念。它不靠富于个性化的清晰完整的艺术形象来揭示外在的具体真实,却更多地通过人物的意象分裂传递内在的精神真实,从而给欧美剧坛带来了巨大的生命活力。我们且不说在世纪之交崛起的象征主义戏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崛起的未来主义戏剧、超现实主义戏剧、表现主义戏剧,即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崛起的存在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等形形色色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戏剧,都无不采用这种崭新的叙述方式,而且还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乃至巨大的成功。譬如20世纪10年代—30年代在欧美国家盛极一时的表现主义戏剧之所以能够“在其基本技巧方面”,作为现代戏剧史上的“一条具有强大力量和生命力的经受住了考验的线,把诸如斯特林堡和奥尼尔、布莱希特和奥凯西等剧坛巨匠连结了起来”,(注:见[英]J.L.斯泰恩著 象禺武文译《现代戏剧的理论和实践》(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影响所及差不多遍及整个世界,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他们对这种反戏剧式的意象性叙述方式的成功铸就和运用。
严格说来:“反戏剧式的意象叙述”并不是表现主义戏剧的独创,早在它产生之前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戏剧中便已初露端倪。由于它们共同的反现实主义性质,使这种叙述方式一经产生便有了一种一脉相承的发展。王尔德关于“最好的艺术,最好的诺言”(注:转引自李万钧 陈雷著《欧美名剧探魅》,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336页。),“人生不是艺术的镜子,艺术才是人生的镜子”(注:转引自李万钧 陈雷著《欧美名剧探魅》,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336页。)的观点,及《莎乐美》中“月亮”意象的心理外化和意念叙述,我们固然并不生疏。然而象征主义戏剧关于“心理的动作要无可比拟地高于纯粹的外部动作”⑤对写实传统的完全背离及其对象征体外在叙述的多义性和朦胧性的执着追求,才真正最终造就了这种叙述方式的形成。而表现主义戏剧之于这种反戏剧式的意象叙述的贡献无非在于,他们在运用这种崭新的叙述方式进行戏剧叙事时,又创造性地为其增加了一些新的特质。
表现主义戏剧的叙事功能较之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戏剧的最大不同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重新打出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旗号,一反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主张。这大概是由它们各自的时代要求所致。他们十分善于把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放在人物的心灵内部来进行。鉴于他们对人类未来的高度自信,他们的创作往往带有很强的启示录性质。他们要么表现对现代文明的反抗(诸如德国作家格奥尔格·凯泽的《煤气》和《美杜莎之筏》、捷克作家卡莱尔·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美国作家埃尔默·赖斯的《加算机》),要么表现人对自我的寻找(诸如凯泽的《从清晨到午夜》、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毛猿》),要么表现传统观念对人性的束缚(诸如德国作家韦德金德的《青春的觉醒》、哈森克勒弗尔的《儿子》、恩鲁的《家庭》),要么反对战争,宣扬和平与社会革命(诸如德国作家恩斯特·托勒的《变形》和《群众与人》、美国作家欧文·肖的《埋葬死者》),要么强调人更新,呼唤“新人”的诞生(诸如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德国作家佐尔格的《乞丐》)这些作品,对人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都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热忱和关心。也许正因为此,不少表现主义作家在生前都受到过纳粹政权的迫害监禁。
表现主义戏剧在艺术上同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最大的类似之处,除了反现实主义性质之外,还在于它们都需要借助于现代化的剧场充分而又全面地表现剧作的基本主题。唯美主义戏剧最看重的是预示人物命运的主题意象的设计,象征主义戏剧最看重的是象征体丰富指向的情绪意念,而表现主义戏剧作为一种大多建立在剧作者的自传性事件上的“灵魂的戏剧”,往往具有一种浓郁的“自我戏剧”和“忏悔戏剧”的意味。由于他们过于热衷于灯光和色彩对内在意象的外化实验及演员极度主观主义的夸张表演,以致于还形成了演剧风格的三个基本类型:A.精神型(Geist);B.狂喊型(Schrei);C.自我型(Ich)。在雷内特·本森看来,“精神型”最为抽象,它赖以表现的多是些“没有传统的戏剧人物或复杂情节的纯表现的最基本的视觉形象”。(注:见[加拿大]雷内特·本森著 汪义群译《德国表现主义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页—9页。)“狂喊型”赖以表现的多是一种多少有点朦胧的“真正的梦境”。而且梦境中的“戏剧动作、场景、语言、动机以及心理逻辑都毫无例外地变得稀奇古怪、非同寻常”(注:见[加拿大]雷内特·本森著 汪义群译《德国表现主义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页—9页。)。“自我型”中赖以表现的情境氛围尽管同“狂喊型”颇为类似,但其表现的重心却主要是在中心人物身上。正是由于表现主义戏剧这些丰富的演剧风格对舞台艺术的一系列创造性的大胆探索及其对写实主义风格的传统背离,给这一现代艺术的发展带来的众多可能性,才造就了莱因哈特、杰斯纳、富茨旺格、布莱希特等一大批世界水平的著名导演和欧美戏剧某一时期的极度繁荣。
因此,我们说表现主义戏剧的叙述方式和叙事规律是十分值得探讨的一个叙事现象。作为一种反戏剧式的意象叙述,无论其文本叙述还是舞台叙述,都为现代主义戏剧提供了新的特质。这里想以斯特林堡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格奥尔格·凯泽的《从清晨到午夜》、恩斯特·托勒的《变形》等若干部作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表现主义戏剧的文本叙述和舞台叙述所铸就的一系列新的艺术特质作一探讨。
二、主题叙述:剧作者主观意念的全面外化和符号化
表现主义戏剧的崛起和繁荣显然与本世纪头25年出现的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表现主义戏剧早期阶段的剧作家大都喜欢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为基础揭示和表现自己内在的隐秘世界,实现自身下意识观念的戏剧化,可视为是弗洛伊德主义的直接果实。西方理论家赫尔曼·巴尔干脆把表现主义戏剧的崛起视为“人从其灵魂深处发出的尖叫”(注:见[英]J.L.斯泰恩著 象禺武文译《现代戏剧的理论和实践》(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这种“尖叫”的价值不在于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而在于对传统的写实主义戏剧的背离、突破和否定。德国理论家卡西米尔·埃德施米德把这种“尖叫”艺术极端主观性的崭新特质概括为“他们不睁眼观看,/他们却看见。/他们不摄影留像,/他们却创造形象”(注:见[加拿大]雷内特·本森著 汪义群译《德国表现主义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页—9页。)应该是贴切而又富于诗意的。那么这种表现艺术对写实主义的突围和否定是否就是为突围而突围,为否定而否定呢?决不是的。德国理论家库尔特·平图斯在谈及表现主义艺术的美学实质时指出:“把真实从它出现的范围里解放出来,把我们自己从真实里解放出来,不是使用它自己的手段或依靠从它跑开来超越真实,而是凭借更加热切地把握它,通过心智的动察力、灵活性和对清晰性的渴望,通过感情的强烈爆发力,来战胜和支配它……”(注:见理查德·谢帕德《德国表现主义》,[英]马·布雷德伯里 詹·麦克法兰编 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55页。)这段话可以说很好地揭示了表现主义艺术的根本宗旨。显然表现主义否定现实主义,决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现实,战胜现实,支配现实。由于他们试图“通过心智的观念力,灵活性和对清晰性的渴望,通过感情和强烈的爆发力”达到目的,这就使表现主义戏剧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浓郁的启示录性质。由于他们过于热衷于帮助人们从绝望中发掘希望,从黑暗中开启光明,为到处充满灾难的世界传播福音,于是他们一反现实主义戏剧对外在现实的客观叙述,把主观叙述和主题叙述作为他们进行反戏剧式意象叙述的一个重要手段。主题叙述说白了也就是剧作者或者隐含的剧作者的观念叙述和思想叙述。其最大特点就在于通过心灵内部的意象叙述,表达一种“救世”方略或某种道德的或者宗教的人生寓言。
主题叙述主要靠什么样的叙述手段完成呢?是剧作者主观意念的全面外化和符号化。它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剧作者主观意念的人物化、人物的无个性化和人物的抽象化;另一个是剧作者主观意念的场景化和戏剧场景的观念化。
作为前者而言,众多的剧中人物都不过是剧作者内在人格的分裂性外射和内心意念矛盾的具化形式。他们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不过是剧作者内心意念和内心矛盾的某个方面。主题叙述这种表现主义式的极端主观主义的叙述行为的完成,主要就是靠这些不同人物之间的观念冲突来交互推进的。无论这种冲突,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无不都在围绕着这一叙述行为进行。一旦什么时候,剧中人物的诸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最终趋向一致时,也就意味着剧作家剧烈的内心意念活动的告一段落和失衡心态的重新恢复,乃至某种新思想的诞生。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都是些无个性的类型化的人物,甚至是某种精神和感情状态的符号和标志。有的人物以“男人”、“女人”、“父亲”、“儿子”、“无名氏”、“职员”、“乞丐”、“医生”、“妓女”、“鬼影”冠之,有些干脆用甲、乙、丙、丁,X、Y、Z等抽象符号来代替。即令有名有姓的中心人物也不过是某一痛苦的内心意念的化身和代表。且更有甚者,由于出于剧作者一个人的观念和修养,这些类型化的人物的对白,无论身份、地位、年龄的差异有多大,统统都是一个腔口,一个素养,一个语言风格。该风格始作俑者的斯特林堡于1898年创作的著名的梦幻剧《通往大马士革之路》最为典型。由于该剧在外借《圣经》中索尔到大马士革去的历程及他改信基督教的故事,叙写剧作者化身的“无名氏”结识一个漂亮的“阔太太”后的灵魂自救和道德自新时,率先采用了把“单个人的个性分裂成几个人物,每个人物代表整个个性的一个侧面,合起来则揭示出一个人的心灵中的种种冲突”(注:见[英]J.L.斯泰恩著 象禺武文译《现代戏剧的理论和实践》(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的方法,取得罕见的巨大成功,从而对后世表现主义剧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为后者而言,主要是通过场景辩论剧的形式推进主题叙述。对此,他们早就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先驱毕希纳(1813-1837)的《丹东之死》(1835)和《沃伊采克》(1836)中得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艺术启示:“戏剧艺术所必需的叙事成分不一定得遵从佳构剧的形式,完全可以先从一个观点铺叙,然后再从另一个观点进行铺叙,亦即像辩论那样写去”(注:见[英]J.L.斯泰恩著 象禺武文译《现代戏剧的理论和实践》(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尽管这两个写于一百年前的典型的表现主义剧作,于一百年后才由著名导演莱因哈特把它们搬上了舞台。然而实际上这两个剧本所做的艺术探索都分别早于1850和1879年就开始在欧洲产生影响。如果说这种场景辩论剧的形式在《丹东之死》中还仅是雏形的话,那么在他未完成的著名杰作《沃伊采克》中却走向了成熟。在这里包括27个未编号的和未分类的场景,还有差不多数目相等的难以确定的片断,由于其开放式的场景结构,后世的编辑和导演们出于各自的艺术需要往往把它们像洗扑克牌那样洗来洗去。“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因果性事件,已完全被一系列戏剧性场景所代替,每一场景的本身均具有某种心理的或象征的意义。一个场面有可能把剧情的部分内容讲出来,但同样也能很好地揭示主题或题旨并对其进行评论”(注:见[英]J.L.斯泰恩著 象禺武文译《现代戏剧的理论和实践》(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第45页。)。这就为表现主义戏剧的主题叙述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艺术途径。因此我们说,后来的那些表现主义剧作家们的场景剧作貌似独到,实际上很少不是从毕希纳开辟的场景辩论剧的传统中而来。譬如美国剧作家欧文·肖的《埋葬死者》就很典型。这是一部30年代深受美国观众欢迎的一部反战戏剧。剧本写6名死于战场的士兵,不愿安安稳稳地躺在坟墓里,要为制止战争尽自己的一份努力。他们表示,直到有一天战争不再发生,甚至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再存在时,他们才肯安心躺下。该剧运用灯光蒙太奇把一个个互相分割的插曲式场景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且诸多场景都一律围绕着“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题旨而展开。尽管将军为了稳定军心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苦口婆心劝他们回到坟墓里,遭到拒绝。又让他们的亲人、神甫乃至妓女去说服他们安心死去,被人葬掉,均告失败。最后诸多场景观点交锋的结果,还是那六位死去的士兵的意见占了上风,即共同致力于对战争的埋葬。作品结束时,他们走出坟墓,和活着的士兵一起,去传
播和平的福音去了,从而给人带来了一种极大的心理震撼。
三、梦幻叙述:亦真亦幻的分裂性意象的自然变换和无时空性接合
表现主义剧作家对“互不连贯而又表面上合乎逻辑的梦幻的形式”(注:见理查德·谢帕德《德国表现主义》,[英]马·布雷德伯里 詹·麦克法兰编 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91页。)这种“内心形式”的热衷和执着,又为其反戏剧式的意象叙述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特质。由于他们“相信确凿无疑的内心真实,对于非逻辑的内在逻辑的感知,并承认并非完全处于意识控制之下存在于个人内部和外界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注:见理查德·谢帕德《德国表现主义》,[英]马·布雷德伯里 詹·麦克法兰编 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91页。)这就使他们在进行戏剧创作时往往喜欢更多地采用“梦幻叙述”的艺术手段进行反戏剧式的意象叙述。
詹姆斯·麦克法兰认为,“梦幻提供了一种手段,它可以赋予形式以明显的随意性——混合、转换、溶解”。(注:见理查德·谢帕德《德国表现主义》,[英]马·布雷德伯里 詹·麦克法兰编 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92页。)这使一个事物溶进另一个事物,一个场景化入另一个场景,显得自自然然,而无需做任何解释。斯特林堡则认为,在反戏剧的梦幻形式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很可能的。时间和空间不存在了;在无关紧要的现实背景上,想像力编织为新的图案:回忆、经历、自由思想、荒谬行为和临时拼凑的东西都融为一体。人物分裂了,变成了双重的、多重的;他们升华、结晶、扩散、聚合。但是都有一个意识支配着一切,那就是梦者的意识。”(注:见理查德·谢帕德《德国表现主义》,[英]马·布雷德伯里 詹·麦克法兰编 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91页。),应该说更是鞭辟入里。这里不仅指出了梦幻叙述的部分特质,而且还指出了这种形式得以自由叙述的根源所在。这一叙述手段的独特性在于“梦者的意识”对貌似杂乱无章的一系列分裂性意象的统一支配和无形控制上。具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通过“分裂性意象”的无时空性接合,使“与梦幻相关的真实”和“梦幻固有的逻辑”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了一起,显示出一种亦真亦幻的奇特性质。托勒尔的《变形》可以算是同类剧中最好的一个。剧作用戏剧形式表现了一位青年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对人的疏远感到对人类未来赎罪的神秘感的变化的各个阶段。主人公逐渐懂得了战争的恐怖和无意义,最后狂热的宣布人类皆兄弟的思想。这是一部典型的自供剧,(Bekenntinsdrama),也是一种歌颂人的戏剧(OMensch-Drama)。在这里“地点只服从于幻觉的法则,而时间则拒绝遵从时钟或旧历的时间”(18)给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无始无终的感觉。时间可能是“夜间”、“傍晚”,也可能是“早晨”,总之不过是欧洲复兴前的一霎那。全剧由个场景组成,这六个场景又进而分解为13个画面。同时这13个画面又是围绕着第七个高潮画面设置的。这样,前六个画面与后六个画面使剧本呈对称状态。在这13个画面中,七个是梦景,它们戏剧性评论其余六个现实画面所提供的戏剧主题。除第四个场景纯系高潮只有一个梦幻场面之外,其余各个场景中现实的画面和梦幻的画面都是交替出现的。区别仅在于第五个场景中是一连三个梦幻画面与一个现实画面交替出现,第一、二、三、五等几个场景都是一对一交互出现的。全剧结束时主人公弗雷德里希又回到了剧情的出发点现实中来,并不给人以丝毫的牵强。
其次通过答非所问的形式推进梦幻叙述。答非所问是一种典型的感情错位,且尤以魏德金德所独创的“孤立”技巧为最。他让人物不是互相对话,而是旁若无人的说话,人物之间往往是有交谈而无交流。尽管对方谈的是他们以前甜蜜的往事,足以吸引交谈者的兴趣,然而交流者却只管沉溺于美好现实的梦幻之中。等到美好现实的梦幻无情破灭之后,对方所述及的往事的线索才又重新回到他们之间,并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新的人生目标,继续努力。譬如美国剧作家赖斯的《加算机》中的一些场景就十分典型。这里我们仅举零先生同他漂亮的女同事黛茜之间的一段对话为例:
黛茜 商店举行野外餐会那次——那次你妻子没有来,当时你待我不错。
零 二十五年干着同一件工作。
黛茜 我们一整天都在一块——就坐在附近的树下面。
零 一转眼二十五年过去了,我说不上老板是否还记得这件事。
黛茜 那天晚上,回来的路上——在大仓库里,你是挨着我坐的。
零 我猜着,我的工资将有大幅度地增加。
黛茜 我想体验一下,真的被亲吻一下是个什么滋味。……
零 如果他不过来,我就去前边的办公室,告诉他该怎么办。
黛茜 我咋不早死呢。
零 “老板”我将说,“我想跟你说说”。“当然可以了。”……我就说“……”、“你真好”,他会说“你的脑袋瓜真聪明,零”。
黛茜 我不能闻煤气味,一闻就恶心,只要你愿意,本来是可以吻我一次的。
零 “老板”我要说,“我还有个想法呢……”(注:引自[美国]赖斯著,郭继德译《加算机》,汪义群编《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3),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思路是毫不相干的平行发展。尽管露茜做出各种努力,想唤起零先生对他们以往恋情的回忆,但零先生却始终没有感觉,只是一味沉浸于老板对他的器重和嘉奖的梦幻之中。至到梦幻破灭,零先生杀死老板,被处死刑,黛茜自杀殉情,双双来到阴间,才使他们过去的恋情死灰复燃,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样貌似不相干的两个思路最终又呈线形给连了起来,不能不说是对梦幻叙述的一个重要推动。
第三,通过灯光分割和音乐乐段的场景对位推进梦幻叙述。所谓灯光分割,即灯光蒙太奇,旨在借助灯光分割演区的方法表现幻觉和梦幻。著名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解决快速转换场景的问题。欧文·肖的《埋葬死者》中“埋葬现场”与“将军办公室”这两个地点之间来来回回的转换都是靠灯光分割演区的方法在同一瞬间展示出来的。一方面大大增强了梦幻气氛,另方面又大大增强了剧作的叙述节奏。至于音乐乐段的场景对位在斯特林堡晚期的剧作中运用得较为充分。他不仅在这些剧作中引进了诸如“尾声”、“装饰乐段”和“徐缓”等音乐术语,而且还用对位法来说明戏剧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譬如布景、灯光、动作和台词等,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另外佐尔格的《乞丐》除使用灯光分割演区,强化人物性格之外,导演马丁还曾让W·R·哈格曼写了一小段小提琴曲来衔接各个场面之间的变换,同样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