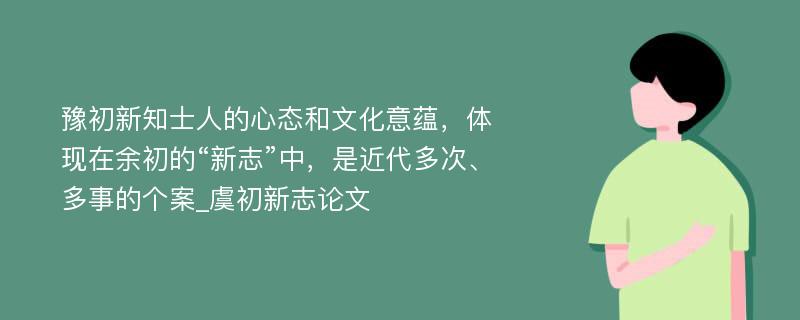
文多时贤 事多近代——《虞初新志》所表现的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意蕴论文,近代论文,心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潮(1650—1707年之后),字山来,号心斋,又号三在道人,安徽歙县南蒋国村人。清初著名的小说家、刻书家,著述颇丰,有《心斋杂俎》、《花影词》、《聊复集》、《七疗》、《幽梦影》等二十多种存世著作。在清初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流风遗韵,给后世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虞初体”小说的开创是其在文学上的影响之一。继明汤显祖选辑的《虞初志》之后,张潮在唐人轶事之外,广搜当代之人,当代之事,编成了富有现实性和新鲜感的《虞初新志》。这部在清代初年最有代表性的传奇小说集,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贤时俊对《虞初新志》小说体制的创新及其表现的小说观颇有研究,而对其表现的士人心态尚无深探。本文着意于此,并从文化意蕴上予以剖析。
一
《虞初新志》用志人笔法,描绘了一幅时代众生群像图,把清初士人形态,“摹仿毕肖”(张潮《虞初新志自序》),(注:本文所引《虞初新志》版本为上海书店1986年版,下不出注。)他们既有各自的特征,又有时代的共性。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类: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避世的闯荡江湖之豪客和玩世的厕身市井之小民。
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明末清初,社会变动异常激烈,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满族的统治,使汉族士人心理普遍失衡,表现出一种怨世的心态,在愤懑与压抑的环境里,一些士人以异端畸行行世,以弥补失落的心理。《虞初新志》不乏诸如此类似疯似狂者,如《武风子传》中的武恬,性好闲,不谋荣利,嗜酒,日惟谋醉,凡游艺杂技,过目不忘。以绘画名天下,擅长在滇箸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人奇之,每得其双箸,争购钱数百。“流贼”索取,武风子匿而不出,大笑曰:“我岂作奇技淫巧以悦贼者耶。”“流贼”系之来,至则白眼仰天,暗无一语。片言就将一个“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武风子形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八大山人传》中的八大山人,性孤介,颖异绝伦,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甲申,国亡父卒,山人承父志,亦喑哑。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颔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又如《鲁颠传》中鲁颠,独行吴越间,裸行,上身披一破布,下身着厚絮裙,污重染,从不更换,以示与世不同污。
小说中的士人们以“异端”自居,显露出了作者的一种故国之思、兴亡之感,“武生岂真风子耶,不过如昔人饮醇近妇,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态,宜其箸之不轻作也”(张潮《武风子传跋》);八大山人“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陈鼎《八大山人传》)
怨世心态还表现为士人借作品隐露出一种反抗之志,旁见侧出,借故事中意象抒发感慨,如林璐《象记》,写崇祯时选用大象作禁卫,后明亡,“皇朝定鼎,征贡象”之时,一象抗命不尊,“呼之不至”,数日后昂然来取其偶,守土者设大炮相威胁,并以“今天子神圣”云云相威胁,象镇定自若,宁愿赴死,不肯入贡。作者于篇末议论云:“爱妻并爱吾身”,“而今见之于一象”。隐喻眷恋故国、不愿仕清的明之遗民,其义自明。林璐,字玉逵,号鹿庵,浙江钱塘人,明末诸生。朝廷选用大象作禁卫,完全是作者用作影射的巧妙构思,寓意不屈仕新朝的民族气节。而变节者更为士人抨击的对象,徐芳《义犬记》写一犬奋不顾身,为主人伸冤报仇,表现了对主人的忠心,篇末作者议论说:“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则应猝而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辨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感慨人不如犬,人不如兽,自然可以说明当时世情之浇薄,而“遇变则渝”,“应猝则乱”,表现了作者徐芳对那些甘心作满族新贵走狗奴才者的痛恨和讽刺。
避世的闯荡江湖之豪客。清兵入关之后,进军江南各地,大肆烧杀抢掠,造成广大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周亮工《书戚三郎事》中的戚三郎身被十三创,还被砍了头的悲惨景象,就充分暴露了满清统治者的残暴。世衰道微,政治黑暗,士人深表不满,并有深刻的批判。慑于统治阶级的残暴,一些士人淡于进取,但不失豪情,却以侠气染荡末世之邪恶。《大铁锥传》中的大铁锥,因手持大铁锥而得名。他力大无穷,识见高远,却所遇不偶。诸响马拥他作领袖,遭他拒绝。投奔宋将军门下,又“皆不足用”,毅然离去,流落江湖,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叹,三称“吾去矣”,语气中透示出意气雄健、磊落坦荡的豪侠英风。又如《汪十四传》中的汪十四,“有燕赵之风”,往来西蜀山中,保护客商行旅,行文曲折跌宕,雄风慷慨,意象豪壮。即使写其思退之语,“吾老矣,不思归计,徒挟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贵也”,仍不失壮士本色,气象宏大,没有丝毫文人式的感叹伤悲,言语风格和人物性格相合无间。
《虞初新志》中不乏女侠,如《名捕传》中的名捕妇。名捕夫妇遇贼劫供银,夫患病在身,妇“更束马肚,结缚裙鞴”,攘臂“绝尘而去,顺风呼贼”,贼发五箭,妇以弹拨箭,箭急落地,急发一弹杀人,又挥斥斫杀一人,贼惊惶失措,“置银,舁尸而逃”。诸捕“舁银而还”,妇“犹旖旎寻常”。片言只语,描绘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勾勒出了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的侠女形象。
除此之外,还有《李一足传》中既孝亦侠的李一足,《髯焦传》中见义必为,矢志不屈的髯焦,《剑侠传》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二剑侠,《王义士传》中以气节自重、任侠好义的王义士,《髯参军传》中人称真奇杰非常之士的髯参军等等。
即使挡路抢劫的强盗,也盗亦有道,《雷州盗记》写雷州太守金陵某人,赴任途中被强盗所杀,盗即假冒其名而就其职,“甚廉干,有治状”,后被太守之子知其情,盗即被械杀。盗假冒太守之后,为官清廉,受人民欢迎,反映了当时官吏的腐败无能。正如时人所说:“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次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即犹愈他守也。”(徐芳《雷州盗记》)
现实中的无奈使士人只能希冀仗剑豪侠的侠士来惩恶扬善,匡正扶弱,通过侠士精神来慰藉自己的心灵。避世心态背后反映出了士人渴望太平之世的愿望。
玩世的厕身市井之小民。明清之际的文人因处在政治风云剧变、天崩地坼的鼎革时期,历尽世变沧桑,笼罩在他们心头的,常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迷惘与感伤情绪。在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困境中,在当时文禁森严的高压政策下,有些士人采取了回避重大的、敏感的政治题材的策略,转而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入世俗生活。其中以“名士风流”标榜的市井小民,他们关注自我,专注自身,追寻玩世的乐趣,如《一瓢子传》中的一瓢道人,性嗜酒,善画龙,敝衣逢跣,担筇竹枚,游鄂渚间,行歌漫骂,学百鸟语,弄群儿聚诟以为乐。《狗皮道士传》中的狗皮道士,冠道冠,蹑赤鸟,披狗皮,作犬吠声,酷相类。张献忠入寇,作犬吠声,侮弄张献忠如襁褓小儿。所谓:“人皮者不能吠贼,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张潮《狗皮道士传跋》)又如《卖花老人传》中的卖花老人,“以种草花为业,家尝有五色瓜”,“朝晨担花向红桥坐卖,遇文人墨客,赠花换诗而归,或遇俗子购之,必数倍其价,得钱沽酒痛饮。市人笑为花颠。”
还有专攻自己的技艺,并以此为乐者,如《汤琵琶传》中的汤应曾,有极高的琵琶演奏技艺,人称汤琵琶。“著名大梁间,颇自矜重,不妄为人奏。”《柳敬亭传》中的柳敬亭,善谈论,“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于是听者傥然若有见焉。”他们的行为突破了传统礼教的藩篱,表现出了一种“狂诞”性格,有魏晋士人之风。
同时,《虞初新志》或为实录,或作虚构,记述了明亡后一些士人入道学仙的生活,表现了他们“清净无为”的处世态度。如陈鼎的《彭望祖传》,主要讲彭望祖得丹书三卷,熟读之后则成飞仙。明亡后弃举子业,往游江南,山川险阻,第相去数千里,望祖乘龙而去,半夜而返回。作者很向往那种生活,曰“神仙固多幻术也,往往以幻术游戏人生”。常感叹无缘与其相遇。又如《活死人传》写活死人爱本素封,“明亡,散家财,弃妻子”,入山学仙,十年道成;后活埋土穴,三年而死。也表现了作者对“清静无为”思想的认同。
《看花述异记》写作者睡梦中走进了一个鲜花烂漫、云霞缥缈的环境之中,会见了一个个古代的仙人、才子、美人,歌颂、赞美了她们美丽的容貌,优美的心灵和奇才异能。作者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与环境的故事,安排在同一个虚幻的境界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刻画她们形象,表现她们心灵。作者与她们同脉搏、共享乐,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爱才、爱美之心,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也为自己心灵创造了一方净土。诸如此类的作品在《虞初新志》中有不少,展现了士人们在另一种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欲望。
正如张潮《虞初新志自序》所言:“其文多时贤”,所收作品有姓名作者约八十人,“佚名”作者五人,大多为清初人氏,部分出生于明崇祯年间,部分与张潮出生仿佛;“其事多近代”,其中记述明末事者约三分之一,记述清初事者约三分之二,有近二十篇直记康熙年间人情事理;以“事奇而核”为标准,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士人的生活风貌和思想情趣,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士人各种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对当时政府不满之情。因而,具有深入研究价值。
二
《虞初新志》能成功地表现当时士人心态并非偶然,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我们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清初文化的纵横交错点上,从其文化心态入手去探索诠解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就会有新的体悟和发现。
直抒胸臆,放性任情,张扬个人情感是其文化底蕴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是一个斑斓多彩的情感世界。它以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象和审美情趣作为支撑依托,显示出特异的风韵和色彩。这里很少有对飘逸高寄、简淡玄远生命情趣的玩味,更多的是忧患意识浸染后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流露;这里很少再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害畏祸的惴惴不安,取而代之的是慷慨陈词,以不可一世的气魄评论国事,张扬灵知。
言情,是明末清初士人的一大追求,从哲学到政治到文学,无不显示出言情的踪迹。这一时期的文人论述及文学创作也都以情为出发点,主张文学的命脉是情,文学的任务是抒情。万历名士吴从先说:“情也者,文之司命也”(《小窗艳记序》)。汤显祖则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注: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0页。)此时的人们,情感至上。在尊情思潮影响之下,明末清初的文学园地里盛开出一朵朵闪耀真情的奇葩,诗文、小说的创作都以情感为纲。被张潮称为“一部悟书的《西游记》,一部怒书的《水浒传》,一部哀书的《金瓶梅》”,(注:张潮著,罗刚、张铁弓译注《幽梦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85页。)以描写人物的情感见长,蕴含着作者的大悲大愤、大彻大悟的感情体验。这些作品不求藏之名山,经世致用,只为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喜乐哀怒之情,所以也不刻意追求内容的伦理与为文的哲理性,而是放性任情,恣意行文,直抒胸臆。
主情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潮,曾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一世界。”(注:张潮著,罗刚、张铁弓译注《幽梦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85页。)《虞初新志》以文采风流为宗旨,特别关注爱情、豪侠、畸人、隐逸,意识形态领域有相对的自由,少一些拘束,多一些洒脱,作品中浸染着他的主情思想。首先,男女爱情是其要表现的性情之一。“红颜薄命,千古伤心”的小青,“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张潮《小青传跋》),表现出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虞初新志》中的佳人与名士之间的关系,多涉及男女风情,给人以风流倜傥之感。比如柳如是与钱谦益:“柳既归守伯,相得欢甚,题花咏柳,殆无虚日。”(徐芳《柳夫人小传》)其中的名士痴于情,深于情。董小宛殁后,“辟疆哭之曰:‘事不知姬死而吾死也!’千古神伤,实堪令奉倩、安仁阁笔也。”(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张灵因思念天各一方的崔莹,呕血不止,三日后去世(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太恨生因情痴而得心疾(徐瑶《太恨生传》)。足见士人们对感情的忠贞和痴情。
其次,诸作者喜以名士自居,流连声色,欣赏畸人,豪纵倜傥,不为时俗所牵。他们对下层社会的畸人兴趣极浓,如对《鲁颠传》中的鲁颠,突出了其异端畸行。他“悬足架上,垂首卧”,世人以为怪异,而在作者眼中却是超凡脱俗的奇人。《刘酒传》中刘酒之嗜酒,“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凸显其嗜酒之性。张潮的这种适世娱世之情还表现在对艺人及其技艺的大力张扬上,如柳敬亭的“滑稽善谈,风生四座”;汤琵琶所弹琵琶,“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由此可见,《虞初新志》所道“甘食悦色人情”,所谈“嗜好之性,皆出自然”,表达了张潮“聊抒兴趣,既自怡悦”(张潮《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跋》)之情。
性好幽奇,搜神记异,喜人谈鬼,以抒发内心积郁和苦闷是其文化底蕴之一。好奇尚异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一大美学特点。仅从《列异传》(曹丕)、《搜神记》(干宝)、《异苑》(刘敬叔)、《玄怪录》(牛僧孺)和《传奇》(裴櫆)等书名中,可以窥见这种艺术风尚的由来已久,实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民族特色。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种尚奇的艺术观。
清王朝中央政权逐渐巩固,加强了对文人言论自由的控制,于是一些作家乃通过搜神谈鬼以抒发内心的积郁和苦闷。宋起凤于“隆替变革之故,稔熟见闻”,乃撰作《稗说》,“聊以排除客游穷愁之感”。(注:宋起凤《稗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当时迷信鬼神的风气盛行,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鬼狐神怪故事。与时代的文学风气桴鼓相应,文人喜搜神记异,任诞矜奇。如蒲松龄说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注: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东轩主人说他“闲居多暇”,“辄求异闻,以资嗢噱”(注:东轩主人《述异记自序》,《述异记》,《说铃后集》本。);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钮琇“喜谈神怪,以征其诡”(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商务书馆1959年版,第1319页。)。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张潮亦是“尚奇”者,在《虞初新志凡例》中曰:“性好幽奇,衷多感愤。故神仙英杰,寓意《四怀》;外史奇文,写心一启(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怀诗》及《征选外史启》)。生平罕逢秘本,不惮假抄;偶尔得遇异书,辄为求购。”他认为“离奇诡异”之文,方能“引人着胜”。曾曰:
……况天壤间浩气卷舒,鼓荡激薄,变态万状。一切荒诞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无;古之所无,忽为今之所有,固不仅飞仙盗侠,牛鬼蛇神,如《夷坚》、《艳异》所载者为奇矣。
借“才子、佳人、英雄、神仙”等“幽奇”题材写“感愤”,这是张潮的重“奇”思想的表现。《虞初新志》选材原则是“表彰轶事,传布奇文”,写豪侠、写异士、写小民,以“奇”作为他们的共同点。张潮的篇末评语一再对此加以强调,如:“叙次生动,觉人奇情跃然纸上。”(《徐霞客传跋》)“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张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诸人仅工诗文,而此公复能书,则尤奇也。”(《盛此公传跋》)“吾乡有此异人,大是为新安生色,而文之夭矫奇恣,尤堪与汪十四相副也。”(《汪十四传跋》)
为了突出其猎“奇”的思想,抒发其愤懑,张潮强调以“核”来增强感情的真挚。《虞初新志自序》提出“事奇而核”。“核”即真实,多是指事物的实际存在性兼有按照事物本来面目予以反映的意思:“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竟为事之所有者。”愈“奇”之事,愈需要“核”之理,“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如《奇女子传》写某女子被兵卒王某掳去他乡为妾,该女子后待王某从军远行时,设计逃归故里,奇计奇行,却合情合理,故深得张潮赞许而称之为“妙”。凡此可见,张潮面对着令人失望,无法立足的社会现实,借助“一切荒诞奇僻”之事,“纵横俯仰,开拓心胸”,表达了他对人生真谛的睿智深刻思考,对实现理想精神的热切希冀,对至真至美人生自由境界的执着追求。其中所孕含的丰富文化意蕴,至今仍值得人们去深思体味。
呼唤豪侠精神,以侠气染荡末世之邪恶,洗刷儒生之酸气,补偿文人之心理,这是其文化意蕴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时代现象是:整个官场是“凡清官都犯事,凡污吏尽升迁”的黑白颠倒,整个社会是“流贼徒蜀败奔”;“张献中屠戮楚中,麻城人为贼所杀,魂走川中”,动荡不安;人们的心态是对金钱趋之若鹜,对道德弃若敝屣的末世心态。士人无力挽救这个“猫鼠同眠”的时代,对统治者也没多少奢望,只希冀仗剑豪侠的侠士来惩恶扬善,匡正扶弱。正如张潮所说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幽梦影》)“有剑须挂烈士鞴,不平肯为人间留。”(注:张潮《杂兴》,转引自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侠”的概念,古已有之,它最早见于战国时期《韩非子·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注:李诚、勾承益译注《〈韩非子〉白话今译》,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644页。)敢以高超的武艺触犯国家的禁令,其行为不受王法的约束,谓之侠。“侠”的出现与“儒生”相对,以武勇雄豪为特征,有英雄之气,可补儒生之不足。豪侠,这一类人多出身于下层贫民,家无恒产,性爱行侠,日常行事多有义举,成为处于困境中人们的精神支柱。在传统文化中,侠士受到历代文人乃至大众的褒扬,特别是到了“纲纪废弛”的封建末世,侠士的活动舞台更广阔了,重要性也增加了,时代在迫切呼唤侠士出来主持公道。正如柳亚子诗所云:“乱世天教重侠游”。(注: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有鉴于此,张潮适应时代的呼唤,满足大众心理,独具匠心地塑造了一批侠士典型。《虞初新志》中除了“有燕赵之风”的汪十四之外,其中的艺人、佳人、小民、异士都具有豪侠之气,如著名艺人柳敬亭“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亡散累千金,再贫困而意气自如”;不以“奇技淫巧以悦贼”的武风子;“尚侠轻财,急人困”的高昽;就连其中的妓女也充满着侠气,如江南名妓李香,侠而慧,知书达理,不阿权贵,感情专一,对东林党深恶痛绝,对民族事业却是一番豪情。侠士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能迅速扫清社会恶势力的一个有力依靠,想凭借他们涤荡社会之阴霾,冲洗儒生之酸腐,强壮民族之精神,一吐积郁在文人大众心头的抑郁不平之气。
从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人生境界来说,儒生之书与侠士之剑能互补统一,方为佳境。张潮的人生理想境界亦如此,从气质禀赋来看,他身上不乏豪气爽朗的风采。如其《四怀诗》所吟:“我所怀兮在英雄,豪侠慷慨气贯虹。秋郊击剑报知己,挥金那顾家计穷。奈何我生交不获,生生块垒凭谁释?不及生当中古时,椎埋屠狗皆堪容。”(注:张潮《杂兴》,转引自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潮所尚“侠”的实际内涵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市民文化气息,在他心目中“侠”成为一个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基本市民道德理念的载体,具有普遍性与平民化的鲜明特点。《虞初新志》中豪侠、隐逸,畛域不甚分明:或由侠而隐,或亦隐亦侠。隐居是性情激烈的一种表示,为世俗所激,不愿同流合污,这就通于侠了,如花隐道人,“慕朱家、郭解为人,尚侠轻财,急人困”。这既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凝聚,一种豪侠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传统的载体,又是由“纲纪废弛”的污浊尘世到不受王法束缚的世外桃源的过渡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