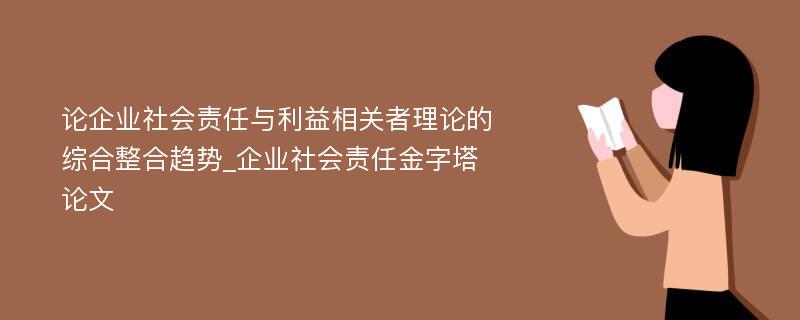
论公司社会责任与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全面结合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益论文,趋势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公司社会责任与相关利益者理论全面结合的背景
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1])、公司社会业绩(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简称:CSP)或公司社会反应(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2])虽然称法不同,但大致上都可以将其看作是研究同一个问题。教科书上习惯上用公司社会责任统而称之,意指:“公司应该为其影响到他人、社会和环境的所有行为负有责任。”(注:见波斯特、弗雷德里克、劳伦斯和韦伯:《公司与社会:公司战略、公共政策与伦理》,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英文影印版,第37页。)相关利益者理论则“提供了一种关于公司战略管理的新思维,即公司如何与应该制定和贯彻其发展方向。”(注:见弗里曼:《战略性管理:一种相关利益者方法》,波士顿皮得曼出版社/巴尔格林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公司社会责任和相关利益者原本一直作为社会学和管理学交叉学科里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前者探讨企业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后者研究社会各相关群体与企业的关系。历史地看,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要早于关于相关利益者理论方面的研究。据说公司社会责任作为社会问题被提起来讨论已经有“数个世纪”之久。(注:见哈里森和弗里曼:“相关利益者、社会责任与业绩:实证检验证据与理论性观点”,载《管理学会学刊》,1999年,第42卷,第479页。)托马斯·杰佛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就此进行过辩论,可见在美国,关于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或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到了20世纪,这场争论仍在继续。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企业的责任仅限于经济方面,企业介入社会和政治领域会危及自由。弗里德曼有句名言:“企业就是在遵循社会基本原则(包括法定的和道义的)的同时赚取尽可能多的钱。”(注:见弗里德曼:“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其利润”,载《纽约时报》1970年9月号,第122—126页。)相反,以德鲁克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却主张,在我们的社会里,企业不可能出于真空状态下,企业的作用更宽泛,应包括社会责任在内。(注:见弗雷德里克·斯特迪文特:《企业与社会:一种管理方法》,里查德·埃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美国在60和7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如石油危机、危及生命的产品及污染等等,使人们认识到企业的环境不仅仅只是具有经济性和技术性,而且往往还带有社会性和政治性。(注:见伍德:“管理中的社会问题:公司社会业绩的理论及研究”,载《管理学刊》1991年,第17卷,第383页。)尽管这时期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如《企业与社会评论》的调查发现莫思科维茨(1972)选出的14家具有社会反应的公司的股票收益率高于市场收益率,支持了公司社会责任概念,而万斯(1975)和福格勒等人(1975)提出的实证检验证据却并不支持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此时绝大部分的理论研究都已经认识到,公司社会责任已成为关系到公司生存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内容不再是讨论企业是否应有社会责任,而是如何正确地界定社会责任的范围。在70年代,有不少学者在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努力。塞思(1975)建议从防御、反应和响应三方面来评价公司的整体社会行动。普雷斯顿和波斯特(1975)提出了公共责任和渗透系统的双重概念。弗雷德里克(1978)认为公司社会反应是更为妥当的提法。(注:同上,第385—386页。)但是,他们部未能得出一个理论上一致和准确的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第一个试图把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带往理论化方向发展的是卡罗尔。在1979年发表的“公司业绩的三维概念模型”一文里,卡罗尔首度提出公司社会责任可以定义为以下四大部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用卡罗尔的原话说是:“公司社会责任包括社会于一个时间点上对组织在经济、法律、伦理和自愿方面的期望。”(注:见卡罗尔:“公司业绩的三维概念模型”,载《管理学会评论》1979年,第4期,第500页。)所谓经济责任指公司必须负有生产、盈利及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所谓法律责任指公司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履行其经济责任;所谓伦理责任指公司必须符合社会准则、规范和价值观;所谓自愿责任指公司所具有的坚定意志和慈爱胸怀。不过,在卡罗尔看来,这四大部分并不是等量齐观的,相反,它们的权数各不相同,其权数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依此为4-3-2-1。这一权数关系后来被称为“卡罗尔结构”(Caroll’s Construct)。在卡罗尔结构里,公司社会责任具有了明确的内容,四大部分内容也隐含了相关利益者的概念和分类的成份在内,突出了经济因素在公司社会责任中的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对于公司社会责任早期研究的“一种进步”,“引进了一种关于CSP的新的概念框架”,“既有可理解性又有综合性”,(注:见克拉克森:“分析和评价公司社会业绩的一种相关利益者的框架”,载《管理学会评论》1995年,第20卷,第94页。)卡罗尔结构为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和相关利益者理论的最终结合提供了一条过渡的桥梁。奥珀尔里等人曾指出:“尽管没有哪一种单一的定义结构得到普遍的接受,卡罗尔(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化处理所具有的多重成份因子让它们可以得到衡量和检验,”(注:见奥珀尔里、卡罗尔和哈特菲尔德:“公司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载《管理学会学刊》1985年,第28卷,第447页。)这就是“卡罗尔结构”的重要之所在。克拉克森后来也称赞说:“卡罗尔模型的影响力可以从它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和后续成果里得到最好的判断。”(注:见奥珀尔里、卡罗尔和哈特菲尔德:“公司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载《管理学会学刊》1985年,第28卷,第94页。)在“卡罗尔结构”的基础上,瓦尔狄克和科齐赫兰(1985年)、卡罗尔(1989年)以及伍德(1991年)等人相继把“卡罗尔结构”里的内容加以定量处理,并把公司社会责任研究进一步推向相关利益者理论的怀抱。
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与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全面结合出现在九十年代,(注:见贾瓦哈和麦劳夫林:“朝向一种描述性的相关利益者理论:组织生命周期方法”,载《管理学会评论》2001年,第26卷,第398页。)这期间先后出现了若干篇重要的文献,如卡罗尔(1991)、布伦勒和科齐赫兰(1991年)、克拉克森(1995年)、唐纳森和普雷斯顿(1995年)、琼斯(1995年)、米切尔、阿利和伍德(1997)以及罗利(1997年)等。那么,为什么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与相关利益者理论在九十年代里会出现全面结合的趋势呢?其原因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司社会责任研究虽然经过近二十个年头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导引与支持,实际上仍然处于踌躇不前的状况。例如,卡罗尔指出,“公司社会责任中的‘社会’一词一直含糊不清,公司应向谁负责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注:见卡罗尔:“公司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朝向组织利益相关者的道德管理”,载《企业望》1991年,7—8月,第43页。)在公司社会责任研究里渗透入相关利益者理论,可以明确地界定公司社会责任所在,从而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的致命问题;另一方面,尽管相关利益者理论自八十年代中期成型后发展势头很猛,但缺乏实证上的足够证据一直是相关利益者理论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而公司社会责任研究虽说理论上尚嫌不足,但在研究方法的技术细节上却修整得很好,且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实证结果,符合工具主义相关利益者理论的要求。所以,把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拉进相关利益者理论的研究范畴里恰好可以让相关利益者理论充分利用公司社会责任在实证上诸多现成的方法。许多学者也都认识到公司社会责任与工具主义相关利益者理论的不谋而合之处。例如琼斯指出:“公司社会业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仍是“工具主义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应用,”(注:见琼斯:“工具主义式的相关主义理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调和”,载《管理学会评论》1995年,第20卷,第430页。)贾瓦哈和麦劳夫林也说:“关于CSR/相关利益者管理的研究无疑是建立在工具主义观点的基础之上。”(注:见贾瓦哈和麦劳夫林:“朝向一种描述性的相关利益者理论:组织生命周期方法”,载《管理学会评论》2001年,第26卷,第399页。)正是因为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与相关利益者理论之间各有所求,相互需要,可以取长补短,“两者的结合可以把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与相关利益者理论都引向对企业和社会关系更好的理解上。”(注:见贾瓦哈和麦劳夫林:“朝向一种描述性的相关利益者理论:组织生命周期方法”,载《管理学会评论》2001年,第26卷,第398页。)所以,当相关利益者理论自身逐渐成熟之后,出现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与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全面结合实属大势所向。
二、相关利益者理论给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带来了什么
那么,相关利益者理论给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带来什么新的内容?换句话说,加入相关利益者理论之后,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又出现了什么新的变化?应该说,相关利益者理论既为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明确了社会责任的概念,同时又帮助公司社会责任实证研究找到了衡量社会责任的方法。卡罗尔建议用一个概念框架将他提出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四个组成部分与相关利益者融合在一起。卡罗尔(1991)在借用相关利益者概念为公司社会责任“指明方向”时,将相关利益者纳入了社会责任框架中。他认为,要针对每一个主要的相关利益群体考虑社会责任问题。克拉克森(1995年)的调查也发现。“管理人员在理解相关利益者管理的概念和模式时并不觉得困难。他们意识到,可以将相关利益者群体的重要事项看作既是相关利益者问题又是社会问题。”(注:见克拉克森:“分析和评价公司社会业绩的一种相关利益者的框架”,载《管理学会评论》1995年,第20卷,第99页。)克拉克森曾经说,相关利益者理论为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提供的是“一种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公司社会责任被明确界定在“公司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上。(注:克拉克森:“一种分析和评价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关利益者框架”,载《管理学会评论》1995年,第20卷,第92页。)所以,正如许多学者明确指出的,在相关利益者理论框架下,“公司社会责任应该按照契约关系的思路而不是某种特定行为来加以定义?”(注:同上,第430页。)“认识到公司与多重相关利益者订有契约乃是获得对CSP和公司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之理论的工具。”(注:见卢孚、默拉里德哈、布朗、詹尼和保罗:“公司社会业绩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种相关利益者理论的观点”,载《商业伦理学刊》2001年,第32卷,第147页。)克拉克森认为,与其使用以公司社会责任概念为基础的模型,不如根据公司与相关利益者关系来分析和评价公司的社会责任,后者会更为有效。(注:同上,第92页。)
公司社会责任的早期研究由于在一些基本概念上的含糊不清,进而导致其在基本方法认知上的混乱。这种混乱状况首先表现在对究竟如何衡量公司社会责任没有一致的认识,也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方法。早期相继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所谓的“声誉指数”(reputation index)。“声誉指数”主要是由专家学者(甚至MBA学生)通过对公司各类相关政策进行主观评价后得出排序结果,最早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研究所采用的象经济优先权委员会编制的“CEP指数”和“米尔顿·莫思科维茨社会责任评级标准”均属于“声誉指数”,莫思科维茨(1972年)、布拉格顿和马尔林(1972年)、万斯(1975年)、斯图蒂温特和吉特(1977年)以及亚历山大和巴奇霍茨(1978年)的研究都是采用这类“声誉指数”。第二种方法是“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内容分析法”主要藉由分析公司已公开的各类报告或文件,其中特别是年度报告来确定每一个特定项目的分值或数值。相比起“声誉指数”,“内容分析法”较为客观。公司社会责任的早期研究里所采用的“内容分析法”大多是建立在欧内斯特和欧内斯特会计师行(Ernst & Ernst)的贝里斯福德(1973年,1975年,1976年)的技术基础之上。运用这一方法的早期学者包括鲍曼和海尼(1975年)、普雷斯顿(1978年)以及阿博特和莫森(1979年)。不过,无论是“声誉指数”还是“内容分析法”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缺陷,“声誉指数”主观色彩太浓,不太可能适用于大样本数据分析;而大部分的公司报告或文件都不是特地为衡量公司社会责任而量身定做的,公司社会行为与公司其他行为常常混杂在一起,又影响到“内容分析法”的准确性。所以,正如科齐赫兰和伍德所指出的:“不管是内容分析法或是声誉指数均无法被完全认为是CSR充分的衡量标准。这方面的文献需要给予衡量公司社会责任或反应的难题以更多的关注。然而,在那一个时刻,显然还无法找到更好的衡量方法。”而“从相关利益者理论的角度,公司社会业绩则是用公司是否满足多重相关利益者的需求来加以衡量,”(注:见卢孚、默拉里德哈、布朗、詹尼和保罗:“公司社会业绩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种相关利益者理论的观点”,载《商业伦理学刊》2001年,第32卷,第143页。)换句话说,原来泛泛而谈的公司社会责任现在被用其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明确地定义起来。在九十年代后出现的文献里,从与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来衡量公司社会责任的KLD(Kinder,Lydenberg,Domini and Company)指数在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得到普遍的采用。(注:另外一个被普遍采用的衡量标准是“《财富》声誉调查”(The Fortune Reputation Survey),不过该标准分析的范围较为狭窄。见哈里森和弗里曼:“相关利益者、社会反应与业绩;实证检验证据与理论观点”,载《管理学会学刊》1999年,第42卷,第481页。当然,即便是在九十年代,仍有小部分学者(例如帕瓦和考斯茨)还在采用传统的“经济优先权委员会”(CEP)评级作为衡量公司社会责任的标准。见帕瓦和考斯茨:“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社会成本之谜”,载《商业伦理学刊》1996年,第15卷,第321—357页。)
所谓KLD指数是KLD公司的分析师们独立创设的一种评价公司与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的评级标准。KLD公司乃是多米尼社会基金(Domini Social Equity Fund)的投资咨询机构,后者为一家专门投资于被列入多米尼社会指数(Domini Social Index)里的公司的共同基金。比起早期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衡量公司社会责任的方法,无论是“CEP指数”还是“米尔顿·莫思科维茨社会责任评级标准”,KLD指数明显有两方面的改进:第一,早期衡量方法大多只是考查某一个行业里公司社会责任的某一个单独的方面,且往住样本规模很小,如“CEP指数”只考虑纸浆和造纸行业里21家公司的污染控制问题。而KLD指数却涵盖了诸多行业里公司的多个方面,且时间跨度较长,可以较好地评估公司社会业绩的变化。KLD指数从公司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八个方面的关系来衡量公司社会责任,其中主要是社区关系、员工关系、自然环境、产品的安全与责任以及妇女与少数民族问题等五个方面。(注:其他三个方面分别是核能、军备和南非事务。不过这三项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究竟是否需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也非常值得商榷,实际上学术界也存在激烈的争论。大部分学者均忽略掉这三方面,见别尔曼、凯撒、维克和琼斯:“相关利益者导向是否有用?相关利益者管理与公司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载《管理学会学刊》1999年,第42卷,第495页注释1,以及卢孚、默拉里德哈、布朗、詹尼和保罗:“公司社会业绩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种相关利益者理论的观点”,载《商业伦理学刊》2001年,第32卷,第154页注释2。)KLD指数涵盖了列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及列入多米尼社会指数中的150家公司,共650家公司。第二,最为重要的是,KLD指数主要是从与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衡量公司的社会责任,每一家公司对待上述五方面相关利益者的态度按Likert五分刻度制进行衡量,其中-2为消极对待相关利益者,+2为积极对待相关利益者。公司社会责任被演化为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因此,KLD指数体现了相关利益者理论的精华,难怪相关利益者的理论大师伍德和琼斯把它看成是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研究设计得最好、也最容易被理解”的衡量方法。
三、公司社会责任给相关利益者理论带来了什么
了解清楚相关利益者理论带给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后。反过来看,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究竟又给相关利益者理论带来什么?这是最后一个必须说明的问题。从前面的阐述中,我们知道相关利益者理论之所以要把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拉进来,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其能够在实证检验方面助一臂之力。那么,到底公司社会责任研究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呢?在卡罗尔1979年的文章之前,半数以上的实证结果证实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特别是那些以会计指标衡量企业绩效方法的实证文献,比如布拉格顿和马尔林(1972年)、鲍曼和海尼(1975年)、帕克和艾尔伯特(1975)、海因茨(1976年)以及斯图蒂温特和吉特(1977年)等人。布拉格顿和马尔林以及鲍曼和海尼部是使用股东权益回报率(ROE),他们均报告说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的ROE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帕克和艾尔伯特、海因茨以及斯图蒂温特和吉特则使用了包括ROE、利润率和每股盈利(EPS)或资产回报率(ROA)在内的若干不同的企业绩效衡量指标,他们的研究结果同样证明在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指标之间确实有一种正相关关系。不过,同一时期“采用以证券市场为基础的企业绩效衡量方法来探讨公司社会责任与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却报告不同的结果。”(注:见麦冈利、桑德格恩和舒尼维尔斯:“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企业绩效”,载《管理学会学刊》1988年,第4卷,第857页。)莫思科维茨(1972年)认为对于社会业绩较好的公司,其股票价格表现高于市场指数,三年后,万斯(1975)的研究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莫思科维茨和万斯都是公司社会责任实证研究的早期代表性人物,两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麦冈利等认为此感叹到:“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前期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注:同上,第857页。)亚历山大和巴奇霍茨(1978年)以及阿博特和莫森(1979年)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们既否定莫思科维茨的“正相关”结论,也否定万斯的“负相关”结论。亚历山大和巴奇霍茨认为“股票风险水平和社会责任程度之间看起来似乎没有显著的关系。这些发现认为莫思科维茨和万斯两人的解释都是无效的。”(注:见亚力山大和巴奇霍茨:“公司社会责任与股票市场业绩”,载《管理学会学刊》1978年,第21卷,第485页。)阿博特和莫森用投资者总收益来代表企业绩效,他们同样指出公司社会责任对投资者的总收益没有影响。上述分析表明“这一领域里前期的实证研究在关于CSR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本质上没能达到真正的一致。”(注:见科齐赫兰和伍德:“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载《管理学会学刊》1984年,第27卷,第47页。)
从卡罗尔1979年的论文之后到90年代初,公司社会业绩的实证研究仍然无法提供一致的结论。其中,部分学者如科齐赫兰和伍德(1984年)等人继续认为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科齐赫兰和伍德采用营业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营业利润与销售额的比率和超常价值(Excess Value)等三类会计收益率来分别衡量1970—1974年的39家公司和1975—1979年的36家公司的企业绩效。(注:所谓超常价值=(权益的市场价值与债务的帐面价值-总资产)/总销售。同上,第47页。)他们发现即使在控制住诸如公司资产年限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仍然有某些关系。”(注:同上,第42页。)相反,麦冈利、桑德格恩和舒尼维尔斯(1988年)则报告说,对1983—1985年间美国《财富》杂志500强里的131家公司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以会计为基础的衡量方法还是以证券市场为基础的衡量方法部倾向于得出公司社会业绩与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结论。麦冈利等人用风险调整过的收益率和总收益率作为以证券市场为基础的衡量方法,另用资产回报率、总资产、销售增长率、资产增长率和营业利润增长率等作为以会计为基础的衡量方法。而奥珀尔里、卡罗尔和哈特菲尔德(1985年)的结论却落在亚历山大和巴奇霍茨(1978)以及阿博特和莫森(1979)的中间。奥珀尔里等人对《福布斯》杂志1981年名录里的818位高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强烈的社会责任导向或对社会的关心度与企业绩效之间没能发现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我们得出结论说不可能支持如下见解,即公司赢利能力与公司社会责任导向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注:见奥珀尔里、卡罗尔和哈特菲尔德:“公司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载《管理学会学刊》1985年,第28卷,第459页。)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卡罗尔1979年的论文之前或之后,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始终处于南辕北辙、各表东西的状态,“出现相互矛盾的结论,”(注:见卢孚、默拉里德哈、布朗、詹尼和保罗:“公司社会业绩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种相关利益者理论的观点”,载《商业伦理学刊》2001年,第32卷,第144页。)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也没有出现一派比较能够被接受的实证检验证据。在公司社会责任研究这样一个现状下,要完全指望它来给相关利益者理论提供实证检验上的强力支持显然是预期过高。
因此,相关利益者理论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在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上量体裁衣,用其所长,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在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关系的总体思路上,借用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在企业绩效衡量方法等技术细节处理上的优势,把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置换成相关利益者的概念,转而探讨相关利益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而这实际上也是别尔曼、凯撒、维克和琼斯等一群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和校友以及卢孚、默拉里德哈、布朗、詹尼和保罗这批学者最近致力进行的研究。
别尔曼等人认识到可以在相关利益者概念的基础上建立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实证模型。所谓“在相关利益者概念的基础上”,别尔曼指“我们集中于对公司经营非常重要的五个主要相关利益者领域:员工、自然环境、工作场所多元化、客户、产品安全性及与社区的关系。”(注:见别尔曼、凯撒、维克和琼斯:“相关利益者导向是否有用?相关利益者管理与公司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载《管理学会学刊》1999年,第42卷,第489页。)别尔曼等人解释说,倘若公司的相关利益者可以影响到公司目标的实现,那么,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公司的决策,即其业绩可能会受到相关利益者的影响。这样一来,公司相关利益者与企业绩效就建立起一种关系,公司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就被纳入到公司企业绩效的模型里了。别尔曼等人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管理者对相关利益者利益的关怀程度以那些相关利益者能够影响到公司企业绩效为限。”(注:同上,第492页。)为此,别尔曼等人提出若干个假设,其中之一即假设衡量相关利益者关系的变量对公司企业绩效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为了检验这一假设,别尔曼等人以1996年《财富》列出的500强里前100公司为初始样本,然后从KLD公司的数据库里挑选出具有完整数据的81家公司,计算其在1991—1996年期间的相关数据。最后,别尔曼等人采用KLD指数里衡量公司与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的五个主要指标即员工关系、多元化、当地社区、自然环境及产品的安全性与质量作为自变量,再用代表公司的企业绩效的资产回报率(ROA)作为因变量,对于上述两者进行双重回归的结果表明,员工关系及产品安全性与质量两个指标与公司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员工关系与ROA之间的参数估计值为0.3270(标准差为0.1162),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大于零;产品安全性与质量与ROA之间的参数估计值为0.2652(标准差为0.1359),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大于零。其他三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也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统计上不显著。别尔曼等人解释说,多元化和当地社区两个变量之所以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变量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往往被忽略掉。或者是由于与之相关的因素没有得到考虑,例如公司的地理位置等等。而自然环境变量没能呈现出显著关系则肯定是因为样本选择问题。所谓样本选择问题,别尔曼认为自然环境因行业文化不同而异,某些行业对环境保护的强调要远胜于其他行业,而别尔曼等人的样本包括了许多行业在内,自然无法区分出自然环境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尽管别尔曼等人的研究成果仍有美中不足之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得出如下定论:“现有的结果支持此一看法,即对多个相关利益者利益在管理上的关心能影响到公司企业绩效,这给相关利益者理论主义者长期坚持的主张提供了坚定的支持。”(注:见别尔曼、凯撒、维克和琼斯:“相关利益者导向是否有用?相关利益者管理与公司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载《管理学会学刊》1999年,第42卷,第503页。)难怪别尔曼自信地说:“我们的这份研究给相关利益者理论现有研究中的一系列前沿问题作出了贡献……这份研究为实证研究者今后用于进一步探讨对相关利益者利益的关心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注:见别尔曼、凯撒、维克和琼斯:“相关利益者导向是否有用?相关利益者管理与公司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载《管理学会学刊》1999年,第42卷,第503页。)
唐纳森和普雷斯顿曾说过:“不幸的是,大部分涉及到以公司社会业绩或道德伦理方面为一端与惯用的财务与市场业绩指标为另一端之间关系的文献无法轻而易举地转化到相关利益者理论内容里。”(注:见唐纳森和普雷斯顿:“公司相关利益者理论:概念、证据和应用”,载《管理学会评论》1995年,第20卷。第77—78页。)所幸的是,与90年代前公司社会责任的绝大部分实证研究相比,别尔曼、凯撒、维克和琼斯这篇实证研究尽管篇数甚少,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但毕竟这是相关利益者和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全面结合后踏出的新路子,同时也较为成功地在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框架里装入了相关利益者的概念,迎合了相关利益者理论对获取实证研究支持上的渴望。
四、公司社会责任与相关利益者理论:今后的发展
相关利益者理论与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确有很多共通之处,在九十年代两者也出现了从概念到实证检验的全面结合的现象。究竟这两种理论研究在今后将会相互借鉴而共生,还是会出现理上的整体融合,抑或由一方取代另一方?这是值得学界关心的问题。
首先,从理论上来看,九十年代以来,公司社会责任借用相关利益者的概念为其明晰了社会责任的范围,并发展出了用相关利益者的关系来衡量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思路。从这些方面看,缺乏理论基础的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与缺乏实证检验的相关利益者理论有可能会走向相互融合。但是社会责任的问题并不等同于相关利益者的问题。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如一个国家、省份或城市,在一定的时期通过法律或行政规定决定其特有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判断什么是必须考虑的社会问题时,要看是否存在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如果没有,则该问题不一定是社会问题,但是它可能是相关利益者问题。例如,在大部分国家,员工的职业计划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涉及到员工这一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可能成为公司的相关利益者问题之一。公司社会责任与相关利益者研究关心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公司社会责任是从整个社会出发考虑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关心的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相关利益者理论更多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待企业与其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看来,两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两者却不可等同。由此可以推断,这两种理论乃会各自保留自己的理论原则,在相互借鉴中共生。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是其中的一种理论取代另一种理论。弗里曼和利特卡在1991年发表的“公司社会责任:一种批判方法”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公司社会责任一说,倡导相关利益者的观点。他们甚至提出“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应当被放弃掉”(注:见弗里曼和利特卡:“公司社会责任:一种批判的方法”,载《企业瞭望》1991,7—8月,第92页。)弗里曼等人列出了7条放弃公司社会责任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公司社会责任的“出身”令人怀疑,它起源于经济学而忽略了历史、宗教和文化等等环境影响因素;各种公司社会责任模型都将公司看作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将实现经济目的做为公司的首要任务;公司社会责任接受的信条是“资本主义:热爱它或者离开它”;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保守的;公司社会责任要求管理者对他们没有经验的问题进行决策,导致管理者无法胜任;公司社会责任将企业和社会看作是互相分离,通过责任才能联结在一起,而事实上企业与社会是不可分的;最后,权利和责任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只有在对分配问题达成共识后讨论权利和责任的分配才有意义。根据这7条理由,弗里曼等人提议“为了建设一个好的社会,企业界必须接受一套新的道德责任。”(注:同上,第92—97页。)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虽然弗里曼乃是相关利益者理论的祖师爷,但他的这一极端观点至今未见到其他附和者。
其次,从方法上来看,别尔曼等人(1999)借用KLD指数作为衡量企业与相关利益者关系的代表变量,通过检验KLD指数与公司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相关利益者理论提供可供实证检验的模型。但是,从模型本身来看,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模型是完全一样的,不过是给KLD指数赋以相关利益者的含义,实质上是在公司社会责任的旧瓶中装进了相关利益者的新酒。从KLD指数的设计来看,充其量也只能说部分地反映了相关利益者理论。KLD指数的第六项(南非投资、军事工业和核能)本质并不是相关利益者的本意,更多的还是在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里。当然,关于相关利益者理论和公司社会责任结合之后的实证检验文章为数不多,尚待进一步的观察。
标签: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论文; 社会责任报告论文; 企业的社会责任论文; 社会责任标准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企业责任论文; 商业伦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