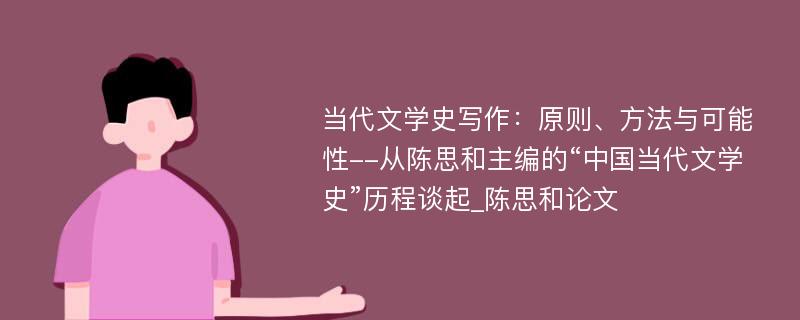
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可能性论文,当代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写”当代文学史的最便利也是目前最通行的方法是“续写”,没有时间下限的“中国当代文学”具有比“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丰富得多的资源,但或许正是这一特点使“当代文学”始终无法确立相对稳定的学科规范。随着新的文学现象不断被新版的文学史收编,作为“当代文学”重要阶段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则不断“缩水”,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少,甚至在有的版本中变成了空白。然而,长达27年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们有着比“新时期文学”更长的历史,也不仅因为在这两个时期文学对社会的影响比“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要强烈得多,还在于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意义。如果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延安文学”视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进行研究,或者进一步上溯到历史更长的“左翼文学”,那么,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文学现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对于“当代文学”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当代文学研究的结构失衡,一方面源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缺乏在今天讨论这种文学方式的知识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由于在这个当代文学史的著名难题上做出的大胆探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教程》集中体现了80年代风靡一时的口号“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者陈思和近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背景上对当代文学史问题的思考,以“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两个全新的文学史概念完成了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重新整合,并以此重构了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构架。考察这些范畴对“当代文学史”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知识结构的冲击,辨析新的探索带来的新的问题,其意义将远远超越对一部文学史新著的评价。
一、“潜在写作”
“潜在写作”是《教程》用来“重写文学史”的一个基本范畴,它指称的是1949年至1976年间(也就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写作其时得不到公开发表,‘文革’结束后才公开出版发行。”《教程》认为这些作品“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这些文字比当时公开发表的作品更加真实和美丽,因此从今天看来也更加具有文学史的价值”(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0页。)。在这一原则下,被称为“潜在写作”的作品如胡风、牛汉、曾卓、绿原、穆旦、唐湜、彭燕郊的诗,张中晓、丰子恺的散文,以及“文革”中的黄翔、食指、岳重、多多的诗,赵振开的小说,等等,都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了文学史的视野,新的文学资源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面貌,正如《教程》的前言所指出的:
“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一个时代的公开出版物为讨论对象,把特定时代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现象来讨论。我在本教材中所作的尝试是改变这一单一的文学观念,不仅讨论特定时代下公开出版的作品,也注意到同一时代的潜在写作,即虽然这些作品当时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发表,但它们确实在那个时代已经诞生了,实际上已经显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多层次的精神现象。以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为轴心,使原先显得贫乏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8页。)
应当承认,“潜在写作”的进入,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一部面目一新的当代文学史。然而,我们在领略“潜在写作”给文学史带来的生机时,也同时面临着这种新的文学史方法带来的新的问题,尤其是这种方式对文学史写作的一些基本原则所产生的挑战。由于“潜在写作”都是在“文革”后才获得正式出版的机会,因此这些作品的真实创作时间极难辨认。《教程》按照“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作品的发表时间”来进行认定,也就是说按照这些作品正式出版时标示的创作时间来确定其文学史意义,显然过于简略地处理了这个对文学史写作而言非常重要的问题。
被称为“潜在写作”的作品的写作、传播、出版的过程都极为复杂,对其创作时间的辨析很难一概而论。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些作品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作品曾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作品发表的时间往往不是由作者本人提供,如“文革”中流行的食指的诗(注:食指的几首代表作如《相信未来》、《命运》、《疯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都曾在“文革”中广为流传,这些作品从1979年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出现,1980年《诗刊》1 月号上正式发表了他的《相信未来》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白洋淀诗歌”中的根子(岳重)的仅存的两首诗《三月与末日》、《白洋淀》亦可以归入此类(注:根子(岳重)曾被称为白洋淀的“诗霸”,但流传下来的“白洋淀诗歌”仅两首,分别为《三月与末日》与《白洋淀》,《三月与末日》有多多保存的手稿,《白洋淀》由上海作家陈村保存,1985年交湖南《新创作》发表。)。这一类作品较为可信,但此类作品在“潜在写作”中数量很少;第二类作品也曾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文革”后由作者本人修改正式出版,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等作品可归入此类(注: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的写作始于1963年,后多次修改,手抄本曾在湖南、北京流传,作者曾因此入狱,1979年7 月经作者重新修订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写于1974年,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阅,1976年修改,1979年再次修改后出版单行本,1981年2月在《长江文学丛刊》第1期正式发表。靳凡(刘莉莉,即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初稿完成于1972年,曾以手抄本和打印本形式流传,1979年经作者修改后,发表于北京《十月》。)。这些作品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正式出版,时代的反差不大,但这些作品出版时已经经过了作者不同程度的修改,我们很难仍将其视为“文革”时期流传的原作;与第一二类作品不同,第三类作品则完全没有“地下”传播史,至发表之日没有任何见证者,我们只能从这些作品正式出版时由作者本人或整理者标明的创作时间来确立其“潜在写作”的身份。“潜在写作”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真实性几乎无法认定的作品,而且正是因为其真实性无法辨析,此类作品至今仍被源源不断地“发现”——或者被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注:诗人廖亦武曾在发表于1996年第11期《读书》的一篇文章认为这种对历史名望的追逐是一种“操作历史”的行为,“同作品相比,围绕着作品,最终偏离作品,直指历史和现实地位的后现代爆炒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诗人被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成名规则熏陶成了从媚俗到领导时尚的阴谋家。”)。
这并不仅仅是《教程》遇到的问题,或许是有感于当代文学史资源的匮乏,近年来,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中,一直存在一种与《教程》类似的以这种“未正式出版物”重构文学史的努力,“潜在写作”、“地下文学”的发掘引发了持续的热情,缓解了我们的“文学史焦虑”,然而,对致力于以这些“潜在写作”来改写文学史的研究者而言,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却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不妨以“潜在写作”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白洋淀诗歌”为例。近年来,“白洋淀诗歌”的发掘与研究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事件。随着“白洋淀诗歌”的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意义被不断发掘出来,人们惊讶地发现与“白洋淀诗歌”达到的人性与艺术的深度相比,8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朦胧诗”不过是浪得虚名,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代主义”诗风也只是向“白洋淀诗歌”的回归。被埋没的诗歌英雄和他们生长的土地引发了持续的激动与敬意。白洋淀成为了诗人、寻梦者、怀旧者、文学史家、汉学家和旅游者的圣地,一次又一次由不同国籍的人士组成的寻访活动踏上了朝圣之旅,在1994年春天由一家著名的诗歌刊物组织的由一大批著名诗人与诗评家参加的寻访活动中,人们接受了一位老诗人的提议,决定以一个诗意化的名称“白洋淀诗歌群落”来为这段历史命名,因为“群落”这个概念“描述了特定的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在一片文化废墟之上,执着地挖掘、吸吮着历尽劫难而后存的文化营养,营建着专属于自己的一片诗的净土”(注: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见《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诗人廖亦武则在他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中干脆将“白洋淀诗歌”更形象地命名为“诗歌江湖”,通常出现在武侠小说中与朝廷、政治对立的“江湖”概念,再度使“明眸皓齿”的白洋淀变成了诗歌的故乡,它不仅如同沙漠绿洲与空谷足音那样填补了十年“文革文学”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象征出一个黑暗幽晦的年代里文学的反抗与力量。发生在那个令人惊悸的恐怖岁月中的诗歌怀想,在沉沉的暗夜里,散发出不灭而温馨的人性光辉。英雄们高举起诗歌的旗帜,与一百公里以外的京城遥遥相抗,写就了一部形象而生动的“双城记”,这是“地下”与“地上”、“乡村”与“城市”的对抗,同时又是诗歌与权力、文学与政治的对决。
在“白洋淀诗歌”的三位主要诗人根子、多多与芒克中,多多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早已辍笔多年的根子的诗歌多已散失,而从未被“埋没”的芒克在诗坛一直影响有限,因此,真正被重新“发现”的诗人是多多。多多的“白洋淀诗歌”包括《啊,太阳》、《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1972),《告别》(1972),《无题》(1974),《夏》、《秋》(1975),《夜》(1973),《黄昏》(1973),《致太阳》(1973),《黄昏》(1974),《乌鸦》(1974),《玛格丽和我的旅行》(1974),等等,这些诗歌对现实的冷峻批判以及波德莱尔、本雅明式的抒情风格不仅使“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黯然失色,而且使新时期风头正健的“朦胧诗人”心悦诚服,人们不得不惊叹在一个蒙昧主义的时代诗人的想象力以及超越现实的力量。1988年,多多被授予诗歌奖,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第二年,多多在一篇题为《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的文章中表达了对当代文学的强烈不满:“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了天空”,从此以后,多多成为了“白洋淀诗歌”最重要的代言人与阐释者。
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或不愿意提到)这些给多多乃至“白洋淀诗歌”带来巨大声誉的诗歌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是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北大五四文学社”为出版内部刊物《新诗潮诗集》向多多征集诗歌,多多提供了这些分别注明了创作时间的“白洋淀诗歌”,随后,这些诗歌又在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诗歌专集《行礼》与1989年出版于香港的诗集《里程》中与读者见面,这两个正式版本中的“白洋淀诗歌”又有了新的改动(注: 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Maghiel van Crevel)以研究多多诗歌闻名,虽然他并没有关注多多诗歌的版本问题,但他对多多不同时期诗歌的清理,仍使我们再度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多多诗歌的政治性与中国性》一文中,他指出多多发表于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的几首重要诗歌与《里程》“略有不同”,而《里程》与《行礼》“两种版本很不一样”。)。包括《教程》在内的所有对多多的评价依据的都是这些80年代中期以后的版本,而多多的这些“白洋淀诗歌”是否真正创作于这些诗歌所标示的时代却缺乏有力的证据。我们在大量有关“白洋淀诗歌”的回忆文章中,在最权威的“地下文学”收藏家赵一凡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材料中,在80年代以前集中发表过“白洋淀诗歌”的一些诗歌刊物中,都没有找到这些重要的“白洋淀诗歌”(注:一些关于多多诗歌的加快文章更加深了这种疑惑,宋海泉在回忆文章《白洋淀琐忆》中提及:“毛头(即多多,引者注)对自己的诗改了又改,精雕细琢。很多作品发表时同我当年看到的已大不相同”。多多的另一位朋友周舵在《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中也表达过这种为好朋友写回忆录的困惑:“是要真实,还是要朋友,你必须二者择一”,这篇文章对多多的回忆似乎包含了许多隐衷。廖亦武则说:“我们收集到著名诗人多多写于1972年的短诗《当人民从干酷上站起》震惊之余又不得其解,因为70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见过‘干酪’,更谈不上‘从干酪上站起’了。”以上文章,均见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一书第254、203、54页。)。对于文学史的写作而言,多多的这些诗歌到底作于70年代前期还是80年代中期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虽然发表这些诗歌的80年代中期距“白洋淀诗歌”时代并不十分遥远,但文学语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始终无法证实这些“白洋淀诗歌”的真实性,我们又如何能赋予一种或许并不真正存在的文学以“文学史地位”,虽然这种文学无论在人性的深度还是在艺术的深度上都更真切地表达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想象与希望。
多多的诗歌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选择多多诗歌来讨论“潜在写作”的真实性完全是因为多多诗歌乃至“白洋淀诗歌”对于“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性。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潜在写作”都存在类似的“版本”问题。以批判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将军吟》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但从作家莫应丰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却得知小说创作于1976年10月以前,在《将军吟》的结尾中我们也看到作者的题辞:“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至六月二十六日冒死写于文家市”。这样,对《将军吟》就会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方式,如果从它的出版日期判断,它应当属于“新时期文学”的范畴,在“新时期文学”中,《将军吟》这样的作品很难获得较高的文学史评价;如果我们将其视为“文革”时期的作品,《将军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就不应被忽略……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对“潜在写作”的真实性的辨析,并无意于进行一种道德的批评,事实上,对作家而言,如何确定作品的创作时间根本与道德无关,不断修改自己过去的作品常常是艺术家的通病——大多数艺术家并无意为文学史创作作品。而且,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尽管我们无法确认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是“真”的,我们也同样无法证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是“假”的。
我们相信将诗歌奖授予多多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甚至我们也无意否认多多是中国当代诗坛不可多得的优秀诗人,对于崇尚艺术永恒的批评家而言,真正伟大的文学创造的文学性是超时代的,这些作品到底完成于何时并不重要。然而,文学史的写作却与此不同。对作品语境的确认历来是文学史最基本的工作之一,按照福柯的“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的“知识考古学”原则,在不同时代讲述的“话语”的文学史意义将迥然不同。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史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尝试以文学史的方式来考察这些作品时,作品的真实创作年代与版本才可能成为问题。
二、“民间意识”
“民间意识”(有时又称为“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等等)是《教程》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它的重要性不在“潜在写作”之下。如果说“潜在写作”的出现补充和丰富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写作,那么,“民间意识”则是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原有经典作品的重读。《教程》的作者这样解释所谓的“民间意识”:
所谓艺术的隐形结构,是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当时许多作品的显形结构都宣扬了国家意志,如一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政治运动,但作为艺术作品,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读物,由于作家们沟通了民间的文化形态,在表达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形式,这时候的民间形式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它把作品的艺术表现的支点引向民间立场,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民间读物。这种艺术结构的民间性,称做艺术的隐形结构。(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9页。)
……这种自民间文化而产生的‘隐形结构’不但在京剧里能发现,在芭蕾舞样板戏里同样能发现;不但在戏曲作品里体现出来,而且在五十年代以来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另一套话语关系。(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51页。)
……有没有注入民间的艺术精神往往成了那个时期艺术创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51页。)
正是依据这一原则,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中,《教程》突出了“十七年文学”中作为“民间文化的代言人”的赵树理小说的意义,同时也对根据李準小说改编的电影《李双双》评价很高,认为它蕴涵的民间艺术的隐形结构“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艺术生命长远的一部优秀喜剧片”(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65页。)。《教程》还认为《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都是“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的成功之作”(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65页。),尤其是《林海雪原》,“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66页。),在结构布局上,则“带有明显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1版第168页。)。因为同样的理由,直接体现民间精神的《刘三姐》、《阿诗玛》等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教程》中也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教程》中单独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章节“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进行论述。这一原则同样贯穿在对“文革”主流作品“样板戏”的解读中,《教程》认为“真正决定样板戏的艺术价值的,仍然是民间文化中的某些隐形结构”(注:见陈思和文章《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载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31页。)。 如《沙家浜》的角色原型,“直接来自民间文学中非常广泛的‘一女三男’的角色原型”,《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则暗含了另一个“隐形结构”——“道魔斗法”。因此,《教程》总结道:“在文革文学中,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实现国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民间文化形态的自在境界不可能以完整本然的面貌表现,它只能依托时代共名的显形形式隐晦地表达。但只要它存在,即有转化为惹人喜爱的艺术因素,散发出艺术魅力,从而部分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僵化、死硬与教条。民间隐形结构典型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无孔不入的生命力,它远远不是被动的,在被时代共名所改造的利用的同时,处处充满了它的反改造和反渗透。”(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68页。)
由于注意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的差异,《教程》中的这种民间意识视角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一些被我们长期忽略的文学史要素,然而,对民间意识的这种独立性的过分强调带来的一种新的危险,就是对民间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同构关系的忽略,以及因过分强调民间意识的稳定性而忽略了民间意识在近现代中国变化与发展的过程。在《教程》的分析中,作为“隐形结构”存在的“民间文化”或“民间意识”,无论在“十七年文学”还是在“文革文学”中都具有稳定不变的形态,这种“民间文化”的理解显然受到著名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的影响(注:见陈思和文章《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载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12页。), 然而,雷德菲尔德对两种文化的分析并没有忽略其内在的联系——“两种传统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一直相互影响及连续互动”(注:(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o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Univ of Chicago press.1956.p.70—71))。事实上,“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历来是特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改变着自己的形态。《教程》中讨论的“民间”,是一种“与当时意识形态发生直接关系的,仅仅是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注:见陈思和文章《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载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18页。),然而, 中国农民的这种文化传统并不是“固有”的,它与农民在古代社会的经济地位、生产方式、土地制度息息相关,当然也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20世纪的“民间”与传统意义中的“民间”并非完全同一,即使是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我们见到的“民间”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在《教程》的分析中,无论在“十七年文学”还是在“文革文学”中,“民间意识”都是以“隐形结构”的方式外在于政治的“显形结构”。这种民间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值得辨析的。因为从30年代即已开始并延续到50年代的使“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传统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民间伦理的回归。平均地权不仅曾是中国农民的持久愿望,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稳定运行的必然要求。“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作品《红旗谱》就生动地记录了农民朱老巩因反抗地主冯老兰对48亩公田的侵吞而结下世代血仇的故事。平均地权不仅仅成为了历代革命家的理想,也成为了包括孙中山与共产党在内的现代革命的目标与口号,因此大多数农民会将实现了自己土地梦的革命视为“自己的”革命。在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民间意识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近代以来被不断中断的传统民间意识得到了回归与修复。孟悦在一篇对歌剧《白毛女》的分析中就曾经使我们清晰地目睹了民间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过程(注:见孟悦文章《〈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载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在《白毛女》叙事开始的地方,出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个由亲子和邻里关系为基本单位、混合传统伦理亲情的和谐的民间社会,这一体现了民间理想的和谐的民间社会随着黄世仁的出现而土崩瓦解,黄世仁以一种秩序的破坏者的身份出场,以一系列的恶行冒犯了一个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而共产党的到来则使被破坏的民间文化——民间意识形态得到了修复,喜儿重新回到了人群中,秩序的破坏者受到了惩罚。在这样的叙事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建构的是“新社会”的合法性,这里的“人”是一种传统意识,它的合法性是无须证明的,需要证明的是“新社会”——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治伦理化的修辞绝不仅仅出现在《白毛女》之中,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修辞手段,在《王贵与李香香》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结构,“反革命”总是意味着对秩序的破坏,而“革命”则意味着秩序的修复与回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样的叙事中,政治的合法性是通过对民间意识的认同与回归获得的。在“十七年文学”中,我们同样清晰地看到这种“显形”而非“隐含”的民间意识,被《教程》视为集中表达了民间意识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一类的作品并不是边缘性的作品,无论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就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而言,这些作品都是不折不扣的主流文学作品。此类小说的大量流行,说明“民间意识”在“十七年”尚未结束其历史使命(注:近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十七年文学”中一些充满传奇性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李陀在 1991 年提出了“革命通俗文学”的概念;198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一书对这一问题有比较系统的阐述;董之林在1999年第5 期《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了文章《“新”英雄与“老”故事——关于五十年代革命传奇小说》,等等。)。
土地改革之后即起的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确形成了对传统民间意识的冲击,然而,以此断言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的分庭抗礼同样显得证据不足。公社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民间意识的经济基础,铲除了传统民间意识的土壤。人民公社的主要内容就是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收归为集体所有,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民家庭的生产职能荡然无存,而在《李双双小传》中反映的农村公共食堂甚至尝试取消家庭的消费功能。失去了生产功能与消费功能的家庭已经成为了一个空洞的能指,血缘甚至地缘都不再是个体的意义所在,现实中的家庭被“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所取代,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传统民间意识分崩离析,作为经济集中体现的政治必然创造出与自己相适应、为自己服务的民间意识,政治内容在创造着与自身相适应的修辞形式。“文革”主流文学的代表样式、“自《国际歌》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最最光辉的成果”——“样板戏”就是这种全新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京剧特有的程式化、脸谱化、符号化的特征为“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提供了有效的形式。《教程》从京剧《沙家浜》、《红灯记》与《智取威虎山》等作品中分离出“一女三男”与“道魔斗法”等“民间”模式,认为样板戏的艺术价值正是这些“民间隐形结构”体现的,事实上,京剧“样板戏”的民间意识绝不仅仅是以这样隐含的方式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戏曲,尤其是集中国戏曲大成、在清代取代文人化的昆曲成为中国第一大戏种的京剧是最为典型的民间艺术,当然也是典型的“民间意识”的承载者,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看到和承认这一点,“民间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在这里再度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民间意识”在《教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是因为《教程》的作者为“民间意识”赋予了“自由”的本质:“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2页。)显然,“民间的传统”或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是否真正具有超历史、超语境的自由本质,或者说“民间”是否能真正独立于主流政治——或者说,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形式”是否与不同时代的“内容”没有关联,这显然都是我们想象“民间”的关键。以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形式感的民间艺术——京剧为例,传统京剧曲目基本上都是以忠孝廉节这些基本道德观念与君臣父子这类尊卑贵贱的伦理方法为基本内核的,这些道德原则通过反复的程式化处理,使观众不知不觉地接受教化,属于京剧“形式”范围的脸谱、服装、音乐无一不显示价值判断的意义。当观众日复一日地沉醉于京剧的程式——形式时,他不断领略的其实是形式蕴涵的道德原则。“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高则诚在《琵琶记》中“副末开场”中的这两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京剧的这种意识形态本质。因此,虽然京剧不属于“诗文”那样的传道教化的正统文化范围,但传统民间文化从来就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明清以降,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民间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虽然文人文化总是强调它的异端性,但事实上,民间文化从来没有发展出超越儒家文化的能力,它的所有运作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固有的框架中进行的,成为封建文化的重要补充;而在现当代,“民间意识”也始终没有真正外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在“十七年文学”还是在“文革文学”中,“民间意识”都始终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就不可能被分离为两个世界或两种结构进行阅读——正如在《教程》中被不断引用而又被不断背离的马克思的名言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三、“本质论”与“知识考古学”
在《教程》的开篇,作者希望这部新的文学史能够“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造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8页。)。 由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所谓的“一元化视角”主要是指“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写作,因此,重写这两个重要时期的文学史就成为了包括《教程》在内的所有新版当代文学史的共同目标。正因为这个原因,“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成为了《教程》中最重要的概念,它们支撑起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基本构架,成为这两个重要阶段的文学史意义的新的生长点,体现出《教程》作者寻求更完整的当代文学史结构的努力。然而,正如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指出的,由于这两个概念难以克服的问题,《教程》作者希望实现的“新的文学创作的整体观”并没有真正完成。仔细分析《教程》的结构,我们不难发现“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在《教程》中呈现的一种“互文性”——它们都是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主流文学的“他者”存在的,按照作者的理解,恰恰是“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这两种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之外,保存和传播了文学的薪火,保留了被主流文学“中断”了的中国新文学的“两个传统”(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7页。 )——“潜在写作”保留了“五四文学”的传统,“民间意识”则保留了“民间文学”的传统。显然,不管是否形成了自觉意识,作者在这里预置了一个潜在的模式,即“非文学”——主流文学与“真文学”——潜在·民间写作的对立模式。这种对文学史的认知方式无疑仍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方式。
指出作者陷入“二元对立”立场多少带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二元对立”(或称为“一元论”)是作者在整个《教程》中不断批判与解构的范畴(注:《教程》前言曾指出50年代文学观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见《教程》第6页), 《教程》还认为这种“在当代各类创作中都是存在的”二元对立模式其实是战争文化的产物,“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因为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成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这种由战场上养成的思维习惯支配了文学创作,就产生了‘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见《教程》第57页)。)。《教程》作者在“前言”中解释“多层面”这一概念时,曾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
以往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常常用一元的视角切入文学史,也即根据当时的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来规范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史在叙述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时,不管其艺术感知力的高低,都一律以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作品作为其时代的代表作,而当时被忽略或者被否定、甚至是没有发表的作品,一概进不了文学史。所以讲散文就只有歌颂性的散文,讲诗歌也只有颂歌型的诗歌,似乎离开了这些流于时代表层的作家作品,当代文学史就无从讲起……但如果深入一步去看文学史,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个时代里,其实仍然有作家们严肃的写作和思考……而这些被时代的喧嚣所淹没的声音,恰恰充满了个人性和独创性,这同样是时代的声音,而且更本质地反映了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1页。)
《教程》对“传统的当代文学史”的批评无疑是非常中肯的,正是因为不满于这种“一元文学史”的武断与粗暴,“重写文学史”才成为了文学史研究者的共同追求,然而,问题在于,被《教程》用来替代这种“一元文学史观”的新文学史观是否真正具有摆脱这种“一元的视角”的能力?
如果对文学史的重写只是“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将“边缘”与“中心”进行置换,新旧两种文学史的差异是非常有限的。就如同我们过去对历史进行“唯物主义”分析时总是过份强调“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对立一样,过份强调“主流意识形态”与“潜在写作”和“民间意识”的对立常常使我们忽略在同一个社会结构中生存的“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主流”与“民间”之间相互依从的关系。应当指出,对于“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的纯粹性,《教程》的作者并非全无疑惑,在《教程》的一些段落中我们也不时读到对相关问题的清醒论述,然而,《教程》的基本结构决定了思想的限度,当《教程》从一开始将“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放置在主流文学的“他者”位置上时,两种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就已经不可改变了。《教程》对“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的认同是以对“主流文学”的否定为前提的。在《教程》的前言中,作者曾表示“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一个时代的公开出版物为讨论对象,把特定时代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时代的这样精神现象来讨论”,因此“在本教材中所作的尝试是改变这一单一的文学观念”(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 8页。),应该说作者的目标部分得到了实现。《教程》的确使我们看到了许多被从前的文学史边缘化的东西,然而在这些历史的盲点浮出水面的同时,许多我们曾经熟知的文学史现象竟然又在不知不觉间沦入到历史苍凉的雾霭之中,成为了文学史上新的“失踪者”,我们因之失去了“把特定时代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现象来讨论”的可能性。在《教程》的“后记”中,作者坦陈《教程》中没有对一些“比较复杂,需要重新认识和解读的重要作品”如《创业史》、《青春之歌》和《红旗谱》等进行细致的讨论(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 月第1版第434页。),显然,在《教程》中,这些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作品被忽略了。虽然文学作品的发行量与社会影响力不是衡量一部“杰作”的标志,但对包括在50年当代文学史上发行量最大的长篇小说《红岩》在内的许多曾经引起广泛社会反响、参与塑造了数代中国人灵魂的作品熟视无睹,这样的文学史很难说具有真正“完整的”文学史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空白论”,如果这种“盲视”并不是文学史的写作者的主观选择,那么就一定是写作者采用的文学史方法存在问题。
《教程》在分析“十七年”小说《红日》时曾论及一些战争小说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即“能不能打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艺术模式写出反面人物的复杂精神世界”(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59页。),《教程》认为这一点对战争小说的成功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为对一部优秀的当代文学史的要求,这一原则要求我们的文学史在充分关注非主流文学的价值时,能够打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写出“十七年”与“文革”时代的主流作家或主流作品的“复杂精神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首先形成方法论的自觉意识。
当代文学史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与文学史观有关,它是建立在一元论或本质论基础上的历史观的再现。在这一点上,近年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他山之石”,其中福柯在思考“人文学科的批判哲学”时提出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尤其值得关注。在对人文学科历史的把握中,福柯所关心的主要是某些特殊类型的话语,但他关心的既不是这些特殊话语本身是否具有真理性,也不是如何去整理和寻找那些被证明为是具有真理性的特殊话语的规则,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不考虑话语“对”与“错”或“是”与“非”的前提下,研究某些类型的特殊话语的规律性以及这些话语形成所经历的变化。他把这种话语研究和分析的方法称为“考古方法”(archaeology)——譬如说, 如果一位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本2000年以前的天文学著作,那上面说地球是方的,考古学家不应因为这本天文学著作对地球的形状作了错误的陈述(因为它明明是圆的——椭圆的)就放弃对它的研究,考古学家要问的是这句话在某时某地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他想了解的是这样的表述如何表达了这个时代人们想象世界与认识自己的方式——在福柯看来,任何话语都有它自己的规范概念和论述范围,有它自己认可的对象和方法,这一切决定了它自认为具有某种特定的“真理性”,“知识考古学”所需要发掘的正是那些因年代久远或因为想当然而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认识机制。
尝试以“知识考古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意味着我们将拆解那个已经进入我们潜意识的、其实完全受控于我们当下价值标准的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认知方式,我们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是那些以今天的观点看来是“真实”的文学作品,而是那些在当时被称为“文学”与“经典”的文学作品。对文学史的研究者来说,这些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今天的“真实”,也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我们今天理解的“艺术性”,而在于这些作品在某时某地的出现意味着什么,生活在某时某地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如此想象世界和自身,这种方法将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通过“文本的语境化”与“语境的文本化”使文学史的研究转变为一个时代与另一时代的平等对话,这不是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文学性、同一性、意向和历史连续性,而是力图把这些元素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方法,同时还将同时适用于对“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它意味着“80年代文学”将被放置在“80年代语境”中进行讨论,同样,“90年代文学”也将在“90年代语境”里进行把握——而不是采用我们通常运用的方法,以建立在“五四文学”基础上的一种被非历史化与高度抽象化的意识形态标准或文学立场研究和把握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期待了很长时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才可能真正由理论变为现实。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仍然只是一种“更好的”理论的可能性,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关于“如何写作当代文学史”的文章远远多于真正的文学史实践,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钱钟书先生的一句名言:“理论是由不实践的人制订的”。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当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写作实践表示由衷的敬意——这种敬意不仅仅针对这些新完成的文学史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应当针对在这些文学史写作中所暴露出的问题。
标签:陈思和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将军吟论文; 林海雪原论文; 白洋淀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