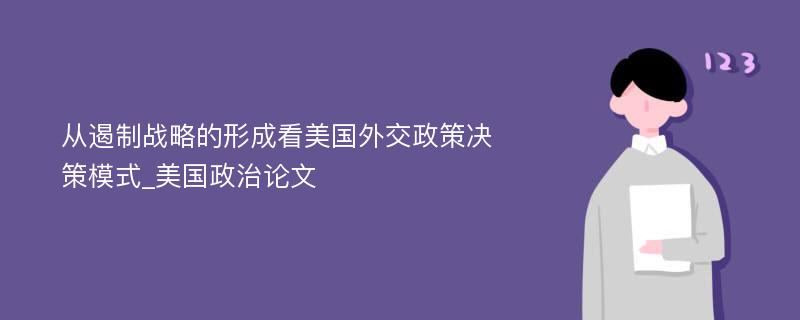
从“遏制”战略的形成析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终究是次要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安全事务的紧迫性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政府、国会、新闻界共同的运作基础,表现出华盛顿与华尔街亦步亦趋的真实关系。
关键词 遏制战略 美国 外交决策模式 总统政治中心 国会 舆论界
本文试图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以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遏制”战略的形成为例(之所以选择此例,是因为它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既有某种“危机”决策的特点,又属于长期战略决策),对美国外交决策模式进行透视。
一
在战后美国的任何一次重大外交决策中,以下成员总是参于其事:总统、国务院领导(包括相关驻外使节)、白宫班子、军队首脑、相关重要阁员、重要专家(即所谓谋士)、国会领袖和舆论界代表。在1945~1950年“遏制”战略酝酿、产生的过程中,参与其事的分别是: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马歇尔、艾奇逊;副国务卿洛维特;驻苏(后驻英)大使哈里曼;陆军部长史汀生、帕特森;海军部长(暨首任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商务部长华莱士;苏联问题专家凯南、波伦;参议员范登堡、塔夫脱等;著名记者及专栏作家李普曼、克罗克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有相当幅度的扩充,但不足以改变以下判断——美国对外政策是由一小批圈内人决定的。
其中,我们可以把所有隶属于行政部门的成员(包括三军首脑)归为一类,因为他们都由总统任用并直接领导(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白宫班子和重要专家(谋士)自然也可归入此类。这个小集团以总统为核心,可以称之为总统政治中心。因此,我们的问题可以简化为:在外交决策中,总统政治中心、国会和舆论界孰主孰次?
首先可以排除舆论界的主要地位。无论“外来人对美国新闻界、尤其是华府新闻界的权力……感到惊讶”〔1〕的程度有多高, 新闻界对决策尤其是外交决策的影响总是间接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常常受到权力人物的摆布。在战后之初美国外交决策形成的关键时期,福雷斯特尔定期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罗克提供秘密电报和备忘录;艾奇逊则随时向该报年轻的明星记者赖斯特提供情况。〔2〕当然, 这些材料已经经过选择。
相比之下,美国国会的情况就比较复杂。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国会有权征税、贷款、招募军队、宣战……并制定“为执行以上各项权力和依据本宪法授于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其他一切权力所需的必要的和恰当的法律”。最关键的,“国会掌握着政府的钱袋”〔3〕——拨款权。
在“遏制”战略形成过程中,国会一直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范登堡参议员在外交委员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两党一致”原则的确立使每一个关键性的拨款计划都顺利通过(最著名的如马歇尔计划),这正反映出美国国会地位之重要。艾奇逊曾由衷地表示:在为美国开辟新的道路或把美国引上新的道路方面,范登堡并没有提供思想、领导或动力,但他使这一切获得成功成为可能。评价不可谓不高。然而,这也促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到:国会的功能主要在于制衡而非决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原子弹。杜鲁门继任总统之前曾担任国会国际计划调查委员会主席,然而,他根本不知道“曼哈顿”计划的存在。〔4〕上台之后,杜鲁门很快成立了以史汀生为首的8人委员会,负责研究并向总统提供有关使用原子弹的建议。当然,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只对总统负责,外人是不得而知的。原子弹的出现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假如国会对此一无所知,那怎么可能在外交决策中掌握主动权呢?
“遏制”战略的基本思想自雅尔塔会议后已经开始在美国领导层中萌芽。杜鲁门上台后的第一次外交政策会议即确立了对苏强硬的调子——“单行道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5〕——他说。1946年2月,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从理论上阐明了“遏制”战略的基础,令华府喜出望外。〔6〕此后,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NSC68号文件,无一不是在杜鲁门直接过问下由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凯南、福雷斯特尔等一班国务院、白宫、军界的干才予以完成,再送国会通过的。
理论上,国会当然可以把总统政治中心的工作一笔勾销,否决提案。但在实际操作中,总统的武库里总是有足够的武器来保证提案的通过(历史上极罕见的一次例外是《凡尔赛和约》在美国国会的失败,但这只是表现了威尔逊总统的僵化,同时也为后任总统们提供了教训)。实在不行,总统还可以运用签订“行政协定”的办法来贯彻自己的外交主张。更重要的是,当国家面临危急局面,必须有所行动时,国会的涣散无力就暴露无遗,往往只能通过修正案的方式保全面子,因为由国会另外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方案是不可能的。
托马斯·帕特森对此作出了精当的评述:“早期冷战的另一个遗产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进程。杜鲁门政府有时使用恫吓政策来左右‘对外政策公众’的想法,大多数的政策辩论集中在支出多少上而不是是否需要支出。国会有时证明是不屈不挠的,但整个来说,杜鲁门得到了他所需要的。”〔7〕
必须指出,在美国政府与国会的关系中存在着相当的弹性。当国际局势动荡、紧张,特别在危机状态时,总统政治中心掌握局面的权威是压倒性的;而当局面缓和、稳定,国家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权力的重心则自然向总统政治中心以外滑动,主要滑向国会。因此,在战后历次美国外交决策中,国会与政府既妥协又斗争,地位此消彼长,常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然而,由此并不能判断总统政治中心基本不具备决策的主导权,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仍然控制着决策进程。因为正如前文所论,外交事务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始终存在,这是国会难以逾越的一道屏障。而更主要的是,在政府与国会基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美国政治的基本趋势是行政权力的加强,国会的权力从本质上讲仍属制衡作用。特别是在外交事务这种事关美国全局的决策上,美国政治运作的后台——垄断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过多的公开争论,真正的妥协在进入国会辩论之前已经完成了。而决策愈重大,这种妥协的完成就愈迅速,国会的声音则愈微弱,愈多纠缠于细枝末节。
在总统政治中心内部,总统的一元化领导是毫无挑战余地的。国务卿只是总统的代言人,不可能走得更远,贝尔纳斯的去职就是因为他对杜鲁门不够尊敬而非政见相异。至于坚持不同主张的亨利·华莱士,尽管资深望重,也只有辞职走人。〔8〕
那些地位稍低的谋臣干将如凯南、波伦等,更是工具型的人物。凯南一封“八千字电报”一举成名是因为其耸人听闻的语气和新颖的论证迎合了杜鲁门的需要。此后凯南一再强调政治遏制为主,正视苏联利益则无人理睬,最后干脆被排出核心圈子。艾奇逊称他是:“一匹到了跟前却不跳的马”。〔9〕其实,在杜鲁门的意志面前, 艾奇逊自己也不过是一匹稍好的“马”罢了。
可见,美国外交决策中总统政治中心是决定性的主体,总统又是这个主体中的核心。
二
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实际上一个以总统为中心协调各方意见的过程,其中既包括与国会、舆论界的协调,也包括总统政治中心内部的协调。此种协调是如何实现的呢?它有什么突出特征呢?本节以杜鲁门主义的产生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杜鲁门主义在“遏制”战略的形成中是一个里程碑。由此,“形成战后40年美国外交的总模式”。〔10〕
1947年2月21日(周五)中午, 美国国务院收到英国关于停止对希腊、土耳其援助,并希望美国接手的“蓝皮书”。副国务卿艾奇逊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国将“填补真空”。〔11〕他立刻指示助理国务卿亨得森主持欧洲与近东司官员们与军方合作起草报告。报告周日完成,周一向马歇尔汇报。当天中午,马歇尔与总统、军方就此事进行讨论。杜鲁门及其主要顾问接受了以下观点:“增强希腊和土耳其的力量以达到维护两国民族独立的目的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2〕周二(25日)杜鲁门批准了行动方案,表明总统政治中心内部协调基本完成。周四(27日)早晨,总统及其助手与国会领袖们讨论此事,最后范登堡表态将予以支持,表明与国会的协调基本成功。当晚,艾奇逊就此向经常采访国务院的20名记者发表谈话,以取得新闻界的呼应。在最后起草总统讲话时发生了争执,凯南和波伦反对其中对苏联威胁的莫须有的夸张,凯南甚至称:“在希腊问题上,这是完全没有理智的思想沟通。”〔13〕对此杜鲁门的反驳极其简洁:“不使用慷慨激昂的语言,国会不会批准这笔钱。”〔14〕事实上,正是范登堡告诫杜鲁门要把美国人“吓个半死”〔15〕才行。
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和“范登堡修正案”的出台,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但实际上,总统与范登堡的默契已决定了这一结果。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议员都已钻进了一个圈套:要么通过议案,要么表示对共产党“软弱”。总统的手腕起作用了。
通过对杜鲁门主义出笼过程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对美国外交政策决策方式的两个基本认识:
⒈决策过程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而“说服”是多元的、双向的。“总统既要去影响又要去反映政府和国家中的各种利益集团和有势力的集团。”〔16〕
⒉最后决定权形式上属国会,实际上掌握在总统手中。总统的决定即使不能原封不动地成为法案,也只需改头换面,贴上一个国会标签。
三
“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的一个特点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可以在政府和他们自己的银行或律师事务所之间轮流任职。”〔17〕——埃及·托马斯这一小段论述雄辩地说明了美国外交决策的动力根源。
总统、国务卿、议员、著名记者,无论他们在外交决策中担当的角色有何重大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前文已论述总统政治中心尤其总统个人在外交决策中的关键作用,但事实上,“以任何标准来衡量,总统的个人观点都不大可能是激进的,他自己之所以被挑中以及美国选择总统的复杂过程都保证他会遵循当前一致的意识形态。”〔18〕这种“一致的意识形态”属于哪个阶级?不言而喻。同样,总统身边的权势人物也“代表了范围相当狭小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19〕”。
这正是总统在外交决策方面实际权力居于国会之上的制度根源——国会所代表的是“各个地区各个利益集团的总和,而总统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20〕国家安全事务是不可分割的,资本家当然愿意(也别无选择)由总统来汇总他们的要求,国会可以批评(以表达部分资本家对利益分配的不满),可以修正,但不可以决定。
“遏制”战略的产生,也是这一原理的产物。
二战以后,美国国力傲视天下,对于其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扩张、再扩张是符合其根本利益要求的,而且这个要求也十分强烈。当时,英、法削弱,德、日战败,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只有苏联了。
实际上,当时苏联的经济实力尚远不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然而经济利益作为深层驱动力并不是孤立作用的,它必然与其他因素如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表现在国际关系中,便呈现多种矛盾相互作用的复杂局面。战后初期,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强有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美国人对自身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同时,自北美殖民时期开始,加尔文教派神学对美国人政治观念的巨大影响,带来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强烈的理想主义成份。“加尔文主义的思想气质视美国为救世主民族”〔21〕,把“自由”、“平等”传遍世界,遏制苏联邪恶帝国的发展成为许多美国人(包括许多中产阶级分子)的共识,二战胜利后美国实力的膨胀,更加剧了这种意识。
拉尔夫·德、贝茨称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为“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私自利”,〔22〕也算比较公允的评价了。
更为明确的结论可以表述为:华尔街的经济利益、价值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支配着华盛顿决策层的工作。
四
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⒈美国外交决策的主体是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国会、舆论界处于次要地位。
⒉外交决策符合一般公共政策的产生规律,须经过总统政治中心与国会、舆论界及其内部多元的、双向的说服工作,达成妥协。在这个过程中,总统实际具备最后决策权。
⒊美国外交政策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又受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强烈影响。上述所有个体均在这个大前提下活动。
外交决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所揭示的只是这座巨大冰山的一小角。任何把以上结论教条化的主张都是笔者坚决反对的。毕竟,每一次决策都是由具体情境下的具体个人作出的,个人的情绪好恶,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判断以及各种偶然性的影响都难以避免。因此,任何两次决策过程都不尽相同。但反之,完全从主观出发看待决策显然也无助于认清事实。笔者认为,外交决策既是个人行为,又是制度行为,而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层面上有组织的行动,因此,有规可循。同样因此,本文试图揭示这一行为基本特征的努力才具有基本的可能性。
注释:
〔1〕〔20〕〔美〕斯提芬·K·贝尼编《美国政治与政府》,河北大学1981年翻印,第24、111页。
〔2〕〔11〕〔13〕〔14〕〔17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等著《美国智囊六人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56、402、405、416、437页。
〔3〕〔16〕〔美〕加里·沃塞曼著《美国政治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60~68、69页。
〔4〕〔5〕〔美〕哈里·S·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出版,第2、3、108页。
〔6〕Dewey W·Curantham评述说:“kennan cogent ard cloqnentlomguage eapressed the uiews and predispositions that hadcome to prevail among American leaders by early 1947.”见其著《Recent America—the United tatessince 1945》Harlan Davidson,Inc.1987 P23.
〔7〕〔美〕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37页。
〔8〕〔9〕参见《美国智囊六人传》中的《杜鲁门回忆录》、《哈里·杜鲁门》、《艾奇逊回忆录》的有关章节。
〔10〕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6页。
〔12〕〔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78页。
〔15〕〔21〕〔美〕拉尔夫·德·贝茨著《1933~1973美国史》下卷,人出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2、48页。
〔18〕〔19〕〔美〕M·贝科威茨等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第292、294页。
〔21〕转引自王辑思著《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截《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第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