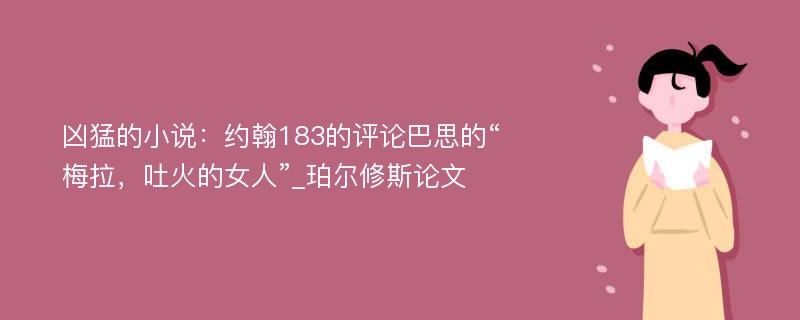
一部“狰狞的小说”——评约翰#183;巴思的《吐火女怪客迈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狰狞论文,怪客论文,小说论文,吐火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个人而言,我的脾气是选择以传统的方式反叛传统,因而我偏爱那种多数人做不来的艺术;这种艺术要求专门的知识和技艺,同时还需具有睿智的审美思想和/或启迪。
——约翰·巴思:“穷尽已竭的文学”
1972年,约翰·巴思出版了他的第5部长篇小说《吐火女怪客迈拉》(Chimera),当时的美国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反应几乎是两极化的,推崇者挟后现代主义劲势对作品的先锋意识及实验创作手法厚加赞誉,贬抑者则在读完作品后斥之以“不堪卒读”云云。争议相持不下,而这份热闹并没有在当年“全美图书奖”的评委中归于寂静,结果是对这部作品的肯定评价占了上风,但双方意见的裂隙却也并非了然无迹,巴思终于未能独折该奖小说项之桂,而是与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平分秋色。同一奖项由两人分享的情况在“全美图书奖”的授予历史上是素无先例的。[①a]
作品的争议性往往在于其不同寻常之处,而巴思的这部小说也的确是一部非常之作。首先是形式上的,若是将此搁置一边,这部小说的题旨几乎无从谈起。实际上可以这么说,这部小说的形式即是内容;形式的演绎便是主题的展现。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该小说的叙述结构入手,观照作品形式与题旨的关系,进而探讨作者的文学观是如何在这部作品中得以实践的。
先从小说的标题谈起。吐火女怪客迈拉(Chimera)源出希腊神话,是一个长着狮首、羊身、蛇尾的穴居怪兽,小说以此女怪命名可以从几层涵义上理解:其一,小说确实涉及有关女怪客迈拉的神话故事;其二是小说由三个中篇故事组合而成,在结构上恰好与女怪的三部分异形构造相对应;其三是小说的三个中篇分别为一个以阿拉伯传说为基础的“天方夜谭”(“敦妮亚佐德篇”)和两个取材于希腊神话的故事(“珀尔修斯篇”和“柏勒罗丰篇”),[②a]而这两种情调迥异的故事并存一体,使这部小说蒙上了某种怪异的色彩。正如巴思本人不无得意地借书中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一部狰狞的小说……一种怪异的混合意象。”[①b]这里自然是巴思惯用的反语。另外,Chimera一词在英文中还可以引伸为“幻想”、“异想”之类的意思,而这也正是作者赋予标题的暗示意味,其中隐含着他对于小说的某种观念。巴思曾经说过:“算了吧,现实是个可以光顾一下的好地方,但你却不会愿意在那儿落脚安居,而文学从来也未曾在那儿久留过。”对于巴思来说,小说是幻象,一如神话想象中的女怪客迈拉。既是幻象,小说自然可以一任想象力天马行空而不必囿于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模仿。这可以说是巴思的小说美学观的基本出发点,而这部名为《吐火女怪客迈拉》的小说正是一部颇富想象力的奇思异想之作。
开篇故事“敦妮亚佐德篇”所展现的情形对于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它取自于众所熟知的《一千零一夜》的传说,美丽的山鲁佐德(Scheherazade)夜复一夜地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讲了一千零一夜,救下了千百条无辜少女的性命,同时也救了自己一命。巴思重写了这一故事,以俚俗化和性感的语言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天方夜谭”。在这一故事中,巴思发挥性地利用了《一千零一夜》中原有的“框构故事”(frame-tale)[②b]的叙述模式。整个故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头至尾都被包容在引号之中,主要叙述声音是山鲁佐德,但主体叙述者却是她的妹妹敦妮亚佐德,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进入第二部分后,叙述变成了第三人称,这就交待了一个衔接点,第一部分原来是敦妮亚佐德对国王山鲁亚尔的弟弟沙·扎曼所讲的故事。而下面发生的则是这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其中的主要叙述声音是沙·扎曼。第三部分的叙述又回到了第一人称的方式,但叙述者是第一部分中出现的“魔仆”(the Genie)。这个人物其实可以看作是作者巴思本人的化身,关于他的外貌书中有这样一段酷似巴思的描写:他长得一点都不象山鲁佐德在床第间所讲的故事中的任何人;就谈一点吧,他虽然模样有些古怪但并不可怕,一个40多岁上下的家伙,肤色浅淡,脸修得挺光洁,脑袋秃得象大鹏下的蛋。他的衣着简单而奇特,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健康而令人舒服,只是他的两眼上架着一对镶在框里的古怪镜片。(第16页)“魔仆”的出现打破了时间和历史的重障,扩大了叙述空间,也使故事具有了现代性。虽然巴思在“敦妮亚佐德篇”中运用了多种叙述视角,又制造了繁复多变的叙述声音(尤其在第一部分中),但故事的叙述结构却是繁而不乱,层层相递:首先是山鲁佐德在对国王山鲁亚尔讲各种各样的奇异故事,这一情形连同山鲁佐德的故事实际上又是敦妮亚佐德正在对国王之弟沙·扎曼讲的故事,最外面一层则是化身为“魔仆”的巴思讲述敦妮亚佐德与沙·扎曼之间互讲故事的故事。因此,整个“敦妮亚佐德篇”的结构便是“故事套故事套故事”,其中以山鲁佐德讲故事为整个故事的核心,亦即故事的第一部分。于是,我们发现,巴思在运用“框构故事”的叙述模式时别出心裁地颠倒了内外框构,对此作者在书中以戏剧化的方式作了解释:在敦妮亚佐德讲述的一个场景里,山鲁佐德和“魔仆”在探讨
这样一些问题:譬如是否可以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将一个故事从内部框构,从而使通常情况下的容器与受容物之间的关系得以颠倒并且具有悖理的互逆性……或者是否可以超越一般的“故事套故事”,甚至是“众故事套众故事套众故事”——我们的“魔仆”在文学的宝库里发现了几例这样的故事,而他则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为这一宝库锦上添花——并且构思出一种故事系列,譬如说7个故事里套故事的同心故事,在安排上使得位于最核心的故事在达到高潮时引发其外的另一个故事的高潮,接着又引发再外面的故事的高潮,如此等等……。(第24页)
“魔仆”,或者说巴思,在文学宝库中发现的那种“框构故事”的叙述文学实际上主要指那些印度和波斯文学中的传奇系列,其中尤以《故事的海洋》(The Ocean of Story)和《一千零一夜》最为著名。巴思最早见到卷帙累累的《故事的海洋》是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当时他曾在大学图书馆里打工归理书籍。在他日后发表的一篇名为“故事的海洋”的文章里他说过:“我对整个框构故事文学作了数年一般性的研究,在与此相关的情况下,我最近终于从头至尾从容浏览了一篇《故事的海洋》。”在文章中,巴思提到了一个他认为对自己极富启发性的发现,那就是《故事的海洋》蕴含着一个非凡的叙述观念——“文本的历史”(history of the text)。[①c]“敦妮亚佐德篇”中的叙述结构便是对这一叙述观念的实践。正如巴思借“魔仆”之口在故事中解释的那样:
写成书的“一千零一夜”并非山鲁佐德的故事,而是关于她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实际上它这样开始:“有一本书名叫《一千零一夜》,里面说道,从前有个国王,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山鲁亚尔,另一个叫沙·扎曼,”如此等等……。(第55页)
巴思对“文本的历史”这一叙述观念的具体运用便是将原《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叙述者山鲁佐德在他的故事里换成她的妹妹敦妮亚佐德,这样,我们所读到的便是敦妮亚佐德的故事。多层次的叙述以及在叙述过程中各层次之间发生的交替使我们得以同时体验这一故事的不同层面,这就是巴思在处理原有故事素材时匠心独运之处。
当然,对这一叙述结构我们并非一开始就有了认识,而只是等读到故事的第二部分时我们方才知道,整个故事是敦妮亚佐德讲述的关于她和她的姐姐山鲁佐德的故事。这一部分的高潮是描写国王兄弟终于分别娶了讲故事的姐妹俩的一段场景,这一高潮引出了最外层的叙述声音,也就是“魔仆”/巴思的声音。故事的这种结构使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不断外扩的叙述张力,而与这种运动相对应的情况是,叙述也越来越远离原本故事的发生情形。[②c]这种叙述运动不是直线型的发展,而是一种扩张式的上升。巴思在书中用了“螺旋式上升”(spiralling)一词来说明这种叙述结构的特点,而且还以生长在马里兰州的沼泽地里的一种蜗牛形象来比喻:“它边爬边就地取材地给自己造壳儿,用自己的体液粘固它,而同时它又本能地爬向那些最宜于造壳儿的材料;它背负着自己的历史,生活于其中,并且在生长过程中不断地在现有的壳圈上增加新的更大的螺圈儿”(第10页)。这一蜗牛的意象同时也表达了巴思本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关注,即作家既要背负文学传统又要力图创造独出心裁的文学,从而超越传统。巴思的方式便是回归叙述的源头,以现代意识重写旧故事,如此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新故事。
小说的第二个故事“珀尔修斯篇”仍然保留了“框构故事”的叙述结构。同样,我们只有等读到整篇故事的结尾才能理解故事的开端;也就是说,这篇故事中也采用了“反向框构”的手法。一开始,珀尔修斯[③c]象第一篇中的敦妮亚佐德一样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他是在天上讲故事,因为此时的他是化作了“英仙座”(Perseid)的珀尔修斯。夜空中,他先是道了声“晚上好”,接着开始了这样的叙述:
每天夜里醒来,我都有隔世之感,继而发现自己原是身在天上,于是回忆起我醒来发现情形与此判然相反的那个夜晚。(第59页)
至此,天上的珀尔修斯开始讲述起他的凡世中的生活。但他的故事从中间讲起,这里可以看作是他后半部分生活经历的起点:他提着自己的战利品——蛇发女怪美杜莎(Medusa the Gorgon)的头颅——在空中飞行时坠入了沙漠,昏迷过去,醒来时发现置身于世人为其修建的螺旋形圣堂中,司管圣堂的是一个专攻古典神话的名叫卡莉克莎的女学生。珀尔修斯一边观看圣堂中的螺旋而上的壁画,一边向卡莉克莎讲壁画上描绘的神话英雄珀尔修斯杀死蛇发女怪的传奇故事。如此,从中间开始的故事又回溯到了珀尔修斯前半部分的传奇经历。这样的叙述是一种双重叙述,因为珀尔修斯在对卡莉克莎讲解壁画上的故事的同时他也是在讲述着他与卡莉克莎之间的关系,前者是故事的主叙述,后者是次叙述。[①d]主叙述的高潮发生在珀尔修斯观看到螺旋形壁画系列中最后一幅的时候:这幅壁画空白一片,延入珀尔修斯几乎渴毙于其中的茫茫沙漠。于是,过去和现在在交汇中失去了分界。这一高潮随即又引发了次叙述中的高潮:珀尔修斯恢复了性功能,终于与卡莉克莎有了成功的性交。卡莉克莎在圣堂中帮助珀尔修斯通过壁画认识子他作为神话中传奇英雄的前半部分的生活经历,这促使他决意去完成对自己后半部分生活的认识。接下来的故事便是关于他如何离开圣堂,前往雅法去解除他与妻子安德洛墨达(Andromeda)的婚约,最终爱上了获得新生后的美杜莎。打破这一故事的叙述框构的是一个新的声音的加入:当珀尔修斯在说起卡莉克莎的“纤美的腰”和“精巧的臀”时,另一个声音打断了他:“没必要一个劲儿地说纤美的腰和精巧的臀之类的话”(第95页)。这个声音便是新美杜莎。闻此话音后,珀尔修斯答道:“对不起,亲爱的,晚上好。”美杜莎的打断把我们一下了从故事的最里层带到了最外层——我们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头:高悬于天上的珀尔修斯原来是在向同样变成了星座的新美杜莎讲述他早先如何对卡莉克莎讲述他的故事。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巴思借“魔仆”之口设想的有关故事的内外框构具有悖理的互逆性之言了。如同“敦妮亚佐德篇”一样,“珀尔修斯篇”的叙述结构也是故事中套故事再套故事。这种框构叙述技巧同样也使整个故事同时展现了三个层面:其一是有关神话英雄珀尔修斯的故事,其二是珀尔修斯向卡莉克莎讲述的他作为凡夫俗子陷于中年危机的故事,其三是作为星座的珀尔修斯与其永恒的情人美杜莎在夜空中的对话。在“敦妮亚佐德篇”中建立起来的螺旋形叙述结构在此篇中再一次出现,而且更为显著:有关珀尔修斯前半部分的英雄传奇故事确实地以螺旋形壁画的方式展现出来;他后半部分的生活作为前半部分的延续,表现了他如何在面对新美杜莎时再显英雄本色,最终羽化登仙,在内容上体现了一种与叙述活动相应的上升运动。在这篇故事将近尾声的时候,珀尔修斯问美杜莎:“柏勒罗丰兄弟的情形如何?”美杜莎回答道:“那可是另一个故事了”(第129页)。这为小说的最后一篇故事“柏勒罗丰篇”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小说中最长的一篇故事。
巴思在“柏勒罗丰篇”中进一步演绎着前两篇故事中的叙述样式。故事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对“珀尔修斯篇”中的叙述形式的戏仿(parody)。珀尔修斯以星座的形式在天上讲故事,柏勒罗丰[②d]则以漂浮在马里兰州沼泽地的一堆书信的形式直接对读者进行叙述。象珀尔修斯的故事一样,柏勒罗丰的故事也是对两个女人的双重叙述,这两个女人分别是他那来自亚马逊女人国的情妇梅勒妮普和他的妻子菲罗诺厄(Philonoe)。变成了书信的柏勒罗丰向读者叙述他是如何把他的生活故事讲给梅勒妮普听的,而这又促使他进一步回忆他先前给妻子菲罗诺厄讲的故事。在这部分的故事中,柏勒罗丰象珀尔修斯一样完成了他的英雄使命(珀尔修斯割下了蛇发女怪美杜莎的头,柏勒罗丰则杀死了吐火女怪客迈拉),人到中年,开始感到生活无聊乏味,于是试图重振他年轻时的辉煌。然而,他最终未能象珀尔修斯那样成为一个永恒的英雄,而是坠入沼泽,变成了一堆混乱的书页。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不能象珀尔修斯那样更新和超越自己原先的生活。他试图重创英雄业绩的过程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英雄生活的模仿,也就是说,他是在固有的神话英雄行为样板上按图索骥,进行不折不扣的模仿,这使他成了“一个神话英雄的地地道道的摹本”(第297页)。而他也的确是个“地地道道的摹本”。故事快结尾时道出了柏勒罗丰的真实面目:他实际上是半神半人柏勒鲁斯的同胞兄弟德里亚底斯,在一次意外中杀死了柏勒鲁斯,之后便把自己当作了柏勒鲁斯,而“柏勒罗丰”则是他以这一角色自居时用的另一个名字。
柏勒罗丰最终变成了有关他的故事的书面文字,他的这一命运与他的一位名叫波吕伊多斯的导师有关。这是一个会变形的魔术师一般的角色,尤其擅长于将自己变成各种文献。这篇故事的开头提到吕喀亚国王柏勒罗丰在其40岁生日的傍晚发现了一部名为“珀尔修斯篇”的希腊神话小说漂浮于他王宫附近的沼泽上,到后来,故事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其实乃为波吕伊多斯所变(“珀尔修斯篇”的真正作者自然是小说家巴思,如同“敦妮亚佐德篇”中的“魔仆”,我们在波吕伊多斯这一虚构的人物身上再一次看到了巴思的影子,而巴思附身于这一角色并非仅仅为了制造一种奇幻诡异的效果,而且还别有一番寓意,这点将在后文中谈到)。波吕伊多斯变身为“珀尔修斯篇”,本意是为了指导柏勒罗丰在其40岁人生危机关头如何象珀尔修斯那样再度恢复英雄人生的辉煌,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柏勒罗丰只是在回顾珀尔修斯的英雄生活中变成了一个刻板的模仿者,一个丧失了个性的假珀尔修斯,最终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记载他自己故事的文字。在柏勒罗丰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出现的扑朔迷离的叙述,实际上都是由于波吕伊多斯变幻无常的易形所致。大约在故事进行到一半的地方,柏勒罗丰曾猜测故事的作者是波吕伊多斯。随着故事的叙述情形变得愈加复杂,柏勒罗半丰甚至都搞不清是谁在写故事了。他一边苦费心机地讲故事一边抱怨说:“我想我是中了邪。我满脑子的各种声音,全是我的,又都不是我;我弄不清是谁在说话”(第147页)。但他终于意识到“波吕伊多斯就是这故事”(第237页)。在“敦妮亚佐德篇”中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的那种源于同心的叙述纠葛在这篇故事中又出现了,其最终的昭揭发生于故事结尾波吕伊多斯与柏勒罗丰之间的一场对话:前者告诉后者他将“由这场会谈把我自己变成你在‘柏勒罗丰篇’之中的形式”(第307页);亦即,波吕伊多斯作为柏勒罗丰作为其故事的文字。
通过以上对三篇故事中叙述特点的分别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从第一篇故事到第三篇故事,叙述形式演变得愈来愈复杂,故事内容也随之变得越来越荒诞离奇。那么,这三篇故事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换言之,它们是如何有机地组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呢?仅仅指出它们在叙述样式上的承续性尚不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因而也不足以显现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因此,有必要继续探索故事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发掘出贯穿它们的题旨,进而凸现这部小说叙述形式的本质意义。
不妨先提一提故事之间在一些表面内容上的联系。在“敦妮亚佐德篇”中,“魔仆”告诉山鲁佐德,他设想了一个由三个中篇构成的故事系列,“并且已经完成了其中两篇的构思”(第28页),它们“和神话英雄有关,一真一假”(第28页)。另外,在“柏勒罗丰篇”中提到,柏勒罗丰的情妇梅勒妮普来自一个叫亚马逊的女人国,而这一女人国在第一篇故事中便已有了交待,即山鲁亚尔之弟沙·扎曼以恻隐之心安置他救下的女人的秘密居住地。“珀尔修斯篇”与“柏勒罗丰篇”在故事内容上则具有更明显的联系:珀尔修斯和柏勒罗丰都已完成了他们的英雄任务,俩人都为中年人生危机所困,都试图再现他们年轻时代的辉煌;不同的是,珀尔修斯最终成了一个真正的神话英雄而柏勒罗丰则以失败告终。波吕伊多斯在他变作的讲义文卷上解释了“柏勒罗丰篇”的来由:“我想象出了一个取材于神话的滑稽中篇故事,也许可以作为‘珀尔修斯篇’的姊妹篇”(第202页)。此外,我们还得知,柏勒罗丰在其40岁生日读到的故事即是“珀尔修斯篇”。然而,这些情节上的相互关涉所构成的联系依然只是松散的,非实质性的。真正重要的联系必须在主题上和结构上探求。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感觉到的那样,这部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风格殊为不同,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类反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流派性小说(批评界通常将这类小说笼统地归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名下),这类小说作为一种具有先锋性的文学实践往往与当时的理论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巴思的这部小说也不例外,因为一方面,巴思本人极其热衷于这类实验小说创作的理论思索,他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穷尽已竭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的文章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自反”特征(selfreflexiveness)也使这部作品与巴思的创作思想形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因此,我们可以将有关的理论背景以及巴思本人的创作思想看作解读这部小说的“副文本”(sub-text),从而把握贯穿作品的题旨。
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在他一篇题为“十字路口的小说家”(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的论文中对一种以迥异于传统小说面目出现的小说作了这样的评述:
……这种小说带着读者(这种读者只是天真地希望作者告诉他去相信什么)经历这样一个集市:这个集市充满了种种幻象、叙述、哈哈镜和常常冷不防在他脚下猝然打开的活板陷门,最终留给读者的不是任何简单而令人心安的启示,而是一个关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悖论。[①e]
洛奇称这种小说为“问题小说”(problematic novel)。对此他继续解释说:
事实上,赋予“问题小说”特征的是,作家对写作本身问题的思考所作的传达(这种思考可以是幽默的,也可以是严肃之至的),即通过在叙述中直接表现小说写作提出的美学和哲学问题,使读者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②e]
洛奇的这些话用来注释巴思的《吐火女怪客迈拉》是颇为恰如其分的,因为这部小说同样表达了一种对小说写作问题的敏锐意识,不仅如此,小说还展现了如何解决身处困境的当代小说家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关于当代小说家的困境,巴思在其短篇小说集《迷失在游艺馆》(Lost in the Funhouse)中一个题为“扉页”(Title)的短篇里作过这样一种形象的描述:“一切都被说过了,被反反复复地说过,我象你一样对此感到厌烦,没的可说了,那就说没的可说的。……实际情形是,叙述者已将自己叙述进了一个死角。”[③e]这种情形在巴思那篇著名的“穷尽已竭的文学”一文中被概括为一种观念,即“穷尽了可能性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他解释道:
我所说的“穷尽已竭”并非指诸如体力、道德等方面的衰竭,或是智力上的颓废,而是说明某些形式已被用完,某些可能性已被穷尽——完全不必因此而绝望。[④e]
巴思对其破折号后面的话所作的具体回答是:
一个艺术家可以以悖而不谬的方式将我们这个时代感受到的终极性的问题变成他创作的素材和手段——之所以说是悖而不谬,是因为这样做他超越了本为无法逾越的绝境……[①f]
这一想法似乎成了巴思在一个时期中的专注之念,在短篇小说“扉页”中就出现过类似的说法,故事中的叙述者提出,作为最后一种可能性,艺术家也许可以“使终极转而与自身为敌,从而推陈出新,化谬为信,而从本质上说,推陈出新又是不可能的。”[②f]对于小说艺术家巴思来说,他所感受到的终极性问题主要是他对于叙述艺术中可能性被穷尽的认识,而他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便是将这种“穷尽”同时用作题材和技巧来创造出别出心裁的作品。
在《吐火女怪客迈拉》中,“穷尽”这一问题是由写作危机来表现的,正是这一意象将小说中的三个中篇故事有机地联系了起来。[③f]“敦妮亚佐德篇”中的“魔仆”抱怨说他正面临写作危机,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写作该走什么样的方向。他坦白说:“我已停止阅读和写作,我已经不清楚我是谁;我的名字只是一堆字母;整个文学也是如此:成串成串的字母和一行行空白,就象我已无法破解的密码……”(第10—11页)“魔仆”或者说巴思的处境就是敦妮亚佐德的处境:她听过了所有山鲁佐德讲的故事;如果说山鲁佐德的处境是“要么讲故事要么被处死”,那么敦妮亚佐德的处境则更糟,因为她已没有新的故事可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巴思把敦妮亚佐德看作是身处困境的现代小说家的形象,而他自己也认同这一形象。对于敦妮亚佐德,同时也是对于巴思来说,唯一的对策便是讲关于故事的故事。“魔仆”最终摆脱了写作危机,因为他发现他可以向未来的山鲁佐德提供她过去的故事,也就是说,通过往回走而继续前进——往回走是一个过程,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延续,同时也就意味着前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魔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他从山鲁佐德那儿得到的启发是,写作的钥匙/秘诀就是写:
无论她找到的是什么样的方式——不管它是魔咒还是一个本身带答案的魔幻故事,或者随便一个魔幻什么——归根到底是我们正在读的这个故事里的一个个具体字词……而这些字词是由字母组成的:这20多个弯弯扭扭的符号又可以用这支笔来画。这就是钥匙……而且也是宝库,只要我们掌握它!全在于一个“仿佛”——仿佛宝库的钥匙就是宝库。(第8页)
作为小说家,巴思的问题是面临着文学可能性被穷尽的情形,因而,对于他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就是把这个问题当作题材写出来,以此超越这个问题。这就是他用以写作另外两篇故事的策略。
在“珀尔修斯篇”和“柏勒罗丰篇”,写作危机是以另一种形式来体现的,即珀尔修斯和柏勒罗丰都陷于其中的中年危机。珀尔修斯在其40岁时发现自己的婚姻生活已经搁浅,体重超了20公斤,开始觉得自己正在变得僵化。正如他自己说的:“没救了,想不起来曾经在哪儿或是往哪儿去,完全搞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了,开始产生错觉,……”(第60页)。他的问题在于其过度的自我意识,在故事中是通过他的“阳萎”来象征的。卡莉克莎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的担心过多……你越是把性看作一种表演,你就越会在开演时怯场”(第70页)。但是,通过卡莉克莎的壁画,珀尔修斯从艺术中获得了对生活的认识,因此而恢复了性功能(创造力的象征)。当他面对既能毁灭生命又能使人重返青春的新美杜莎时,他终于甘冒风险,揭开她的面沙,吻她,并且正视她的眼睛。这时候,珀尔修斯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自己的真正形象:“一个还算健康,不再英勇的凡人,后面还有一半多的生活,他已不如20岁时那么强壮有力和心高气傲,但仍不失精力旺盛”(第132页)。与此同时,他又看到自己被不可思议地变成了真正的神话英雄。珀尔修斯的成功在于他承认自己已不再是英雄,因而超越了自己。他敢于改变既定的英雄模式,表现自己的个性,这使他再次将自己创造为一个真正的英雄。珀尔修斯的策略是“魔仆”在“敦妮亚佐德篇”中所说的那种:“要知道去哪儿就得搞清楚我现在在哪儿,于是又得回顾我原先在哪儿——我们原先都在哪儿”(第10页)。珀尔修斯也以自己的语言表述了同样的意思:“我是想通过回顾自己被记载下来的过去来带着理解超越我现在的所谓段落,在这样的方向下进而平静地走向未来句子”(第81页)。这番话无疑是在公开地谈论写作危机的问题。作为故事叙述者,珀尔修斯以其恢复的创造力终于讲了一个好故事。巴思也是如此。
象珀尔修斯一样,柏勒罗丰也为中年生活的乏味无聊困扰。在40岁生日的晚上,他承认自己正在走下坡路,他的“生活是一个失败”(第138页)。正如在上一篇故事中写作危机由珀尔修斯的“阳萎”来象征,这里的比喻是柏勒罗丰的沉滞不前。具体地说,他的问题是难以驾驭飞马珀格索斯飞上天空。写作“柏勒罗丰篇”使巴思得以用一个更长的篇幅来表现写作危机这一主题以及展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巴思在这里的奇巧构思是写关于一个假神话英雄的失败生活的故事,并且把这故事本身也写成一个失败的故事。巴思在故事中借柏勒罗丰之口说:
讲故事不是我的拿手戏……我的故事情节缺乏有意义的阶段性起伏,而只是自我盘缠,就象一个螺壳或是赫尔墨斯杖上的蛇:离题、退缩、迟疑、哼哼唧唧,等等、衰竭、死亡。(第196页)
这里同样是“珀尔修斯篇”中的那种悖论:在承认失败的同时超越了失败。在确立柏勒罗丰的失败与写作危机之间的类比关系后,巴思按照马里兰州沼泽的潮涨潮落的样式来记述柏勒罗丰的生活的失败,以此作为情节和结构对其主题进行戏剧化的处理。如果状写失败艺术的过程超越失败,那么就需要一种恰当的风格来表现这一过程,以充分体现其中的悖论性。这种风格可用巴思推崇倍至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Borges)的话来表述:“它蓄意穷尽(或试图穷尽)种种可能的方式,使其自身近乎滑稽可笑的地步。”[①g]这正是巴思在“柏勒罗丰篇”中采用的风格,其叙述方式之繁复如同迷宫一般。巴思让故事叙述者柏勒罗丰以作者涉入的方式解释道:
我并非喜欢晦涩、难解,如果不能给人以启悟,我希望至少可以娱人。但问题是我们已经见过一个错综复杂得几近不可理喻的体系:就象从飞到最高点的飞马珀格索斯上俯瞰到的迷离曲折的沼泽一样,其形态间或可辨,我们看到水是怎么流的以及它何以那样流,水上浮载着什么以及它们漂向何方。而其余的时候我们则是陷于迷津之中。船在继续漂流,但其航线显得任意而荒谬。(第147页)
这种陷于迷津之中的感受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是难以避免的,它产生于这样一种觉察,那就是我们的思维过程已经变得自觉化和历史化。正如巴思在其《迷失在游艺馆》中的一个故事里说过的那样:“我们不能硬充天真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重蹈故迹,除非是以再次循环的方式。”[②g]巴思在“柏勒罗丰篇”中以迷宫式的叙述风格实践了这一思想。实际上,整个这篇故事就是围绕“迷宫”这一支配性意象结构而成的。巴思之所以对这一意象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它同时也体现了他所关注的“穷尽的可能性”这一主题:
迷宫毕竟是这样一种地方,在理想的意义上说,它体现了所有的选择可能性,而在你到达它的中心之前——除去一些特别之道,譬如提修斯[③g]之径——你必须穷尽所有这些可能性。[④g]
因此,可以这样说,巴思本无意将“柏勒罗丰篇”写成一篇看似成功的故事,他的用心所在是通过写这篇故事来礼赞“穷尽”这一过程本身,亦即礼赞写作本身,再延伸地讲,是对创造力的赞美,因为写作活动的持续是创造力不衰的象征。这就是关于巴思的悖论:写作一个失败的故事却孕育了故事的生命;展现失败的过程变成了失败自我对抗的过程,从而超越了失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思实现了他关于将“感受到的终极性问题”变成“他创作的素材和手段”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敦妮亚佐德篇”中反复出现的那句话:“宝库的钥匙就是宝库。”结果,“柏勒罗丰篇”成了小说中最长的一篇故事。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小说中各故事篇幅上的安排。“珀尔修斯篇”大约是“敦妮亚佐德篇”的两倍长度,“柏勒罗丰篇”则是前两篇故事长度之和。这种篇幅上的扩展同小说中重复出现的“螺旋形”意象保持了统一。扩展既是主题上的,也是结构上的。
由于“柏勒罗丰篇”代表了小说家对“穷尽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最高意识层次,这就涉及到有关小说家的自我身份定义问题。作为故事叙述者,柏勒罗丰被这一问题纠缠困扰,怀疑波吕伊多斯是故事的作者,而波吕伊多斯是个变形人物,他的身份的不断变化暗示了巴思本人对艺术家自我身份定义的态度。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它指向艺术家与其传统之间的关系。作为当代作家,巴思自觉地意识到,艺术家无法摆脱传统但也不能局限于传统,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再现传统,在回归过程中注入现代性。巴思同意博尔赫斯的观点,那就是当今的作家谁也不能声称自己文学上的原创性;所有作家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注解以往文学原型。因此,他承认他的所有小说都是“由一个模仿‘作者’这一角色的作者写的模仿‘小说’这一形式的小说”。[①h]巴思在“穷尽已竭的文学”一文中表达的这一思想在“柏勒罗丰篇”中得到了回应。当柏勒罗丰怀疑自己的作者身份时,他便作出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变形的波吕伊多斯是他的故事的作者,那么这一作者的身份就无法确定,他可以是
譬如说,赫西奥德、(Hesiod),或是荷马(Homer),希吉诺斯(Hyginus),奥维德(Ovid),品达(Pindar),普鲁塔克(Plutarch),《伊利亚特》的注释者,罗伯特·格瑞夫斯(Robert Graves),伊迪斯·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拉格兰勋爵(Lord Raglan),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珀尔修斯篇”的作者,模仿那个作者的某个人。(第237页)
在《吐火女怪客迈拉》中,巴思创造了象“魔仆”和波吕伊多斯这样的人物,把他们视为与文学传统进行交流的现代艺术家的形象,他(艺术家)跨越时空的界限与古典文学中的人物(山鲁佐德和柏勒罗丰)交流,并且向他们提供他从文学宝库中借来的他们自己的故事,让他们利用这一资源来传达他们自己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表现了传统但同时又超越了传统。
关于“穷尽的可能性”这一思想不仅仅在主题上而且也在结构上联系着小说的三篇故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三篇故事中都采用了“框构故事”的结构,而巴思对这种形式的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无穷回归的一种文学性表现,”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结构是“穷尽,或试图穷尽可能性——在这里是文学上的可能性——的一个意象”。[②h]实际上,这三篇故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框构故事”系列。“敦妮亚佐德篇”的作者说:“敦妮亚佐德的故事是从中间开始的;在我的故事的中间,我现在无法结束它——但它一定是结束在所有美好的早晨到来前的那个夜晚……”(第5页)。这种悬而不定的语气把我们带入了下一个故事。“珀尔修斯篇”以“晚上好”开始,以“晚安”结束,但那种悬而不定的口气仍然存在:变成了天上星座的珀尔修斯和美杜莎无法得知他们在“凡世间的生活是正在他们寿限之外继续着还是早已结束——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在一起还是分开,喜剧性的还是悲剧性的,美的还是丑的。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无法知道……”(第133页)。因此还得有另外一些夜晚来讲这个故事,于是便有了柏勒罗丰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以“晚安”开始的,它的末尾是这样一个句子:“这不是‘柏勒罗丰篇’,这是 ”(第308页)。这里的空白使我们想起“魔仆”在第一篇故事中说过的话:他将以“敦妮亚佐德篇”来结束他的三部曲。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篇故事在次序上的安排再一次体现了巴思反向框构的手法,这种反向框构的结构代表着一种需不断返回开端的穷尽形式。与这种结构样式相对应的是巴思对原初文学之源的回归。
在《吐火女怪客迈拉》中,巴思主要是借古希腊神话作为故事素材的,正如写有关写作危机的问题超越了这一问题,重写原有神话故事的过程——把旧故事变成新故事——是重新焕发创造力的过程,因此也超越了关于“穷尽的可能性”的问题。但巴思运用神话素材还有另一番意义,这里面反映着他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态度。在由波吕伊多斯变成的讲义文卷中,巴思解释了他对神话的兴趣:
(因为)神话本身……是我们平常心理经验的诗化精萃,因而总是暗示日常现实,而现实小说却总是暗示神话原型,因此写现实小说——不管这样的小说在其它一些方面多么值得称赞——在我看来是在神话之棒上误执一端。还是直接在原型上做文章为好。(第200页)
巴思的这段话里有这样一个意思:神话,或者说艺术,和日常现实有关但却终究不能完全描摹或反映现实。话中出现的“精萃”,“原型”这样的字眼暗示了艺术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弥合之隙。由是,巴思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
调和艺术与真实事物之间差异的一种不同办法,就是肯定艺术的虚假成分(不管怎样你也无法消除这种成分),并且把手段技巧当作你的目的的一部分,而不是用许多文学的高低音立体声音箱来求获至善至美的“高传真”。这就是我的办法。[①i]
巴思的这种见解可以说为他创作的那种神话性虚构小说提供了合理性解释。他还在另一个场合对这一思想作过进一步的阐释:这是个古老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它和古希腊戏剧一样古老,那里有这样的调侃:这是一出戏,你们是在看戏。莎士比亚惯于此道:“整个世界是一个戏台。”如此等等。《暴风雨》是一个典型例子:魔术师一方面在暴露幻象的本质而另一方面却又维持着幻象……这是一种表达某类情形的方式。[②i]
在《吐火女怪客迈拉》中,巴思通过一个名叫杰洛姆·勃瑞的作家人物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小说的真相是事实即幻想;虚构的故事是世界的原型”(第244页)。这句具有悖论意味的话反映了巴思关于小说本质的美学观,也可以说是对他为什么要利用神话原型来创作他自己的故事而非描摹现实世界所作的注解。巴思运用神话素材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如“Chimera”一词所意味的幻象世界,即虚构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以艺术本身为现实而非表现现实世界的现实。也许在巴思看来,艺术与其模仿现实,不知模仿自身,因为一方面,日常现实不可能被完全而确切地描摹,另一方面,艺术在对现实的模仿中丧失了其自足性;而艺术模仿其自身则保持了同律性,而且这种模仿具有双向的交换性,如同镜子照镜子——一方面互为反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模仿的结果依然是镜子,或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巴思的《吐火女怪客迈拉》是关于艺术的艺术,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叙述艺术/小说形式的小说。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推测,巴思在创作《吐火女怪客迈拉》之前曾经历过写作危机的痛苦,就象“魔仆”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作家,停止写作便等于死亡——艺术生命的死亡。要么接受这种死亡,要么继续写作,巴思选择了后者。而他的办法事实上又是合乎逻辑的,那就是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心理历程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穷尽已竭的文学可能性”这一终极性问题上,巴思以悖论的思维同时获得了创作的题材和方式。《吐火女怪客迈拉》是融智性洞察与艺术想象力为一体的产物。不论人们从什么样的小说观念出发来评说这部作品,以美学角度看,它的确是一部富于启迪性的作品,在这部小说出版7年以后,巴思发表了一篇名为“重新充实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1979),如果我们把这篇文章看作是巴思自“穷尽已竭的文学”以来的思索轨迹的延伸,那么《吐火女怪客迈拉》也许可以算作是巴思自己的“重新充实的文学”的开始。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上说,巴思是一位生活在焦虑时代的小说家,他总是在探究叙述的本质和虚构的意味,以求恢复小说的活力和意义。”[①j]以这种眼光来看《吐火女怪客迈拉》,我们便能以钦佩之心来欣赏这部“狰狞的小说”,体味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
注释:
[①a] Harold Farwell,"John Barth's Tenuous Affirmation:′The Absurd,Unending Possibilily of Love,″in Critical Essays on John Barth,ed.Joseph J.Waldmeir(Boston,Massachusetts:G.K.Hall & Co,1980),p.55.
[②a] 《吐火女怪客迈拉》中的三个中篇故事的标题分别为:“Dunyazadiad”、“Perseid”和“Bellerophoniad”,这种标题形式均系模仿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
[①b] John Barth,Chimera(New York:Random House,1972),p.308。此后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均据此版本,以页码注于本文内。
[②b] “框构故事”总体上仍为一个故事,其中讲述一个或几个小故事。除《一千零一夜》外,其它例子如有关500则古印度民间传说的《本生记》和流行于中世纪的《罗马七圣》,前者以佛教的伦理教义为框架,后者描述一个王子被判处死刑,他的拥护者(七圣)每天讲一则新故事来拖延执行他的死刑。
[①c] John Barth,"The Ocean of Story"in Directions in Literary Criticism,ed.Stanley Weintraub and Philip Young(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1973),pp.2-3。
[②c] Cynthia Davis,"The Key to the Treasure:Narrative Movements and Effects in Chimera"in Critical Essays on John Barth,p.218.
[③c] 珀尔修斯(Perseus)原系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杀死了蛇发女怪美杜莎,并从海怪手中救出了安德洛墨达,娶为妻子。详细故事可参阅斯威布所著《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第55—60页。
[①d] David Morrell,John Barth:An Introduction(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The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1973),p.146.
[②d] 柏勒罗丰(Bellerophon)原系希腊神话中骑飞马珀格索斯(Pegasus)杀死吐火女怪客迈拉的英雄。参阅《希腊的神话降传说》第196—199页。
[①e] David Lodge,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1),p.22.
[②e] 同上,第24页。
[③e] John Barth,Lost in the Funhouse(New York:Bantam,1969),P.108.
[④e] 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1967)in The Novel Today(Fontana Press,1990),ed.Malcolm Bradbury,p.71.
[①f]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in The Novetl Today,p.79.
[②f] Lost in the Funhouse,p.106.
[③f] Jerry Powell,"John Barth's Chimera:A Creative Response to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in Critique,Vol.18(1976),p.72.
[①g]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in The Novel Today,p.82.
[②g] Lost in the Funhouse,p.174.
[③g] 提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国王和著名英雄,他的最大功绩是在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进入克里特迷宫,杀死了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罗斯。
[④g]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in The Novel Today,p.84.
[①h]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in The Novel Today,p.80.
[②h] 同上,第82页。
[①i] Gerhard Joseph,John Barth(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8.
[②i] New American Review.No.15(New York:Sin and Schuster,1972),p.143.
[①j] Richard Rutland and Malcolm Bradbury,From Puritanism to Postmodernis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1),p.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