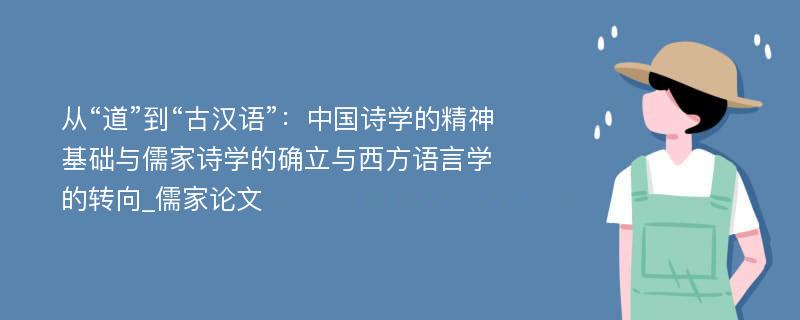
从道不可言到文言:中国诗学的精神奠基——兼及儒家诗学的确立与西方语言学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儒家论文,语言学论文,文言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诗学的中心观念应是孔子的文言说。孔子标举文言,扭转当时“道不可言”的思想潮流,继而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主张,成为《文心雕龙》以文言为天心之心的思想宗旨,为中国诗学精神奠基。孔子的文言说,与西方当代的“语言转向”并不相同,它意在建立以道德教化为主的、有德有言的诗学模式,而不仅是对形而上学的“道”的思维方式的反叛。
关键词 中国诗学 儒家诗学 西方语言学 文言 言辞美学
公元6世纪初成书的《文心雕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完备建立的标志,但是,从文艺思想的发展角度看《文心雕龙》中《原道》及贯通全书的中心观念,却来自早它1000年左右的孔子的文言理论,如果以主要思想观念的确立作为理论体系的确立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最早的,也是基本的构架创立时代,应当向前推移1000年,定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孔子删定六经及《论语》成书前后。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孔子的文言理论造成了当时思维模式的转折,占居主导地位;老庄的道不可言说思想遭到排斥后,沉积澄清,成为道家的美学精神,屈居其下,与儒家诗学及后来的佛家思想,共同制约着中国古代文论的长期发展。文学理论作为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构成部分,代表着民族精神的进展,这一转折也必然有精神现象的意义,恩格斯在论及精神现象学时,曾谈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诸阶段的缩影”[①a]。考察这一转折阶段的历史,自然也会对把握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和意识嬗变的总体形态有所裨益。
1
春秋时期之前,中国诗学已经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念,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其一,认为文学是人类自身活动与要求的产物,包括人的思想、情志、心理、语言、娱乐、劳作、交往等,因此,文学具有本体与主体(在先民的意识中,这两者的界限有时没有严格区分)的特性。这类观念中最著名的是《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它被称为中国文论的“开山纲领”(朱自清语)。此外,还有《吕氏春秋》中的“适音”说。《吕氏春秋》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但书中反映的观念却可能较早,如“凡音者产于人心者也”。其二,主张文学来源于人类主体之外,甚至超自然存在,属于更高层次的存在即道,文学是道的外化和显现。这类观点至少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诗经》中“德言”说,是一种堪与诗言志相匹敌的古老观念,它在《诗经》中屡见。如:《日月》“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谷风》“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有女同车》“彼姜孟姜,德言不忘”;《狼跋》“公孙硕肤,德言不瑕”;《隰桑》“既见君子,德言孔胶”;《假乐》“威仪抑抑,德音秩秩”等。以上用法,德言与德音互见,古字中,音与言同源异流,德音亦即德言[①b]。郑笺把德言释为“先王道德之教”,显然是汉儒说诗的迂腐见解,宋严粲《诗缉》中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说它是言语、教令和声名。虽然有的地方仍可存疑,但总体来说已经清晰,诗为德言,指道德之音声,已经超越世俗的王教,含有天道与圣贤之道的显现意义。《左传》中也有德音说的影响,如《昭公十二年传》及《文公七年》。第二种则是《周易》中由道而象,而言的思维路线。《说卦》“神也者而为言者也。”《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以上两大类观念各有特点,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类以诗言志为代表,经验意识色彩浓郁,以对文学本体的直观把握为主,感性特征突出。第二类以德言说为代表,德言亦即道言,从人类精神现象角度来观察,有形而上的认识特性。这两类观念之并存,犹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Imitation of nature)和柏拉图的艺术观互相补充,共同发展。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与一个“实体的”和“正在形成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世界相联系。柏拉图则认为艺术与一个理念的,纯粹存在的世界(World of ideal,absolute"Being")相关[②b],可见在人类精神发展初期,意识所构成的形态有超越民族性的一面。
然而对最初的经验意识的批判是不可避免的,黑格尔把这种批判和进步的不同阶段称为达到新的“立足点”。认识“个体却又有权要求科学至少给他提供达到这种立足点所用的梯子”[③b]。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勃兴为先民们提供了这样的梯子,使他们进到理性思维的新立足点,重新审视前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了根本的转折。这一转折开始于老子,在他之后是庄子,以道与言的关系为中心,阐发了道不可言的思想,对德言论等观念予以否定。老子和庄子学说有不同之处,但基本精神是一贯的,他们共同体现一种玄思的、形而上的思索。其主要观念如下:
其一,崇尚自然天道,强调道的不可显现,不可传达,不可认识的特性。老子以道为万物之本,万物皆生于道。“道冲而用之或有盈,渊合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庄子也说“道生天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庄子·渔父》)。他们的天道冲淡高远,与人道相阻隔,因此无法把握。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形无名,万物之宗”。庄子论道曰:“渊乎其不测也”(《庄子·天运》),“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这种不可知的认识论,倒过来则必有无法显现的神秘本体性。否认道可以外化为人们接受的形式,而形式则是艺术美的基本要素,因此也就否定了艺术美的存在。
其二,贵道贱言,以为道不可言。在老子《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中,如果把第二个道解释为言说,无疑就已经含有道不可言说的暗示。这种立场,若与老子的其他论述相联系,则可以看得更为清楚。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到庄子则发展为完全否定言说的地步。在言意之辨中,庄子竭力贬抑言说已经是人所皆知的了。他涉及道与言关系的一段话也很典型:“世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不可以言传也”。
其三,弃绝音象,否定文章之美。六经中的象、音、声、文章都与言联系密切,也与文学有内在的协同关系,都有道的显现媒介和形式的意义。这些概念都被老庄所贬抑或淡化。老子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辨若讷”、“五色令人目盲”等说法中,都用了一种具体否定的方式。庄子说:“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庄子·骈拇》)。
老庄的道不可言说是有所为而发,他们议论的对象是六经中有关道与言的观念,特别是直接指向《易》中的取象,诗与《左传》中的德言(音)观念。而且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否定型的形而上学,对前人意识的否定固然有一定的砥砺作用。但是,这些观念本身要进入理论建构,更需要的则是肯定方向的延伸和深化。老庄道不可言思想在当时客观上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建设是有一定危害作用的,会造成基本观念的迷失和湮灭。幸而,孔子以文言说来挽救颓势,一举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基石。
2
孔子文言说主要由他的《论语》和经他删定的六经中的有关论述构成,这一学说的观点是鲜明的,统一的,它的重心也很突出,集中在道与言的关系,并使之系统化,成一家之说。
首先,孔子对六经中道的观念进行改造,变自然之道为人道。这当然是适应当时社会文化形势的需要。但不应当忽略,这种改造,从精神现象角度而言,具有从经验意识向精神观念的提升作用。这一改变,使道具有了可言的性质,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贡献。在《易经·系辞下》,孔子有针对性地反驳了圣人之意不可见的说法:“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道与德,对孔子来说,主要不是虚无的自然天道,而是人间道德伦理,特别是礼乐制度。这样使道的传达和显现成为可能,而外化的中间媒介便是言。由于言能传道,言代替了道的地位,居于思维的中心,言成为本质的存在。基本上实现了从道本位向言本位的转换。这一大趋势的扭转,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和中心观念。
其次,孔子标举文言,创立了以言辞为中心的美学观念。《左传》:“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言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中心观念。《说文》释文以“错画为文”,《广雅》认为“文,饰也”。《国语·晋语》有“文,文辞也”。《荀子·性恶》说“文谓言不随饰也”。可见文的本意及转意,从最初的依类象形,渐具修饰文辞的含义。而言的意义则比较清楚,《国语》“生民之音曰言。”“音声犹言语”(《诗经·凯风》)。言指话语,那么,孔子为《易》作《文言》,意图是否只在于修辞呢?孔颖达《周易正义》:“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门户邪?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作《文言》以开释之。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阮元说:“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铨释四道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阮元《研经室三集》卷2)。文言之义在于阐发乾坤大德,使难以显现的道德化为人间言辞。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孔子的论述中,或以文言,或单用文,或单用言,都与道德观念相联系,也都与他的礼乐制度、人伦教化密不可分。这种用法在《论语》中十分普遍,如孔子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无一不体现了道可以言的观念。
再次,孔子以诗为言之宗,主张不学诗无以言。很多人感到奇怪,孔子尤为推重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若是理解文言精神,则昭然若揭,因为孔子赞颂诗,目的在于肯定言,倡导《诗经》的德言意旨,扭转道不能言的观念。“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学诗关乎社稷大业,也是个人事业和家族的兴旺的保证:“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他对伯鱼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孔子从语言角度论诗,使很多人想起了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在其著作中说:“人安居在语言所构成的家园,思想者和诗人是这一家园的看门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说使存在开启,并成为语言,保存在语言之中”[①c]。应当说这种比较和联系并非没有道理,海德格尔把语言与存在相关联,如同孔子将言与礼乐并论,而且两人都以诗作为语言的具体形式,其中有着思维方式的相似,但从精神进化的历程看,这种相同既存在于不同层次,也存在于不同时期,如果没有与之相适的历史环境的联系考察,这种相同的意义是很有限的。
3
孔子文言说对中国文论的发展有极重大的影响。首先在于,它是对中国春秋以前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创造,它把中国文论的两类最初形态结合起来,提炼意识,创铸了新的精神概念。孔子文言本于《易》,“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子曰:“夫《易》……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但孔子又不限于易象之说。在《论语》的有关议论中,提出一系列以言来代表礼乐道德的观点,将言与诗书礼乐合一,合理吸收了《诗经》德言和《尚书》诗言志的现实性,造就了文言的主旨,自铸伟词,格耀千古,岂非始于仲尼。孔子对这种思想的创造,基础观念是天地人三才三道合一,但不可否认,其中略含远天道,迩人道,薄造化,厚人伦的儒家思想原则。这种思想基础必然导致人道显化的观念,在显化中,言辞上升为中心,彻底扭转道不可言的局面。而且,凸显言辞,也就是强调诗,不学诗无以言,如果以前只是简单地说诗言志,那么孔子就具体指出:“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如果先民只是抽象地谈到德言,那么是孔子首次以天地之文来喻道德之辞,这一番大改造终于造成了文言的宏旨。
更为重要的是,文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石。《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与儒家学说的真实联系历来为学界关注,特别是《原道》篇中的思维方式的来源,更是重要问题。加拿大梁燕城博士指出,《文心雕龙》中运用了《易传》开出的哲学思维方法[②c],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不应忽视,《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中都有两个源泉:一是《易》,另一个则是孔子文言。刘勰说得极明白:“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龙·原道》)。因为道心惟微,刘勰才以文言的言作为文心。易是孔子文言之本,文言又是《文心雕龙》之本,其间的层递关系就明确了。从思维的路线看,孔子文言的影响尤其显著,天地万象为道之文,人道又是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其中有一条:道——象——文(言辞)的主导思想。刘勰在《原道》篇末,犹恐中心不明,再次强调“《易》曰:鼓天下动者存乎辞”,“辞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与”。在《征圣》篇中,引用阐发孔子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说教,又引《易》“辨物正言,断辞则备”,更能看出与孔子确立言辞的中心地位,远天道,贵人言的观点一致。《宗经》篇中,概观五经,以扬子雕玉之喻为总结,“谓五经之含文也”,“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也以建立言辞的中心地位为指归。若对扬子《法言·寡见》中的“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作个小考证,可见出,扬雄此处的比喻与《论语·学而》中的一段话可以相互发明,“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把《卫风·淇澳》中的这个比喻应用到言诗中,启发了扬子把它用到典谟。刘勰有感于此,指出五经含文,为自己建言修辞服务,都是效法了孔子。
无须再指出,孔子文言说的确立,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石,也制约它几千年的演变。特别是文以载道的观念,始终环绕着道与言之间的关系而波动。当然,这里的道已主要不是指所谓天道,在文言说后,道的观念已经以人道为主。而人道之本,又存在于其辞,舍其辞,无法求其道,这个原理,韩愈说得最清楚:“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辞。”从言辞入手来求其道,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根深蒂固的原则,对此,持各种见解者很少异议了。而讨伐异己者,又都必以其言辞不文为理由,大张挞伐。这种演变的趋势中,分明可以看出文言的巨大作用,进入到一种精神现象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开端,不能不回溯到孔子文言说。
4
中西文化的汇通造成了一种形势:中国古代文论的精髓往往与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相映成趣,而且它们的演进阶段也常有中西古今的对应效应。于是就有各种比较诗学的发现:以道不可言说与西方逻各斯的言谈相对[①d];以孔子文言中的片言只语与海德格尔比附等等。特别容易使人迷惑的是哈贝马斯阐述的西方语言学转向(die linguistische wende)与孔子文言说确立所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方向转折,应如何看待呢?
哈贝马斯把西方人文科学的历史演变归纳为两次范式转换。第一次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与中世纪之交,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过渡;第二次是20世纪初,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经过此次转向,主客体关系即意识与世界的关系被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所代替。哈贝马斯这种粗线条的归纳大致划出了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变化轮廓,其中不少地方可以质疑,特别是断言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已超出意识与世界关系,更是证据不足。这里姑且不作进一步评说。
孔子文言说的出现,标志着道本体论的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复合型的语言论,在其中,道的本质与它的显现直接结合在一起。从道不可言过渡到道可以言,言辞十分圆滑,顺利地取代了道的中心地位。在这一意识的进化过程中,如果与西方意识的发现历史相参照,会发现,缺少一个重要的意识自我确立和自我扬弃的大环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所代表的意识自我确立与20世纪初的尼采哲学等所代表的意识自我解体,是西方主客体认识论的关键时期,这种确立和扬弃意识,在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升到峰颠,然后急剧坠落,走向解体。近年愈刮愈盛的语言哲学风,只是一种取代意识自我扬弃的企图和走向,结局如何,难以预料。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言,在实现转化中,并没有经历意识扬弃进程,这是福还是祸呢?
文言说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哲学,倒不如说是一种言辞美学(借用俄国学者M.巴赫金那本论集的名称: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творчества)。与西方人文科学的思维方式相比较,首先,它根本就没有绝对超验与经验的意识对立,没有声音与图像的对立,思维与对象的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它是另一种文化的声音,文言的产生基于对言、意、象三者离异的克服,这种克服的途径是一种融合性的。在当代思想建构中,巴赫金的思想出发点是新康德主义理想,即克服康德的二律背反的理想,巴赫金创造的方法是动力学式的对话理论,他用对话在壁垒森严的双方中间联络沟通,他的名言是“言辞(слово)……产生于对话”[①e]。文言的言辞并不是从对话中来的,但是它与对话言辞一样,有天人共享的权利,它是一种超对话的言辞,先验地具有了沟通意识与世界的能力。怎样才能具有这种言,这种既能言道,又能顺世的能力呢?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诗就是礼乐,也就是雅言,学诗就是经过人文教化,经过道德伦理的教育。文言的认识基础在诗书礼乐,在伦理层次,与西方语言哲学的根本宗旨相去甚远,双方没有共同的超越对象。
从思维模式看,语言哲学并未完全摆脱形而上学,不过像哈贝马斯所说,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文言同样具有反形而上学的特征,但它的出发点不同,它所反对的并不是抽象玄思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反对的是道不可言的结论。在它的转变中,也没自觉拒斥玄思的思维方式。那么,是什么使它具有了这种性质呢?思维方式被抽象地讨论本身就是被迫而为之,其实任何思维方式的进化都是精神历史的阶段性表现,促成这种进化的是具体的历史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黑格尔时,已经指出他具有历史感,但缺少具体历史内容的弊病。文言的思维转变,如我们上文所指出,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因素,即从天道向人道的转变,孔子有针对性地批评道不可言,对道的本义作了改变,删定了六经,制定礼乐,树立天地人三才的说法,是这种历史行为改变了思维方式,而不是相反。中国人向来是脚走路而不是用头走路,他们重视的是足下之道,而不是玄思的逻各斯。另外,如上所述,文言的历史内容也包括从六经遗产中承继原有观念,诗言志和德言的观念被重新熔铸,它们的意识也得到升华,在我看来,这种升华的过程,有别于西方的“具体否定”和扬弃的过程,而是用融汇、疏导的方式,这样所形成的思维模式转换,也是有承继性地、有节制地,但是仍然有实质性变化,有力度的转换。
西方语言学转向未必有实质性地突变,但西方学者都喜欢竭力突出这种转变。中国古代的文言转变带有实质性的历史内容改变,中国文化的精神却努力使它变得平滑圆顺。西方学者重视思维方式的形式改换,中国文化重视内在观念的嬗变,西方学者力图否定旧的思维形式之时,中国文化却默默地将旧日的理论涓流溶入自身的洪波巨澜。
其实任何平行的比较参照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内容,即使在思维方式转换这样的抽象问题中,精神的历史演进也是它的主要内容。人类精神的进化包括各民族精神的独特形态和共同的进化阶段特征,这两者又是互为辩证的,在共同阶段性中含有不同民族的特性,在不同民族特性中又含有共同的阶段性,这样必然具有中西古今的逻辑与历史的综合参照。从这种视角来看,文言与西方语言学转向,虽然都有共同的对本体论的冲决,对言辞中心的创建;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有各自精神发展的历史阶段特性。借用一个不完全相关的比喻,文言是中国人作为人类童年时期的思想,而西方语言转向是成人的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永远不能再回到童年时期,尽管如同古希腊神话这样的人类童年时代的创造“就某些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②e]。孔子文言说,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而言,亦应作如是说。
收稿日期:1996-11-20
注释:
①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
①b 参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8页;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b W.J.Bate,Criticism:The major texts.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70.P.41.
③b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
①c Heidegger:Brief ueber Humanismus.
②c 梁燕城:《后现代美学格局》,《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9页。
①d 参见《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2年英文版。
①e М·Еахтин,Слово в романе,вопросоилитературы эстетики,1975,стр.93.
②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