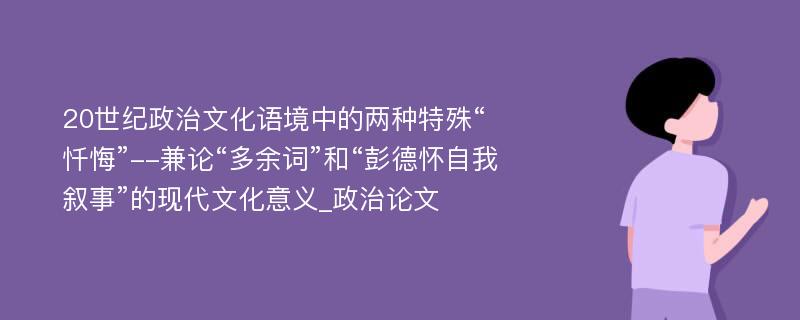
20世纪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两份特殊“自白”——再论《多余的话》与《彭德怀自述》的现代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语境论文,自述论文,两份论文,多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瞿秋白、彭德怀,这两位对上世纪革命史乃至整个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一生驰骋风云却又曾经备受争议,虽罹难于不同阵营的囹圄中,却有着相似的时代悲剧况味。透过世纪交替处的暮霭和晨曦再回望这两座业已蒙上岁月尘埃的历史雕像时,我们也许应该更多地瞩目他们生命末端所曾迸发出的眩目光华,而他们在囹圄中分别写下的《多余的话》与《彭德怀自述》既是其心灵轨迹的生动定格,也是留在20世纪茫茫星空中的人生弧线和巨大问号。
考察20世纪的这两份特殊“自白”,不能忽视其所处的现代中国特有的强势政治文化语境。因此,选择政治文化这一视角并继而从权威政治文化、求真文化信仰和个体文化性格三方面来审视这两份“自白”,其意义已经超出了这样的历史个案所提供的一种可能阐释而凸现其足以给后人警示的现代文化意义。
一、政治的罡风与命运的旋涡
如果比较一下同处在革命政治阵营的瞿秋白和彭德怀,我们会发现在出身、才能和性格这些迥然相异的表象下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而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还是他们身陷囹圄并以“自白”遗世的人生大结局。惟一不同的是,彭德怀现在已享有忠臣的哀荣,而瞿秋白身后还连绵着谤议。
无论是瞿秋白的锒铛入狱还是彭德怀的庐山遭谪,不但有某种偶然的因素,而且有众多必然因素共同铸成了这一悲剧结局。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极左思潮的巨大“无影手”和个人性格的致命“软肋”在这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对“自白”的剖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政治的罡风所生成的足以主宰人物命运的旋涡。
在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中,“多余”一词值得仔细玩味,其中那种欲说还休、欲休还说的感伤与执著成为无法拂去的主题情绪。传主就义时的壮怀激烈并不能自动刷新“自白”中低回哀婉的基调。他所声称的“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1](P320)是众多主题句中的一个。如果仅仅把这句话解读为政治失意时的激愤牢骚之语或理解为因迷惑敌人而故作掩人耳目的曲笔的说法都显得过于简单。联系瞿秋白从意气飞扬到局促困顿的短暂人生沉浮,不难发现,瞿秋白内心对作为革命理想的操作形态的政治有着难以逾越的陌生感和根深蒂固的拒斥感。但这并不意味着瞿秋白一直缺乏充沛的政治热情和过人的政治才干。事实上,无论是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的瞿秋白还是尔后为共产国际所倚重的“政治领袖”瞿秋白,是丝毫体会不到“历史的误会”或“力不胜任”的挫折感的,至于后来他在一系列政治风波和党内斗争所显示出的政治手腕和政治魄力大约是那些把瞿秋白想像成一个政治低能儿的研究者所忽视的。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瞿秋白从一个“学生领袖”角色到“政治领袖”角色的确未能完成圆满的转换,反而被从权力的飓风中心抛出,遗落到政治的边缘地带。个中原因如果仅仅用“欲罢不能的疲劳”、“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1](P324)来自我辩解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从“政治领袖”的认同到“政治动物”的认知,其中包含了主人公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罡风中所遭受的难以言说的精神内伤。从共产国际要瞿秋白“取独秀而代之”的“不合式”的尴尬,到体验清算李立三主义路线时所遭遇四面楚歌的境遇,再到红军西撤自己领受的作为多余的包袱扔给虎狼之口的厄运,所有这一切使瞿秋白切实领略到了汹涌在政治斗争旋涡底下难以逆料的寒流暗潮,彻底洞察了在冠冕堂皇的政治整肃背后的权威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冷酷面孔[2](P48-96)。
瞿秋白屡屡称“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要退出领导地位”,并又一再表白“一生没有什么朋友”、“渴望‘甜蜜的’休息”[1](P324-342)。这对一个曾经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先是抱着朝圣般热望而后陷入有如但丁游历地狱前的困惑的革命家而言,这些失望之语的弦外之音不可不察。当从理论形态的革命追随着进入操作形态的革命时,瞿秋白最先感受到的不适应便是政治中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主义的结构力学。从党内放逐到借刀谋杀的悲剧命运让瞿秋白深深体会到“政治动物”与“动物政治”的内在关联:“政治动物”从事的这种政治角力游戏其所信奉的潜在规则便是丛林法则与奴隶哲学。因此,从这些故意省略了大量潜台词和事件背景的表白中,不难体会到他对权威主义、对自我的放逐以及宗派主义对人性的漠视的反感乃至厌恶。
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彭德怀在上奏万言书时所秉持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以及是否预察到可能面临的危险。尽管我们不能判定作为卓越的军事谋略家同时又经历了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一系列政治风云变幻的彭德怀对当代政治的游戏规则和敏感凶险如孩童般的一无所知,然而从彭德怀的悲剧命运来看,他在政治生态环境中生存智慧和生存表现的确是“很不够格”的。如果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整肃就像猝然刮起的暴风骤雨已让他满含委屈,那么“七千人大会”对彭德怀的再批判就如从天而降的惊雷令他困惑悲愤。于是为他所获的阴谋篡党、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的弥天大罪作坚决的辩诉,声称如果发现事实确凿情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3](P245)。结果更落得罪行升级,横暴加身,最后含恨而殁。其实杨勇在庐山会议上揭发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发言却道出了彭德怀虽获罪而不自知的根源。“彭德怀有两大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大。”[4](P230)而这里的“忠”和“功”在他自己和别人(尤其是最高领袖)心目中的理解和分量恰恰是大相径庭的。它不仅没能成为彭德怀的护身符,反而成为他获罪的火药桶。在彭德怀看来,忠于党的领袖、忠诚党的事业是建立在忠实自己的理想基础上的一种水到渠成的统一;而在最高领袖看来,自己是党及其正确路线的化身,对最高领袖忠诚的情感应该与对尊崇真理选定正确路线的理性具有自明的高度统一。因此,在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说,政治、思想、情感是同一的东西,并当着彭德怀的面声称“我自己的理智与感情总是一致的”[4](P172)时,彭德怀仍固执称“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4](P183)。当“忠”心有二时,其“功”只不过成为这种离心倾向的倍增器。随着奇斯玛效应和政治围猎手法的娴熟运用,这位身经百战、屡建奇勋的军事家成了权力角力中的猎物和路线斗争的祭品。
其实,触碰政治游戏规则禁忌的举动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屡屡出现了。无论与毛泽东的两次“误会”,还是被毛泽东指称的两次“摇摆”,彭德怀既未意识到自己所处领袖政治“棋局”中的位置,也未能抓住及时而坚定地向权威传达认同和忠诚的时机。这对有着英雄情结和平等意识的农民之子来说,是一场灭顶之灾。
综观党内的路线斗争,对于各种主义和路线的清算总是缠绕着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结,这使得党内斗争较之对敌斗争常常别有一种惨烈冷酷的意味。话语权的专擅乃至硬性权力的占有成为思想裁断的前提。而在权力场中,当事人所拥有的实力和影响便成为政治博弈的对象和政治天平的砝码,并纳入到这种博弈所遵循的潜在规则和思维模式中,这时当事人的思想信仰、个人品质、行事动机如何便不再重要,即使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亦是不可能了。
二、世纪炼狱中的狂沙与真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瞿秋白、彭德怀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的血肉之躯是被党内的极左政治这架冷酷无情的巨大机器所毁灭的。难能可贵的是,当众多被倾轧的血肉之躯也变异成这架机器中的一个个齿轮时,瞿秋白、彭德怀仍然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来作悲剧性的抗争。诚然,瞿秋白、彭德怀都不是没有缺陷和弱点的至圣完人,但对真的信仰和执著却是这两位共产党人的共同特质,而这正是他们在任何炼狱的旋风和狂沙中仍能保持一个真纯的赤子之心的根本所在。被囚禁在国民党监狱里的瞿秋白本可以像无数舍生取义的共产党人一样,以一个纯净透明、热情慷慨的烈士肖像留在历史的扉页。但瞿秋白凭着对自我忠实、对历史诚实的勇气以及执著追求真理的浮士德精神,“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1](P319)。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洞比面对敌人枪口的黑洞更需要勇气和力量,因为这种会经受一个“士”告别最低荣誉的痛苦以及承担一个人丧失精神支柱的恐惧。
《多余的话》开篇即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为题记道出了“心忧”和“何求”这一直纠缠在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自我”。“心忧”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症候,他们从对个体生命生活境遇之忧扩展到对全体民族生存困境之忧,从而产生实现自我、救国救民的充沛热忱和宏大理想。这一求索充满了艰辛也收获着欣悦。瞿秋白就是其中优秀的一员。然而综览全篇,人们如同走进了一座弥漫着低沉、感伤、自弃和忏悔的心灵炼狱。
照理说,一个用主义武装的灵魂是自信而充实的。然而,瞿秋白却又称自己其实有着“真正的懦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因为他总希望有一个依靠[1](P336)。这便是他一直无法解开的“心忧”之结。这种因缺少“依靠”而“动摇”的“心忧”虽有悖于纯粹的党性,却正是一个未曾放弃独立思考和良知感悟的真实人性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其实这一倾向早在去“饿乡”的途中就显现了,他在怀着朝圣的心态前往赤都时,也不忘声称“遥远的未来如果能允许我国劳动者一胜利,也得先立条约:以他们在‘实际生活学校’中的成绩作预支‘胜利基金’的信用(credit)”[5](P73)。这种基于个体方式求索真理的心结与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深度浸淫,一开始就铸就了摇摆于“现实派”和“浪漫派”间的“多余人”性格。
“实练明察”的现实内力一旦仍留驻在一个革命实践家而不是一个革命鼓动家身上时,就常常会成为他施展政治手段的掣肘,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悲剧效应。像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清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时所表现出的调和主义和温情主义这种政治的“不坚定”和“不成熟”,其实正显示了瞿秋白对政治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然而他的个性和观念有许多仅属于良好愿望,既不尽符合政治的游戏规则,也损害了共产国际的不可冒犯的天威。既然违反了规则,那么被逐出这个圈子便是必然的了。后来他在上海与鲁迅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尽管比周扬他们更有业绩,但由于前者是自由出击派,后者是奉旨作战派,追求真理的竞争规则最后还是不敌争夺权力的垄断定律,最后连政治家的文人梦也破灭了。终于,瞿秋白意识到他所面临的其实是类似于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求真的自我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瞿秋白对真的追求体现了理性引导的特点,那么彭德怀对真的执著就显示了经验确证的色彩。它们对于权力意志和权威话语构成某种紧张关系。
彭德怀在党内以耿直刚烈著称,有“猛张飞”和“现代海瑞”之称,在对真的追求的基础上生发出对真理坚持的倔强以及对党的事业和领袖的忠诚。倔强中既有知错就改的勇气也有不惧压力的硬气;忠诚中兼备不一味盲从的独立品格和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尽管在对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和高饶集团的斗争中在政治战略和思想路线的认识上常常“见事迟”(而这种错误被毛泽东斥为“经验主义”),但就是在这种经验和事实的基石上建立起的忠诚是不可撼动的。彭德怀在狱中回忆他的一生时,似乎对他的“见事迟”并无太多自责,反而为自己作了这样有趣的辩护:“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6](P229)虽然彭德怀并不拒绝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然而他对经验事实的崇信有着农民般的执拗。这种执拗甚至让他忽视了在险象环生的政治权力场中个体生存应具备的机敏和智慧。由于不惮说出真话,而且采取直抒胸臆的、绝不设防的性情方式,因此在同僚和领袖的心目中有时留下“狂狷”和“犯上”的阴影。
1959年的纠“左”庐山会议在神闲气定的表面下翻卷着莫测风云:一方面,毛泽东的大跃进的宏大试验造成严重后果,最高领袖的权威极有可能受到挑战;另一方面,重臣大员们携带着各地的败绩和怨气,来追寻责任者和始作俑者。形格势禁,危机四伏。怀着“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彭德怀上书痛陈全国惊心动魄的现实危机。可他无暇顾及、也未曾预料的是,他的举动可能对庐山上的政治态势产生微妙的改变(至少在毛泽东眼里)。直到后来,突遭围猎式反击的彭德怀似乎意识到可能产生的难以逆料的政治震荡。从力避党遭分裂计,彭德怀第一次违心揽下了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责,但坚决拒绝泼在自己头上的所谓里通外国的污水。从软禁在吴家花园起到囚禁在北京西郊小院时,他始终坚信自己是无罪的,并通过各种方式申辩自己的清白和忠诚。如他将吴家花园大门的“教养局”改为“挂甲屯”,意即只承认“罢官”不承认“获罪”。他甚至放弃在“文革”前夕与毛泽东握手言和的机会,只是不愿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以示驯服,因为他能掂量出坚持真理与个人荣辱、党的整体利益与领袖个人威信孰轻孰重。
以耳闻目睹的党内极权对异己的整肃以及自己切身经历的触怒权威的苦涩体验,彭德怀不会不明白对真理和公正的执著需要付出多大政治代价。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实践了自己信念。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彭德怀这一文化性格的现代性,我们还可以发现,让真理挑战权威的朴素举动具有了政治伦理学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农民自身所固守的分殊主义价值观而具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的萌芽。
三、秀才与农民的革命之梦
瞿秋白不断声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并说是无产阶级意识在他内心里“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1](P331-336)。彭德怀则坚信他心中的“榜样”和“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6](P112)。在正统马列主义者心中他们的“党性”都不够纯洁,羼杂了与“党性”不够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的另一个“自我”。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坦称,他心目中有非无产阶级意识,这是一种毕生之力也未能祛除的“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和“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他对自己身上这些“异己分子”感到有些遗憾和困惑,但并未产生多少悔意。因而他把自己命名为“脆弱的二元人物”[1](P326)。
早在决然赴俄之前,他就有一种深深的隐忧,感到“心灵里清纯洁白的一点爱性,已经经过缠绵悱恻的一番锻炼。如今好像残秋垂柳,着了严霜,奄奄地没有什么深意了”[5](P14)。这就预示了无论今后在红色浪潮中卷入多深,他也难以捐弃心灵中真正属于自己的最后一块领地。而这块领地是与他青春岁月里一段伊甸园般的真实人生(有关“秋之白华”的校园师生的惊世恋情与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易妻情敌竟成金兰之交)是紧密相连的。这样,一个还没有从伊甸园里走出来的可爱的大男孩角色与一个中国政坛上纵横捭阖、吞吐乾坤的政治领袖角色之间的一脉相承(青春浪漫与政治激情)与致命冲突(个人性情与政治人格)就不难理解了。绅士的费尔泼剌和精神贵族倾向、中国式的士大夫的崇尚性情的遗风、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与个性自由、所谓市侩的世俗温情道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对政权暴力的拒斥,共同构成了瞿秋白二元性格中的一元。当深藏着这种底色的布尔什维克被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台中央,并将他的真性情扩展这座舞台,这时的瞿秋白便在每日体会悲剧况味的同时与日俱增地感受到角色的错位感和荒诞感。他把这称作“历史的误会”。
作为一个政治家,瞿秋白也许是不“高明”的。尽管在对敌战斗和党内斗争中他不乏“虎气”,但他缺乏一个“高明”政治家应有的纵横捭阖、通晓权变的“猴气”(注:毛泽东在自我估价时曾称自己性格中兼具“虎气”和“猴气”(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化》,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即使这“虎气”也需要所尊崇的信念来激发如虹的热情。然而,在处于分裂的二重人格的观照下,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在瞿秋白的心中逐渐出现了鸿沟,而且始终存在、无法弥合。他试图在这断裂的“鸿沟”重新寻找被遗落的“人”。
在一个旧世界开始解体的时刻,身处其中的先觉者首先感受到时代精神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道德的失败感。“它使得当事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以及个人存在的现实相脱离,鼓励他们去追求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以代替难以忍受的现实。”[7](P221)瞿秋白身上的二元人格就可以看成是这两种精神运动留下的轨迹。而瞿秋白在狱中的心灵自白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但并不意味着他已找到了出路。尽管瞿秋白已分明感受到了带有末世论色彩的未来神圣的承诺终究不能代替人性和自由的现实质朴的需求,然而他终于不能从理性上洞察激进的乌托邦理想与放逐自由的极权主义的共生关系。从他最后开列的可视为精神遗嘱的书单来看,它仍然是一个未曾找到归宿的“多余人”,是一个没有能说出赞美词而溘然倒下的浮士德。
彭德怀的悲剧既是政治悲剧,也是自身性格的悲剧。这种悲剧性格也蕴含着可以从文化渊源考察的两重性。不过,与瞿秋白不同的是,彭德怀性格中的两重性没有表现为明显的分裂性和不可调和性。他的性格中导致悲剧的那一元,一方面与他的家庭出身和童年境遇相伴相生(自幼丧母的贫苦家境培育了彭德怀不畏强暴、冒颜犯上的叛逆性格);另一方面也与他赖以成长的湖湘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湖湘学派有经世济用和忧国忧民的传统)。彭德怀虽在历次路线斗争中屡次受指责的“经验主义”和“摇摆立场”,其实正有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求真理的积极意义。
中国源远流长的农民反抗历史中相关的文化基因的遗传更是彭德怀性格中深层要素。这种文化基因既有追求平等、反抗权威的一面,也有深通谋略、崇尚专权的一面(仅限于其军事韬略)。追求平等、反抗权威的一面才是他性格的底色,其价值内涵是对真理的崇仰和执著。这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尤其是与领袖的关系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与此相反,同是从湖湘之地走出来的并毕一生心血致力民族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宏大试验的伟人,毛泽东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征所体现的是农民文化基因中的深通谋略、崇尚专权的一面,而且他把这一面从对敌的军事斗争的领域扩展到对己的党内斗争的领域。从实现目标的方式上看,毛泽东更多地倚仗他出神入化的政治谋略;而彭德怀更多地凭借他横刀立马的英雄气魄。从政治与感情的处理上看,毛泽东重感情但不会让感情成为政治的掣肘,相反常把感情作为政治博弈中的筹码;而彭德怀却可以让“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时的桀骜不驯与对领袖的亲密无忌、由衷崇仰并行不悖。手段与目标的分殊使得中国现代政坛上的“将兵之将”和“将将之将”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即使仅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分合”史中撷取一个片段来考察也能加深对彭德怀性格悲剧的体认。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不过是作为“补天派”直陈了自己对大跃进带来的大饥馑的认识和意见,无论是忧国忧民、维护党和领袖利益的动机与从根源上纠正主观冒进错误的效果来说都是光明磊落、无可指责的。彭德怀谈到大跃进的错误时在西北小组发言坚称,“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4](P195)这种追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尽管有时还带着草莽气息)超过对自我保护意识和领袖尊崇意识(曾自称对毛的认识经历了“大哥—老师—领袖”三部曲)。这其中并无偶像膜拜的奴性与苟且邀宠的驯从的成分。
深谙个中三昧的林彪只一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4](P185),便为彭所有“罪名”背后的“罪名”下了极精辟的注脚,而形同政治围猎的庐山会议则再一次展现了最高领袖拿捏乾坤、吞吐日月的绝对权威。在传统农民反抗文化向现代工农革命文化的趋变中,如果说彭德怀更多地受到追求神圣真理的激励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更多地受到裁定真理极权的诱惑。
瞿秋白和彭德怀的悲剧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份值得总结的遗产,浓缩了几千年来中国秀才与农民的革命之梦。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自白”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份需要清理的备忘录。我们不妨把它们看成是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思想中的诸多潜脉与现代思潮中的若干湍流互相交汇、碰撞而涌起的小朵浪花叠映在现实的时空中。面对它们,只有运用人类实践中经过证伪而驻留下的现代理性作为出发点来反观走过的脚印,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海市蜃楼式的历史迷宫和鬼打墙式的现实梦魇,从而走向一个自由创造的境界。
标签:政治论文; 彭德怀自述论文; 多余的话论文; 瞿秋白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彭德怀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