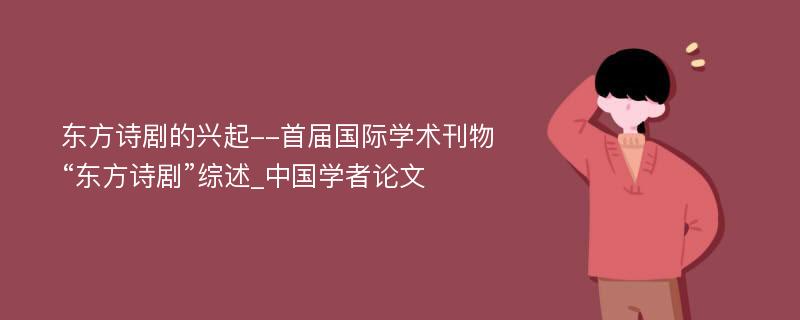
崛起中的东方诗话学——第一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学术论文,大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面新的学科旗帜,正在世界的东方学术界飘扬。这面旗帜上写着“东方诗话学”五个大字。
1999年7月9日,晴空万里,气候宜人。为期三天的“第一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正在韩国大田市的国立忠南大学校隆重举行。大会由韩国著名诗话研究专家、东方诗话学会第一任会长赵钟业教授主持,来自中、韩、日三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数十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
一、东方诗话学会
这次学术大会由“东方诗话学会”主办,是这个学会成立以后的首届学术年会。
东方诗话学会,是一个以东方诗话(含中国诗话、朝鲜诗话、日本诗话以及越南文论等)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性学术团体。著名诗话研究专家赵钟业、蔡镇楚、船津富彦等经过多年筹备,中、韩、日三国及港台地区其他同仁努力合作,1996年5月26 日在韩国大田市“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
东方诗话学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酝酿过程。1989年10月,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上海年会上,蔡镇楚先生在《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一文中,曾提出建立“中国诗话学会”的设想;经过多方联络协商,1990年2月在《中国文学研究》杂志上公布了钱仲联先生等22 名同行专家共同发起的关于《筹建“中国诗话学会”倡议书》。之后,为争取有关政府部门批准立案,钱仲联先生几次写信于民政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年11月,蔡镇楚先生专程去桂林,与广西师大张葆全、周满江教授共商举办首届中国诗话研讨会事宜。然而,鉴于种种原因,北京批复迟迟不下。1993年10月,蔡镇楚先生第二次出访韩国,正式向赵钟业教授提出创建“东方诗话学会”的意见,并立即着手筹备之。当学会诞生之际,学会章程由蔡镇楚起草,赵钟业、任范松协同,经过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章程规定每两年先后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学会主办的一个会刊《诗话学》,创刊号已于1998年由韩国汉城太学社出版发行。从筹备到学会成立,从会刊《诗话学》的编辑出版和首届年会胜利召开,赵钟业先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
古往今来,一切有志于诗话之整理与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从元代的方回、清代的纪昀、章学诚、何文焕,到民国时代的丁福保、徐英、郭绍虞、罗根泽、陈一冰,都曾经为之奠基。特别是日本的船津富彦、韩国的赵钟业、中国的蔡镇楚、刘德重、张葆全等教授为开创诗话研究之一代风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东方诗话学会的成立,是中、韩、日三国几代学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是方兴未艾的诗话研究走向国际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主要标志。其社会意义与国际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二、诗话学
这次学术年会的主要议题与突出成就,乃是为“诗话学”立论。大会围绕着“诗话学”这个中心展开讨论,基调发表有蔡镇楚的《诗话与诗话学》,刘德重的《诗话范畴与诗话学》,赵钟业的《诗话学与比较文学》,张寅彭的《诗话发展正义》。
诗话学,是以诗话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或曰“学科”。中外学者认为,从“诗话”到“诗话学”,乃是诗话之整理与研究的历史之必然,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学术发展潮流。其突出表现在于:
其一,“诗话学”之名,出现于20世纪三十年代。1936年徐英先生发表的《诗话学发凡》,旗帜鲜明地标举“诗话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尚属首创,代表着前辈学者对“诗话学”的热情呼唤,为中国诗话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其二,半个世纪以后,为继承前辈学者的未竟之业,蔡镇楚先生于1990年5月出版了一部名为《诗话学》的专著, 使徐英先生为诗话立“学”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从徐英《诗话学发凡》之文到蔡镇楚《诗话学》之著问世,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诗话研究实现了一大新的飞跃,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此中确实凝结着无数学者的滴滴心血和研究成果,但其开创之功应该归于蔡镇楚教授。
其三,东方诗话学会创办的会刊以《诗话学》命名,与徐英之文、蔡镇楚之著前后呼应。这样以来,“诗话学”之名同时赋予了一种学术杂志的内涵。这既是国际学术界对徐英、蔡镇楚标举“诗话学”的广泛认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东方诗话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将徐英、蔡镇楚为“诗话学”张目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际化、集团化的学术行为的一个重大举措。此举所为,应该归功于韩国著名学者车柱环、赵钟业先生和秘书长金周汉教授。
应该指出,关于为“诗话”之立“学”,中国大陆学人中尚有异议。有人主张以“诗学”名之,认为“诗学”大于“诗话学”,提倡从“诗学”方面研究诗话;有人反对诗话与诗话学,把历代诗话贬斥而为“一堆无聊的文字”,以严厉尖刻的言辞质疑于“诗话学”。对此,绝大多数诗话研究者并不以为然。蔡镇楚先生在《诗话与诗话学》中运用历史比较法从正面阐述了为诗话立“学”的几点理性思考和重要依据:其一,“诗学”在西方是广义的概念。中国人没有必要步西方诗学之后尘,勉强建立一门不可与西方诗学同日而语的狭义的“诗学”。其二,“诗学”之名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包含着多种内涵,如诗经之学、诗格之学、现代意义上的“诗学”等,故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或今日所谓的“诗学”。其三,“诗话学”之名较之于“诗学”,其概念之内涵与外延,更合乎中华民族乃至东方民族谈诗论诗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特性。其四,以中国诗话为代表的东方诗话并非仅仅限于诗论,其内容远比诗论要广泛得多。因此诗话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不能仅局限于诗学之研究。其五,诗话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的主要样式,中国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只有通过诗话研究才有可能实现。轻视中国诗话而欲建立所谓“中国诗学”,就只能拾“西方诗学”之牙慧而已。
对于那种贬斥历代诗话之论,刘德重先生在《诗话范畴与诗话学》中逐一给予针锋相对的批驳。他提出界定诗话范畴的三项原则,即主体性原则、约定俗成原则、历史存在原则,认为“诗话学能不能成立,关键不在于诗话范畴的确定,而在于诗话研究的成果积累”。
三、东方诗话学
本来,以“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命名者,1996年5 月曾经在韩国大田市召开过一次,为忠南大学校赵钟业教授退任之贺而举行。东方诗话学会首届年会题名为“第一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其意义之重大深远并不亚于替诗话立“学”。它表明赵钟业先生等国际学术界的朋友对“东方诗话学”的普遍认同和公开承认,说明“东方诗话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以创建“东方诗话学”为己任,高扬起“东方诗话学”这面学术旗帜,为力争东方诗话应有的国际学术地位,敢于以“东方诗话学”向“西方诗学”进行公开挑战的学术勇气。
“诗话学”之名,创始于徐英先生;“东方诗话学”之名,则出之于蔡镇楚教授。十年以前,蔡镇楚先生在其《中国诗话史·序》中明确提出建立“东方诗话学”的学术主张,把建立“东方诗话学”作为自己撰著《中国诗话史》的目的之一。比较而言,徐英之标举“诗话学”,立足点仅仅在于中国诗话;而蔡镇楚之倡言“东方诗话学”,则着眼于中国诗话、朝鲜诗话、日本诗话及其历史形成的东方诗话圈。
自古以来,东方文化以中国为核心,以儒家文化为纽带,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与地区形成一个儒家文化圈。东方诗话圈,是儒家文化圈的产物;盛极一时的中、韩、日三国诗话等,是古代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交融混一的宁馨儿。由于时代的局限,前辈学者的诗话研究尚停留在中国;而今时空的扩展,学术视野的扩大,开拓出前辈学者未曾有过的思维空间,“东方诗话”与“东方诗话学”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诗话学”的建立,是对诗话研究本身的学术动向和学科建设来说的;“东方诗话学”的创立,是对人们长期顶礼膜拜的“西方诗学”相对而言的。从“诗话学”到“东方诗话学”,这种历史时空的变换,正是诗话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广博的学术胸怀与思想境界,是“东方诗话学会”赋予诗话研究者应该自觉肩负起来的历史使命感,这就是使独具特色的“东方诗话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获得与“西方诗学”平起平坐的学术地位。因此,排斥“诗话学”或“东方诗话学”,显然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四、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
此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是处于世纪之交而召开的一次盛会。既是对千年诗话特别是二十世纪诗话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也是对下一世纪东方诗话研究前景的一种科学性的展望。
大会认为,以中国诗话、朝鲜诗话、日本诗话为代表的东方诗话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是东方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千年诗话,作家云蒸,卷帙浩繁,经久不衰,理应为之立一专门之学而加以系统研究。
大会认识到,二十世纪的东方诗话之整理与研究,从微观到宏观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应该充分予以肯定。诗话丛书如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郭绍虞《清诗话续编》,杜松柏《清诗话访佚初编》,广文书局《古今诗话丛编》《古今诗话续编》,赵钟业《韩国诗话丛编》《日本诗话丛编》,池田胤《日本诗话丛书》,吴文治等《中国历代诗话全编》,周维德《全明诗话》;专著如郭绍虞《宋诗话考》,蔡镇楚《中国诗话史》《诗话学》《石竹山房诗话论稿》,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张葆全《诗话与词话》,台湾张健《清诗话研究》,韩国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韩国诗话研究》、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日本船津富彦《中国诗话研究》;诗话研究论文数以千计,代表作如郭绍虞《诗话丛话》、陈一冰《诗话研究》、徐英《诗话学发凡》、徐中玉《诗话的起源及其发达》、钱仲联《漫淡诗话》、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中国诗话与印度梵语诗学》、张伯伟《中国古代诗话的文化考察》等;还有诗话类编、选本,如台静农《百种诗话类编》、李钟殷等《韩国历代诗话类编》、赵永纪《古代诗话精要》、王大鹏等《中国历代诗话选》、程毅中等《宋人诗话外编》;辞典有张葆全等《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曹旭等《中国诗话词典》、蔡镇楚等《东方诗话学大辞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颇具代表意义的丰硕成果,凝结着一代一代中外学者的心血,是诗话研究者奉献给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厚礼。
然而,学术研究总是后来居上的。展望未来世纪的诗话研究,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这就是所谓“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的真正含义。令人欣喜的是,一批优秀的学位论文在不断涌现出来,如台湾连文萍《明代诗话考》、韩国金姬子《韩国品则研究》、中国李清良《略论理学与诗话》、饶毅《中国诗话与唐宋诗之争》、张红《清代朴学与清代诗话》、蔡静平《钟嵘诗品与古代诗话》、欧海龙《论中国诗话的生命意识》、吴果中《象喻:中国文学批评的艺术生命》等,正代表新一代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眼光和研究水平,拓展了诗话研究的思维空间,是诗话研究的希望之所在。
大会特别强调,对于诗话作诗学研究,是必要的,但并不全面,我们还应提倡对诗话作文化学的研究,或者作美学的研究,文人心态的研究,审美语言学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民族文化性格的研究,文献学的研究,民俗学的研究,宗教文化的研究,等等。惟有使诗话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呈现多元化的格局,才有利于诗话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才有益于独具特色的东方诗话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体系的创建,才有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大家一致认为,“东方诗话学”当以中韩日三国诗话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学术坐标,以儒家文化圈为时空范围,以西方诗学与印度梵语诗学为参照系,运用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地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其学术前景是相当广阔而辉煌的。
与会者看到,“东方诗话学会”创造了一种开放性的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提倡学术自由论争,反对派别攻讦之习,主张在“东方诗话学”这面崭新的学术旗帜之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东方诗话研究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理事会决定,“第2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于2001 年在香港举行,并任命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为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事宜。
标签:中国学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