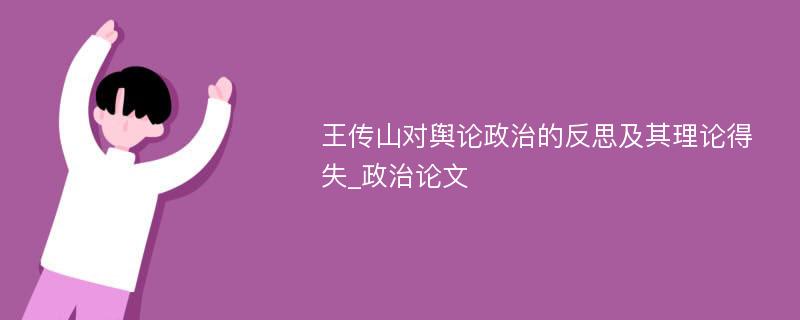
王船山对于民意政治的反思及其理论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意论文,得失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王船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贝马斯曾指出:“在不求助于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政治体系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性忠诚。”①阿尔蒙德等人也认为:“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妨碍。如果社会成员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常常是导致内战或革命。”②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在于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即符合民意。民意,又称民心。美国学者詹姆斯·M.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等人认为:“民意并不是一个坚实的整体,而是一些观点、态度的松散而复杂的结构,它具有稳定性、流动性、强烈性、潜在性、约制性、一致性或两极分化的性质,而这些都受社会成员对于意见、对于他们自己的突出性感觉如何的密切影响。”③民意能够通过一定的语言、行为等方式进行表达的社会意识,最终实现民意主体的要求与愿望,是政权决策的前提和依据。
对民意政治的反思是船山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船山政治思想注重辩证分析的理论特色,笔者在肯定其民意政治的反思总体上是积极性的、合理的、具有许多真理性因子的同时,也注意到其部分的理论盲点,遂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意与天命——“即民见天”与“援天观民”的二难
船山对于民意政治的反思是以考察民意和天命二者之间的关系为逻辑起点的。船山有五重天的分析,他既注意到了“天之天”、“物之天”与“人之天”的区别,又注意到了“己之天”与“民之天”的区别。④船山批评“滥于物之天”、“僭于天之天”的天人感应论和神学史观,认为圣人不应专于“自矜其贤智”的“己之天”,强调圣人所用之天乃“民之天”。可见船山在思考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复杂问题时,看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识到了“天视听自民视听”的巨大力量,但对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判断力,表示出极大的怀疑。他说:
尊无与尚,道弗能逾,人不得违者,惟天而已。……举天而属之民,其重民也至矣。虽然,言民而系之天,其用民也尤慎矣。
故可推广而言之曰:“天视听自民视听”,以极乎道之所察;固可推本而言之曰:“民视听自天视听”,以定乎理之所存。之二说者,其归一也,而用之者不一。展转以绎之,道存乎其间矣。
由乎人之不知重民者,则即民以见天,而莫畏匪民矣。由乎人之不能审于民者,则援天以观民,而民之情伪不可不深知而慎用之矣。⑤
船山一方面强调“重民”的必要性(“举天而属之民,其重民也至矣”);另一方面又强调慎用之(“言民而系之天,其用民也尤慎矣”),徘徊在“即民以见天”和“援天以观民”之间。一方面,船山反对“舍民而言天”。因为船山认识到“天显于民,而民必依天以立命”的道理,认为天意显于民意之中,对民意的尊重就是对于天意的尊重。船山也注意到了人民的视听、聪明、好恶、德怨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情所必逮、事所必兴”的。他承认民意的合理性,肯定民意“莫不有理存焉”,认为这是“谨好恶以亶聪明者所必察”的。⑥如果“舍民而言天”,独夫民贼就会利用符瑞、图谶、时日、卜筮作为其假借天命的统治工具。另一方面,船山又反对“舍天而言民”。因为“舍天而言民”会导致“筑室之道谋”、“违道之干誉”和“偏听以酿乱”的后果。所以用民必慎,因为“民之重,重以天”。而且由于民众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有限,人民的视听、聪明、好恶、德怨虽有根据但并不可靠(“非能有所稽”,“一动而浮游不已”),主要表现在易受鼓动和迷惑(“视炫而听荧,曹好而党恶”)、贪图小恩小惠(“忘大德,思小怨”)、盲目追随(“一夫倡之,万人和之”)、容易见风使舵(“旦喜夕怒,莫能诘其所终”),如不“奉天以观民”则无以定其权衡。船山对于这样的“民情”有生动的描写:
一旦之向背,骛之如不及,已而释然其鲜味矣。一方之风尚,趋之如恐后,徙其地而漠然其已忘矣。一事之愉快,传之而争相歆羡,旋受其害而固不暇谋矣。教之衰、风之替,民之视听如此者甚伙也。⑦
形象地描绘了民众“一旦之向背,骛之如不及”的盲从心理,“一方之风尚,趋之如恐后”的无意识状态,“一事之愉快,传之而争相歆羡,旋受其害而固不暇谋矣”的因缺乏深谋远虑而产生的冲动和易变。船山对于民情的心理揭示与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对于集体心态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勒庞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心态是群体行为发生时的基本心理状态,“群体总是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⑧他说:“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⑨在勒庞看来,群体有不少弱点,比如“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⑩“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11)“永远漫游在无意识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12)由于群体简单幼稚的本质,它往往会被一些炫目的说辞而左右;一些语焉不详的言论,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就可以让群众慷慨赴死。因此,群体是可以而且也往往是被利用的。船山也注意到了群体的轻信、极端、从众、多变、好冲动、易被人利用与情绪化反应等等弱点。他用典型的历史史实来证明民众的冲动、盲从、情绪化、无意识性、非理性:“司马温公入靓,而拥舆缘屋以争一见矣。李纲陷天子于孤城以就俘,而欢呼者亦数万人矣。董卓掠子女,杀丁壮,而民乐其然脐矣。子产定天畴,教子弟,而民亦歌欲杀矣。”(13)船山用史实证明自己观点的方式居然也与勒庞的相关描述有惊人的相似!勒庞说:“正是这个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14)船山和勒庞一样都看到了民众的冲动、盲从、情绪化、非理性、无意识性,因此船山引用舜之戒禹的话说:“无稽之言勿听!”认为民众之言是不可靠的:“民之视听,非能有所稽者也”、“民之视听,一动而浮游不已者也。”船山对于群体心理的描述和揭示有其部分的真理性因子,甚至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日本普通民众为何曾变成战争机器、“文革”中青年为何曾变得丧失理性、入市股民又为何会变得群情激亢、甚至是今天的网络民意的行为为何无意识和非理性等等。但他的理论失误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船山一方面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强调“即民见天”、强调民意不可违;另一方面又突出“民情”复杂、民意不可靠,必须“奉天以观民”,以天为标准来“审民之视听,以贞己之从违”。所以主张“征天于民,用民以天,夫然后大公以协于均平,而持衡者慎也”(15)。在“征天于民”与“用民以天”间彷徨,在“即民见天”与“援天观民”中徘徊。船山这种对待民意的双重态度突出体现在其对于民岩以及“清议”和“公论”的看法上。
二、“民本非岩,上使之岩”——船山对于古代民意政治之雏形的思考
梁启超曾说:“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则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16)在梁启超看来,“民岩”说是中国古代民意政治的雏形,是民众反对中央高度集权而主张分权之呼声的反映,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原初形态。梁启超强调尊重民意的重要性,认为立宪之国皆从民意为政:“西哲有言: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谅哉斯言!凡腐败不进步之政治,所以能久存于国中者,必其国民甘于腐败不进步之政治,而以自即安者也。人莫不知立宪之国,其政府皆从民意以为政。”(17)对于这样一种中国民意政治的雏形,比梁启超早两百多年的船山已经表达了一些自己独到的看法。
“民岩”一词,出自《尚书·召诰》:“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岩。”这是召公对周成王说的话。岩字本义为积石高峻貌,引申为僭越、险阻。“畏于民岩”就是畏惮民众僭越、民情险恶而难于治理的意思。(18)专制统治者从“私天下”之心出发,害怕民众有不同意见,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视民为岩。船山不赞同这种传统的“民岩”说:
古之称民者曰“民岩”。上与民相依以立,同气同伦而共此区夏者也,乃畏之如岩也哉?言此者,以责上之善调其情而平其险阻也。(19)
民非本岩,上使之岩;既岩,孰能反之荡平哉?(20)
船山认为民众与统治者本是“相依以立,同气同伦而共此区夏”的群体,怎能畏之如岩?“民本非岩,上使之岩”,民众之所以成为“岩”,完全是统治者自己造成的。这是对传统“民岩”观的巨大颠覆,标志着船山对于民意政治有了清醒的认识。船山举例说明由于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导致“民岩”的出现:
唐至懿宗之世,民果岩矣。裘甫方馘,而怀州之民攘袂张拳以逐其刺史;陕州继起,逐观察使崔荛;光州继起,逐刺史李弱翁;狂起而犯上者,皆即其民也。观察刺史而见逐于民,其为不肖,固无可解者。(21)
由于前文所说的专制统治下之民众本身总体素质低下以及民意具有盲从性、无意识性、非理性等等特点,使得船山对于民众持不甚信任的态度。他举例说明,唐宣宗考察官吏“微行窃听,以里巷之谣诼为朝章”,注重民众的意见,但是有的官员(如李言、李君奭)为了升迁,“贿奸民以为之媒介”,宣宗依然以里巷谣诼、街谈巷议为官员升迁之参照。船山对此批评道:“乃决于信,而谓廷臣之公论举不如涂人之片唾也,于是刑赏予夺之权,一听之里巷之民。而大臣牧帅皆尸位于中,无所献替。……长是不惩,又何有于天子哉?……民非本岩,上使之岩;既岩,孰能反之荡平哉?裘甫方平,庞勋旋起,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势也。山崩河决,周道荆榛,岂但如岩哉?……民气之不可使不静,非法而无以静之。非知治道者,且以快一时之人心为美谈,是古今之大惑也。”(22)唐宣宗注重倾听民众的呼声,官员任免升迁、荣辱生死皆操之民,这种“廷臣之公论举不如涂人之片唾”的做法的确是历史上难得的“快人心之美谈”。船山却看到了这种政治的负面影响,一些邪恶之人正是利用了君主尊重民意的这一善政而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民乃曰此褏然而为吾之长吏者,荣辱生死皆操之我,天子而既许我矣。其黠者,得自达于天子,则讦奏而忿以泄,奸亦以售;其很者,不能自达,则聚众号呼,逐之而已。曰天子而既许我以予夺长吏矣,孰能禁我哉?不曰天子固爱我,即称兵犯上而不忍加罚于我;则曰天子固畏我,即称兵犯上而不敢加刑于我。”(23)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将是对于君权的极大威胁(“长是不惩,又何有于天子哉?”)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船山认为唐宣宗之举是“古今之大惑”,并将造成“民岩”的原因归为这一善政,这种基于民意的复杂性而不盲从民意的看法也是辩证的合理的,与他所持的民众与统治者本是“相依以立,同气同伦而共此区夏”的群体的观点并不冲突。
中国的农民是以具有极坚强的忍耐性见称的。然而,他们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忍耐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再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农民“小人”确实是“学道则易使也”!可是,正惟他们不是天生的“易使”,而是“学道”则“易使”,所以,一旦当作“道”来范围他们的社会组织、伦理教义、政治权力发生破绽,他们即使谈不上什么政治自觉,也将因所受社会经济压迫剥削的过火,而使他们的极度忍耐见机突发为不可抑制的反抗。(24)用船山的话说即是“民非本岩,上使之岩”,“既岩,孰能反之荡平哉?”所谓“官逼民反”,民众居然已经到了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起来造反的地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船山认为“民岩”是专制统治者所造成的,那么就应该“知畏民之岩者,调制其性情于早”,要“善调其情而平其险阻”,即早日预防,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民众造反之后再去镇压。怎样“调其情而平其险阻”呢?一方面他强调“夫粟所以饱,帛所以暖,礼所以履,乐所以乐,政所以正,刑所以侀,民岩之可畏实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诚有其事。”(25)其实也就是尽量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以礼乐教化之,以政刑约束之。“民岩之可畏实有其情”,此“情”就是没有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实情。另一方面,他强调“民气之不可使不静,非法而无以静之”,主张“不可唯意以乱法”,他说:“人君所恃以饬吏治、恤民隐者,法而已矣。……于是乎民有受墨吏之荼毒者,昂首以待当守之斧钺。即其疏脱而怨忿未舒,亦俯首以俟后吏之矜苏。而大臣牧帅既得其人,天子又推心而任之,则墨吏之能疏脱以使民含怨者,盖亦鲜矣。”(26)船山认为“不可唯意以乱法”最重要的是要做到“饬吏治、恤民隐”两件事,这也与船山“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旨趣相同。就是说对于贪官墨吏,要依法严惩。他要民众相信统治者澄清吏治的能力和决心,民众尽管昂首以待贪官墨吏就刑就可以了,因为在“大臣牧帅既得其人,天子又推心而任之”的法治情况下,贪官墨吏是极少能够逃脱其罪责的。由此可见船山对于法治的效果充满信心,同时表明船山对于法治前景有着美好的憧憬。
三、“后世庶人之议,大乱之归也”——船山对于民间舆论监督的质疑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27)舆论有质量上的分别,舆论的质量是指舆论所表达的价值观、具体现念及情绪的理智程度。(28)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主导舆论,是大多数公众的意志,这种意志应当尊重,至少要得到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舆论是民主的重要因素。但从舆论的特征考察,舆论又是一种内容十分庞杂而多变的社会精神形态,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29)显然,识别舆论的质量,需要较高的素养,尤其需要冷静的理智和丰富的知识。舆论有时带有较多的传统成分,并非时时代表社会的良知和发展方向。民间舆论监督是民意政治的又一重要形式。
在中国古代,“议”一词即可看作是舆论的对应词。《论语·季氏》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孟子·滕文公下》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清议”的字面含义是“纯正不污的谈论”,有时也可以笼统地意译为“公共舆论”。清议乃是原始氏族民主制之遗风,是民众表达其对于社会公共事务之意见、议论政教风俗得失、评议官员人品高下的一种自发的方式。这个词在后汉时期,曾用来意指一批无权的儒家文人对朝廷日益为宦官外戚所把持而发出的抨击。南宋时期,中国受“北狄”入侵的威胁,“清议”又用来意指激烈反对绥靖政策的一部分政见。在各个时期,清议都是为维护儒家道德文章的纯洁性而进行坚决斗争,矛头指向以种种方式威胁或破坏儒家秩序的当权人物。(30)早期启蒙思想家把舆论监督看作是弥补体制内的权力制衡之不足的又一种权力。顾炎武指出:“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31)黄宗羲主张学校议政,以造成“朝廷之上,闾阎之细”都不以天子之非是为非是的民主氛围。
王船山也并没有否定清议的价值,他说:“清议者,似无益于人国者也,而国无是不足以立”,“清议不明,非一时一事之臧否已也”(32)。但与顾炎武过于迷恋清议不同,总体而言,船山对于清议是持批评态度的:“畏清议也,甚于鬼神”(33),“故获市井小民之歌颂者,必溃之将也;得学士大夫之称说者,必败之将也;多其兵而寡其食,必亡之国也;以名求将而不以功,授将帅殿最之权于清议者,必乱之政也。”(34)这与船山对于民意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船山看到了清议有非理性的层面,所以主张以法约束之:“恐其亡实而后以法饬之,《周官》、《周礼》、《关雎》、《麟趾》之精意所持也。”(35)应该说船山关于清议的思想是辩证的合理的。其前辈吕坤早就指出,对于社会上流行的所谓“清议”要作具体分析。他认为“清议”具有两重性:“清议酷于律令。清议之人,酷于治狱之吏。律令所冤,赖清议以明之,虽死犹生也。清议所冤,万古无反案矣!”(36)指出以传统的道德标准去裁量人物,足以使“清议”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明朝大将熊廷弼和袁崇焕的悲惨遭遇即是明证!萧萐父、许苏民认为:“历史事实证明,民族危机的造成,不仅直接导源于专制主义的制度性腐败,而且与被滥用了的、不负责任的、排斥社会功利的‘清议’有着直接的联系。——王夫之在他的很多论著中极力申说民族大义高于君臣之义,既对专制主义的制度性腐败深恶痛绝,又对明末被滥用了的、严重干扰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清议’颇有微词,正是基于对晚明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之关系的洞察。”(37)鉴于晚明东林党人的“清议”常常以泛道德主义去衡量一切,难免做出一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之事实,船山对于清议持有谨慎的保留态度。的确,如果不破除传统的泛道德主义,而以道德评价来取代对其本身的政治评价,即以道德批判这种抽象的价值判断来否定具体的政治成就,将政治批判变为人身道德攻击,那么这种道德上的否定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往往非常有限。以社会政治为其主要关注点的清议,很容易偏离政治路向,流于抽象的道德谴责。“清议”极有可能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所以,船山担心“清议”名存实亡而强调“以法饬之”的主张无疑是远见卓识!
船山的清议批评,包含了对“众论”之为“公是公非”的怀疑,尤其包含着对于东林党人以“以公论定国是”的批评。在船山那里,舆论即公论,也即公是公非。以舆论为公论,符合士大夫的传统信念。(38)这里的“公”(也即“公正性”)是以参与者的数量(即“众”)来注释的。船山对公论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闻乡之有月旦矣,未闻天下之有公论也。”(39)“置神器于八达之衢,过者得评其长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抵于败亡。”(40)“以名誉动人而取文士,且也跻潘岳于陆机,拟延年于谢客,非大利大害之司也,而轩轾失衡,公论犹绌焉,况以名誉动人而取将帅乎!”(41)当然,明末清初对公论持批评的态度的并非船山一人,吕坤曾说:“公论并非众口一词之谓也。满朝皆非而一人是,则公论在一人。”(42)陆世仪也不以“处士横议”为然:“嘉、隆之间,书院遍天下,讲学者以多为贵,呼朋引类,动辄千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谓处士横议也,天下何赖焉!”(43)陈确也以“在野言朝”为“妄言”、“乱说”。(44)不过,赵园认为,明清之际的有识者中,对“众”、众论持严峻的批评态度者,似以船山最引人注目。他有关众论不足恃的陈说,是其明亡后的反思中富于洞见的部分。(45)我们可以将船山对于“公论”的理解与较之稍晚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对于“公意”的阐发进行比较。卢梭肯定舆论的巨大力量,认为它是正规法律以外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俗、习惯,而尤其是舆论。”(46)卢梭同时又将舆论分为“公意”和“众意”,众意着眼私人的利益,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是指人们最初自由结为共同体时的协议、约定、公共意愿,它是“普遍的意志”和“有机结合的意志”。他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47)船山对于众论与公论的怀疑正是注意到了众论与公论着眼于私人的眼前利益,这种个别意志的总和难以保证自身的公正性和正确性,从这一层面讲,众论与公论与卢梭所阐发的“众意”具有相同的内涵,但是船山没有意识到舆论民意的另外一个层面的涵义——即卢梭所指的“普遍的意志”和“有机结合的意志”——公意,因而反对公论群议。也正是这个原因,船山反对庶民议政,他说:“后世庶人之议,大乱之归也”,又说:“且夫元后之思,庶民思之则只以乱;圣人之思,愚不肖思之则无所从。惟好恶者可率天下以同遵者也。悦生恶死,喜远怨劳,王者必与兆民同之,而好善恶恶,兆民固与王者有同情也。”(48)但是,应该明确的是,议政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政治行为,民间议政能监督政府,使之向善。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但是“政教苟非尽善”的时候,庶人还是可以议政。清议的存在至少说明了当时社会的言路畅通和社会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的开放性,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就可以尽可能地反应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态度(当然,主要是士大夫群体),进而成为对朝廷政治的某种制衡因素,对传统的政治结构进行某种有益的补充。船山这种过于担心庶人议政引起党争和动乱而反对庶民议政的态度是不可取的。(49)
船山之所以对于公论群议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论群议的复杂性往往会影响正确的决断,所以船山反而强调“独”的重要性,凸显了政治精英的政治作用,他说:
用人则采公论,而后断之以其真;其合者,则曰此众之所允惬者也。行政则访群议,而后析之以其理;其得者,则曰此众之所襄成者也。此其所当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奸邪窥伺于旁,主心疑贰于上,事机决于俄顷,祸福分于毫厘,则疏远之臣民,既非其所深喻;即同朝共事,无敢立异而愿赞其成者,或才有余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胜。徒取其志,则清谨自矜之士,临之而难折群疑;抑取其才,则妄兴徼利之人,乘之而倒持魁柄。如是者,离人而任独,非为擅也。知之已明,审之已定,握之于幽微之存主;而其发也,如江、河之决,不求助于细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独知,而震行无眚,夫孰得而与之哉?(50)
“处江湖之远”的“疏远之臣民”由于对于“奸邪窥伺于旁,主心疑贰于上,事机决于俄顷,祸福分于毫厘”等异常复杂的决断环境缺乏了解,往往对于“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之类的国家大事难以作出正确的决断;即便是“同朝共事”之臣民,由于主观条件的差别(“或才有余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胜”)对于一些国家大事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这种情况下,船山充分肯定“离人而任独”的作用,并以“江、河之决,不求助于细流”为喻否认“任独”是一种擅权的行为。他在《周易外传》更是明确地论述了独与众的关系:“善致功者,用独而不用众,慎修德者,谨始而尤谨终。众力之散,不如独之一也;终事之康,不如始之敏也。”(51)船山充分肯定政治精英在政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众力之散,不如独之一”)。诚然,如果众人之力没有相同的矢量,不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就形成不了强大的合力,反而会削弱各自的力量,船山显然是很清楚这个力学上的简单道理的。勒庞也有类似的说法:“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52)“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如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53)又说:“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54)当然船山将“独”与“众”简单分离,过于强调“独”,未能重视“众”,也是不能原谅的理论失误。同时期的顾炎武则与船山相反,强调“众治”而不是“独治”,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顾炎武认为“独治”反映的是君主的意志,而不是民众的意志。乡村的一切纠纷都必须诉诸法律,这就导致狱讼繁多,贪官、师爷、书办、衙役、狱卒各色人等皆可以趁此渔利,以其暴而济其贪,使得老实善良的农民处于苦不堪言的境地。要改变君主的“独治”所造成的这种“以刑穷天下之民”的情形,救焚拯溺于百姓,就只有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实行乡村自治制度,让农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在顾炎武看来,就叫做“众治”,因为它反映的是农民群众自己的意志。王船山与顾炎武对于“独治”与“众治”的不同理解反映了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转型初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于精英主义和全民主义的不同看法。张灏在评析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时,指出转型时期的全民主义是以反抗儒家的精英权威主义的思想面貌出现的。但是即使如此,精英主义也并没有被全民主义所完全取代,当时的精英主义不仅反映传统的圣贤崇拜,同时也反映一种客观环境的现实需要。他们提倡民权鼓吹群众的言论常常是伴以提高“民智、民德、民力”的呼吁。这显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困境感。一方面在理论上他们强调群众是神圣的,人民的“公意”已取代传统的天意;另一方面,就实际情况而言,他们也知道人民大众的愚昧与落后,需要提高他们的“德、智、力”各方面的素质;一方面他们在理论上宣扬群众是历史的动力,社会的巨轮;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一般人民在现实情况下,往往不是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因此,在群体意识中,全民主义与精英权威主义往往有吊诡的结合。(55)虽然张灏所说的近代民主观念的转型主要是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主要代表,并不涉及船山,但是张灏揭示的全民主义与精英权威主义往往有吊诡的结合的论断是很有见地的,这一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船山对于“民意”与“天意”的态度、对于“独”与“众”的态度,可以合理地解释船山对于“民岩”、“清议”与“公论”的复杂态度。
梁启超批评中国的政治思想时说:“要而论之,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56)任公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中国先哲大都知道民意应当尊重,即使是昏庸的帝王也知道民心向背的道理,明白“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缘由所在,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民意、如何顺从民心。先贤们往往在实现民意、顺从民心的路径上,容易出现偏差,因为怀疑民众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而因噎废食,最终反对清议、反对庶民议政,强调贤人政治、精英政治,即便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颇具反思批判力的船山也不例外。徐复观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这便与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争的发生发展的情形,成一极显明的对照。正因为这样,所以虽然是尊重人性,以民为本,以民为贵的政治思想;并且由仁心而仁政,也曾不断考虑到若干法良意美的措施;以及含有若干民主性的政治制度。但这一切,都是一种‘发’与‘施’的性质(文王发政施仁),是‘施’与‘济’的性质(博施济众),其德是一种被覆之德,是一种风行草上之德。而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尽管以民为本,而终不能跳出一步,达到以民为主。于是政治问题,总是在君相手中打转,以致真正政治的主体没有建立起来。”(57)应当承认,在明清之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王船山等早期启蒙思想家们较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家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近代性因素以及可与现代接榫的思想资源,此乃自不待言。然而即便如此,中国政治真正的政治主体没有建立起来也是不争的事实。王船山虽然提出了旨在限制君权的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暗示着中国政治学说开始出现向近代转型的征兆。然而由于船山的视域相对狭窄,没有充分重视民间舆论对于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作用,因而对于“清议”和“公论”等民意政治形式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其实“清议”和“公论”等民意政治的雏形经过改造,是可以转化和发展成为现代民主政治下的舆论监督机制的,这是船山没有重视的,不能不说是船山政治思想的理论失误。
①[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
②[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6、37页。
③[美]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美国式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40页。
④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⑤王夫之:《尚书引义》卷4,《船山全书》第2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327、328页。
⑥⑦王夫之:《尚书引义》卷4,《船山全书》第2册,第328、330页。
⑧⑨⑩(11)(12)(1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49、37、70、59、52―53页。
(14)(15)王夫之:《尚书引义》卷4,《船山全书》第2册,第330、327页。
(16)梁启超:《梁启超文集》,《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223页。
(17)梁启超:《梁启超文集》,《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181页。
(18)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1页。
(19)(20)(21)(22)(2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7,《船山全书》第10册,第1025、1027、1025、1026、1026、1027页。
(2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5)王夫之:《尚书引义》卷4,《船山全书》第2册,第378页。
(2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7,《船山全书》第10册,第1026页。
(27)孟小平:《揭开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28)(29)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2、22-23页。
(30)[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第29页。
(31)顾炎武:《日知录·清议》,载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第478页。
(3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5,《船山全书》第10册,第198页。
(33)王夫之:《宋论》卷10,《船山全书》第11册,第240页。
(3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7,《船山全书》第10册,第279页。
(3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船山全书》第10册,第398页。
(36)[明]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中册,《呻吟语》卷2《修身》,中华书局,2008年,第684页。
(37)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第23页。
(38)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公论”提出自己的理解:“明末屡屡出现以‘公论’为名的主张,这种‘公论’兴起的背后,存在着所谓地主制的发展的新的社会变化。”“……官僚的制约能力相对削弱,以地主阶层为中心的地方统治势力的舆论力量强大起来,这就是所谓‘公论’。”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3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3,《船山全书》第10册,第125页。
(40)王夫之:《宋论》卷4,《船山全书》第11册,第120页。
(4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3,《船山全书》第10册,第140页。
(42)[明]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中册,《呻吟语》卷5《治道》,第825页。
(43)陆世仪:《思辩录辑要》卷1《正谊堂全书》。
(44)陈确:《辰夏杂言·不乱说》,《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414页。
(45)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46)(4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0、35页。
(48)王夫之:《尚书引义》卷4,《船山全书》第2册,第359页。
(49)据萧公权研究,近代的冯桂芳也曾因庶人议政引起党争和动乱而对清议有批评的看法:“冯氏(指桂芬,笔者注)所以不令诸生上书直陈时事者,盖以鉴于汉王咸、陈蕃、晋嵇康、唐鲁傥,宋陈东等虽以太学清议为人所称,而究其终极不免朋曹干政,斗讼成风。”(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萧公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8-669页)其实,甚至萧公权本人对于清议也并无好感:“清议本身,既大体以儒家之名教为依据,末流之弊遂至于吹毛求疵,无的放矢。……此种维护纲常之毁誉,虽略伤琐细苛刻。然苟诚意出之,尚可不失其正人心之作用。然而吾人稍按史实,即知其不必尽然。……清议云云,徒致守道者于困穷,便黠者之眥讦而已,何尝有正俗之功乎?”(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萧公权卷》,第320页)
(50)王夫之:《宋论》卷5,《船山全书》第11册,第146页。
(51)王夫之:《周易外传》卷3,《船山全书》第1册,第927页。
(52)(53)(5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49、49、38页。
(55)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载《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5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0、41页。
(57)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载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