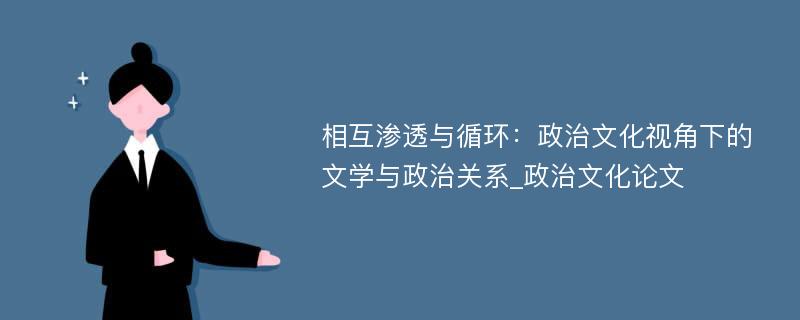
互渗与回环: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文学与政治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视角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该从“账面”与真实两个方面分别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先来从“账面”的关系说起。长期以来,文学和政治是“熟悉的陌生人”,都自以为对对方知根知底,但实际上误解重重。文学家往往把政治当作运用权利对自己进行压制的怪兽(利维坦),忘记了文学与政治的种种玄妙的渊源关系。政治家又往往拒斥文学的复杂性,总想把文学简化为工具(传声筒),或者变为建构自身的砖瓦,或者作为解构他人的弓弩。文学家和政治家实际上在进行一种“平行游戏”(注:平行游戏指儿童游戏时靠得很近,但并不一起游戏,每个儿童的游戏都互相独立。见[美]詹姆斯·卢格:《人生发展心理学》,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但是,在实践中,二者的关系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政治不是文学的简单目的,文学也不总是处于被钳制的地位。文学促进了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政治的发展也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在“符号秩序”的生产和流通中,文学与政治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各自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套用福柯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赞扬?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注:福柯指出:“权利问题不可能再与奴役、解脱和解放的问题分开。佩特拉尔格曾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颂扬”那么我们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见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互相缠绕,互相影响,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一 叙事——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
利奥塔把科学与其他各种知识都归结为叙事:“科学希望它的陈述是真理,但是它没有将其真理的合法性诉诸它自身。”(注: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政治也是如此。而叙事的功能恰恰在于提供了人类所有知识的原初合法性。利奥塔说:
叙事(如神话、传奇或寓言)讲述了某些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业绩直接赋予故事发生时的社会机构以合法性,而间接地牵涉到现存社会的机构的合法性。“叙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提出了一些评价事物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人们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注:Lyotard,Jean-Francis,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xxiii.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文学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形式,例如利奥塔在上文中列举的神话、传奇或寓言都属于今天知识类型划分中的文学的范畴,因此,叙事的功能可以看作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中所起的“上行作用”。
一切政治家所“耿耿于怀”的,总是大众对其政权是否有认同情感。人心向背,是一切国家、政府和统治秩序的存亡之本。“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老,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正义》卷三十七)。礼乐“同民心”方可出政刑之“治道”。
中国有“盛世修史”之说,而修史就是通过对以往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进行叙事,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工程之一。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叙事决不是完全客观的记述,它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历史重新编织的过程,它是通过讲述的权力试图建立新的秩序的重要途经。在中国,《史记》以来的历史著作的编纂表明,修史甚至已经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文学也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洪子诚指出: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洪子诚教授在复述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中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时说:“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之所以把历史与小说这两种现代知识论中完全不同的类型混为一谈,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真实更在于政治的合法性,因为,小说一般是以虚构为特征的,推导到“真实”还需要一些迂回曲折的勾连。当政治转换为叙事的时候,它就会弥散为在人们的信仰和观念、行为与习惯中的“流动的秩序”,变得亲近而温和甚至优美起来。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岩》等长篇小说,已经发生的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景象。
二 拟剧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成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起源于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尔博(Sidney Verba)1963年发表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该书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强调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以及对于政治物和政治过程——对于整个政治制度、对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对政党和选举、科层机构等等——的感情和价值取向”(注: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eds.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Toronto,1980,p.27.转引自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第52期。)。
实际上,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注:[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徐江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经典和整个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包括)这个“剧场”提供剧本。设计剧情发展,规定人物台词和动作。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经典和文学就是人们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剧本。
那么在政治和其他社会过程中人们(包括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所依据的剧本是什么?是周围人们的行为“示范文本”(不成文的习惯、惯例)和各种成文文本(包括法律条文、文学经典等)。而由于行为文本的零散性、流动性,人们在其中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和体会政治行为的规则,因此,才有《红楼梦》第五回中的一副对联: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实际上,这副对联道明了“剧本”(学问、文章)与“演出”(世事、人情)的对应关系或者“互文性”,不仅仅是什么“封建阶级陈腐的说教”。贾宝玉采取了“去政治化”策略,似乎学问和文章是永远不会与仕途经济纠缠的,但这种策略的恰恰反衬了政治的神秘化。
据《宋史·赵普传》记载,北宋著名宰相赵普曾经对宋太宗(赵匡胤)说:“臣平生所知,无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此即后世“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来历(注: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第三折《倘秀才》:“卿(赵普)道是用论语治朝迁有方,却原来只半部运山河在掌。”)。显然,赵普是把《论语》当成了战争和治理的手册,虽有夸张,但其言仍然不谬。
因此,中国的传统经典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剧本。而这种典籍所培育出的政治文化生产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意识,一是君王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二是臣民意识,事君如事父,分享“天下”的“幻相”,“做稳奴隶”。二者之间又构成了“合谋”的关系,天下于是“其乐融融”。
所以,政治上的角色也是“做成”的,而不是天成的。政治学里的精英和公民这两个词正好可以合并为哲学里的“主体”范畴,而且分解了它的两个义项,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现代社会里,公民首先是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来定义的,主体表明了自由的主观意志,主体做出行为。但是,这种所谓的“权利”本位论遮蔽了另一个真实,主体同时也是一个服从者,是被决定的。后现代理论一般认为要成为主体,就必须要成为各种制度(政治制度、科学话语)的服从者。文学中有两个词分别指涉主体和臣民——性格和命运。每个人的实际境遇都是性格和命运互相作用互相生成的结果。没有纯粹的性格悲剧,也没有纯粹的命运悲剧。好的作品总是深刻地反映了两者的纠葛。
现代政治中核心的角色是公民。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文学生产的。文学通过“描写”现代政治与社会的场景,在这种场景里人物的行为模式,积淀出许多惯例,提供新的公民角色认同,同时纪录和改编了政治过程潜在的“演出脚本”。文学的新类别——小说与新时代的公民几乎是伴生而来的:“美国批评家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认为18世纪的小说和行为指南创造了‘现代的个人’,这个个人首先是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现代人的属性和价值都是从感情和个人的品质中生成的。……到后来才扩展到男人。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个概念是通过小说和别的捍卫情感和个人价值的话语得以发展和拓宽的。如今这个关于(主体的)属性的概念通过电影、电视和各种话语得以延续。这些电影电视和话语的设计和情节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文学使《人权宣言》中的抽象设想成了具体生动的形象。
所以文学是培养精英(政治精英的亚文化来源于更高的教育程度,也即更多的文化文本)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土壤,是政治文化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三 政治对文学的介入——文学的经典化过程
政治权力对文学的政策除了极端的文字狱和绝对的放任外,主要的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介入。“介入”一词完全是中性的。政治扶持主流文学的发展。而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为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空间,文学的多样性促进了政治的发展,文学与政治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政治介入文学的目标为什么选择经典呢?因为经典是文学的“关键种”,对整个“文学群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的涨落演替决定着文学群落的涨落演替。经典既是阅读和教育的中心也是作家和大众学习模仿的源泉和典范,同时,经典还有跨文学的泛文化功能:
经典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49页。)
因此,经典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这个“剧场”提供剧本,编写情节,指派人物角色,设计台词和动作。
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参与》中讨论西方经典的重要性时指出:文学经典在中世纪的重要性来源于它统治着整个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只有其他两种社会机构被授予了权力:教会和政府。或者如恩斯特·罗伯特·古提斯的简要的概述:“存在着学校的文学传统、政府的司法传统和教会的宗教传统:这些是中世纪的三个世界性权力机构:教育权、帝权、神权。”(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而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围绕“四书五经”来展开的。
因此,文学与政治之间事实上是通过“成规”连接起来的:成规是行为之中或行为与信仰之中的规律性,它们是任意的,但却使自己永存,因为它们符合某些共同的利益。过去人们对它们的遵奉,使得他们将来也会遵奉它,因为它给予了一个人继续遵奉下去的理由;但存在着可以选用的另外的某种本可以取而代之的规律性,而且一旦开始了就会以同样的方式使自己永存。(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施密特指出:“一个社会中规定在某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的一条成规必须是社会成员中共同预设了的一种知识,因此:对于采取这种举动存在着一个先例或者协议;由于这个先例,该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期待他人采取此种举动;由于这一期待,所有社会成员在适当的情况下都将会采取这种举动”(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所以,成规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政治介入文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修订社会“成规”的行为推进公众(读者)对社会规范的认识、认同和理解。遗憾的是,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似乎法律的规范才能影响社会的成规。
经典生成后它的边界仍然是流动的,即经典本身还有演替的过程。而政治往往是经典演替的环境因子和目标。例如,德国在1859年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二战期间的苏联对伟大的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经典构成的新的样式。与经典的原生过程和涨落不同,因为那的确是一场革命,几乎所有的传统经典都被当成了“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去经典化),新的经典在革命的加速器中生产着,真正的“断裂”出现了。整个过程我称之为“再经典化”。但是,就文革而言,决不应该看成政治对文学的胜利,那实际上是一个荒漠化时期,政治尤其是政治中的民主和自由都受到了践踏。首先是政治的退行性演替,接着引起了文学的退行性演替,结果是政治与文学的“双败”。
文革结束后,被“去经典化”的许多作品又重新被发掘出来进行“再经典化”,起因仍然是政治本身的转变,而当“生活政治”兴起的时候,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又成了出土文物,经典的结构又重新回到多元化的格局。
四 文学对政治的祛魅
文学对政治的解构,与其一般地理解为对某种政治派别或者政治主张的否定或反对,毋宁在于将政治无意识文本化,使我们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终于文学对政治的祛魅,拆穿政治仪式的神秘性。杰姆逊(又译詹明信)指出:“历史不是一份文本,不是一种叙事,也不是主符码或其他符码,不过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原因,除了在文本的形式中对我们却是不可及的,我们要对它即真实本身进行研究,只有先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文本化和叙事化。”(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政治的文本化导致了政治与审美构成了错综回环的关系。
杰姆逊从“文本意识形态”归纳出了一般的“政治无意识”,指向三种不同层次的语境,提供给人以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框架。即1.直接的社会历史层面;2.更大的阶级间的互动关系;3.生产方式。(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
因此,在政治过程中乃至文学中,政治的合法性能够以“温和的方式”施展符号暴力权力(注:[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在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6页。)。同时也正是文学在自我解构中渗透了对政治的解构。在文学的实践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理论特别值得关注。文学中的所谓元叙事不同于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即“把所有的证明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证明”的陈述。利奥塔已经指出了这种元叙事的不可能性,并且将它转换为“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问题(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47页。)。文学中的元叙事是关于叙事的叙事理论,它揭露了言说的“我”与行动的“我”分裂的事实,质疑言说的权威性和真理性。文学的元叙事因而也构成了对文本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过程,或者说是对政治的解码。政治的美学风格主要是崇高,优美兼之。而文学的元叙事使文学总是呈现出反讽的风格,充满对语词与言说的质疑,充满对语言所指称的世界的质疑。甚至“作者”也走进小说指指点点。这样,文学作为精神圈里的不同“群落”又的确和政治发生竞争和“争辩”的关系。
目前,我们应该把文学所有的错综性和复杂性都看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机制和社会实践。……不论什么正统思想、什么信仰什么价值观,文学都可以编排出各种不同的、怪异荒诞的故事来嘲笑它,以模仿的方式戏弄它。文学一直有通过虚构而超越前人所想所写的东西的可能性。从萨德侯爵那些描绘出一个行为产生于欲望不受任何约束的社会里会发生什么的小说到萨尔门·拉什迪的《撒旦诗篇》,那些诗作因为在讥讽和戏谑模仿的语境中使用了神圣的名字和主题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论任何看似合乎情理的东西,文学都可以使其变得荒谬不堪,都可以超越它,都可以用一种向其合理性和适当性提出质疑的方式改变它。(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阿多诺甚至认为:“艺术作品的伟大性,单单在于这一事实中:它们向意识形态掩饰之物发出声音。它们的成功超越了伪意识,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注:阿多诺:《文学笔记》Vol.I,39,转引自[加拿大]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汪民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77页。)
利奥塔思考了文学的否定性,它的一个来源是:“在后现代状况下,优先性被赋予了崇高的情感,而崇高的情感同语句所表达出来的描述是连在一起的,这也就是同事件相连的情感。这种情感把行动的冲动和任何行动都不会是正确的行动这种情感聚合在一起。”(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证明迥异(deferend),也就是说,证明一般的事件与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和理解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结果产生了“不可公度的语言游戏和风格(genres)。”(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
历史上,柏拉图非诗,孔子删诗都是极具“远见”的,他们参透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文学家和批评家们往往强调文学的“自足性”或者“超越性”神话,这里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新写实主义流派(按文学生态学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文学群落),通常批评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流派的政治意味。
吉登斯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他所称的“生活政治”,即将统一的社会认同瓦解为分散的个体化的生活政治。“解放政治”关注的是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意图建立正义、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生活政治”更加关注每个人“自我”的整体性(personhood)、个体性(individuality),呼吁重新关注道德和存在的问题。“生活政治”是一种更为宽容的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七章“生活政治的兴起”;[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第2章。)这不正与陈晓明对新写实主义特征的指认相符吗?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暗示两者的一致性,而是说明“没有经典的那种强调和暗示”的新写实主义仍然不能逃脱与某种政治理念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关系。
从文学的立场看,政治未必不是文学的“面具”或者“资源”,甚至是今天所谓的“炒作”手段。陈平原指出:文学之所以与政治结盟,有时候其实是出于文学自身的需要。政治毕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更是充满激情、想像力与冒险精神。对于文学家来说,人生百态,没有比“革命”更富有刺激性与诱惑力的了。想革命、写革命、干革命,20世纪中国的小说家,曾如此痴迷于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革命”,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其中还隐含着审美的意味。尤其是大动荡的年代,“革命文学”的粗犷、悲壮与崇高,自有其独特魅力。单就文学风格而言,江南的小桥流水固然可人,塞北的大漠孤烟同样摄人心魄。(注:陈平原:《怀念“小说的世纪”——〈新小说〉百年祭》,《书城》,2003年第3期。)
总之,不论文学家们如何“躲避”、“拒绝”甚至“反抗”,都无法自外于政治。政治不仅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的“质询”文学,甚至于“打上门去”。当然,我们反对把文学简单地归结为政治的工具。而实际上文学要迂阔繁芜得多,它有着自己的生态复杂性。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化,必然会陷入打棍子或者文字狱的泥潭;过分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也会使文学脱离社会实践,让文学面临从反面被抽空的危险。文学与政治既不是敌手,也不是主仆,它们是人类精神圈里协同共生的“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