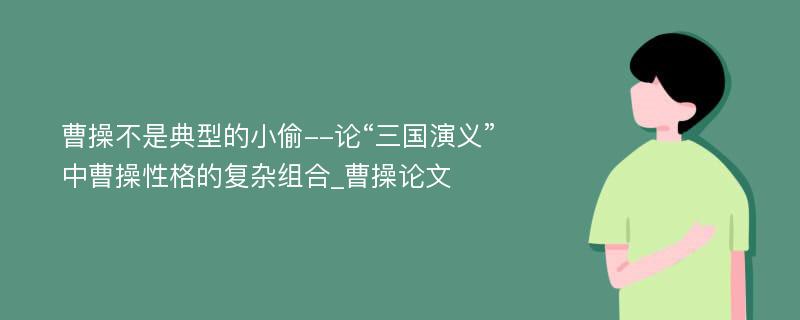
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谈《三国志演义》中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奸贼论文,组合论文,演义论文,典型论文,性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认为:《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传统的“奸贼典型”论与近年来兴起的“又奸又雄”论,以及影视剧编导中的无往而不奸的编演模式,不仅没有如实反映出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而且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国志演义》中曹操形象实际上已经达到的美学高度。文章用“美恶并举,有贬有褒”、“主次变换,重心转移”、“善恶难辨,亦美亦丑”三部分,详细论证了曹操性格的二重性、流动性、模糊性。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本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统一的乱世英雄。但历来被视为“奸贼的典型”。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曾说他“假忠欺世”,“万古贼奸”;毛宗岗更斥之为“一生奸伪,如鬼如蜮”,“是千古第一奸雄”。直到今天,不仅一般读者把曹操看作反面人物,就是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曹操奸诈,一举一动都露出一副奸诈相”,“罗贯中用斥责和讥笑的态度描绘出一个令人厌恶的曹操形象”。这些看法,把一个本来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简单化、绝对化了,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国志演义》实际上已经达到的美学高度。学术界虽有人早已意识到曹操性格的复杂性,但其所论,往往是把“奸雄”二字释为又“奸”又“雄”,对所谓“奸”与“雄”,即“奸诈性格”与“雄才大略”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机械的、静态的罗列,因而也未能很好阐明曹操性格的复杂性。现趁电视剧《三国演义》连续播放之机,对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进行一番详细论证,来同广大编导、观众及学界同仁交流、讨论。
美恶并举 有贬有褒
刘备曾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为使曹操与刘备在这些方面形成鲜明对照,《三国志演义》确实写了不少曹操的急、暴、谲,诸如:故杀吕伯奢,兴兵报父仇,借头压军心,许田迎众贺,假手杀祢衡,肢解吉太医,族灭董国舅,勒杀董贵妃,横槊刺刘馥,许都纵火案,忌恨杀杨修,多疑杀华佗,以及为称魏公、魏王而杀荀攸、荀攸、崔琰、伏皇后、伏完、穆顺、赵俨等,并对此类欺君、诡诈、残暴、利己的言行,直言不讳地予以贬斥:“此是曹操奸雄处”,“此是曹操平生最不是处”。
但是,上述丑德恶行,并不是曹操性格描写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曹操性格元素中,事实上还存在着与欺君、诡诈、残暴、利己截然相反的另一极表现。不信请看:
十常侍专权时,“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曹操提出先正君位,然后图贼,忠义凛然,顺乎民意。董卓纵横朝廷,残害百姓。曹操先是自告奋勇冒险刺杀董卓,后又发矫诏会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扶汉救民,既忠且义。破下丕俘陈宫后,曹操本有“留恋之心”,无奈陈宫愤然下楼就戮,士兵“牵之不住”,曹操只得“起身泣而送之”,并令“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恩养。怠慢者斩!”罗贯中不仅特意用小字补注后事:“后曹公养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而且热情赞颂说:“此乃曹公之德也。”可是,到了毛宗岗修改本《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小字补注不见了,“回许都吾府中恩养”被篡改成“回许都养老”,然后斥“德”为“诈”,大骂曹操“假惺惺”,“一味权诈”,“真狼人哉”!简直令人视之瞠目!关羽降曹后,曹操待之甚厚。关羽不辞而别,“诸将皆不平”,意欲“赶上诛之”。曹操坚持守信不追,“使归其主,以全其义”。对此,裴松之等人均认为“斯实曹氏之休美”。罗贯中也深怀同感,他把曹操“不追关公”和“不杀玄德”两件事联系起来,实事求是地评论说:“可见的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毛宗岗不以为然,不仅删去这些称颂,而且巧言舌辩:“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说曹操“虽似君子而终怀小人之心”,实在令人难以信服。官渡破绍后,在袁绍图书中发现一束许都官员和曹军将士私通袁绍的书信。荀攸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并“尽皆将书焚之,遂不再问”。对此,罗贯中引史官赞诗说:“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并认为这是曹操后来能得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围攻冀州时,敌将发老弱残兵及妇女小孩出降,以解城中饥色。曹操知百姓欲“就食”,便让其到自己后军中去讨粮食。破城后,又下令:“河北居民遭兵军之难,尽免今年租赋。”显系恤民、爱民之举。如果把曹操作为一个军事家来考察,我们更会发现:曹操戎马生涯三十余载,虽曾有过濮阳、宛城之败,赤壁、潼关之窘,还算不上是常胜将军。但在平徐淮,战官渡,征柳城,击当阳,讨关西,算合肥,解襄、樊等大战役中,不仅表现了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深通韬略的指挥天才、从谏如流的统帅风度,而且通过驱兵百万,南征北战,为抑制汉末封建割据的恶性发展,促成由乱而治的天下一统,作出了千古不磨的历史性贡献。关于这一点,曹操自己所说“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决非吹嘘不实之词。
从上述一类表现中,我们完全可以窥见曹操性格的另一大系列:忠君、诚实、宽厚、仁慈、重义、爱才、勇敢、多智等。它们与刘备所说的急、暴、谲,同样都是曹操性格的基本要素。曹操性格的整体,就是由这正、负两个系列中那些看来是水火不相容的多种元素组成的一组组组合单元,即欺君与忠君、诡谲与诚实、残暴与仁慈、义气与不义、爱才与忌才、愚蠢与多智、胆怯与勇敢、利己与大公、罪过与功德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庞大系统。毛宗岗等人批评《三国演义》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竭力夸大曹操性格系统中的负极因素,并把这丰富、复杂的性格系统片面归结为一个“奸”字。如果我们今天仍象过去那样用单侧面的观察方法来观察曹操性格,用传统的“奸贼典型”论来编导和表演曹操形象,那就只能造成对曹操形象的片面肢解。曹操在《三国志演义》中第一次出现时,作者还曾介绍说:“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智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除“论赵高”一句略含贬意外,其余都是热情赞赏。曹操气绝身亡后,作者的盖棺定论也是有贬有褒。贬词所言“丑恶”,一是“秉圭升玉辇,带剑上金銮”;二是“杀人虚堕泪,对客强追欢”。仅仅如此而已。而褒词所讲“功德”,却涉及很多方面,诸如生活作风上的“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待士用人上的“知人善察”,“随能任使”;文采风度上的“登高必赋,对景必诗”;沙场征战中的“运筹演谋”,“芟刈群雄”;初露头角时的“胸蟠星斗气凌云”;老大将终时的“总御皇机,克成洪业”。结论是:“明略最优”——“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功德”最大——“当时若使无公在,未必山河几处分”。这些画龙点睛式的盖棺定论与作者赖以立论的大量描写,都告诉我们:《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作者对曹操的态度不只是善恶并举,有贬有褒,而且在用盖棺定论对其一生作整体性评价时还是功大于过,褒多于贬的。这似乎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后世读者和编导的足够注意。
主次变换 重心转移
一分为多,多又合而为一,构成了曹操性格的整体。但是,这种合,并不是美丑、善恶、长处短处的机械相加和等量组合,而是一种有重心的、流动着的辩证组合。
所谓有重心的组合,是指人物性格虽因元素本身的不同性质而呈现出双向性,但总有一种性格元素处于性格组合单元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每个二极组合单元总是表现出自身的定向性。所谓流动着的组合,是指人物性格组合单元虽因重心不同而呈现出某种定向性,但这种定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而必然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中呈现出主次变换、重心转移的历史差异性。曹操一生不同时期的性格特点,就是由这种有重心的、流动着的辩证组合体现出来的。
在《三国志演义》前三十则中,曹操虽有幼年诈风,欺父欺叔;故杀吕伯奢,“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徐州报父仇,“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的丑德恶行,但其性格的主要特征却是仗义除奸,匡扶汉室。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十常侍、董卓及其余党李傕、郭汜的对立面,不仅未见丝毫篡逆之心,而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忠直感人、谋略超人、胆量过人的汉朝忠臣。就是“移驾幸许都”,其缘起也是出于为汉朝廷、汉皇帝着想。书中明明写道:“帝在洛阳,百事未备,城廓崩倒,欲修未能”。李傕、郭汜兵临洛阳,献帝便产生了离洛阳,“投曹操”的想法,而且事实上已带领百官,步出洛阳,“望山东而进”。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提出“许都地近鲁阳,城廓宫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矣,可幸銮舆”,正合献帝之意,解了朝廷之危。况且首倡徙驾迁都者,并非曹操,而是董昭、荀彧等大臣、谋士。曹操不过是在他们多次劝说下,由疑而“决”,“决”而遂行的。毛宗岗妄言迁都之策“非为朝廷,专为曹操”,说“操之迁帝许都,与卓之迁帝长安,傕、汜之迁帝坞,无以异也”,不过是用一种主观臆断的“奸绝”偏见,来硬套此时的曹操罢了。
移驾许都后,曹操位高忘义,权欲薰心,“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出入朝廷“长带铁甲军马数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一切“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把自己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而君臣、上下、左右、朝野的不满,又促使他把一切聪明才智都用作保护自己、战胜对手的精神武器,从而使奸、谲、暴逐渐上升为他性格中的主导因素。但是,这只是就曹操性格运动在移驾幸许都以后的大致趋势而言的。如果深入到作品实际中加以具体考察,我们则会看到移驾许都后不同时期曹操性格的一些更为复杂的动态组合情况。
赤壁之战前,曹操身受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对来自皇帝及保皇大臣们的威胁,曹操起初虽有疑虑,但无实据。当他察觉“众皆”不满,发现皇帝与董承密谋害己,搜出衣带诏后,便立即产生“诛其君而吊其民,择有德者而立之”的想法。后虽因谋士劝阻,没有付诸行动,但却杀了一批密谋害己的保皇大臣,并明确宣布:“但有外戚内族,不曾禀奉于吾,辄入宫门者,腰斩之。守御不严者,罪同。”从这以后,汉献帝便成了一个傀儡,曹操对他确实再也无忠心可言。曹操与袁绍、袁术、孙策、孙权、吕布、刘备等人之间的矛盾斗争,表面也象忠奸矛盾,因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袁、孙、刘、吕动不动就斥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罪恶“甚如王莽、董卓”。实际上,袁术率先“淮南称帝”,袁绍“亦有篡国之心”,孙氏兄弟均有“据江东”,“建号帝王”之意,刘备也是以扶汉室为幌子与曹操争王天下。两方之间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忠奸之别。《三国志演义》写曹操与袁、孙、刘、吕的军事争斗,也并不是为了表现曹操对汉朝廷和汉皇帝的忠奸与否,而主要是通过曹操破袁绍、擒吕布、驱孙权、逐刘备,突出曹操的多智谋,善用兵。至于面对部下和士民的不信任情绪,曹操采取了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的策略。其中除对“裸体骂曹操”的祢衡借刀杀之;因误听谗言而把孔融“灭夷其族”;明知蔡瑁、张允是“谄佞之徒”,反加以显官“权且用之”,打算“成事之后,便当杀戮”以外,其余均能以诚相待,施之以仁,如留恋陈宫,恩养其母;厚待关羽,言而守信;恭迎许攸,信而不疑;尽焚私书,通袁不究;抚民忧民,罢兵冀州;赈济降民,以解饥色;收复冀州,尽免租赋等,因而“贤俊多妇”,百姓感服。对此,不仅曹操手下人称赞其“至心待人,推诚而行”,“恩之所加,皆过其望”,就是他的敌人,也是承认和深惧的。这三个方面的情况,说明赤壁之战前,虽然对汉献帝奸而不忠已愈来愈成为曹操性格的显著特点,但在暴与仁、谲与诚、急与宽、愚与智这些二极组合单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还不是急、暴、谲、愚,而是宽、仁、诚、智。也就是说,宽厚、仁慈、诚实、多智,也是这时期曹操性格的突出特点。
但是,当扫平中原,旌麾南指,孙权、刘备皆胆战心寒,终日不安时,曹操便有点利令智昏,骄傲轻敌了。周瑜连施反间计、诈降计、连环计,他都中了圈套。自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还得意忘形,饮酒作乐。程昱、荀攸几次劝他“提防火攻”,他摆出一副“明天时”、“察地理”、“知兵法”的姿态置之不理。直到黄盖战船逼近,程昱再谏“来船必诈”时,他才以之为“然”,急命“去止”,但是已经无法挽回了。“盈江战舰一时空”,自家败走华容道。他显然不是败在物质力量的弱和少上,而是败在战役指挥的骄与愚上。在愚与智这组二极组合单元中,智此时已退居到性格矛盾的次要和服从地位,而骄与愚却反宾为主,成为这一性格单元中的主导因素。
赤壁之战后,曹操虽然“心中尝欲雪赤壁之恨”,但三国鼎足之势已成,要想在短时间内吃掉孙、刘,统一天下,已不可能,便陶醉在以往的丰功伟绩之中。自恃功高,傲视天下的心理,加上失去政权、军权必为人所害的忧虑,促使他权欲更增。刚刚当众表白完“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一转眼却要封魏公,加“九锡”;称魏王,造王宫,并为此接连杀害了好心劝阻的荀彧、荀攸、崔琰和竭力反对的伏皇后、伏完、穆顺、赵俨,逼迫汉献帝立自己女儿为正宫皇后。还杀了站在红旗下的朝官三百人、才高如己的杨修、闻名华夏的神医华佗等。这都可说明,赤壁大战后,曹操才在政治斗争中充分显现了自己性格中的欺君、残暴的一面。
以上分析,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说,忠、诚、宽、仁、智与奸、谲、急、暴、蠢,都曾在曹操的性格系统中占有过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尤以欺君、诡谲、爱才、多智给读者的印象最深。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曾在曹操一生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和核心地位,更不是曹操性格中的唯一元素。性格组成多元素、多特点;主导性格随天走,随地变:有忠有奸,时忠时奸;有诚有谲,时诚时谲;有仁有暴,时仁时暴;有智有愚,时智时愚。或忠显而奸隐,或奸显而忠隐;或诚主而谲副,或谲主而诚副;或仁多而暴少,或暴多而仁少;或智强而愚弱,或愚强而智弱。性格整体中包含着多种元素组成的多组单元;每组单元之中的正反两极总有一极处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性格重心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异、流动;性格重心的变异、流动形成了各个时期性格的不同特点。这就是曹操一生性格的有机整体性和辩证复杂性,一个简单化的“奸”字,一个类型化的“奸贼典型”的结论,一个无往而不奸的表演模式,是无法揭示出曹操一生性格的丰富内涵,无法表现出曹操性格的复杂多变的。
善恶难辨 亦美亦丑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些性格现象,都是一眼就可判断出美丑善恶的。但是,象现实人生和活人言行中本来就存在着大量模糊现象一样,罗贯中为我们提供的有关曹操性格的所有信息,并不都是具有明确定性的,有相当一部分人们至今也很难准确道出它们的美丑善恶。它们好象似善又非善,让你说不上美,也说不上丑。这是曹操性格复杂性的又一不可忽视的表现。
罗贯中在曹操首次出场时曾介绍说,“操年幼时”,汝南名士许邵评论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喜而谢之”。对此,毛宗岗在其修改本中批评道:“邵意在后一语,操喜,亦喜在后一语。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称之为奸雄而大喜,大喜便是真正奸雄。”这显然有些武断。因为说“治世能臣”也好,“乱世奸雄”也好,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承认曹操聪明、多智。这种性格元素,虽对曹操后来成为奸中之雄,起了重要作用,但本身并无美丑善恶可言。用于“乱世”,能成为奸中之雄;用于“治世”,可成为能干的大臣。用在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上,可造福国家民族;用在于国于民有损的事情上,可祸国殃民。体现在好人身上,被誉为足智多谋;体现在坏人身上,被斥为阴谋诡计。年尚幼的曹操听后“喜”之,并不一定是喜在预见自己将来能成为奸中之雄上,而恐怕是喜在这两句话实际包含的承认自己聪明多智上。因而只能说是一种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模糊之喜。
建安三年四月,曹操进兵荆州,沿途看见“麦已苍黄”,便命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作践者,并皆斩首”。这显然具有明显的爱民性质。不料自己的马却因受惊,践倒小麦,他便“割发权代首”,以示惩戒。对此,罗贯中借史官之口评论说:“此乃曹操能用心术耳。”毛宗岗则一会儿说“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一会儿又连声嗟叹:“权诈可爱”!“权诈可爱”!今人对曹操此举也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这情况就是由割发代首本身的模糊性质造成的。从它与驾驭军队的关系来看,似乎含有借之欲申军令的“权诈”成份;但作为一军之帅能以对自己实际上是最大限度的惩罚,来表示护麦的善心和决心,又是难能可贵的。所以《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说:“老瞒自刎割发等事,似同儿戏,然万军悚然,兆民受福则实事也。”我们切不可用单侧面观察方法看待这种含有二重意义的模糊现象。
建安十年正月,兵进南皮时,河道尽冻,粮船不通,曹操欲让百姓敲冰拉船。百姓皆望深山而逃。曹操大怒,下令:“捕得百姓来,斩之!”但当百姓闻之,纷纷主动前往曹操营帐投首时,曹操却对百姓说:“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无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军士擒之。”罗贯中在此加了一行小字注:“此操之奸雄也。”毛宗岗更视此为“奸雄之极”。其实,曹操的所言所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质,并不纯粹是出于欺诈和玩弄权术,而是不杀令已出、欲杀又不忍两种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仁心”与欺诈两极因素兼而有之的模糊组合。
赤壁大败,逃归南郡,曹操“仰天大恸”哭郭嘉。众将问他“此哭何意”,他回答说:“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并越哭越伤心,致使“众皆默然”。对此,罗贯中在引了史官诗评“曹公深识真梁栋,兵败犹然想郭嘉”后说:“此时深赞郭嘉之才,可惜先亡,以致操深思痛哭于中夜。”毛宗岗针锋相对:“哭死的与活的看”,“胜似打”,“奸甚”!其实,“大失”思郭嘉和惨败怨众将,在当时的曹操,都是情之自然。真心与假意,善心与恶意,在这里是巧妙糅合在一起的。
曹操晚年,东吴孙权,侍中陈群,尚书桓阶,部将夏侯淳,都曾劝他早登帝位。曹操坚持不肯,说“位至于王,于身足矣”,“苟天命在孤,孤即周文王矣”。对于曹操不轻易称帝的想法和做法,罗贯中曾借司马光之口评论说:“操欲篡位久矣,犹畏其名而不敢行,故意愿为周文王也。”毛宗岗更进一步说曹操是有意“以篡逆之事留与曹丕”,因而更显其奸。其实,曹操至死坚持不称帝,既有“奸”的一面,也有“德”的一面。因为他毕竟没有最后突破君臣界限,做出以臣废君,篡位称尊的事情。所以,“宋贤赞曹操功德”说:“虽秉权衡欺弱主,尚存礼义效周文。”
总之,如果说性格的多元素多组合,给曹操性格带来的特征是二重性;不同时期的变化发展,又使其性格呈现出了主次易位的流动性,因而我们不宜用单一的、静止的分析方法对曹操不同时期的性格整体作任何片面的、固定的归结的话,那么某些性格现象的模糊性质,给曹操性格带来的另一个特征便是朦胧性。对于这一类模糊现象,我们切不可追求抽象思维的精确性,一定要把问题说得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那样反而会距离形象的实质、人物的性格更远。毛宗岗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是值得我们后人引以为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