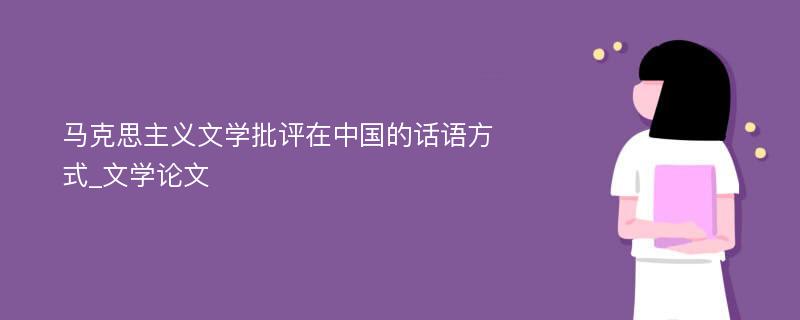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为依据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制约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
一、文学批评的不同言说方式
文学批评是对作家艺术家、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现象进行判别评价的实践和理论。它是批评家或者相关评论者对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一种审美感受、价值判断和态度表达的言说。这种言说包含着审美感受、价值判断和态度表达的话语和文本。正因为审美感受、价值判断和态度表达都是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和地域性的,所以,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言说,它的言说方式是随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而变化发展的。因此,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不仅有中西之分,也有古今之别,还有阶级之差。
从总体上来看,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中西之分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直觉感悟的体悟,西方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理性分析的阐释;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古今之别主要在于:古典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一言堂、一元化、舆论一律的独语或者自言自语,现代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则主要是一种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百家争鸣的对话或者交流沟通;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阶级之差主要在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一己私利、独断专行、遮蔽真情的矫饰或者言不由衷,人民大众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却是大公无私、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坦言或者直抒胸臆。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应该多方面地考虑这些民族差异、时代差别、阶级区分,不过,在今天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民族差异,或者简单说,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中西差异却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方面。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之间求得一种和谐平衡的协调关系。
一般而言,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理性分析的阐释。它注重的是,从某种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出发,对作家艺术家、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现象进行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演绎归纳的逻辑分析,从而得出符合这种理论框架、基本原理、立场观点的判别评价,或者印证和扩展这种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这种言说方式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就已经形成雏形。柏拉图关于文学艺术的一系列对话,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基本上就是为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建构起来的文艺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诗学》是在总结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和悲剧等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实践而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其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作为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理论总结,形成了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标本。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又来源于他的老师柏拉图。柏拉图就是从理念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来批评文学艺术作为“摹仿”的非真实性,而且他的一些文艺对话录就是以老师苏格拉底与像伊安这样的诗人、理论家的对话批评构成的,或者可以说也就是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本人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实践的记录,也就是运用自己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包括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来进行批评实践的概括化记录。尽管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很少对作家艺术家、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的批评,但是,对于文学艺术现象的规律、本质、特征、起源、发展、功能、构成等等都进行了理性分析的阐释,给后人进行文学批评造就了理论框架、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古罗马时代贺拉斯就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圭臬和准绳来进行批评实践。他的《诗艺》,实际上就是贺拉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对古罗马的文学艺术创作进行一般性批评的理论概括。古罗马晚期的普罗丁(一译普罗提诺)则是运用柏拉图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融合基督教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立场观点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在涉及文学艺术现象的部分论说之中显示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新柏拉图主义的言说方式被圣奥古斯丁充分发挥,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言说方式则被圣托马斯·阿奎那所发扬到极致。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关于自己年轻时代文学艺术活动的忏悔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批评,其言说方式也就是以新柏拉图主义的美学和文论来反省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主要是一种理性分析的阐释。因此,在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往往是二位一体的:文学理论是文学批评的根据和准则,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阐发和运用;一个是理性的准则,一个是理性的阐释。这种情况在17、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文学艺术思潮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法国美学家和文论家布瓦罗的《诗的艺术》既是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法典,也是新古典主义批评实践的结晶。其中所谓“三一律”就是一种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二位一体的典型。它几乎成为了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标志,同时它又是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标尺。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和文论家莱辛的《汉堡剧评》,应该说是典型的文学批评文本,但是它同时也是莱辛戏剧美学思想的理论表述。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汉堡剧评》的言说方式就是理性分析的阐释,每一篇剧评都是从一部具体的戏剧作品的分析之中得出某种美学观点和文论观点,或者是作者实际上就是以具体的戏剧作品的分析来阐释自己的戏剧美学思想。莱辛的《拉奥孔》就更是如此了。它从《拉奥孔》的雕塑作品的具体分析,批判温克尔曼的新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阐释他自己的启蒙主义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从启蒙主义美学和文论及其文学批评开始,这种理性分析的阐释式言说方式就完全定型和成熟,以后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以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进行理性分析揭示矛盾而达到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形成了一种“剥葱头”式的发展态势,不断以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否定另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大体上来看,启蒙主义美学和文论及其文学批评内在地孕育了现实主义(莱辛、狄德罗、青年歌德)和浪漫主义(卢梭、赫尔德、青年席勒)的文学批评流派,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前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否定了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否定了浪漫主义文学批评,20世纪60年代之前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否定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评,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否定了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甚至连文学艺术本身都在文本化和不确定性的否定之中给消解了。因此,西方文学艺术和文学批评就这样被“剥葱头”而“终结了”,只剩下了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异延”和“播撒”及其“痕迹”。它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非理性主义的,但是实质上却是一种极端的理性主义。
与此相反,一般说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则是直觉感悟的体悟。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基本上没有完整体系的鸿篇巨制,即使是《文心雕龙》那样的大部头著作,看上去非常完整、全面,可是它主要仍然是对文学创作现象的体悟,运用的仍然是中国《周易》式的“象思维”和“喻叙述”或者“象喻”和“比兴”言说方式。刘勰为了他说理的象喻化、比兴化,在《文心雕龙》的整体建构上,以人体比拟文体的直觉体悟的方式,构建了一套所谓“剖情析采”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其中作为核心的“剖情析采”的创作论最为典型地运用了比兴之法和象喻之思。刘勰以人体比附文体,对应于人体之神明、骨鲠、肌肤和声气,就是文体的情志、事义、辞采和宫商。人以神明为主,相应文就以情志为先。以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情志问题,相应地形成了位体与含风的问题,这就是所谓风格论。相对于人体的骨鲠,文体要有事义,这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事义与树骨问题的关联,提出了附辞会义和据事类义,形成了所谓文骨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题材论。就像人体仪表的美在于肌肤,文体形式的美同样就在于辞采,这就是修饰文学作品仪表的修辞问题,构建了所谓的辞藻论。人体的声气,似同于文体的宫商,追求文学作品的语调辞气的美,当然不能不研习调协声律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体势论。此外,《文心雕龙》之中的比兴象喻的语言和直觉感悟的体验,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它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的直觉顿悟、象喻妙悟、意念觉悟的言说方式,大体上构建了唐宋之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除了《文心雕龙》这样的个别鸿篇巨制的特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主要就是直觉感悟的体悟,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文本形式就基本上没有体系化、逻辑化和完整化的理论著作,主要是语录、对话、信简、序跋、札记、笔记、诗话、词话、曲话、点评、注解、传注。《论语》中关于《诗》的一些片言只语,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些典型的文学批评话语或文本,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却是儒家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直觉感悟的体悟式表达;它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理性分析的阐释,却内在地蕴含着孔子的儒家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它是以比兴和象喻的方式言说出来的,却具有直接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尤其是把这些片言只语或者即兴对话放在特定的语境之中,或者经过了历代学者贤人的注释传注,就是言简意赅、微言大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学批评的实践和理论。这就形成了在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儒家文学批评理论的注解、注释、笺注、传注、注疏等等“滚雪球”式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感性化理论表述。像《十三经注疏》中关于《诗经》的注解、注释、笺注、传注、注疏,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文本形式和理论形式。先秦文学批评,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文学批评,散布于先秦的经史子集的浩瀚文献之中,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先秦诸子著作,都是在有关“仁”、“道”之类的哲学伦理问题的叙述时顺便论及文学批评问题,因而孔孟等人的儒家文学批评思想、老庄的道家文学批评思想,都不是一目了然的理论系统,而是后来的研究者们进行注解、注释、笺注、传注、注疏,而逐步滚雪球形成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文学批评意识觉醒自觉的时期,这时出现了许多专门化的甚至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和文论思想论著,像《毛诗序》,王逸《楚辞章句序》,曹丕《典论论文》,阮籍《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陆机《文赋》,卫夫人《笔阵图》,郭璞《山海经序》,王羲之《论书》,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谢赫《古画品录》,乃至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这些论著探讨了诗、画、书等艺术的具体问题,以十分感性的方式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研讨了作家艺术家、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现象。因此,中国审美意识和文学批评思想的自觉化就是主要表现在对文学艺术具体问题的直觉感悟的体悟,却没有文学批评思想体系的完整建构。这种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一直绵延到近代鸦片战争以前。这种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传统,经过隋唐五代、宋金元,直至明、清,一直没有根本改观,即使一些比较大型的诗话论著、小说评点、论画作品也依然承守旧制,严羽的《沧浪诗话》,胡应麟的《诗薮》,金圣叹、毛宗岗的小说评点集录,李渔的《闲情偶寄》,叶燮的《原诗》,袁枚的《随园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直至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都不是体系化的思辨性的形而上归纳或演绎。更有甚者,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论著有大量的诗词体的作品,像陆机的《文赋》,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李白、杜甫的论诗绝句,元好问的论诗诗等等,它们本身就是诗性智慧的结晶,充满着比兴、象喻、形象化、诗意化的言说。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为依据的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因此,它的言说方式也应该在这二者之间寻找一种最佳的结合方式,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
二、以直觉感悟的体悟为根基
作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土壤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当然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直觉感悟的体悟为根基。这是一种文化基因的决定和制约,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本土以前,由于西方文化及其文学批评和理论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强制入侵,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理论似乎表面上哑然失语,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如梁启超和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人,就自觉地接受和运用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及其言说方式来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和建构文学批评理论。但是,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依然决定和制约着他们的批评活动和理论建构。像梁启超和王国维,他们都自觉地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阐述自己的批评观和进行批评实践。梁启超对小说文体的推崇,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运用西方美学和文论的理论框架、学说观点、基本原理来进行的,然而他们的言说方式从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传统批评的直觉感悟的体悟方式,不仅采用了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叙述语言,而且《饮冰室诗话》、《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等仍然是采用了中国传统批评的札记、随感、诗话、词话的形式。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蔡元培的《赖斐尔(欧洲美术小史第一)》,甚至后来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朱光潜的《谈美》和《论文学》,乃至钱钟书的《管锥篇》、《谈艺录》,也都是如此。就是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文学语言的常态言说方式以后,20世纪30年代前后所兴起的也主要是一种感悟式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批评,像沈雁冰(茅盾)、李健吾、李长之、沈从文等人的感悟式的“体验批评”就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①。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述言说方式的影子。这些都表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直觉感悟的体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基因。
这种直觉感悟的言说方式的优长之处就在于,它是以批评家的艺术感受力为起点,以文学艺术的文本和现象的体悟为依托,把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建基于文艺欣赏的体验和感悟之上,因而是从文学艺术的实际存在之中生发出审美判断和艺术评价,避免了抽象议论和空泛演绎,是一种诗性智慧的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具有一种艺术感染力。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就是如此。文章开篇就引用了一首俄罗斯的诗歌来阐明俄罗斯文学的特征:“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俄国有一首诗,最为俄人所爱读,诗曰:俄国犹大洋,文人其洪涛;洋海起横流,洪涛为之导。俄民犹一身,文人其神脑;自由受摧伤,感痛脑独早。此诗最足道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二者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这种以诗论文的方式是最为直观入思的比兴方式,使人直接感悟体验到现象的本质。李大钊文章之中还到处可以见到比兴的运思方式,如他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②这里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自由之警钟”,“革命之先声”,就形象生动地阐明了俄罗斯文学的社会色彩浓厚特征,让人感同身受,如历历在目,似声声在耳。像这样的直觉感悟的体悟批评文字在这篇文章中处处皆是,不胜枚举。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曹丕《典论·论文》的比兴、气势和体悟:“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③像这样把文学创作现象描绘得如此生动形象,声情并茂,活灵活现的文学批评文字,恐怕也只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能够达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当然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直觉感悟的体悟式言说方式,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的魅力。
这种直觉感悟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之所以能够显示出这些优长之处,就因为它充分地发挥了批评主体的审美感受力、艺术鉴赏力、诗意表现力,同时又是从文学艺术文本的实际存在出发进行的,从而是以审美欣赏为基础的,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定义、原则出发的演绎推理。这样的直觉感悟的体悟方式就可以直接以审美的方式穿透艺术作品本身,达到一种“现象学还原”,从而不离开文学艺术的意象世界本身,直接揭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文学艺术作品的本真状态、文学艺术现象的真谛,同时它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文学艺术文本,以审美的方式沟通了世界、创作者、作品、接受者这些文学艺术的构成因素,让接受者在审美和艺术的氛围之中感受到现实世界、创作者的意象世界、文本的形象世界、批评者再创造的审美世界,因而更加直接形象地把握艺术世界及其所呈现的现实世界的本质。
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就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先河,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底蕴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试看其中的一节:“当十九世纪全期,社会的政治的动机流行于俄国诗歌之中。有名普希金者,人称‘俄国诗界无冠之帝王’,尝作一诗,题曰‘自由歌’(现通译为《自由颂》——编者)。其诗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辈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此外尚有一大诗人莱蒙托夫,于普希金氏失败于悲剧的决斗之后,有所著作,吐露其光芒万丈之气焰,以献于此故去诗人高贵血痕之前,痛詈贪婪之群小环绕于摧残自由与时代精神之皇位侧者。同时又有雷列耶夫氏,于其思想中唤起多数为自由而死之战士,诗中有云‘我运命之神,憎恶奴隶与暴君’等,可以见其思想之一斑。赫尔岑氏之友人,有称奥加辽夫者,于一八四八年高声祝贺革命风云之突起。此一骚动,促人奋起于安泰之境,扬正义而抑贪欲,其光明一如纯粹之理性。一八四九年,此诗人之心,几为革命破灭、专制奏凯歌之光景所伤透,穷愁抑郁,常发悲叹。是年,氏尝为伤心之语曰:‘欧洲之大,曾无一单纯之所,为吾人可以达其生活于光明和平之状态者。’但自兹十年后,此先圣之心理,又从过去之星霜以俱消。是时氏复告赫尔岑氏曰:昔时方童稚,品性温如玉。忽忽已少年,激情不可屈。韶光催人老,渐知邻衰朽,入耳有所闻,始终惟一语;一语夫惟何?自由复自由。音义在天壤,煌煌垂永久。并乞其友于临终之际,勿令其尸骸已寒,而不以最终神圣之一语细语于其耳边。其语惟何?曰:‘自由!自由!’”④读这一段文字真可以让人热血沸腾,亲炙俄罗斯社会的生动光景,深刻把握俄罗斯文学与革命的血肉联系,从而感悟俄罗斯文学的浓厚社会色彩。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不足之处。那就是,由于缺乏完整、系统、逻辑的理性分析,诉诸随感、书信、札记、诗话、词话、曲话、评点等文体形式,从而显得零碎、散乱、模糊,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学说观点的阐发。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理性分析的阐释,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即保留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优长之处,又能克服它的不足之处。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也可以视为这种典范之作。
三、结合理性分析的阐释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还应该结合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分析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初产生和发展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一种现代形式。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为依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自然应该融合西方文学批评重视理性分析的阐释的言说方式。
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讲究理性分析的阐释,追求文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学说观点的系统、完整、逻辑严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而且更加表征出一种革命性变革,即追求现实社会实践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写出文学批评理论的鸿篇巨制,但是,从他们关于文学批评的一些书信和相关论述来看,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是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坚持实践本体论的文学本体论,把文学艺术视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即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坚持实践认识论的文学掌握论,把文学艺术看做一种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即“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坚持实践价值论的文学意识形态论,把文学艺术当做整个社会构成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主张无产阶级的倾向性,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精神,即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化”;坚持实践辩证法,科学处理文学艺术及其批评中的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美学与历史、倾向性与艺术性等等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具有现实社会实践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理性分析的言说方式,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整体传入中国就已经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并且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的最早代表就是李大钊。如上所述,他写于1918年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先声,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直觉感悟的体悟言说方式,而且也继承和发扬了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分析的阐释言说方式,同时还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社会实践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理性分析言说方式。在此文中李大钊分析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和诗人的人道主义特征和革命精神时说道:“此时之诗人,重视为公众幸福之奋斗,而以个人幸福为轻。就中有一诗人,尝训示青年曰:‘离尔父母,勿建巢居,其独立自营……第一须于尔灵魂中扑灭情欲,其冷酷无情于恋爱、财富、荣誉之诱惑,其庄严神圣……保尔心之自然与清粹于尔胸中,然后全以授之于尔不幸之同胞。尔闻悲叹之处,尔往焉……比大众多受艰苦……留得清贫与明白。然则尔将成为伟大,举世将为尔叱责之声所扰。’俄人于此无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而有革命的禁欲主义。自我之畀赋,全为竞争,全为奋斗,故其时之诗歌实为革命的宣言,读者亦以是目之。杜勃罗留波夫者,诗人而评论家也。其诗句颇足状此派抒情诗家之精神,诗云:死别告吾友,杀身为忠厚。深信故国人,常忆吾所受。死别告吾友,吾魂静以穆。冀尔从我行,享尔以多福。简要、鲜明、平易,全足以表示此时俄国青年之心理,此心理与现代中产阶级精神之精密复杂相去远甚。”⑤这里的分析是充分理性的,逻辑严密的,渗透了阶级分析的精神,在直觉感悟的基础上升华为理性分析的阐释。这一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轶文的发现,给我们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言说方式的先驱、先声和先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社会实践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理性分析方法的另一个典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他发表于1933年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性分析的阐释的范文,它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社会实践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联系起来进行了入木三分,切中肯綮,准确精到的分析。我们来看看瞿秋白对于“席勒化”的分析。
瞿秋白写得十分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和拉萨尔辩论过文艺上的问题,他们说:不应当‘塞勒(即席勒一引者按)化’,而应当‘莎士比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据梅林的解释,仿佛他们两个人的私人的兴趣,不大喜欢塞勒的作品了,而喜欢莎士比亚。这种解释显然是错误的。把莎士比亚和塞勒对立起来,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原则上的意义的。这就是鼓励现实主义,而反对浅薄的浪漫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在这里瞿秋白反对梅林的解释,提出了自己的明确观点,即“席勒化”就是浅薄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或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而“莎士比亚化”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现实主义文学。接着他以席勒作品的具体分析来进行论证:“塞勒晚年的作品,他的小说里和戏剧里的‘英雄’——只不过是主观的抽象的‘思想’的号筒:对于塞勒,所谓斗争只不过是‘世界史上的人物’之间的热闹的决斗,这些‘世界史上的人物’仿佛代表着历史的力量,他们之间的决斗就代表着历史的冲突,那算是决定一切的动力,那算是社会发展的要素。那时候的塞勒(当他写《堂·卡洛斯》的时期),只在希望开明的君主来做从上而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他看不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因此只在主观道德的‘伦理’方面找寻出路,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和恶,勇敢和懦弱,公德和自私等等,来支配他的作品里的‘英雄’。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塞勒化’的意义。他们所主张的是:对于事实上的阶级斗争,广大群众的历史斗争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他们要求文学之中对于这种斗争的描写,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里,就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成分。而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六日写给拉萨尔的信里说:‘人的性格不但表现在他做的是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在这一方面,我以为你那篇戏剧的思想上的内容,决不会受着什么损失,如果把各国人的性格更加鲜明的互相对立起来;用古代的风格来描写性格,在现在已经不够的了,我以为你在这里可以不受什么损害的更加注意些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最后,他得出结论:“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对‘塞勒化’和鼓励‘莎士比亚化’,是他们对于文学上的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上的意见。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第二种是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鼓励的。固然,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结算起来,也还是唯心论的现实主义;然而只要它在勇敢的观察和表现实际生活的时期之中,还能够多多少少暴露一些客观的矛盾,那就对于一般的文化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将来,可以有相当的价值。因此,譬如说罢,马克思所喜欢的作家是:荷马,丹第(即但丁—引者按),谢尔房蒂斯(即塞万提斯一引者按),莎士比亚,狄德洛,菲尔定,歌德,巴尔扎克。”⑥这里的理性分析的阐释充满了逻辑的力量,也具有社会历史的内在根据,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框架、学说观点、基本原理,具有强大的理论说服力,可以说是不刊之论,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创作精神做出了科学、全面、系统的解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真髓和本质,既有对作家艺术家、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直觉感悟的体悟,也有对作家艺术家、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理性分析的阐释,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个典范。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邓小平思想文学批评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言说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言说方式。
注释:
①王铁仙、王文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77页。
②④⑤⑥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二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499—500页,第500页,第502页,第576-577页。
③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第136页。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文艺论文; 诗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