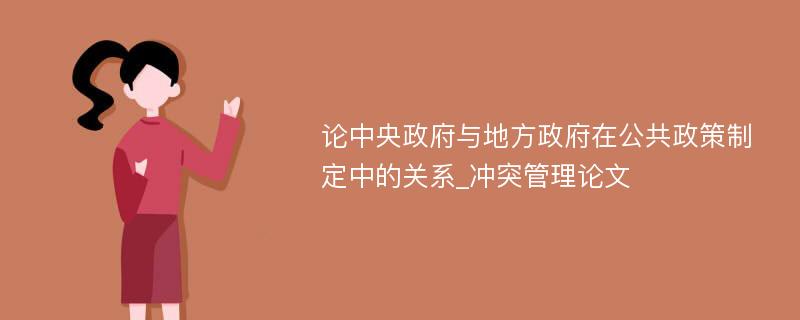
公共政策制定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中央政府论文,地方政府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内部对国家结构形式的再划分。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国家政权结构在纵向与横向之间的分布与联系就产生了。实际上,自从组织诞生以后,就有权力在不同的层次和方向上作水平或垂直的分布。权力及其结构总是组织体的相伴物。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功能差异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功能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功能的差异,无论是在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是存在的。我们暂且不作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之间的功能比较,而是分析一般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功能差异,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协调问题。
权力的作用范围不同。中央政府的作用范围能够辐射到全国范围,其政令在国土范围内具有号召性。第一,组织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的隶属性和传递性。中央政府设立总揽全国政务的中央机关,在中央机关的隶属下设立相统属的各级机构。在中央政府之外,各种核心组织、隶属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的组织体系。第二,核心权力和最高权力属于中央政府。在社会组织体系中,中央政府拥有最核心、最高的权力,一个国家社会与经济全面发展的最主要权力都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单一制国家是这样,联邦制国家也是这样。第三,中央政府权力的作用范围是全国性的,全权管理国家行政区划内的事务。对国内重大事项的处理,以及出台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都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范围。地方政府机构的最大特点是其地位的隶属性。这种隶属性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些国家的地方政府既隶属于地方立法机构,也隶属于中央政府。有的仅仅隶属于中央政府,有的仅隶属于地方立法机构。这种从纵和横两方面进行的权力分割,是地方政府权力内容和权力范围有限性的决定因素。
与这种地位隶属性相联系,地方政府在权力内容上具有一般性,在权力空间上受地域的制约。在权力的内容上,地方政府不能享有中央政府的核心权力,其权力是有限的。比如,在对外关系上,即使是非常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主权。地力政府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联系的地区密切相连,具有地方社会性的特点。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社会职能上具有非常明确的分工。我们还可以以美国政府的价格管理制度为例,来分析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具有能够影响国计民生的产品和劳务,比如,资金市场的利率(资金的价格),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信息收费,房租,以及一些重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糖、烟叶、牛奶、木材等。州政府管理能源公用事业部门的电力、石油价格,地铁、巴士、的士运价,以及过桥费、公园门票等。市政府管理一些地方性公用事业价格,如自来水、电话、排污费等。另外一些公用价格实行归口管理,如邮政资费由邮政委员会管理,航空通信收费由民航局管理,电讯、广播、电视等通讯行业收费由联邦通讯委员会管理和监督等等。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作基于功能分析基础之上的明确职能分工,是一个国家公共行政制度化的基础。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政府制度的完善是和整个市场体制的完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的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自中世纪以来市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民间社会。在这个民间社会里,受到法律保护的民众的自由和权力是社会的基础,民商事法律极为完善。政府组织作为民间社会中的一个组织,是受到民众授权、受法律程序严格制约的特殊组织,政府的行为能够得到通过代议机关和社会监督力量从多方面的监督。由于对政府权力和行为的扩张性的恐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政府的权力范围具有明确的界定,政府的政策选择被赋予更多的民众性。
但是在缺乏市民社会传统的国家里,政府的专制力量强有力的统治着社会的所有领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所有的要素都被纳入到政府的专制体系之中,没有一个始终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缺位,不仅独立的民商事行为被严厉的制约起来,而且民众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产难以被法律保护而被合法化,个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也被剥夺殆尽。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使得政府的权力不断地得到扩张,民众权利受到权力的压制,官本位成为社会唯一的分配体系和价值体系。当这样的国家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时,就面临着市场的培育和政府的退出的双重任务。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更为复杂的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一方面要让政府从不同的领域里开始撤退,放弃政府组织的全面垄断;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积极推动和培育民间力量的成长,政府的政策选择在这样的国家里具有双重的任务。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市场化改革,其艰巨性就正在于此。
二、政策冲突与政策协调
政策的实施与权力的行使是始终相比附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是权力的具体化,权力的行使必须通过政策体现出来。政策在制定与执行中的复杂性,是因为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政策总是与一定的政府职能紧密相连,职能在不同管理者和相对人之间的不同划分,使得政策的作用范围也按照一定的方向辐射,辐射面总是和职能体相重叠。从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在结构得到优化的组织体中,总是能够制定得较为正确,制定以后一般也能够得以很好的执行。任何一个政策的表现形态,无不是组织结构使然。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是权力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划分形式,但是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政策的形成机制和执行机制。在中央集权制条件下,中央政府集中国家权力是最主要的方式,地方受中央的制约,中央政府负责协调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全国性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约束力,地方所制定的政策不能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违背。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独立制定自己的政策。
不同的政策主体具有不同的政策制定权限,其所制定的政策具有不同的辐射范围,也就具有不同的影响力。按照这种不同的权力作用范围,可以将政策作进一步的划分。按照政策的不同影响力,也可以将政策作进一步的划分。这两种划分,一个是从权力体系进行划分,另一个是从影响力进行划分。
中央政策依据宏观性和微观性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全局性政策和部门性政策。全局性政策在单一制国家里一般由中央政府直接做出,在联邦制国家里由联邦政府做出,对全国所有的行业、部门和地区内的所有个人和单位具有影响力。各个行业和各个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只要是对全国范围内起作用的政策,都是全局性政策。如果各个行业和各个部门所制定的政策的作用范围仅仅局限于本部门和本行业以内,就不属于宏观性政策,而是属于微观性政策。
中央政府直接做出或者由各个部门代表中央政府做出的全局性政策,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效力的作用。这样的政策由于其本身在法律上的效力,不存在与其他政策相冲突的问题。当然,如果政策本身在实际的执行中发现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可以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修正。
微观性政策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地方性政策,由各级地方政府做出,在各自的行政范围内起作用。权力的作用范围是按照行政体系进行划分的。依据这种划分,大体上有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具有地方属性的地方政策,大都是按照各个地方的民族、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做出,是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具有微观性、针对性。
政策的直接效益就在于政策的贯彻和执行。然而,执行中的各项政策,由于其各自针对的领域、作用的范围、效力等级的不同,会发生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会产生政策作用范围的盲区。这种情况出现以后,就需要调整政策的作用对象和作用范围,增加政策的辐射性。另一方面,更多的情况是政策的冲突现象。现实中的政策冲突现象,具有很复杂的原因,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冲突。这些冲突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利益冲突的动机,而其表现形式则是各种政策主体之间的冲突。具体来看,存在着全局性政策和局部性政策、全局性政策内部之间和局部性政策内部之间的冲突。政策之间的冲突,是制度不完善的体现。制度完备的环境中,任何一个特定方面的政策都是在法定的程序中进行运作,由于制度内部不存在体制上的冲突,因此,由政策主体制定的政策一般都具有较为清晰的边界,政策之间相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在转型社会里,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政策主体之间相冲突的现象很突出,因此常常出现政策之间的冲突。这里我们着重探讨转型社会的政策冲突。
全局性政策和局部性政策之间的冲突,一般表现为中央政府政策与中央各部门政策以及与地方政府政策之间的冲突,更多的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冲突。全局性政策和局部性政策之间的冲突一般是由于中央政府放松规制产生利益多元化而造成的。在转型社会里,这种全局性和局部性政策之间的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进入转型期以前,所有的利益动机均被中央政府的强有力集权所压制,利益表现形式单一化。但是这种利益的单一化是暂时的。一旦集权体制被外来的力量所打破或者是内部产生松动,利益多元化的局面就会产生。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各个利益主体为利益动机所驱动,就会利用政策制定的机会去寻租。由于刚刚从集权体制下分解出来,独立的民间社会还没有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大都是与某一个“单位”相联系,呈现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之间利益的分化,这种单位为利益单元的局面,无疑会大大强化各单元追逐利益的行为。政策之间冲突的表现背后,是利益的冲突。这是转型国家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全局性政策与局部性政策之间的冲突,在转型国家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的法制化程度很低,政策调节的范围远远大于法规调节的范围,政策的权力范围比法规的权力范围要大得多。政策主体的作用范围要远远大于法律的作用范围,而且由于法律的实际效益被既定的制度所降低,法律的实际作用范围就更加有限。
全局性政策内部之间的冲突。中央政府不同部门所制定的政策有时也会发生冲突,由于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及在转轨过程中发生的机构改革,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会发生转移,这种职能之间的转移过程就必然会发生政策之间的冲突。这是导致中央政府政策之间相互“打架”的最主要体制原因和机制原因。而且,各部门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也会造成各个部门主体之间所制定的政策之间的冲突。另外,由于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发育和培植一个民间社会,那么,在政府开始退出的过程中,政府各部门之间原本有序的衔接也会出现无序,形成政策之间的冲突。
局部性政策内部之间的冲突。局部性政策冲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中央政府的单个部门的政策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冲突;另一种是地方政府之间政策的冲突。中央政府的单个部门的政策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冲突通常称为“条块冲突”,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冲突形式,在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转型国家里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地方实力的膨胀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几乎所有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必然出现的现象,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经济形态上,由于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没有形成,各种生产要素没有在国内市场上流通起来,各个地区之间也缺乏交流,这种地方市场的封闭性必然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地方的割据政权已经形成独立王国,在地方格局已经实体化的情况下,地方保护主义会得到强化。地方割据实力为了保护自己的狭隘利益,会不断强化这种格局,只有到各个地方实力都认识到只有打破这种割据的时候,在讨价还价的情况下,逐步形成各个地方之间的合约,在此基础上,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开始形成。另一种是在中央高度集权的情况下,由于地方官员的晋职和升迁都系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为了获得可供上级青睐的政绩,就会千方百计的打自己的小圈子,对内形成封闭的独立王国。地方保守主义最为有害的是地方政策的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的地方政策与国家宏观政策的冲突,势必导致国家整体效益的降低。而要使全局性政策与局部性政策相协调,最根本的办法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政策的影响力除了权力的影响以外,还有非权力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尽管不具备权力的强制制约力,但是却拥有很大的权威。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不同权威的政策,在实行中会对既定的行政体系构成不同的影响,形成政策的权力主体和政策的权威性之间的差异与矛盾。
政策的权力主体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主体的这种权力是通过法定的程序、通过授权而获得的,政策只能由具备资格的主体作出,其他的任何主体都没有这种权力。不具备资格的主体作出任何规范性文件都不具备效力,也就不能作为政策发挥效用。这种情况就是,没有权力的主体也是没有权威的主体。然而,我们还必须考虑另外一种情况,即一个政策主体具备法定的权力,但是却不具备权威性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情况。一般的情形是,一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机关,尽管可以制定和执行政策,但是由于其权威性不够,会明显地影响政策的正确制定,即使制定出来也会影响到政策在实施中的效力。如果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出现“执行不能”的情况,制定政策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就不仅会影响到一个已经出台的政策的实施,而且还会影响到政策主体以后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的减损是一种制度性的减损,就必然会影响到政策的权威性,导致政策群体效益的损失。因此,在现实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实践中,如何保持政策主体的权威性是保证政策的真正到位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保持一个政策主体的权威不致受损,最关键的是保持机体的活力,保证队伍的廉洁,保证工作的高效。只有具备廉洁高效条件的政府,才能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