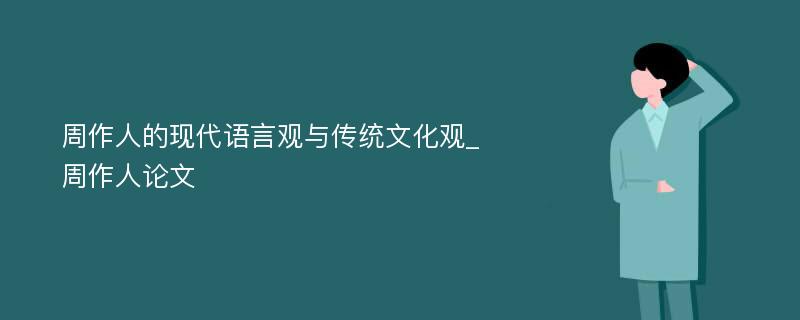
周作人的现代语言观与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周作人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的五四文学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语言革命。现代语体文的倡导者提出了种种方案和设想,然而不论是胡适、钱玄同还是陈独秀,他们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背景都来自西方。胡适认为文言是“死文字”,只有白话才能造出“活文学”,他的观点来自西方进化论的影响①。他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是以文艺复兴为参照,并在杜威实验主义思想基础上提出的②。钱玄同“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和陈独秀对“世界语运动”的执迷,则来自对“世界主义”的乐观想象③。1930年代“大众语运动”的兴起,又有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背景④。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家,周作人对于现代文学语言变革与建设也有自己的看法和构想。与上述诸人不同,他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汉代王充无分古今、不避雅俗、“适用”为贵的实用理性精神,六朝佛经翻译以“信”“达”为本、重在创造的主张,六朝骈文追求华美、重视文学语言审美特性的创作实践,启发并影响了周作人,使他的理论既顺应了时代要求,又没有背离民族文学传统,既有着丰富的内涵,又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既体现着先行者筚路蓝缕的探索试验色彩,也对当下的文学语言建设不无启迪意义。
一
周作人曾称王充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之一,称赞他的思想“和平公正”。“和平公正”既指一种依据“常识”评判事物的态度,也指一种思想方法⑤。王充思想的这一特色体现在文章语言问题上,即指一种无分古今、不避雅俗的宽容态度和实用理性精神。周作人也是在这一思想方法指导下形成自己关于现代文学语言建设构想的,这就使其理论既避免了极端片面性,又因继承了“致用”的精神传统而具有切实可行性。
文学语言变革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恰当处理古语与今语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贯穿整部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上,王充是周作人的先行者。在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经学统制,辞赋流行,思想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和文学领域里的模拟风气甚嚣尘上,表现在文章语言层面上,就是崇古卑今,以艰涩难懂、深覆典雅为时尚。面对这一状况,王充从“常识”出发,提出了言文本应一致,无需强分古今的主张。他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语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王充的意思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口语容易灭遗,所以用文字来记录它;说话的目的,在于使人能听得懂,写文章是要人能看得懂。既然如此,文章语言就应当追求明白通晓,“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就必须“文字与语言同趋”,才能使作品发挥“欲悟俗人”的功能⑥。这就从文章语言的起源和功能两个层面上论证了言文一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既然古今文章都是为了明白准确地记事论理和表情达意,那就没有必要在语言上强行划分古今,也没有必要迷信古言,贱视今语,模拟古人,僵化保守,而应当无分古今,“适用”为贵,即根据文章内容需要自由选择。他说:“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澧异气,饮之皆碎,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⑦
与王充一样,周作人也认为现代文学语言变革与建设没有必要以“生死”为标准在文言和白话之间划出畛域。他说:“古文与白话文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二者“系属与趋势总还是暗地里接续着”,“白话文学的流派决不是与古文对抗从别个源头发生出来的。”⑧因此,现代文学语言变革主要是文体改变,在文字、词汇以及文法上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改换,当然更谈不上废除汉文重建新的语言体系了。不仅如此,周作人还提出要“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他认为白话中常缺少“形容词助动词一类以及助词虚字”,这就不得不“采纳古语”⑨;“纯粹口语体的文章”虽然行文流畅,却只适合说理叙事文体的发展,而在“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文体里,“纯粹的口语体”则不能适应要求,就必须有文词上的变化,尤其是将文言融入其中,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⑩。既然文言成分对于现代文学语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恰恰是适切表现现代人情思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不仅不能简单认为是与白话势不两立的“死文字”,还要根据文体特征和文章内容积极择取与转化。
与古今问题相应,如何处理文学语言雅与俗的矛盾也是一重大课题。在这一问题上,王充的观点同样不同流俗。他不仅主张写文章应“直露其文”,还可“集以俗言”,即写文章应不避俗字俗语。他认为春秋以来的所谓“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实际上是根据当时各地的语言文字写成,只是由于语言文字演变,加上四方方言不同,这就使汉人读起来有“古今言殊”,不易理解之感,而并非当初写作之人故作艰深,追求典雅所致。既然儒家经典都是如此,现在的人写文章也就没有必要回避俗字俗语。王充的这一观点有理有据地批驳了当时认为“贤圣之鸿才,故其文语与俗不通”(11)的谬论,为文章语言吸收俗语的有机营养做出了有力论证。
周作人对方言俗语与现代文学语言关系的看法与王充相近。他说:“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只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而这恰恰能够补充中国语体文词汇贫弱之不足(12)。他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虽然“议论文照例不选”(13),却收录了吴稚晖的文章,就因为吴氏那“糅合俗语与经典,村言与辞赋为一炉的创格”的文体,对于现代文学语言建设有着特别的意义(14)。这就是说,周作人不仅认识到了白话文的固有缺陷,还认为方言俗语能够弥补这一缺陷。
不论以白话为主融合文言成分,还是在书面语言中吸纳方言俗语,周作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适用”,这与王充所坚持的实用理性精神完全一致。周作人指出:“白话文之兴起完全由于达意的要求,此外并无什么深奥的理由”,只要作家能够充分地叙事说理、抒情达意,语言体式的运用与变化应尽可能自由,至于文学语言中白话、文言乃至方言俗语如何配合,各占怎样的比例,“则完全由作家个人自由规定”,不能强求一律,也不必硬性规定(15)。而此后文学语言的变革与发展,同样应该以此为方向和途径。正如他精辟总结汉字改革问题时所说:“汉字改革的目的,远大的是在国民文化的发展,切近的是在自己实用的便利”,“汉字应当为我们而存在,不是我们为汉字而存在。”(16)
二
任何民族文学语言的丰富与发达都离不开对其他民族语言的吸取与转化,也离不开文学翻译的有力推助。通过文学翻译改造本民族语言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共识,因此,他们的翻译理论也就是他们现代文学语言建设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现代翻译大家,周作人对六朝佛经翻译甚为推崇,他在阐释自己的翻译理论和介绍自己的经验时,反复引用,以为佐证。六朝佛经翻译不仅为周作人关于现代文学语言应如何吸取外来语言并实现有机转化的思路提供了历史经验,也使其翻译理论和文学语言观念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
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以“信”为本,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改造民族文学语言。在周作人看来,中国文学语言有着词汇贫乏、语法不够严密、表达不够明晰之弊,而这些弊病恰好可以通过文学翻译来救治。因此,必须通过“直译”,从外来文化中输入新的字汇、语法和修辞,以达到改造民族文学语言的目的。周作人认为对那些无法用汉字译出的专用名词,应该“名从主人”,即以音译为主或杂入原文;对于外国文学中的句式、语法和修辞方式,则在不过于生硬艰涩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原貌。为了给自己通过“直译”改造民族文学语言寻得历史依据,周作人将目光转向了六朝佛经翻译。他说:“我以为此后的译本,仍当杂入原文,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譬如六朝至唐所译释教经论文体,都与非释教经论不同,便是因为翻译的缘故。”(17)他的意思是,六朝佛经由翻译而来,自然在语言形式上与本土典籍不同,但经过历史淘洗和转化,仍有机融入了民族语言传统。
六朝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正是以“信”为本,存真为指归的。以前的佛经翻译由于文化差异与语言隔阂,译者往往以“格义”方式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即以中国传统思想学说解释佛教经义,也往往采用本土典籍中的词汇翻译佛教术语,因而造成佛经原意的讹传和语言形式的歪曲。罗什对此深为不满,认为前人译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于是,他决定重译以纠正前人错误。罗什既博通佛教经典,梵文极有根柢,又因留华日久,汉文也有相当素养,在翻译时“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18)正因为罗什注重求“信”并审慎采用音译,他的译经避免了以往牵强附会艰涩难懂之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因适当保存了音译词汇,既可使后来者通过搜寻语源,理解原作本意,久而久之,这些音译词汇又必然渐变为熟语,从而丰富汉语词汇系统。因此,罗什的翻译实践为周作人坚持“直译”以改造民族文学语言的理论提供了恰当坚实的历史例证。
其次,周作人认为文学翻译还应将“达”与“信”结合起来,既能将原文意思不多不少地移译出来,又能“将外国文里的意思说成中国话”,为中国人所理解,必要时可在文句上调整或增删,但必须保证原文意思完整。他介绍自己的翻译经验:“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惟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19)可见,周作人虽主张“直译”,但他的理论比较合理辩证,通达可行。文学翻译倘若“达”而不“信”,自然是“胡译”;但若过分拘泥,不知变通,生搬硬套,“信”而不“达”,则是“死译”,其结果也只能等于使人念咒。
周作人以“信”为本,“信”“达”结合的要求也正是罗什极力要达到的境界。罗什的译文以“曲从方言,趣不乖本”为原则,同时考虑到中土诵习者的要求,在传译上或增加文字,只是为了将经义阐发得更为通俗易懂,或删削冗赘部分,只是为了使文句更为精炼便于诵读,或前后有所调整,只是为了符合汉文文法习惯,其最终目的则是务求达意。因此,他译《法华》时,为表达言外之意而有增文;译《中论》时,则将繁复缺失部分加以删补;译《百论》时,反复陶练,务存论旨;译《维摩经》时,一言三复,精求原意;译《大品般若》时,则与诸义学沙门对校旧译,详其意旨,必求文合然后确定付写,可见他在翻译上惨淡经营之苦心。因此他所译经论,特为中土佛徒所乐诵,对于后来的佛教传播影响极大(20)。
文学翻译以“信”为本的同时还应求“达”并不仅仅为了使作品内容更易于接受,还由于将外来语言融入本民族语言体系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民族之间语言形式的不同其实是由于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只有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对其他民族的思维、心理及文化传统有了深入了解,其他民族语言中的句式、语法、修辞等才会有机融入。因此,周作人尽管也主张“欧化句法”的加入,但他也认为应当考虑到“中国语言的性质与力量”而在程度上有所限制(21)。
第三,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不同民族文学语言之间的传述转换,还应该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字在相互吸收、渗透、变革基础上更高层次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周作人也注意到了罗什译经提供的历史经验。据《高僧传·本传》记载,罗什曾与弟子僧睿商讨佛经韵文翻译问题:“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咏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罗什认为佛经韵文在梵转汉时虽可大意不失,但在语体风格上总是隔了一层,不但不能传达宫商体韵,文藻韵味也会失掉。为使佛经韵文既通俗化,又保留原作之风姿,罗什可谓匠心独运。他既不愿将其改译为散文,也不愿采用中国旧有韵文形式,于是独创“偈颂”之体,即一种“无韵的非散文”。它既不受中国古典诗歌声调格律之限制而相对自由,又因语句相对整齐和大致押韵,有别于散体文章而质雅可诵,成为了此后佛经中特有的语体现象,可谓不同民族语言形式在交融过程中实现创造的成功范例。罗什的这一创造性贡献令周作人感佩不已,认为“这给予我们一个教训,便是旧文体纵或可以应用,新时代应当自己去找出途径来。”(22)
由此可见,周作人之所以推重六朝佛经翻译,一方面是为他以“信”“达”为本的翻译理论张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他的现代文学语言变革与建设理论寻求历史依据,试图从历史经验总结中探索一条融合中外语言资源、重在创造的实践道路。
三
与实用语言不同,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审美性是其根本属性。文学革命之后,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代替文言获得了主导地位,奠定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周作人对此基本认同。但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白话文不“耐读”和缺乏“艺术之美”的缺陷(23)。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将目光转向了六朝骈文,认为“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24)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着力追求艺术之美的文体,骈文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对偶为主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是结合汉字特性并发挥其优长形成的,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而在文言中也往往就是一个词。汉字这种单音而孤立的特性给以采用文言为主的骈文形成对偶、整齐和对称之美带来了便利;同时,起于汉代的复音词由两个单音字构成,每个单音字除了是这个词的词素外,本身还有自己的形、音、义,这就不仅同样容易形成对偶、整齐、对称之美,还给属对方式带来了丰富性和灵活性。汉字的这种特性与优长是词形长短不一的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是骈文中丽辞对句这一语言形式得以形成的文化资源,也因暗合了中华民族喜欢对称的审美心理而有其历史必然性。
兴盛于六朝的骈文因讲求字数、结构和声律上的对偶而获得了空间上的整齐对称之美和节奏上的声韵音乐之美,为散体文章所不具备。正是从这里,周作人发现了六朝骈文对于现代文学语言建设的价值。针对白话文句法单调之缺陷,他主张通过利用骈偶,丰富白话文在句式上的变化:考虑到“中国国民酷好音乐”(25),注重音调,讲究节奏,而六朝文章“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26),他主张将骈偶辞句杂入白话文之中,从而增加文章的音乐节奏之美。周作人对白话文应适当利用骈偶的合理性同样是从汉字特性出发的。他说:“我们一面不赞成现代人的做骈文律诗,但也并不忽视国语中字义声音两重对偶的可能性,觉得骈律的发达正是运命的必然,非全由于人为,所以国语文学的趋势虽然向着自由的发展,而这个自然的倾向也大可以利用,炼成音乐与色彩的言语,只要不以词害意就好了。”(27)这就是说,周作人试图从六朝骈文中挖掘出合理因素并将其融入白话文,使其成为一种散中有骈,骈散结合,句法多变,节奏和谐,既能自由流畅地表情达意,又不乏形式之美和音乐之美的具有民族文化特性的现代文学语言。
其次,周作人认为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缺乏细腻的表现力,尤其缺乏描景状物时的色泽之美,而这却正是六朝骈文的长处,因此,他提倡从中汲取营养,使现代白话文成为“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28)。六朝骈文之所以被称为美文,辞藻华美是其突出特征。在当时的许多文人看来,五色相宣,绮縠纷披,文辞华美绮靡,色彩绚烂秾艳是文学之美的必要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或者大量使用色彩词语和修饰性描写,使景物描绘“状溢目前”,在读者心目中引起明晰的图画感;或者选用色型差别较大的色彩词语形成对偶,在强烈对比中造成鲜明华艳的审美效果;或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增加语言的形象性,使对客观事物的描绘穷形尽相且鲜活灵动;或者注重炼词炼句,刻镂精工,趋新求奇,力避平庸,摆脱陈旧的、熟悉的、普通的日常语言束缚,创造出一种新异的、特殊的、富于表现力的艺术化的文学语言。
骈文华美称艳的风格在六朝达到最盛,唐宋以后渐趋清淡,而中国文学语言的色泽之美也逐渐丧失。周作人说:“我常常觉得用八大家的古文写景抒情,多苦不足,即不浮华,亦缺细致”,“自韩退之起衰之后,文章重声调而轻色泽,乃渐变为枯燥,如桐城派之游山记,其写法几乎如春秋之简略了。”(29)这一看法恐怕也是他终生批判作为八股文之远祖的八大家和孪生兄弟的桐城派古文,而对被称为“选学妖孽”的六朝骈文不仅网开一面,且不时称赏的原因之一。
最后,以抒情为本是六朝骈文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周作人曾将其与新文学相捉并论:“骈文和新文学,同以感情为出发点,所以二者也很相近。”(30)但六朝骈文的抒情方式又有其特殊性,即注重通过隶事用典抒情达意,从而形成一种含蓄蕴藉、典雅华美的美学效果,这又是白话文学所欠缺的。隶事用典虽是修辞手法,同时是文学语言的炼造运用问题。近人刘永济曾对骈文用典之艺术效果有过恰当概括:“用典所贵,在于切意。切意之典,约有三美:一则意婉而尽,二则藻丽而富,三则气畅而凝。”(31)“意婉而尽”就是指用典因具有象征性而使作者情感可以含蓄委婉地表达出来,能够在短小文句中包含曲折隐深的思想感情,同时传达难言之隐和不尽之意;“藻丽而富”指用典如用词,大量典故经过铸造,可以成为新颖别致的佳词丽句,使作品语言风格典雅华美;“气畅而凝”则指用典可使文气畅达而语句凝炼。另一方面,从读者接受角度看,典故往往又起着阻碍顺畅阅读的作用。但正因为如此,读者就必须参与到文本中去,不断依据自己的知识积累、生活阅历和审美经验,突破障碍,使阅读得以继续进行。这就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审美空间,延长了审美快感,扩展了作品的审美内涵,提升了其审美价值。
六朝骈文的这一抒情特征和语言风格很被周作人看重,他也时常以此为标准评价其他各时期的文学。周作人虽然认同晚明公安派“信口信腕,皆成律度”的主张,却认为其创作“过于空疏浮华,清楚而不深厚”;而一部分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流弊也在于此。他说:“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浓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看的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32)当然,要使现代文学语言“耐读”和有含蓄蕴藉之美,隶事用典未必是唯一的方法,但却不失为一条可以探索的途径。周作人自己后期散文“文抄公”式的写作方式,实际上就具有试验意义和垂范作用,也表明了他对现代文学语言应当具有的品质和达致途径的期望。
总之,周作人关于现代文学语言变革与建设的总体设想是“融合”,是由“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33)。但在如何实现“融合”的路径与方法选择上,他往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撷取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从王充那里,他取来的是处理文学语言古与今和雅与俗关系的实用理性精神;从六朝佛经翻译中,他发现了如何将外来语言融入民族语言肌体并实现更新创造的历史经验;从六朝骈文中,他又找到了加强现代文学语言审美性的有效途径。周作人的这一思路和资源取向使他的理论内涵显得丰富复杂,而其方法却又切实可行,既体现了他不同于“五四”其他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特殊态度,也保证了他的理论的民族文化身份,即便是对于当前的文学语言建设来说,也有着充分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第7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②许家鹏:《胡适实用主义哲学与白话文运动》,《华侨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③苏桂宁:《“汉字革命”与钱玄同的文化选择》,《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④黄岭峻:《从大众语运动看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⑤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2卷第21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⑥⑦王充:《论衡·自纪篇》,《论衡校笺》第925、928页,杨宝忠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⑧⑩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第99、64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⑨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第77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1)王充:《论衡·自纪篇》,《论衡校笺》第926页,杨宝忠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2)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6卷第58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3)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第67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1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15)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1卷第83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6)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第72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7)(20)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8卷第691、68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8)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第295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19)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22)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8卷第804、80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3)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第77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4)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1卷第79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5)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2卷第11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6)(29)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第404、47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7)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卷第18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8)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第56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0)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31页,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1)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第14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26页,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3)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第77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标签:周作人论文; 文学论文; 汉字演变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王充论文; 六朝论文; 白话文论文; 罗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