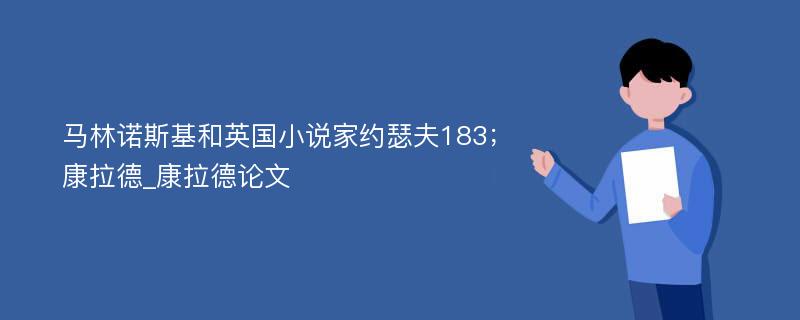
马林诺斯基与英国小说家约瑟夫#183;康拉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瑟夫论文,英国论文,小说家论文,诺斯论文,康拉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林诺斯基试图创建“文化的科学”,并创建了民族志的方法论。他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论述了他的“文化科学”的理念和民族志方法论。他说,任何一门学问,“都应以绝对坦诚和毫无保留的方式披露其科学研究的结果”。“方法原则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该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民族志者在田野工作中面临的任务,是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马林诺斯基,2002)
马林诺斯基主张“文化的科学”,是否与他早年学习数学和物理学有关?马林诺斯基是真诚的、执著的、富有科学精神的。科学是他的理想和追求,在他的观念里,科学也应该是人类学的理想和追求。当他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返回英格兰之后,后来成为著名人类学家的雷蒙德·弗思、伊文思-普理查德、费孝通都先后成了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们都继承了马林诺斯基的传统,同时又在他们的著作中有各自不同的发展与建树。他们民族志的撰写方式基本遵循了马林诺斯基作品的轨迹。
马林诺斯基的作品是什么轨迹呢?他的作品被乔治·马尔库斯和迪克·库斯曼称为“现实主义民族志”( George 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1982) 。他根据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田野资料撰写的第一部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马林诺斯基,2002)洋洋洒洒、气势如虹。但在这科学的、客观的文化描述的文本之中,还是有马林诺斯基的自我。詹姆斯·克里福德通过比较马林诺斯基和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关联,论述了他作品中的“自我模塑” ( Clifford,1988) 。康拉德是英国小说家,他与马林诺斯基一样来自波兰,在英国从事了20多年的航海事业。他描写的航海的故事和非洲异族的生活曾深深地震撼过笔者。
马林诺斯基也描写航海的故事。这其中有什么联系?现实主义民族志起源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而马林诺斯基的作品是否有康拉德的痕迹呢?这一问题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重读了康拉德的小说。结果我发现,马林诺斯基并没有拘泥于康拉德作品的风格,而是在写实性方面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更重要的是,马林诺斯基对于海洋的向往,对于异族文化的眷恋,对于西方文明的反思,与康拉德有异曲同工之处。马林诺斯基以另外一种视野,即人类学家的功能主义理论视野来观察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以及那里生活的人们。他试图以另外一种眼光,即科学的眼光,来分析库拉交换的象征意义,他试图用另外一种笔调,即人类学的文化描述,客观地表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社会整体和文化全貌,“这些描述清楚地展现了一幅幅社会制度的图画,其宽广和繁复程度往往出人意料;这些描述把生活在宗教和巫术的信仰和实践中的土著人形象带到了我们面前;这些描述史无前例地让我们洞察到土著人的精神世界”(马林诺斯基,2002)。这种描述作为一种文本体裁,就是现实主义民族志的基本写作手法。
1915年,马林诺斯基来到了西太平洋的一片岛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在这块宁静的地方,居住着特罗布里恩德的岛民。他们有的耕种田园,有的出海打鱼。这是一个近乎原始的社会,但这里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宗教信仰。马林诺斯基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并根据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经历写下了人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叙述是民族志的基本写作手法。《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首屈一指的民族志经典。它的基本内容是叙述新几内亚东部的南马辛区域( Southern Massim) 特有的库拉活动。这是一个组织得极其漂亮的文本。马林诺斯基的成就并不在于发现了库拉,而在于以开创性的民族志阐释了库拉。库拉是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村或一个岛的男子,他们在一年中要建造、维修远程库拉所需的木船,其间要举行各种仪式,亲戚要来送礼,地方上的人都会参与。因此,叙述库拉的过程就是讲述整个社区生活。其实,早在1853年就有西方人提到这个地区的项圈交易。1888年的西方文献中出现了“库拉”这个术语。随后的几年里,出现了对于定期的贸易远航的报告和类似圆圈的库拉路线的概括( Leach 1983:9) 。但是,马林诺斯基当时认为,库拉真正成为科学的整体论方法所研究的对象是从他开始的。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前工业社会的、非货币化的和跨区域的交易体系的样本( Appadurai,1986:19) 。马林诺斯基在书中几十次提到“科学”,他说要用科学戳穿西方人关于土著人的虚假漫画。他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言中写道:“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务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田野民族志者进行严肃的、冷静的研究,达到了包括部落文化的每一方面现象的程度,对那些平常、乏味、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异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同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中取得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马林诺斯基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大量篇幅(第四至第二十一章)讲述了有关库拉远航以及各种各样相关风俗和信仰的连贯故事。马林诺斯基以优美的笔触描写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
我们暂时离开安富列特的青山密林继续向北航行,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平坦的珊瑚岛世界(我们将不时返回安富列特,以增加我们对当地土著人的认识)。这是一个与巴布亚美拉尼西亚其余地区都不同的区域,有许多特殊的风俗习惯,使其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志区域。直到现在我们都航行在蔚蓝清澈的海面上,在清可见底的海水里有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生气盎然的水藻和鱼群。至于四周的景物,则有热带森林、悬崖火山、水道瀑布、浮云深谷,蔚为大观。继续向北航行,我们要与这一切告别。安富列特的轮廓不久便在暑气中消失,余下的只有科亚塔布修长的金字塔峰顶仍在水平线上优雅地挺立着,直至我们过了基里维纳海湖为止。
我们驶进一片暗绿色的海面,四周是清一色的海水,没有高山,没有森林,中间只有几处沙洲点缀在枯燥的画面上。这些沙洲,有些空荡荡,只有海浪拍击声;有些则只有寥寥几棵露兜树,高高地盘踞在沙滩上,根茎露在外面。安富列特人有时也到这里捕捉海龟和儒艮,一呆就是几个星期:这里也是好几个库拉话的发源地。再往前走,在烟雾弥漫中,地平线逐渐呈现,先是轻描淡写,然后逐渐浓重起来。其中有一抹开始加长,其余较小的则显示出小岛的形状。这便到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大海湖,右方是群岛中最大的博约瓦岛,还有许多有人或无人的小岛,集中在北方和西北方。
我们在海湖中继续航行,在浅水航道中辗转。当我们接近主岛时,那厚厚而低矮的层林渐次裂开,露出一片海滩,可以看见一个有支柱的棕榈树蓬,里面好像有一个空间,说明这里有村落。我们弃船登陆,近海的地方满是泥巴和废弃物,也有几条被拉上岸的独木舟,停放在离海较近的地方。我们穿过树丛,便进了村庄。(P46)
他描写了独木舟及远航,描写了独木舟的价值以及土著人对独木舟的浪漫情怀,描写了建造独木舟的过程与仪式,描述了库拉旅程的起航,描述了库拉的航程和沉船的故事,描述了库拉神化、巫术和交易的细节。
对土著人来说,这笨重不堪,大大咧咧的独木舟是伟大的,甚至奇迹般的成就,是美好的事物。他为他编织传统,饰以最好的雕刻,涂上油彩并加入装饰。对他来说,这是驾驭大自然的利器,使他能够横渡险象环生的海洋,到达遥远的彼岸。与独木舟相关联的是充满惊险、希冀和欲望的海上旅程。这些都在土著人的歌曲和故事中反映出来。事实上,在他们的传统、习俗、行为、言语里,我们可以发觉他们对独木舟的爱慕和激情,有如它是有生命的东西,这是航海者对他的船只特有的感情。
船身长而深,外侧担着一个平衡的浮架,和船身等长,并有一个横跨的平台,从船的一边到另一边。由于材料比较轻,使它比任何欧洲的远洋船只都可以更深地吃水,所以浮力也更大。前进时,它在水面上滑翔,随着波浪起伏,时而隐身在波涛之下,时而又踏浪而上。坐在独木舟的修长船身中,你有一种不安但畅快的感觉。只见独木舟乘风破浪,浮架在水上飞荡,平台左倾右斜,海水频频涌上。更妙的是,你蹲在平台或浮架上,会像悬在海面上一样,这时你觉得奇趣无比、惊险刺激。偶尔一个浪头打来,海水冲上平台,这笨头笨脑的独木舟会纵横回避,以美妙的姿态破浪而出。张帆的时候,它厚重的帆席窸窣作响,间杂以格格之声,独木舟徐徐而动;当它乘风破浪、扬帆向前时,水在船底下咝咝作响,金黄的帆在蓝天碧海中发出耀目的光芒,这情景令人陶醉,引人入胜。(P99)
在这一切描述中,马林诺斯基浸入了他自己的情感,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看到的,他经历的,他体验的,他感受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对于独木舟的专注,看到了他对于航海的迷恋。他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写了几乎每一个细节,简直就是小说中的描述。接着,真正的库拉旅程开始了:
库拉冒险家们乘风破浪,不久便把特罗布里恩德的海湖丢在后面。绿得有点浑浊的海水,时而因水底海草的浓密而变成深棕色,时而因浅水照见洁净的海沙而显出耀眼的翡翠色,时而又因进入深水区域而显出深邃的暗绿色。围绕特罗布里恩德海湖的一环低地逐渐淡化,最后消散在霞雾里,而南部山峦却在晴朗的天空下逐渐显现。安富列特群岛的工笔轮廓虽然在高高的蓝色阴影的衬托下显得细小,但却越来越清晰和坚实了。遥远的群山顶峰笼罩在朵朵白云之中,群山中最近的一个叫科亚塔布,即禁忌之山的意思。它在弗格森岛的北端,山体修长,像个倾斜的金字塔。它是最能吸引航海家目光的灯塔,指引着南下之路。山的右边,即我们的西南方,耸立着笨重的科亚布瓦加乌大山,即巫师山的意思,它位于弗格森岛的西北角。至于古迪纳夫岛,则只能在极为晴朗的天气下才能隐约见到。
在这里他们也会发现许多光怪陆离、颜色艳丽的石头,与他们家乡千篇一律的白色珊瑚石不同。除了各种花岗岩、玄武岩和火山岩外,他们还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黑曜岩,这种岩石有金属条纹,边缘十分尖锐。另外,藏有丰富的红色和黄褐色赭石的山地,也使他们大开眼界。除了由火山灰形成的大山外,他们还可亲历温泉间歇性喷发的奇景。所有这些神奇的事物,年轻的土著人以前只能耳闻而不曾目睹,或只能看是归航的人带回的标本而已,如今,这一切却呈现在他们眼前。这是一个难忘的、令人快慰的经历,难怪从此他们要把握每一个去Koyo的机会,因为面前的景物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乐土奇邦。(P192~193)
在马林诺斯基刻意追求“文化的科学”的时候,他不经意间运用了文学手法,把大自然的景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的描述中表现了他的自我,也就是说,他在整个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人物,那就是作为人类学家的马林诺斯基自己。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子。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在他生活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着波兰裔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 Malinowski:1967,P40)。可以想象,马林诺斯基有多少个孤独的夜晚都是与康拉德的小说为伴呢。康拉德的小说都是关于航海的故事。
马林诺斯基是一代新学派的创始人,撰写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田野作品,他以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资料写了7部专著。试想,他的著作为什么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他为什么单单去了西太平洋的一片岛屿?其实,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对马林诺斯基的经历和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1857—1924) 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个特殊人物。西方评论家誉为本世纪最杰出的英国小说家之一的约瑟夫·康拉德原来是个波兰人,他的原名是约瑟·提奥多·康拉德·考泽尼奥斯基。他1857年12月3日生于现属乌克兰的别尔吉切夫,父母都是波兰乡绅。他的父亲阿波罗·纳雷兹·考泽尼奥斯基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爱国志士,参加了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斗争。1861年10月,他被俄国人逮捕,流放到俄国的北部。他的家人也跟着他到了那里,包括还未满4岁的小康拉德。俄国北部的气候十分恶劣,小康拉德险些死在路上。他的母亲染上了肺结核,终于在1865年4月去世。家庭的不幸和斗争的失败使小康拉德的父亲陷入极度的失望,他的健康状况随之恶化。于是,他因病获释回到波兰的阿波罗转而从事翻译工作,主要翻译莎士比亚和雨果的著作。在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他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可惜,他的父亲也患上了肺结核,于1869年去世。
父母早丧,童年颠沛,生活艰辛,使他养成了忧郁、孤独和飘零的情绪以及对俄国统治的痛恨。后来,当律师的舅舅收养了小康拉德。从1872年起,少年康拉德便一心一意想去航海。1874年10月,康拉德到了马赛,终于在一艘商船上当上了水手。4年后,他到了英国,成为一名英国的水手,从学徒升为船长。1886年,他加入英国国籍。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他航行到过西印度群岛,到过东方,也到过非洲和澳洲,多次经历过风暴和疾病,经历过生死的折磨和考验,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1890年,他去刚果的航行构成他创作《黑暗的心灵》的基础。1896年,他因为健康的原因放弃了航海的事业转而从事小说创作。1899年,他发表了代表作之一《黑暗的心灵》( Heart of Darkness,1899) 。在截止到1924年为止29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31部中、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康拉德被西方文学批评界誉为英国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利维斯F.R.,2002)。
康拉德的作品传达了海洋上狂风暴雨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海洋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康拉德越来越将海洋及船上的生活环境作为一种手段,用以探索人类经验中深刻的道德含义”( Jacques Berthoud,1979) 。他的小说往往描述船只的一次航行,而同时又是描述人的精神所经历的一次航程。《黑暗的心灵》是康拉德根据刚果之行为基础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康拉德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的题目具有象征意义,“心灵”既是指形似心脏的非洲大陆,特别是它的心脏地区刚果河上游,同时也是指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神智活动。因此,小说所描写的刚果之行,不仅是进入黑非洲腹地的航程,同时也是探索自我、发现人内心黑暗世界的历程。“这一深入丛林的旅行也是追溯人的历史,回归到人的原始起源的旅行。马罗(故事的叙述者)冒险闯入沉沉的黑暗,这种黑暗的核心也存在于人的胸膛之内。”( M.H.Abram,1968) 《黑暗的心灵》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是20世纪小说一个普遍的主题。
马罗担任一家比利时公司的船长,率船前往非洲。当马罗抵达刚果时,他描绘了一幅非洲丛林阴森恐怖的景象:村舍凋敝,锁着铁链的奴工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贫病交迫的土人倒在路旁奄奄一息,伤痕累累的尸体上还留着子弹的窟窿。白人殖民者是充满强烈欲望、暴力和贪婪的魔鬼,“攫取这块土地上的财富是他们的欲望,他们就像要打开保险箱进行抢劫的强盗一样,肆无忌惮,没有道义”。马罗讲述了关于科兹的故事。那是一个贪婪成性、掠夺成狂的西方商人,他巧取豪夺,聚敛了大量的象牙。在一份给国际组织的报告中,他呼吁“杀尽一切野蛮人”。他的火枪能发出雷鸣闪电,当地的土著把他当成半神半鬼,对他顶礼膜拜。当马罗最终找到科兹的时候,科兹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不久即死于船上。他临死前高声呼喊:“可怕呀,可怕!”他的心灵里潜伏着罪恶的深渊和黑暗的地狱。在这最后的呼喊中,“科兹获得了对自己的理解,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对人类的理解。他对自己的判决也是对人类生活的判决”( M.H.Abram,1968) 。这最后的呼喊,也包含着科兹对自己所从事的殖民主义事业的谴责,因而也寄托着对与此不同的生活的向往。
科兹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他年轻时富有理想,到非洲去冒险,想教化野蛮蒙昧的土人。但是在追求权利和财富的欲望的驱使下,他堕落而跌进了罪恶的深渊,恣意愚弄、欺骗、奴役和杀戮非洲土著人,贪婪和欲望剥夺了他的人性和理性。科兹远离文明社会的种种约束,摒弃了各种宗教观念和道义责任,原来受到抑制的躁动不安的不自觉的自我,包括各种欲望,便泛滥起来,吞灭了理性,使他成为疯狂的人。
《黑暗的心灵》发表于1899年,那年,马林诺斯基15岁,康拉德42岁。康拉德年长马林诺斯基27岁。少年马林诺斯基充满幻想,康拉德描述的航海的故事深深吸引着年轻的马林诺斯基。而且,康拉德在英国文学界取得的成就,也激发了马林诺斯基到英国去获得成功的远大抱负。于是,马林诺斯基说,“里弗斯是人类学的哈格德( Rider Haggard.) ,我要做康拉德( to B.Z.Seligman,quoted in Firth l957:6) ”。对于马林诺斯基来说,康拉德的名字是深刻、复杂和细腻的象征。但是马林诺斯基不是人类学的康拉德。他最直接的文学模式是弗雷泽,他的很多作品很像左拉,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加上一种凝重的气氛,他的文化科学的描述产生了充满道德的人文主义象征。但人类学还是等待着它的康拉德( James Clifford,1988:96) 。
马林诺斯基和康拉德相互认识。他们都是因为历史的变故而离开他们的祖国浪迹天涯,他们来到欧洲,来到英格兰寻求写作和学术的成就。两位漂泊者都来自于遥远的波兰文化,他们都出生在一个国度,一个自18世纪以来就是一个充满集体认同传奇故事的国度。在波兰的社会结构中,贵族是显赫的。他们对欧洲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不感兴趣。他们都漂泊不定。
《黑暗的心灵》作于1898—1899年,这期间正是康拉德从航海转向了写作生涯。《黑暗的心灵》是根据康拉德1888年到刚果的一次航行写成的。他的小说描写了大海,描写了丛林,以及在大海和丛林中非洲黑人所遭受的苦难。小说探索了自我精神的世界,描述了西方文明的局限中对道德沦落的抗争,隐含着对西方殖民话语的批判。康拉德小说中所传达的海洋的信息,深深吸引着少年马林诺斯基。大海的汹涌,大海的神秘以及大海中生活的人们,一直萦绕在马林诺斯基的心中。那里的人群是如何生存的呢?
1902年,18岁的马林诺斯基考入了杰格隆尼大学,开始时主修物理学和数学,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哲学。1908年,马林诺斯基完成了博士论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阅读了弗雷泽的《金枝》,从此对人类学情有独钟。他自己后来写到:“我刚一开始阅读这本巨著,就沉溺于此书中,受其役使。”(哈奇,1988:165)1910年,26岁的马林诺斯基到了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开始了人类学研究的生涯。英格兰是他向往已久的国度,因为康拉德22年前来到这里,开始了他在英国的航海和创作的生涯。1910年,康拉德在英国文学界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推测,马林诺斯基与康拉德的相识是他到英国之后开始的。马林诺斯基到英国之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找并拜访康拉德。在他的心目中,康拉德是波兰民族产生的,是英格兰和大海造就的传奇人物。他们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马林诺斯基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澳大利亚的土著家族》,他把这本书送给一位长者,书中有波兰文的署名,至于康拉德对这部父系社会研究的著作有何评价,已不得而知。尽管他们的相识是短暂的,但是康拉德给马林诺斯基留下了长久的影响。
1914年,30岁的马林诺斯基得到马雷特和塞利格曼的支持前往新几内亚进行田野工作。由于一战的爆发,身为敌国(奥匈帝国)臣民的马林诺斯基被迫滞留在作为大英属地的新几内亚。然而,正是这次历史的变故,使他有机会接近大海,接近大海中生活的人群。1914年9月,他在土伦岛( Toulon) 的梅鲁人中调查,此后,他又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断断续续生活了两年(1915年5月至1916年6月,1917年10月至1918年7月)。在马林诺斯基去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着康拉德的小说,并且在他的日记中表述他的生活的时候,经常使用康拉德的语汇。
马林诺斯基来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时候,面对着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西太平洋,他肯定想到了康拉德小说中描写的海洋。当他见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生活的岛民,他肯定想到了康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非洲部落的黑人。他要用他的人类学研究探求这个文化,描述这个文化。他试图创立一个文化的科学。
他写道:“很早以前,有人问一位权威:‘土著人的习惯和风俗是什么?’他的回答是:‘风俗吗?没有。习惯?像野兽一样。’这个有名的答案和现代民族志者的知识已是相去甚远了。现代民族志者用土著的亲属称谓表、谱牒、地图和图表,证明了一个广泛而庞大的组织的存在,呈现了部落、宗族和家庭的构造,展示了一幅土著人严格行为和良好习惯的图画,相比之下,凡尔赛宫或埃斯库里尔的生活却是散漫和随便的。”(马林诺斯基,2001:7)
马林诺斯基主要关注的,是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一切初看起来似乎是纯经济性的活动。但是,凭着素有的宽广视野和精敏理解力,他审慎地指出,发生在特罗布里恩德及其他岛屿的居民之间的贵重物品的奇异周转,虽与普通的贸易相伴随,但是本身绝非纯粹的商业性交易。他揭示出,这种周转不是建立在对实际效用和利润得失的简单计算上,而是因为它满足了比动物性满足层次更高的情感与审美的需要。
马林诺斯基还批判了西方教科书中“原始经济人”( Primitive Economic Man) 概念。他写到:“这个经济学假想出来的傻瓜,目前颇为流行。它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连最有能力的人类学家也受了蒙蔽,接受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根据这些想法,这个假设的原始人或野蛮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利的理性考虑,而达到目的的方法都是最不费力的直接方法。‘原始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特别是文化低下的人,其行为纯粹是出于为自己打算的经济动机(马林诺斯基,2001:7)。”马林诺斯基继续写到:
原始的特罗布里恩德人便是一个能驳斥这个荒谬理论的例子。他的工作动机来自高度复杂的社会和传统,其目的明显不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要,或是为了直接的功利效果。因此,第一,我们已经看到,土著人做工并不以花最少的气力为原则;相反,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土著人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毫无必要的事情上。工作和努力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在特罗布里恩德,园丁直接因他付出的劳动和耕种园圃的大小而获得荣誉。tokwaybagula这个尊称,意思是“好园丁”或“高效园丁”,乃是不能随便颁授的殊荣。我的朋友之中有几个是tokwaybagula,他们向我夸耀说他们工作的时间怎样长,他们耕种的园地如何大,他们比起其他人做得如何有效率。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几乎所有收获和盈余并非属于他个人所有,而是属于他的姻亲。但可以简单地说,一个人生产的粮食的四分之三,一部分是献给酋长,一部分则是给他姐妹(或母亲)的丈夫和家人。虽然从功利的角度看,园丁没有得到个人收益,但他却从收成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直接而具体地得到赞誉。(马林诺斯基,2001:55)
在西方文明的字典里,西方文化和西方人是上等的,所有非西方的文化和种族都是二等的。用19世纪英法国会议员的话来说,“白人的责任”在于要将这些落后于时代的人们从几个世纪的衰败、疾病和政治腐败中拯救出来,在于用教育儿童的办法来教育非白人社会里的人们。( George Marcus & Micheal Fisher,1986) 这种西方话语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因而导致了康拉德小说中科兹所从事的殖民主义事业。对马林诺斯基来说,对西方话语的批判就是创造现实主义的文化描述,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就是他的第一个成功。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肩负着反思西方知识和理念的人类学,是从西方殖民主义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终究也没有改变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的不平等地位。正如赛义德所说,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在现代理念的今天依然存在。马林诺斯基在八十年前所作的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意义。康拉德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小说里所描写的黑暗的心灵,并没有因为新世纪的光明而变得豁然开朗。康拉德小说中的场景,不是在今天一幕一幕地以其他的形式重演吗?但今天没有了康拉德对人类精神的追问,没有了马林诺斯基对异文化的描述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约瑟夫·康拉德和布洛尼斯罗·马林诺斯基已经逝去。这个世界因而变得更加混沌。
詹姆斯·克里福德在《文化的困境——二十世纪的民族志、文学和艺术》(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Literature and Art,1988) 一书中论述了康拉德与马林诺斯基。他认为,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1980) 的《文艺复兴之自我模塑》(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追溯了自我的出现和发展。民族志的主观性便是这一自我模塑的变种。自我是在文化的底色中经过模塑和虚构的。因此,主观性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文化的产物,因为自我是在文化的范围内表现的。文化的象征和展示是在权力之中形成的。民族志话语中自我的表现亦如此。尽管民族志描述了他文化之形成,同时也模塑了一个权威的本体,来表述、解释、甚至相信不同世界的真实。( James Clifford,1988:93~94)
詹姆斯·克里福德认为,在《黑暗的心灵》和《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康拉德与马林诺斯基都以松散的文本表现了两个世界的文化碎片,表现了他们的自我。马林诺斯基的田野日记是断断续续的景象,它们必须被制成一副完整的画面。为了把残缺不全的景象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就必须选择、组合、重写这些文本。结果马林诺斯基就产生了真实的虚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其他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民族志。他的民族志像小说,又不是小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较少自我的反思,但它的确是一个文化的虚构,并且宣告了一个权威角色的存在,那就是马林诺斯基,一个新型的人类学家。( James Clifford,1988:101)
马林诺斯基的两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一个扩展的文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和他的经典之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James Clifford,1988:110) 当《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在1967年发表的时候,曾引起人类学界哗然。日记清楚地表明,马林诺斯基的田野经历无拘无束,他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土著充满矛盾的情感,他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土著人也怀有愤懑之情,从而使他的田野经历充满矛盾。权威的人类学家像是沉溺于忧郁之中,他时常沮丧,时而寻欢作乐,又要尽力保持他的道德,振作他的精神。他试图说出不同的声音,表现不同的角色。“航海者”中完美的人类学家事实上并不总是对他的报道人怀有理解和同情之心;日记所记录的主观体验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的描述截然不同。那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令人震惊。那个权威的参与观察者,那些对异文化的系统理解的章节,在日记中荡然无存。而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却是理解、严谨和慷慨充溢于字里行间。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的痛苦、混乱、兴高采烈和愤愤不平与文化相对主义的民族志所具有的坚定和理解的态度大相径庭。《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没有润色,行文飘忽不定,但是充满至诚,表现了一个没有修饰的现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只是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描述的一个版本,这个岛屿还创造了另外的版本,那就是《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其他的民族志作品。日记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多声道的文本,对人类学史是一个重要的作品,不是因为它揭示了田野经历的真实,而是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田野际遇的复杂性,并且迫使我们把基于田野经历的叙述文本视为部分的文化建构。( James Clifford,1988:110) 他在田野中的情绪是冷酷和客观的,最终完成的民族志研究故事是经过设计和选择的。
雷蒙德·弗思不同意詹姆斯·克里福德把马林诺斯基的两部作品《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可以看做是一个扩展的文本的观点。他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于1988年重版时所作的序言中说,詹姆斯·克里福德“不但忽略了两部作品之间有四年的时间跨度,而且忽略了如下事实,即这本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写作的,而是记录他生活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日日夜夜,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困扰的时期;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则是在加纳里群岛( Canary Islands) 写作的一部完整的作品,那时他已是处于相对平静状态的幸福的已婚男人。克里福德对虚构( fiction) 的概念饶有兴趣,并且认为任何文本都有个人主观性的因素。不知道他是怎样理解‘虚构’的,但是对他来说,日记是马林诺斯基自我的虚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一个文化的虚构,尽管是‘现实主义的文化虚构’”。( Raymond Firth l988) 不难看出,雷蒙德·弗思对詹姆斯·克里福德的观点持批评的态度。
比较两位著名人类学家的观点,笔者认为:
1.弗思所说两部作品之间的四年的时间跨度,只是个表层问题。事实上,正如弗思所说,马林诺斯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并不是作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作品来写作的,因为马林诺斯基并不想把它发表。它是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整个生活的记录,当然也是最真实地体现了马林诺斯基的情绪,包括他的沮丧、他的困扰、他的痛苦和他的无奈。如果说他的日记体现了马林诺斯基真实的自我,恐怕没有人反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应该苛求马林诺斯基就应该是一个英雄。既然他的日记发表了,我们有机会了解马林诺斯基的内心深处和精神世界,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文本之间的关联,认识人类学文化撰写的主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克里福德把马林诺斯基的两部作品《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看作是一个扩展的文本,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其实,克里福德并不是把《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看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本,他只是说,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更充分地认识一个有血有肉的马林诺斯基和他在那个群岛上的真实经历,以及他根据那个经历所撰写的文化。
2.《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体现了马林诺斯基一个方面的真实自我,两个方面的自我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那就是作为人的和作为研究人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既然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文化撰写中有自我的存在,那么马林诺斯基试图创造的“文化的科学”,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化虚构。如果说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灵》是伟大的文学的创作,那么,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就是伟大的文化的创作。因为科学中是没有自我的,而马林诺斯基的作品中自始至终充满自我,并且是经过塑造的自我。
马林诺斯基的作品的描述中,留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痕迹,而他描写的对象和作品的主题与康拉德都有异曲同工之感。这与他少年时代就崇拜这位同是波兰裔的伟大作家有关。他声称要做人类学的康拉德,实际上他做到了。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人类学既然是人的科学,就不仅要有科学理性,还要有人类情怀。马林诺斯基和林先生都是人类学大师。他们都写了无愧于科学的民族志作品。但同样地,他们也都有深情的人文关怀,并且都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大量地运用了文学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