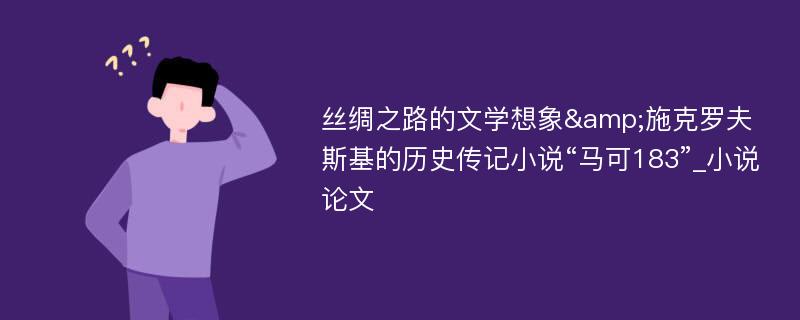
丝绸之路的文学想象:什克洛夫斯基的历史传记小说《马可#183;波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罗论文,丝绸之路论文,传记论文,夫斯基论文,克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是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散文作家,他创作了一系列题材风格各异的散文作品,践行了他的文艺理论思想和主张。20世纪20—30年代,什氏对历史题材兴趣浓厚,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几部反映历史内容的小说,例如《马特维·科马罗夫,莫斯科市民》(1929)、《主教追随者的生活》(1931)、《马可·波罗》(1931、1936、1958)、《画家费多罗夫的故事》(1934)、《米宁和波扎尔斯基》(1940)等等。其中,《马可·波罗》是什氏散文创作中较为特别的一部历史传记小说。自1931年起,什氏开始创作以马可·波罗为主人公的作品,先后冠以《侦探马可·波罗》《地球侦探》《地球侦探:马可·波罗》等书名出版,1935年作家对其稍作修改并于1936年出版单行本,定名为《马可·波罗》。1958年该书经过再次修改和补充,收入什氏的文集《中短篇历史小说》,由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终成定稿。 《马可·波罗》(Марко Поло)描写同名主人公的经历和遭遇,勾勒大旅行家的一生,无疑是一部历史传记小说,其中有大量的真实史料。什氏在小说中采用多种陌生化叙事方式,赋予小说较强的艺术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也使其与众多同类作品相异。诚如俄罗斯学者扬·列甫琴科所言,什氏的《马可·波罗》及其另外一些历史小说的“主题以及较为官方的演说术并没有抹去陌生化的手法,这是唯一的原则,也是‘认识论的方法’,它能够认识文学并将认识的主体写进‘最根本的满是创伤的历史进程’”。[1](134)在《马可·波罗》中,什氏采用纪实与评注结合的方式书写主人公的个人遭遇与东方文化,通过蒙太奇与延宕互渗的手法组接个人传记与人类历史,以重复与隐喻交织的艺术手段解读丝绸之路与人类发展道路,传达了对丝绸之路的文学想象以及对人类历史的思考,反映出特有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念。 一、纪实与评注结合:个人遭遇与东方文化的书写 所谓历史小说,“是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2](118)也就是说,历史小说必须要有历史根据,人物和事实都要有根据。“在历史小说这一概念中,‘历史’是小说的限定词,构成历史小说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一个基本的历史的事实或根据作为历史小说的起点而去创作历史小说是不可思议的。”[3](70)传记是指“一种专记人物生平事迹的叙事性散文”[4](18),传记作家要对传主的生平进行准确、连贯、完整的叙述。由此可见,历史传记小说必须要反映历史和人物的真实情况,史料的纪实性、人物经历的真实性是其必不可少的条件。 作为历史传记小说,《马可·波罗》正是建构在对真实历史事件回溯的基础之上的,小说中的事件和故事均在浓厚的历史氛围中展开,其中塑造的形象多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几个世纪以来,虽然一直有人怀疑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真实性,但是随着世界马可·波罗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什氏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参考资料之一便是马可·波罗本人的《马可·波罗游记》。该书的俄文译本最早出现在1861-1862年,什氏主要参照的是1902年出版的И.П.米纳耶夫(И.П.Минаев,1840-1890)的译本。米纳耶夫是俄罗斯著名的东方学家,其译本在出版时由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巴托尔德(1869-1930,В.В.Бартольд)审校,从而确保了该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这也许正是什氏选择该译本的主要缘由。在《马可·波罗》中,对于主人公在威尼斯的生活、其东方之旅的路线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种种遭遇、沿途各地的历史和现状,什氏在小说中都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并且多数符合历史事实。小说中所写到的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历史上的名人,例如成吉思汗、忽必烈、阿合马等人,与之相关的一些事件也确有其事,例如十字军远征、忽必烈统一中国、阿合马其人其事等均为历史事实,因此该作品无疑是纪实性小说。 需要指出的是,什氏并非仅参考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而是对比和研究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他虽然以马可·波罗的叙述为基石,但是却在小说中融入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和结论。什氏在直接引用《马可·波罗游记》、若望·柏郎嘉宾的《蒙古史》等著作中一些段落时常常予以明确评价,指出其传递的信息是否准确无误,并辅以佐证进行说明,例如什氏认为,马可·波罗有关可汗科齐及其臣民和哈萨克草原的讲述是正确的,而关于新疆沙漠地区夜间的噪声和恐惧在此前有很多游客谈及过,关于忽必烈的宫殿的记述也与当时情况相符;若望·柏郎嘉宾则准确地记述了蒙古人征服中国北方以及中国南部抵抗的史实等。什氏常常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小说中提及的一些事件予以详细解释,例如在谈及马可·波罗对各种语言的掌握时,什氏对比多个版本的相关书籍和史料得出结论:“据推测,马可·波罗不会说汉语。一般认为,他会八思巴文、阿拉伯文、回鹘文和叙利亚文。”[5](452)而马可·波罗则在游记中说“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蒙古语)和四种文字及其书写。”[5](452)什氏所做的解释说明以及得出的结论,仿佛是在为《马可·波罗游记》做注释。在什氏看来,“马可·波罗本人的书中很多事情都覆盖着手帕,只有懂得商人手语的人才能理解。”[5](455)什氏将纪实性艺术描写与评注结合,其目的就在于意欲通过自己的解释和说明揭开所有的“手帕”,小说也因此具有科学性倾向,不仅成为“著名旅行家的传记”,同时也是对其生平所做的“独特的文学注解”。[5](733) 俄罗斯批评家阿·伊维奇(А.Ивич,1900-1978)认为,“什克洛夫斯基对马可·波罗笔记的阅读,与那些迷恋于做注释和寻找地理知识错误的评论者不同。他在马可·波罗描写自己旅行的书中看到的是马可·波罗本人,他是走在那个时代前面的人。”[5](733)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什氏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马可·波罗的人生历程、遭遇和成长上,在作家看来,主人公的“遭遇——这才是小说中最主要的东西”[6](231)马可·波罗的身世及其东方之旅因此成为小说的叙事核心:旅行家在威尼斯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少年时代跟随父亲和叔父离开威尼斯,向南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由此沿波斯湾经霍尔木兹海峡从霍尔木兹上岸,穿过伊朗的一个大沙漠向阿富汗前进,此后继续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新疆的喀什,在中国生活了17年后,与同行者从泉州乘船启航,途径爪哇岛、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最后抵达家乡威尼斯,在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口述其游记,出狱后在威尼斯生活直至终老。在这一过程中,马可·波罗从懵懂少年、无所畏惧的青年逐步成长为睿智的商人、阅历丰富的伟大旅行家,他接触了故乡威尼斯以外的世界,波斯、帕米尔高原、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以及其他东南亚各地的物质、制度、习俗、观念和文化,也随着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父的游历逐渐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什氏在《马可·波罗》中依托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父的经历和真实的历史事件,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带领读者做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真实而又生动地再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丝路沿线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东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和风物人情,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什氏以马可·波罗和东方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并非偶然。什氏一直关注着东方和中国,他在著述中常常提及东方的许多国家及其文化和文学。什氏对东方文化的兴趣,首先来自于其构建理论的需要,他认为“必需有宏大的理论,它应该来自实践——各国人民的艺术,——这是我们的必需”。[6](68)作为文艺理论家,什氏阅读并分析过一些东方小说,并对东方小说的结构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东方小说在作品构建要素方面比托尔斯泰、雨果等作家“要大胆得多”。[6](58)什氏关注并研究印度文学,他阅读过古代印度故事集《五卷书》、《嘉言集》、《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鹦鹉故事七十则》等,发现“穿插作为一种阻缓手法”在上述作品中处处可见。[6](58-59)什氏在著述中还经常提到《一千零一夜》,对其中的故事及其情节极为熟悉,他认为《一千零一夜》里所有的童话都有寻找奥秘的内容,“转述故事的特点正是又缓慢,又漫长”。[6](58-59)什氏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兴趣更为明显,他专门撰写《中国小说初探》一文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看法,并借用俄罗斯中国学专家弗·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说法指出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在他看来,中国文学虽然没有影响全世界,但是西方各国文学也没有影响全世界。中国文学是另一种体系,另一种规律的文学,这种文学令他感到诧异,他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便始于这种诧异。什氏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童话故事、唐人小说、明清小说的人物和结构特征以及中国小说与民间创作的关系等,并呼吁人们“读几篇中国小说吧!也不要为它们不像我们以前读过的一切而烦恼”。[6](196) 可以看出,什氏不仅对东方怀有极大的兴趣,而且还尝试认识东方世界,解读东方及其文化之神秘。什氏对东方各国一直有自己的想象,他认为印度是“最富饶的国度”,“比较近,但是不可企及”,虽然“中国并不遥远,但是道路艰难”,[6](67)而且“中国——是个充满永恒传说的国度”[6](179),因此“中国应当被发现,正如当年美洲被哥伦布发现,发现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文化、风景和谬误的规律”,而在这方面,“只有人才能做到,象马可·波罗那样的人”。[6](196)什氏在分析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时曾经指出,要想表现外省城市,就要让人用不同的眼睛来观察城乡,而这首先要通过描写旅行来进行,因为“旅行者们在探究世界”。[4](446)由此可见,以马可·波罗及其经历和旅行为描写对象,对于表现东方、研究东方、发现和解读东方,对于读者了解东方的丝路文化,进而解读人类发展道路之谜,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意义,因为“寻找主人公在世界的位置,他的‘历险记’——这就是对世界的研究”。[6](445) 二、蒙太奇与延宕互渗:个人传记与人类历史的组接 《马可·波罗》无疑是马可·波罗的个人传记,然而什氏却采用蒙太奇和延宕相互渗透的陌生化叙事手法将为马可·波罗个人立传与讲述人类历史结合起来,使小说具有双重主题,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小说的容量。 蒙太奇手法是形式主义派喜爱的艺术表现手法。[7](194)什氏指出,“蒙太奇——剪辑,这不是联结固定不动的材料。……蒙太奇——是摄影师的事。他们拿上自己的相机,自己的暗箱,开始寻找拍摄的视点:从上往下拍,侧面拍,在活动中拍。”[6](276)什氏认为,通过这些不同视点所摄取的片段剪辑组合,可以形成仔细审视事物的方法。基于上述认识,什氏首先将小说《马可·波罗》的文本分割成40个篇幅不长的章节,每个章节均有标题,构成众多相对独立的故事和画面,作家将它们巧妙剪辑与组合,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小说文本。此外,在每一个章节内部,在各个章节之间,作家还常常通过延宕的叙事手法,勾勒出一个个场景,用蒙太奇的手法予以组接,以此表达他的创作意图。 《马可·波罗》是历史传记小说,但却以马可·波罗为主人公,以其经历和遭遇为主要描写内容,所以更像是马可·波罗的旅行记。所以,值得注意的是,什氏借鉴并运用了斯特恩游记类作品的主要艺术方法——延宕。作者一直推崇斯特恩的游记类作品,将其视为此类作品的典范,不仅如此,他“还把斯特恩式小说写作方法恰如其分地应用到自己的散文小说写作中”。[8](87)如在《马可·波罗》的开篇,什氏并没有让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父立即进入读者视线,而是用较大的篇幅,描写了威尼提族①的起源、威尼斯城的历史和概况、蒙古人的历史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以此“阻挠”主人公现身和延缓小说情节的发展。而在接下来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又大量采用穿插、重复、发现以及突转等延宕的手法制造了陌生化叙事效果。例如,在讲述波罗兄弟的第一次东方之旅时,什氏设置了多个重复的情节:威尼斯(有房子)——波罗兄弟经商——离开(原因:购置货物);君士坦丁堡(有房子)——波罗兄弟经商——离开(原因:这里并不太平);索尔达亚(有房子)——波罗兄弟经商——离开(原因:在这里生活的并不好);克里米亚半岛(有房子)——波罗兄弟经商——离开(原因:黑海并不太平);伏尔加河流域(别儿哥汗热情款待)——波罗兄弟经商——离开(原因:战争开始);布哈拉(贸易繁盛)——波罗兄弟经商——离开(原因:购买二手货价格昂贵);中国(留在忽必烈的王宫)——波罗兄弟经商——离开(作为大汗的使者载誉出发)。 从以上情节设置中可以看到,波罗兄弟原本在某地生活安定或生意比较顺利,却往往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往往是相同的原因)而被迫离开,即从顺境转入逆境,再由逆境转入顺境。这样一来,小说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自然离不开主人公自身的主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其个人之外的客观原因,即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才是左右和影响其命运的关键因素,或者说其个人意愿和遭遇无不依赖于历史环境。如此一来,作者对其个人经历的描写无异于对社会、环境、历史的描写。不仅如此,什氏在小说中还穿插进大量的历史故事,例如克里米亚的历史、伏尔加流域的历史,以及蒙古可汗之间的征战、布哈拉的发展史等等,这些插叙在叙事过程中制造了各种悬念,使小说内容更加丰富。这些插叙和描写承转自然,毫无违和之感,充分体现了作家有效地将各个画面和场景巧妙接合起来的蒙太奇手法。不同的镜头剪接组合就构成新的意义和新的艺术效果,小说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一来,什氏以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父的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为背景,穿插描写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历史和现状,从而巧妙地组接出整个人类漫长的历史画卷。 俄国诗人、作家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较早意识到什氏《马可·波罗》的与众不同,他指出这部小说“是取代任何阅读形式的开端,类似电影”。[9](358)通过阅读《马可·波罗》,不仅可以了解丝绸之路,了解马可·波罗的经历、遭遇及其思想,还可以深入理解他的命运,“就像理解自己的命运一样。因此这是一本有现代性意义的、及时的书。”[10](157)著名的作家、文艺评论家亚历山大·马里亚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арьямов,1909-1972)在致什氏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马可·波罗》的喜爱及其原因:“我非常入迷地再次拜读《波罗》。但是没有任何变化:我依然喜欢这本书,喜欢它现在的样子……依我看,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其主人公是历史。确切而言——这是一部用人类传记写就的长篇小说。”[10](157)确实,什氏关心的不仅仅是马可·波罗个人的经历和命运,而是要通过《马可·波罗》表达对世界、对人类历史和发展的关注。“在世界,在海上漂浮的人们——他们漂浮是由于人类的自我体验,而人类理应得到幸福。”[6](462)人类获得幸福的前提就是要破解人类发展道路之谜,而什氏关注丝绸之路,关注各国的文化艺术,他对各国文化的研究,“不单纯是一个年迈的作者对异国情趣材料的雅兴。这是把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展示的分析融合起来的尝试。”[6](118)不仅如此,他还寻找其中的共性,因为“对道路共同性的探索——决非出自心血来潮,这种共同性就是要破解人类道路之谜”。[6](118)可以肯定,什氏的《马可·波罗》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书写和思考,因为“人类有赖于那似乎来自各个星球的众多文化而生存”。[6](196) 三、重复与隐喻交织:丝路与人类发展道路的解读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总的来说是经济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因此什氏笔下的丝路首先是贸易繁盛的商路。商人们正是在这些丝路上频繁往来,在其沿途各地开展贸易。在商路沿线和船港附近,分布着居民点和不同民族的商行,哈萨克的“道路大多是由毛皮收购商而不是士兵开辟出来的”。[5](437)重要的是,丝路沿线各国不仅重视外来商品,也同样重视随之而来的文化,常常吸纳这些外来文化,以此促进本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在一路上常常受到尊重,因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商品,还有一些信息。……商人们让鞑靼的贵族习惯了新的商品,习惯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5](430)可以说,文化交流是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特征”。[10]难能可贵的是,什氏对丝路的描写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采用陌生化手法描写丝路,隐喻人类历史和发展道路,这无疑成为什氏创作《马可·波罗》的重要主旨之一。 在《马可·波罗》中,作者反复描写丝路的漫长、遥远(далёкий,дальний)、陌生(незнакомый,неведомый)及其可望不可即。在作家笔下,那是“一些宽阔的商路;那些大路通往遥远的国度”[5](413);“漫长的道路穿过整个世界”。[5](422)对欧洲人而言,鞑靼人居住的亚洲仿佛在“地角天涯,那是个向来毫无音信的地方”,[5](417)那是“很遥远的地方”。[5](418)遥远而漫长的丝路成为一条神秘之路。对于欧洲而言,东方就是遥远而神秘的想象世界。什氏一再强调,丝路通向遥远的国度,“欧洲完全不了解它们”,[5](413)因为“世界是广阔和未知的,商路将各个国家联系起来”。[5](414)在遥远的东方有辽阔的草原,“草原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遥远的中国,牧民自古以来就在那里游牧;在欧洲,人们甚至不知道是哪个民族在那里游牧,各民族原本的称呼传到欧洲都已经失真了”。[5](412)欧洲对东方人的印象最初都来自于传言和想象,这更增加了东方的神秘,也激起了西方予以探究的兴趣,由此开始了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交流和认知。事实上,西方对东方而言同样是神秘的,东方也需要去了解和认识西方,例如“对于忽必烈来说,欧洲是大地上贫穷的地区。但是不仅要了解邻国的势力,也要了解邻国的众多邻国。……欧洲好比星体更不为人所知;它很遥远,但是要把它探察清楚”。[5](446)基于此,在《马可·波罗》中反复出现“走在路上”、“缓慢行进”的画面,走在路上的不仅有蒙古人、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父,还有其他各国的商队和使节,丝绸之路成为各民族融合的最好舞台,这是连接东西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之路、促进人类发展的文明之路。正是在丝路沿线上,各国才不断地交流和融通,并形成了独特的丝路文化和丝路精神。 与此同时,《马可·波罗》中描写的丝绸之路,还是一条动荡艰辛(неспокойный,тяжёлый,трудный)之路,行走在丝路上的商队往往要遭遇许多坎坷和阻碍,其中有人为因素,也有大自然的因素。在小说中反复勾勒出丝路动荡不安的画面:商路上各个游牧部落之间常常发生战争,“草原上总是动荡不安。游牧圈袭击游牧圈”,[5](413)蒙古的王子们、领袖们相互角逐,争夺着富饶的土地,于是“旭烈兀和别儿哥侵犯了商队和商人的权利,并开始掠夺商人的财富,甚至杀死商人和工匠”。[5](433)伏尔加河沿岸也不太平,蒙古人和俄罗斯人时常抢劫,他们为得到食物和马匹而常常袭击商人,抓捕行人和牲畜。什氏把战争看做是“恶魔把妖魔鬼怪从时光瓶里放了出来”,[5](433)而“箭头令太阳黯然失色”[5](435)甚至“13世纪的前15年被战火映红了”。[5](417)事实上,即便没有战争,没有劫匪,漫长的丝绸之路也充满艰辛,一路上要爬过高山,渡过河流,穿越草原和沙漠,时而遇到河水泛滥,时而遇到恶劣的天气,时而天降大雪,时而天气酷热。在攀越高山时,“四周都是悬崖,覆盖着厚重的白雪。在这里需要保持沉默,因为大家都担心发生雪崩”。[5](443)即便走在平原上,田野上也“布满白色骨头……周围已经见不到人影;双唇干燥,整天整天默不作声地赶路。大地就像干涸的大海的海底”。[5](443-444)可见,穿越丝路往往要以生命为代价,丝路上到处是骆驼和马匹已经干枯的骨头,甚至形成了“白色的稀疏的篱笆”。[5](413)在描写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艰难旅途时,什氏重复使用颇具隐喻意味的情节和意象——北斗星。马可·波罗一行从中国踏上期待已久的归家之路时“天空中升起了北斗星”,[5](510)然而当路遇艰难或者迷失方向时,北斗星便消失了,此时“空中的北斗星既不是太高,也不是不低——而是根本看不到它”。[5](511)当船队将抵达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汗合赞的领地时,“只有一件事让人感到安慰——北斗星出现在天空中”。[5](516)此后波罗一家“从桑给巴尔转向归家之路,朝着北斗星的方向航行”,[5](519)将至家乡威尼斯时北斗星再次出现:“夜空中的星星是熟悉的。北斗星还在老地方高悬着。”[5](523)可以看到,什氏的隐喻性描写不仅带给读者异样的审美感受,也增强了所描绘画面的凝重。 丝绸之路的“漫长艰苦”[5](464)是毫无疑问的,人类的发展之路何尝不是如此!什氏通过对丝路的上述描写和解读,喻指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人类的发展是艰辛漫长的过程,往往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阻碍,“在某些时间节点有冲突、有战争和苦难,而在历史长河中却平静持久又规模庞大”。[11]。从古至今,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探索中发展,各民族则在不断接触和碰撞中逐渐融合,即便如同古老的丝路一样“已经被……踏遍”,[5](428)“到处都是骆驼那长满老茧的蹄子的印记,还有强壮的马蹄和驴子的小蹄子踩踏的痕迹”。[5](413)即便如同丝路这般伤痕累累、印记斑斑,各个民族、各国人民却“都是思于寻觅,勇于前行,完成交流,勤于传承,于是有了‘丝绸之路’文化”[12]和丝路精神,甚或才有了人类文化和历史的持续发展。什氏由此认为,各个民族经由丝绸之路通过不断交往和交流,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也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因此他在《马可·波罗》的结尾明确指出,“人类的文化不是在欧洲,不是在地中海创造的,不是意大利人,不是斯基泰人,不是德国人,不是阿拉伯人,不是中亚居民,不是俄罗斯人,不是中国人创造的——它是由整个人类和全世界的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5](546)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功劳,而是全人类各民族努力的结果。人类历史是由整个人类共同创造的,其过程漫长曲折、满是血泪,正如看似繁盛的丝路也充满艰辛和苦难一样。基于上述观念,什氏在“书中围绕着波罗描写了几个世纪令人相当伤心的生活。这是事实。认识世界并不能带来快乐。”[10](157)应该说,路也是一种语言,丝绸之路正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自然述说、历史述说、文化述说,千百年来,它具体存在于中西方这条漫长而久远的地域上,向世界向人类述说着它的独特感悟”[12],什氏以丝绸之路及马可·波罗传记为切入点思索人类历史、人类发展道路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什氏的《马可·波罗》是一部有趣的历史传记小说,更可谓一部“科学传记长篇小说”,[5](733)其趣味性无疑离不开作家选择的独特的叙事方式。什氏基于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人类文化、历史以及发展道路的思考,从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父的人生经历和丝路文化为切入点,采用多种陌生化叙事手法来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什氏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不但是文艺理论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文体家和小说家”,他“不但通过理论著作阐述其学理,而且还通过富有感染力的、文采斐然的小说和散文,既阐述其学说,更进一步实践之,实验之。”[13](4)甚至于“他的散文小说与小说理论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14](45)《马可·波罗》可谓什氏较为成功的文学创作实践,其深刻的思想蕴含和艺术魅力仍有待进一步发掘。 ①“威尼提”(veneti),罗马时代的民族,也是最早进入意大利的部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