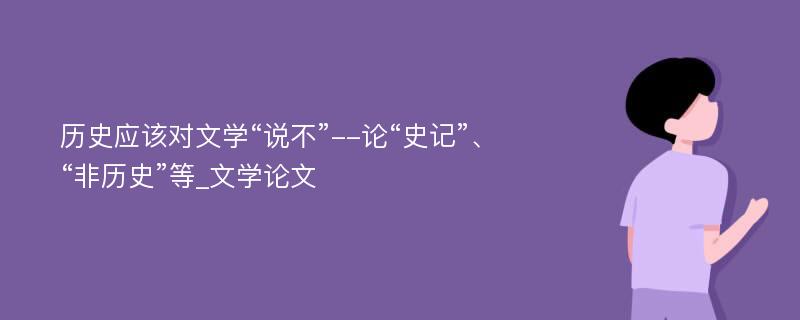
历史应当向文学“说不”——论“《史记》非史”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说不论文,及其他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5-0023-10 概略而言,历史著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史录(史实著录,含考订)、史论(历史观与史学理论,含历史哲学)、史学批评(方法论探讨,含历史编纂学等)、史学史以及综合类(如论文集、各种工具书之类)。有史录,有史论,然后方可称为有史学。而“史录”又是其它各类的前提和基础,故尤其显得重要,本文即以之为主要讨论对象。① 今天学界一般认为,古代中国与西方(古希腊、罗马)同是世界史学最早的发源地,而以往则多把这一荣誉独归于西方。②相形之下,现在的说法似已较为公允。不过,细究起来会发现,原来古代西方所有并可引以为傲的实际只是“史论”(史学思想),他们并无真正的“史录”,所以,和二者俱全的中国相比,其实尚有差距。可见,说“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乃是希腊人的发明”,[1]那若非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真正了解,便显然是“大西方”心态作祟之故。而就算把史学始源地的荣誉同归于中、西两方,也未必就见得完全合理、公允,因为,它仍然不符合客观事实。 何所据而云然?关键问题在于:到底怎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史录”(信史、实录)。 一、历史必须与文学“联姻”?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都普遍认为:由于“古代学科分类不严”,故难有可跟文学完全划清界线的纯粹的“史书”,因此,只能“把史著当文艺作品读”。 比如司马迁《史记》,在中国,人们总喜欢以它为例,说明古代文、史两者是如何地难舍难离: 我们更必须注意《史记》在是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2] 由于……古代学科分界不严,历史著作也往往是文学性或学术性的著作;加以司马迁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卓越的叙事才能,所以《史记》也是震烁古今的学术性著作(特别表现在八书中)和优秀的传记文学(特别表现在数量最大的世家和列传中)。 《史记》是上古至西汉武帝时代的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在全世界范围中,《史记》也是一部迄今尚无伦比的历史巨构。[3] 直至最近,有论者仍明确声言:“古代文史关系密切,史笔往往同时又是文笔。”[4]而关于史、文不分的问题,现代西方学者有更坦率直接、也更“理论化”的有趣阐述(以下引文从美国史丹福大学王靖宇教授所赠有关论文转录,谨致谢忱): 一切的真知和述说都受艺术常规的制约,因为我们是通过被文化所确定了的样式来理解现实的,所以我们只能以代表现实的小说的形式转述最特别的事件,按照我们自己最好的理解来确定它的动机、原因和结果,而不是按照绝对的事实来做。(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凯洛格[Robert Kellogg]《叙事文的特性》) 而盖利(W.B.Gallie)在其极具影响的《哲学与历史的理解》一书中干脆认为: 写历史就是在写故事。历史家在撰写历史时,心目中一定先有一个暂定的故事,而在撰写过程中,依据材料的情况,可能需要对原先暂定的故事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写。 美国名史学评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把上述观点再加发挥,在其名篇《把史著当文艺作品看》中如是说: 没有任何一套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构成一个故事,他们最多只能为历史家提供故事的元素。历史家将事件编制为故事时,对某些事件会加以压抑或使之沦为次要,对某些事件则加以突显,而其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平常我们认为小说家或戏剧家在编造情节时才会使用的方法。[5] 所有以上见解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历史不能自立,必须跟文学“联姻”。然而,那些文、史难分,充满“编造情节”的著作又怎可称为“信史”、“实录”? 二、唯中国有真“史” 西方学者认定“史”、“文”不可分,“写历史就是写故事”,因而主张把史书当作文学作品读,那其实同样是有意无意地反映了他们学术上“大西方”的心态——“此地无粮”便等于“天下无粮”。对世界而言并无真正的普适性。 西方从来就没有如中国那样的史官制度与史官们可贵的“记实”传统,自然也没有像《春秋》、《竹书纪年》、《秦记》(司马迁据之编成《六国年表》)、《编年记》(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等那样不具文学性的真正的史书。 从上古时代起,中国(那时还未叫“中国”)便有史官之设。传说中创制汉字(那时当然也未叫“汉字”)的仓颉,据说便是黄帝的史官。有实证为凭的,至少商、周时代王室已有史官,如甲骨文中有不少贞(占卜)人的名字,那些便是商代历朝的史官。在周代铜器铭文和传世典籍中,也载有史官的名字,著名者如西周的史佚、史伯等。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6]《隋书·经籍志》说:“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记言行。……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7]其记述的原则是扼要录载,如实反映,“不虚美,不隐恶”。目的就是保存数据,并提供经验、教训,令人“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有所惩劝”,以助治平天下。孔子曾赞叹:“直哉史鱼!”[8]又称晋国的史官董狐为“古之良史”,推许他“书法不隐”,不给任何权贵留面子的风骨。[9]有的史官更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维护求真记实的“直书”原则。[10]由此可见他们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实足以为今天广大传媒的借镜。 由史官依此准则著成的“国家之典”被统称为“史”或“史记”。《左传》提到的《周志》,《国语》引及的《郑书》,《孟子》所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之《乘》、《梼杌》、《春秋》,以及司马迁《太史公书》(后被讹称为《史记》)中谓“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孔子读史记”等语所指的“史记”,都属这同一类著作。司马迁更干脆把《春秋》称为“孔子史记”。只可惜,到秦一统后,除《秦记》外,那些列国“史记”便多被付之一炬了,③只有经孔子修订的“鲁史记”《春秋》因由儒家传习之故得以幸存。 大诗人杜甫的十三世祖、晋朝学者杜预(222-284)犹及见当时出土经整理的先秦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他在仔细比较研究后认为:“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如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伐下阳”;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等等。可见当时这类史册有共同的写作规范,便是:“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④而由《史记·六国年表序》所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之“有所刺讥”一语,我们又可知那些实录的史册和《春秋》一样,在扼要记述之余,必要时还往往会以特定的措词、用语(即所谓“笔法”),表见相应的历史观。⑤所有这类史册(无论尚存、已佚),便是古代中国独有的纯正的“史录”。 可惜,中外学者至今仍普遍认为“古代学科分类不严”,故难有可跟文学划清界线的纯粹史书。其实,真正的史书眼前即是,只是人们惑于成见,“有眼不识”罢了。 三、为西方“史学名著”正名 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史官制度与修史传统,在欧美等其它国家从未出现过。古希腊所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撰写的《希波战史》(原名《历史》)以及与之齐名的古罗马史家塔西佗(约55-120)所著《历史》等名著,均属私人著作,其中都搀杂有不少“故事”成分,与《荷马史诗》相比,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因此,严格说来只属“历史文学”,而非史学著作。难怪西方的学者们囿于定见,会认为非史、文“联姻”,“把史著当文艺作品看”不可。⑥ 由于古代西方缺乏纯记实的史书,所以希罗多德在撰写《历史》(即《希波战史》)时,所能参考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除《荷马史诗》和海卡太奥斯的神话集以及若干碑铭实物等之外,希腊官方的档案就只有些君王、执政官、祭司的名单,因此,他主要靠十年之久的亲身游历去搜集材料,基本上是有闻必录:“我的规则是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无义务相信每件事情的真实性。”[11]他把大量的传说、诗歌和故事纳入书中,另外,还杂有不少神迹、梦兆、占卜预言等等,其中朕兆应验之处竟多达三十五次;有时甚至出现明显的虚构——例如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其在位迟于雅典人梭伦游历该国之后数十年,但书中第一卷却出现前者带领后者参观宝库,并问他“谁是最幸福的人”的一段对话。[12]这些特色和中国的《左传》、《史记》都颇有相似之处。 就由于这样的内容和叙事手法,故有人戏称希罗多德为“可爱的传奇小说家”,而亦有人贬之为“说谎者”。[13]其实,无论是“小说家”的美称或“说谎者”的恶谥,都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证明着同一个事实而已: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是历史文学家,不是史学家;其《历史》是文学著作,不是史学著作。 古希腊修昔底德(约前460-前396)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继希罗多德《希波战史》后的另一“史学名著”。希罗多德记事至公元前479年为止,他写的是古-近代史,未尝亲历,所以数据中包含有大量传闻。而修昔底德写的主要是当代史(分别以雅典与斯巴达为首两阵对垒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于公元前431至公元前404年),有一段时间他还曾直接参与这场战争,因此,书中所载实况较多,奇闻异事大为减少。但是,此书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引述雅典名人演说甚多,各种讲辞竟占了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那些滔滔雄辩文彩丰盛、意态激昂,不少成为名篇,吸引后学者以之作为研习演说修辞的模板。然而作者在书中坦白表明:“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许多现成的演说辞。……但即使是我亲自听到过的,我也很难记得清确切的词句,而那些把从各种来源获知的演辞告诉我的人也感到有同样的困难,因此我只能一方面尽量保持演说辞原来的大意,同时也写出我认为在该场合他们理应如此说的话来。”[14]而实际上,有的演辞更纯出于杜撰,并无根据(例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礼上的著名演说)。就如《史记》所引述苏秦、张仪有关合纵连横的“大块文章”一样,原来那些名人演说也多是“想当然”地“撰作”出来的,那又怎能成为“信史”? 生活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塔西佗,其大作《历史》以记述严谨著称,但他的叙事方式同样充满各种可疑的细节。比如书中这样描述一次罗马城的兵变: 奥托(当时的罗马皇帝)这时正在举行盛大宴会款待贵族男女。客人们惊惶万状,不知道这是当兵的偶然发疯,还是皇帝搞了什么阴谋……接着,国家的官员们就各自逃散了……最后,奥托竟顾不得自己的皇帝尊严,站在他的床上哭着哀求起来,好不容易才使他们住了手。[15] 这里有表情刻画、心理活动、行为细节。未知当日是否曾有“狗仔队”深入现场,并逐个跟踪采访,问明意向,故能收集到如此周至详尽的情报?书中接着又一字不漏地记载了奥托对士兵发表的一篇“既是责备又是安抚的”、长达千言的演说。莫非罗马帝国彼时已经发明了录音装置不成?难怪有西方论者称塔西佗是“最杰出的人物素描家与最卓越的古代剧作家,但是他不可相信”了。[16] 四、历史记述可以“想当然”吗? 钱鍾书先生盛赞《左传》述事记言(尤其是记言)之妙,他认为:“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17] 钱先生首先正确指出:“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曰:‘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盖非记言,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18]钱先生虽觉得那些“生无傍证、死无对证”的独白或对话是“想当然”,有明显疑点,但依然肯定这种做法,并引《韩非子·解老》之言为其助势,同时又取证于西方类同之事例(如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行“增饰”、“制作”名人演说辞),认为此皆著史者所难免,而也是合情合理的行为。[19] 一些史学家(如汪荣祖先生)极韪其言,并加申述说: 盖古人征信甚难,有不得不凭传闻臆想之处。……钱丈默存参照狄尔泰(W.Dilthey)、柯林乌(R.G.Collingwood)之意,发为精义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记言固然不免代言,记事或亦属代记,盖“遥想古人,叙事陈词,乃史家之叙词,未必即古人之叙词也”。[20] 然而,中外不少史诗、历史剧、历史小说里面描述的情节、刻画的人物,其中许多“对话独白”与“事件因由”也是作者“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去“悬想”、“忖度”出来的,并非完全“向壁虚构”,要是按钱、汪等先生之见,那么历史著录和“历史文学”两者还有没有区别?是否毋须区别?难怪晚清名士、古文翻译家林琴南初读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名著《孽海花》时,会拍案赞叹道:《孽海花》非小说也,乃三十年之历史也!⑦看来,诸公可能都是灵犀一点、“所见略同”吧。不过,由此会衍生一个问题: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之类的“讲史”说部,是否也可跻身为“正史”的一员呢(尤其是,当假定《三国志》、新旧《唐书》等有朝一日“失传”的话)? 末后,钱先生再次肯定:“《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21]指出《左传》表达手法可算后世小说、戏曲之始祖。诚哉是言!不过这样一来,便直接坐实了我认为“《左传》、《史记》不是史”的论断了。 五、“史笔”与“文笔”之别 西方学者们可能囿于所见(或存在偏见),而认为非史、文“联姻”,“把史著当文艺作品看”不可。但中国不同,历史早就向文学“说不”。除了先秦有一批全无“故事”色彩的“国史策书”之外,历代还有各种《实录》以及帝王《起居注》等类著作,大都严格地以非文学的“史笔”而非“文笔”形式撰成(至于内容是否全部真实可靠,有没有“为尊者讳”,则属另一个问题,与叙事形式无关)。直至现代,这种不“编故事”、扼要“据实而书”的《春秋》式写法仍得到承传发展,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撰成出版的十卷本《清史编年》,便是有意义的尝试。例如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经过,《编年》这样记述: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郑成功督师至台湾,克赤嵌城。郑成功于三月二十三日启程,本月初一日乘涨潮入鹿耳门,登陆。初三日,全歼荷军上尉贝德尔以下数百人,遂克赤嵌。荷军总督揆一率残部据守台湾城(周按,即今台南市安平古堡),郑成功以兵围之,谕其降。揆一遣使谈判,愿赔款,要求郑军撤走,郑成功严斥之。”……八月,“荷兰支援舰队自巴达维亚(按,即雅加达)进抵台湾海峡,配合城堡荷兰侵略者攻击郑成功船队,双方激战,郑军击沉荷甲板船两艘,俘获两艘、小艇三艘。自是甲板船退入台湾港,不敢复出再犯。”……“十二月,郑成功围台湾城已九月,是月,荷兰总督揆一以城降,成功与订降书,许其携钱财珍宝率残部五百余人离台。”[22] 据说明,这部份史料取自徐鼒《小腆纪年附考》、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和杨英《先王实录》,而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删除繁芜”的归纳、鉴别、整理工夫,“力求准确可靠”。可见其审慎。(周按,台湾民间传闻,安平堡下有海底隧道,荷兰人最后藉之而遁。但近年经考古发掘,证明非是。)如果酌加修订,把“残部”改为“余部”,“严斥”改“严拒”,“荷兰侵略者”改“荷兰军”,“不敢复出再犯”改为“不复出”,令行文更呈中性,那么,可能更合乎历史“冷纪述”的样式。(当然,像现在这样也未尝不可,因为可反映编撰者的“历史观”。这也是肇源自周代修史传统、而为孔子发扬光大的“《春秋》笔法”。) 由此可见,“史书”与“历史文学”不仅应当区分,而且完全能够区分。韩愈《进学解》的两句话:“《春秋》谨严,《左氏》浮夸”,[23]已画龙点睛地为史笔与文笔,也就是史学与文学著作划出了鲜明界线。具体来说,它们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差别: 1、两者之目的、宗旨不同:史书要求“可信性”,志在“传信”,“传真”,发挥“彰善惩恶”、令人“鉴往知来”的作用;文学则追求“可读性”,志在“传神”,“传诵”,让人把玩欣赏,感发起兴,陶冶性情。 2、因而,两者之写作手法迥异:史笔重记述,甚至不妨平铺直叙;而文笔则重描述,务求曲折多姿,引人入胜。史笔强调冷静、公允、客观;文笔往往突显主观色彩,如轻重抑扬、是非评断以及鲜明之爱憎等等。史笔要求证据确凿,言不蹈虚;文笔则可以妙手翻空,凭想象加以渲染、夸饰、虚构。 3、是故,两者之取材标准亦不一致:史笔既要求证据确凿,便必须摒弃传闻、臆说和未经验明的孤证(纵使是当事人提出的孤证),只采用有多方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言而喻,在记录、通讯、交通设备都极其简陋落后的古代,要获得那样的资料,真是“戛戛乎其难哉”!因此,历史要存其真,便必须审慎地采取较笼统、概括的手法去记述,否则一涉描摹,便有“失真”之虞。如是,史官就算身处现场,但为求记录不受个人情绪、观察角度或书写速度影响,也不会详写细节(比如表情、心态、某些言语、动作之类)。而文笔一般不受限制,可以天马行空,兼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中广泛取材。 4、与之相应,两者的文体以及撰作人的身分与写作情况也有较大区别:朝廷史官的“史记”与私人著述之“历史文学”(史诗、史剧、历史小说或散文)所以有如此大的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是:史官出自职责,行文有“成规常法”,并可充分利用国家历代累积的丰富、可靠的档案数据,成书之后,又不必面向公众,只作为机要文献,收藏于“石室金匮”,其阅读对象仅限于统治阶层的少数人,所以可以而且必须以审慎的态度与“谨严”的手法去撰述,因此存真度亦高;其文体属于全无花哨的“实用之文”。私人著述则反是。它纯出于个人的志趣或抱负,凭兴之所至,从选材到处理手法都可以“别出心裁”自行决定,不必向谁负责,而文成之后,则须要引起公众兴趣,方得以存世与广泛流传,所以无论有意无意,都定会力求文笔绚丽,写得姿态横生,具有韩愈所称的“浮夸”风格。在文体分类中,属于“文学之文”。⑧ 由此亦可见,那些真正史书的撰作人(史官)是尽责任、守原则、甘于默默耕耘的学者;反之,那些驰誉世界的“史学(实际是‘历史文学’)名著”的作者,则多是有抱负、有理想、感情炽烈的诗人,每喜把写作的宏图伟抱表曝天下。比如希罗多德便自言:我“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亡,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固有的光彩”。[24]而他亦因此书及其优美文笔被称誉为西方“历史之父”、“散文之父”,“不但是历史家而且还是一位诗人”。[25] 东方的司马迁有“太史”之名而无传统史官撰史之责,[26]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重要原因之一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完成其志业,甚至不惜“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而无悔!并自信:“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27]终于亦赢得“史家绝唱,无韵离骚”之颂声。果然是个激情喷薄的热血诗人!⑨ 由之可见,“史学”与“文学”是应当而且能够区分的,历史就是要向文学“说不”。“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正缘有见及此。比如《春秋》记事:“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28]这是史笔,只有简洁的一句。而《左传》却把它敷演成五百字的长篇故事,从郑伯兄弟间矛盾的形成、发展、激化,到最后如何“动粗”解决,作了曲折、细腻的描述,情节完整,人物个性鲜明,心理刻划亦异常生动,遂成为后世选本必备的名篇(《史记·郑世家》也作了类似描述)。公元前607年,晋国发生宫廷内斗,晋太史董狐振笔直书:“赵盾弒其君。”[29]这是“史笔”。《左传》又把它铺叙成一篇首尾完备、引人入胜的历史演义。(《史记·晋世家》也采用了同样的写法。)赵国与秦国的“渑池之会”,司马迁据前朝“史记”的材料,在《六国年表》中仅扼要记载:“与秦会渑池,蔺相如从。”[30]当日两国史官的现场记录稍为具体一点:“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廉颇蔺相如列传》)[31]但双方如何为争占上风而勾心斗角、唇枪舌剑的细节,则一概欠奉。这正是史笔的特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却反其道行之,以优美的笔调从容挥洒,令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千载下犹觉虎虎有生气。于是此篇又成为历久传诵的佳作。那正是凭搬弄文笔之“魔法石”取得的成效。 六、《左传》、《史记》不是史 总括而言,“历史事实”与“史书”和“历史文学”三者的关系,可用个通俗的比喻去表示:“事实”就像游水的“海鲜”,是有血肉有呼吸有生命,因而多彩多姿,变化无穷的。而“史书”就如博物馆或实验室里的鱼标本,已去掉肠脏及好些鲜活的“细节”,只把主要的特征固定保存下来,供人认知、研究。而“历史文学”则是宴会上由厨师加上各种佐料,以不同花式炮制,供人品味、享用的海鲜佳肴:或清蒸、或红烧、或干煎、或油炸,或更切成鱼块,剁成鱼饼,绞成鱼丸,熬成鱼茸……。“清蒸”者其本来面目尚依稀可辨,其它便渐趋模糊,终至面目全非,仅存“鱼味”,而不成“鱼样”矣。 无论是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所著《希波战史》、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或被称为古罗马“最伟大史家”塔西佗著的《历史》,虽然在选材之严谨度与数据的可信性方面续有改善,但就重描述、多细节、因而难验证的文体特色而言,都只能算“半为想象半为真”之“历史文学”作品,而非纯粹的“史书”——真正的“史学著作”,就如同样鼎鼎大名的中国的《左传》、《史记》等那样。 司马迁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见《汉书·艺文志》),与《晏子》、《孟子》、《商君书》等先秦古籍“以人名书”的惯例相同,书名并不涉及书本的内容性质。而“史记”一词是专指史官记述,即官修的史书。这类史书体例明确,大抵编年记事,简明扼要,作为国家档案文献保存。司马迁此书却是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私家”著述,他自知写作意图、体例、内容、手法均与“史记”完全不同,故绝不会把自己呕心沥血的巨著取名《史记》。到了东汉中后期才被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东汉末叫《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再省称为《史记》(荀悦《汉纪》、陈寿《三国志》),遂与古代那些真正的史书相混淆。太史公泉下有知,恐会大感不悦呢。因为他的抱负比仅仅当一个诚实记事的“良史”要大得多!请看其自白: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32] 原来作者意图效法孔子,上接“六经”传统,写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用今天观点表述,那应是一本探索天道人事奥秘、穷究历史演变规律、验明国家兴废原因的“历史哲学”。因而在内容方面,天文地理、军政财文、人情风俗、周边族裔、域外国家,古今上下,几无所不包。而结果,最终写成一部当时举世无双的百科全书。其中影响最大,最具创意,也最占篇幅的传记部份,多采用当时流行的讲史、演义(如《左传》、《战国策》、《楚汉春秋》等)手法结撰而成。那些篇章有些纳入了虚妄诞幻的传闻,有些则本来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已加渲染、夸饰,且带上不少想象、虚构成分,是文学色彩极浓的历史小说(或历史散文)。⑩ 比如涉及上古历史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封禅书》诸篇,便不少沾上神话色彩。如谓:“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33]商人的始祖原来是“卵”生的!又如神化刘邦的“高祖斩白蛇”故事(《高祖本纪》),或张良“圯上纳履”受《太公兵法》的轶闻(《张相国世家》)等等,都充满迷幻离奇、不可思议的情节,但书中全都作为“信史”去津津乐道。古人说史迁“好奇”,大约和此有关。 除神话传说外,《史记》更多的是历史小说:内容部份真实,部份则“想当然”或完全子虚乌有,并渗入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尤其是被广为传诵的篇章,如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咸阳纵观、圯上纳履、鸿门之宴、乌江自刎等等,都有类似特点,因此,只可列入“历史文学”范畴,而不能算真正的“史录”。其中《刺客列传》可谓开后世侠义小说乃至武侠小说之先河。比如写荆轲刺秦王一幕,悲壮顿挫,感人至深,作者自言,资料乃亲得之于公孙季功、董生口述,但两人并非现场目击者,可见所录至少已是间接的传闻。(11)难怪古小说《燕丹子》和它那么相像: 秦王谓丹曰:“取图来进!”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按,应为揕,刺也)其胸……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34] 《史记·刺客列传》少了点“琴声密码”的奇幻色彩,但所记同样曲折生动,彷似经由声情并茂的录像带数据直接整理得来: 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方环柱走……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35] 两者描述之框架大体相同,而细节则甚多出入。这正是口耳传闻的特点。 再如聂政刺侠累,《史记·六国年表》韩烈侯元年(公元前400年)记道:“盗杀韩相侠累。”[36]可见确有其事。但《刺客列传》却以“全知”角度,肆意渲染发挥,写得如全程直击般淋漓慷慨,十分煽情。[37]无怪明人焦竑有这种感觉:“《刺客传》序聂政事极其形容,殆其抒其愤激云耳。”[38]当然,也只有小说才容许这样做。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则堪称“才子佳人小说”之鼻祖。 明清之际,所谓“才子佳人小说”大行其道,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金云翘传》、《好述传》等等。其所叙述,“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39]《玉》、《平》两书有法译,《好述传》更有法、德、英文多种译本,连德国大文豪哥德亦对之甚表倾倒。这类小说的渊源,论者认为是“上承《金瓶梅》等明代人情小说”。[40]而事实上,中国现存最早之才子佳人小说,当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莫属。其内容、情节、写作手法,与上引鲁迅的经典表述实完全吻合。且看传中“琴挑卓文君”的一段: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41] 相如所奏据说乃《凤求凰》曲。[42] 小说《西京杂记》所记正好和《史记》此段互相映照,互为补充:“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43]如把以上描写添入《史记》中,情节当更美妙完整,读之惟觉水乳交融,全无扞格。可见司马迁用的确为文学而非史学家手段。 对“琴挑”等情节,宋代已有人指出“是一段小说耳”,又云:“子长以奇著之,如闻如见,乃并与其精神意气,隐微曲折尽就,盖至俚亵,而尤可观,使后人为之,则秽矣”。(12)后世才子佳人小说,正继承了这种“俚亵而可观”、俗不失雅的传统。 据本人统计,《史记》中,属于历史小说或文学色彩浓厚的作品,在“本纪”占一半,“世家”占百分之七十,“列传”占百分之八十五。总计而论,传记部份的文学作品竟逾三分之二。[44]而人物传记正是《史记》全书的重点和精华所在。可见,说“《史记》不是史”并非故作惊人语。 七、《史记》的性质及其真正价值 总之,虽然《史记》一书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史料(见于“十表”、“八书”和许多纪传中),这点毫无疑问,但无论从作者主观创作意图、作品主要文体特征乃至全书客观效果看,它都难以划归“实录”、“信史”一类史学著作的范畴。整体而言,它属百科全书——是西周晚期所著《周易》之后最出色、最完备、堪称当时举世无双、至今仍感到无与伦比的一套百科全书;(13)而传记部份,则基本是历史文学(代表着唐以前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鲁迅的颂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严格说来,只有后半句可以成立。 这个结论,许多人可能一时不易接受,总觉得似有损于司马迁及其杰作的史学成就与光彩。但其实,正由于《史记》大量运用瑰伟的“文笔”,蕴含深邃的哲思、超凡的睿智和炽烈的感情色彩,才令其闪耀千载不灭的思想光辉。清人宋湘(1757-1826)诗云:“六经以外文章尽,三代而还世变兴。天扶日月风云气,史有龙门诗少陵!”[45]盛赞《史记》(和杜诗)是足以上配“六经”,流惠百代,作为华夏社会精神支柱的不朽之作。由此评价,足见《史记》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何崇高,其影响又是何等深远。这本划时代的鉅著,无愧是中华文化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而假若司马迁只如古代的“良史”般,满足于严格依循“国史策书之常(法)”,把《史记》写成一部诚实记事的“实录”(即真正的史书),那么它的价值恐将不出于历史学、语言学范围之外;而司马迁及其旷世杰构在整个人类思想史,尤其是文化学术史上的意义、地位和影响,与今天情况相比,也肯定不可同日而语。 注释: ①笔者早年发表《〈史记〉不是史》一文(刊广州《文艺与你》季刊1986年第二期),蒙北京《新华文摘》录载主要观点。其后又发表《再论〈史记〉不是史》(载香港《明报月刊》1990年第四期),对前文补充申说,并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之有关课程中作为专题讲授有年,引起一定反响(参见[美]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43页注1)。今复撰此文,拟从更广之角度,全面阐述鄙见,冀能得同道方家不吝赐教,共同研讨。 ②参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载张越编《史学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3-75页);[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又[美]J.W.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1869-1941)《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上卷,第一分册,第一编“古代”,1-206页。 ③《史记·六国年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卷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 ④详见杜预《春秋左传注·后序》。(《十三经注疏》第十六册,《春秋左传正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第2735页。)孔颖达“正义”云:“杜以《纪年》记事大似《春秋》之经,知古之史官记事如比。”同上,第2736页。 ⑤按,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参考的正是“西观周室”所见的各国“史记旧闻”。那些“史记”既“独藏周室”,必依王家所定的写作规范。而凭孔子“奉天法周”、尊王崇圣,不敢擅益“史之阙文”(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故往往“述而不作”的恭谨态度,可推知《春秋》的纂述也必遵王室统一标准,而不会亦“不敢”另辟蹊径。也就是说,现存《春秋》“据事迹实录”的体例和时有“微言大义”的“笔法”非由孔子所独创,乃是当年周王朝(包括各诸侯国)之“国史策书”编撰时共遵之写作模式,不过在《春秋》中,因曾经孔子“笔削”而更显细密、精严罢了。 ⑥这种观念自有其渊源,因为在古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克力奥居于九个文艺女神之首,所以(西方)古代历来把历史著作当作文艺的一支”。参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之“译者前言”第1页。 ⑦《孽海花》问世时,作者曾朴(笔名“东亚病夫”)说明:“本书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出版广告》)。其后为广宣传,又声称:“这部《孽海花》,却不同别的小说,空中楼阁,可以随意起灭,逞笔翻腾,一句假不来,一语谎不得……”。俨然以“信史”实录自命。后因诘责、质疑者众,渐觉招架为难,便改口道:“友人林琴南在《贼史》序上,揭明《孽海花》为曾朴所著,一时向余打交涉者甚多。至于《孽海花》之内容,诚如林琴南在《红礁画桨录》序上所说:《孽海花》非小说也,乃三十年之历史也。唯小说着笔时,虽不免有相当对象,遽认为信史,斤斤相持,则太不了解文艺作品为何物矣!”(崔万秋《东亚病夫访问记》)可见曾氏认为“历史著录”和“历史文学”还是要区分清楚的。详见拙著《闲话〈孽海花〉》(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11-16页。 ⑧关于中国文体的分类及其特点,请参阅拙文《论中国文体分类及文体与句法的关系》,载《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395-402页。 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云: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见《史记研究集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六卷《史记集评》(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汇辑),32页。关于这点,李长之、王靖宇两位有更深细的研究和分析。见李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五、七、九章,尤其90-92页、325-326页。王著《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七、司马迁为何要把一部历史著作也写成文学作品?”143-150页。 ⑩明人焦竑已有此见:“夫良史如迁,不废群籍……但其体制不醇,根据疏浅,甚有收摭鄙细而通于小说者”(《焦氏澹园集》卷二十三《经籍志论》,“史部·杂史”,《续修四库全书》13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 (11)《刺客列传》:“太史公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马非百云:“若荆轲刺秦王经过,则《战国策·燕策》述之甚详。《史记》不过转载之而已,非夏无且所道也。”(马菲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387页。) (12)宋.倪思、刘辰翁《班马异同》卷二十六。见《史记集评》,519页。李长之先生亦有类似看法:“司马迁写的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便也很像给后来的恋爱小说作了先驱,而朱家、郭解的故事也直然是《水浒传》一类小说的前身。”(《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九章,503页。) (13)关于《周易》本经的成书年代,详见周锡韦复《〈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兼论西周礼乐文化对中国韵文艺术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四期)一文的有关论述。近年经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又发现了更多《易经》著成于西周后期的有力证据,及其“以百科全书为‘体’而以占筮为‘用’”的性质特点,将以另文专论。标签:文学论文; 史记论文; 儒家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文; 读书论文; 司马迁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