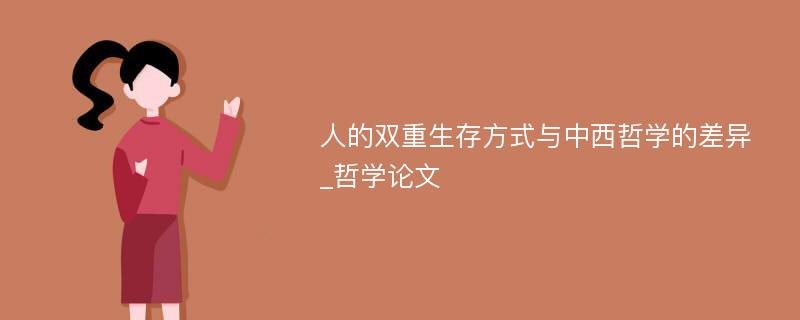
人的二重性存在方式和中西哲学的层面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层面论文,差异论文,哲学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 (2000)05-0040-07
近年来,国内有种说法影响很大,即:西方哲学是天人二分(主客二分)的,而中国哲学则相反,是天人合一的,后者有优越于前者之处。其实,中西哲学的内涵、外延、思维方式均有很大差异,进行简单的、浅层次上的比较显然是行不通的。本文试图从一个特殊角度,即人的二重性存在方式的角度,考察中西哲学的区分,并探讨中西哲学之间的层面差异,为二者的深层次对话和互动做点工作。
一、此岸与彼岸:一个西方哲学的主题
此岸与彼岸,这种比喻性的说法是指人的有限本性与无限本性。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员,本身具有生物性,人又是历史的,具体的人,在特定时空之中的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有认识能力上的,也有行为能力上的,这就是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人作为最高级的灵长类动物,具有自我意识,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即具有主体性,因而必然产生对自身能力的信任甚至崇拜,以及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趋向完善地步的要求(虽然它们是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人的无限性。人的有限本性和无限本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不能互相代替,这就形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上的二重性。与之相联系的还有现实与理想,必然与自由,是与应是……等一系列的二重性。对人的存在方式二重性的思考,可以说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一个主题。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主题。
1.古希腊罗马时期。
在西方的早期思想中,人对神和自然的敬畏是始终存在的。哲学之所以被叫做“爱智慧”就是因为,古希腊人认为智慧只属于神而不属于人,所以,人没有智慧,只有对智慧的爱。这意味着人永远不能达到神的地位。神和自然作为彼岸的“绝对者”,与人相对立,是人服从的对象。
但是,从泰勒斯开始,古希腊的哲人们就试图认识世界、总结宇宙的规律,试图接近神,理解“绝对者”,这就昭示着,在承认自身的绝对有限性的条件下,人已经开始有了超越界限的要求。从智者派开始,人真正成为哲学的中心。后来,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潜能变为现实的思想。可见他试图打通从有限性到无限性,从此岸到彼岸的哲学路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演化史的最初雏型。
古罗马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是希腊爱智传统到希伯来信仰传统的中介。其代表人物普罗提诺认为,人的最崇高事业就是要回到神,与神(太一)合一。他给出的途径是通过神秘直观。由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途径到普罗提诺的神秘途径,标志着一个哲学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哲学对人的二重性存在方式的思考即将进入新的阶段。
2.希伯来精神:原罪与救赎。
基督教哲学用人人俱有的“原罪”来代表人的有限性,认为人的肉体生命无法摆脱有限性。只有信仰上帝,把希望寄托在上帝复临和末日审判上,用对他人的爱和自身的修行来取得灵魂的最终解脱。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同古希腊罗马时期一样,人仍不能正确地理解人的无限本性,只能把人的无限性“让渡”给上帝,歪曲地投射到上帝身上,在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设置鸿沟。这一切最终根源都是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在当时还无法得到确证。
而且,现实的天主教教义和制度,用教会的统治和繁琐的礼仪体系代替了上帝的权威,导致人被动地屈服于神的代言人——教会的淫威,致使希伯来精神的内核——信仰精神和界限意识——中的合理成分受到遮蔽。不管是为了达到对人的二重性存在方式的正确理解,还是为了打破教权对人的禁锢和压迫,启蒙都是必须的。
3.近现代哲学:启蒙的命运。
启蒙是近代哲学的主题。近代是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时代,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强的证明。人的地位不断上升,和上帝分庭抗礼。所以,人不用把超越性、无限性赋予上帝,而是证明自身的超越性本质,无限性本质。这就是启蒙的哲学内涵之一。此岸与彼岸的张力依然存在,但二者不再分属人神两方,而是存在于人内部。
在近代哲学中,康德对人的二重性存在方式作了深刻的阐述。他限制了人类的知识(感性和知性)而为信仰和道德(在康德那里二者是接近的)留下了地盘。他区分了两重世界,即作为认识对象从属于自然律的现象界与作为现象界的根据的不受自然律支配的智性世界[1]。 前者是必然的,后者是自由的。自由是实践理性的主题,必然是纯粹理性(理论理性)的主题。人既属于现象界也属于智性世界。这恰恰是对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表达。康德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高扬理性,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同时,也看到了理性的局限性。康德谨守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界限。这表现在对道德法则的敬畏中。正因为人是有限者,所以不可能完全符合道德法则,道德法则来自于人的超越性。康德说:“在那个被‘自由’所建立并被实践理性提出来让人敬重的道德国度中,我们诚然是立法员,但是同时又是其中的臣民,而非统治者,因而我们如果忽视了我们(作为被造物)的低微等级,而妄自尊大地排斥了神圣法则的权威,那在精神上就已经背叛了那个法则,纵然我们实现了它的条文。”[2]康德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不恰当地夸大了超越性, 而伊壁鸠鲁正相反,把超越性最后归结为有限性,以属于感性世界的幸福作为最高原理,二者都是偏颇的。康德把上帝存在、灵魂不朽、意志自由作为道德哲学的三条公设(postulate )和超越性的“至善”概念联系在一起。“至善”包含两个成分,即至高的道德和至上的幸福,而且用道德来统率幸福。康德认为,伊壁鸠鲁派用幸福代替至善,固然错误,斯多葛派在把道德定为至善之条件的同时,却忽略了幸福,同样是偏颇的,只有基督教的教义才是最符合至善概念的。
康德对基督教伦理学的认同,不是道德哲学的宗教化,而恰恰相反,是宗教的道德化。康德把信仰统一于道德,置换了信仰的根基。上帝成为人的无限本性的代名词。康德实际上拯救了希伯来精神的积极内核,把它转变为对人的本质的确认。但是,康德的不足在于,他所表述的人的内在分裂是静态的、消极的,他把认识领域和价值领域绝对地分离开来,看不到这两个领域是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有机联系着的方面。所以,他所表述的人的二重性存在方式尚不全面。正如齐良骥先生所说:“康德习惯于抓个别的研究对象的实质,为了抓住这个实质,常常不顾种种关联,以致陷于孤立地看问题。这种方法使他常堕入形而上学再进而堕入先验唯心论而不能自拔”[1]。 康德的弱点是因为无法脱离当时自然科学影响下的孤立、片面、静止地看待问题的思考方式有关,也与16—18世纪欧洲哲学过于重视认识论的倾向有关。毕竟,人类实践活动的整体的哲学把握,是经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中介,直到马克思才达到的思维水准,也只有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才有提出这个理论的可能性。
启蒙哲学的一个最重大的后果,就是技术理性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内容之一,就是把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追根溯源至对启蒙本身的批判。启蒙演变到技术理性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是和人的实践密切相关的。技术理性的内涵是以技术所代表的价值为元价值,进一步就成为技术崇拜,它其实是把人类实践的手段变为目的,变为实践的评价标准。技术取代了神的位置,人把无限性赋予技术,技术因而成为人的膜拜对象,这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异化的表现。技术的异化导致无限性吞并和取代有限性,它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人成为单面人,成为技术的奴隶。
在本世纪,对技术理性的抗击,终于汇聚成声势浩大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它高扬人的非理性存在方式,高扬与技术理性相对的价值理性,其内在的要求,则是基于人类应该全面发展的理想。但人本主义思潮亦不无矫枉过正之嫌。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对立,象征着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深刻分裂,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刻分裂。
4.青年马克思:实践的二重性。
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想,隐含着对人的二重性存在方式的整体把握和全面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表现为实践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一方面,现实的以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实践的特定历史形态,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但其局限性就是产生异化,推而广之,一切具体的实践都有局限性,只有局限性的存在,才能推动人超越局限;另一方面,人类的实践的无限总体过程又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具有无限性、超越性,永无止境。
实践具有二重性,同样,作为人类实践的物质基础、对象和成果的自然,即人化自然,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和人在原始状态中是统一在一起的。不论是最初的自在自然,还是被人的实践参与和改造过的人化自然,都是人类实践的基础。人对自然的具体的改造活动都是有限的,所以,人化自然也有其有限性;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就是异化的扬弃和消除,是人与自然界的最终和谐和高度一致。人化自然作为实践的终极目标,又具有无限性。实践二重性和人化自然的二重性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青年马克思把现实与理想、是与应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统一在一起。从他的角度看,人关于彼岸或神的观念无非是人自身的无限性的歪曲的投射而已。人对神的感情起初是意味着对无法抗拒、无法改变的规律的敬畏,后来逐渐演变为对自身的无限性的信念。人由服从神,变为自身渴望成为神,这就是启蒙的历史,而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张力无法最终消除,二者在无限的人类实践中达到了动态的统一。
二、“天人合一”:一个中国式的迷误?
“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当然不能涵盖中国哲学的方方面面,但也不仅仅是儒家的一家之言。我在这里把它当作一种基本的思维取向、讨论问题所立足的一个基本语境,制约民族精神发展的一种主导性的内在的理论趋势来讨论。
“天人合一”的意义,按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分析,也是涵盖“是”与“应是”两层含义。如进一步区分,其中可分为“天人相通”与“天人相类”二种涵义,后者以董仲舒为代表,主张天人形体相类,性质相类。形体相类乃附会之谈,性质相类与“天人相通”一义相近。前者也分两层意义,一是指天人本身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二是指天道与人道相通。张岱年先生批评“天人相通”说的弊端在于:“表面上似将天道说为人性,而实际乃是将人性说为天道,即将人伦义理说为宇宙之主宰原则,这就陷于拟人的错误”[3], 此论甚为精当。这种“拟人的错误”不仅是儒家的错误,也是道家的错误,它的要害是掩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的实践关系。
所以,本文对天人合一所作的基本界定就是指中国传统哲学中各主要流派中共有的一项基本理论设定(各派对它的具体阐释不尽相同,但都未能偏离这个基本点),主要指人道与天道的本然合一状态,其中也涵盖着现实与理想,是与应是的两重性,只不过理想的,应是的维度指向本然状态的复归,所以具有保守性。
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相关,中国传统哲学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用化。中国是一个富有实用精神的民族,缺乏对纯粹知识的兴趣,形式逻辑体系没有产生在中国,中国的科学没有纯粹独立的形态,都与此种精神气质相关。在儒家看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以贯之的,“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并维持“道德—政治”的一体化秩序,通过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儒家思想中关于自身修养的思想特别发达,“为帝王师”的抱负也特别普遍的缘故。
在道家那里,情况也有相似之处。《老子》一书被称为“君人南面之术”,是因为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治国之本被提出来的。该书最明显的论证方式即“推天道以明人事”,所谓“道”,既是宇宙的最高原则,也是涵盖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老子对“道”的论述并不是抽象的,而是要落到实处,落到人(主要是君王)对规律性之“道”的运用上。庄子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不以治国为宗旨,但还是把“道”作为规律,只不过人掌握规律的目的是要维持个体生命,达到“逍遥”的境界而已,这在《养生主》等篇目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以后的黄老派、魏晋玄学派以及道教,在思维的基本取向上都未能摆脱老庄所规定的这个范围。
以上是大传统,即文人传统中实用化的表现。在小传统,即世俗传统方面,世俗的儒家道德与儒家经典的精神是一致的。民间宗教也充满了实用的精神,道教不用说,佛教和基督教的中国形态也有实用化的表现。中国本土宗教不能产生纯粹的、超越的宗教信仰,就是这种实用化的结果。
第二,伦理化。儒家所讲的“天”,不是指自然界,或主要不是指自然界,而主要是指作为先验的宇宙秩序的天道。“人”的含义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的人,而主要是道德人,是以纲常名教为代表的社会关系、名分秩序中的人。这个秩序被预设为贯通天人,“天”实际是现实中的道德关系的虚幻反映,这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的“拟人的错误”,这也就是儒家的泛道德主义的根源。
道家的伦理色彩相对要淡一些。老庄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具体规范,但也不是全盘反伦理。毋宁说,道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具体内容与儒家不同而已。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第四十五章),所以说,伦理化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特点。
第三,现成化。明代泰州学派的代表王艮、罗汝芳提出“良知现成”说,认为每个人都现成地自然具有良知,人只要循此良知自然而行便是成圣成贤的工夫。这种思想把以程朱为代表的艰苦的“格物致知”的工夫路线变为简单的内心体悟。其特点就是把常人与圣人的距离拉近、简化成圣途径。我把这种思想特色称为现成化。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流派都有一个现成化的过程,可以说明其思想的内在理路中存在着“现成化倾向”。
儒家从程朱到陆王再到王门后学的泰州学派,现成化色彩不断增加。程朱学派是界限意识比较强的学派。他们严守格物致知的工夫次序,认为格物是一个逐渐变化气质的过程,若单讲内心体悟,则离成圣甚远,因为圣人是道德人格、学识技艺的典范和极致,是儒家理想中的全面人格发展的目标,非朝夕可至,甚至用毕生的力量也难以达到,所以成圣工夫决不能简易化。朱熹批评陆九渊的“发明本心”、过分强调内心体悟路线的结果只能“为一乡善士”而不可能达到人格的终极完善[4] 。朱熹的思想和西方传统中严格区分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思维方式已经相当接近了,但由于深层思想背景的限制,他的思想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同时由于陆王派内心体悟的方式简便易行等多方面原因,在明中叶以后,王学逐渐盛行。到了泰州学派时期,现成化的流弊完全暴露出来:学者“认轻率放逸为天机”,自然放任,空谈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原始儒学的初衷,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现成化的思维来自于“天人合一”的内在逻辑。
道家的现成化特色在郭象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原初道家的基本理论设定是自然与人为二分,贬斥人为,崇尚自然。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在他看来,儒家的伦理道德属于人为,是违反人类自然本性的。而郭象主张“名教同于自然”之说,认为“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即认为,“落马首、穿牛鼻”也符合自然。这就导致把自然与人为混同起来,把儒家和道家混同起来,抹平“天”与“人”的差别,抹平理想与现实的差别(注:道家的理想是向自然的“原初状态”回归的,中西哲学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具体界定有很大差别。本文不准备讨论这些差别,关键在于中西传统如何对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郭象消解了老庄哲学批判现实的力度,使他的哲学沦为对现存秩序的论证。
现成化特点也表现在中国佛教之中,这就是慧能开创的禅宗哲学。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迷悟之别只在一念之间。它把佛教的修行平常化、世俗化,导致了简易化的结果,鼓吹“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种顿悟法门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不但影响了宋明理学(泰州学派的理论中就有受禅宗影响的成分),也进而影响了后来的整个文人传统和世俗信仰。为什么如此?禅宗的产生,本身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现成化色彩绝不是外来的,而是根植于本民族自身的思想趋向。
这里必须声明一点,现成化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特色,如同更基本的“天人合一”一样,我们不能对之作简单的褒贬,上述各派的内在思路不尽相同,我在这里也忽视不计。总的说,现成化的特点是“简易直截”,它把天国与尘世的差异减至最小。如果说,“天人合一”的思维在承认天人有同样的规则,有把两者统一在一起的基础和理论可能的同时也承认天人的现实差距的话,那么,现成化倾向就是在理论上努力地把这种差距减至最小,把人与天同一的过程和方式变得越发简单。
三、中西之异:自觉的实践层面和自发的伦理层面
综上所述,中西哲学中“人的有限/无限二重性”和“天人合一”其实分属两个层面:自觉的实践层面和自发的伦理层面。在这里,“实践”的意义来源于马克思,指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活动。“伦理”的意义指广义的交往关系,它包含狭义的伦理道德。从西方哲学的角度看,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觉的实践关系。通过人类实践的发展,神的无限性的观念逐渐转变为人的(实践的)无限性的观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通过实践,自然成为人化自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地揭示出了此岸与彼岸观念的真正来源和秘密,即人的实践二重性和存在方式的二重性。马克思揭示出,西方哲学关于此岸和彼岸的论述都可以被破译和转换为实践关系。而中国哲学所讲的天人关系是在自在自发的人类早期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自发伦理关系、价值关系。它以“人”的秩序为中心来定义“天”的秩序,从自然与人的早期的朴素的原始同一的经验出发,追求自然、社会秩序与个人的同一。对这两种传统不能简单加以褒贬。在人与社会、自然的调适、和谐及全面发展中,实践层面和伦理层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二者不是毫无关系的两张皮。也不应、不能分出高下。伦理层面是人类实践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一个内在的向度,不能把它单独抽出来,与实践相脱离。在康德那里,“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其实是人类实践的不同侧面,伦理层面统一于实践层面之中(注:康德所用的“实践”一词和笔者所论的“实践”一词含义不同。康德的“实践理性”从本文的视角看来,就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价值理性,它属于自为的伦理层面,不能把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自发伦理层面混合起来。)。哈贝马斯区分了“工具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前者应归属于狭义的实践,后者大致应归属于伦理层面,二者统一为广义的实践层面。而中国哲学基本属于狭义的伦理层面。所以中西哲学差异既包含着逻辑层面的差异,也包含着历史阶段差异。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涵盖了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统一发展的伦理、价值层面,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融会中西的新路。
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评价本文开头提到的“天人合一优越论”了。这种论点简单地把“天人”关系与“人与自然”关系等同起来,而没有注意二者之间的差异。它认为西方文化是“人征服自然”的,是“主客二分”的。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而忽视了西方哲学更根本的内核,即人的存在方式二重性及实践二重性。它忽略了人与自然之别是实践中必然要形成的分别,实践上(也包括认识上)的主客二分是人类实践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哲学从未自觉地达到过这个阶段)。所以人与自然关系(主客体关系)不同于“天人”关系,也不同于“此岸/彼岸”关系。中国的“天人”关系更多地落脚在主体间关系上,它必然着重于伦理层面或交往层面,只不过这种伦理层面或交往层面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实践活动之上。“天人合一优越论”不能区分实践层面和伦理层面。实际上,它是从中国传统的泛伦理主义预设出发的。强调伦理层面本身并没有错,错误在于忽视了人的实践层面,认为无主体、无实践的交往层面或伦理层面比实践层面优越。这种观点,无法改变中国哲学中实践的缺席状态。
“天人合一优越论”的另一件理论武器,是把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人的异化等现象作为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必然结果,从而要求结束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而且进一步主张利用“天人合一”来取代“主客二分”。此论粗看起来似乎不无合理之处。但这中间有着多重的理论误解和思维跳跃。除了对概念理解的混淆,以及对中西方思想背景差异的忽视以外,它把自然的破坏和人的异化一齐都算在了西方哲学的账上。其实,上述现象是东方和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共有的世界性现象,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不能简单理解为西方哲学的必然结果。上述现象只是人类实践的有限性一面的表现。人类的实践过程就是不断超越有限性、扬弃有限性的过程,没有哪一种具体的实践可以脱离有限与无限二重性的互动过程。
目前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靠抱残守缺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无的放矢、缺乏现实根据和逻辑根据的“阐释”或“改造”就能解决得了的。我们必须面对具体的实践,理解中西传统的真实底蕴,立足于具体的时空环境,提出既适应中国现实,又符合世界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对未来具有前瞻意义的哲学理解构架。中国正处于“后发现代化”的过程中,拒不接受外来的学理固然行不通,一味证明自身传统比外来传统优越,照样是故步自封的表现。我们不应固守既成传统,而是应勇于“拿来”、勇于创新,在实践中保持思想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1999-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