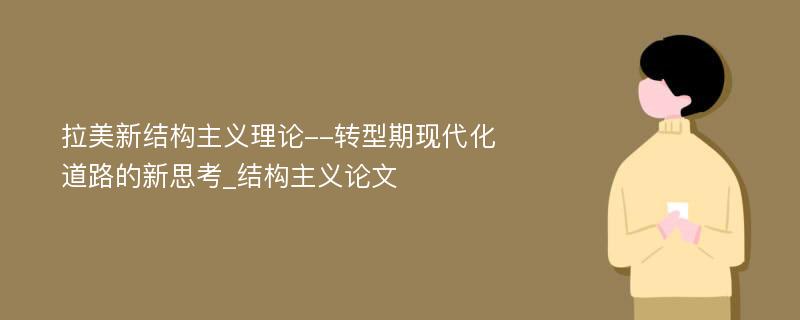
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转型时期现代化道路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时期论文,道路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拉美国家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并不亚于30年代初的大萧条,是其现代化的又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结构主义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导向的结构调整并不顺利,于是,新结构主义理论便悄然兴起,它既保留了传统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些内核,同时又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合理成分,是结构主义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调和的产物。早期新结构主义较多地关注经济的短期调整,力图通过非正统的稳定和调整计划,以较低的萎缩和衰退代价解决通货膨胀和贸易失调问题。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强调提高系统竞争力和社会公正,进入新世纪后,新结构主义理论日渐成熟,特别在社会政策的研究方面又有明显的新进展。近年来,新结构主义越来越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替代理论。本文拟对拉美新结构主义理论的演变、特点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一 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
新结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式微、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效果又不佳的情况下产生的。
结构主义是拉美经委会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拉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工业化论、结构性通货膨胀论、对发展障碍的分析以及一体化、计划化等。在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初期,这种理论曾对促进工业化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结构主义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对“中心”与“外围”关系的判断过于僵化;过分信任政府干预经济的优点;过分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过分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等等。特别是其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具有局限性,低估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尤其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在规范对外贸易、确定公共企业的目的和规则、选择促进投资、创造生产性就业、控制外国投资、建立金融体系等有效机制方面,结构主义发展思路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处理这些层面上的问题时也未形成系统的经济政策。拉美各国政府在实施结构主义政策过程中也有不少失误。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经委会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第一,进口替代工业化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非出口市场,对国际贸易的参与继续依赖于原料和初级产品,致使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继续受到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不利影响,不能形成国际收支的良性循环。第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进口替代虽然减少了消费品进口,但实施进口替代所需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某些原材料的进口却大大增加。加之国际市场上能源、机器设备等价格上涨高于拉美出口的农矿产品价格的上涨,因而使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连年出现逆差及与之关联的国内高通货膨胀。第三,过度的保护主义措施客观上吸引了跨国公司的进入,虽然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但购买技术的成本加大了,外汇需求也增多了,同时,长期受到保护的本国企业未能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依旧缺乏竞争力。第四,通过进口替代建立的工业部门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并不能解决日益加重的就业问题。第五,过度重视工业,忽视农业发展,土地改革大多半途夭折,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第六,高收入阶层模仿性的消费模式。外围模仿中心的消费习惯,却无法同时复制中心的生产能力,因此使得需求方的模仿与供给方的模仿之间产生了失衡。这种失衡阻碍着工业化以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收入向广大劳动力提供就业的机会。结果是经济改造的自我持续能力不断下降,对外部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增大。只有部分居民或集团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参与到相应的经济政治过程之中,而为数更多的居民则被排斥在发展成果之外。从而形成了现代生产部门和落后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局面。拉美经委会对有些问题已经有所察觉,60年代初就倡导“促进出口”,70年代中期平托提出了改变“发展方式”的论点,普雷维什后来又提出了“体制变革论”,但这时国内市场通过正式的地区一体化安排得到了扩大;有选择地推动非传统出口的政策缓和了反对出口的政策偏见;再加上1973年以后大量低利率贷款涌入导致拉美国家的“负债发展”①,拉美享受进口替代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结果延误了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转换。直到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最终走到了尽头,结构主义也失去了话语权。
新自由主义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在拉美国家,它主要以新货币主义政策形式对一些拉美国家产生了影响。当阿连德“智利社会主义道路”实验失败之后,新货币主义政策逐渐在一些拉美国家占据上风。新货币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货币供应量对名义收入变动起决定作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活动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变动的不稳定性,因而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关键;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通过价格机制而发生作用的。价格机制通过市场自发地起作用,最终总能使经济恢复均衡,因此,政府采取经济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只会造成不稳定;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当私人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时,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应当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当政府反复无常地变动货币增长率、不断打破货币供求的平衡时,才会破坏经济的稳定而导致经济动荡。因此,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当货币供应量明显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社会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时,通货膨胀就会发生。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最重要,货币的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因此,制止通货膨胀的唯一有效方法是限制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他主张把国家干预的重点放在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政策上,反对任何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新货币主义寻求通过废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来实现民族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完全一体化。这样,资源配置最终为国际价格和比较利益所控制。发展的节奏和方向将由国际市场力量而不是本国政府干预所决定。新货币主义取得的唯一成功是某些国家的对外出口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支撑这一成功的政策也导致了外债的急剧上升,巨额外债会抵消出口的增长。由此而来的净效果是国际收支明显恶化,在许多拉美国家,债务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的中心问题。作为新货币主义主要目标之一的降低通货膨胀,在最初获得了某些成功,但很快通货膨胀又开始加剧。更为重要的是,新货币主义的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虽有一种短暂的刺激作用,但却导致了非工业化、失业、收入不平等,加剧了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成果仅对一小部分人有好处。同时,新货币主义政策也极大地增加了一国经济应对外部条件变化的脆弱性。这样,当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衰退来临时,拉美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80~1985年下降了14%,南锥体国家的下降幅度更大。②
债务危机相应地加深了人们对新货币主义稳定政策的怀疑。债务危机发生后,IMF强加给拉美国家的稳定计划大多遵循新货币主义的路线,对经济危机作出的结论总是需求过度,而忽视了供给因素。与IMF旧处方不同的是将反通货膨胀措施与意在减少债务负担的政策结合在一起。一些稳定措施的目的是减少进口和促进出口,以便停止举借外债。用来专门对付通货膨胀的政策包括:控制银行信贷、提高利率,减少政府赤字,抑制名义工资上升,取消价格控制。这些紧缩计划的效果是穷人收入不同程度的急剧下降,失业率上升,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憎恨IMF干预其经济政策的制订。但大多数债务国又不得不与IMF达成条件,以便得到急需的贷款,尤其是同外国银行谈判重新安排债务时,这些银行答应借款的唯一前提是债务国必须吞下IMF的苦药。但问题是IMF制定的一揽子调整计划到8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成功的迹象。
就在拉美国家由IMF倡导的经济结构调整遇到僵局的同时,东亚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东亚国家因成功地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改善了它们融入国际经济的地位)。东亚的经验很重要,它对国际多边机构和工业化国家政府强加给拉美国家的结构调整建议提出了质疑。第一,当结构调整的捍卫者拥护弱化甚至取消国家作用的时候,东亚国家宣布赞成更大的国家管理。第二,当结构调整计划按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利益原则寻求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候,东亚国家将它们的竞争力建立在与新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基础之上。第三,当结构调整的捍卫者劝说拉美国家重新确定它们面向国外市场的发展战略的时候,东亚经济在国内市场与对外出口活动中保持了紧密的、充满活力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东亚经验构成了对拉美主流经济政策的一个真正的否定。③
同时,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也要求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出现。新货币主义模式的推行最初发生在军人威权主义政府的框架内。在某些拉美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左翼政党的国家,新货币主义政策只能在镇压的环境下推行。一种矛盾的现象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常通过政治上的反自由主义而获得。新货币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削减工资,以带来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下降。这将有助于减缓通货膨胀,也有助于一些工业企业在面临取消保护主义措施的情况下仍保持竞争力。尽管新货币主义政府宣布让市场力量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它们明确地干预劳动力市场。在许多国家,这种干预意味着一系列镇压措施。另外,民众主义和发展主义年代建立的有限的国家福利也被大大地削弱。新货币主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结构,鼓励了物质主义的个人主义。结果,人们要求公民自由、人权、民主权的呼声和反对军人政权及其新货币主义政策的呼声日见增高。到80年代后期在那些军人独裁让位给文人政府的国家(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形成了拥护新结构主义政策的群众基础。
巴西和阿根廷的新的民主政权和秘鲁阿兰·加西亚的民众主义政府已经采取了结合结构主义和货币主义特征的新的稳定政策。这些包含一整套经济和社会措施的“非正统休克”稳定计划包括阿根廷的奥斯特拉尔计划(AUSTRAL,1985)、巴西的克鲁扎多计划(CRUZADO,1986)、秘鲁的印蒂计划(INTI,1985),这些计划的名字来自各自国家的新货币,在这些计划中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取得民众的支持。尽管这些计划带有激进的性质,但它们最初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先前的货币主义稳定政策受到广泛怀疑,且在经历多年专制统治之后,巴西和阿根廷的新的文官政府及秘鲁加西亚的民众主义政府得到了认同。同时猖獗一时的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得到了控制。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早期新结构主义初露端倪。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早期新结构主义力图通过非正统的稳定和调整计划,以较低的萎缩和衰退代价解决通货膨胀和贸易失调问题。因此,同新自由主义一样,当时的新结构主义实际上成为一种处理短期经济问题的理论。新结构主义面对新的现实,在继承结构主义通货膨胀理论和批判货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惯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非正统“休克疗法”的主张⑤,新结构主义的创新在于将通货膨胀预期理论和惯性通货膨胀的概念以及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引入结构主义理论的分析模式,强调传播机制的作用;提出在短期内消除惯性通货膨胀的一整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主义理论忽视短期调整政策的不足;将反通货膨胀列为优先目标,认为它是经济获得新发展能力的先决条件。⑥ 新结构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消除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新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偏重于消除通货膨胀的传播机制,忽视消除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结果在惯性通货膨胀被初步克服之后,因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依然存在,惯性通货膨胀继续重现,致使反通货膨胀政策最终失败。美国经济学家A.费希洛在80年代中期曾简略地提到了这一时期新结构主义学派在外债、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和国家作用4个方面的独到见解⑦:不能因为偿还债务而牺牲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同IMF和债权银行的重新谈判来减轻外债负担;在许多国家中,通货膨胀问题是同外债管理有联系的,并且一般说来同国际经济震荡的联系更密切,因此,否认正统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有些政府为了保持稳定,实行了用大量增加名义工资来补偿实际收入下降的政策,但这会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压力,未来的考验是分配新增长的收益能力,公共政策应该在就业目标和对付赤贫及失业方面影响生产;倾向于重建一个有效的发展主义国家,支持政府在生产方面实行更多的干预。
1988年4月《拉美经委会评论》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⑧ 初步勾勒出拉美早期新结构主义的大致轮廓。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在题为《新结构主义思路的轮廓》一文中对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联系债务危机前后拉美经济运行的实践,着重强调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提出的理论和经济政策,并分别就二者的理论、经济政策两个方面各列出了10点加以对比,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最后强调,新结构主义尚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就它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地区自主发展的政策方面需要有进一步设计。另一篇文章是塞尔休·比塔尔的《拉美的新保守主义与新结构主义》。作者宣称,在拉美“新自由主义”是用来表示旨在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削弱国家作用、贸易和金融更加开放的一整套经济措施,但在英语国家中,这些政策更多地以“新保守主义”闻名,除了这些经济内容外,“新保守主义”还与政治考虑联系在一起。作者指出,大多数拉美经济学家认为结构调整计划并不成功,危机仍然持续不断,他们正在形成一些共识,诸如必须超越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计划与市场、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等所谓的两难困境,实际上这种二元对立是可以相互兼容的;承认政治和制度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确认通货膨胀是一种社会现象;认同增加国内储蓄水平以提高投资率的紧迫性;必须降低参与国际经济的风险;为保证实现自主增长和提高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需要拥有自己的生产和技术基地以及协调核心;必须为拉美一体化注入新的活力;必须改变IMF的调整形式;必须尝试建立基础广泛的社会联盟以便长期支持新的发展战略。然后,比塔尔归纳了新结构主义在对外贸易、生产结构、金融、储蓄和投资、收入分配、国家的作用、其他政治和社会因素等方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针。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拉美早期新结构主义思路的一个概括总结。
二 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形成
就在拉美多数经济学家转向短期调整与稳定研究的时候,少数经济学家对经济长期发展的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拉美经委会关于发展战略的辩论奠定了基础,其中的两本重要著作是智利经济学家费尔南多·法齐贝尔撰写的。一本是1983年出版的《拉丁美洲未竟的工业化》⑨,它对拉美工业化进程的停滞作出了独到的分析,指出这种工业化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差距、缺点和扭曲的方面,建议走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新工业化基于一种赢得“增长和创造力”意义上的效率概念,基于技术进步的内源核心的创造上。另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拉美的工业化:从“黑箱”到“空箱”》⑩,这是一项拉美国家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作者指出,与兼顾增长和分配的韩国和西班牙不同,拉美国家可分为3种类型:快速增长但收入集中;拥有比较好的收入分配但增长速度缓慢;两者表现都很差,收入集中而没有增长。作者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结构主义工业化战略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即“黑箱”(技术进步匮乏)和“空箱”(不平等),由此而倡导新的发展战略。法齐贝尔的著作为拉美经委会随后发表的《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的报告奠定了概念基础。
1990年拉美经委会发表的《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报告在对80年代拉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估价的基础上,对拉美国家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的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经济地位的改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家的作用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它代表了拉美经委会对发展理论的重新定向,第一次希望把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三者结合在一起制定发展战略。(11) 这一思路又被随后的两个出版物所完善,即1991年拉美经委会环境部提交的《持续发展:变革生产模式、社会公正和环境》和1992年提交的《公正与变革生产模式:一种整体考虑的思路》报告。报告强调了环境问题,深化了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解释。这些成果成为拉美新结构主义形成的标志。但是,新结构主义思路还不够充实和丰满。
1993年由奥斯瓦尔多·松克尔主编的《从内部发展:对拉美新结构主义思路的探讨》一书出版。(12) 该书由关于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数篇专题论文组成,各章基本都是先回顾50年代的结构主义理论,再与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经历相比较,强调它们的成功和失败之处,建议改进传统结构主义思路,提出克服危机和重新走上发展之路的总体方针和具体政策建议。在这本书里,松克尔提出了“从内部发展”的新的发展战略,这代表了拉美人试图形成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战略的尝试,是对新结构主义思路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拉美经委会在整个90年代又从下述4个专题上深化了对1990年报告的诠释。
第一是“开放的地区主义”。(13) 拉美经委会的文件强调拉美通过目前的一体化计划加强区内贸易和同时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好处。开放的地区主义是兼容政策导向的一体化与受到非歧视政策鼓励的实践中的一体化这两种因素,这种方法有利于拉美国家竞争力的发展,同时对更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一定的屏障。换句话说,兼容对外部世界(主要指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低壁垒和区域内国家间互惠这两个方面。开放的地区主义既区别于从前封闭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并非要求全世界同等地和完全彻底地开放。
第二是本地区的金融脆弱性。拉美经委会在1994年代表大会文件的第三部分中第一次提到这个问题(14),该项研究对资本市场的脆弱性提出了警告,指出目前资本流入的逆向效果并未导致生产性投资和出口竞争力的相应增加。尤其是指出了使用资本流入作为一种价格稳定因素的危险性,因为这样的行为导致汇率上升,与(要求中长期对外账户平衡的)贸易平衡的表现不协调。因此,提议建立周密的银行规范政策,认为在金融自由化阶段更应如此。
第三是财政问题。拉美经委会1998年代表大会文件提供了一种对本地区财政问题宽泛的经验性和分析性观点。(15) 这些文件关于“财政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巩固财政调整,增加公共支出的生产率、透明度、推动社会公正和民主体制等。
第四是可持续发展。拉美经委会在整个90年代的文件中都指出了发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强调环境保护与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之间的辩证关系。拉美经委会利用世界峰会扩展了它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分析了公共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由于对发达国家和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来源有了一种新的环境视角,国际贸易谈判的筹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进入世纪之交以来,拉美经委会的研究突显了全球秩序中严重的非对称性,表明在这一秩序中拉美和加勒比一体化的条件逆向地影响了该地区生产和金融条件,引起了严重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低水平的经济增长和逆向的社会效果。拉美经委会也根据国际上不断增加的对拉美经济脆弱性的确认,扩大了其针对改革影响的警示性和批评性的观点,宣称需要寻找更加平衡的全球化方式,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第二次改革。
拉美经委会2000年和2002年的代表大会文件,在国家、地区、国际范围的经济政策议程是相互补充的,它们的建议包括:纠正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的非均衡性,加强制度建设,一种宏观经济稳定的宽阔视野,生产性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强社会联系,环境的持续性,地区范围的关键作用,等等。(16)
从2004年开始,拉美经委会提出了“一体化与社会凝聚”的新思想。社会凝聚的概念来源于欧盟,在欧盟的发展过程中,欧洲人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实行积极的政策消除地区差距,由此导致了1975年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创立,1992年随着欧洲社会基金的建立,社会凝聚成为欧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拉美经委会提出的社会凝聚的概念是“制度上的社会容纳和排斥机制与公民对这些机制运行方式的反应、感受、态度之间的辩证关系”。(17) 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地区内部各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鉴于这种情况,拉美经委会提出,在加速发展进程的同时,必须强调社会政策,在设计财政契约以满足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方面做出努力,同时要发展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建立社会凝聚基金,从而把社会公正提高到地区层面。
总之,拉美的新结构主义思想正在不断被发展和完善,并在实践中走向成熟。(18)
三 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拉美新结构主义主要体现在拉美经委会《改变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的报告和后来的一系列文件以及松克尔主编的《从内部发展:对拉美新结构主义思路的探讨》一书中,其最主要和最有新意之处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指出了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
新结构主义认为,拉美主要的经济问题基本不是经济政策引起的扭曲,而是来源于内生的、结构的和历史的问题。它强调80年代末拉美经济的3个特征:由于未能改善初级产品生产者的地位,生产的国际专业化缺乏潜在活力;盛行一种内部相互脱节的、高度异质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使技术进步无法推广,并无力充分地和生产性地吸收新增劳动力;收入分配始终将大多数人排斥在进步成果之外,这种制度无力显著地减轻贫困。(19)
(二)提出了系统竞争力的思想
拉美经委会认为,80年代的结构调整再次使拉美经济转向专门发展拥有相对优势的部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的依附性和落后性更加突出。变革生产模式主要目的之一是将这种经济转向高附加值和高增长潜力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活动上,而这又需要更多地建立在生产过程对技术进步进行周密而有系统地吸收的基础上。技术进步不仅仅局限在技术的采用上,而且包括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生产组织改善以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上。为此,必须强调系统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国家之中,尽管企业起着关键作用,但它是连接制度、技术、能源和运输基础结构、雇主和雇工之间、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以及金融部门等的一个完整的网络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企业是被纳入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之中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加速生产模式的变革需要坚决的、持久的努力,而最重要的是需要恰当的整体努力”(20),通过整个系统提高生产率。拉美经委会号召整个生产系统的现代化,强调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提高整个系统的生产率。这样,工业化必须超越狭窄的传统部门框架,与初级产品部门和服务部门相联系,形成整个生产系统的一体化,并逐渐推动生产力水平的一致性。同时,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变革生产模式也要与保护自然环境相一致,资源和环境必须被充分地纳入到发展进程之中。这一思想无疑是受法齐贝尔观点的启发。
(三)强调“从内部发展”的思想
“从内部发展”的战略与“内向发展”是截然不同的。“内向发展”把重心放在需求、扩大内部市场,以及用当地产品取代原来进口的产品方面,从而形成一种扩大国内消费,重复中心国家的消费模式、工业生产模式和技术模式的战略,具体体现为进口替代进程。这个进程是由极不平等的国内收入分配所造成的一种狭小的、倾斜的内部需求来引导的。也就是说,进口替代进程是以满足社会中上阶层的需求为目的的。这种工业化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普雷维什工业化思想的初衷,因为普雷维什认为,就像工业革命以来的中心国家一样,拉美国家的国内工业化进程会创造一种内生的资本积累机制,产生技术进步和改进生产力,他当年强调的是生产,是经济的供给方面。松克尔重申普雷维什的这一思想,并将其放大。他认为,内部发展的重心应该放在供给方面,而不是在需求方面。借用法齐贝尔的话说,这是“一种内部的创造性努力,争取建立一种同本国的具体缺陷和实际潜力相适应的生产结构”。这种发展首先要求建立一批支柱性产业,如钢铁、电力机械、金属加工、基础化学和石油化工,以及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并积极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加强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协调。在此基础上,加强大工业与中、小企业,科学技术机构、各级人才培训机构、群众性通讯手段以及制定战略、政策、标准的公共机构之间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一旦各方代表的通讯、交流形成,作为一种全国行为的决策水平得到巩固,一种“内生的技术动力的核心”就将形成。(21) 这种战略是要创造一种内生的产生和积累技术进步的机制,能使拉美发展自己的能力以提高生产力,实现带有活力的增长。它决不是要把工业化再度引向“进口替代”,因为这最终将陷入一种无出路的境地。恰恰相反,是要把工业化引向在长期发展战略中被认为是优先的和有希望的国内外市场,而且在这些市场上,拉美国家能够拥有或能够获得保证自己稳固参与世界经济的相对优势。换句话说,真正的关键不在需求和市场,发展的核心在于供给方面,如质量、灵活性、生产资源的综合和有效使用、对技术进步的审慎吸收、革新努力和创造性……总之,从内部做出独立性的努力,以实现自我持续的发展。(22) 这一思想是松克尔的贡献。
(四)强调社会公正
拉美经委会认为社会公正是增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生产进程。法齐贝尔讲:“拉美经委会建议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竞争力和改善社会公正,并认为二者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没有社会公正的竞争力最终将被证明是短命的,而至少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没有竞争力的社会公正也是短命的。”“不仅由于种族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要取得社会公正,而且为了获得现代商品和服务,取得社会公正也是必要的。”(23)1990年的报告把社会公正提高到了战略方针的高度,并提出采取补充性的重新分配措施,包括提供技术、金融、服务和大量培训小企业家、个体经营者和农民的计划;改革各种建立小型工商业的规章;使社会服务适应最贫困阶层的需求;促进相互援助的措施和恰当地向当局反映贫困阶层的要求;采取措施在收入和有关公共开支趋向两方面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潜力,等等。(24) 国家应该优先关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在生产、生产率、收入和社会服务方面对最贫困和最易受损害的阶层提供支持,缩小外部冲击对他们的影响;第二,减少结构调整中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重新配置劳动力的代价;第三,一旦增长恢复,就要为根除贫困和解决收入及财富的过度集中提供便利。同时,为了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和吸纳劳动力,有必要采取一项重视非正规部门的新战略。(25)
(五)重新阐释国家的作用
拉美经委会认为,1990年代国家工作的重心应该发生变化,要从80年代集中解决偿付外债问题转移到推动形成真正的竞争力和社会公正问题上。同时,要分清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分清哪些属于国家干预的领域,哪些是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干预的形式会发生新的变化,确定公共行为的作用和保证其有效的执行方式很重要。(26) 要坚持有选择的政府干预,实质性问题不是国家规模的大小,而是其管理能力和与私人部门达成共识的能力。国家应该通过积极的、有活力的行动来补充市场。就新阶段国家的作用而言,目前需要加强其传统职能、基本职能和辅助职能,而不是加强其生产职能。国家作为“从内部发展”的有效推动者,应该制定一个优化干预的战略,该战略包括确立优先干预的领域;对公共管理实行分权和非政治化;建立干预的平衡机制等。(27)
(六)提出建立一种公开的参与式的民主政治体制
拉美经委会认为,变革生产模式必须基于人们对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共同参与的政治背景的确认,也就是说,支持任何国家意图的协议必须通过建立共识来达成,社会冲突必须保持在民主制度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因此,一方面,需要建立参与性的政治体系,为了得到中产阶级和城市民众阶层的支持,有必要保证他们短期和中期内能够分享到变革进程的好处。(28) 通过作为利益代表和有效对话者的稳定的社会组织来加强政治参与,对增强民主功能很重要。对那些由于种族、年龄、社会、地域、性别关系的特征通常被排除在发展的好处之外的个人和团体,应该专门为他们创造一种实际参与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协调各种代理人的行为,“协调战略”包括政府和主要的政治、社会代理人之间就合理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以及由此所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进行的体制改革达成各种广泛的明确和含蓄的协议。理想的结果是加强雇主与工人之间共识的直接形成,国家只是作为被最终诉求的调解人。(29)
另外,新结构主义的内容还包括重视基本的宏观经济平衡,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可持续发展,以及关于工业、农业、金融、贸易、技术、环境等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议。
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罗森塔尔概括道:新结构主义“是正统经济理论和非正统经济理论的结合,换句话说,即一种稳定的一致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在微观和中观经济层面的新干预形式的结合。”(30) 新结构主义实际上是对传统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因此,它既有与二者相似之处,又与它们有所区别。关于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异同之处,法齐贝尔概括得最精确。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工业与发展》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谈到,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相同之处涉及4个领域,即改革的紧迫性、全球经济联系、国家的新作用和宏观经济平衡。他认为二者都相信必须加强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必须密切拉美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必须改变国家在拉美发展新阶段中的作用;必须重视宏观经济平衡。同时,他指出二者具有差异性。(1)形成理论思路的方法不同:新结构主义基于拉美发展进程与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进程比较的基础之上,而新自由主义则基于某种经济理论模型。(2)实现社会公正的方式不同:前者依靠每个人参与生产过程,而后者依靠市场力量。(3)对技术进步重要性的强调不同:前者认为技术进步在推动生产力和竞争力中发挥了一种关键的作用,并将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再分配的公正性,而后者则没有把技术进步的地位提到如此之高。(4)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方式不同:前者强调通过技术进步得到增强的竞争力是真正的竞争力,不再看重通过降低工资或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得到增强的竞争力,而后者虽然强调与全球经济和出口联系的重要性,但因忽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并没有区分竞争力的不同类型。(5)对生产部门联系的观点不同:前者认为制造业是技术进步的传播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该部门必须与农业、服务业等其他部门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而后者认为各生产部门在推动生产活动方面没有什么区别。(6)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不同:前者认为国家与市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而后者强调国家的辅助作用,认为国家的作用越小越好。(7)对宏观经济平衡的理解不同,尽管都认为保证宏观经济平衡很重要:前者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并非充足条件,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体制因素,而后者并不重视维系宏观经济平衡所需要的体制因素。(8)对政治体制与改革的关系看法不同:前者把建立一种公开的、参与式民主制度作为改革方案的保障,而后者则认为具体的政治制度类型更多的是一种本地偏好问题。(31)
新结构主义与传统结构主义也有许多差别。如在工业化与国际贸易问题上,二者虽然都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把进口替代看作建立本地高效的和有竞争力的产业基础以及打入国际贸易市场的必要阶段,把推动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看作以更为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贸易市场的一种准备条件。但是,结构主义更强调国际环境的不利因素和拉美国家的欠发达,认为加速发展进程就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尽管不排除出口的可能性。而新结构主义则认为,为了发展国内外市场,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同时,加速推动出口是非常必要的。新结构主义强调“开放的地区主义”。同时,新结构主义强调的工业化不再是“内向发展”的工业化,而是“从内部发展”的工业化。
关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二者都对“市场主宰论”表示怀疑,都主张为了维护私人经营活动,需要有一个积极的和有效的政府。但是,结构主义认为,为提高私人部门的活力而实施的国家干预是重要的,更强调政府作用,而新结构主义则坚持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相结合,强调为保持市场活力进行有选择的政府干预。干预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要求国家注重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私人部门不能作为的领域、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再分配领域。
关于经济稳定与发展问题,二者都对关于通货膨胀起因于货币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通货膨胀是导致价格上升的因素与其传播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二者用来解释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不同,结构主义更强调导致通货膨胀的结构因素,而80年代的早期结构主义强调导致通货膨胀的惯性因素,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强调惯性和结构两方面的因素。二者形成政策的方法也有区别,结构主义的特点是缺乏对短期问题的分析,早期新结构主义仅仅强调短期稳定和调整政策,而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则综合了短期和长期的稳定与发展措施。(32)
另外,新结构主义强调社会公正,但认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既不能像传统结构主义那样单纯强调依靠国家的力量,也不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单纯强调依靠市场的力量,而应该依靠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两条腿走路。
总之,新结构主义建立在传统的结构主义基础之上,同时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长处,为拉美各国提出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新的发展思路和政策。
四 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
尽管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导向的结构调整并不成功,但这被解释为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不彻底的缘故,在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压力之下,9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在整个拉美大陆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到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新结构主义的影响逐渐显露头角。
第一,新结构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产生了影响。拉美新结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并在这10年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但90年代拉美的主流经济思潮仍然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范式在1989年被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森归纳为10条原则,即所谓“华盛顿共识”。(33)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如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崩溃,一些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拉美地区重新出现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由于受新结构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在1996年之后也发生了与新结构主义的趋同。因为在这一年的泛美银行年会上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华盛顿共识”的第二个版本,即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其中增添了政府应该增加在社会领域、特别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公共开支;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必须重视通过对制度和人力资源的投资来创造一种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34) 这些内容的补充无疑是受到了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据德国学者查尔斯·戈尔的研究,“后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是受到了南方共识的影响,所谓“南方共识”是一种政策性结论,它是在拉美经委会1990年的报告和亚太经社理事会1990年描述的东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4年、1996年、1997年和1998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进一步阐述所形成的,这种思路强调了发展的目的是“以人为核心”,检验发展的最终标准是人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了改善,发展应该建立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援助国平等伙伴的基础上。相反,原来的“华盛顿共识”强调发展的核心是GDP的增长,发展是自上而下的、援助国附带条件的帮助以及出口导向的战略。一方面是《贸易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的人文发展指数”推动了国际多边机构把减轻贫困作为发展的目标,使“华盛顿共识”增加了人情味。另一方面“南方共识”中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作的不同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是令人信服的,迫使“华盛顿共识”转变其观点。(35) 最终是拉美的新结构主义范式影响和改造了新自由主义范式。
第二,新结构主义为拉美政坛坚持“第三条道路”的党派提供了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到90年代末,当人们回顾新自由主义改革成效的时候发现,尽管这10年里拉美实现了新的经济增长和抑制了高通货膨胀,发展模式发生了转换,地区一体化得到了加强,但是,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经济的快速自由化和外向化加深了国民经济的脆弱性;二是失业增加和非正规部门扩大;三是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人口急剧增加。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拉美发生了几次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增加了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怀疑,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呼声开始高涨。新结构主义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名气大增的时期,以至于美国社会科学界也将对拉美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与新结构主义有关的若干课题。
面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问题,一批拉美政坛的新秀试图选择一种既不太右、也不太左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如墨西哥的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巴西的卢拉、智利的拉戈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人,而新结构主义思想就成为这一政治派别所提出的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如查韦斯主张走一条“既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也不是国家主义的”,而是一条介于二者之间的、市场经济与国家作用结合的、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坚持民族利益并举的道路,也就是他所说的“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目的是想通过“和平、民主革命”,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权利国家”(36)。由于新结构主义在拉美国家有了“市场”,拉美经委会也从新结构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中重新找回了尊严。
第三,新结构主义思路体现于拉美左派的发展纲领中。进入21世纪后,随着拉美地区广大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高涨,社会运动的兴起,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拉美的“第三条道路”向左转,左翼运动出现新的高涨,特别到2006年大选之后,10个举行选举的国家中有巴西、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7个国家的左翼或中左翼领导人赢得了国家领导权。加上此前赢得大选的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结果,除古巴之外拉美已经有12个国家属于左翼政权,这些国家的人口之和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5亿总人口的70%以上,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80%。这些左翼政权上台后,一般都强调加强国家的作用,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公正给予更多的关注,如查韦斯1998年执政后,在委内瑞拉实行土地改革、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政策。2003年至今,查韦斯政府推行了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住房等近20项社会扶助计划,并实行免费公共医疗和小学、中学、大学的免费教育。委内瑞拉贫困人口比查韦斯执政之初已大幅度减少。巴西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在2002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口号是:“让巴西人能够吃饱早餐、午餐和晚餐”。4年后,他再次参加竞选的口号仍然是让更多的巴西人摆脱贫困。卢拉在第一个任期内,实现了他所许诺的部分目标。从2002年上台以来,卢拉政府接连推出了家庭补助、教育补贴、东北地区电力发展计划等一系列帮助贫困人口和地区的措施,直接受益人口达1亿多,使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20%。此外,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尼加拉瓜和厄瓜多尔等国也已经或者表示将要采取同样的支持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从拉美左派的发展纲领中,我们不难看到新结构主义范式的影响。在2004年10月3日《您好,总统!》第206辑电视节目中,查韦斯直接号召全国民众阅读松克尔的《内向发展:对拉美新结构主义思路的探讨》,学习该书中提出的新结构主义关于从内部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37)
当然,对新结构主义的影响也不宜估计过高。由于世纪之交以来拉美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新结构主义也遭到了批评,如有的学者指出,拉美经委会假定现代制度的变革有助于民主化,但现代技术的引进并没有导致自动地创造竞争力体系,也没有看到依靠技术的帮助来解决社会问题,拉美经委会的乐观主义完全没有得到证实。拉美经委会的确勾画了一种共识的轮廓,但并没有解释如何去实现它;新结构主义发展政策的实行必须由国家启动,但国家如何能使这种建议被接受,如果遇到工会、企业家等利益集团阻碍的话,如果国家本身缺乏自主性的话,如果民主体制不能推动这种激进改革的话,我们是否还要接受威权主义政权?拉美经委会的文件并没有描述从传统的进口替代模式到一种开放的面向世界经济的模式过渡会是如此的不稳定和困难。新结构主义低估了结构调整项目的社会经济成本。(38) 还有的学者指出,拉美新结构主义屈从于新自由主义,虽说是在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实质性的成分,抛弃了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因素。作为长期传播拉美经委会思想的喉舌的《拉美经委会评论》,在逐渐地向诸如世界银行、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多边机构的一些以其正统立场而著名的作者开放。1999年2月拉美经委会竟然毫不犹豫地推荐拉美经济美元化。这说明拉美经委会在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认可方面已经走得很远。(39)
我们认为,总的看来,新结构主义思路不能被解释成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屈服,而是结构主义在一种新的历史现实下的变通。它是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拉美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加速的国际环境下,继承传统结构主义理论的内核,吸纳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合理成分,对两者加以综合而提出来的,并在90年代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尽管新结构主义思路仍存在缺陷,但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它是拉美各国替代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相对可信的和可行的选择,它的影响力在未来几年还会有不断扩大之势。
收稿日期:2007-10-20
注释:
① Gert Rosenthal,“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ies :the Way Ahead”,Cepal Review,Vol.60,December 1996,p.10.
② Cristobal Kay,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velopment,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89,p.202.
③ Hector Guillenromo,“From the ECLAC Development Order to Neo-Structuralism in Latin America”,Comercio Exterior,April 2007.http://revistas.bancomext.gob.mx/rce/en/articleReader.jsp?id=3 & idRevista=89
④ 但在取得一些最初的成功之后,这些稳定计划最终被放弃,因为政府、企业和工会之间没能就如何分摊沉重的调整负担而达成共识,并且对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尚缺少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⑤ Ricardo Bielschowsky,“Evolución de las Ideas de la CEPAL”,Revista de la CEPAL,Número Extraordinario,Octubre de 1998.http://www.eclac.cl/publicaciones/SecretariaEjecutiva/7/
LCG2037PE/bielchow.htm
⑥ 陈舜英等著:《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拉丁美洲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33页。
⑦ Albert Fishlow,“The State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s”,in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Insights From Six Disciplines,Edited by Christopher Mitchel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88,pp.110-115.
⑧ Ricardo Ffrench - Davis,“An Outline of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Cepal Review No.34,April 1988,pp.37-44 ; Sergio Bitar,“Neo-Conservatism Versus Neo-Struturalism in Latin America”,Cepal Review,No.34,April 1988,pp.45-62.
⑨ Fernando Fajnzylber,La Industrialization Trunca de Ame-
rica Latina,CET.Mexico D.F.1983.
⑩ Fernando Fajnzylber,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from the“Black Box”to the“Empty Box”,UN,ECLAC,Santiago,Chile,1990.
(11) ECLAC,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 Santiago,Chile,1990.
(12) 其中松克尔和拉莫斯写的《走向一种新结构主义的综合》一文成为松克尔和苏莱塔合写的《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文的主要部分发表在1990年12月号《拉美经委会评论》上。见Osvado Sunkel,Gustavo Zuleta,“Neo- Structura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 in the 1990s”,Cepal Review,No.42,December 1990,pp.45-51.
(13) CEPAL,El Regionalismo Abierto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La lntegración Económica al Servicio de la Transformación Productiva con Equidad (LC/G.1801/Rev.I- P) ,Santiago de Chile.Public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N'de Venta:S.1994.Ⅱ.G.3.
(14) CEPAL,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Políticas para Mejorar la Inserción en la Economía Mundial ( LC/G.1800/Rev.1 P),Santiago de Chile,Public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N' de Venta:S.1995.Ⅱ.G.6.Segunda Edición Revisada y Acatulizada,Santiago de Chile,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1998.
(15) CEPAL,El Pacto Fiscal,Fortalezus,Debilidades y Desafíos(LC/G.1997/Rev.1 ),Santiago de Chile,Public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N' de Venta:S.1998.II.G.5.
(16) ECLAC,Background Information - Evolution of ECLAC,http://www.eclac.cl/cgi -bin/getprod
(17) United Nations,Social Cohesion:Inclusion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Santiago,Chile ,LC/ G.2335,May 2007,p.18.
(18) 佩亚达·金柏认为,从90年代末以来,新结构主义的提法在拉美经委会的文件中不再频繁出现,但类似的改革仍在推行,说明新结构主义的许多建议仍在被继续实施。Peadar Kirby,“Resituating the Latin American State”.Working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Dublin City University,2002.http://www.dcu.ie/~cis/2002_3.pdf
(19) Osvaldo Sunkel (ed.),Development From Within :Toward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 for Latin Ameri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1993,p.7.
(20) ECLAC,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Santiago,Chile,1990,p.14.
(21)(22) Osvaldo Sunkel (ed),Development from Within:Toward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 for Latin Ameri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1993,pp.45-47,pp.8-9.
(23) Fernando Fajnzylber,“ECLAC and Neoliberalism:An Interview with Fernando Fajnzylber”,Cepal Review,No.52,April 1994,pp.205-206.
(24) ECLAC,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Santiago,Chile,1990,pp.14-15.
(25) Osvaldo Sunkel,Gustavo Zuleta,“Neo-Structura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 in the 1990s”,Cepal Review,No.42, December,1990,p.42.
(26) Eugenio Lahera,Ernesto Ottone and Osvaldo Rosales,“A Summary of the ECLAC Proposals”,Cepal Review,No.55,April 1995,pp.23-24.
(27) Osvaldo Sunkel (ed.),Development from within:Toward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 for Latin Ameri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1993,p.17.
(28) ECLAC,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UN,ECLAC,Santiago,Chile,1990,p.18,pp.58-59.
(29) Eugenio Lahera,Ernesto Ottone and Osvaldo Rosales, “A Summary of the ECLAC Proposals”,Cepal Review,No.55,April 1995,p.23.
(30) Gert Rosenthal,“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ies :the Way Ahead”,Cepal Review,Vol.60,December 1996,p.17.
(31) Fernando Fajnzylber,“ECLAC and Neoliberalism:An Interview with Fernando Fajnzylber”,Cepal Review,No.52,April 1994,pp.205-206.
(32) Berthomieu Claude and Ehrhart Christophe,“El Neostructuralismo como Renovación del Paradigma Estructuralista de la Economía del Desarollo”,Problemas del Desarrollo,Vol.36,No.143,Octubre-Diciembre 2005,pp.9-32.
(33) 这是个有争议的提法,因为威廉姆森并不承认,他说:“很多人开始用与我的初衷完全不同的释义来使用该术语,其中之一是将华盛顿共识等同于新自由主义。……但很明显的是,我的列表中并没有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建议,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的低税率、小政府的主张,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等。”(见《从改革议程到破损了的招牌——华盛顿共识简史及对未来行动的建议》,载《金融与发展》2003年9月号,第11页)但多数文章和著作将华盛顿共识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范式,如《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11月号发表的“超越华盛顿共识”的一组文章就持这种观点。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有力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华盛顿共识主张的是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政府作用的最小化。还有人认为问题不仅在于确定何种标准何种政策,更在于如何落实。
(34) Robert N.Gwynn and Cristobal Kay( ed.),Latin America Transformed:Globalication and Modern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9,p.83.
(35) Paul Drake and Lisa Hilbink,“Latin American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UCIAS Edited Volumes,Vol.3,2002,pp.18-19.
(36)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42页。
(37) “Aló Presidente 206 desde Bramón,Revolucion Venezo-
lana Impulsa Modelo de Desarrotlo Endogeno Como Estrategia de Independencia”,3 de Octubre de 2004,http://minci.gov.ve/noticias-prensa-presideneial/28/6876/revolucion_venezolana_impulsa_html
(38) Andreas Steiner,“The CEPAL - Concept for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t the End of Our Century,Neostructuralism”.http://tiss.zdv.uni-tuebingen.de/webroot/sp/barrios/themeA3a.html
(39) 当年富尔塔多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见Hector Guillenromo,“From the ECLAC Development Order to Neo- structuralism in Latin America”,in Comercio Exterior,April 2007.
标签:结构主义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