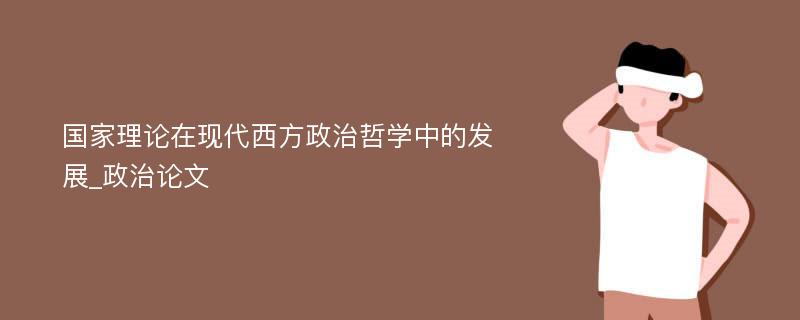
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国家学说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近代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关于国家的学说,存在着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然法理论的对立,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二者并超越二者,但他把国家视为市民社会与家庭组织的本质、目标和真理。在马克思之前,国家被看作代表伦理要求、最终目标、普遍利益的、永恒的、能动的组织机构,而马克思则视国家为工具性的、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从属性和过渡性机构。
[关键词]政治国家 前国家社会 理性 阶级
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人把苏格拉底作为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有人根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战争》一书中所包含的政治智慧而把这一创始人的殊荣归功于修昔底德。[1]不论这二种说法会引发多少争议,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哲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为西方后来的政治哲学家提供了经典话语和叙事框架。在中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笼罩在神性的光辉之下,天启宗教、圣经权威构成了关于人和政治事物(国家)的真理的最终源泉。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摆脱了神学的卵翼,开始自身独立的发展。近代政治哲学家们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的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2]
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纷繁复杂,形态各异。但从霍布斯到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近代政治哲学家在研究人类社会和国家时,往往预设一种与社会状态、国家状态相对立的自然状态,或前国家状态。他们把自然状态中的人看作自然人,自然人是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自然人是由本能和生理冲动支配的愚昧、有局限性的动物,而在社会状态下,人变成有智慧的生物、政治的人和理性的主体,“成为依赖于分母的分数”。与此对应,他们把国家或政治社会看成是人类的共同的集体生活的最高阶段、最后阶段,看成是对本能、激情、利益加以理性化的最完美或近乎完美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国家或政治社会的确立,已往那种不能协调、相互冲突、矛盾四起、依恃强力的统治转变成协调的自由的统治,国家被视为理性的产物、理性的社会。这样,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国家中,人类才能过上一种符合理性的生活,而符合理性的生活也就意味着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
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中,若就思想家对政治和国家进行研究的方式而论,我们大致可区分两类思潮,一种是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另一种是自然法理论。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其基本倾向是从经验出发,按照国家的实际情况来描绘国家,构造其国家学说。这一思潮以马基雅弗利为始作俑者。马基雅弗利作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他的《君王论》同古典传统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政治学》不同,它不是对理想政体形式的构想,不是根据德行、正义来构想国家生活,而是根据国家生活的现实来描述国家及其统治。他认为“对国家的研究应着眼于人们实际行事而不是人类之应然行动。”马基雅弗利以此而开创了近代政治思潮的现实主义传统。马基雅弗利之后的培根以及主张“国家理性”,认为国家自身有其理性,无需从世俗生活之外注入一种自然的或道德的基础作为国家的合理性依据的理论家,都可纳入现实主义传统。西方近代政治思潮中的自然法理论产生要稍晚。严格说来,自然法的概念并非近代才进入政治哲学视野。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西塞罗、奥古斯丁、阿奎那、迈蒙尼德、阿尔博在其政治哲学著作中都谈到自然法,但是他们要么把自然法(即按其自然本性或出于自我保存而需遵从的规则)视为低于成文法和神圣法(西塞罗);要么把自然法纳入神圣法中,从神圣法(上帝律法)中寻找自然法的依据(奥古斯丁、阿奎那);要么视为理性法的次要构成要素(阿尔博),认为自然法的唯一目标只是肉体的完善,而只有理性法才能促成政治社会和城邦生活中人类的道德与精神的完善。只有霍布斯才真正提出近代意义上的自然法理论。霍布斯通过自然状态理论的建立而确立了自然法对理性法(成文法)的优先地位,认为自然法及所有政治社会的责任、义务来源于个人自我保护的自然权利,而基本自然法即确保自我保护、寻求永久和平的规则。它体现为社会契约的制订及契约的忠诚。霍布斯认为自然法实质上是理性的命令,但它仅在道德心上对人有约束力,必须要通过政治国家的建立,使自然法上升为理性法,成为法律意志。霍布斯从自然状态、自然法推演出国家的建立,由此开创近代自然法理论传统。卢梭、康德皆步霍布斯后尘。总体而言,自然法理论建构的是理想的国家模式,确立国家应如何才能实现其真正目的。
不难看出,现实主义理论同自然法理论二者研究基点不同,一个是从现实出发,主张国家有其内在理性。一个是从理性出发,认为理想的国家应建立在合乎自然法,即合乎人类理性的基础上。尽管如此,二种思潮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因为二者基本上都是把同自然状态相对立的国家看作是人类集体生活的最高、最完善阶段。按照自然法理论,作为理性社会的国家,其关键是国家合理化过程,即对国家进行理性重构。而根据现实主义理论,亦即根据主张“国家理性”的学说,关键是理性的国家化,即国家自身内在的理性的自我实现。我们说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黑格尔也是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将现实主义传统与自然法传统综合起来,在国家问题上,他把国家的合理化过程与理性的国家化过程综合起来,从而在国家理论上对传统有所超越。黑格尔一方面认为国家是永恒理性的产物,是“伦理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3]这样,他继承了自然法哲学传统,把国家看作是一项理性的设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历史运动的结果,理性的展开与世界历史的进程是相对应的,历史进程在根本上是合乎理性的。他说他并不想构造理想的国家,而是想以证明现实的国家的合理性来恢复国家的应有地位。这样,他又延续了马基雅弗利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们从《法哲学原理》中可以看出,国家的理性化得到最终表现,它不仅代表着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而且也是理解真实历史运动的钥匙,国家的合理性不再只是必需,而且也是现实,不再只是理想,而且也是历史事件。正是循着这一思路,黑格尔在法哲学中不仅描述了绝对精神的概念进展,而且也描述了其现实发展及其表现,特别是论述了家庭、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特点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上述特征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之受到责难并不是因为他按照近代国家的本来面目描绘了国家的本质,而是因为他把国家的那些实在内容如家庭、市民社会说成是不同于实在本身的主观的理念的产物。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这种现实性也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它之所以合乎理性,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理性,而是由于经验的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中附加一种超出其本身范围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当做事实本身来看待,而是被当做神秘主义的结果。”[4]
按照西方近代政治思潮,国家的理性化往往以二分对立的模式出现,国家被看作积极的要素或阶段,而前国家的或反国家的社会则是一种消极的要素或阶段。大致说来,西方近代政治思潮中,霍布斯和卢梭是把政治国家看作彻底的否定阶段,它消灭和废除自然状态,同国家之前的人类发展阶段相比,政治国家是新生事物。洛克、康德则把国家看成是对自然社会的保护与管制,这样,国家不是被看作前国家阶段的替代物,而是被看作使之现实化、使之完善的阶段。而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既被看作是对前国家社会的保护,又被视为对它的超越。就国家是一个新阶段而言,它并非只是使先前阶段更完善,这样,其国家模式不同于洛克、康德模式。但国家并未构成绝对的否定,因而它又不能说是先前阶段的替代物。这样,其国家模式又不同于霍布斯、卢梭模式。在霍布斯、卢梭那里,国家最终把自然状态排除在外,而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包含着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不过是自然状态的历史化生成,或者说是自然法哲学家(如洛克)所讲的自然社会。黑格尔所理解的国家包括市民社会,又超越于市民社会,它把一种纯粹形式的普遍性转变成一种有机的现实性。黑格尔的这一国家模式同洛克的国家模式不同。洛克所讲的国家,虽然包含着市民社会(洛克把它认作为自然社会),但在洛克那里,国家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超越自然社会,而只是为了使其存在及其目标得到合法保障。
正是由于黑格尔的影响,西方近代政治思潮对国家的合理化过程加以空前强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同一时期,出现了对国家问题展开思考的新思路。圣西门基于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观察,提出社会的深层转变并不导源于政治变革,而是导源于工业革命。他预言一种新秩序即将来临,同那种由哲学家和军人把持的传统秩序相反,新秩序将由科学家和实业家控制。他在1818年撰写的《加强实业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国的财富的制宪措施》中提出用实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响亮地提出“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的口号。[5]从此,关于国家的不可避免的消亡的学说和信念开始被人们系统地提出来。事实证明,这一信念成了盛行于19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就吸收了圣西门的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国家不再是黑格尔所谓的“伦理理念的现实”、“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6]相反,国家是“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的社会暴力”,“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就叫国家。”[7]马克思所提出的国家学说同黑格尔作为集大成者所代表的自然法哲学传统形成鲜明对立。同霍布斯、卢梭的国家模式相反,国家不再被设想成自然状态的消除,而是被看作对自然状态的保存、延续,在国家中,强力的统治并未得到克服,而是被永久地保存下来(就阶级社会而言)。唯一的区别在于原先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现在被一方反对另一方的阶级斗争所取代,国家是这一斗争的表现和工具。同洛克和康德模式相反,国家是社会的最高管理者、统治者,社会并不是同人类永恒本性相一致的社会,而是受历史决定的社会,它受特定生产方式和特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因而,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制度,并不是什么普遍的、理性的需要的表现,而是特殊利益的重复与巩固。此外,同黑格尔的国家模式不同,在马克思那里,国家不再表现为对市民社会的超越,而只是对市民社会的反映。市民社会是怎样,国家就会怎样。“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8]这样,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合,不是为了把市民社会转变成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按其本来面目保持它。受历史所决定的市民社会,也并非消失在国家中,而是在国家中,市民社会的所有具体表现都得到再现。
总体来看,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在多个层面上同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传统形成鲜明对照。
首先,马克思在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政治国家时,其研究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和人类历史,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特别是一定经济关系中的人。正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的现实的历史活动构成了马克思对国家进行研究的前提。马克思曾经高度赞扬了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国家观,他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说:“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和其后的霍布斯、斯宾诺莎、胡果、克劳修斯,以及卢梭、费希特、黑格尔等人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9]但是他批判自然法思想家从自然人、自然状态、自然法来构造其国家学说的思维方式,认为自然人、纯粹的自然状态不过是纯粹的臆想,是空想家头脑中的产物。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沿续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中由马基雅弗利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一个强制性的机构,是“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这样的国家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工具性的国家概念。它不同于自然法理论家所持的伦理性和目的性的国家概念,国家不再被视为终极价值。
第三,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0]这样,马克思对国家的概念作了特殊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的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就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立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11]国家“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12]在他看来,“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都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13]也正是在现代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道:“工人没有祖国。”[14]马克思的这一具有阶级属性的国家概念同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所有自然法理论家所持的普遍化国家概念形成对立。可以说,对国家作普遍化理解,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制度,这是所有自然法政治理论的一个根本特征。
第四,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是第二位的、从属的现象。他们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着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着国家。”“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15]市民社会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成一定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的物质交往,它包括整个经济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国家概念是一个积极性的国家概念,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能动的因素,是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结构构成社会的基础结构。马克思的这一国家概念同近代政治思潮中所见到的消极的国家概念形成强烈对照。
第五,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强制的、代表特定阶级的从属性的机构,国家并非历史发展过程的最高阶段,相反,国家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它注定要被超越。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16]马克思根据19世纪西欧社会化大生产的加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断言未来的发展必将是一个无阶级、无政治国家的社会,“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里,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而是自行消亡的。”[17由于马克思把政治社会即国家奠定在市民社会之上,而不是象黑格尔那样,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是国家“理念的有限性领域”,看作“主观理念活动的结果”,[18]这样,马克思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也就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自然法政治思想家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完全不同。在自然法政治思想家那里,社会进步表现为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从市民社会到政治社会的过程;而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社会进步将是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19]这样,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自然法国家理论本来是以国家是对自然状态的废除这一观念为其开端,最后却是以认为国家本身也终将废除这一观念的提出和逐步完善而告终的。
总之,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家的学说,最初出现现实主义国家理论,尔后是自然法国家学说的系统提出,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将二种学说加以综合。但即便是黑格尔,也仍然站在抽象的人、抽象的理性立场研究国家,把国家看成是理性设计、伦理要求,看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组织,并且把国家看成是独立的、决定性的因素。只有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人、现实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研究,才真正认清了国家的阶级本质,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从属性、过渡性与历史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国家学说。
收稿日期:1997-02-05
注释:
[1]列奥·斯特劳斯著,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绪言及第一章。
[2][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252-253、128页。
[3][6][18]黑格尔著,范扬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2、253、263页。
[5]参见《圣西门选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丁冰著:《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81页。
[8][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439页。
[10][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70页。
[1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1页。
[15][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54、41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页。
标签:政治论文; 自然法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自然状态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家生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哲学家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