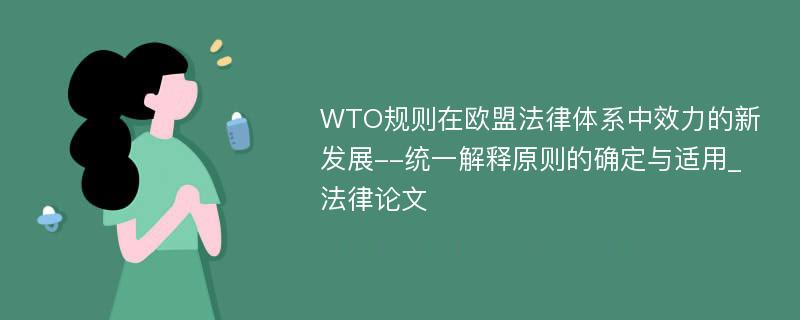
WTO规则在欧盟法律体系中效力的新发展——统一解释原则的确定与适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效力论文,新发展论文,法律体系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文献标识码:A
本文分四部分。在问题提出之后,文章简要介绍统一解释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国家实践及其理论背景。接下来的部分将集中于欧盟的具体实践,重点分析欧盟法院在WTO规则国内效力问题上引入统一解释原则的做法。文章最后将对欧盟实践进行分析评价,探寻该实践对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多边贸易体制长期发展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1994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无疑可以作为各国政府协调国际贸易活动管理行为的一个重要成就。目前为止,WTO成员已经扩展至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成员驱动”型(member-driven)国际组织,WTO对其成员设定了国际经济管理活动上的诸多义务,而这些义务对于WTO成员内部私主体利益的影响问题也一直没有离开学者和公众所关注的视野,包括WTO规则在成员方国内能够以何种方式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发挥其国内法上的效力问题。
在国内法效力问题上,WTO诸协议存在不同于一般性国际条约的特点。WTO诸协议规则主要涉及WTO成员对国际贸易的政府管理行为,而WTO规则对成员政府管理行为的义务规定间接决定了成员境内私人(包括个人和企业)的行为模式和经营方式①。WTO成员不履行其所承诺的义务或者怠于履行都会破坏私人在国际贸易活动的各种既定安排,从而损害多边贸易体制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
对于私人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所获得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保护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在国际层面上,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明确表示,“WTO争端解决体制在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②WTO成员可以启动争端解决机制来纠正其他成员违反WTO规则的行为,私人利益可以通过其政府启动争端解决机制得以保证。当然,如果WTO成员政府决定不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私人利益在国际层面上也就无法得到保证。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保护私人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所获得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局限,引发人们对于WTO规则国内法效力的期待,即在国内层面上,WTO规则可否拥有与国内法相类似的效力,从而在国内司法系统中为私人利益提供保护。
在WTO义务的履行问题上,WTO成员们大多通过国内立法将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纳入本国法律体系当中③。但对于WTO规则的国内法效力问题,大多数WTO成员却采取消极的态度,反对国内法院在审理贸易案件时直接适用WTO规则解决争议,以此对WTO规则的国内法效力加以控制④。以美国为例,作为WTO主要成员的美国,在WTO成立以前从未对GATT的直接适用问题做出明确界定。直到国会通过《乌拉圭回合协定法》指出,WTO诸协议在美国法律体系中不属于“自动执行”(self-execute)条约,法院无法就美国法律与WTO规则的冲突直接适用WTO规则⑤。从国内政策性因素来看,美国国内立法者担心在国内法院直接适用WTO规则会损害国家在多边贸易协定中主权的行使[1]。
如果把WTO规则的直接适用问题放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视角中考察,结论亦不乐观。知名学者Jackson教授从多边贸易体制与国家宪政互动的角度指出,允许国内法院直接适用WTO规则会阻碍WTO成员参与更进一步贸易自由化谈判的积极性,因而影响多边贸易体制的长远发展[2]。
美国在WTO规则直接适用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WTO其他成员的决定。欧盟法院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件”中否定了WTO协议在欧盟范围内的直接适用。欧盟法院在该案中指出,由于美国否认国内法院在审理贸易案件时直接适用WTO规则,如果欧盟单方面认可WTO协议的直接适用,就会使得欧盟在解决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时陷于被动,失去必要的自由裁量权⑥。
尽管如此,私人利益寻求WTO规则保护的努力在欧盟内部一直都没有停止,欧盟法院近十年的案件裁决也似乎为私人利益的保护透露了一线曙光。1996年“欧盟法院在欧盟委员会诉德国”一案中裁决:不管是否具有直接效力,“欧共体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相对于欧共体二级法律的优先性意味着对于欧共体二级法律条款的解释必须尽可能地符合国际条约的规定。”⑦1998年欧盟法院在爱马仕案中裁决,国内法院应该参照TRIPS条款的措辞和目的对荷兰程序法进行解释。⑧
在直接适用被WTO主要成员(包括欧盟)所反对的情况下,欧盟根据统一解释原则运用WTO规则解释欧盟法律及其成员国国内法的这一实践,使得学者们再次对WTO规则国内法效力问题予以关注,有学者甚至认为,WTO协议通过统一解释原则产生的对国内法的间接效力,在效果上有可能与直接适用相媲美[3]。笔者无意对上述观点进行评价,但统一解释原则对于WTO协定国内效力问题的影响以及可能具有的局限,正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如同直接适用问题一样,统一解释原则也属国内法问题,对其研究不能离开一个国家的宪政背景和司法实践,欧盟的实践为统一解释原则的研究提供了及时而且恰当的语境。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国际法场合涉及条约的国内法效力问题时,通常采取“直接适用原则”(direct application)和“统一解释原则”(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两个术语来概括。但有些学者分别用“直接效力”(direct effect)和“间接效力”(indirect effect)对应上述两个术语的使用,因为欧盟法院最早在其案例中使用直接效力和间接效力区分欧盟层面的法律、法规及其指令在欧盟成员国内法律体系中的不同效力。笔者认为这两套术语所表达的意思是相近的。间接效力原则通过效果来定义,因为与直接效力相比,通过解释国内法而使指令产生的效力是间接的。统一解释原则通过方式来定义,即利用条约规则来解释国内法以保证国内法与条约的统一性。间接效力原则和统一解释原则这两种表述在欧盟法和WTO协定两种语境下经常不加区别地加以使用,本文出于在WTO范围内研究问题的方便,对于国际法一般层面的分析使用“统一解释原则”,但涉及欧盟实践时笔者更多选择“间接效力”来概括。
二、对国际法背景下统一解释原则的一般性考察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曾在其一般性意见第9号中总结到,对国内法的解释应尽可能地符合一国的国际法义务这一原则已被普遍接受。⑨经社理事会的这一总结是基于国家实践基础之上的,很多国家的国内司法实践对统一解释原则的适用给予了肯定。以美国为例,美国最高法院在“Charming Betsy 案”中曾确定,“在其他可能的法律解释存在的情况下,对国会通过法律的解释不应该违反国际法。”⑩因此,该原则在美国又被称为“Charming Betsy Doctrine”。美国《对外关系法第三次重述》中第114节也对这一司法实践进行了总结,即“如果可能,美国法律的解释不应违反国际法或美国签署的国际条约。”(11)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统一解释原则也并不陌生。Brownlie教授在《国际法原则》一书中曾提及早期英国法院的一个案子。该案亦确认:相关公约的条文可以用来辅助对法律进行的解释(an aid to interpretation),尽管该公约条文并未被纳入该法之中,甚至亦未被提及[4]。英国现在的人权法案相关条文也规定,对国内法律的解释符合国际法是英国法院的义务[5]。荷兰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荷兰法律条文的解释不应违反国际法[6]。
该原则在中国也有相应的表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加入WTO后所发布的司法解释中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相一致的,应当选择与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相一致的解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12)
对于国内法院适用统一解释原则的合理性,国际法学者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国际责任论;一种是传统的一元论观点——国内法秩序论。持国际责任论的学者认为,统一解释原则作为国内法的补充,可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精神相符合。根据这一观点,即便一国所承诺的国际法义务并未在国内法体系内生效,但是根据统一解释原则,使国内法的解释符合国际法规则仍然是可能的,避免产生违反国际法责任是统一解释原则存在的可能动机[7],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法院被认为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代理机关”[8]。
与国际责任论不同的是传统的一元论,持该观点的学者主张国际法是国内法秩序中的组成部分。Snyder教授以WTO规则在欧盟法中的位置为例,认为运用WTO规则解释欧盟法并非源于WTO协议这一国际性规则本身,而是因为WTO规则已被纳入欧盟法律秩序当中[9]。根据一元论所给出的统一解释原则的合理性,尽管不同国家对国际法规则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直接效力或是优先级(Supremacy)问题有着不同回答,但是国际法规则却可以因为国家的“核准”(Approval)与“批准”(Ratification)行为获得其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内部效力”(Internal Effect),从而为国内法的解释提供积极的帮助。
两种观点相比较,国际主义观点根源于国际法责任的神圣性,一元论观点则基于国际法进入国内法律秩序的方式认为用国际法解释国内法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这两种观点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模式分析统一解释原则的理论合理性,当然作为一个国内法问题,对于统一解释原则的分析必须同时结合国家具体的宪政结构及其司法实践。
三、统一解释原则在欧盟的具体实践
统一解释原则在欧盟的适用体现了三种法律体系之问的三角关系。首先,统一解释原则可以作用于欧盟法与成员国法之间,欧盟法院为此建立了直接效力原则和间接效力原则。前者规定了《欧共体条约》以及“法规”(regulations)在成员国法律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后者则要求国内法院对国内法的解释“应尽可能地参照‘指令’(directions)的措辞和目的来进行”。(13)其次,统一解释原则还作用于欧盟法和国际法之间,欧盟法院确定欧洲共同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尊重国际法,在相关案例中要求对欧盟法规的解释要符合欧盟的国际法义务。(14)最后,统一解释原则还涉及欧盟成员国法与国际法的关系。统一解释原则在这一层面上的作用最近几年在WTO规则背景下有集中的体现,经典案例是1998年的“Hermes案”。(15)统一解释原则在第一种关系下的确定和适用为其在后两种关系下的适用提供了必需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基础。
(一)欧盟法律秩序中的间接效力原则
欧盟法律秩序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欧盟立法在成员国法律体系中的效力,间接效力原则所涉及的是欧盟指令(directives)在成员国国内的效力问题。根据《欧共体条约》第249条(原第289条)的规定,欧共体指令对其指向的每个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但是国内机关有权选择执行指令的方式与方法。而对于个人可否依赖于欧共体指令的直接效力,欧共体条约并没有规定,欧盟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区分两种诉讼:一种是私人针对成员国怠于履行欧盟指令义务所提起的国内行政诉讼,另一种是私人之间援引欧盟指令的国内民事诉讼。
对于第一种诉讼,欧盟法院曾在1982年的“Becker案”中指出,如果指令条文是无条件的而且充分明确,个人就可以因为成员国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将指令转化为国内法而针对该成员国提起诉讼(16)。在四年后的“Marshall案”中,欧盟法院进一步明确援引指令的诉讼只能针对成员国及其国家机关进行(17),“指令本身并不设定对个人的义务,因此指令条文不能被用来作为起诉个人的依据。”(18)因此,对于私人针对成员国怠于履行欧盟指令义务所提起的国内行政诉讼,欧盟指令具有“垂直的直接效力”(vertical direct effect),但是对于私人之间援引欧盟指令的国内民事诉讼,欧盟指令不具有“水平的直接效力”(horizontal direct effect)。虽然原告和“总检察长”(Advocate General)曾多次要求取消垂直直接效力与水平直接效力的区别,但欧盟法院对此一直没有让步[10]。因此,欧盟指令在私人之间的民事诉讼中不具有直接效力。
尽管如此,欧盟指令仍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发挥其在私人之间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欧盟法院在“Colson案”中首次要求国内法院对旨在执行指令而制定的国内法进行解释的时候要对该指令加以参照。(19)在其后的“Marleasing案”中,欧盟法院对Colson裁决进行了修正并确立了“间接效力”原则,即要求国内法院对国内法的解释要参照指令的语句和目的来进行,而不管所需解释的国内法条文是制定于指令之前还是指令之后。(20)因此,即便是在私人间的民事诉讼中,一方仍然可以根据间接效力原则要求法院利用欧盟指令的规定对涉案的国内法律规则加以解释。下文将对欧盟法律体系中的这一间接效力原则进行详细介绍。
1.欧盟间接效力原则的起源:“Colson案”和“Marleasing案”
“Colson案”
“Colson案”源于两个德国妇女关于在德国监狱担任社工的申请。监狱认为,由于服刑的全部是男性,所以只有男性社工能够胜任对服刑人的辅导工作,申请因此被拒绝(21)。这两位妇女认为监狱的作法违反了《德国民法》第611a条禁止在雇佣上设置性别歧视的规定,将监狱诉至地方劳动法院,请求法院判定监狱雇佣原告,并赔偿其基于工作申请所发生的所有费用以及申请至起诉之际的6个月工资。
地方劳动法院认为原告的确受到了性别歧视,但合理的赔偿范围只能包括因信赖利益而导致的损失,即原告只能就与工作申请相关的费用得到赔偿,6个月的工资不在赔偿范围之中。至于应否判定监狱雇用原告这一问题,由于《德国民法》第611条是德国将欧盟委员会指令76/207《男女平等权利指令》(以下简称“《指令76/207》”)纳入国内法体系所进行立法的一部分(22),地方劳动法院因此暂时中止了诉讼程序,将该问题转至欧盟法院请求欧盟法院就下列问题给出先前裁决:如果一个人在雇佣过程中遭受性别歧视,《指令76/207》是否要求歧视方为被歧视方提供该职位?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在歧视明显发生的情况下,《指令76/207》规定了何种替代性救济措施?如果欧盟法院对上述问题给了回答,可否据此肯定《指令76/207》在联邦德国具有直接效力,从而对本案中违法的雇佣者具有执行力?
欧盟法院在审查上述问题时指出,《指令76/207》并没有就救济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由于指令没有给出具体救济方式,即便欧盟法院判定该指令具有直接效力,对于如何救济原告也是无能为力的。欧盟法院由此认为第三个问题没有意义。于是,第二个问题—违反《指令76/207》时存在什么样措施进行救济—成为本案的关键。
欧盟法院指出,“提供成员国内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平等待遇,尤其是给予男性与女性在就业上的平等机会”是《指令76/207》的立法目标(23),该指令同时要求成员国进行必要的国内立法以保证受到歧视待遇的个人能够在法院实现其权利。因此,尽管该指令没有规定特别的救济措施而允许成员国自行选择,成员国的决定也必须能够保证实际和有效的司法保护,并对违法的雇佣者产生实际的警惩效果。如果一成员国决定采用损害赔偿的方式来惩罚违法行为的话,其数额必须是充分的,而不能象本案德国地方劳动法院所认定的赔偿范围那样仅仅具有象征意义。(24)
欧盟法院同时指出,《欧共体条约》第5条要求成员国应采取所有适当措施以保证指令所期待目标的实现,这一义务对成员国的所有机关都有约束力,也包括在相关事项上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欧盟最后得出结论,“在适用国内法,特别是适用为实施指令而制定的国内法条款时,国内法院必须参照指令的措辞和目的解释其国内法以实现《欧共体条约》第189条所指的结果。”(25)
欧盟法院在“Colson案”中第一次提出了根据指令来解释国内法的问题,这一裁决成为欧盟法律体系中间接效力原则的重要来源。需要注意的是,“Colson案”所确定间接效力原则的适用存在一个重要条件,即只有国内法规则是为了实施相关欧盟指令而制定的,对于该国内法的解释才可以参照指令。而迟于国内法制定的欧盟指令可否用来解释国内法的问题,“Colson案”并没有给出答案,该问题因此引发了后续的诸多争论。最后,“Marleasing 案”就此给出了“宽松”的裁决,使得间接效力原则在欧盟法律体系中得以最终确立。
“Marleasing案”
“Marleasing案”涉及西班牙对《指令68/151》的实施。《指令68/15》第11条给出了“公共招股有限公司”(public limited company)“无效的列示清单”(an exhaustive list of possible grounds of nullity of public limited companies),而西班牙需要在1986年1月1日之前实施该指令68/151,但西班牙直到1989年底才通过国内立法完成实施行为。就在1986年1月1日到1989年底之间西班牙怠于实施指令的这段时间里,Marleasing先生请求国内法院判定一家公共招股有限公司的成立合同无效,其依据是《西班牙民法》第1261条和第1275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事由之一——“缺乏原因”(lack of cause)(26)。《西班牙民法》规定缺乏原因或原因违法可使合同无效,但这一事由并不在《指令68/151》可使公共招股有限公司无效的列示清单之中。被告公司因此在抗辩中指出,缺乏原因并不是欧盟法下可使合同无效的合法事项。该抗辩也因此给国内法院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尚未被成员国实施的指令是否在本案中存在某种效力?西班牙法院将该问题提交至欧盟法院请求先前裁决。(27)
欧盟法院首先援引指令不具有水平直接效力的先例,确定本案被告不能直接适用指令条款针对原告主张进行抗辩。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内法院是否应该参照相关指令的措辞和目的解释国内法,从而把一个使公开招股有限公司无效的事由排除在《指令68/15》第11条的列示清单之外?(28)
欧盟法院在援引“Colson案”裁决时注意到,该案中采用指令解释国内法必须以国内法的制定是为实施相应指令为前提。欧盟法院在“Marleasing案”中对其先前确定的原则进行了发展,最终确定不管国内法条款制定是在指令生效前或生效后,国内法院都应该参照指令的措辞和目的解释国内法。(29)较之欧盟法院的上述分析,总检察长AG van Gerven在欧盟法院裁决前所给出的意见在法理的分析上更为清晰。van Gerven先生指出,西班牙1951年的《公开招股公司法》中并没有对这些公司的无效问题做出特别的规定。由此,van Gerven先生认为,西班牙法院所面临的是一个公司法解释的问题。根据法律界的通说,与合同无效相关的条款可以类推适用,本案原告也如此主张。但van Gerven先生认为,类推适用合同法中的一般概念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存在需要解释的概念;二是类推解释是唯一可能的解释方法。(30)但是,本案对于待解释的概念有多种解释方法:合同法一般概念的类推适用和指令的适用。van Gerven先生认为,在存在多种解释的情况下,国内法院有义务按照指令对国内的立法进行解释。
2.间接效力原则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性
需要明确的是,欧盟法院作为一个超国家司法机关(supranational judiciary),其确定指令在欧盟内部具有间接效力原则的这一实践根本源于欧盟法院的职责,即在解释和适用欧盟条约的过程中保证法律得到实施。(31)在这一职责的驱动下,欧盟法院适时引入间接效力原则可以推动成员国实施欧盟指令,从而促进欧盟法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成员国法院经常使用指令解释国内法,是否会有成员国政府怠于实施指令,而依赖法院的解释来实现在国内实施指令的功能呢?这个发问本身揭示了司法解释的功能远不及指令在国内的完全实施来得彻底:其一,国内法更容易被一国国民所了解;其二,司法解释的不确定性也会造成权利保护的不完整。
基于欧盟法院在指令间接效力上的裁决,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既然对成员国国内法进行解释可以参照欧盟指令,那么可否将间接效力原则的适用加以扩展,将一个国际条约作为对欧盟立法以及成员国国内法进行解释的参照。
欧盟国家长期以来尊重国际法的传统可以为上述问题的回答提供积极的线索[11]。欧盟国家尊重国际法的传统还反映在《欧盟宪法条约》第I-3条第4段,该段要求欧盟在处理和世界的关系上应该对严格遵守和发展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原则)做出贡献。与此同时,在处理国际条约在欧盟内部的效力问题时欧盟法院角色的变化也不应忽视。与其他国内法院一样,欧盟法院面临着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间的利益冲突,赋予国际条约在欧盟内部间接效力对于欧盟法院而言并非简单的决定。
(二)涉及WTO规则的统一解释原则在欧盟的适用:一个令人欣喜的进步
WTO规则在欧盟法律秩序中的解释作用体现在第二和第三层面,即适用WTO规则对欧盟法规加以解释和适用WTO规则对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法进行解释。
1.适用WTO规则对欧盟法规加以解释
欧盟法院曾在1992年“Poulsen案”中强调欧共体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尊重国际法,并由此裁定对于某欧盟法规的解释应参照相关的国际海洋法规则(32)。欧盟法院在随后1996年的“委员会诉德国案”中做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裁决,即不管是否具有直接效力,“欧共体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相对于欧共体二级法律的优先性意味着对于欧共体二级法律条款的解释必须尽可能地符合国际条约的规定。”(32)
“委员会诉德国案”中的原告欧盟委员会认为,被告德国涉及奶制品进口的某一海关行为违反了GATT东京会合《国际奶制品协定》的相关规定。德国认为其行为是符合欧共体立法的,而欧共体立法的存在就排除了《国际奶制品协定》的适用。针对德国的抗辩,欧盟法院强调欧盟所缔结国际条约相对于欧盟二级法律的优先性,这一优先性要求对于欧盟二级法律的解释应尽可能地符合这些条约,当然包括欧共体所缔结的《国际奶制品协定》。(34)
欧共体第一审法院(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在诸多反倾销案件中也多次将《WTO反倾销协定》作为解释欧盟反倾销立法的辅助规则(35)。Snyder教授指出了这一司法实践的必然性:欧盟反倾销立法一直紧密遵循GATT/WTO规则,因此欧盟一审法院多次适用《WTO反倾销协定》解释欧盟反倾销立法也属自然[12]。
2.适用《TRIPS协定》规则解释成员国国内法
欧盟法院在WTO成立之前并没有处理过根据国际法规定解释成员国国内法的问题,直到1998年,荷兰法院在“Herms案”中要求欧盟法院对可否利用《TRIPS协定》规则解释国内法这一问题给出先前裁决。欧盟法院对于该案作出肯定性裁决,并在其后的多个案件中反复要求国内法院要按照《TRIPS协定》规则解释国内法(36)。
欧盟法院曾在“葡萄牙诉委员会案”中彻底否定WTO协定在欧盟范围的直接效力(37)。在这一背景下,按照《TRIPS协定》规则对国内法加以解释从而使《TRIPS协定》甚至其他WTO协定在欧盟范围内拥有不同于直接效力的统一解释作用,欧盟法院的这一动向另辟蹊径,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Herms案”
“Herms案”中的原告Herms公司认为另一家FHT公司经销的领带是冒牌货,因此向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申请采取“临时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请求没收FHT公司正在销售的463条领带。同时,Herms公司请求法院根据《TRIPS协定》的相关规定,设定临时措施的实施期间。(38)
根据《TRIPS协议》第50条的规定,WTO成员的司法机关有权责令采取迅速有效的临时措施以防止侵权货物进入相关商业渠道并保存有关证据。该条第6款同时要求请求采取临时措施一方必须在措施实施之后的一段合理期间内启动案件实体程序,否则,被告可以请求撤销临时措施或终止该措施的效力。《TRIPS协议》将合理期间的设定交由WTO成员自行确定,如果国内法没有相关规定,则该款规定不应超过20个工作日或31天(以时间长者为准)。(39)而在《荷兰民事程序法》涉及临时程序规定的第289条中恰恰没有关于合理期间的规定。(40)
阿姆斯特丹法院请求欧盟法院就本案所涉及的措施是否属于《TRIPS协定》第50条所指的“临时措施”作出初步裁决。欧盟法院首先确定自己对于该案的管辖权,接着将该问题归为统一解释问题,并作出肯定性裁决:阿姆斯特丹法院应该参照《TRIPS协定》第50条的措辞和目的对荷兰程序法进行解释。(41)
欧盟法院在裁决正文中并未对采取统一解释原则的依据给出具体分析,只是引述了其在以“Poulsen案”和“委员会诉德国案”中的裁决。(42)如前文所述,欧盟法院在这两个案件中都确定了参照国际法解释欧盟二级立法的原则。欧盟法院也许在暗示其在以往案例中参照国际条约解释欧盟二级立法的裁决可以类推适用于“Herms案”,从而确认可以参照《TRIPS协定》解释成员国国内法。
“Dior/Assco案”
“Dior/Assco案”涉及的是一个合并的先前裁决。“Dior案中”的原告Dior香水公司发现另一家Tuk公司在荷兰销售的香水侵犯了其商标权,于是请求法院采取临时措施。荷兰法院认为该请求与《TRIPS协定》第50条第6款的直接效力问题相关,就将问题转给欧盟法院,请求欧盟法院就《TRIPS协定》第50条第6款在没有相关国内法规定的情况下是否具有直接效力给出先前裁决。(43)“Assco案”中的被告埃斯科公司的产品因为专利侵权事宜被执行临时措施,埃斯科公司就此上诉(44),该案中荷兰法院请求欧盟法院就《TRIPS协定》第50条是否具有直接效力问题做出初步裁决。
由于两案都涉及《TRIPS协定》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效力问题,欧盟法院进行了合并裁决。只是两案所涉及的领域有所不同,“Dior案”涉及商标权,“Assco案”涉及专利这类工业产权。欧盟在案件发生之时还没有工业产权保护方面的欧盟统一立法,因此欧盟法院在专利侵权领域事项上没有管辖权,国内法院在这一事项上具有排他管辖权。(45)两案的共性在于仅和临时措施的实施程序相关,都不涉及商标侵权和专利侵权的实体问题。欧盟法院从这一事实出发,指出分属国内法和欧盟法管辖的不同领域同时适用《TRIPS协定》第50条所规定的程序性规定。考虑到“一致性解释”(a uniform interpretation)对于欧盟在法律和实践上的意义,欧盟法院认为,《欧共体条约》第177条要求欧盟法院有义务与成员国法院进行合作,这一义务足以使自己承担保证成员国法院在法律解释上一致性的责任。欧盟法院据此认为其对于工业产权侵权的程序性问题也具有管辖权。
在解决了自身的管辖权问题之后,欧盟法院集中解决荷兰法院所提交的问题,即《TRIPS协定》在成员国国内是否具有直接效力?在这个问题上,欧盟法院援引其在葡萄牙诉委员会案中的裁决(46),认定《TRIPS协定》并没有为个人在成员国法院面前创设权利,个人不能在国内诉讼中直接援引《TRIPS协定》。
尽管已经回答了“Dior案”和“Assco案”中荷兰法院所提交的问题,但欧盟法院认为上述结论并不能解决荷兰法院在两案中所面临的问题。欧盟法院接下来沿用其在“Herms案”中的裁决认定,对于处在欧盟法适用范围中的“Dior案”,荷兰法院应该按照《TRIPS协定》第50条的措辞和目的解释适用国内法,而对于处在国内法适用范围中的“Assco案”,荷兰法院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解释适用国内法。
至此,欧盟法院通过“Herms案”和“Dior/Assco案”确定了《TRIPS协定》对于国内法的统一解释作用。在随后的“Schieving-Nijstad案”中(47),欧盟法院重申统一解释原则,并特别指出在适用统一解释原则时,需要分析案件中所有因素以确保权利所有者和被告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48)
“Herms案”与“Dior/Assco案”的比较
“Herms案”和“Dior/Assco案”都是由荷兰法院向欧盟法院提出的先前裁决申请,为什么其他成员国法院没有提出相关申请?其他成员国法院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也许这并非本文分析的重点,但如果关注荷兰尊重国际法的传统,就可以发现荷兰是承认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律系统中具有直接效力的为数寥寥国家中的一个[13]。这一事实也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只有荷兰的法院频频就WTO协议的国内效力问题请求欧盟法院做出先前裁决。
尽管欧盟法院在“Herms案”和“Dior/Assco案”中确定了《TRIPS协定》可以通过统一解释原则发挥其在欧盟成员国国内的效力,但是欧盟法院对于《TRIPS协定》直接效力问题上态度的差异耐人寻味。
“Herms案”中的荷兰法院请求欧盟法院进行初步裁决的问题是《荷兰民事程序法》中的临时程序是否属于TRIPS第50条第6款所指的“临时措施”。总检察长在分析该案时认为《TRIPS协定》第50条第6款可以直接适用于该案而具有直接效力。欧盟法院在随后的裁决中却避而不谈直接效力是否可行,转而认定在对国内法进行解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参照TRIPS协定的措辞和目的。而欧盟法院在“Diro/Assco案”中没有回避荷兰法院在先前裁决请求中提出的《TRIPS协定》第50条第6款直接效力问题,直接给出了否定结论。
欧盟法院对于WTO协定直接效力问题在两案中不同态度可能源于其在“葡萄牙诉委员会”一案中的裁决。“葡萄牙诉委员会”案发生在“Herms案”之后,欧盟法院在该案中明确认定WTO协定在欧盟法律体系中不具有直接效力。而对于在此之前的“Herms案”,欧盟法院对于直接效力原则的态度尚未明朗,不便做出明确的指示。即便总检察长建议赋予《TRIPS协定》第50条第6款直接效力,欧盟法院也只能采取谨慎的态度对直接效力避而不谈,况且荷兰法院提交的问题在字面上也不涉及直接效力问题。欧盟法院对于发生在“葡萄牙诉委员会案”之后的“Dior/Assco案”则可以直接引用其在葡萄牙案中的裁决,明确否定《TRIPS协定》第50条第6款的直接效力。
利用统一解释原则肯定《TRIPS协定》在欧盟内部的解释效力,相对于全面禁止私人以任何形式在欧盟内部得到WTO规则的保护,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进步。
(三)欧盟法院提出统一解释原则的背景分析
欧盟法院在WTO区域内效力问题上所确定的统一解释原则,也许可以从以下两个背景加以考察。第一,欧盟法院对于WTO规则直接效力原则的一贯排斥并无法解决私人利益保护的问题,该实践也同欧盟一贯尊重国际法的传统相背离。WTO规则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条约,虽然WTO规则为其成员创设了权利和义务,但旨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WTO规则本身对于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私人行为发生着重要的指引作用,WTO成员对于WTO诸协定的实施会极大影响私人参与国际贸易的活动。因此,WTO成立初期在欧盟内部关于WTO规则直接效力的讨论有肯定化倾向。然而,欧盟法院在“葡萄牙诉委员会案”中考虑到各成员在实施WTO协定上的“结果对等”问题(reciprocity),否定了WTO协定的直接效力。(49)由于否定直接效力原则会直接将个人利益的保护置于司法审查之外,这对于欧盟法院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荷兰法院所提交的关于《荷兰民事程序法》的解释问题刚好为欧盟法院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第二,《TRIPS协定》与其它WTO协定相比可能更宜适用统一解释原则。《TRIPS协定》在其第三部分的第二和第三节设定了一系列条款以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这些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比很多WTO成员的国内立法都要详尽,这就为按照《TRIPS协定》解释国内法提供了可能。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欧盟内部会有诸多案件涉及《TRIPS协定》第50条对于国内法的解释作用。
四、结论兼对欧盟实践的评价
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说,漏洞补充是指法律对于应规定的事项,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未预见或情况变更而没有进行规定,造成法律漏洞后,由法官加以补充的情形[14]。因此,法官在进行漏洞补充之前必须首先确认某一事项上法律规定的缺失是属立法者有意不为,还是因立法者的疏忽、未预见或情况变更所致。一般而言,法律规定的缺失往往是立法者有意的沉默而非无意的疏忽。在不能确定法律规定的缺失是因立法者的疏忽、未预见或情况变更所造成之前,不能将立法者有意的沉默当作其无意的疏忽,从而进行漏洞补充[14]。如果错将立法者有意的沉默当作漏洞进行补充,法官的行为势必构成了“造法”行为,违反宪政的要求。
如果我们再次审视欧盟法院针对《荷兰民事程序法》中“临时措施”一词所进行的法律解释,不难发现该案中的《荷兰民事程序法》对于临时措施期限没有做出任何限制。《荷兰民事程序法》的这一缺失属于应被法院所补充的漏洞吗?欧盟法院在利用《TRIPS协定》第50条第6段补充漏洞之前,理应具体分析《荷兰民事程序法》这一缺失是属立法者的有意不为,还是立法者的无意疏忽。只有首先确定了此属应予以补充的漏洞,欧盟法院才能接下来利用包括统一解释原则在内的各种方法进行漏洞补充。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问题直接进行漏洞补充,欧盟法院的这一行为在实质上类似于对《TRIPS协定》条款的直接适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1997年一个专利案中对于统一解释原则的适用。该案涉及对《日本专利法》中“为专利发明的实施所进行的商业准备”一语的解释,东京地方法院参照《TRIPS协定》第70条第4款的规定将该用语解释为“准备过程中进行的重大投资”(a significant investment for the preparation)(50)。与“Herms案”不同的地方在于,该案中《日本专利法》中有相关条文,只是不甚明确,属于狭义的法律解释的范畴。而“Herms案”所涉及的《荷兰民事诉讼法》在临时措施的期限上没有任何规定,因此要对其是否属于漏洞首先进行判断,进而决定是否采取广义法律解释的一种——漏洞补充来进行解释。
欧盟的实践说明了统一解释原则只能解决对国内法的解释问题,而无法解决国内法规定的有意缺失或与WTO规则相冲突的问题。如果国内法院在统一解释原则的适用过程中略微超前一步,利用WTO规则补充国内法规定的有意缺失,就可能构成被国内法律或实践所禁止的直接适用原则,有滥用司法权力的嫌疑。因此,虽然统一解释原则可以为个人和企业从多边贸易体制中获得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提供现实的保护途径,但对这一原则的适用仍要考虑到WTO成员内部的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分权与制衡,需要考虑到宪政民主对这一原则适用所设定的限度,否则这一实践所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不稳定性。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WTO成员司法机关在适用统一解释原则时分析国内法中条文模糊或缺失的具体原因,进而决定应否适用该原则对国内法进行解释,则统一解释原则适用的影响仅限于司法层面,并不涉及对立法者原意的违反。统一解释原则也因此相对于直接适用原则更容易被WTO成员所接受,成为WTO协议在国内法律系统中发挥更大效力且更为现实的可能途径。WTO一专家组在其报告中也指出,在直接效力被WTO成员普遍否定的情况下,通过统一解释原则实现WTO规则对于私人利益的保护实属必要。(51)
如果说美国在WTO规则直接适用问题上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欧盟的决策取向,那么欧盟在统一解释原则上的司法实践会对其他WTO成员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笔者始终认为,WTO协定国内效力问题上国家实践的发展可以反映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过程中国家决策与私人利益驱动之间的较量与平衡,从而预示着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传统国际法意义上私人角色的嬗变。
注释:
①回想《关贸总协定》缔结初期,《ITO宪章》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缔约方的国内批准,参加谈判各国却急于使《关贸总协定》通过《临时适用议定书》的方式而得以生效,其主要原因在于:缔约方在1945年到1947年中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关税减让的第一回合谈判,这一关税减让成果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实施的话,一旦具体减让内容被泄漏,由于关税减让会造成交易成本的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买卖双方会停止本该继续进行的交易,而等到关税减让结果实施后恢复贸易,这无疑将会对当时的国际贸易产生极具破坏性的扭曲作用。
②参见DSU第3条第2款。
③同大多数国际条约的规定相类似,WTO并不强制规定缔约方在国内法层面的履行方式,对于如何保证一致的问题,则留给各成员自行决定。参见《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
④在这个问题上,WTO成员哥斯达黎加是例外。
⑤See U.S.Uruguay Round Implementation Act,Sec.102 (a) (I),19 USC 3501.
⑥See Case C-149/96,Portugal V.Council,[1999] ECR I-8377.
⑦See C -61/94,Commission V.Germany,[1996] ECR I-3989,para.9.
⑧See Case C-53/96 Hermes,[1998] ECR I-3603,para.28.
⑨"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domestic law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far as possible in a way which conforms to a State's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See The domestic application of the Covenant :03/12/98,E/C.12/1998/24,CESCR General comment 9.
⑩Murray V.Schooner Charming Betsy,6 U.S.(2 Cranch )64,118 (1804).
(11)Restatement(Third)of Foreign Relations,§114(1987)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 条(2002年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9次会议通过).法释[2002]27号。
(13)参见Case C-106/89 Marleasing, [1990]ECR I-4135.
(14)在Poulsen & Diva Navigation一案中,欧盟法院要求委员会法规的解释必须在国际海洋法的相关规定下进行。See Case C-286/90 Poulsen & Diva Navigation, [1992]ECR I-6019, para.9.
(15)See Case C-53/96 Hermes,[1998] ECR I-3603,para.35.
(16)See Case 8/81 Becker V.Finanzamt Munster - Innenstadt,[1982] ECR 53,paras.23 - 25.
(17)See Case 152/84 Marshall V.Southampton and South -West Hampshire Area Health Authority,[1986] ECR 723.
(18)Id.para.48.
(19)See Case 14/83,Von Colson and Kamann V.Land Nordrhein-Westfalen,[1984] ECR 1891.
(20)See Case C-106/89,Marleasing SA V.La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de Alimentation SA,[1990] ECR I-4135.
(21)See Case 14/83 Von Colson and Kamann,[1984] ECR1891.
(22)See Council Directive 76/207,1976 O.J.( L 39) 40.
(23)Directive 76/207,1976 O.J.(L39) preamble.
(24)See Case 14/83 Von Colson and Kamann,[1984] ECR1891,paras.15 -23.
(25)Id,para.26.
(26)See C-106/89,Marleasing SA V.La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de Alimentation SA,[1990] ECR I-4135,para.3.
(27)See id.
(28)See id.para.7.
(29)See id.
(30)See id.para.10
(31)See the EC Treaty Article 220 (ex Article 164).
(32)Case C-286/90,Anklagemyndigheden V.Poulsen & Diva Navigation,[1992] ECR 1-6019.
(33)Case C -61/94,Commission V.Germany,[1996] ECR I-3989,para.9.
(34)See id.
(35)E.g.Case T - 213/97,Committee of the Cotton and Allied Textile Indus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cotton) and others V.Council,[1997] ECR II-1609.
(36)See Join ed Cases C -300/98 and C -392/98,Parfums Christian Dior V.Tuk Consultancy,and Asseo Geruste V.Layher,[2000] ECR I-11307; Case C-89/99,Schieving-Nijstad vof and Others v Robert Groenveld,[2001] ECR I-5851.
(37) See Case C-149/96,Portugal V.Council,[1999] ECR I-8395
(38)爱马仕公司请求法院认定,被告在临时措施实施3个月后才有权提出撤销临时措施的请求。而在被告提出该请求之后,原告可以在14天之内决定是否进一步提出有关案件实体部分的诉讼。尽管爱马仕公司声称其根据TRIPS第50条的规定提出该请求,但仔细分析TRIPS第50条的规定后会发现,爱马仕公司的请求曲解了TRIPS第50条的含义。
(39)See Article 50 (6) of the TRIPS Agreement.
(40)See Article 289 (1) of the Netherlands Code of Civil Procedure.See Case C-53/96 Hermes International Case,[1998] ECR I-3603,para.8-11
(41)Case C-53/96 Herme,[1998] ECR I-3603,para.35.
(42)See Case C-53/96 Hermes,[1998] ECR I-3603,para.28.
(43)Joined Cases C-300/98 and C-392/98,[2000] ECR I-11307,para.19
(44)See id.
(45)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管理知识产权事项的《TRIPS协定》常被称为混合协定(a mixed agreement),欧盟和其成员国共享管辖权(joint competence)。
(46)See Case C-149/96,Portugal V.Council,[1999] ECR I-8377.
(47)See Case C-89/99,Schieving - Nijstad vof and Others v Robert Groenveld,[2001] ECR I-5851.
(48)See id,para.35.
(49)See Case C-149/96,Portugal V.Council,[1999] ECR I -8377.
(50)参见东京地方法院于1997年4月11日的判决,953判例时报[J]268。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最高法院尚未在统一解释原则问题上发表意见,因此,东京地方法院的意见在日本的普遍适用性是有限的。
(51)See United States - Sections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WT/DS152/R,paras 7.73-7.77 (22 December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