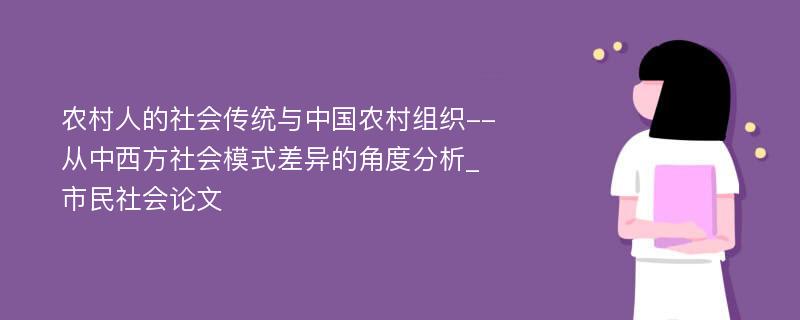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乡民论文,中西方论文,型态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西方合作经济理论传入中国后,合作社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提高中国社会最大弱势集团——农民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并使其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成为一种经济上的抗衡力量的最佳途径。学界关注的焦点强调合作对农民或乡村社会的必要性(存在合理性的分析);或是对合作社组织自身的剖析(产权、契约、博弈、代理、交易费用等经济视角)。然而客观现实却是,在最需要合作事业的中国乡村,其命运一直多舛,发展远不如发源地欧洲那样蔚为壮观①。乡民世界渴望合作而又难于走向真正合作。基于合作社组织发展的目标与现实之间的逆向和落差,笔者立足于中西方社会型态比较并从经济社会学的视野对此做一简要剖析。
一、中西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路径的差异性
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当社会经济生活日趋复杂之后,政府干预才渐渐增多,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期可能表现为主导力量,但这样的主导毕竟是短暂的,而且必定是既有市场主导积淀在前,又有重新过渡到市场主导于后。相反,20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相比,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逆体制”,即从一开始就强调政府主导。这方面,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中西方社会发展路径上的差异性。在西方,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和个体经济理性相当成熟的基础上形成的合作社组织,更多的是一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而在中国却是呈现为政府强力之下的“强制性”变迁中的“逆向运作”②。也即“民治”与“治民”之间的差别,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表现之一,主导体制上的逆向运作。从根本上看,合作社在西方是工业革命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工业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终确定,机器大工业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的分配失衡,一方面是少数资产者的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贫穷、饥饿的大量积累。在商品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组织的合作社,就是力图通过社员的集体行动,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也能有效分享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新收入流”的一种“制度安排”。最先是工人,后来农民跟上来,为对抗中间盘剥,在购买、销售、资金融通等某个生产经营环节上建立的联合经营组织。所以,西方农民的组织化总体上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社会需求”。
与西方相比,中国合作事业的推进路线是反其道而行,呈“自上而下”态势。原由就在于依附性社会中合作行为经济主体(民众)的个性解放与主体自由的不发达。曾主持过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秦亦文分析说:“近数十年来的中国问题,是西洋文化流入中国之后而来的,中国的社会运动是受着外来的刺激而发生的,即此已限制着中国的社会运动非由接近新潮流的知识分子发动不可,况中国乡村农民浸沉于传统的盘旋不进的文化之中,以安分守己、乐天知命为行动上最高之标准,更无由发动而为新社会组织之要求。从事于农民运动的人,常慨叹着乡村破坏日趋紧急,而农民不自觉,经济压迫日趋沉重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于有效的自救事业置之漠然而无奔赴参加之意趣。从事运动的人摇旗呐喊,大声疾呼,而农民并不动。若待他自动兴起,殆为绝对不能之事。”③民众自身的无主体意识和不自觉,使西方“自治性质”的合作事业在中国必须靠政府外力“强动”。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是一种“主导体制的逆向运作”。有学者曾指出:中国的“合作运动之萌芽、生长及发展,并未经自发的过程,全由于政治势力的孵育和金融资本的诱迫”,目的在于使合作社成为“政府对人民实施‘管’‘教’‘养’‘卫’之基本组织”④。政府力量的“强制性”,或者说合作事业行政化,在20世纪50年代后农村“合作化”、“公社化”运动中达到了极致。“人民公社”是一种异化的合作社,它是在超经济的政治强制下运作的,塑造出的多是封闭的、“政社合一”、“政经合一”的村社模式。其中,政治权力向自然村落的渗透、政府对农民行为的控制、泛政治化、计划经济、预设的经济发展模式等外部力量左右着村社和村民行为。这种组织化不是依据经济规律,从建立农业生产的利益激励机制角度出发去提高农业效率,而是追求政治认同,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教育和运动来激发农民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人们从权力对经济干预角度称之为“集权式的经济模式”⑤。显然,中国乡村的组织化过程中政府权力自始至终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运作模式,明显有别于西方“市场主导”下制度变迁的次序:先是有合作经济的根基——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形态,即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将其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⑥,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然后才是社会成员在市场主导下自发合作经济制度的诞生。
表现之二,发展层次上的逆向运作。建立在以自由、民主、平等为价值诉求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合作社组织,在中国却要“倒因为果”,成为实现这些价值诉求的一种工具。民众组织化的目的在于追求个体收益的最大化。合作社原则是自愿和开放、民主的社员管理、社员的经济参与及自治、自立等,由此体现出的合作社基本价值是:自助、责任、民主、平等、公正和团结。这些价值作为合作社组织“集体的价值”,实质上是以西方社会思想传统中所谓的“自然权利”(即天然的权利,通常认为包括人的自由、平等和财产等权利),观念和个人独立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推导和构造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言,在西方,个人作为终极实体在价值、权利、道义上的优越性和至上性始终存在,而且也是孕育现代性和合作社组织发展的“社会母体”与文化土壤。
中国与之截然相反,合作社组织被委以培育现代性与实现个体独立、解放及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如中国创办最早的一个合作金融组织——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在其颁布的旨趣书中就明确提出:该合作银行特点“就是公有的而非私有的,并不是银行家的银行,也不仅是股东的银行,乃是储蓄存户的银行,并且简直是无论什么人的银行。无论什么人只要能储蓄,只要赞成这个银行的宗旨,就可以享这个银行的完全利益。……所以这个银行的好处是完成各人经济上的独立平等与自由,是打破资本家的垄断,是培养民众的势力。”⑦再如,许多人士曾将合作社制度看作是“平均地权”的工具,试图借此来实现“耕者有其田”。实际上,这也是强制性变迁中制度发展上的一种“逆向运作”。在西方,拥有土地或承认私有财产及个别的所有权,即产权的明晰化,是合作社得以较好运营的基础。而中国却是将其顺序倒置,把高级阶段的事情提前来做,先要有合作社制度,而后希望靠它去创造促进这一制度良好运行的基础性条件——解决土地问题。这种“逆向运作”也同样体现在人民公社制度安排之中。当时所言的“农业合作化”,是在将比较抽象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和比较具体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问题对立起来,强调集体所有制下土地应该由集体共同使用、共同获得收益的土地产权制度⑧理念支配下运作的,主旨在于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劳动以保证产出增加并使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传送到工业化链条上去,即合作化服从于国家工业化目标和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灌输,而不是着眼于初级行为主体(农民)预期收益的实现和增加。很显然,此种运作模式也有别于英、法、美等国家先是国家的工业化,而后才是农民等弱势群体为有效分割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新收入流”而自发组织起合作社的经济结构变迁顺序。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国家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并行运作的制度安排,实质上是以淡化制度创新带给社员(农民)的经济绩效或对农民的“隐性剥夺”为基础,以有利于国家的收入流分割,并力图使社员的个人收益服从于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国家利益⑨;而西方工业化之上的社会民众组织化,则纯粹是以追求和实现入社社员的私人收益最大化为旨归,从不妄言代表国家利益。质而言之,无论是“逆向运作”,还是“倒因为果”,都体现了合作经济组织由以生长的欧美式市民社会的土壤在20世纪中国的极为匮缺与不足。
从总体上分析,中西方社会农村合作组织发展路径的差异在实质上体现出的是利益诉求内涵和利益诉求主体的不同。20世纪中国农村组织化(包括国民政府时代农村合作社及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收益最大化,利益诉求主体是政府而绝非是个体农民,由此而来的合作社不是农民自愿选择结果,而是政治压力下的被迫选择;相反,西方社会合作组织实现的是自愿结社者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利益诉求主体自然是社会中居于弱势地位的个体成员而非政府,即或是其中有点微弱的政府力量,但其充其量也只是为合作社组织更好发展扮演着“服务者”的角色。一语以蔽之,就乡村社会而言,借助政治力量而来的外部“嵌入性”与根植于社会土壤当中的“内生性”,就是中西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路径的差异。
二、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中西方乡村组织化差异发展的社会型态解释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指出:经济行为的根基在社会关系中,而各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却不一样⑩。如果说农村或农民组织化可以视为是一种经济行为(至少在初始阶段是这样)的话,那么中西方乡村社会组织化之间的差异和其利益诉求乃至于诉求主体之间的不同,就在于社会型态的悬殊。
20世纪中国社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谓之是一种“乡民社会”(peasant society,时至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情况虽有所改观,但从整体上看依然如此。特别是观念层面更是如此,大量存在的小农意识和乡土观念就是明证(11))。“乡民社会”是一个狭小的地方性社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内农民与手工业者的社会,受传统与历史支配;它是在“身份”(status)统制行动状态下存在的社会;个人被淹没在家庭之中,从来不被看作是“他自己”,没有任何基于自身特质与成就的地位(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理性思维以及商业活动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中西方社会发展上的时代差。然而,身居于传统依附性社会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却是以“共时态”的眼光去审视根植于契约性社会中的合作经济制度,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绩效——合作社组织对弱者利益的保护。因而,在功利性心态的驱迫下,试图通过“横向移植”的方式在中国推行合作经济制度,以解决社会中的经济问题。然而,缺少同合作经济相应的环境配合,致使强制性制度安排上的“逆向运作”状态。
经济行为是人类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从发生学上看,西方乡村社会的组织化,是西方社会经济环境的“内生性”产物,或更确切地说,合作经济产生于西方,但并非产生在社会秩序的“目的并不是把应属于每个人的东西给予每个人,而是维持集体的团结”的中世纪(12),而是产生、发展于“人的独立性”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国有许多学者则喜欢将其译为“公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内在特质,即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公民文化,是合作组织的催生剂。相反,20世纪中国社会,“一因国势贫弱刺激;二因经济制度之变化;三因欧风美雨之沾染,蓬蓬勃勃,大有一番新气象”(13)。知识分子基于现实的观点和工具理性而对西方合作经济理论作“简单性移植”,却对合作制度的社会经营环境缺少相应关注。所以,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合作经济,“不容讳言,那只是一种不加选择的外国货的转运贩卖工作,对国内社会经济实际情形的适应性,显然是非常不够的”(14)。事实上,从当时人们的合作经济思想演化的内在逻辑上看,他们也只是想把西方“市民社会”中既成的模式——合作经济制度直接地“嫁接”到中国这一“乡民社会”之上,这样无可置疑地就造成了理想与社会现实及文化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
“先天的不足”自然带来“后天的失调”。许多人士从反思角度对中国合作事业进行中的困境做了总结:“从理论上讲合作运动在中国,既有发展的必要,也应该有其发展的可能的,可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关系方面太多,也太复杂了,所以事实的表现,与据理的推断之间,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本来,合作运动是一种社会经济改革运动的具体实践形态,而事实的表现,往往非但对社会经济的改革无补,反而为经济现势中坏的权力倾向所操纵,所控制。同时,合作社是社会经济弱者的自救运动的组织,是为改善社会经济弱者的经济生活,为提高社会经济弱者的经济地位的,同样,事实上的表现,也往往非但不能完成此项使命,反而握有社会经济操纵权的强者所利用,加强对社会弱者的压榨和窒息,中国过去合作运动的情形,虽未必尽走上反作用的歧途,但究竟有多少社会经济弱者(也就是广大的人民大众)在合作运动的开展下改善了生活,提高了地位,却也是很难说的,至改革社会经济的不良制度,矫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良倾向,那更是有心人的一种希望了。”在此之上,人们更深入地强调:合作在经济上效用的发挥非但是其“真实灵魂”的存在,而且“本质上,也就是表现民主精神的一种尺度”。但这一切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着极大关系,在民主体制的制度下,“代表人民的经济利益的合作组织,自能发挥其民主的精神;否则,整个政治经济的体制如果是在独占、操纵、垄断的情形下,则合作组织的民主精神往往被阉割,合作运动的灵魂往往被出卖,合作的效用,亦就往往被变质的利用”。(15)契约性关系是自由、民主、平等存在的前提和保障,而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身份性社会和习俗经济,却是以压抑人的个性自觉和否定契约人格为条件的,靠其来推动商品生产者的契约性联合,实现社会个体利益的组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即便是勉强合作起来,也会是一种“有组织的无秩序状态”中的“垃圾筒”模式。
合作经济制度必须同相应的环境条件结合,才能展现效率、民主、平等诸价值。这一环境条件就是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包括法人人格)的存在(16)。从质上言,也就是要实现从身份性社会向契约性社会的转变。英国法律史学家梅茵(Henry Marine)在其名著《古代法》中写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7)只有在契约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社会成员才能挣脱以家族为核心的“礼俗文化”(或称之为臣民文化)的羁绊,走进具有普遍理性的公民意识,进而成为拥有独立个性的社会主体。马克思也说,“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不是手段而已”(18)。合作社组织,就是经济理性精神成熟的自由个体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现代化的合作经济只有在现代契约性社会取代传统依附性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20世纪以来中国的合作事业(其中也包括建国以后一直到现在的合作经济)和前苏联国家推行的合作制经济出现的困境,也都从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制经济的制度安排之基础是拥有所有权的私人之间的一种合约,契约性与依附性两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社会性质与经济关系,是这种以契约为依托的合作制经济在依附性社会陷于危机的根由。
一句话,从社会学上所谓的“模式变量”(Pattern-specific Variable)这一层面来理解:与乡民社会相对应变量值包括情感色彩的关系、特殊主义、集体取向和先赋地位,而市民社会相对应变量值则包括情感上中立的关系、普遍主义、自我取向和成就地位。两种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的悬殊,必然会使得制度在被行政力量强制性地“嵌入”到中国乡民社会时发生所谓的“制度变通”和“制度适应”(19)。20世纪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合作社“异化”和“异化”的合作社诸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这种“变通”或“适应”的结果。实际上,其变通或适应的最终,也必然损伤合作社制度绩效的正常发挥。
三、总结性评论
乡民社会是一个社会空间,或者说是一个“场域”(field),它是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农村社区中历史性地形成的生产、生活场域。在这一场域当中,传统和文化因素将人们之间的差异性抹去而遵循着社区认同的原则,并在此为基础上形成了乡民们作为个人或团体成员的特定认知和选择。而且这个场域往往是与自然村、邻里或血缘组织高度叠合。由此而来,亲情与“利他”也就成为维系这一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而现代市民社会的以个人命名的契约关系、理性思维及商业原则是乡民社会的“异己性”的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种社会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其在生存状态及信念方面有着迥然差别:乡民社会是一个“身份性社会”,个人被淹没在等级的制度之中,缺乏任何基于自身特质与成就的地位和冲动;市民社会则是在普遍自由、公平原则下运作的以个人的作为、利益的实现和贡献为自我命名的新的社会型构。也正是社会主体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性不同,直接决定了市民社会中以契约为纽带的“陌生人”之间合作,在其来到血缘、亲缘关系之上“熟人结构”编织而成的乡民社会时的两种必然遭遇:一是合作社的“异化”,最终形成“异化”的合作社,如人民公社制度;另一则是民众难以合作,即或是合作起来,合作组织也只会是受到发展缓慢、数量弱小、规模不大和业务无多等诸多困厄。实际上,农民的合作社组织是陷入到了“发展难”和“难发展”怪圈之中。这也正如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格雷夫(Avner Greif)在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经济制度运行剖析后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制度由两个相关要素组成:文化信仰(个人对他人在各种可能性下行为的预期)和组织(即内生的人类设计,它们改变了非技术决定的博弈规则,且只要付诸实施,总要形成均衡)。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一个函数,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应用其他社会组织的能力是有限的。……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于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20)。
总之,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准则及其型塑而成的“制度环境”,会对社会组织化、农民合作化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型态及与此相应的文化观念。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课题,除了“面对国家的个人”,还有“面对列强的主权”和“面对工业的小农”。质言之,中国社会的主体是阿Q式的农民,而不是西欧的市民。充分、自由的社会合作,只有在单个个体处于充分自由的、自主的状态下方有可能。个人的自主高度依赖于社会与社会合作。一个自己不能做主的人,首先是被剥夺了通过结社与他人进行社会合作的权利,故也无法在合作中承担相应的责任。个人不能自己做主,被剥夺结社自由的社会,即便是用保甲制度联成片,或用单位将个人穿成串,也仍然是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因为承认私有财产或个别的所有权是防止政府不当强制的根本条件,尽管不是唯一的,“一个不承认所有权制度的民族,是缺乏自由的首要前提”(21)。同时,一个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移植科技和管理制度,但如果“没有基本的和普遍的文化与人格类型的支持,赋予这些空洞的形式以生命,并赋予其行动者以意义和持续性。这些物质资源,这些修理和维护的规则,这些组织上的图表,这些伴随制度转移的行政管理大纲,都变得毫无意义”(22)。中西方社会的历史落差,就已经注定了合作制度在中国的不祥命运和它的历史限度。同时也昭示着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国现代性的多元性,并由此内在地规定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与方式的多元性。但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组织化而言,其中至少有一点是必然的:那就是农民从身份向职业转变、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并且要尽可能地向乡村社会或农民赋权,进而改善农民社会资本“存量”和扩展社会资本的“增量”。否则,政府所有的一切变革农村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乃至于陷入到“上面热,下面冷”、“官员热,群众冷”的困境之中。因为在个人失去表达利益和建议的权利和机会之时,外在的任何漂亮的承诺都不过是响亮的口号而已。
注释:
①据农业部2006年统计,全国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万多个,成员235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与67万个村相比,每4个村不足1个,所占比重极小。相反在工业化、现代化程度极高的许多欧美国家,合作社力量甚大,如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分别占市场份额的95%、78%、70%;在美国,4/5的农场主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80%,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参加合作社农民达90%以上;南美的巴西、智利80%左右的农户都是合作社社员。此外,就连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于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入社农户所占比重也不算低,像亚洲的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入社农民占30%-60%;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毛里求斯、乌干达等入社农民也达到了10%-30%(数据来自于《中国合作经济》2007年第3期)。中外之间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②此处的“逆向运作”概念受到杜恂诚教授启发,是指“人们为了求得发展速度或某种特殊的利益,跳过事物低级和简单的基础发展阶段,而致力于‘高级’和‘复杂’的经济事务形式,尔后却从‘高级’向低级,从‘复杂’到简单的逆向而行。”(参见杜恂诚《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性周期与逆向运作》,《史林》2001年第4期)。
③秦亦文:《邹平学制与合作运动》,《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3期,1935年11月。
④罗正纲:《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自主路线》,《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13期,1937年7月。
⑤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⑦《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旨趣书》,《申报》1919年10月24日。
⑧赵阳:《共有与私用——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3页。
⑨冯开文:《合作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⑩参见[美]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11)参见谢晖《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
(12)[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13)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页。
(14)陈仲明:《民元以来我国之合作运动》,载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52页。
(15)陈仲明:《民元以来我国之合作运动》,载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53-354页。
(16)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17)[英]梅茵:《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6-97页。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5页。
(19)李汉林等:《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以社会团结为视角》,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13-215页。
(20)[美]约翰·N·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张宇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美]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淮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221页。
(21)[英]阿克顿:《自由的历史》,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22)[美]英格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农民论文; 农业合作社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民合作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