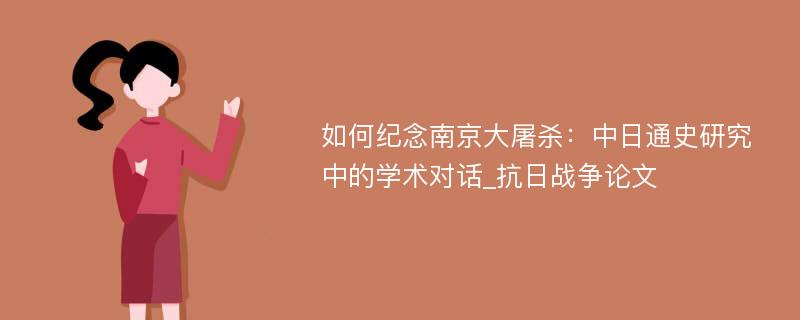
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大屠杀论文,中日论文,学术论文,记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1月,历经三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自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一直是学界和媒体报道、讨论的焦点,笔者作为中方外部执笔人承担撰写中方报告中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参加了多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研讨会议,现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讨情况作一简述,并结合自身研究谈几点个人观察与感想。由于囿于个人观察和笔录,其阐述或挂一漏万,或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关键词
在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2006年12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正式启动。根据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商定,中日共同历史分为古代与中世纪史、近现代史两个组开展共同研究。近现代史组以1931年到1945年的战争为界,确定了战前、战争中与战后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按时间顺序分设三个时期,分三部九章撰写论文。为了使中日双方学者围绕同一时期的研究内容大体对称,双方学者共同确定了每一时期若干重要的、必须涉及的问题点即关键词,要求双方的论文必须包括对这些关键词的论述。考虑到两国学者对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的认识可能存在分歧甚至是较大差异,双方确定先由中日双方学者围绕各个时期以各自视角分别撰写论文,然后双方对论文进行对照比较,互相交换意见,进行充分讨论。在接受了认为妥当的对方意见并修改后,仍然以双方论文并存的形式发表。即采取的研究原则是“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①
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双方委员共同商定的关键词,作为第二部(从1931年到1945年战争时期)第二章(从1937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共同历史中的必须论述的内容。中方研究报告第二部分第二章由《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研究员主持,笔者作为外部邀请的执笔人承担南京大屠杀关键词的论述。中方研究报告书第二章的题目为《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是该章第一节《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中第四目的标题。其内容包括:日军向南京进攻和南京保卫战的简况、日军对俘虏和青壮年男子的屠杀、日军在南京近郊农村对平民的屠杀、日军对妇女的性暴力、日军在南京大肆掠夺和焚烧的罪行、战时国际舆论谴责与日军掩盖真相、战后审判及受害数字。该目重在揭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包括注释内容在内共3000余字。
日方研究报告与此相对应部分由筑波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波多野澄雄教授和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第一战史研究室庄司润一郎研究员共同担任,南京大屠杀部分由庄司润一郎研究员执笔。2008年1月,庄司润一郎先生曾专程前往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进行交流。日方报告书第二章题目为《日中战争——日军侵略与中国抗战》,其第一节标题为《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与扩大为全面战争》,该节第四目题目是《攻占南京与南京大屠杀事件》,其报告内容主要有:日军进攻南京的复杂背景、中国守军不成功的防守与溃败、不同死亡数字及原因、日军军纪整顿、南京大屠杀原因分析。其字数(含注释)约2000字,重点论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上述研究报告虽然由各执笔人撰写,但经过双方委员和外部参加撰写人员的共同研讨,其修改后正式公布的研究报告事实上已成为集体共同的研究成果。关于南京大屠杀文本的讨论主要有两次会议,第一次是2008年3月14日至16日的日本鹿儿岛会议,第二次是同年5月5日至6日中国山东的济南会议。在会上,与会学者大都能冷静客观、真诚坦率地交换意见,纵有不同意见,其讨论甚至争论都能遵守学术规范,做到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两次会议之后,针对会议上对方委员提出的意见,双方既有坚持己见未作修改者,也有接受建议而作不同程度修改者,整个研讨过程极具学术理性。
二 围绕中方文本的讨论与回应
中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本是在鹿儿岛会议前提交给日方委员的,因此,在2008年3月15日上午和下午的鹿儿岛会议上,日方委员围绕中方文本进行了讨论。在5月4日的济南会议上也有简要的讨论。归纳起来,日方委员在下面三个方面提出了讨论意见:
一是关于日军处理俘虏的政策。中方文本在第二段专门讨论日军搜捕和屠杀俘虏的情况,其描述内容如下:
在日本海军封锁长江南京江面后,中国守军大都未能突围而被俘。一些部队于是“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大量中国军人被俘后均遭日军集体屠杀。据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师团长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说:“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②在攻占南京之后,日军仍然不断地集中屠杀俘虏,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在日军举行入城式的前一天,在长江沿岸的幕府山脚下分批屠杀了约2万人。③从现已发现的日军南京战斗详报来看,其战果中大都列有具体的歼灭人数,但却很少有俘虏人数。在南京战役过程中,日军自上而下执行屠杀俘虏的政策无疑十分彻底。
针对这段描述,日方委员认为:日军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日军方面并没有统一应对俘虏和制定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俘虏政策。因为没有统一的政策,因此,各个部队则有屠杀或是释放等不同的做法。关于日军战斗详报中很少有俘虏人数问题,日方委员认为当时可能如果上报俘虏数字,就意味着要粮食,所以就释放或者没有报告,但这不等于俘虏全部被屠杀了,因此,日方委员认为没有上报俘虏人数就一定是屠杀的结论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是关于中方文本中的史料选择问题。日方委员认为中方文本中的大多数史料都有充分的论证,很好地运用了许多第三方和加害方的史料,但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实,应该考证后再引用,如关于埋尸的资料与数字及1945、1946年国民政府的调查资料,其真实性应作考证。另外,如何选择史料也很重要,选择不同的史料其结论也会不同,如拉贝日记中既有关于日军的暴行,但同时也有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守军的批评。中方第一稿文本中涉及埋尸的一段话是: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被集体屠杀的遇难者人数19万余人,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④文本中在论述日军在南京近郊广大农村地区的屠杀暴行时引用了1946年汤山区战后调查的材料,其内容为:在战后1946年国民政府所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南京东郊的第十区孝陵卫呈报死亡名录为456人,60岁以上者117人,年龄最大者为90岁;在男女比例上,男性为344人,女性为112人,女性比例接近25%。⑤日本国内一些学者对战后国民政府南京大屠杀案调查的数字特别是关于崇善堂收埋112266具尸体的可靠性表示怀疑。⑥
三是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中方文本中在论述日军屠杀俘虏与平民、强奸妇女、焚烧等一些暴行个案时引用了具体数字,如:
同城区相比,日军在南京近郊广大农村地区屠杀平民的暴行也十分猖獗。据1938年3至4月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斯迈思(Lewis S.C.Smythe,原译史密斯)教授在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和六合部分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因日军屠杀而死亡者总数为30950人,居民平均每1000人中死亡29人,每7户中就有1人被杀。在年龄结构上,15-59岁之间占死亡人数的77%,60岁以上的老人占12%。另外,在被杀害的4380名妇女中,83%都是45岁以上的妇女。⑥。
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主要引用了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判决中的数字:
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在日军队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⑦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被集体屠杀的遇难者人数达19万余人,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⑧
日方委员围绕中方文本中的数字从两个方面发表了评论:其一,如果将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判决当作历史事实本身,而不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其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被屠杀者与阵亡者有无区别?平民与军人的比例是多少?日方委员认为对此应作进一步的讨论。
针对日方委员的评论,中方最后文本主要作了以下两点修改:一是在描述日军屠杀俘虏政策时,增加了一个注释,向读者介绍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根据现有资料显示,第十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第六十六联队、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都有证据表明当时日军确有屠杀俘虏的命令。参见程兆奇的论文《日军屠杀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在描述日军屠杀俘虏背景时增加了一句:“由于日军后勤准备不足,且因俘虏众多而担心带来不安全。”二是在介绍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判决时,淡化和删除了慈善机关收埋尸体的具体数字。由于讨论这一问题需要较大篇幅,因此文本没有就数字真实性的问题进行论述。关于学术界对慈善机关包括崇善堂收埋尸体的研究,日本学者洞富雄教授和中国孙宅巍教授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成果。⑩考虑到战后中日两国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死亡结构等研究成果有较大争议,在短短的3000字中无法展开讨论,为避免引起新的争论,中方文本在修改时没有增加论述介绍。
三 围绕日方文本的讨论与回应
在2008年3月14日下午鹿儿岛会议上,第一次正式讨论日方委员庄司润一郎研究员所撰写的“南京攻略与南京事件”(文本第一稿的标题)的内容。作为该主题的初稿,中方成员提出四点讨论:
(一)关于本目内容的定位。中方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二战暴行的重要标志,其他各章很少涉及日军其他暴行,因此,为了中日两国民众加深对二战日军暴行的了解,并从反省战争悲剧的角度出发,则应对日军南京暴行本身进行全面叙述,包括日军屠杀、强奸、抢劫和焚烧等。如轻描淡写而不以一定的篇幅进行表述的话,则较难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思考。在日方提供的第一稿文本中甚至没有提及日军的强奸、抢劫和焚烧行为。另外,日方文本虽然承认了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却没有使用“南京虐杀”或“南京大虐杀”这样的字眼,而是用“南京事件”来取代,尽管其所表述的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毫无疑问,使用“南京事件”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大屠杀”这一事件的性质。
(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日方文本中首先分析了日军方面的原因,“被认为存在欠缺关于处置俘虏(捕虏)的指针以及占领后保护居民等等的军政计划、约束军纪的宪兵数目过少之点,以及无视粮食和物资补给遂行南京攻略的结果,发生了掠夺行为,进而诱发军纪松弛的不法行为等诸点”。同时作为次要原因,文本也对中国方面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中国军队南京防卫作战的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指挥统制的放弃、缺乏民众保护对策等等。”中方与会代表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是侵略者、加害者,如果日军不侵略中国南京,根本不可能发生南京大屠杀,其责任完全在日方。如果在检讨南京大屠杀原因时,日方也讨论受害国的责任,则会模糊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让读者产生为侵华日军开脱战争责任的误导。当然如果是探讨南京保卫战成败的主题时,则可以检讨中国方面的失误。关于此点,在鹿儿岛和济南会议上双方都有较激烈的争论。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人数的描述。日方初稿在正文中没有表述,只是在叙述“华中方面军设想南京陷落后进城的部队,准备了所谓‘特别严肃军纪风纪’的严格规定策略(南京攻略要领)。这是对于上海战争以来违反军纪行为频发的对策,但是,在南京还是发生了包含俘虏和非战斗员在内的大规模屠杀事件”这段话时加了一条注释:“关于牺牲者的人数,中国方面的正式说法是30万人以上,日本方面则以20万人为上限,有着各式各样的计算。”中方认为人数问题虽然不必进行详细讨论,但在正文中如不作必要表述,而过分弱化屠杀人数的话,则无法说明南京大屠杀具有的大规模集体屠杀的性质。
(四)关于南京城内外的焚烧与破坏。在日方提供的第一稿文本中,没有提及日军焚烧和破坏南京城内外建筑的罪行,却特别强调了中国方面“为了不让日军利用,南京附近以及市内的主要建筑物因中国军队的焦土作战而付之一炬”。其引用的资料来源是中国学者孙宅巍教授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和日本笠原十九司教授(在日本被称指为“大屠杀派”的重要成员)的《南京事件》等,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强调其事实的客观性。但事实上,中国军队为了战略需要所进行的焚烧同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焚烧的南京城内外建筑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显而易见日方文本的叙述会对读者产生误导。
日方委员对中方的讨论和意见进行了积极回应,在2008年5月济南会议上提交的修改稿以及最后的定稿均有一定程度的修改。其主要修改之处有:一是本目标题作了修改,由“南京攻略与南京事件”改为“攻占南京与南京大屠杀事件”。二是在正文中增加了南京大屠杀数字的描述,介绍了远东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判决中的数字,当然也介绍了日本学界有不同认识的数字及其产生差异的原因。三是增加了一段南京暴行引起日本国内上层注意的叙述,当时日军参谋总部针对日军不法行为,下令要求松井石根进行整顿。但日方最后提交的文本中没有删除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次要责任的论述,日方委员在回应中方委员的要求时认为: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在日方,但中方的责任也可以作分析,如果中国军队不死守和投降,则结果可能不一样。除此之外,日方在修订的文本中也没有增加日军南京暴行的史实叙述;在叙述日军进行屠杀之后,增加了一句“同时强奸、掠夺和放火事件屡有发生”,但没有修改关于中国军队焚烧南京很多建筑物的叙述。
四 走向学术:寻求中日共同的历史记忆
众所周知,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步平研究员指出,中日历史问题是政治判断、学术研究和民众情感三个层面相互交错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学术研究是最终解决历史问题的基础。曾经是战火频繁、冲突不断的欧洲特别是德、法两国,经过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在20世纪后期走向联合,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欧盟,提供了解决历史问题的欧洲模式。步平期待经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这一通道,促进“亚洲模式”的建立。(11)毋庸置疑,中日共同历史的学术研究是亚洲能否建成共同体至关重要的一步。
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历史问题中最具象征的历史事件。近30年来,中日双方(包括政府、学者和民众三个层面)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从上述中日双方围绕南京大屠杀文本的讨论和回应的过程来看,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阶段性的成果,笔者认为有两点十分重要:其一,通过学术研究与对话,对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认定与日军犯罪的定性,在原则上两国学者基本渐趋一致。其二,由于运用史料、视角、方法的差异,以及研究者立场身份的局限,再加上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双方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仍存在许多差异。(12)“在实证研究不充分,或者实证研究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存在不同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13)
共有的历史真相是中日两国形成共同历史认识的前提,中日两国的学者肩负十分重要的责任。 为寻求中日共同历史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笔者以为中日两国学者今后至少可以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起努力来推动历史共同认识:
第一,建立资料库,加强史料研究。历史学者对历史事件进行解读就必须充分掌握和运用各种不同史料。但是,由于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资料在战争结束前夕绝大多数为日本所销毁(据藤原彰研究称经过多方努力寻找,参加南京战的部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记之类的正式报告保留下来),战争结束后由于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也未能及时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些因素导致为还原历史真相的研究带来了相当多的困难。最近中国方面由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牵头,通过艰辛努力,广泛搜集,整理出版了78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本方面也出版过一批相关资料。中日双方学者应加强翻译,共享这些资料,共同开展史料分析考证研究,建立可靠可信的历史资料库,从而奠定共同研究的基础。
第二,构建对话机制,深化专题研究。开展学术交流是推进学术研究进步的重要途径,中日双方学者围绕南京大屠杀研究虽然已开展过较多学术讨论活动,但仍未形成有效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机制。中日双方学者可经由民间和政府等建立多层次交流通道,有计划地设置双方关心的研究课题,如可以围绕南京大屠杀中的史料、图像、人数、西方人士心态、暴行原因、心理影响、日军部队行为差异等开展共同研究,拓宽研究视野,进行深入研讨,寻求历史真相,形成共同认识。
第三,拓展学术影响,引导社会共识。在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两国的民众、学者和政府三者之间相互制约。学者研究成果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术界,中日两国学者应尽可能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最新研究成果向社会推广,从而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笔者希望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应尽快出版公布,通过媒体进行准确报道,让中日两国民众和政府真正了解中日双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从而形成全社会良性的共同历史认识。
笔者深信,中日两国学者只要本着“以史为鉴”的理念,不断加强学术对话,寻求超越国境的中日共同历史认识,就一定能找到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亚洲模式”。
注释:
①参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会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报告书·近现代史卷前言》(未刊本),2010年1月,第136页。
②《中岛今朝吾日记》,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南京战史资料集》Ⅰ,东京,偕行社1993年版,第220页。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③笠原十九司著:《南京难民区百日》,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16页。
④《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馆藏号:五九三/870。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4),胡菊荣编;《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
⑤《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十区调查小组委员会办法、委员名单及抗属调查表》(1946年7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4,目录号1,卷号382。
⑥参见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内部读物),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261页。
⑦路易斯·S·C·史密斯:《南京战祸写真》,“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57、358页。
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杨夏鸣编:《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
⑨《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馆藏号:五九三/870。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4),胡菊荣编:《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
⑩洞富雄著,毛良鸿、朱阿根译:《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步平:《创建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亚洲模式”》,《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
(12)参见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学海·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3)步平:《创建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亚洲模式”》,《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