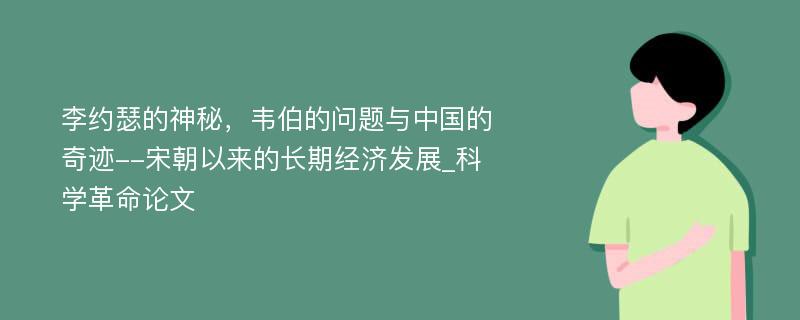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韦伯论文,之谜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疑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中国自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来,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持续快速增长,已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经济在古代已有极其辉煌的成就。根据麦迪森教授的估计,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Maddison,1998,p.40)①。但是,中国经济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以后人均收入就开始停滞不前②,欧洲却在肇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中逐渐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并在18世纪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尔后人均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欧洲GDP从1820年占世界比重的26.6%迅速上升到1890年的40.3%,人均GDP年均增速从1700—1820年的0.22%增加至1820—1952年的1.03%,而中国在整个近代史经济一直停滞,人均GDP在1820—1952年间甚至还下降了,同期GDP占世界的比重则从32.4%下滑至5.2%。
如果说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乱局是造成近代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78年,不再有战乱,而且在国家的主导下经过一整代人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步履维艰,人均GDP在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2.34%,低于同期世界2.56%的水平,GDP占世界的份额从1952年的5.2%略微下降到1978年的5%,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同期日本6.66%的水平,也低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只有直到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像其他东亚地区经济一样出现奇迹般增长。1978—2005的27年间GDP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6%,按官方汇率计算,2005年GDP达到2225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GDP从1978年的220美元大幅提高到2005年的1730美元;对外贸易总额2005年达到14219亿美元,从1978年的全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3位,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火车头(NBS 2006)。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一系列可能使中国突然出现危机的问题。中国经济有无可能克服困难,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如麦迪逊教授在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Maddison 2001)中文版序言中所预测的那样,在2015年GDP总体规模达到美国的水平,占世界的20%,此后继续维持较为高速的增长而逐渐恢复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历史地位?
本文以下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节讨论中国经济自宋以后长期停滞,并在18世纪以后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第三节探讨为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现代化未能使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分析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并存的原因;第四节,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并探索中国未来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可能性。
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一个经济长期的增长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对于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创新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主要来自于工人或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的数量多,因此,在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上占有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在前现代社会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并且,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的空间越来越小,技术创新的速度减缓,经济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停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无法深化。西方世界在15、16世纪出现了科学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新技术的发明转向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速,中国未能自主进行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迅速扩大,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迎来了百年动乱后的和平建设的机遇,作为一个技术和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的后发国家,中国可以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短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靠政府以扭曲各种要素产品价格、利用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才能将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建立起来,这种计划经济的体制固然可以使中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是,也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工人、农民缺乏积极性,经济发展绩效差。1978年底开始,中国以双轨制的渐进方式进行改革: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的赶超部门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以必要的保护补贴,并根据改革的进程和条件的成熟而改革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各种扭曲,使得经济得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提高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增加农户和企业可以自主支配的资源,并放松对原来受到抑制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准入,使得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渐进的改革,必然使得原有计划体制的某些制度安排和市场体制的某些制度安排并存而出现体制的不配套,其结果是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收入分配的恶化。只有放弃赶超的思想,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如果能够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资本快速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比较优势变化、产业结构升级时,能够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为主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中国应该可以再维持数十年的快速增长,如麦迪逊教授所预期的一样,在本世纪前半叶恢复在前现代社会的国际经济地位。
二、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18世纪以后中国国际地位的大逆转
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繁荣的国家。③ 特别是在9世纪后随着大量人口逐渐从干旱的北方迁移到多雨潮湿的长江以南④,牛耕轮作等新的生产技术的发明使垦荒日增,11世纪初又从越南引进新的水稻高产品种,并伴随相应的耕作制度和农具创新⑤,迄至13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农业的高剩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劳动力和资金。中国工业自汉代即有较大发展,宋代则达高峰。⑥ 以作为工业基础的铁的使用为例,11世纪末中国铁产量已达15万吨,人均水平是同期欧洲水平的5到6倍。⑦ 此外,井盐业、纺织业等工业也颇为发达,如13世纪已使用水力纺织机纺织麻线,其技术不亚于1700年欧洲同类机器水平(Elvin,1973,第195页)。由于农业和工商业的高度发展,13世纪中国城市的繁荣景象令来自以发达商业城邦著称的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感到惊讶(Elvin,1973,第177页)。此外,早在公元前300年的战国时期,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如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劳动力高度分工和自由流动、产品和要素市场的高度发育等(Chao,1986,第2—3页)。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Eberhard,1956; Elvin,1973; Tang,1979; Needham,1981; Chao,1986),但是,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⑧ 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博士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Needham,1986,第6页)?
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⑨ 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世纪中国已接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Chao,1986,第227页)。同时,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Tang,1979,第7页)。相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积累足够冲破工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Chao,1986,第227页),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Tang,1979,第19页)。
但是,上述假说的内部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这个解释变量自身为前提的,否则在技术不断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是难以出现的。进一步地,经验证据也并不支持这个假说,虽然在12世纪前确有许多节约劳动的农具发明,而后则寥寥无几(Chao,1986,第9章),但是在14、15世纪和17世纪中叶人均土地拥有量显著高于11世纪⑩,按这个假说,这些时候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应更强烈,人均剩余也应更高,尤其在1368年明朝开国后,天下太平,更应如此。可我们只看到人口的增长,而非节约劳动型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20世纪初,劳动力资源依然并不宽裕,尤其在南方灌区,农户全年不息(Buck,1937),因而Chao(1986)关于“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的论断难于成立。而且,中国在 1953—1958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农业技术仍基本停留在传统水平,但是,年均积累率也高达24.2%(NBSC,1988,第60页)。可见,中国农业可供积累的剩余不足的说法值得怀疑。而且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在14—20世纪初,仍有许多新发明出现(Elvin,1973,第289页)。若无技术创新,谷物单产要在10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段时间内翻番(11),也是不可设想的。因此,“高水平均衡陷阱”关于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农业剩余和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停滞的假说,逻辑不自洽,经验也不支持。
既然14世纪后中国的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为何与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后了呢?关键的事实在于,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有所减缓,而西方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创新则大大加快了,且一直保持了较快水平。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在于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Lin 1995)。
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trial and error)。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技术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依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小修正而产生 (Musson,1972,第58页)。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就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Simon,1986,第一章)。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的,但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Temple 1986),因此,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和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扩散(Maddison,1998,第23页)。8—12世纪,中国人口从较为干旱的北方大规模南迁到湿润多雨的南方,相应的交通工具从马变为船,合适粮食品种从高粱、小米转为高产的水稻,合适的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等随之改变,导致这段时间里较快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Chao,1986,第224页),中国因此维持了一千多年的领先于西方和世界各个文明的地位。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
欧洲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相对中国为小,工匠和农民的数量和相伴随的生产实践的经验也相对较少,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型技术创新中处于劣势。但是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广泛运用(Mathias,1972),“试错和改错”的次数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因而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特别到19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9,第165页),使得技术发明遭遇到瓶颈时,能够经由基础科学研究的努力,增加对自然界的认识,打破技术发明的瓶颈,扩展新技术发明的空间,而使得技术创新的不断加速成为可能(Kuznets,1966,第10—11页)。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渐转变为“为发明而发明”。这种有针对性的实验活动,代价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经济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制度可能确有利于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创新活动。但是,如果没有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技术发明在碰到瓶颈时可以利用科学来打破瓶颈,那么,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给西方带来的技术发明优势将会是一次性的,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小,西欧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迎来一段时间的技术发明的速度加速以后也应该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渐趋停滞。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宋朝以来的长期领先迅速转变为近代的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时发生在欧洲。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现象的一种系统的知识,在15、16世纪以前的原始科学来自于对自然现象好奇的科学家的观察所得,科学革命本身是一种方法的革命,15、16世纪以后对自然现象好奇的科学家开始把有关自然的假说“数学化”,并以严谨的可控制实验检验由数学模型推论出来的假说(Needham,1969,第15页)。这种科学方法的革命使得被证伪的假说迅速被抛弃,也使得不被证伪的假说易于传播和积累,对自然界的认识在这种方法的革命以后突飞猛进。但是,在19世纪以前,科学研究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科学上的新发现并未能直接运用于新技术的发明,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没有作用,因而,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不同,没有商业利益的动机。好奇心应该像智商一样是一种天生的禀赋,在人群中具有相同的分配比例,中国自古以来人多,具有高好奇心的人在数量上应该比欧洲多,在原始科学时代,中国在科学发现上的成就也不亚于西方世界,而且,中国古代已有较高的数学成就和相对系统的实验方法(Needham,1969,第211页),那么,这些众多具有好奇心的中国天才为何未能推动一场科学革命,发现用数学来表述其提出的假说,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其假说是一种探索自然、满足其好奇心的更好的方法?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Needham,1969,第211页)。钱文源等人则强调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不容异说,阻碍了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发展(Qian,1985)。可是,事实上中国重农抑商和正统意识形态对科学的阻碍并非那样绝对;而且在科学革命前夕的欧洲,政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好(Monter,1985),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革命先驱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与顽固不化的经院哲学家以及强大的教会势力作斗争。(12) 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即废除了封建,代之以官僚治理的郡县制度,各级官员由皇帝从非世袭的官僚中选派。在汉朝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初级官员的选拔是采用由各级官员推荐其任所内才能卓越、品德高尚人才给皇帝的荐举制度,虽然理想的状况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但是,不可避免地,裙带关系成为各级官员推荐人才的重要考虑因素,既失公正,也因而出现可能威胁皇帝地位的强有力氏族。隋朝(589—618)创立了科举考试制度,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来选举人才,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1904年被废除止(Ho,1962,第13页)。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举考试,分别针对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例如“明算”科是专门选拔数学能力强的人,“秀才”科专门选拔具有不寻常能力的人,此外,还设有举荐其他一些有全方位资质的人的渠道(Ho,1962,第12页)。但很快考试的范围就缩小到以“进士”科为主(Miyazaki,1976,第9页)。(13) 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14) 学生们需熟记长达431286个汉字的内容,并需熟悉篇幅数倍于原文的注解,以及仔细浏览其他相关的历史、文学等经典著作(Miyazaki,1976,第16页)。然而记忆并非最难之处,真正的难点在于,这种考试还考查学生运用汉语进行创造性写作的能力,因而带有智力测验的性质(15),只有那些天资足够聪颖且用心学习儒家学说的学生才能够在一层一层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16) 而当他们获得科举考试的最高学位时,平均竟要花费二十余年的光阴。(17) 尽管这样的过程痛苦而漫长,但学生们却有足够的激励投身其中,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官员从各种意义上都是最荣耀、最有回报的职业(18),以至于传统中国社会把做官看成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捷径(Ho,1962,第92页)。而且,科举制度本身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通过科举各层次的考试而获得相应各等级学位的人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特殊待遇。政府甚至通过公开宣扬科举考试能带来的个人利益来引导形成争相参加科举考试的社会风气。(19)
这种特殊的激励结构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人力资源状况。不仅因为最终岗位有限的官员的选拔是以绝大多数未考中的学生牺牲大量时间作为代价(20),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回报的激烈竞争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包括数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艺的学习。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从地方官员到中央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取得相应学位以及做官资格的人,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规范来行事才能获得晋升,因此,也无暇进行其他知识的探索(21),中国明代科学家的人数因而少得可怜。(22)
总之,我认为以儒家经典学说为主要内容并以高级汉字游戏为载体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中国具有较高天赋的人才大多专注于科举应试做官,或者进行人文研究,缺乏学习数学知识和进行可控实验的激励,更难以在这两者的结合和积累方面以及不断将自然知识数学化并加以实验验证方面做出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因此科学革命不可能自发地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时就具备了欧洲18世纪出现工业革命的许多重要条件,并且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韦伯,1997),但是,由于科学革命未在中国发生,技术在原始科学的条件下达到一定的高度后进一步发明的瓶颈不能被打破,没有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本也就无法不断深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受到限制,以至于当欧洲18世纪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并在19世纪用舰炮打开火药发明国度的大门时,中国仍停留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由于没有发生西方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在西方科技日新月异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曾经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出现巨大的逆转,并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的枪炮轰开了国门。从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在西方列强武力的胁迫下逐个签订,赔款割地成为家常便饭。(23) 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在中国衰弱落后的残酷现实面前开始了文化的反思,掀起的社会运动也从文化的器物表层逐渐深入到文化的制度和价值内核。(24)
起初的鸦片战争虽使中国认识到了西方器物的先进,但天朝上国的迷梦依然未醒,于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5) 的思想指导下,由许多清政府官员发起了意在自强的“洋务运动”,向西方购买枪炮、战舰等先进器物,兴办近代工业等,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可是这美好的幻梦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被彻底粉碎,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在于技术,也在于制度和组织(26),因而又分别由立宪派发动了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1898年戊戌变法(27),以及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试图建立民主共和制的1911年辛亥革命。但是,这些制度变革的努力,并未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尽管1912年推翻了清廷,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很快军阀混战却使得中国更加民不聊生。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中(28),旨在打倒陈旧的儒家伦理观念、高扬科学和民主旗帜的五四运动终于在1919年爆发,中国人第一次全面而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也在于伦理、价值观。
尽管1928年国民党政府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又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从1937年开始了全面抗战。当1945年中国取得了8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又经历了3年的国共内战。战火纷飞不断,人民流离失所,中国仍未能摆脱衰弱落后的局面。(29)
中国近代蒙受的百年耻辱,带给了太多中国人反西方情结。(30) 同时,许多中国人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所存在的周期波动、失业、收入分配不公、城市贫民窟等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因而认识到即使是比中国传统的制度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远非完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不断寻找着一种能实现他们历来志向“大同”的先进制度,既能实现国家富强,又可做到“天下为公”。因此,随着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有着富强、平等的美好理想的社会主义就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苏俄单方面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并帮助中国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而且其自身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梦想,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大国,恰与20世纪 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了社会主义。于是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党,并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纵观中国近代百年乱局,虽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本主义革命等尝试,但历届政府都未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挑战,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进程缓慢。战争外侮使中国丧失了诸如海关、铁路等经济主权,并对经济破坏巨大;战争赔款则使资本更加贫乏。(31) 战争还对劳动力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贫困和缺乏教育形成恶性循环,劳动力素质低下。百年乱局还使得中国始终缺乏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32) 总之,经济增长被技术落后、战争破坏以及赔款外侮所阻滞。只有到了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才迎来了推动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和平建国新时代的到来。
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败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奇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近代百年的乱局。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当时发达国家都拥有强大的重工业,因此,重工业的发达自然被当做国家富强的标志和目标。而且,苏联20世纪30年代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也给中国领导人以强烈的示范和激励。重工业自我服务循环的特征被认为可解决由于贫困农业人口为主而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需求的问题(33),并且朝鲜战争(1950—1953)使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中国迫切需要独立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和军事工业体系。因此,朝鲜战争刚刚结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成为贯穿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指导思想。
然而,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大量设备尤其是初期的关键设备需进口、一次性投入很大的特性,恰恰与中国当时资本稀缺(34)、出口少从而获取外汇的能力小(35)、资金少且分散的小农经济现实相违背。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实行低利率和汇率政策以压低重工业投资和进口成本,同时压低原材料和工资以减少重工业投入、保证较高的利润率和积累率,以及相应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保证城市工人生活,就构成了中国为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选择的宏观政策环境。这就造成了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为了保证资源能有效流向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国家垄断了这些资源的供应并以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而且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以防止它们将资源投向轻工业而违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36)。由于市场配置制度被全面扭曲,利润不再能成为考核业绩的有效指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防止国有企业经理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而损害国家最大程度积累剩余以发展重工业的意图,就全面剥夺了他们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利。(37) 由于农产品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工业原料,所以对农产品也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同时,农业又是国家换取外汇的主要出口品,为加大其生产能力,同时又不分散投向重工业的剩余,政府试图主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利用大规模劳动力密集投入的办法来兴修水利,并利用传统的密植、除草、增肥等方法提高单产,而且这也更便于政府实行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收购制度。由于要从农业部门转移更多的剩余以为不断推进的重工业建设提供积累,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断加速,并发展成了规模巨大的人民公社(Lin 1990)。至此,为了在资本稀缺的落后农业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宏观政策环境到资源配置制度再到微观经营体制这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便在中国建立起来。(38)
如果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最大限度地动员了资源。1952—1978年平均积累率高达29.5%,投资结构中重工业的比重从相当于“一五”时期轻工业投资的5.7倍上升到1976—1978年的8.4倍,重工业在1953—197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轻工业的1.47倍,工业占GDP比重从1949年的12.6%上升到1978年的 46.8%,中国在较低的人均收入下达到了很高的制造业比重(Lin,Cai and Li,2003,第70—77页),并且使中国在1960年代就拥有原子弹、氢弹,在1970年代发射了人造卫星。从在贫穷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动员一切资源以加速重工业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在1952年以后所推行的计划经济体系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由于中国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较低成本和较强竞争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背了这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而且由于微观主体缺乏自主权,劳动激励不足(39),产出实际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仅被压抑(Lin,Cai and Li,2003,第79—80页),而且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均十分低下,1952—198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根据最乐观的估计也仅为0.5%,只是19个被研究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World Bank,1985a),在国有企业这一数字甚至为负(World Bank,1985b)。而且,中国1978年人均GNP仅为210美元,一直未能越过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265美元的界限。(40) 劳动力大都滞留在农村(41),城市化率也远低于正常水平(42),经济内向性不断增加。(43) 事实上,不单中国,所有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发展都面临增速较低、结构扭曲、效率低下和福利损失、财政恶化和通货膨胀等类似困境 (Lin,Cai and Li,2003,第92—95页)。
同在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一样的低起点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步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成功实现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World Bank,1993)。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的经济绩效如此迥异于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对此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类不同的假说: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World Bank,1993);采取了政府干预(Amsden,1989; Wade,1990);推行外向型发展政策(Krueger,1992)。这些假说无疑看到了事实的不同方面;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较好地利用了那个阶段的比较优势。除香港外,“东亚奇迹”在早期也曾试行过赶超型的进口替代政策,但由于人口规模小、人均资源少而无法持续(44),因而较早放弃了政府干预下的赶超战略,于是在缺乏政府补贴的政策环境下,企业为了提高在市场的竞争力只能根据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等,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积累资本,然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才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 following strategy)(Lin,2003)。
违背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的各种弊病源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所谓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指“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不需要外力扶持或保护即可预期获得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Lin,2003)。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产品和产业选择是否符合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特性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然是在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的产业,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在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企业才会有自生能力(Lin,2003)。推行赶超战略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违背比较优势,试图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扭曲要素相对价格、行政干预资源配置、给予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制造贸易壁垒和行业垄断等一系列扭曲性措施来支持其投资和继续经营。并且,由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由于承担政府赶超战略任务的政策性负担所致,政府需对企业的亏损负责,给予各种补贴,在信息不对称下,政府难于区分企业的亏损是由于政策负担或是由道德风险所导致的经营性亏损造成,于是产生了企业为获得更多保护和补贴而产生寻租现象和预算软约束的问题(Lin and Tan,1999)。而那些本来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由于得不到足够资源而难于发展。推行这种战略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低下,欲速不达。
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缩小和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上的差距,才可能在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方面赶上发达国家。由于自然资源禀赋难以改变,劳动力增长相差不大,故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后者则取决于每期生产的剩余和积累率。当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时,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将会依据要素禀赋的特点选择技术、产品和产业,这样的选择会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能够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可以有最高的竞争力、最大的剩余和最高的资本边际报酬率,所以,可以有最快速的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的缩小也会最快。
一个企业产业、产品、技术的选择决定于企业所面对的各种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要使企业自觉遵守比较优势的原则来进行产业、产品、技术选择的决策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能够充分反映该经济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各种产品和要素的价格都由竞争的市场来决定,价格体系才会具有这种特性,所以要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前提是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东亚的经验来看,一个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会很好,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会很快,相应的也会有快速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的升级。这些升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需要有信息、协调,升级的成功失败都会对其他企业的决策产生外部性,因此,一个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除了和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必须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外,也应该用产业政策来为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协调,并以一定的税收或资金的扶持来克服企业升级时所产生的外部性。(45)
另外,遵循比较优势的国家会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并且,集中资源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出口这类产品,和实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国家相比,进口和出口都会较多,而呈现出外向型的特性,但是,进出口的数量其实由比较优势内生决定。
上述的讨论可知,“东亚奇迹”经济发展的三个特点正是它们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结果(Lin,2003)。
中国从1979年开始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从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向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型所取得的结果。(46) 1978年底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打倒了极“左”的四人帮重新取得领导权,并推动了旨在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改革之初并未有事先设计好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而是从微观入手推行双轨制渐进式改革。
当时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直接可观察原因是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所导致的工人、农民的积极性低下,因而改革最初就从这里入手,通过增加微观主体的自主权,激励其积极性,从而提高经济绩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农村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取代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剩余索取权,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巨大的生产绩效(Lin,1992)。同样,在城市的国有企业也推行了利润留成、承包制等放权让利的改革,允许企业有部分自主权,并分享企业的部分利润;到了1990年代,则将众多中小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其中有些则在国内和国际的资本市场上市。每个阶段政府计划干预逐步减少,而企业自主权则逐步扩大。
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极大提高了效率,中国农业在1978—1984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年均 7.7%的高速增长,其中几乎一半的增长份额来自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所带来的积极性的提高(Lin,1992)。同时,据估计,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也有了显著提高(Groves et al.,1994; Li,1997)。这样,微观经营机制改革就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创造了大量新增资源,有利于做大蛋糕,保持经济增长,从而为中国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由于国有企业被允许生产和出售计划外产品以获得更多利润,这就要求有计划外的资源配置来满足这种需求,因而迫使国家逐渐放开对物资供应、产品销售等资源配置环节的控制,逐步缩小计划配置,同时扩大由计划外市场配置的份额。由于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大量新增剩余,而国家对资源配置的放松又提供了获取原料和市场的机会,使得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有了发展的空间。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定位在长期被压抑、产品供不应求因而回报较高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因此,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甚至被某些经济学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伟大的成就(Sun,1997)。由于非国有企业不属于传统经济体系,不能通过国家计划而只能通过竞争在计划外的市场上获取资源,其产品只能通过计划外的市场渠道销售,因而面临较硬的预算约束,业绩取决于经营状况,所以生产率高于国有企业(Weitzman and Xu,1995; Sun,1997),给后者带来了竞争压力,迫使国家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仿照非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改革国企、减少以扭曲价格进行的指令性计划以增加国企利润 (Jefferson and Rawski,1995),这些改革也提高了国企生产效率(Li,1997)。因此,正是伴随这些非国有企业的成长,计划外的竞争市场才得以发育扩大,国有企业也才逐渐被推向市场。同时,由于非国有企业必须根据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决定的市场价格信号选择技术、产品和产业,因而大多在更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这就大大矫正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和低效的资源配置(Lin,Cai and Li,2003,第184—196页)。这样,微观经营机制的改善在创造大量新增资源的同时,也推动了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以满足将新增资源投向符合比较优势因而回报更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于是资源由计划配置的比重不断缩小,逐步发育的市场配置的比重则不断扩大,改革就从微观经营机制推向资源配置制度,不断深化。
计划外的资源配置通过市场定价,传统计划内资源配置依据政府定价,因而出现了价格双轨制。这也是用较高的市场价格对国有企业进行边际激励的同时,用较低的计划内资源价格为那些承担赶超战略任务因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保护补贴的必要手段。这种双轨制的好处是既避免了缺乏自生能力的赶超企业的大量破产,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同时,又让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有发展的空间,而使经济充满活力。
尽管最初双轨价格相差较多,但随着政府根据市场价格不断调整计划价格、非国有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两轨价格不断接近,同时由市场配置的资源比重日益增加,这就为最终的价格并轨创造了条件。到90年代中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都已完全放开而由市场决定。汇率改革也有类似的进程,从最初仅有政府为降低发展重工业门槛而压低的官方汇率,到为激励出口企业创汇而允许“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并存,再到数次调低官方汇率并建立起外汇调剂系统(47),最终在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
相比之下,利率改革最为缓慢,虽经数次调整,但始终为政府控制,至今仍未实现市场化。这既反映了承担赶超战略任务而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需要,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并未完全放弃原来的赶超战略的事实。低利率导致对资金的过度需求。在信贷配给权下放给银行以后,各地各部门积极争取贷款以投资扩大生产,使得能源、原材料和交通等基础部门供不应求,形成“瓶颈”;同时信贷需求超过计划供应,只好增发货币以弥补不足,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只好以行政手段严格控制投资和信贷规模,并重新收回某些下放权利,宏观调控具有向传统计划体制复归倾向,这使符合比较优势的非国有企业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相比,较难得到信贷、能源和原材料等关键资源,因而经济发展速度骤降。由于不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难以创造利税,因而财政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具有较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Lin,Cai and Li,2003,第199页),在后者由于宏观调控出现困难局面时,财政就相应吃紧,同时经营自主权的回收也造成微观主体的抵制。这样政府只好重新下放管理权限,并放开信贷和投资管制。在相同的逻辑下,又造成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可见,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发达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其根源在于改革中宏观政策环境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不配套,直接原因在于利率管制。(48) 同时也由于利率管制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行政干预措施使得寻租行为盛行,收入分配恶化。
既然原来计划经济下的许多价格扭曲和对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干预是直接服务于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那么,只有解决了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才能根本消除利率管制和其他行政干预的措施(49),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难以区分政府政策所造成的亏损和企业经营所造成的亏损,企业有让政府将亏损全部包揽的道德风险,形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Lin,Cai and Li,1998 and 2001; Lin and Tan,1999),从而削减了企业改善经营的动力,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企业治理问题。如果在不剥离政策性负担的前提下进行私有化,政府补贴在缺乏监督情况下将直接进入私人腰包,增大了企业向政府寻求补贴的激励。政府则由于这些企业的战略重要性,并担心这些企业倒闭将导致大量失业,带来社会动荡,只好继续提供保护补贴,因此政府补贴将不降反升。政府在大规模私有化后收税能力下降,补贴则不减反增,大量的财政赤字导致货币增发,价格因而飞涨。事实上,这正是苏东推行休克疗法后出现的情况。(50)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由于承担了政府的赶超任务而缺乏自生能力,在自生能力不解决情况下,试图一次性取消各种价格扭曲、市场干预、大规模私有化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休克疗法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51),因此失败难以避免。(52) 解决国企的自生能力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首要问题要解决必须首先剥离其政策性负担(Lin,Cai and Li,1998 and 2001),使政府不再需要以低利率政策性贷款、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维持其生存,然后才能实现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商业化(Lin,2000),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才能深入并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相协调。
回过头看,由于三位一体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起点而建立,因而中国的渐进改革尽管在每一步实践中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却遵循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改革从直接导致效率低下的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切入,迅速带来效率提高和新增资源,为实现微观主体将资源投向更符合比较优势的被压抑部门以获取更多利益的要求,必须允许计划外资源配置和市场价格存在,这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新增资源和计划外的市场配置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实现价格并轨和配置方式统一。因此,渐进改革不仅具有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使分两步跨越一条鸿沟成为可能。(53) 同时,微观经营效率的改善和新增资源给大多数人都带来了好处,不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则避免了重新分配存量资源带来的社会冲突,因而改革最接近帕累托改进(Lin,Cai and Li,2003,第327页)。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休克疗法忽视了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这个关键问题,因而在实践中遭遇困境(Lin,2005);与此相反,渐进改革最成功的一点则是:在经营自主权增加和市场竞争压力下,国有部门效率提高;保留计划配置方式使政府依然可提供低价资源维持其生存,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符合比较优势因而迅速发展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增长则使国企改革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小,为完成国企改革创造了条件,也提供了动力。所以,尽管中国的渐进改革最初并不被看好(54),但却以实践证明了它的有效。既然实行赶超战略的各国也都由于相同逻辑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改革之初与中国同样面临结构扭曲和微观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渐进改革就应具有普遍意义。(55)
不过双轨制的渐进改革固然使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来获得了奇迹般经济增长,但是,大型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使得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尤其利率的改革依然滞后,它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摩擦导致改革以来经济出现了周期波动和寻租行为盛行等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只有彻底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中国的渐进改革才能沿着自身的逻辑,在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的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完成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任务。
四、小结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展望
在这篇论文里,我分析了自宋以来中国经济绩效总体变化的原因。根据过去千年的中外发展经验,持续的技术升级是一个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主要来自于工匠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中国人多,在技术发明上,因而也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优势。15、16世纪在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使得实验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成为技术发明的主要机制,从而产生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技术日新月异。在前现代社会,由于科举制度所提供的激励机制妨碍了有才能的人获得除了儒家经典以外的人力资本,从而使得中国自身无法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因此,当西方工业革命后,技术升级加速,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远远落后于西方。
在现代社会,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技术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只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中国将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升级,这样技术创新的成本较低和风险较小,技术升级的速度会较发达国家快。然而,就像二战后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扭曲和行政干预来补贴和保护其建立及生存。通过这一战略,中国建立起了现代重工业部门,但是,经济效率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
1979年中国开始以双轨、渐进的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模式使中国经济在过去27年间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然而,在200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达到了1730美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因此,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中国人民至关重要。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64.1%,为所有大国之最,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
如上所论,持续的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中国能够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继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增长潜力,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再保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实现技术创新。(56) 二次大战以后的东亚四小龙得以实现大约40年的快速增长,就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来推动技术的快速升级。
从所有的主要指标来看,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跟日本1960年代早期非常相似(57),中国应该有像1960年代早期的日本一样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果中国实现了这一潜力,那么,正如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展望》中文版序言里所预测的,中国将成为21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将会成为第一个经历从鼎盛到衰弱、再从衰弱到鼎盛的主要文明。
然而,为了使这种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中国需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也应当遵循根据比较优势来推动产业发展的正确战略(Lin,2003)。同时,中国也需要把自己融入到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之中,从而有利于技术的引进、吸收、再创新,并随着经济发展,产业水平的提高、接近世界前沿而逐渐转向自主创新。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对这种转型、战略和一体化的承诺。
本文为2006年12月5~6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为庆祝Angus Maddison教授80岁生日而举办的“世界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和亚洲主要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长期绩效和展望”的研讨会而准备。本文的许多观点和论据参考作者过去的论文和著作。感谢易声宇同学在准备此文以及陈勇和海荣在准备本文英文版时提供的协助。
注释:
①GDP的估算有按官方汇率,有按购买力平价两种。除了特别标明以外,本文引用的GDP,均为麦迪逊教授按购买力平价并以1990年的国际货币为计价单位来估算。
②许多学者都同意宋代(公元960—1280年)是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经济活动异常活跃,见:Elvin,1973; Gernet,1982; Hartwell,1967; Jones,1988; Shiba,1970。根据Maddison的估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公元960年和1850年是相当的,而在宋朝期间则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在1280年后直到1820年的漫长岁月中则几乎没有增长。见: Maddison,1998,第25页。
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Needham,1954; Elvin,1973。虽然Maddison怀疑中国汉朝的经济和科技水平是否要高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前欧洲的水平(Maddison,1998,第38页),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欧洲处于黑暗中世纪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科技水平是领先的。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被Francis Bacon(1561—1626)认为是加速了西方从黑暗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重要发明,但他却不知道这些其实都源自中国(Jones,2003,第58页)。
④根据Balazs的估计,8世纪中叶(即唐朝早期),长江以南的人口比例为24%,见:Balazs,1931,第20页。而到了13世纪末,此比例可能已达到85%,见:Elvin,1973,第204页。
⑤由于新引进的水稻抗旱、早熟,有利扩大种植区域。关于旱作改为稻作引发的农具创新,参见:Chao,1986。值得一提的是,由Arthur Young发明的科学农业方法曾引起英国18世纪农业革命,而此法13世纪在中国即已盛行(Tang,1979)。
⑥关于这个时期工业方面的技术成就,Elvin,1973,第179页有扼要的叙述。
⑦见:Jones,2003,第202页。Hartwell认为从公元806年到1078年宋朝铁产量增长了9倍,人均增长了6倍,因而认为这是一次“早期的工业革命”(Hartwell,1966,第29页)。不过Maddison怀疑他仅仅基于宋朝首都铁的生产情况所作的估计是否合理(Maddison,1998,第37页)。
⑧见韦伯:《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载《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和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Daoism,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and Edited by Hans H.Gerth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K.Yang( 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Free Press,1968)。
⑨该假说最早由Elvin(1973)提出,后经Tang(1979),Chao(1986)等人进一步阐述。需要指出的是,Elvin和Tang强调的是可供积累的农业剩余不足,而Chao则侧重于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不足。
⑩中国人口增加持续到1200年,在1200—1400年间下降,1500年左右又恢复了1200年的水平,1600—1650年间人口再次下降。因此,14、15世纪及17世纪中叶人均土地面积应高于11世纪。关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历史资料,见:Chao,1986,第89页。
(11)这段时间内人口增长了5到6倍,同期谷物产量同步增长,且几乎同等程度的来源于耕种面积和单产的增加;也就是说,谷物单产在10到19世纪间至少翻番。见:Perkins,1969,第13到17页。进一步,根据Chao,1986,第 89页提供的资料可以发现,从10世纪末到14世纪末,可耕地和人口几乎都翻番;而从14世纪末到19世纪,可耕地虽然再次翻番,但人口数量却增长了6倍多,若采用Perkins(1969)关于人均谷物消费量和种植谷物的耕地比例基本不变的假定,则说明从14到19世纪谷物单产也至少需翻番。
(12)前汉时期商人基本受到了平等对待(Ho,1962,第42页);中世纪的中国,商业可以成为年轻人的一条出路(Eberhard,1956);而明清时用钱捐官位、学位已正式化(Ho,1962,第51页)。中国的意识形态也非绝对僵化:如明代王阳明对以官定的朱熹儒学的革命性挑战给中国的儒家思想留下了永久烙印(Ho,1962,第198—202页),中国在古代也未曾像欧洲那样,出现有人因为对自然现象提出异于当时人们接受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异端学说而遭受迫害的情形。
(13)关于科举选拔范围缩窄的原因,Ho(1962,第13—16页)列出了许多,比如“秀才”科的实际要求太高,数学、法律等知识对于主要的官员招聘渠道来说过于特殊化,“明经”科则仅仅侧重记忆而相对简易等,但最关键的原因却是:“进士”科考察对圣贤智慧的掌握程度和文字的创造性运用能力,这两点最接近儒家思想所要求的治国之才必须具有的深厚道德素养和聪慧品质,并也最有利于适应官员的管理工作,而且它比起汉朝的荐举制度又要公正客观得多。
(14)从汉武帝(156 B.C.—87 B.C.)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官僚体制的正统思想(Ho,1962),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本质上是分等级的,需要聪明、有道德的人来治理国家,而要选拔这样的人才,首先需要给民众提供机会平等的教育,以他们的表现来区分不同能力的人,并以此维系等级社会(15)。此观念早在战国时期即已深入人心(Ho,1962,第7页)。
(15)Ho(1962,第14页)认为“进士”科考试真正难的是创造性写作的要求。明代(1368—1644)科举考试逐渐形成了八股文定式,要在苛刻的格式要求中写出优美的文章,是高级文字游戏,被认为可测验聪明才智,因而被认为是较理想的科举考试方式。
(16)明清两代是科举考试鼎盛时期。一个完备的考试阶梯大体上可分为:预备阶段、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另外还有乡试的许多预备资格考试,以及乡试、会试后的加试。通过预备阶段的学习即成为童生,通过院试者称为生员,通过乡试者称为举人,通过殿试者称为进士(Miyazaki,1976)。
(17)科举启蒙教育自3岁始,8岁入学,15岁完成儒家经典学习,过程枯燥劳累(Miyazaki,1976,第14—16页)。然而这仅是科举考试准备阶段。据Zhang(1991)的研究,晚清平均年龄生员为24岁,举人31岁,进士34岁。这意味着从入学到中进士平均需26年。虽然这并不排除少数天赋极高的人在少年即中进士(Qian,2004,第128—130页),却仍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明代进士年龄则约在30岁左右(Qian,2004,第132页)。
(18)西方官僚从未获得过像中国官僚一样的社会地位和权力(Maddison,1988,第21页)。
(19)宋真宗所作流传千古的《劝学诗》直接以金钱、美女和社会地位诱劝读书人投身科举。见:Miyazaki,1976,第17页。
(20)当王朝统治进入稳定时期后,官员岗位数量将难有持续增长,如Ho(1962,第259页)估计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全国官员总数在10000—14000之间,因此科举人才严重过剩的问题便十分突出。明朝科举录取率,乡试在 4%,会试在10%左右。从生员到进士仅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生员以下还有数量更为庞大且无国家补贴的童生群体,由于科举考试造成的单一知识结构,多数读书人自我谋生能力有限(Qian,2004,第68、110、209页)。生员数量明末约50万,占人口0.33%(Qian,2004,第137页),远大于官员。
(21)中国科举考试的特殊激励机制对中国的人才结构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使得有志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寥寥,如一本重要技术著作《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在序言中写道:“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Sung,1637)
(22)根据Shen and Du(2006)的研究,明清两代合计进士共51561名,其中顶尖人物(即殿试前四名和会试第一名)925人。同期各科一流的专家学者共计1000人,其中科学家和思想家仅有86人。尽管无论是数据可靠性还是可比性方面都可能存有一定问题,但这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
(23)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可参阅:Maddison,1998,第二章。或参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0-v.13。
(24)根据Malinowski(tr.by Fei,2002)的定义,文化可分为器物、组织和价值观三个层次。
(25)即认为儒家思想文化仍然是好的,落后的地方在于器物层次,故应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
(26)日本曾经深受中国政治文化影响,但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无论技术还是制度上都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逐渐强大起来并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打败了千百年来的学习对象中国。
(27)变法主要内容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建立新型教育体制和现代行政机关、发展近代工业等,但很快便被官僚体系当权派推翻,史称“百日维新”。
(28)1919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德国在中国的租界青岛转给了日本而不是归还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29)长时间的战争使1952年中国人均GNP竟然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见:Maddison,1998,第48页。
(30)也有主张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的思想,但在实践上要完全彻底摈弃中国传统文化是很难行得通的。
(31)关于历次战争赔款统计,可参见:Xiao,2004,第12页。由于财政捉襟见肘(Young,1971,第146页),政府只得不断拖欠外债(Maddison,1998,第49页)。
(32)中国近代(1840—1949)共经历了12次大的战争,平均每9年一次。见:Xiao,2004,第7页。
(33)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计划前,苏联和中国一样小农经济比重很大,靠自身积累难以迅速增加资本形成,于是一些苏联经济学家构造出重工业封闭循环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型。参见:Domar,1983; Jones,1976。
(34)建国初中国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业占GDP高达58.6%(Maddison,1998,第56页),1952年人均收入仅为 104元人民币,即使按1952年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2.23元,也不到50美元,因此资本极为稀缺。1950年代初市场年利率合30%(月利2%—3%),每1元重工业投资5年后须有回报3.71元,10年后则为13.79元。如此高的利率严重阻碍了大规模重工业建设。见:Lin,Cai and Li,2003,第38页。
(35)1950年中国出口占GDP仅为1.9%,人均出口额不到12美元(1990年不变价)。见:Maddison,1995,第38、115、237页。大规模发展重工业需要进口大量技术设备,少量的出口所得外汇难以满足进口需求。
(36)这并非全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教条的缘故,而是存在利益动机。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宏观政策扭曲价格以加速重工业发展,但其收回投资的周期仍4—5倍于轻工业(Li,1983,第37页),使得投资轻工业对利益最大化的私营企业仍不啻为更好选择。
(37)企业生产资料和所需资金由国家定额配给,产品流通由国家控制,盈亏纳入财政预算,用工和工资分配完全根据国家计划执行。当1978-1981年刚进行改革,下放了部分企业自主权时,就出现了企业争发奖金影响上缴利润的情况。见:Lin,Cai and Li,2003,第55、151页。
(38)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者进口替代等本质上都要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我们称之为赶超战略),因而也具有相似的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高度管制的资源配制制度。这说明中国的经济体制并非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因而对中国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分析实质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详见:Lin,Cai and Li,2003,第60—67页。
(39)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不是以其表现,而是以教育程度、年龄、职位等国家工资标准发放(Lin,2004,第21页)。农村人民公社尽管以工作天数发放工资,但由于农业劳动地域广、时间长、影响因素多等原因而导致很高的监督成本,因而农民被强迫加入而无退出权的公社实际只能实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Lin,1992)。 Lin(1990)认为1959年后的农业生产大滑坡正与此有关。围绕其论文在美国学术界展开了争论,有关论文见: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17,June 1993。
(40)World Bank(1992,第184页)估计1978年中国人均GNP为220美元。265美元(1975年美元)的标准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1980,第49页)制订的。
(41)1952—1978农业产值份额下降了25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份额仅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减弱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吸纳能力的必然结果。
(42)1980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9.4%,只高出1952年6.9个百分点,低于Chenery(1988)所做的一般预测。
(43)对外贸易总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52-1954年的8.16%下降到1976—1978年的5.89%。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必然减少资本品进口占其总需求的份额,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由于获得资源不足,出口也会大为减少,从而导致整个进出口规模的相对萎缩和经济内向性提高(Lin,Cai and Li,2003,第83页)。
(44)正如下面将要论述的,由于赶超战略牺牲比较优势来维持重工业优先发展,因而低效高耗,其可持续性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和人口规模(人均负担资源浪费的程度)。
(45)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和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的最大差别在于产业政策所要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是否有自生能力。另外,遵循比较优势和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都可以有补贴,但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的补贴只是为了补偿外部性,这种补贴所需要的量很小,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的补贴是为了克服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需要很大量的补贴。
(46)在1978年前,中国也曾对计划体制进行过某些改革,但主要限于部门和地方资源配置权力的划分,并未改变赶超的实质,因而并不成功(Wu and Zhang,1993,第65—67页)。
(47)到1880年代末超过80%的外汇在此系统进行交易和结算,见:Sung,1994。
(48)腐败寻租也有同样根源:价格双轨制使得差价成为寻租对象,1987和1988年的租金分别达到2000亿、3500亿元,占GNP的20%—25%(Hu,1989),1992年光信贷利率的可寻租规模即达2200亿之巨(Hu,1994)。由于腐败寻租使国企难以得到计划内低价资源,而且引起社会不满,政府在1986和1988年试图重新严控资源配置,这损害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由于同样的原因,只能再次放开。
(49)休克疗法认为快速私有化是改革的前提,也是国企重组前提(Sachs and Lipton,1990)。对苏东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绩效并非主要取决于产权安排,而是激励结构和市场竞争程度,国有企业同样可以做到高效(Brada et al,1997)。
(50)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后尽管直接补贴减少,间接补贴仍名目繁多;即使在波兰,税款拖欠问题也依旧(World Bank,1996,第45页)。国有产权解除后各种管制、保护和补贴仍然盛行(World Bank,2002)。
(51)我们已看到,由于国企缺乏自生能力,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后财政恶化和通胀不可避免,无法保持宏观稳定;快速大规模私有化则不切实际,因为重工业资本难以流动(Brada and King 1991),人需重新培训,新的市场体制建立也需时间和资源(Lin,1989; Murrel and Wang,1993);世行的研究说明,私有化需数年才能完成,而法律和金融等体制的建立则需更久,因而即使休克疗法也是个渐进过程(World Bank,1996 and 2002)。
(52)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普遍产出下降,通胀奇高,社会状况恶化(World Bank,2002);尽管华约组织贸易崩溃加剧了产出下降,但休克疗法无疑被认为是罪魁祸首(Brada and King,1991)。
(53)从资源配置扭曲的计划体制转向符合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由于扭曲程度过高,苏东直接改革宏观政策环境、试图一次性成功的努力不免失败,不过价格双轨制也付出了寻租腐败的代价(Lin,Cai and Li,1996)。
(54)中国的渐进改革被认为有致命缺陷,而休克疗法则是理论完美和可行的(Sachs,1993)。
(55)一些经济学家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于其独特的初始条件,如比重巨大的农业人口和较少的补贴、相当分散的经济系统、许多富裕的海外华人华侨等,见:Woo,1993; Balcerowicz,1994; Qian and Xu,1993。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转型的成功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见:Chow,1997; Perkins,2002。我们不否认特殊条件对中国的贡献,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改革都应充分考虑并利用其特殊条件;然而有相似体制,面临相同问题,中国的改革办法之于其他转型经济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56)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引进并非原样照搬,而是要消化吸收,更要在引进的过程中创新。因此,即便依靠引进实现创新,也必须保持技术研发队伍,才能最好地吸收、运用、改进所引进的技术。同时,保持一定的研发能力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比较优势变化时,从引进技术转变为自主研发。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必要的自主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流程的创新。中国劳动力成本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当引进技术时,在不牺牲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生产流程中的许多步骤可能能够以劳动替代资本,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这种创新只能靠中国企业自主研发。
其次,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发达程度高于中国的国家却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创新只能由中国自主实现。
第三,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差距很小,且难以通过引进实现技术升级的产业中,中国企业必须进行自主创新。
最后,一些与国家安全相关,又不可能从国外引进的产品和技术,中国也必须进行自主创新。
(57)比如,生命预期,1998年时,我国男的是68岁,女的是72岁,日本在1965年时,同样是男的68岁,女的73岁;婴儿死亡率,1999年时我国是3.1%,日本1960年时也是3.1%,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2000年时是15.9%,日本1969年时是16.7%(Kwan,2002)。
标签:科学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第一次工业革命论文; 李约瑟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数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