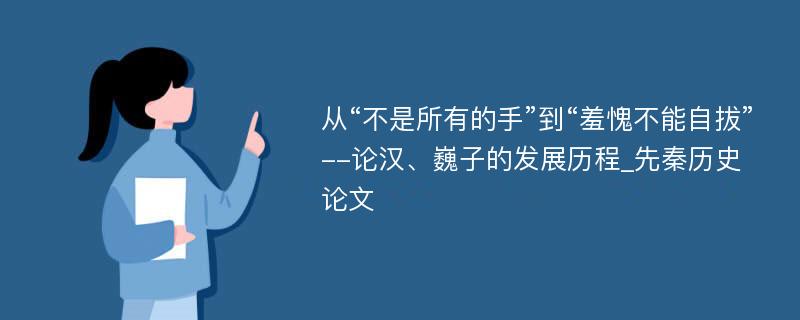
从“不皆手著”到“耻一字不出己手”——论汉魏子书的发展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书论文,汉魏论文,不出论文,一字论文,发展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1)04-0044-06
先秦子书很少出于诸子手著,先秦诸子的所有辩论、讲学、言谈皆着眼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人情、世态、或哲学思辨,关注其思想传播的共时性与影响力。所以经诸子门人弟子编辑而成的诸子书,不过是先秦诸子讲学布道的副产品。虽然汉初人即以“诸子”称呼先秦各家,但是“子书”这一名称在东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中才首次问世。即使如此,子书定义以及其文体的确定,其创作体式与规范的成熟定型更加滞后。假如我们视汉魏子书为一整体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虽然是渐进的,但仍可大略分成几个发展阶段。这几个阶段中,子书创作情况基本与子书概念的确定,以及世人对子书创作体式的认识和规范意识的成熟相始终。
一、初创
汉魏子书的初创期大约在西汉早期,此时期的子书创作固然有对先秦子书的延续,但是于作者主观上却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创新意识,此阶段的代表作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和晁错《新书》。
此时的子书创作尚处于无意识状态,成书原因多同于先秦。如陆贾《新语》的创作为受刘邦之命,自觉著书的意识不明显,所以班固把它算作刘邦开国初的功绩之一:“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汉书·高祖本传》)[1]81只是这十二篇文章因为写作时间比较集中,与贾谊、晁错二人的文章分别作于人生各个时期不同,所以更像是在写“书”。但是在陆贾写文之初也只是想着给刘邦上疏,想到一个问题即写一篇文章,并非本着创作一本“书”的想法进行宏观构思。所以,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陆贾述存亡之徵,奏之高祖,号《新语》,此与上疏无异,而分为十二篇。”[2]546即视《新语》为疏,只不过因篇幅较长而分章罢了。
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和晁错《新书》中的篇章因为大多为所上书、疏,因此文章内容多出手著,编辑成书则为学生或门人所为(如贾谊、晁错)。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古之诸子,平生所作书疏,既是著述,贾山上书,名曰《至言》;晁错上疏,谓之《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并见本传;”[2]547所论即是书疏与子书的关系。汉初诸子同先秦诸子一样,着眼于当世之“立功”,基本没有为后世“立言”的自觉。此时的子书,从体例上讲如同后世文集,但因其成书的滞后,所以书中亦间有非出手著的篇目。余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至于《连语》诸篇,则不尽以告君,盖有与门人讲学之语。故《先醒篇》云‘怀王问于贾君’,而《劝学篇》首冠以‘谓门人学者’五字,其《杂事》诸篇则平日所称述诵说者。凡此,皆不必贾子手著,诸子之例,固如此也。”[2]550-551所言“诸子”当指先秦诸子,意指贾谊《新书》中某些篇章,有沿袭先秦子书“追记”的传统。
此时的汉魏子书也同先秦子书一样,多为单篇流传,未经诸子之手统一整理编定。至于单篇流传的原因,多是受书写条件的限制。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案古人之书,书于竹简,贯以韦若丝,则为篇;书于缣帛,可以舒卷,则为卷;简太多,则韦丝易绝;卷太大,则不便卷舒;故古书篇幅无过长者,而篇尤短于卷。其常所诵读,则又断篇而为章,以便精熟易记。故汉人五经诸子,皆有章句之学。”[2]546余先生所述反映出西汉及以前书籍,受制于书写条件的情况及其变通措施。
此时诸子因为写作时不曾抱有写“书”意识,所以书名皆为后起。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中说:“古人著述皆书成之后始有大题:周、秦立言之家,多起于救世之急,但思载其论以行之天下,传于后世,初未尝先立一名而役役于著述也。下逮西京诸儒,有所论述,莫不先抒意虑,集为群篇,书成法立,始有标题。”[3]18所言“书成法立,始有标题”的现象亦存于三书中,但所言“西京诸儒”似不能涵盖汉初诸子。陆贾《新语》一书的得名在十二篇完成并献给刘邦之后,贾谊、晁错的著作连专名都没有,以子书的泛称“新书”传世。如(明)何孟春在《贾太傅〈新书〉序》中所说:“谊盖汉初儒者,不免战国纵横之习,其著述未尝自择,期以垂世。”[4]523
此期子书的文体意识未形成,往往掺入其他文体内容。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新书》曰:“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余皆录《汉书》语,且略节谊本传于第十一卷中”[5]270(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陈氏(陈振孙)称其末,载有《弔湘赋》。”[6]506余嘉锡也注意到了二人所说现象,他在《古书通例》中说:“《贾子新书》内有《弔湘赋》。《书录解题》卷九曰:‘《贾子》十一卷,首载《过秦论》,末为《弔湘赋》。’即史、汉传内之《弔屈原赋》,《文选》之《弔屈原文》,今本无此篇。案《汉志》有《贾谊赋》七篇,《新书》独载《弔湘赋》者,以此篇尤其平生意志之所在也。”[7]53余先生从文章立意的角度解释子书内收有赋作这一“非正常”现象,或可作为一种答案。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亦可归结为汉初诸子文体意识的淡薄,又加之此赋与立言之文主旨相近,所以编书者才会选其入子书。但亦可如此理解:编辑《新书》的人之所以会在《新书》中收入与子书之“立言”体完全不同的《弔湘赋》,系因此赋能述贾谊“平生意志”,即具有“自传性”,收入此赋可以弥补贾谊《新书》没有附益“自传性”文章的缺憾。附益“自传性”文章于代表作,尤其是期以传世的子书中,是自两司马之后逐渐形成的惯例,贾谊《新书》中无此类文章,后人以赋补之。(见拙作《汉魏子书的体式》)
此期子书虽无书名,但篇名已不可或缺。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陆贾为高祖著书十二篇,而本传言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然则随著随奏,固当时之通例也。……盖与其前后诸篇,皆所上之书,而以一事为一篇也。《新书》正是此例。汪中《述学》卷三《新书序》云:‘自《数宁》至《辅佐》三十三篇,皆陈政事。’按《晁错传》,错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则知当日封事事各为篇,合为一书,固有其体。”[2]547-548指出汉初子书的篇名是创作之初即已确定了。源于书、疏多为专题论文的原因,汇编的子书篇章也有明确篇名,这点与先秦子书取首字名篇相比,是创新与进步。
此期子书特点:第一、子书的篇章多出手著,少数出自门生弟子追记。第二、作者没有作书意识,书名后起,甚至没有专名。第三、子书多以单篇形式流传,全书编定于后人。第四、篇章有确定名称,而且多为专题论文的形式。第五、全书多是书、疏的集结,类似后世文集。
二、发展
自汉武帝至东汉初为汉魏子书的发展期。此期的代表作有:刘安《淮南子》、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桓谭《新论》和王充《论衡》。据其成书情况言又可分为两类,以下分别述之:
(一)假手与改编
《淮南子》与《盐铁论》是其代表。两书的共同点是:内容皆有所依托,不全系署名者构思,但又区别于先秦子书及初创期中少数的后人“追记”。《淮南子》的成书依托刘安门客的群体智慧,名之曰假手。《淮南子》“假手”的作法,实是模仿秦相吕不韦,所以萧绎在其《金楼子·序》中把两人并提:“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讬人。”[8]1《盐铁论》的内容是依托于盐铁会议上的双方辩论,名之曰改编。余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桓宽《盐铁论》虽非奏疏,然皆记当时贤良文学与丞相御史大夫丞相史御史问答辩论之语,首尾前后相承,直是一篇文字,而必分为六十篇,此其篇名,明是本人所题,非由后人摘录也。”[2]547即说桓宽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改编。正因桓宽改编,使之符合子书分篇的体例,《盐铁论》亦可算作他的著作。虽然二人之书皆有所依托,但是无论是“改编”还是“假手”,皆出于完成一部“书”的目的,这与初创期的无意成书相比是一个进步。
无论是吕不韦、刘安,还是桓宽,在“假手”与“改编”之时,只是想要完成一部书,毫不留意内容的原创,即刘安与桓宽从未对自己成书方式的合理性产生过质疑,这依然受先秦余绪的影响。张舜徽所论:“上世质朴,群视道术为天下公器,人惟期于明道,非若后世文士,欲暴其才,有所作必系以名氏也,其立言可谓至公矣。”[3]27正好可以解释上述三人的举措。东汉的桓谭在谈及此事时,评价曰:“秦相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王,聘天下辩通,以著篇章。书成,皆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异者,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9]2桓谭称“假手”为“请迎高妙”与“聘天下辩通”,言辞间充满赞许与仰慕。萧绎之所以讥刺二人“假手”,实因时过境迁,思想有了很深的隔阂。西汉前期距战国尚近,文章著作只为“载道”,而所载之“道”姓“公”,所以不在乎文出谁手,署名只为著述的方便与标志,创作群体也以参与著作立言为荣,并无著作权的考虑。至萧梁,著作与所言之“道”已经完全“私有化”,子书作者亲著的体式也已成熟定型,所以吕不韦、刘安二人借助门客著书与萧绎著书“不令宾客窥之”形成鲜明对比,让后者觉得难以理解并加嗤笑。
刘安主观上有了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的意识,虽没有篇必亲著,但是整书结构的谋划及其主导思想与书中一些篇章的写作,均来自刘安本人。所以《淮南子》虽然内容庞大且存“假手”现象,但绝非杂乱无章的拼凑,而是各篇既独立成文,又有内在联系,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子书。它所具有的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特点,是汉初学术复兴的一个缩影。汉魏子书内容上无所不包的特点,也在《淮南子》中初步形成。
此期子书设有大、小序,用以说明作书和谋篇的想法,体式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需要明确是,虽然《淮南子》一书既有“大序”也有“小序”,但其“小序”与篇章的关系并不像他言说的那样紧密,某些篇名仅仅是其创作愿望的一种表达而于篇章内容中没有体现。比如《齐俗》、《氾论训》、《诠言训》、《说山训》、《说林训》等篇,并无一个特定主旨,其内容以类相从,编排体例似类书。桓宽《盐铁论》的最后两篇《大论》与《杂论》,原意也是想对全书主旨及其内容设置做出交代与总结,只是受其依托的辩论内容所限,这两篇内容都未能体现篇旨。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受其成书方式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子书体式不成熟的反映。
(二)模仿与批判
此类子书的代表作有扬雄《法言》、桓谭《新论》和王充《论衡》。扬雄的《法言》与《太玄》关注于模仿与固守,这源于他的尚经思想,如“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问神》)[10]164。桓谭《新论》则是对于传统与现实批判的开始,此种批判为王充《论衡》所继承并发扬。无论是模仿还是批判,三人又把子书创作导向更进一步的成熟。
扬雄两书均出于模仿,《太玄》模仿《周易》,《法言》模仿《论语》。《易》是“六经”之一,所以在当时《太玄》也被视作经书,以桓谭为代表的汉人多以《太玄经》称之。《论语》在当时虽未被视作经书,但因孔子身为儒家宗师,汉人不以“子”待之,所以《论语》也不被视为“子”书。在《汉书·艺文志》里,《论语》被作为班固所谓“序六艺为九种”的“九种”之一。在《扬雄传》中,班固“赞”曰:“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1]3583,班固以“传”称《论语》,所以扬雄对己作《法言》也不认为是一部“子”书。如《法言·君子》篇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10]498扬雄认为孟子尚且不在诸子之列,更何况孔子。又《吾子》篇云:“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10]67可以看出扬雄对于先秦诸子轻傲的态度,所以他是不会把自己模仿孔子的著作归于“子”类。
究竟如何看待扬雄对于先秦著作的“模仿”?其实扬雄本人早已在《法言》中给出了恰当的评价,如《问神》篇说:“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则述,其书则作。’”[10]164根据义疏所说:“道之大原出于天,虽圣人亦但能有所发明,而不能有所创造。若夫援据所学,发为文辞,垂著篇籍,则正学者之所有事,虽作,亦述也。”[10]166汉人著作,若论所持之“道”则为模仿,若论“文辞”、“篇籍”则无疑是创造。
两汉之际的桓谭,不仅承担起了陆贾在汉初的责任,自觉为刘秀总结新莽覆亡的教训,且为汉魏子书的创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扬雄《法言》中所云“书与经同”,视己作如“经”的意思尚较隐约。桓谭在《新论·本造》中向世俗的迷信发出质问,称己作“何异《春秋》褒贬耶”[9]1,不仅自诩如此,对扬雄的《太玄》也一样,预言后人“必以《太玄》次五经也”[9]41。《新论》中设《正经》篇,从经书字数、内容,研经之人、研经之法以及时人对于《五经》的种种误解与偏颇的认识予以集中地批判与纠正,开启了汉代子书以“批经”作为现实批判之一种的先河。《正经》与《祛蔽》、《遣非》、《辨惑》诸篇,共同构建了《新论》批判的模式。桓谭在“破”的同时,也在“建”,他在《正经》篇中为扬雄《太玄》、《法言》于当世的不公正待遇而大声疾呼,做出“《玄经》数百年外,其书必传”[9]41的大胆预言,就是“建”的体现。桓谭不拘流俗的鲜明个性,使得《新论》呈现出此前子书所没有的批判特征。
《淮南子》虽然自称“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11]700,号称其书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并没有专门谈论音乐艺术的专篇。而桓谭《新论》设专文谈琴乐,种种琴乐的起源以及与琴有关的故事皆网罗其中,有故事,有赏析,有制度,有人物,有心得,是子书历史上第一篇琴乐专论,开子书设乐篇的先河。
王充《论衡》的成就体现于以下几方面:第一、大力拓宽桓谭所开创的子书“批判”性格的新局面,使得“疾虚妄”的内容更加广泛,分类也更加详细。比较桓谭《正经》篇,《论衡》针对“经”的批判分别设有《艺增》、《问孔》两篇,对于史书、传书、子书的批判分别设有《非韩》、《刺孟》、《儒增》、《语增》、《道虚》等篇分门别类地一一纠正。他对于世俗之人所持的种种偏见与误解的批判也是不厌其详、事无巨细,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的《论衡》之文过于“重”,但他本人不以为意。第二、虽然书中有很多观点前后矛盾,但是他以“鸿儒”自居的信念从未动摇,并且第一次从经、子的不同区别出“世儒”与“文儒”的迥异身份。他在书中为著作之“文儒”们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凭借己作以称王、相的幻想,发前人所未发;第三、王充以其敏感的心灵关注有理想、有抱负个体的人生际遇,对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予以全面而详尽的描述,如《逢遇》、《累害》、《命禄》、《幸偶》诸篇所谈论的内容,这也是此前子书所没有的;第四、语言浅显通俗,也是《论衡》所开创的独特风格。这使得子书的读者层下移,从而更容易实现其“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12]611的目的。
此期子书的特点:第一、无论子书内容依托与否,作者皆具著书的自觉意识,亲自编定成书并命名;第二、子书作者的自信心进一步增强,表现为或把己作上攀至子书作者的“经”的位置,或为处于子书作者行列而张扬呐喊;第三、子书的著作体式进一步发展,如大、小序的出现和“自传性”篇章的附益;第四、子书的大多数篇名能够涵盖篇旨,少数例外。
三、高潮
此期在东汉中晚期至汉魏之际,表现为思想上的融汇与争鸣。此期子书大量涌现,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所说:“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璅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13]308。不论其言语间是否含有贬低之意,此时子书的鼎盛无疑是确定的。此期的代表作有: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崔寔《政论》、陈纪《陈子》、魏朗《魏子》、侯瑾《矫世论》、荀悦《申鉴》、应劭《风俗通义》、徐干《中论》等。
汉魏子书的高潮在此时出现的原因有三:第一、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这是汉魏子书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先秦至此,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子书无论从体式形成还是其概念的认识上均已定型,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著作形式;第二、新学兴起,儒学独尊的局面被破坏,文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学创作自觉意识快速发展,大大促进了文人进行子书创作的热情。第三、从子书功能看,此时的子书创作完成了由“公”向“私”的转变,它的“言以载道”功能在逐渐弱化,而越世“流名”功能被不断强化,导致士人对之青睐有加。第三、从生活环境看,作者所处政治环境的恶劣与社会环境的动荡,促使更多有识之士投入到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与关注中。另一方面,诸子身处混乱的境遇,现世的“立功”愿望更难实现,所以专注于为后世“立言”。
此期子书作品宏富,加速了子书创作规范化进程。桓范在《世要论·序作》篇中说:“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14]1263这段话,是对于此时子书泛滥的批评以及当世文人的奉劝。文中的批评之辞“世俗之人,不解作体”,反映出他对于子书体式规范化的强调。从另一方面来看,子书的泛滥以及对此现象的批评也促进其规范化意识的提升。汉魏子书创作到达高潮而趋于泛滥,既有利于促进子书写作的规范化发展,还是产生更多子书精品的保证。子书创作得愈多,才愈能提供更多比较鉴别的对象,促使判断的标准更加完备,反过来指导与鞭策子书创作,促进子书作者的精益求精。
具体来看此阶段子书,其突出成绩有:第一、“后汉三贤”是继桓谭、王充之后子书“批判”功能的发扬者,最终掀起东汉末的批判风潮;第二、《潜夫论·志氏姓》篇与《风俗通义·姓氏》篇前赴后继,完成了先秦“姓氏志”遗留给汉代的使命,使得姓氏学薪火相传;第三、《风俗通义》更是开创出子书贴近社会底层的风格,在通往世俗之路上比王充走得更远,成为汉末世人兴趣由“雅”转“俗”的风向标。第四、《风俗通义》的篇章内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分类排比者,在资料整理方面似类书,但是又比类书更有条理;第二、专题阐述者,几乎每篇皆可当作相关主题的历史综述。这样的体式,使其书表达手段更加灵活,增强了反映现实内容的适应性;第五、无名氏《中论序》为第一篇他人AI写作的“大序”,并且置之书首,奠定了后世书序置书首的模式;第六、仲长统的《昌言·自叙》一改先前子书中“叙传”文章以叙述为主议论为辅的惯例,纯为抒情描写,亦是创新。
此阶段子书的特点:第一、子书创作盛况空前,但是良莠并存;第二、子书“量”的大增更利于世人评判比较,从而突出精品,促进子书体式的规范与成熟;第三、无论从内容所涵盖的范围,还是篇章的构成看,子书对“全”与“专”的要求齐备;第四、子书的政治服务性特点比较突出,这是当时政治影响的辐射所致。
四、尾声
此期约在三国时,代表作品有:曹丕《典论》、杜恕《体论》、《笃论》、阮武《政论》、刘廙《政论》、王肃《政论》、蒋济《万机论》、桓范《世要论》、钟会《刍荛论》、陆景《典语》、谯周《法训》、诸葛恪《诸葛子》、顾谭《新言》、张俨《默记》、裴玄《新言》、姚信《士纬》、周昭《新论》、刘廞《新议》、殷基《通语》等。
此期子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对于前世子书创作的总结与对后世子书创作的垂范意识相结合。且不论先秦子书提供的经验,仅从汉魏子书自身的发展讲,经过三个阶段的积累,特别是在经历了其巅峰之后,此时已有对之做一总结的客观需求。虽然大的政治环境依然是分合不定,但是局部的小环境还是相对稳定的,尤其是曹魏,在曹氏父子的经营与努力下,社会上层弥漫着良好的著书论文的气氛,这使得对前代学术进行总结成为可能。
从主观条件讲,自汉代中晚期开始的文人自觉意识的萌发至此已经发育得比较成熟,子书创作不再是“不得已”之举,不再具有此前子书所附着的浓郁悲剧色调,担负过于沉重的寄托。子书创作与现实功业的建立不再表现为尖锐的对立与冲突,而是作为子书作者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是“不朽”于后世的捷径之一,还是作者借之与同时之人交流并炫耀才识与谋取声誉的手段。
此期子书所体现的总结与垂范倾向,在曹丕《典论》中有集中体现。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14]1090侯芭从扬雄受其《玄》《言》,被时人视为怪异。曹丕却能在“诸儒”面前“侃侃无倦”地讲解《典论》“大义”,这个现象反映两个问题:其一,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浓厚的著书、品文之风,子书不再是次于经书之后的精神寄托,它已体面庄重地登堂入室。其二,曹丕不仅著书,而且讲书,其目的不仅在于为后世“立言”,也在指导与影响当世。著书立说成为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才可以理解他赐书孙权与张昭的郑重,和他在《典论·论文》中所云“文章经国之大业”并非夸言。《典论》有《论文》一篇,这是子书中第一次出现文论的专篇,对于包括子书在内的几种文体特点做了归纳,既有对于前人的总结亦体现其指导当世与垂范来者的自觉意识。它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更进一步开拓了子书内容涵盖的范围。
第二个特点是,此期子书作者的身份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不同。曹丕的皇室身份姑且不论,其他作者中除了少数几人事迹无考外,多为朝廷大臣,不仅官位不低,而且有的在政坛上还堪领一时风骚。曹魏的蒋济、桓范都是重要谋臣,孙吴的传世子书中也包括了诸葛恪等“太子四友”的著作。从其一生的主要阶段来看,政治上都算是得意的,而且其子书并非写于他们的人生失意之时(个别例外)。作者身份地位的变化,影响了他们对于子书创作的态度,进而影响其主题的选择。所以此时的子书内容少了些“不平之鸣”,多了些积极向上的辅政愿望和学术探讨的自觉追求。
此期子书的第三个特点是,自我服务性。曹丕《典论》所表现出的“自传性”倾向,使得子书成为一个全方位展示自己从政以外的才华与思想的载体,就是此期子书作者自我服务意识的典型代表。比如,《典论》中《终制》篇的设置,《太子》篇言自己作家书之踌躇,尤其是《自叙》篇中不厌其烦地言说自己对于骑射、击剑、弹棋之道的精通,更是他自我展示愿望的鲜明体现。《三国志·顾谭传》所云:“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难篇》,盖以自悼伤也。”[15]535虽然史学家的眼光还拘泥于司马迁时期的“发愤著书”,但实际上司马迁的思想早已被此时的子书作者游离与超越了,他们在著作中昂扬自信地走向了自我服务。子书创作由“公”向“私”转变了一次,至此再进一步,走向了“自我”。此时的某些子书类似于著作者个人历史的书写,更像是一篇放大了数十倍的“叙传”,不单单是哪一篇中能够寻觅到作者自我的身影。这一倾向也为萧绎所深刻认同并予以很好地继承,所以才会有《金楼子·序》中所言:“由年在志学,躬自搜纂,以为一家之言。”[8]1“一家之言”之说还是沿袭了司马迁的旧话,但其“私”想已今非昔比。
简述这个阶段子书的特点:第一、子书作者政治地位高端化;第二、子书创作进一步私人化;第三、子书中体现了作者对此前子书的总结与对后世的垂范意识相结合的愿望。
五、结语
汉魏子书四个阶段的划分或许不甚严谨,但于勾勒汉魏子书发展的渐进过程有所助益,子书概念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其创作的体式与规范成熟的过程也得到了很好的揭示。每个阶段的子书发展水平不是等齐匀速的,而且这一过程中也有曲折起伏,但总体趋势是发展与进步的。在对这一渐进过程进行勾勒时,我坚定了一个认识:对汉魏子书文本进行解读时,仅仅避免带着现代人的子书概念进行孤立地衡量与评判,或者把诸子放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去解读还不够,还应该把子书个体放置到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使汉魏子书的个案阅读与其整体发展过程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加接近汉魏子书的真实面貌,也才能保证所得结论相对公允。
[收稿日期]2011-07-10
标签:先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汉朝论文; 论语论文; 文化论文; 盐铁论论文; 论衡论文; 风俗通义论文; 新语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