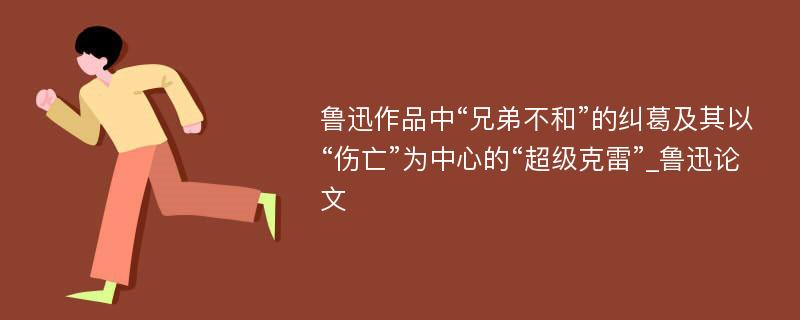
鲁迅作品中的“兄弟失和”纠结及其超克——以《伤逝》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兄弟论文,作品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鲁迅曾经遣佣人要求见面解释被拒,甚至搬走后返回八道湾企图取回自己的图书亦曾遭到周作人夫妇詈骂和羞辱,直至最后老死不相往来。毋庸讳言,兄弟失和对鲁迅的身心有着相当沉重的打击:咯血、生病既是一种隐喻,同时又是一种内伤的切实外显。由于二人相对默契的对此事件的真相近乎闭口不提也着墨不多,更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一大谜团。① 1925年10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罗马盲诗人喀都路斯(或卡图路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84 B.C.-54 B.C.)的一首诗,题目是《伤逝》,被译者视为悼念兄弟之情的作品,“我走进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大海,/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献给你一些祭品,/作最后的供献,/对你沉默的灰土,/作突然的话别,/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②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失和两年后的周作人的一次借故抒发情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无独有偶,1925年10月21日,9天后鲁迅完成了名作《伤逝》,但收入《彷徨》集子出版前却从未单篇发表过。耐人寻味的是,在绝大多数读者将之视为爱情小说的时候,多年以后周作人如此解读此篇小说,“《伤逝》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解的一篇。大概写得全是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根据。我深信:《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③毫无疑问,其中亦不乏争议:《伤逝》到底想要呈现一个怎样的内涵或指涉?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探寻可能亦有某种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的关怀。换言之,《伤逝》的指涉主题本身可能就是多元的,乃至是狂欢的。 不必多言,从“兄弟失和”开始的1923年到《伤逝》创作的1925年,其间有两年多的时间跨度,某种程度上说,“兄弟失和”事件已经成为名作家鲁迅的精神梦魇或心理阴影之一,为此,《伤逝》只是这种情结/纠结承载的核心篇章之一,因此实际上同时期的小说《孤独者》《弟兄》《离婚》等都与此主题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而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野草》中也不乏深深浅浅的纠结再现,简单而言,随手拈来,《风筝》自然是关联了兄弟神情和自我忏悔,《秋夜》中的两棵枣树可能也有对兄弟的纪念,《影的告别》也有自我分裂和对兄弟之情的感慨。如人所论,《野草》深受“从八道湾出走后产生的幽怨情绪与悲悯情怀的深刻影响,那种把几乎所有其中所有篇章都归结为爱情因素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鲁迅借助《野草》的创作,缓解了长达数年的内心紧张,平复了心灵创痛;因而无论从创作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鲁迅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④ 但无论是限于论述篇幅,还是避免论述涉及文本的过度化和粗疏化,本文毋宁更选择以《伤逝》为中心,而以其他有直接/精神关联的小说/散文文本为辅进行探勘,而非面面俱到。本文的问题意识如下:1.《伤逝》如何呈现兄弟失和?2.有关文本如何逸出这种纠结?3.借助于《伤逝》,鲁迅如何超克这种情结? 一、“兄弟失和”的要素及其逸出 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从《伤逝》中读出鲁迅对兄弟之情的哀悼主题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文本中间富含了备受打击的当事人的情感宣泄及其各种沉淀寄托,甚至也关联了不少显而易见的失和要因、元素和鲁迅的态度。但同时另一方面,周作人的过于简略和自信的评价亦可能简单化了鲁迅,即使单就“兄弟失和”纠结来说,鲁迅亦有其复杂深邃的一面,甚至有其独特逸出,值得论者仔细探究。 (一)情感创伤及其结构。某种意义上说,《伤逝》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兄弟失和”之后的情感创伤表征,比如孤独失落感、忏悔情结,甚至是轻微的报复心理;但同时鲁迅更借助其他文体/文本呈现出对这种结构的完善与深化,比如繁复曲折幽微的复仇情感。当然其中的指涉也因此更丰富而有可能超出《伤逝》的涵盖了。 1.孤独:自成风暴。毫无疑问,哪怕是普通读者都可以读出《伤逝》中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而且还包含着不同的层次、程度与方面,如子君和涓生同居后的孤家寡人、众叛亲离,“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而此后的涓生丢掉工作日益困顿,而二人之间有着更多真正的隔膜:比如子君的日益世俗化乃至物质化、平庸化。而涓生对子君的感觉也因此日益疏离,直至最后以“我已经不爱你了”戳破幻觉。这当然都有一种内外交困的孤独感。 毋庸讳言,描写鲁迅“兄弟失和”产生孤独感的小说不只是《伤逝》,也包括《孤独者》,如人所论,“只有充分认识到兄弟失和给鲁迅带来的创伤,才能理解鲁迅一生的愤激和敏感、偏执和痛苦、仇恨和报复、绝望和阴暗的心态,以及在这些心态之中体现出来的无以言表的愤怒和悲伤。周作人曾解读出《伤逝》里有鲁迅对兄弟失和的忏悔,意在表明‘兄对不住弟’,自己是无辜的,但他怎么就读不出《孤独者》里鲁迅遭受不公待遇时的悲愤与哀伤呢?恐怕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的隐藏与隐瞒吧。”⑤但在我看来,魏连殳(或背后的鲁迅影子)的孤独感投射至少包含了两大层面:一个是显而易见的新旧冲突所导致的主人公魏在“失败的成功”(坚守理想生活困顿但精神成功)与“成功的失败”哲学(放弃理想物质成功但精神溃败)之间的流转、纠结与自我毁灭,这是旧制度、伦理体制及其文化政治对魏的围剿;而另一个少为人关注的孤独感则是来自同行/同道“我”的屡屡不理解、误读,乃至见死不救(或无力挽救?)比如他们关于过继孩子话题的隔阂,明明是旧有的婚姻伦理制度借过继小孩收编魏连殳的精神、存在与物质财产,但“我”却质疑他道,“‘总而言之: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也是久已想问的话,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他诧异地看着我,过了一会,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髁上去了,于是就吸烟,没有回答。”但魏连殳一直引我为同道,直至他自己为谋生背叛了理想,貌似成功实则失败,他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已经无须同道挂念了,“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换言之,来自同道的无助、误解才是更令人倍觉痛楚的孤独体验和镌刻。 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写于同时期的《离婚》亦呈现出别致的孤独感:不太平凡具有“钩刀式的脚”的爱姑的折腾或许为了尊严而离婚,但骨子里依然呈现出对旧有伦理道德的依恋,甚至是对“小畜生”亦有一丝寄托(其中不乏对兄弟友谊的投射与唏嘘);而同时,作为一个内心不够丰富深邃乃至强大的农村妇女,他们同样亦有被不争气的懦弱的父兄们抛弃的孤独感。而有着直接关联的《弟兄》一文中,沛君在书桌边对病中的弟弟靖甫所做的昏昏的残梦(他要帮死去的靖甫处理丧事,同时也要安排琐屑的后事,“——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却还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权和极大的力。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劈过去……”)其实更像是借助潜意识断片对“兄弟怡怡”表面的洞穿与嘲讽——兄弟感情在面对现实责任分担与切割(比如帮助抚养小孩)时亦难免大打折扣,从此意义上说,孤独既是一种兄弟分裂之后的被动,更清醒反映出鲁迅对此经历的必然痛苦立场、命运与遭遇的深切体会与确认。 2.忏悔:纷至沓来。作为一个自省能力上佳、自我批判意识极强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兄弟失和”事件中的自我责任和可能错误有着强烈的忏悔精神,《伤逝》当然是一个绝佳的承载。涓生对子君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他也痛心疾首进行忏悔,尽管偶有可疑之处,但涓生的真诚和悔恨浓度溢于言表,这或许也可视为作者鲁迅的一种自剖。但同时,若细读文本,其中亦有一些玄机,“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这里对真实/不虚伪的慨叹自然有其深刻之处:一方面要坚守现代性的“诚与爱”哪怕真相残酷,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注意现代性中的冷酷性和即席负面效果。当然如果结合周氏兄弟失和事件,这同时也可视为鲁迅对兄弟失和不明真相/不可深究的叹惋。 有论者指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不是人们以及鲁迅自己所谈的经济原因,而是时代使然,性格使然,是鲁迅长子意识所造成,是他那大家庭美梦的破灭。从鲁迅兄弟的日记中可见,他们都不是节省的人。不能将他们兄弟失和的原因归咎于羽太信子。祸兮福兮,兄弟失和造成了鲁迅生活的改变,性格的变化。没有兄弟失和,也就没有人们现在见到的鲁迅。”⑥其实鲁迅自然没有放弃对自己性格缺陷乃至国民性的反省,比如《风筝》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此文含义丰富,当然可以解读为最显而易见的对儿童本性的尊重,但同时其中也借批判一己的错误及无可挽回的深度忏悔来悼念逝去的“兄弟怡怡”之情。显然此事中他和周作人都有责任,风筝意象也喻示了兄弟之情的藕断丝连,至少从鲁迅的层面看是如此。当然此文中的风筝有更繁复的内涵——风筝意象中其实也富含了多元角色,如作为心绪的风筝,并非爱情指涉,而更是不可排解的愁绪;作为意义的风筝,鲁迅在处理兄弟失和、天性本位时都与风筝勾连,而作为叙事的风筝层面,无论是回忆还是虚构都起到了较好的推进作用,但也不乏吊诡。⑦ 作为长子长孙长兄的鲁迅其实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一方面,他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让大家庭其乐融融,“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另一方面却又因为习惯而难免一种长兄如父的大家长心态,他和周作人的可能张力乃至冲突会因为后者的日益强大而增强,如果加上羽太信子等人的可能挑拨离间则极可能造成悲剧事件。如孙郁所言,“深知人文主义和个性价值的鲁迅,对中国古老的家庭结构,备尝其苦。这大概也正是他特有的地方。一方面残存着东方人古老的积习,另一方面却又清醒地意识到其顽固性与陈腐性,但又无能为力。”⑧而在小说《弟兄》中则反映出长兄内心处理家务的现实考量乃至私心,这又不能不说是鲁迅对此心态的另一种自剖乃至忏悔。 3.繁复的复仇。如前所述,“兄弟失和”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为此他孤独无依,同时也极其深切地反省与忏悔,然而在内心深处亦有一种浓郁的复仇情绪挥之不去,比如1924年9月24日,在一封给李秉中的信函中,鲁迅首次袒露“曾经想到自杀”的隐秘心迹,“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反映到创作中,这种心态纠结与释放可谓比比皆是,“《风筝》显示的是兄弟失和后,鲁迅想宽恕而无法消除怨恨的沉重心情。《颓败线的颤动》是鲁迅为了摆脱这种沉重心情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不得不以自我圣化、自我伟大化的方式,拓展胸怀,加强力量,与天地同流,化解汹涌的怨恨。《弟兄》的写作意味着鲁迅从兄弟失和的巨大阴影中解脱出来,从人的本性层面,获得了对周作人的一定程度的谅解与宽恕。”⑨ 无论是《伤逝》,还是同时期的《孤独者》中,鲁迅营造了一种压抑乃至自戕的氛围,一方面是深切的忏悔、自剖乃至自我折磨的魏连殳投降后的自毁心态,而另一方面他也将这种复仇指向了对方。《伤逝》中的涓生似乎很容易被女性读者道德化为冷酷无情乃至忘恩负义,这其中却有更繁复的指涉:一方面鲁迅借涓生之口指出了子君的逐步世俗平庸乃至堕落化倾向,这在相当险恶的旧环境中无异于自寻死路,但另一方面,涓生却又因此呈现出推卸责任的自私性,他也没有避免子君的平庸并帮助她不断自我提升,而是选择真实以及自保,这不能不说其中凝结了鲁迅幽微的复仇心理。换言之,如从“兄弟失和”角度阅读,当事人子君和涓生的指代是可以互换的,鲁迅的批判矛头同时双杀,这其实可以反映出鲁迅内心的纠结。 《颓败线的颤动》同样折射出这种心有不甘的复仇心理,一方面鲁迅呈现出老妇人年轻时维生的不易:耻辱、卖身但亦有隐秘的快感;另一方面,他又相当繁复地坚守了维生的真相与隐忍牺牲被指责和抛弃之后的反弹。这当然可以从宏阔角度解读为“展示出鲁迅内部世界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绥惠略夫式的‘个人主义’)激烈的纠葛”⑩,但也可以从微观上解读为鲁迅的一种复仇情结,其中既包含了对来自同一战壕忘恩负义者的斥责,又包含了对“颇昏”的周作人的不满——主动走出房子吐出无词的言语亦有对被周作人、羽太信子逐出八道湾大房子的影射。 当然更复杂的复仇情结还体现在他的两篇同名作《复仇》散文中,其中既有对看客(也包括兄弟失和看客们)的调戏、杀戮和报复,同时又有对自我牺牲的深切展示和细描(thick description)。其中当然可以做宏观/微观解读,但若关联“兄弟失和”事件,毋宁更是他的一种自虐、虐他(包括看客和昏聩的周作人)的复杂复仇心理投射。 (二)失和要因及其逸出。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之所以确认《伤逝》是悼念兄弟感情之作亦有其理由和支撑,而细读《伤逝》其实亦不乏要因呈现。 1.经济的压迫及反弹。如果单纯把《伤逝》看作是一篇爱情小说,显而易见破坏子君与涓生幸福的要素之一就是经济压力。用鲁迅的话说,“人必须生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不少论者往往从此入手,甚至误入了唯物质主义的歧途。其实从此角度讨论婚恋往往也是片面的,即使回到文本本身,鲁迅又写道,“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精神内涵、气质兼容、积极对话等等都是重要组成部分。有论者指出,“鲁迅并非要仅仅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故事只是隐喻的躯壳和载体,他要表达的仍是一个关于身体和精神的隐喻,表面上与疾病无关,却是更整体的更深入的病的隐喻。生病时,身体就必然成为精神的羁绊,而精神又不能脱离身体,一旦脱离就只能是虚空。执着于日用日常的子君成为身体的隐喻,而憧憬于新生的涓生则进行着精神的高蹈,这种高蹈却又必须归于身体,首先要活着,然后才能开辟新路。涓生对子君的疗救由成功而失败,但子君的实有却无处不在地制约着涓生。”(11)子君和涓生的关系变成了疾病隐喻视角之下被救治与纠缠的复杂关系。 在我看来,经济元素在《伤逝》中亦有复杂的对流与反转。子君的平庸、世俗、停滞不前乃至堕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她是以精神上的勇敢姿态开始(“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后逐步卷入了日常物质的羁绊,从涓生失业后陷入了生计困顿到与隔壁的小官太太相互攀比、钩心斗角,再到让一日三餐占据了二人世界乃至她自己所有的生活内容,直至最后离开时却留下了全部物质作结,“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在我看来,这个离开时的细腻奉献颇具悖论,她因为物质日常而琐碎不堪,最后却得以善终,以物质/经济成全了精神,实现了临死前的温馨反弹,“视爱情胜于生活的子君最后的确以实际行动捍卫了她的尊严、立场,也以金钱等生活方式表达出浓浓的爱意。”(12) 如果结合“兄弟失和”议题来看,《伤逝》中对经济/物质呈现出既重视又轻视的吊诡态度。换言之,可以做个假设,若子君、涓生物质丰裕,他们是否就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我想结论或许是,他们可以延迟分手,但似乎也必然走向分离。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虽然重要,但显然不是分手或兄弟失和的第一元素。《伤逝》中部分呈现出鲁迅对此元素的态度——成长的重要基础但绝非全部。周建人曾经把两位哥哥的失和归结于经济原因,尤其是羽太信子的大手大脚,力图掌握财权肆意处理让八道湾入不敷出、经济紧张(13),但坦白说,这依然只是一个重要元素或导火索,兄弟之间真正的精神隔膜或性格冲突才是主因。同样在其他文本中,如《颓败线的颤动》中,以出卖身体获得经济来源赡养全家被误读也投射了鲁迅对经济的态度——它既是临时救急救命的凭借,同时又该超越此物,更尊重和理解为此牺牲奉献背后的心灵与精神。 2.暧昧的身体/性。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传言中最沸沸扬扬的性骚扰在周作人认可的《伤逝》中却是相对暧昧,似乎只有那么一句,“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我们可以抽离“兄弟失和”事件,将之解读为对男权权力话语的揭露,“毫无疑问,鲁迅对子君爱情悲剧的思想写意,是对男权启蒙话语的调侃与否定——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男权启蒙话语的虚伪本质——‘自由’是男性世界的专属权利,而女性只能是男性精神狂欢的欲望对象。”(14)当然我们甚至可以借此批判鲁迅叙事中的男权视角或倾向,比如子君是一个被凝视(to be gazed)的对象,她的相对沉默、刻板化和鲁迅的刻画息息相关。 但若结合“兄弟失和”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伤逝》中的裂缝——如果当作是爱情小说来读,其间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尚可紧扣主题,而其间的性爱书写则显得仓促而粗糙——不仅分量很小,而且往往也无法呈现出年轻男女如何在内部激情结合以对抗外来压迫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鲁迅有意淡化了性爱的元素,而周作人则心照不宣,更自信这是悼念兄弟之情之作。换言之,在《伤逝》中,鲁迅有意暗示适合与所谓的性爱元素关联不大。而在“兄弟失和”之后的实际关系认知中,鲁迅对周作人除了“昏”的评价外,多数都是相当厚道的,兄弟之情和惺惺相惜依然存在,而将矛头更多指向了以性骚扰借口挑拨离间的羽太信子。 如果结合稍早创作的《颓败线的颤动》,其中的身体作为卖淫以谋生的主体恰恰也是繁复的、吊诡的:它既无奈(不得不出卖赚钱维生),又在被动中有一丝快感(毕竟它是年轻的,而侵入者孔武有力)。但若从更高的层面思考,即使有悖于伦理,但亦是无奈之下的举措,完全情有可原。鲁迅以老妇在广袤天地间发出无词言语的愤怒表达丰富情感:它既是一种宣示,又是一种复仇;既是一种悲怆,又是一种自怜。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兄弟失和”中性猜测和质疑的一种顺带回应。 二、意绪的狂欢与自我救治 某种程度上说,想对《伤逝》的主题进行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哪怕是一锤定音的解读都相当困难,这不仅是说既有的爱情、悼念兄弟之情等主题多元并存、众声喧哗,而且从其作为小说文体的结构设置自身考察也不乏裂缝和其他可能性。换言之,它并不强求书写主题的单一性,甚至是统一性,但却同时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有论者指出,“因为鲁迅意在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写出兄弟恩情断绝后内心难言的隐痛,叙事和抒情就是一体的,不可分的,叙事就是抒情,抒情也是叙事,这是事件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如果我们硬要分出实写是事,虚写是情,那么我们就永远跳不出《伤逝》是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和批判个性解放的思路,就永远要试图去寻找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而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鲁迅先生本意不在于此。”他还特别举例说明有关书写的刻意为之的断裂性,“以失业为契机,小说开始进入叙写兄弟恩情断绝后内心的真实境域中去,越来越不像一部恋爱小说,没有合理的原因,也没有详细交代,用一句‘然而觉得要来的事,却终于来到了。’来说明子君突然离去,并且反复强调说出真实是造成一切的原因。”(15) 毫无疑问,有关《伤逝》主题的探寻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也欢迎更多自成一格、自圆其说的更多探勘,比如有论者就认为《伤逝》的主题内核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并将其意蕴揭示过程分为终极意义的憧憬期、现实生活的品味期、凡俗人生的彻悟期、生命追求的抉择期等四个阶段。(16)而本文则从抒情性角度思考,更认为《伤逝》是鲁迅一种悲剧性意绪的狂欢抒发与自我救治/超克。因为更多是强调情绪的抒发,所以其中的抒情性大于叙事性,其情感的宣泄和包容性往往超越了严谨的中心结构营构,甚至因此焦点多元并存,而显示出全文的狂欢特征来,也因此会造成单一主题(即便很宏阔)观照下的狭隘性与可能的捉襟见肘。之前曾经有论者指出了鲁迅铺陈这种意绪的策略,比如语言的音乐性和结构的节奏感等等,“《伤逝》语言的音乐性,除通过语言的修饰和陌生化造成鲜明的节奏、音律外,还体现在作品叙事与抒情的顺序即作品的整体结构上。”(17)本文主要从空间转换与声音政治两个层面展开。 (一)空间转换及其隐喻。耐人寻味的是,《伤逝》中间存在着一种空间的转换,而其中亦有各自的隐喻,而实际上也因此可能造成普通读者和当事人周作人不同角度和立场的解读侧重及其差异性观点。 1.会馆与家:虚空与死亡。小说中主人公私奔和回归的起点/终点不大相同:于子君而言,是家。一般读者往往容易将子君看作是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续篇及个案实践,但其中也有细微的差异:相较而言,从寄居地(她叔子的家)出走/私奔,到最后不得不回到父亲那里去,子君的死似乎是一种宿命,而有关其“家”的书写却是相当含混而冷漠,无论如何都无法和同居地点——吉兆胡同的简单租房相比,这种无奈回归和子君必死的命运息息相关。 而涓生的寄居地——会馆,既是其起点也是其终点,但自始至终又呈现出一种客居的孤独与空虚。当然,若仔细追究起来,似乎又有质的差异:作为起点,会馆之于涓生是“寂静和空虚”的所在,但却因了爱情拥有期待,而涓生对子君的期冀却恰恰是拯救他逃出虚空的外在借助;但作为回归终点的会馆既有交叉又有差异,“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虚空是其交集,但却很难有新的期待了。周作人却从会馆的具体描写和回归的角色读出了鲁迅的实指与寄托,所以才可能把它看作是悼念兄弟之情的证据之一,如人所论,“鲁迅一生最寂寞的光阴,是他于绍兴县馆独住的日子”,但他和周作人在失和之前的友谊和神交却因此更加浓烈,“鲁迅一定程度上借助了二弟广阔的知识背景,二弟也发挥了哥哥张扬人道个性的长处,两人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之状,从文字中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18) 但若比较会馆和家的巨大差别,我们不难看出男性和女性在勇敢对抗旧习俗和伦理之后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于男性涓生而言,回到会馆并未产生本质的改变,无非是经过了一场事故之后的平静,最多不过是调试;而于女性子君而言,回家等同于赴死,这种主人公角色之间以及叙事之间的分裂乃至危机甚至也可视为是鲁迅自身思想中的危机、分裂与焦灼,“这两种解读方式的结合试图揭示的一个事实是:也许《伤逝》本文的分裂正来自鲁迅主体的分裂,本文危机正反映了鲁迅潜意识中自我意识的危机。”(19) 2.吉兆胡同:幸福与坟墓。吉兆胡同租房成为子君和涓生私奔之后的交集,但对于二人却也有差别:简单而言,对于子君来说,这往往意味着美好,但也可能变成了金丝笼子,她变成了忘记振翅高飞的囚鸟。但即使是到了分手的最后,这里依然是比家更温暖的所在,毕竟这里有爱人——其中既有子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命定性,同时又有视爱高于一切的简单与纯粹。 于涓生而言,吉兆胡同却有更繁复的内涵。第一阶段与子君有类似的感受:这是一个温暖而“暂时可以敷衍的处所”,其中既有饮食男女的甜蜜,但也暗含危机,比如经济危机,“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第二阶段则是“家”。日益变成了背负,尤其是令子君停止了更新,比如瞎忙以及养宠物之间的内斗,“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第三阶段,这里变成了一种束缚,即使贫困交加,却也无力安心做事。“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然而又加以阿随,加以油鸡们。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甚至变成了一直不敢直视的逃避,离开了通俗图书馆,“又须回到吉兆胡同,领略冰冷的颜色去了。”第四阶段,吉兆胡同已经变成了涓生的梦魇,“我要离开吉兆胡同,在这里是异样的空虚和寂寞。我想,只要离开这里,子君便如还在我的身边;至少,也如还在城中,有一天,将要出乎意料地访我,像住在会馆时候似的。”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丝无法实现的悲戚幻想。 3.周边及社会。《伤逝》中还有其他空间设置,比如工作环境、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它们其实往往就是扼杀子君涓生爱情的厚障壁。 第一个是涓生的工作地点——某局。正所谓人言可畏,而涓生失掉工作的核心原因就是局长儿子的赌友——雪花膏的告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这是断绝他们经济来源的黑手。 而第二个则是吉兆胡同租房中的主人房,尤其是和小官太太的明争暗斗。“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扼杀子君活力、更新能力的世俗环境与黑手。 第三个地点则是通俗图书馆。类似于“我的天堂”“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它既温暖了涓生的身体,又温暖和壮大了涓生的一颗逃避之心,“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但同样这个分手的真相却也致子君于死地,从此角度看,作为涓生逃避天堂的通俗图书馆却是谋杀子君及其爱情的预演地。 当然,上述空间的转换往往是并置的,毕竟它们都是来自于涓生的回忆拼贴或营构。如果要丰富化“空间”包含,除了实际的地点以外,我们也可把主人公涓生的思维空间置入,如人所论,“作家还借助章节并置达到冲淡因果关系的目的。《伤逝》的全部章节是由涓生零乱、无序的记忆片断组成。这种记忆片断之间缺乏起承转合的必然联系,桩桩件件的难忘事件之间是可重复、可调换,因而也是并置的。”(20)甚至还可以包含文本的叙事空间,但这些其实有另外的理论支撑,似乎不宜过于泛化。 (二)声音及其文化政治。另一个相对为人所忽略的视角就是《伤逝》中的声音书写及其文化政治内涵。(21)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可以做出如下总结阶段梳理: 1.期待与甜蜜。从声音的层面看,子君其实就是拯救涓生于“寂寞和空虚”的救赎者,“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有时候,不仅是期待,而且也是精神的碰撞与激荡,“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贴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而更令人感慨的是,在私奔伊始,子君所呈现出的勇敢与率性,“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儿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这个话语可谓掷地有声,变成了一个时代女性的强音。甚至他们爱情关系的确认亦有声音介入,“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当然子君和涓生的关系中也难免男权的权力话语,甚至也呈现出这种话语的虚弱和单薄,“子君只不过是涓生自己的镜像,她的空虚如明镜一般,映照出涓生及其所代表的五四知识青年以新的知识与思想作为华丽装扮的表演,映照出徒具形骸而毫无‘生’之可能蕴含其中的困窘人生。”(22)但无论如何,这种美好关系——甜蜜与交心也部分喻示了周氏兄弟之间曾经的浓情蜜意。 2.重复与隔膜。某种意义上说,从子君涓生二人关系伊始就夹杂了不和谐音,甚至是难以避免的隔膜,即使在甜蜜结合期亦然,“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而当涓生失业时,子君明显底气不足,甚至连涓生自己都觉得如此,“‘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声音的断裂可以反映出其色厉内荏。 而当他们关系出现明显裂痕时,声音也可告诉我们子君于恐惧之中的努力,“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难以呼吸。”甚至这种重复性也显示出涓生的无奈、隔膜与无谓咀嚼,“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 若跳出兄弟失和的视角,其实也可看出鲁迅对“五四”新文化的反省,新话语和内涵的割裂以及内涵自身的可能脆弱与虚空,“《伤逝》就是这样的一篇小说。它的人物形象、主题内容、叙述方式甚至情感基调都成为鲁迅对‘五四’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反省的表达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伤逝》是个隐喻性的文本。”(23) 3.沉默与懦弱。等到涓生发出真实的不爱说明后,子君的表现令人感伤,“我同时豫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这沉默其实意味着绝望、惊恐与无助。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她必死的前奏。 然而鲁迅更是残忍,甚至剥夺了她说话的权利,如离开时的无话可说,别人转述说,“没说什么。单是托我见你回来时告诉你,说她去了。”可谓坐实和延续了她的绝望感。等到最后,连她的死也只有靠代言和传说才得以确认,但沉默之中却有如许的不甘和挣扎,“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但实际上,真正的人生何尝不残酷呢?沉默也可能是最好的表述。如孙郁所言,“在人生苦海的面前,世俗的价值与理性是无力的。我于兄弟间由挚意到分手的故事,看到的更多是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残酷……当我们对己身与客体存在无法断言的时候,沉默或许是最好的表达罢,此外,还会有什么呢?”(24) 有论者指出,官太太指羽太信子,子君形象中有周作人的影子晃动,“鲁迅的《伤逝》是一篇运用美人象征手法创作的小说,而且是一篇深藏不露唯有作人明白的绝妙作品。其借男女情爱喻兄弟关系,巧妙而又隐晦地向弟弟周作人的悼念文章做了相应的回答。”(25)所论貌似有理,但同时又过于坐实。涓生和子君身上都凝聚着鲁迅的意绪——忏悔、抗议、牺牲、爱意等等不一而足。某种意义上说,政治这种情绪过于繁复、浓烈与多元,空间的不断转换与回归、声音到最后大音希声,都变成了一种对应的别致呈现。 “兄弟失和”事件对于鲁迅的人生和创作影响至深,实际上鲁迅在不少小说篇章和《野草》中都投射了相关纠结,《伤逝》也不例外。作为鲁迅少见的爱情小说,周作人却坚称它是悼念兄弟感情之作。在我看来,不无争议、不乏叙事裂缝颇有主题狂欢风格的《伤逝》包含了“兄弟失和”的元素、要因(如经济、身体性等)与情感抒发(如孤独、忏悔、复仇等),但又有独特逸出,而这些若结合鲁迅的其他创作则更清晰可辨。 企图另起炉灶或对《伤逝》的主题一锤定音是困难的,但借助其空间转换策略并考察其间的声音发展及其文化政治,我们不难发现里面更是散布了鲁迅的诸多意绪、人生感悟以及借此自我疗治的苦心,从此意义上说,《伤逝》是一个狂欢的文本,其主体既不单一,又不统一,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逸出性与独特魅力。而在李长之先生看来,“长于抒情”原本是鲁迅的特点之一,“在他的抒情的文字中,尤其是长于写寂寞的哀感,所以‘伤逝’这题材是再适合没有了,因而也就无怪乎是他的完整的艺术品之一了。”(26) ①具体可参葛涛主编:《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中的第五个谜,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②具体诗作及失和评述可参陈漱渝:《鲁迅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11章,第66-77页。 ③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④刘骥鹏:《郁结与释放——从作者的人生困境与心理语境中把握〈野草〉意蕴》,《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第31页。 ⑤王宗凡、徐续红:《“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从〈孤独者〉看“兄弟失和”对鲁迅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80页。 ⑥丁仕原:《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原因新探》,《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93页。 ⑥具体可参拙文《自解的吊诡:重读〈风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⑧(18)(24)孙都:《鲁迅与周作人》,现代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第80页,第133页。 ⑨张永辉:《劫波渡尽,恩仇难泯——鲁迅作品中的兄弟关系探微》,《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5期,第17页。 ⑩[日]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秦弓、孙丽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11)安文军:《病、爱、生计及其他——〈孤独者〉与〈伤逝〉的并置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6期,第55页。 (12)拙著《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13)具体可参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14)宋剑华、邹婧婧:《〈伤逝〉鲁迅对思想启蒙的困惑与反省》,《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第96页。 (15)谢菊《〈伤逝〉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1期,第59页。 (16)刘起、林易瑛:《〈伤逝〉主题内核: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06页。 (17)张忆:《情无尽,长歌音不绝——〈伤逝〉语言的音乐特质》,《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5期,第27页。 (19)汪卫东:《错综迷离的忏悔世界——〈伤逝〉重读》,《鲁迅研究月刊》199年第10期,第36页。 (20)马丽蓉:《在空间维度上叙述——〈伤逝〉新解》,《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第62页。 (21)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的著述《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值得参考,虽然他更多是从噪音和音乐的视角加以论证,但声音在现代政治中的独特作用、私人领地和公共生活的交叠以及其中的意识形态元素值得认真关注。此处更偏重声音政治的性别内涵。 (22)刘堃:《写实主义的边界:重新解读〈伤逝〉中的性别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9期,第29页。 (23)胡群慧:《论〈伤逝〉文本对五四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反省的隐喻性》,《松辽学刊》2002年第2期,第21页。 (25)庄小虎:《从〈九歌〉到〈伤逝〉——试析中国文学的美人象征手法》,《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5-16页。 (26)李长之:《鲁迅批判》,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9页。标签:鲁迅论文; 伤逝论文; 风筝论文; 周作人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颓败线的颤动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野草论文; 孤独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