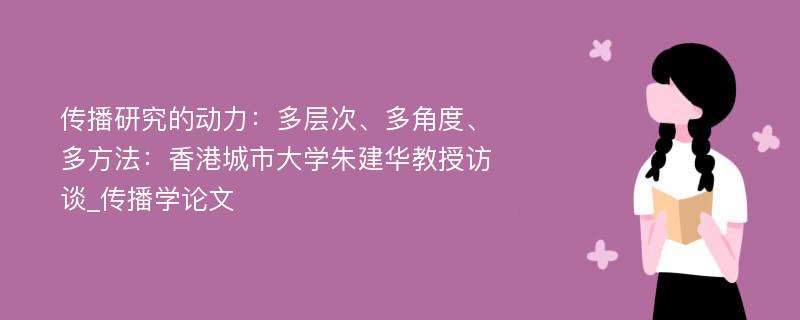
传播学研究的动力: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香港论文,多角度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访谈对象:祝建华,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学系教授
访问者:丰帆、周萃,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生
访谈时间:2004年11月1日,2005年3月6日
访谈地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问:祝教授,您长期从事实证研究,先后在中国内地、美国和香港三地做了20多年的实证研究,能否谈谈你是如何开始做实证研究的?
答:说来话长。1980年春,那时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二年级,与三位同学去《常州报》实习。在编辑部一次讨论报纸改版的会议上,我们提出为报社做一次读者调查。建议被采纳后,我们制作了一个简单的问卷,四个人分头跟着送报的邮递员逐家发。收回以后,我们靠最原始的画“正”字的方式统计了数据(当时哪有电脑)。一个星期后的第二次编辑会议上作了调查结果的报告,其中有些即被采纳到该报的改革中,从此喜欢上实证研究。当时之所以会想到这种方法,主要是它比较新颖,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而当时复旦大学进行学生会选举时,会进行一些简单的民意测验、统计候选人票数什么的,我也参与过。
问: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那一次看似粗糙的临摹之作却成为您从事实证研究的动力和起点,并且一做就是20年。
答:确实是这样。创新是必要的,但科学更讲究累积。所以我主张,学生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可以适当模仿传播学上的经典案例做些研究,以积累研究的感性经验,然后再接受系统训练时就学得进去、学得深入了。我真正开始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当时我参与翻译了由导师陈韵昭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由于当时国内出版的传播学方面的书籍很少,我们对该书涉及大量实证研究的背景、术语等所知甚少。为了力求准确,我就只得求助于复旦新闻系资料室所藏的英文学术期刊(如《舆论季刊》、《新闻学季刊》等,很全),同时还在复旦应用数学系选修了一年的概率论与统计学,还跑到上海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学习了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翻译完成后,我也有了一个额外的收获:不仅仅是对该书的翻译能够做到准确和深入浅出,对于美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经典案例也比较熟悉了,以后自己再做实证研究时,觉得有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之效。
比如那几年我做的“上海居民闲暇时间分配和媒介使用”等几项调查,从抽样设计、问卷设计、实时操作、统计分析等技术性的环节来看,比起以前的调查也精确、严格了不少。从这些经验中我进一步体验到实证研究的科学是讲究积累的。有些理论如果只是说说而已,没有通过验证,这里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可被证伪性:其论点既不可被证明也不可被证伪。这样一来也就谈不上什么科学的积累与继承。
问:您在《受众研究20年》(祝建华,2001年)一文中提到,1986年秋,您去美国读大众传播学博士,能否简单说一下那段时间的生活与研究情况呢?
答:好的。我是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招收的第一批两名博士生之一(另一位是我以后的长期合作者和现在的同事何舟博士)。实际还在国内时,我已经为博士毕业论文准备了相当多的数据资料。最初的选题借鉴了传播学上的一个有关教育程度与收看电视之关系的经典案例。当我的美国导师了解到这个选题时、特别是看到我对SPSS-X(当时的最新版本)玩得比他们还熟时,十分诧异,问我这些都是从何得来的。因为在那时的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是未开化的原始人。所以,有时我在研究方面获得小小的成功时,我总会告诉自己,这首先得益于复旦在物质并不丰富的时代给我提供的条件和空间。
当然在读博士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敢懈怠。印第安纳大学规定博士生必须要在博士论文之外修满25门课,即完成75个学分。出于完成学分的考虑,同时也是兴趣所至,我在4年中修了6门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的课程。这些对我以后的教学和研究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问:在您移居海外的近二十年中,传播学研究方法又有怎样的发展呢?
答:大家知道,研究方法有两种取向:一是定性或称质化的研究,二是定量的即经典的实证研究。前者主要包括文化研究,还有历史研究、政策或机构研究等。其中以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为主。在这段时间里,传媒事业越来越发达,传播学的教育也在不断扩展。我在到了美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美国研究大众传播的主要学会之一)。拿当时的会员人数和现在相比,大致只是今天的一半。而其中新增加的成员中从事质化研究的人占了较大比重。比如说本来是2000人,其中有80%的人是作经典研究的;现在有4000人,其中3000人在做经验研究,质化研究有1000人,那么按绝对人数来说,后者的增长速度肯定比经验研究的速度要快。
有人曾对传播学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所用的研究方法做过内容分析,即统计有多少人用定量方法,又有多少人是做定性方法的,在这些方法中又用了哪些具体的统计技术等。结果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做定量方法的比例在90%以上,而在90年代以来则减少到大概在70%~80%。
与此同时,文化研究方面的杂志也越来越多。因为像刚才提到的被统计的核心期刊都是比较经典和保守的,质化研究的文章就很少有机会刊登。这样一来,搞文化研究的人就自己办期刊,当然这类书籍就更多了。因书和期刊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是非营利的,主要是靠学会支持的,像那几本核心期刊,如《传播学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除了《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之外,其余都是各个学会的官方期刊,主要由会员费所支持。而书会受到更多的如市场等商业因素的影响。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表明文化研究是有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文化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像在美国的文化研究学者、学生中,主要还不是来自传播学的。而对于我们做实证研究的来说,写书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们的实证研究论文充满技术细节、本身可读性不强,读者市场不大;另外实证研究本身要求发表的速度要快,所以期刊是最合适的渠道。
问:那在您看来,目前的实证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或是面临着哪些困难?
答:我想,这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现有研究方法所能回答的理论问题相当有限。大众传播的一些经典研究,往往不是靠一次调查或是某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就能得出结论的。像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就是将内容分析和调查研究的巧妙结合,而知识沟理论则建筑在历史数据的分析之上,可称之为追踪研究方法的运用。传播学的发展、突破的动力大多来自于普遍地使用这些方法,这些方法的意义就是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
其次是与学术训练有关。我在美国读博士时,除了必修的两门研究方法(入门和高级)和一门统计学之外,还在其他系选修了三门方法或统计的课(还旁听了好几门类似的课)。如其中有两门是动态分析(dynamic analysis),一门是社会学教授教的、另一门是政治系教授教的,内容完全不同,因为两者均是以建立各自学科中的理论模型为主、统计分析为副,我得益不少,深深体会到理论对方法的依靠和方法对理论的贡献。但是即使如此,在后来的研究和调查中,我还是觉得在学校里所学到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又不断地自学。相比之下,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给研究生开设的有关课程只有两门,这样的学术训练当然是不够的。
最后有关经费。这是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像做跨文化比较研究需要几个国家的数据。尤其是需要根据理论的要求来选择国家,而非“拿到篮子里就是菜”;做追踪研究需要多年的数据;做多层面分析,则抽样的设计也比较复杂,这样一来,成本也就高了。传播研究的经费虽然比起有些人文或社会学科要多一点,但要做如此庞大或复杂的研究还是力不从心。
问:目前国际传播界有哪些比较前沿的研究方法,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么?
答:最近我在深圳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提到了四种较前沿的方法。一是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参见Wimmer and Dominick,2003清华版)。其实这种方法并不新,拉扎斯菲尔德在做选举研究时,就用到了这个方法,由此而发现了如二级传播、意见领袖等理论概念。不过这种方法要求成本较高,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二是(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这也不算新的。从传播研究刚刚开始,就有人拿几个国家的文化现象作比较。而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比较”方法的价值。不过它的成本也较高。同时使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许多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学成归国以后,将其在美国读到的经典案例(尤其是自己导师做的)与本国的相比较。这就很容易产生一个“为了比较而比较”的问题。
问:那么,“为比较而比较”会带来哪些后果呢?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切身体会呢?
答:简单地说,“为比较而比较”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所比较的国家之间不一定有可比性。如前面提到的有些留学生将美国与阿尔及利亚,或是法国同肯尼亚进行比较,可比吗?其二,比较的是国家和国家的差别而不是变量的关系。当研究者在做受众研究时,虽然(通过随机或非随机的方法)抽到张三、李四、王五、马六,但大家都很清楚他们并不是对这些个人感兴趣,而是对造成这些个人之间差别的变量感兴趣。然而,当研究者从个人层面的研究抽象到跨文化比较时,却忘了在这个层面上国家或社会仅仅是个体而非变量。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流于简单、肤浅的描述,自然难以抽象到理论高度,毋论其理论的推广之。
我与几位合作者在1997年做了一项理论导向的比较研究(Zhu et al.,1997)。我们比较中国大陆、台湾、美国三地记者对媒体的社会功能的认知,提出了一种新的比较框架,不是用来比较这三个国家或地区,而是用来检验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两者之间对记者认知的影响谁大谁小(最后实证研究发现是前者影响大大超过后者)。这样,一个“2X2”的理论框架(其中涉及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两个层面;而每一层面又分两种情况)就呼之欲出了。我们最近在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时,也采用了这种比较框架,比较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网民上网时间对其社会交往的影响(Lee and Zhu,2002),也颇为成功。
问:您刚才为我们介绍了前两种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的学习和研究都很有启发。能否继续介绍后两种方法呢?
答:好的。多层面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这是一种研究个体和集体不同层面的变量对个体行为影响的专门技术。个体当然一般是指受众个人,而集体则可大可小,从家庭、公司到社区、国家。多层面研究的重点是强调集体层面对个人层面的影响。1997年我与香港城市大学市场学系的两位同事在研究中国内地企业所有制对消费行为和媒体使用的影响时,就采用了多层面分析。我们在九个省会城市(分别代表“高”、“中”、“低”三种发展水平)中随机抽出45个国有企业、45个集体企业、45个股份制企业、45个三资企业,再各自从中抽出20名员工,这样就可以考察不同所有制下的个人消费行为和使用媒体行为规律。
这种分析方法与媒体依赖理论是相通的。如人对IT的依赖,表面上是人对技术的依赖。但依据媒体依赖理论,实际上是IT产业与政府勾结的结果,是微软和Intel两大巨头的合谋:微软不断开发新版本,这就要求用户升级硬件,所以Intel开发的CPU从奔三奔四,IBM推出64bit的处理器。像这种分析就是多层面地分析,并非是针对微软,而是说个人行为不是那么自由随意,社会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种方法在其他社会学科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不过用于传播学却是最近三五年的事情(如Shah,McLeod,and Yoon,2001)。
而关于复合分析,英文名为Holistic Analysis,与前面提到的三种研究方法不同。它并没有某种具体的数据搜集和统计方法,而只是一种松散的研究取向或是认识论(所以译成“拼合分析”可能更确切)。这种方法不拘泥于内容分析、问卷调查、控制实验或是深度访谈其中某一种方法的使用,而是强调多因素的考虑、多方法的结合。在海外,复合分析已被提出了多年,只是很少正式被用于传播学的研究。创立媒体依赖理论的Ball-Rokeach用的方法基本上可算是复合方法。上面我讲到其理论与多层面研究有相通之处。但她与其学生们在验证媒体依赖理论以及最近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传播机体理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见2004年第2期《国际新闻界》)时用的方法,却是较为松散的复合分析而非更严谨的多层面分析。
另外要提一下的是近年来开始流行的媒体生态学,也可以看作是复合分析的一种(当然,其更多的是理论框架而非分析方法)。所有研究都要解决三个W问题:做什么(what),为什么(why)和如何做(how)。我觉得媒体生态学的很多文章只解决了前二者,对于how却未曾触及。做出来的东西也类似于“系统论”,系统论研究计算机是成功的,但引入社会科学是失败的。这样的研究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即“媒体是一个大的生态,各种因素都在这个生态里面”,“要以整体的眼光来看”等等,这些说法是不无道理的,但失去了可操作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张首先从人的闲暇时间分配入手。在某种程度上,时间的生态是最大的生态,某个人对于闲暇时间的安排往往可以折射出传播学中所要解决的很多问题。我们可以挖掘不同选择背后的原因,一步步地向上追溯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媒体生态”。
问:您在《20年》一文中谈到“精确化只是科学化的一个充分条件。科学的必要条件是理论化”,您在给我们做讲座时也反复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作为一位在方法研究方面颇有心得的学者,您是如何看待方法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的?
答:相对说来,传播学是个小学科,没有必要进行独立的方法研究;另一方面,同其他相对成熟的社会学科相比,传播学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其方法研究不成系统,缺乏共识。在实际工作中,方法问题和理论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方法是为理论服务的,理论的发展是主产品而方法的改进是副产品。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单纯追求方法的“精密”或“新奇”,这也是有些学者将某些实证研究斥之为“幼稚的”、“玩弄数字游戏”的原因。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不懂方法的理论家是难以有所成就的“空头理论家”——像麦克鲁汉这样天马行空而又有理论贡献的天才毕竟罕见。首先,一个理论在被大家接受之前,就需要一套方法来验证;其次,许多理论概念的形成与深化需要有合适的方法作为思维工具。传播学史上的一些经典理论,其实都是对前人早已有所领悟的观念或比喻用实证方法进行科学推理和验证的结果,如“议题设置”、“知识沟”、“沉默的螺旋”、“第三者效果”等等,都是如此。这些理论当初都是一些易懂能记的比喻。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它们只有在一套严密的程序方法的支持下,才能发展为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反之,再生动的比喻充其量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另外,科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有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如概念能够被操作、测定和证实(其实是证伪)。有时,通过操作、测定和验证的过程,可能会发现某些理论(其实仅仅是描述性的)存在漏洞。
如“数码沟”就是一个例子。当美国商业部于1995年第一次提出“数码沟”这一名词时,立即引发了全美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与讨论,有关“数码沟”的定义也是林林总总,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将数码沟等同于互联网普及率。然而,当我2001年研究香港和中国内地互联网使用时,想找一个测量数码沟的指标来比较两者的状况时,居然找不到一个。于是我就自己设计一个祝氏数码沟指标(Digital Divide Index,祝建华,2002)。由于我的理论与方法的训练,这也不是难事。根据这个指标,我发现香港的数码沟最大、中国内地其次、美国最小,从而说明数码沟的大小与互联网的普及并无关系。其实香港、中国内地和美国数码沟的大小与这三地的基尼指数(反映社会贫富差别)高低的排序一致,这就从操作层面上证实了数码沟实际上是社会贫富差别在媒体信息资源占有上的反映。这个例子说明理论问题的澄清和解决通常是以科学方法为前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