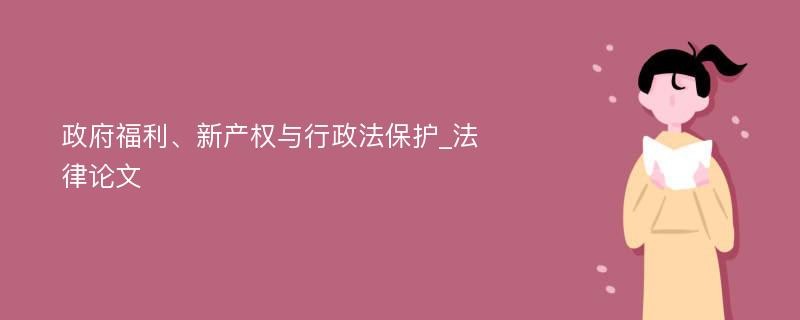
政府福利、新财产权与行政法的保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产权论文,行政法论文,福利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保障私有财产权不受政府或者其他国家机关侵害一直都是宪法与行政法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在近代,私有财产权的范围较窄,主要包括了财产法或者民法通常定义的不动产、动产和金钱或证券。而社会福利、政府职位与特许经营权等具有现代财产意义的权利均被认为是政府授予的特权(privilege)与恩赐(bestow),而非个人享有的财产权利,因此在任何时候,政府无需经过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法律程序,即可以没收或撤销这些特权。①此种状况直到1970年代才初步得到改善,如美国当时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②出现了一系列著名的判例。③这种变化与政府理念、④私有财产权保障及其限制的方式等是紧密关联的,⑤系对现代社会变迁在财产权保障范围上的回应,行政法应如何关注并予以制度架构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课题。本文拟以美国为例,介绍其学界、实务界对“新财产权”概念的阐释与应用,分析其行政法保护的具体措施,并指出可能为中国所借鉴的成分。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整理与思考,尚有待进一步结合中国具体的行政法制度进行分析并系统建构。
二、公法形态下的新财产权
作为一个古典的法律概念,“财产”或“财产权”(property)长期被视为是民法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强调其为私权利,应由意思自治主导的私法调整,而尽可能地禁止公权力对其干涉。⑥但随着人类生存形态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逐渐转变到商业(市场)社会,通过私人合意以及国家的积极介入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新财产”(new property),导致财产问题的研究也渐渐进入到了公法领域。在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宪法与行政法学界关于财产权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了一种“繁荣”的景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然也与2004年修宪以及物权法制定、颁布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巩献田事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⑦而民法学者的研究则另辟蹊径,开始探讨当代财产权的公法、私法性质的定位,⑧认为在现代和当代,随着“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现象的出现,财产权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私权,传统大陆法系关于公法、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也产生了根本的动摇。与此相对应,英美法系财产权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因此研究当代财产权的公私法性质定位成为当代财产权体系构建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但事实上这种超越公、私法体系的定位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本文中提到的“新财产权”。它们可能长期被排除在传统财产权体系之外,以生产企业的排污权与特种经营许可权为例,这两种权利仍不失为市场主体享有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再如福利权,有大量的个人及家庭在依靠政府给付生活着,显然也成为他们的重要权利。⑨“新财产权”理论无疑为我们整合财产权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一般认为系统阐释“新财产权”的理论首见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Reich教授在《耶鲁法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之中,⑩他认为财产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土地、动产、钱财,同时还包括了社会福利、公共职位、经营许可等传统“政府馈赠”(government largess),(11)这些“馈赠”一旦变成了个人的“权利”,那么就应受到宪法个人财产权保障条款的保护,对它们的剥夺就受到“正当程序”和“公正补偿”的严格限制。以职业许可为例,最初尽管少数高级职称如律师、医生或建筑师的营业执照被视为某种有价值的个人权利,但其他诸多较低层次的职业,如销售烟酒、开办饭店酒吧等营业执照便不具备程序保护。依照Reich教授的观点这些较低层次的职业许可也应受到程序性的保护。(12)197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基于福利社会的“新财产”概念,极大扩充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之所以如此,根据Reich的分析认为,现代社会之下政府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主要包括:薪水与福利、职业许可、专营许可、政府合同、补贴、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劳务等。这些财产是现代社会重要的财产形态,对这些财产的分配是通过公法实现的,而不是私法,其对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3)基于此,各种形式的政府赠与物应被看作一种“新的财产”,因而应给予适当的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他同时主张通过宪法控制、实体法限制、程序法保障等方式保障此类财产分配的公正。
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公共权力是财产概念变迁的最大推动力。”“由不同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正在对财产进行重新定义”。(14)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行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职能与权力的相对扩张,政府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基础,积极介入到市民社会之中,而且总是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到财产的价值甚至财产的创造过程中去。例如,政府可以发放巨额的金钱、产品、服务直接增加私人财富,也可以以颁发执照、证件、以及授予特许权等方式增加公民的财富。(15)因此,Reich教授指出,“新财产权”理论是在组织社会之下对于个人价值的充分保障的可行性体系,(16)体现了个人与组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必要借用财产权保护的有效手段控制行政机关的权力滥用。此外,“新财产权”理论重点关注的是政府与权利持有者之间的关系,而非私有财产与其持有者之间的关系。(17)因而也促使人们去考察政府可以产生哪些利益,如何保护权利持有者的合法利益,这对于行政法制建设水准的提升是有益的。不过,根据Reich自己的分析,自其关注这一课题的二十五年来,新财产不断增长,授予的方式也不断开放,当然其间的腐败丑闻也不断发生,而政府也不断通过新财产来控制个人行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但总的来说,这一理论,重构了财产的内涵,对法律制度特别是宪法、行政法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18)
对于Reich教授在此领域的贡献,许多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但也存在反对的声音,如使用新财产或新财产权这一概念是否有益于、适合于讨论这类非传统的利益?如基于政治理由对职业许可的撤回可以适用公民自由来分析而用不着引进所谓的“财产”概念。还有学者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财产权”。(20)对于上述意见,Reich教授的回应是有一些政府福利可能仍然需要这一概念来分析,其与传统的财产无法进行关联,而其又是当今社会人们追求安全与独立的重要基础。(21)他一再强调新财产权对个人的保护如同传统财产权所期望的一样。
有关“新财产权”理论的论争必须提到两位重要的学者。一位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R.J.Pierce,1996年他撰文指出引发正当程序革命的“新财产权”理论消弭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使个人丧失了责任感并产生对政府的依赖,这就违背了制宪者设立“正当程序”条款的初衷;此外,“新财产权”导致了民众对政府过度的权利要求,也给政府增加了难以承受的重负,所以他主张取消“新财产权”这一概念。(22)另一位学者是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C.R.Farina,1998年撰文反驳Pierce教授的观点并为Reich教授进行了辩护,(23)他指出创立“新财产权”理论并非是为了模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而是为了巩固个人在现代行政国家中的独立地位。在走向行政国家的进程中,政府的给付应当发挥(旧有的)财产权的作用,在业已模糊的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确立一条中间地带,成为个人独立的保障。为此,执照、许可、赠与以及其他从规制政府中得到的利益,都应当被重新解释为“权利”或者“公共财富中的个人投资”,并伴之以实质性与程序性的宪法与行政法保护。
三、政府福利的范围与保障面临的困境
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当事人必须有与其生命、自由和财产密切相关的利益,且该利益正受到政府行政行为的影响。美国在适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初期,正当法律程序所保护的利益是由权利法案规定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引致而来的。但公民具体哪些权利属于此三种形式,进而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则完全由法官裁量。于是判例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也即权利、特权二分法,(24)其核心意旨在于只有权利(right)而不是特权(privilege)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既然特权源于政府,政府当然可以任意取消,不受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限制。(25)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权利定义为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例如金钱、房屋、从事特定行业的执照等,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26)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因而不可剥夺,也只有权利才能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换言之,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是公民的宪法权利而非政府赋予的利益即特权。特权是指包括财产性质的、由政府给予的利益如社会保障和福利津贴、退休金和政府部门、公共教育机构的职位、名誉、政府合同、工商企业和科研活动补助、使用公共资源、服务等。显然社会保障问题并不属于正当法律程序保护范围,如1966年法院可以福利受领者没有“权利”而驳回任何一件相关案件,(27)其声称特权“可以任意撤销,其不受正当程序条款保护。”(28)
美国最高法院对“财产”的这一简单切割把公民大量“特权”背后的利益弃诸于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外,(29)Reich教授列举过这种“特权”所涵盖的广阔范围有:1.社会保障收入和福利津贴(income and benefits),例如社会福利津贴,失业津贴,抚育儿童补助,退伍军人补助,各州及地方所举办的福利事业等;2.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职位(jobs);3.职业许可(occupational licenses);(30)4.特许(franchises);5.政府合同(contracts);6.工商企业和科研活动补助(subsidies);7.免费或者减价使用包括公有的水力、矿藏、森林、牧场、道路、河流、原子能、技术诀窍在内的公共资源(use of public resources)。8.服务(services),政府所提供的大量服务,例如邮政、教育、新闻报道、消防设施、公共交通,构成私人利益必不可少部分。私人在自由方面的特权主要有外国人的入境利益、犯人的赦免、减刑、假释、缓刑、监狱对犯人的公平管理等各种利益。(31)可见,“特权”理论为行政权逃避司法控制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以致在20世纪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无法在上述诸多领域里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实现司法控制。
“新财产权”理论的提出以及正当程序革命之后,人们很少使用“特权”、“恩赐”或“馈赠”一类的词语来概括这类新的财产的范围,而是使用了“政府福利”(government benefits)“来描述福利较为宽广的范围,其包括了福利与社会保障、公共职位与政府合同以及职业许可或建筑执照”。(32)1970年代之前,这些政府福利保障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出于任何理由撤销政府福利,受领者对诸如政府职位或福利仅具有“特权”而不享有权利,其因此也超出了正当程序的范围。就像Holmes法官著名的断言一样:一个人“享有宪法权利可以谈论政治,但他无成为警察的宪法权利”。(33)如Bailey v.Richardson案件一样,(34)该案中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拒绝了一位政府职员主张他未经听证就被总统免职违背正当程序,法官明确地指出:“正当程序条款不适用于对政府职位的保持。”(35)当然困境也与这一时期正当程序理念的探讨缺乏精确度有关,如联邦最高法院在Flemming v.Nestor案中明确指出不需要用财产权来激发正当程序,(36)认为社会保障福利并不是“授予”的权利,因而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该法(社会保障法——引者注)之下的个人在福利支付中没有这样的权利,其将使每个‘附随’的利益作废而违反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37)低级法院则认为福利是“附随的财产权”,其终止侵害了正当程序,但其并没有就如何适用正当程序作出说明。
四、对政府福利的行政法保护
对于“新财产权”理论回应最为积极的正是行政法领域。(38)当然,学界的建议也极富建设性,如Reich教授建议从宪法、实体法、程序法等几个层面对这些政府福利进行保护。他认为必须要为个人划定一个私人空间,此时政府与其他权力均不得进入。(39)其他的学者认为要对基于财富分配的政府权力的增长设定一定的界限,否则就会形成过剩的行政国家。(40)而实体法方面的限制则包括了这样三个原则:第一,相关性原则。“实际上,在规制方面的任何事务都与一些正当立法目的是相关的,这一点已被证明是可能的。”(41)此处强调的是立法政策与行政手段要与所规制的事务相关,以避免对政府福利的规制成为对别的所有事情的规制。正如一位法官所言:“据我所知,个人的政治信仰,并不会使他不能安全有效地修复骨折或切除阑尾。一位执业的外科医生,在他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不可能发现太多的国家秘密。”(42)第二,明确性原则。学者们认为被授予的制定规则的权力,要尽可能有明确的界限,规制机构不得被分配执行相互冲突的政策的任务。尤其是对于裁量权的限制成为本原则探讨的重要内容,对此,甚至有议员曾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官员撤销政府合同和相对人投标的权利,以迫使未来的合同方履行或不履行时,他并无任何法律特权。(43)第三,排私性原则。即不得将制定政策的权力交给实质上属于私人的组织,显然这并不排除供给方面行业协会或私人组织的广泛参与。同时,他指出实体限制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程序限制应受到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即所有政府馈赠的授予、拒绝、撤销与管理,均应遵守公正的程序。(44)程序法方面的限制,实质是学者们在依照西方国家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及发展,保障政府福利非经正当的程序和适当的补偿,是不能任意被剥夺的。
行政法保护的具体措施就是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条款在政府福利领域的广泛适用。(45)1970年发生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以后至今的30多年间,正当程序适用范围以及加强正当程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保障力度的趋势不断得到扩大,当然其间主张抑制正当程序的呼声也时常发生。(46)Goldberg v.Kelly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福利是财产,对其终止适用正当程序。(47)在Board of Regents of State Colleges Et.a1.v.Roth案中,坚持了同样的做法。(48)但1974年在Arnett v.Kennedy案中,(49)大法官Rehnquist指出:政府有权决定是否给予行政相对人福利,那么它也有权决定福利的范围和终止福利。法院不应当强迫政府按法院认为的适当程序来授予或终止福利,“作为当事人的被告应该苦乐并享”。(50)这样的反复不明,说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反思历程及对立法或行政机关的尊重,如法院认为制定法有时也会满足正当程序的。(51)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本质,本质在于行政程序及其规制的行政案件类型上。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又在Mathews v.Eldridge案中对正当程序的判断标准进行了论述,(52)提出了所谓的三阶利益衡量标准,来判断对财产剥夺时所使用的程序是否是“正当”的,其中:
X=可能受到政府行为所影响的私人利益
Y=利益在程序中被错误地剥夺的风险,以及因任何额外或替代程序所产生的利益
Z=政府的利益,包括因为额外或替代的程序所带来的财政或行政负担
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分析时,如果X+Y>Z,那么目前所提供的程序保障是不足的,替代性的程序保障应被采纳,方能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相反地,X+Y<Z,则表示如果采用较为周全的程序,所获的权利保障利益低于政府的成本,因而现行的程序保障已能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也就是说现行的程序已经够“正当”了。利益衡量的精髓是成本与利益分析,是一种奉行经济理性的决策模式,在此模式下,法律程序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就在于其正面的作用大于负面的作用。利益衡量模式的优点在于使正当法律程序这个模糊的概念变得明确且易于操作,由法院所列举的三要素可以发现,法院所关心的重点是以行政行为的正确性为前提的相关利益衡量,其对正当程序所关心的重点是各方的利益,这说明了人们对程序要求的基本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判断者逐渐意识到了聚焦某一种价值或某一方利益的谬误。目前,美国在社会保障程序方面就已经构建了相当精细的规定或判例,如听证制度,会结合具体事项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类型的听证形式(事前的或事后的听证、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听证),(53)譬如在Mackey v.Montrym案,法院认为因驾驶人拒绝接受呼气酒测,而吊扣其驾驶执照,仅需事后听证即可;(54)在Memphis Light,Gas and Water Division v.Craft案,法院则认为政府所有的公用事业,于终止其客户提供服务前,必须履行正当程序,即应予通知以及终止前的听证,但此听证不必是对抗型的听证,而为非正式的听证。(55)这些经验对于中国构建相应的制度将是有益的。
不过由于正当程序理念本身的不精确性,导致了行政法对政府福利保护也存在不充分的情景,但无论怎样,由于美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相互制衡,(56)相信其所期望的与现实终将达成一致。
五、中国可资借鉴的成分
美国学者之所以提出“新财产权”,其良苦用心在于可以借助传统财产权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尊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权至少在近两个世纪是作为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界限的最典型的例证,财产权划定了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合法范围的界限。近现代学者正是基于个人与政府的对立自然而然地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57)但从另一个层面考量“新财产权”理论似乎恰恰为政府直接侵入财产权或自由提供了“隐藏式的理由”(这是一种由政府直接界定和给予的财产权,而不仅仅是提供一种外在保护的传统财产权,可能导致“大政府”的产生),因而不由我们时常保持警惕之心。(58)那么,中国的情景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能够从中汲取到所需要的养料来充实自己的法律体系呢,是否能够借鉴该理论为个人财产权(无论旧与新)的保护建立足够的行政法保障机制呢?这是大家所真正关注的课题,也是比较法的意蕴。
首先,“新财产权”理论对中国法学研究的启示。基于此理论,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仅表现为私法上的权利体系这一说法就可能过于狭隘,因为公法上的权利也具有与物权和债权相同的性质。尤其是在当代政府不断地通过法律创造新的财产权,使财产权的种类骤然膨胀的情况之下,将其纳入到财产权体系之内,有益于充分保障与实现相关的权益。如当代公众对环境资源享有重要的法定权利,正是这种权利的存在,使污染环境的一方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显然,仅仅以行政法律关系解释环境污染问题很难正确、全面解释受污染者的索赔权利的实质,也不能理解企业排污权的性质。这也必将引起财产权体系的构造及其方法的重要变革,(59)需要民法学与宪法学、行政法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要进行辨析的是公法上的财产权与私法上的财产权是否是一致性的概念,(60)将公法上的保护措施与民法上的保护措施严格独立分开的做法是否正确。事实上“新财产权”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中国传统财产权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健全。
其次,“新财产权”理论对于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启示。行政法学是以“行政”为研究起点的,通说认为目前中国行政的干预范围过于宽泛,所以要进行政府职能转变,进而有些人简单地将政府职能转变等同于“政府退出”。(61)其中显露出的行政法学理念显然是与“新财产权”理论中强调的政府积极介入某些领域进而形成诸多新财产的观点并不一致。受“政府退出”观念的影响在一些的领域之中,民营化、私营化、市场化似乎成了惟一的运营方式,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事实上,虽然国外在大力推行社会保障的民营化进程,但政府并未完全放弃此方面的职责。(62)中国行政法学对此问题应该进行反思,尤其应该在理论上探讨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介入是否充分。近几年来,中国也有人开始注意到将福利行政引发的权利视为是财产权的新内容(如养老金、福利资助、补贴、退伍军人伤残补助等)进而加以研究的现象。(63)但问题在于这种跨越了公法与私法两个层面的“财产权”能否得到应有的保障?我们可否或者如何借鉴“新财产权”理论,既防止社会保障金被挪用、侵害,又切实保护受领者免受非法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显然,这种既公也私的财产给行政法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课题。(64)而在单纯的给付领域之中,如何借鉴美国的正当程序理论,(65)构建中国福利行政中的给付程序,究竟什么样式的听证(前听证、后听证或者正式听证、非正式听证)可以充分保障福利受领者的“新财产权”呢?(66)中国实定法上目前尚不多见这方面的规定,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0条规定对于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因收入发生变化应办理停发、减发或增发,此时并未明确规定听证要求。相类似的还有《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7条规定的确定五保对象问题,也仅是经村民委员会审核,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发给《五保供养证书》,未规定听证的要求。总之,在相应制度建设之前,理论的探讨以及充分的论证是十分必要的(如在制定行政程序法之前,这样的讨论更为必要,因为简单规定“听证”可能并未解决问题的全部)。
再次,保护政府福利对于中国行政法制度建设方面的启示。事实上,尽管理论上并不多见此类“新财产权”的论述,但中国近几年的实践基本上是将诸如福利金、行政许可等视作为“财产”的范围。(67)特别是行政许可,如学者所言:“政府管制之下的‘市民社会’,民法上的私权利不再是权利主体可以自由支配和行使的私权;政府公权的行使也不完全在所有场合下都是公权力。一些政府许可便是在这里创造着大量的不属于民法上的财产权,但又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许可可以与其他财产一起或独立地成为交易标的。如果按照具有经济价值且可以交易的东西即为法律上的财产标准的话,那么,许可也具有法律上的财产特征。(68)相关的内容基本体现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的具体规定之内。不过,由于理论探讨不足,制度建构仍有改善的空间。如《行政许可法》对于行政机关作出不利于“单个”被许可人的变更、撤销或撤回许可的决定,是否应当举行听证并未作明确的规定。从理论层面上讲,这种变更、撤销或撤回的决定,往往影响到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财产权”。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变更、撤销或撤回的决定,应保障相对人享有听证的权利,使其能在行政机关面前陈述理由,为自己的利益辩护。(69)尽管考虑到行政机关完全遵循事前的听证程序增加了行政成本,因而不要求政府完全遵循正式的听证程序,(70)但行政机关依然应当在个人利益大小与行政负担之间进行平衡,灵活采取不同的听证程序。“正当程序经常导致政府开支过高与迟延。但在任何一个案件之中,这些开支成本必须接受正当程序试图保护的实体利益重要性、价值的检验。”(71)因此,为保障相对人的利益不受行政机关的专横侵犯,对行政机关依《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69条规定作出严重影响被许可人合法权益的变更、撤销或撤回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告知被许可人有举行听证的权利。被许可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组织“个别听证”。此外,也有一些所谓的政府福利在实践中仍然不予以承认,典型如公务员职位的问题,其人事任免等皆未受到正当程序的充足保障,且让我们寄希望于理论与制度的推进吧!
六、结语
行政国家、福利国家之下,新财产类型层出不穷。正如文章前面介绍的那样,美国政府汲取了大量的税收与权力,产出了诸多的财富、金钱、利益、服务、契约与许可。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何更加充分保障财产权,实现个人自由、独立与尊严均成为当代行政法学及其实践需要考量的因素。本文对美国“新财产权”理论及政府福利的保障实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指出了中国可资借鉴的成份。总的来讲,美国在提出“新财产权”理论之后,并未较多地进行争论,而是在行政实践中就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予以了充分探讨,产生了诸多的判例,这对中国进行行政法制建设尤其是程序建构具有借鉴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可能还特别需要从立法政策学的视角去探讨哪些应该成为个人的“新财产权”,此问题的探讨在美国并不多见。此外,政府福利的提供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仅仅依靠一种理论、一种制度肯定无法自足,尚需其他环节的整备,所以这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范畴,也希望诸如此类的研究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制建设中的“新财产”。
注释:
①See Sidney A.Shapiro & Richard E.Levy,Government Benefits and the Rule of Law:Toward A Standards-based Theory of Due Process,57 Admin.L.Rev.107 (2005); Richard E.Levy & Sidney A.Shapiro,Government Benefits and the Rule of Law:Toward A Standards-Based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58 Admin.L.Rev.499 (2006).
②See Henry J.Friendly,Some Kind of Hearing,123 U.Pa.L.Rev.1267 (1975).
③See,e.g.,Goldberg v.Kelly,397 U.S.254 (1970); Perry v.Sinderman,408 U.S.593 (1972); Board of Regents v.Roth,408 U.S.564,571(1972); Goss v.Lopez,419 U.S.565 (1975);Mathews v.Eldridge,424 U.S.319(1976).
④参见杨建顺:《宪政与法治行政的课题——宪法与行政法学领域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⑤德国宪法学家舒柏特(Gunnar Folke Schuppert)教授指出:“在探索宪法财产保障的范围和强度过程中,可区分财产的两种职能:首先,财产具备独特的个体或私人职能,因为它对个人自由发挥保护作用;其次,它具备独特的社会职能,其使用必须为公共福利服务……两种职能当然相互对立:如果强调财产保护个人自由的功能,那就易于导致宪法的财产保障之扩充;如果强调财产的社会职能,就倾向于允许议会去限制个人拥有者的支配范围。”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1页。
⑥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7页;[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5页;[美]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⑦如行政法学界关于财产权保护的最新著作可参见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的文章可参见杨海坤、金亮新:《公私法视野中的财产权分析》,《法治研究》2007年第4期。
⑧参见梅夏英:《当代财产权的公法与私法定位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5-245页。
⑨See V.Camp Cuthrell,III,Welfare,Due Process,and the Need for Change,1 St.Mary's L.J.224,225 (1969); Michael MacNeil,Property in the Welfare State,7 Dalhousie L.J.343,354 (1982-1983).
⑩See Charles A.Reich,The New Property,73 Yale L.J.733 (1963-1964).主攻财产法的他最早关注这一问题是在1951年,当时还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以及《耶鲁法学杂志》的总编辑,当时他的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护照问题的评论,引起了他对此问题的关注。See Comment,Passport Refusal for Political Reasons:Constitutional Issuse and Judicial Review,61 Yale L.J.171 (1952).Also see Reich,Midnight Welfare Searches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Act,72 Yale L.J.1347 (1963); Reich,Individual Rights and Social Welfare:The Emerging Legal Issues,74 Yale L.J.1245 (1965).
(11)中文文献中也有译作“政府供给”,参见[美]查尔斯·A·赖希:《新财产权》,翟小波译,http://www.gongfa.com/caichanquanlaixi.htm,2005年1月18日访问。
(12)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595页。
(13)See Charles A.Reich,The New Property,73 Yale L.J.733,737-38 (1963-1964).
(14)See John Edward Cribbet,Concepts in Transition:The Search for a New Definition of Property,1986 U.I11 L.Rev.1,30 (1986).
(15)参见宁红丽:《私法中“物”的概念的扩张》,《北方法学》2007年第3期。
(16)See Charles A.Reich,The New Property After 25 Years,24 U.S.F.L.Rev.223,224 (1989-1990).
(17)See John A.Powell,New Property Disaggregated:A Model to Address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24 U.S.F.L.Rev.363 (1989-1990).
(18)参见[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80页。
(19)See Betty B.Fletcher,Foreword:A Tribute to Charles A.Reich,24 U.S.F.L.Rev.221 (1989-1990).该杂志还发表了一组文章专门予以研讨。See Charles A.Reich,The New Property After 25 Years,24 U.S.F.L.Rev.223 (1989-1990); Robert L.Rabin,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d Its Excesses:Reflections on The New Property,24 U.S.F.L.Rev.273 (1989-1990); Willaim M.Kunstler,A "Real World" Perspective on the New Property,24 U.S.F.L.Rev.291 (1989-1990); John A.Powell,New Property Disaggregated:A Model to Address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24 U.S.F.L.Rev.363 (1989-1990); Michael C.Blumm,Liberty,the New Property,and Environmental Law,24 U.S.F.L.Rev.385 (1989-1990).
(20)参见[美]克里斯特曼:《财产的神话——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张绍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3页。
(21)See Richard A.Epstein,No New Property,56 Brook.L.Rev.747 (1990-1991).
(22)See Richard J.Pierce,The Due Process Counterrevolution of the 1990,96 Colum.L.Rev.1973,1982 (1996).中文文献可参见王锡锌:《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23)See C.R.Farina,On Missusing "Revolution" and "Reform":Procedural Due Process and The New Welfare Act,50 Admin.L.Rev.591 (1998).中文文献可参见王易锌:《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24)See Comments,Judith Harris Brown,The Clouded Issue in Public Welfare:Right v.Privilege,5 St.Mary's L.J.299(1973-1974).
(25)McAuliffe v.Mayor of New Bedford(155 Mass.216,29 N.E.517 (1892))中合理(或不合理)的意见严格区分了权利与特权的界限。Also see W.Van Alstyne,The Demise of the Right-Privilege Distinction in Constitutional Law,81 Harv.L.Rev.1439,1440 (1968).
(26)See Kenneth Culp Davis & Richard J.Pierce,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Vol.II,Little,Brown and Company,3rd Edition,1994,pp.21-23.
(27)See Bernard Schwartz,Administrative Law,3rd editi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1,p.252.
(28)Gilchrist v.Bierring,14N.W.2D 724,730(Iowa 1944).
(29)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第393-394页。
(30)Also see Note,Entrance and 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for Occupational Licenses in California,14 Stan.L.Rev.533(1962).
(31)See Charles A.Reich,The New Property,73 Yale L.J.733,734-737 (1963-1964).
(32)Sidney A.Shapiro & Richard E.Levy,Government Benefits and the Rule of Law:Toward A Standards-based Theory of Due Process,57 Admin.L.Rev.107,110 (2005).
(33)Mcauliffe v.Mayor of New Bedford,155 Mass.216,220,29 N.E.517,517(1892).Also see Linde,Justice Douglas on Freedom in the Welfare States: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Public Sector,39 Wash.L.Rev.4 (1964).
(34)182 F.2d 46 (D.C.Cir.1950),aff'd by equally divided Court,341 U.S.918 (1952).
(35)Id.at 57.(认为“在我们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个政府的行政人员因从公职中被免职而获得准司法式的听证”)
(36)363 U.S.603(1960).
(37)该法院解释道因为受领者的福利“并不依靠于他在多大程度上通过税收来支持……该法覆盖的雇员的非合同利益不能合理地推理为养老金持有,其对福利的权利建基于他的合同保险支付金。”363 U.S.at 610.下级法院认为福利是“附随的财产权”,其终止侵害了正当程序。参见Nestor v.Folsom,363 U.S.at 611.
(38)从发生的案件来看,基本上都是在探讨行政程序是否充足的问题。
(39)See Charles A.Reich,The Liberty Impact of The New Property,31 Wm.& Marry L.Rev.295 (1989-1990).
(40)See Robert L.Rabin,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d Its Excesses:Reflections on The New Property,24 U.S.F.L.Rev.273,282 (1989-1990).
(41)(43)Charles A.Reich,The New Property,73 Yale L.J.733,782 (1963-1964),733,783 (1963-1964).
(42)Barsky v.Board of Regents,347 U.S.442,472,474 (1954) (Douglas,J.,dissenting).
(44)详细的讨论可参见高秦伟:《论社会保障行政中的正当程序》,《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4期。
(45)See Charles A.Reich,Due Process and the Fallacy o f the "Rights Revolution",1 Mich.L.& Pol'y Rev.285 (1996).
(46)See Richard J.Pierce,The Due Process Counterrevolution of the 1990s,96 Colum.L.Rev.,1996.
(47)397 U.S.254 (1970).本案首次引用了Reich教授的文章与观点。
(48)408 U.S.564 (1972).
(49)(50)Arnett v.Kennedy,416 U.S.134,134,154(1974).
(51)Cleveland Bd.Of Educ.v.Loudermill,470 U.S.532,540(1985).
(52)424 U.S.319 (1976).
(53)最近的中文文献可参见胡敏洁:《美国社会保障中的听证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
(54)443 U.S.1(1979).
(55)436 U.S.1(1978).
(56)这种制衡远非仅有行政程序法就可以实现的,而系三权之间相互发挥作用又相互尊重对方专业的基础上整合而来。参见高秦伟:《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Also see Peter N.Simon,Liberty and Property in the Supreme Court:A Defense of Roth and Perry,71 Cal.L.Rev.146(1983).
(57)梅夏英:《当代财产权的公法与私法定位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58)See Hon.Stephen Goldsmith,Inner Cities,the Courts,and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1 Mich.L.& Pol'y Rev.281,282(1996).
(59)参见刘剑文、杨汉平主编:《私有财产法律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17-128页。
(60)参见赵世义:《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和制约》,《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田宝会、刘静仑:《私有财产权与法律改革——1978-2003中国法律改革史考察》,《河北法学》2006年第8期。
(61)参见徐月宾、张秀兰:《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2)See Lewis D.Solomon,Geoffrey A.Barrow,Privatization of Social Security:A Legal and Policy Analysis ,5 Kan.J.L.& Pub.Pol'y 9 (1995-1996).
(63)例如可参见张百杰:《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路径》,《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64)参见翟绍果、王佩:《超越公与私的社会保障财产权》,《新疆社科论坛》2005年第6期。
(65)See Alfred A.Oldham,Jr.,The Social Security Appeals Process:A Critical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Reviews,13 Cumb.-Semford L.Rev.279 (1972).
(66)See Comment,Due Process and the Right to A Prior Hearing in Welfare Case,37 Fordham L.Rev.604 (1969).
(67)例如可参见杨明、曹明星:《特许经营权:一项独立的财产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彭云望:《出租车经营许可证的财产权分析》,《行政与法》2003年第11期。刘畅:《是市场资源还是行政资源,取消出租车运营权起争议》,《中国青年报》2002年2月14日。
(68)高富平:《浅议行政许可的财产属性》,《法学》2000年第8期。
(69)See Sidney A.Shapiro & Richard E.Levy,Government Benefits and the Rule of Law:Toward A Standards-based Theory of Due Process,57 Admin.L.Rev.107 (2005).
(70)Mathews v.Eldridge,424 U.S.319(1976).
(71)Charles A.Reich,Due Process and the Fallacy of the "Rights Revolution",1 Mich.L.& Pol'y Rev.285,286(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