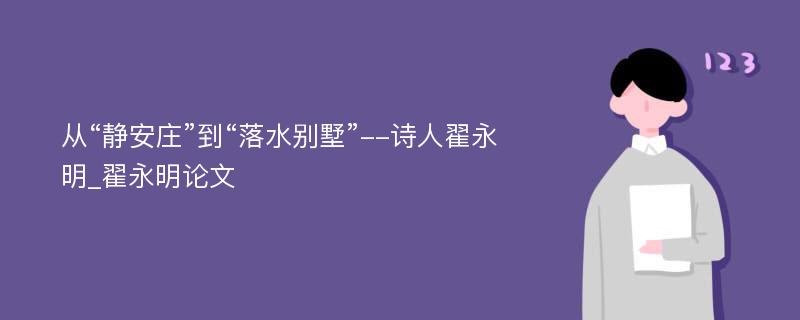
从“静安庄”到“落水山庄”——诗人翟永明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静安论文,山庄论文,诗人论文,翟永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4-0052-05
一
人(当然也包括诗人)与时间的不同结合、组合方式,注定会导致不同的时代。笔者用 最简单、最省力气的口气说,时间既内在于人,又外在于人。从内在于人的意义上可以 认为,一个人就有可能是一个时代;从外在于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无数个人拥有的 不同时代无可置疑地又有着相似的、相同的部分,这一部分通常被人们看作是纪元意义 上的时代,也就是历史学上的时代。很明显,个人的时代与历史学上的时代并不必然吻 合,尽管后者始终都在要求前者必须要向历史学上的时代折腰和脱帽鞠躬。翟永明就说 过:“诗歌在我们的头脑里,生活在我们的回忆中,一切的秘诀在于时间”,对于“一 个原创的时间(即外在的时间——引者注)和一个存在的时间(即内在的时间——引者注) ,人们常常不能将它们区别,而艺术就是这两种寂静所存留下来的不可磨灭的部分”。 [1](P183)——这既道明了时间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的形态,也一举点清了诗人尤 其是诗人的成就和时间的关系。
不少批评家都曾正确地指出过,翟永明是在1984年完成组诗《女人》后,才算确立了 自己的诗人地位。(注:翟永明自己就说过:“1980年至1982年我读了大量的书,写了 不少失败之作,大部分是些风花雪月的胡乱抒情……”(参见翟永明《纸上建筑》,第2 24页)事实也如此,《女人》之前的作品既谈不上成熟,也谈不上有新的创意,基本上 还是对朦胧诗人不成功的仿写(参阅《纸上建筑》,第222页),比如《昨夜,我有一个 构思》、《蒲公英》等诗作(参阅民刊《次森林》,1982年,钟鸣主编,第34—35页。 这差不多算是四川最早的民间诗刊之一),就是如此。)其实,《女人》的意义远不止于 此。从更宽广的范畴上说,《女人》开创了一个诗歌写作的时代。在这里,在不露声色 的时间面前,翟永明实际说出了一个迟早都将由她说出的命题:把女人当作女人。而在 当时,按“朦胧派”诗人舒婷表达的意思却是:把女人当作人。——后者当然是更流行 的“主题”。这毋宁已经向人们清楚地表明了:翟永明的时代与别人的时代是错位的。 也只有当她找到了(准确地说,是机缘巧合地遇到了)与时间结盟的本己方式,她才找到 了诗歌写作内部所需要的时代或时间方式。
鉴于热衷于诗歌赶集运动的人太多,(注:对此,翟永明有一个幽默的说法:“在80年 代初,写诗的人多到几乎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是诗人。”(见翟永明《纸上建筑》,第222 页)民谚也可作为参证:“这年头,扔一块石头就可击中两个诗人的脑袋。”或者:“ 中国的每一片树页至少有两个诗人在写。”)《女人》中的许多词汇、情绪被众多女诗 人借用和集体分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注:钟鸣的话能够证明上述事实:“翟永明 ,以她神秘的语言魅力,最终使一代女诗人躲在了她的阴影下,只有少数人能够幸免。 ”(钟鸣《天狗吠日》,载香港《素叶文学》,1996年4月,第49页)翟永明则从另一个 角度道出了事实:“不知从何时起,更形成了一股‘黑旋风’。‘黑色’(即翟永明《 女人》中的关键词汇之一——引者)已成为女性诗歌的特征,以致于我常常开玩笑说, 应该把我的《黑房间》首句‘天下乌鸦一般黑’改为‘天下女人一般黑’。”(翟永明 《纸上建筑》,第232页))翟永明的“策略”非常简单、也非常幽默,那就是十分隐蔽 地在自己开创的路子上继续深入地走下去,并始终和那些集体分食者保持不失礼貌的距 离,或者她就在她们眼前,却又让她们找不着她。翟永明对自己的“秘密诗歌通道”充 满了顽皮似的信心。这一“策略”的后果之一是一大批组诗——比如《静安庄》、《在 一切的玫瑰之上》、《死亡的图案》、《称之为一切》——的出现。随着时间把一个多 愁善感、歇斯底里的女人塑造成一个饱经沧桑的诗人,翟永明渐渐放弃了早期那种声嘶 力竭的写作风格,代之以一种相对平缓的、客观的和戏剧性的风格。这一转换的直接后 果,则是一大批断章残片式作品——比为《落水山庄》、《咖啡馆之歌》、《小酒馆的 现场主题》——的出现。我愿意把《静安庄》(它差不多是早期翟永明最好的作品之一) 和《落水山庄》(它是晚近翟永明较好的作品)当作翟永明前后两期作品的象征性名字: 如果翟永明的“静安庄时代”与纪元上的20世纪80年代大致对应,“落水山庄时代”则 与历史学上的90年代基本吻合。
二
指出翟永明的诗歌渊源也许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西尔维西·普拉斯就堪称她的诗 歌启蒙师傅。(注:翟永明在回答藏棣与王艾的书面提问中有这样的话:“我在80年代 中期的写作曾深受美国自白派诗歌的影响,尤其是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罗伯特·洛威尔 ,……当我读到普拉斯‘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以及洛威尔‘我自己 就是地狱’……时,我感到从头至脚的震惊。”(见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书面 访谈》,载民刊《标准》,1996年·创刊号,北京,第132页))大胆、直露、撕心裂肺 的疼痛与汉赋般铺排的独白式音调,构成了翟永明早期的诗歌风格;而要指名道姓地说 出她晚近诗歌的渊源,显然是一件冒险的差事。我宁愿相信这是时间的作用。时间始终 在充当着伟大教诲者的角色,是它促成了一个诗人的转换,通过日常生活,也通过语言 。
静安庄时代的翟永明是独白的翟永明,她以滔滔不绝的语势、一泄千里的激情,诉说 着女人的痛苦与渴望,以尖锐的声调向世界发出了几近拒绝的回答。这声音的潜台词不 是朦胧诗时代集体性的口号“我——不——相——信”,而是纯粹个人性的痛苦呐喊“ 我无助”!围绕着这一主题,或者说这一主要音势,翟永明不断地与想象中的世界辩驳 、反诘或者自我辩解与辩护。在《女人》中,它甚至看出了母亲对女儿的残忍,亦即一 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在无意间、在潜意识中造成的伤害,更把那种“无助”感推向了前 所未有的境地:
听到这世界的声音,你让我生下来
你让我与不幸构成
这世界可怕的双脆胎
(《女人·母亲》)
不排除这是真实的境况,但翟永明在《静安庄》、《在一切的玫瑰之上》和《死亡的 图案》等主要作品中反复陈述的这一意念,由于她情绪上的过于猛烈而省略了应有的过 程。像许多年轻、易于冲动的诗人一样,她在滚烫的独白中忘记了给独白“淬火”,由 于心理需要,独白也不具备自我“淬火”的能力。在静安庄时代,她试图通过对死亡的 体认来加强上述事实。的确,死亡几乎一直都是翟永明诗歌写作的重要主题,如同普拉 斯一样,她也力图使“诗歌与死亡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注:参见A.Alvarez:“
Sylavia Plath”,Review,(October,1963)。)但在早期,死亡只限于自己的死亡,或 者夸大一点,是女人的死亡。翟永明宁愿给死亡赋予性别上的涵义。那是一种呈阴性的 死。不排除女人死亡的特殊性,但死亡也是一个过程,不是突然到来的陌生者、异己者 。翟永明并没有给死亡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没有给死亡本身以充分成熟的时间就迫不 急待地把它给呈现了出来。《死亡的图案》对此有充分的展现,尽管翟永明的组诗分明 是在抒写持续了七天七夜的死亡、有过程的死亡。
与青春年少的激昂独白相适应,静安庄时代的翟永明在诗歌写作中的另一大显眼点是 组(长)诗现象的出现,无论是《女人》、《在一切的玫瑰之上》、《死亡的图案》,还 是《无垠的时刻》、《人生在世》、《颜色中的颜色》,都是组诗,《静安庄》就更不 用说了。组(长)诗现象意味着,诗人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激情、痛苦甚至绝望要 表达:
我十九,一无所知,本质上仅仅是女人
但从我身上能听见直率的喊叫
谁能料到我会发育成一种疾病?
(《静安庄·第九月》)
正是在这里,滋生了翟永明诗歌写作中另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将空间溶解在时间中 。这不难理解。由于她狂热的独白,不可挽回地省略了事物发展的过程,时间往往只存 在于一瞬,而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中的却是空间,也只是空间。在《静安庄》中,“ 瞬间”性的“十九岁”包纳了“静安庄”内的各个角落。在《死亡的图案》中,情形丝 毫没有改变。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独白是不在乎过程的,是注定(?)要消灭过程的。 这也许正是抒情之所以成为抒情的一大技术特征。在此,死亡是在瞬间完成的,拒绝、 烦恼、痛苦、呼喊、尖锐、激情、绝望……也注定只在瞬间呈现——和“见性成悟,直 指本心”的禅宗在思路上一致却在情绪上刚好相反——,它们都仅仅是强辞夺理式的突 然成熟。
由于独白过于浓厚的排他性,在静安庄时代,翟永明的诗歌写作有一种天然的单纯, 即便是看上去较为复杂的《静安庄》也是这样。由于主题的单一,具体倾诉对象的丧失 (这是独白之所以成为独白的根源所在),无依无靠的“我”成为诗中唯一的角色与人称 ,(注:《静安庄》最末一节中出现了“他”,但这个“他”更多的是诗人自己内心的 外化,是立普斯所谓的“移情效应”。这个“他”实际上就等同于“我”。在早期作品 中,翟永明大都使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出现,与晚近时期的处理方法绝不相同。 详论见下文。)使静安庄时代的翟永明无可避免地有着把世界简单化的嫌疑。在此,笔 者不妨说,静安庄时代与纪元上(即历史学上)的80年代基本吻合:“把女人当作女人” 和“把女人当作人”,并不绝然对立。我的意思是,尽管前者是以“我无助”的口气出 现,后者是以“我反抗”的语调现身,但在思维方式上仍然有着较为浓厚的一致性:对 自我的重视和对自我的寻找。——虽然我并不否认前者比后者未始没有“进步”性。在 这里,我仍然可以看出时间的鬼把戏:内在的时间与外在的时间尽管表现不一致,但时 间本身自有它的恒常品性又是毋庸置疑的。
从1987年写作长诗《称之为一切》开始,翟永明进入了漫长的探索期和裂变期。这首 明显有着自传性质的长诗开始有意识地放缓了语调,也开始有意识地试图从独白中出走 ,以便进入吵吵闹闹的日常生活的集市去寻找对话者。但翟永明并没有很快找到适合自 己语势的手艺和方法。这一漫长的时间阶段可以称作中间地带。直到1993年写完《咖啡 馆之歌》,翟永明才开始进入自己的落水山庄时代。也就是说,她是在1993年才开始进 入历史学上(即纪元上)的90年代的(注:钟鸣在为翟永明的诗集《黑夜里的素歌》(改革 出版社,1997年)所作的序中说:翟永明是在1991年彻底摆脱了普拉斯的影响,发生了 自己的重要转折。不过,本文认为,远离了普拉斯并不能说翟永明已进入了九十年代。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落水山庄》里,翟永明写道:
建筑师对他的图案呵护备至
不知名的人在击碎的硝石中寻找静谧
三月风清,我带来本地的流水行云
窗户穿越工作者的灵魂
气候和风景浮上他的脑际
建筑师在保持他的空间经验
形式在朝着多变的方向迈进
“我”并不是唯一的诗中主角,因为出现了“他”;也因为“他”的出现,“我”不 仅有了可以面对的东西,也彻底修改了“我”的原意:“我”不再作为纯粹的抒情者、 独白者,而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旁观者而现身。经过了漫长的中间地带后,静安庄时代 的独白被落水山庄时代的陈述所取代。我们是以客人的身份来到世界的,却往往把自己 误认为主人。翟永明或许参透了这一点。因此,从容、大度、冷眼旁观的客人心态,构 成了落水山庄时代的翟永明的主要特色。在这里,“让女人成为女人”也被“让女人成 为人”取代:它的潜台词不再是“我无助”而是“我思考,我陈述”,犹如蒙田所说“ 我不指点,我叙述”,或者按照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说,“事物在桌子低矮的一端议 论起来才最妙。”正如翟永明在《脸谱生涯》中写道的:“事物有事物的规律/那人说 :‘愿闻其详’”。《落水山庄》有一个小小的叙事骨架:它描述了这个山庄从草图到 修建成功的过程。“我”目睹了这一切。这就是说,在时间的教育下,饱经沧桑的诗人 终于拣起了她曾经省略了的过程:给事物以成熟的时间;事物和人一样,它也需要有一 个饱经沧桑的经历。在《咖啡馆之歌》、《道具和场景的述说》、《玩偶之家》、《脸 谱生涯》、《一个朋友的死讯》、《剪刀手的对话》、《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 小酒馆的现场主题》……等重要作品中,也都充满了这一特征。死亡主题也不再只具有 性别的涵义。它并不只是阴性的。它也同样具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静安庄时代,死亡 被看作一件可以吟咏的事情,在必然中竟然有着不可能的性质,而如今,死亡只是一个 可以被陈述的事实。这个可陈述的事实,在诗歌营造出的时空之内,几乎就是伊夫林所 谓“赛以斯宅第的母鸡下的蛋全英国最好”。这只要把《死亡的图案》与《一个朋友的 死讯》两相对照就相当清楚了。更为醒目的是,在落水山庄时代,死亡主题已不再处于 最耀眼的位置,这毋宁是说,它已被慢慢的、注定要来临的、正在来临的衰老与凋零过 程所取代。过程是最重要的。衰老的过程更是令人毛骨耸然的,但它又是可以被理解的 :是一个理解得服从,不理解也得服从的命定之物。好吧,那就理解吧。——这就是落 水山庄时代的翟永明诗歌写作的口气。死亡并不重要,衰老和凋零的过程才是实质、才 是一切,你我都明白,这同样是时间的作用,是时间惹的祸!
与这种重视过程的平稳陈述相适应,落水山庄时代的翟永明在诗歌写作上的另一大显 眼点是:组(长)诗现象被断章残片现象所取代。这里的断章残片更是个比喻性的说法, 它不仅不是指作品的不完整,也不是指就没有像《十四首素歌》(这同样是晚近的作品) 那样的组诗出现,它只是说,如今的翟永明已不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独白者,而是一个 打捞日常生活的残章断片、为日常生活的残章断片倾注热情的人。这意味着,她已经没 有太多的话要讲,她不用反问世界,她只是试图理解构成世界的事件的运动过程,她也 不再为单纯的抒情奔波忙碌,只为残章断片式的生活而沉默。我曾经论证过,一种文体 就代表一种观察世界和生活的角度,代表一种世界感,但它归根结底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注:参阅敬文东《从野史的角度看》,《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组诗长 诗是这样,断章残片也如此。它们都是为框架某种生活以及对某种生活的观感而出现的 。而关于沉默,维特根斯坦曾精辟地指出过:我们想要学会它,首先要学会说很多话。 天生的口吃者不会懂得真正的沉默。我的看法是,沉默更是个时间概念,它让你不得不 从滔滔不绝中转为哑口无言。但这一暗中的转换对于转换者却又有着惊天骇地的内容。 ——我不知道维特根斯坦是否相信,人也可以在说话中保持沉默。但落水山庄时代的翟 永明是承认的,因为残章断片本身就意味着,描述过程(即有节制地说话)却只能抓住过 程的片段(即只能相对地沉默),没有任何人可以获得整个过程(即滔滔不绝地言说)。当 然,为了防他个万一,我还是承认:狂徒和青春年少者可以例外。
在这里又滋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诗歌中的时间处理方式。翟永明这一回是将时间溶 解在空间中。由于她开始重视过程、描述细部,由于过程从来就不只是一瞬而是一段, 因此,在陈述过程中,变化得最多的将是时间,空间则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顶多从一个 场景缓慢跳到另一个相对稳定的场景。在《咖啡馆之歌》、《小酒馆的现场主题》、《 在乡村茶馆》、《走过博物馆》……等等作品里,时间在心平气和地,然而又是不断地 处于变更之中。在时间近乎匀速的流动过程中,事物——它被相对地固定在某一个空间 ——在成熟,结果在缓慢来临,就像樱桃在期待最后完成的一瞬,事物在等待着一个框 架它的特定的、稳定的空间。《剪刀手的对话》就很说明问题。翟永明通过对“为了美 ,女人永远着忙”,“为了美,女人暗暗流血”,“为了美,女人痛断肝肠”等主题句 的事实性陈述,把女人日渐衰老的过程给充分陈述了出来,在此过程中,空间要么是相 对稳定的,要以就是干脆溶解在时间中并且几乎隐而不见。(注:这种说法当然只是相 对的,甚至只是比喻性的。因为时空的不可分割性已成科学常识。问题在于,诗人是可 以也可能打破这种科学定见的。在空间溶解在时间中这种情况下,时间既是瞬间的,其 流逝又是疾速的,因此,空间必然有很多变化,快速地忽东忽西是免不了的;而在时间 溶解在空间中这种情况下,时间按正常速度流动,甚至比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流动得更慢 ,有如慢镜头,这样,在某一个特定空间“停留”的时间就相对要长一些,空间的变化 相对也就少一些。)
由于陈述的包容性——不仅包纳了“我”,也包纳了以“他者”面目出现的别人—— ,翟永明的诗歌写作具备了相当浓厚的戏剧性色彩。《道具和场景的述说》是个好例子 。在诗歌制造出的话语空间中,作为舞台道具的鼓、琴、幕、台、扇以及作为场景的三 种形态——楔子、附录、注释——分别得到了诗人的陈述和说明,这首长达六节的诗中 充满了各种人称的转换,时而是被陈述的事物,时而是“我”的谈论与旁白,使“我” 与“物”之间形成的时而紧张、时而缓解的戏剧关系,产生了一种松紧适度的张力,诗 歌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也由此得以呈现:它把静安庄时代的抒情的简单性打进了冷宫。
三
在独白性质的静安庄时代,翟永明的诗歌中缺少一个与抒情主人公交谈的对象,“我 ”的出现是铺天盖地的;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以“我”的出发点,以“我”的眼光 和抒情角度来设定世界、界定万物。时间更多的是属于自己的,是内在的。但正如美国 佬罗伯特·佩·华伦在《龙的兄弟》中所说:“认识完善的方向便是自我的死亡/而自 我的死亡正是人格个性的开始”。认识自我、表现自我,其实与所谓发现自我、暴露自 我、发泄自我是一个意思,有着相当多的自私性的个人中心主义味道,毋庸置疑,在不 少情况下,甚至还有着法西斯的暴力色彩,尽管它也可能以温情脉脉的面孔出现。但软 刀子也能杀人,“美女蛇”是所有蛇中最厉害最可怕的蛇!到了落水山庄时代,情况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翟永明意识到了“自我的死亡”的必要性。这就是说,尽管时间首先 是内在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时间同时还外在于所有人,人与时间的结盟方式除了各 自不同的内在性外,还有共同的外在性。我已经指出过,相对于整个汉语诗歌的潮流, 翟永明进入历史学上的90年代大约在1993年。这可以从“人称”的转换这个看似渺小的 角度来分析。
人称不是随便使用的,在某些时候——尤其是在人们的说和写之中——它有着相当的 致命性。一个人使用什么样的人称来说话,同时也就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态度,也表明了 他观察世界、进入世界的角度与方式。翟永明在晚近时期,“我”、“你”、“他”、 “我们”等人称是大量混用的,尤其使用得最多的是“他(们)”。《咖啡馆之歌》以后 的作品几乎全部如此。一般而言,我/我关系大都表示独白和自言自语,有相当的自恋 嫌疑;纯粹的我/你关系大都表征着某种倾诉(比如我们向自己的亲人写信),一如马丁 —布伯所说。它表明“我”有痛苦(或幸福)要向“你”倾诉。不排除这中间有对话关系 ,但它也有着明显的自我中心成份和自恋成份,却又是明白无误的。
我/他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第三人称(“他”)的引入,“我”的立足点变了,“ 我”再也成不了中心(这当然是在理想的情况下),也充当不了界定世界的法则。我/他 关系在更大的程度上表明:“我”站在“我”的位置上(但不是中心)观察“他”。尤其 重要的是,我/他关系还隐含了一个前提:“我”要向“你”报告有关“他”的消息。 在我/他关系中,“你”是潜在的,是我/他关系设定了的。这也就把事情给一举点明了 :时间不仅内在于“我”,也内在于“你”;“他”不仅内在于“我”、“你”、“他 ”,同时也外在于“我”、“你”、“他”。“我”虽然观察不到或很难观察到内在于 “他”的时间,但能观察到外在于“他”的时间,并能准确地向“你”汇报。这是一种 诚实、谦逊的方式,一般情况下,也是陈述的本来意思。陈述只需要真相。由此,“我 ”再也不以纯粹抒情的身份内含于诗歌文本,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人间消息的传递 者,一个谦逊的信使。这就是翟永明在《孤独的马》中说起的:
它的双眼,借我的光
把四周重新打量。
基于对时间与时代的这种方式的体察,翟永明晚近诗歌中的人称是混合的,就几乎有 它的必然性了。表现方式在许多时候就是我/你/他(们)的和合。在《咖啡馆之歌》中, “我”以咖啡享用者的身份从下午坐到第二天黎明,“我”看见了许多别人(即他或他 们)的行动,他(们)有聊或无聊的举止,他(们)说出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只言论语,最 后全化作时光中的一缕烟雾,但又同时存在于“我”的眼中,存在于“我”的记录中。 也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人生的真实事境。它不需要痛苦,不需要人为它付出痛苦,更 不需要人为它解除痛苦,因为很可能它根本就无所谓痛苦不痛苦。“我”要把“他”( 们)的这一切都告诉“你”。即使是全诗结尾时出现的那位与“我”对话的“你”,也 不再是“我”要把消息告诉“你”的那位“你”。理由很简单,在《咖啡馆之歌》中, “你”只能是隐含的、假定的、潜在的;而与我对话的“你”,毋宁说只是一个被“我 ”观察的“他”,是以“你”的面孔出现的“他”。
长诗《重逢》则有另一番景致:是“我”在对重逢者“你”讲话。全诗一共描述了“ 我”与“你”的六次重逢,每一次重逢都以“我看见你——”开始叙说。然后是“我” “看见”“你”的一系列行动。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纯粹的我/你关系。但它不是。因 为这首诗设定了一个第三者“他”作为听众。不可否认,“我”首先是对“你”讲话, 但“我看见你”表明“你”听不到“我”的声音,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就在“你”面 前,尽管很可能“我”的确渴望“你”能听到、能意识到。因此,这个被“我”渴望的 “你”,实际上只是一个“他者”,是“你”身上暗含的“他”,是隐含的“他”。— —很有些类似于巴赫金所谓“人身上的人”。“我”只是在描述“你”自己看不见的行 动——“他”——罢了。当然,“你”也永远感觉不到这一点。这首题为《重逢》的诗 作,实际上正是一个反讽:“我”不是在与现实中的“你”重逢,而是在与“你”的某 几个动作、某几个曾经的人生画面相遇。我想把一切都讲给“你”听,但这个听“我” 说话的“你”,已不是做出人生动作并与我重逢的“你”了,而是以隐含的“他”来表 现的,即“他”身上的“你”。
以上两种情况是落水山庄时代的翟永明在诗歌写作中的惯常方式。由于“他”的引进 ,完全改变了诗歌的格局。它最直接的后果是,过程才是一切,对过程的感知、观察并 向他者(即你或他)报告感知和观察到的结果才是实质。但“我”的观察决不是、也决不 会是完整的,因为观察者并不具备全知全觉的能力,这或许就是落水山庄时代断章残片 现象的又一根本缘由。由此,翟永明修改了自己早期的个人诗学辞典,并为这些词赋予 了落水山庄时代的特殊涵义。早期的词是“黑色”、“死亡”、“爱”、“肉体”、“ 女人”……晚近时期的则是给它们加了规定过程的定语后产生出来的新词:“谈谈…… ”(《莉莉与琼》)、“现在谈谈……”(《场景对道具的述说》)、“我看见……”(《 重逢》)。黑色、死亡、肉体、爱、女人……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填充在上述三个省 略号中的任何一个后边。实际上,这正是落水山庄时代,翟永明诗歌写作的几乎全部内 涵。它表明,早期用来身受式地用作抒情的东西(比如肉体、死亡等等),现在完全可以 被当作一个一个的事实来观察和谈论,黑色、死亡、肉体、爱、女人……都在一个个不 可例外的过程中,走向没落、凋零。这大约就是饱经沧桑的意思了。
假如只是到此为止,翟永明仍然逃脱不了平庸之嫌。翟永明摆脱平庸的主要方式之一 ,就是在此之上把“我”转化为“我们”。这同样在《咖啡馆之歌》后的许多作品中可 以得到观察。它表征的意思是:虽然对这一切的观察只是“我”的,但如果大家愿意, 也都可以观察到,因为说到底,这一切都与我们有关,不仅和我们的生存有关,也和我 们的死亡有关。——难道时间在表征活着的时候,就没有表征死亡吗?难道时间不是“ 我们”的地狱形式之一种吗?而这显然是在说,静安庄时代的“我”只表征“我”一己 的情感,还远不能上升为经验,到了落水山庄时代,这一切都可能、都可以上升为经验 ,而经验就意味着可重复性,意味着很可能为“我们”所共有。当然,经验也意味着有 限;但有限不正是“我们”这些叫做人的东西的本来面目么?翟永明发现了这一点,陈 述了这一点,也承认了这一点。这也是饱经沧桑的意思。这也是时间给出的伟大教诲。
不可否认,翟永明确实具有从女性的认知角度来观察世界的特征,这一线索实际上穿 插在她的整个诗歌作品里。但这并不表明她的写作就一定是所谓的“女性写作”。我反 对把一个成熟的诗人说成跟性别绝然相关的诗人。说一种写作、说某个人的写作是“女 性写作”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很可能并没有说出更多、更深刻的东西。翟永明在时 间本身的教诲下,理解了时间本身;不仅理解了自己的时间,也理解“我们”的时间, 这让她有可能把女人只看成普通人——而一切所谓的“女性写作”在这一点上,倒也许 持较为相反的观点。翟永明说:“男人在思考问题,女人也在思考。我说的‘把女性意 识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领域来开拓’,只是女人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的一种,但它决不 仅仅是女人思考的全部”。[1](P241)因此,在“把女人当作人”(朦胧诗,舒婷)被转 换为“把女人当作女人”之后很久,翟永明通过人称的转换为手段,又把这一命题转化 为“把女人当作(普通)人”。这不是对朦胧诗和朦胧诗人的简单回归,因为它们产生的 背景是绝不相同的,其内涵也各有禀性。我们可以说,这是时间的作用,是时间把“饱 经沧桑”设定在翟永明身上之后产生出的直接后果。这种命题的转换更与辩证法毫无干 系,尽管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辩证法确实很伟大。
收稿日期:2003-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