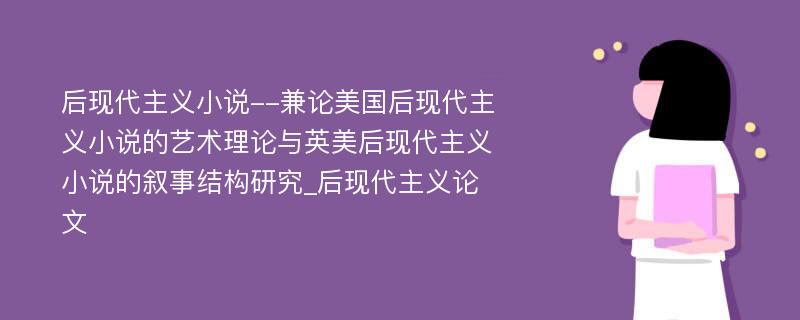
谈后现代主义小说——兼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和《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小说论文,美国论文,英美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002年有两部研究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中文专著问世,一部是陈世丹著《美国 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由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5月出版。另一部是胡全生著《英美 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11月出版。两本书出版时间相隔6 个月,虽然是研究同样的课题,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以及工作的质量却有相当的差异。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共11章,各章的分工是“第一章综合论述后现代主义 小说的审美特征,以后的每一章集中探讨一位代表作家的重要作品,揭示其主题思想与 艺术特色,从而反映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创新艺术的全貌。”(注:陈世丹《美国后现 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76、97、4、78、85、8 9、4、36、47、4、36、138页。)第四章“哲学文本戏仿 黑色喜剧 元小说”讨论巴 思的小说《路的尽头》(The End of the Road),提到了巴思1967年在《大西洋月刊》 发表的著名文章《枯竭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断言该文“阐述了 他关于当代小说的理论”,“枯竭”“实际上指的是叙述可能性的枯竭”,(注:陈世 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76、97、 4、78、85、89、4、36、47、4、36、138页。)并称“巴思意识到了文学可能会枯竭” 。(注: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 75-76、97、4、78、85、89、4、36、47、4、36、138页。)其实,《枯竭的文学》只是 表达了60年代末巴思对当时美国文学的一些想法,而如果要全面了解巴思“关于当代小 说的理论”,还必须阅读他的其他论著,特别是两篇重要文章:《富足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1980)和《再探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Revisited,1988)。巴思在《枯竭的文学》一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是“艺术及其各种形 式和各种技巧存在于历史进程之中,必定发生变化”。(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in Malcolm Bradbury ed.,The Novel Today:Contemporary Writers on Modern Fic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72,p.70,p.79,p.75.)他所说的“枯竭”是指“某些形式被用尽”(the usedupness of certain forms),(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 ,”in Malcolm Bradbury ed.,The Novel Today:Contemporary Writers on Modern Fic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72,p.70,p.79,p.75.)是 艺术形式的“枯竭”。针对别人对他的误解,巴思在《富足的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 永远不会枯竭”,(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in The Friday Book:Essays on Other Nonfic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205,p.206,p.196,p.203,p.203,p.203,pp.203-204.)他所说 的“枯竭”之本意是“高雅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美学的枯竭”,(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in The Friday Book:Essays on Other Nonfic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205,p.206,p.196,p.203,p.203,p.203,pp.203-204.)而并非“叙述可能性的枯竭”。
巴思在《富足的文学》一文中回忆了自己被贴上各种标签的经历:50年代是“存在主 义作家”,60年代初期是“黑色幽默作家”,后来成了“后现代主义作家”。(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in The Friday Book:Essays on Other Nonfic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205,p.2 06,p.196,p.203,p.203,p.203,pp.203-204.)一般认为,《迷失在开心馆》(1968)是巴 思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路的尽头》发表于1958年,《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对 巴思这部早期小说只是一带而过,称该书与贝娄的《荡来荡去的人》等小说反映了“存 在主义遗留下来的荒诞意识”。(注:Emory Elliott,ed.,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1147.)杨仁敬 教授在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写的序言中说:“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 ,大体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的黑色幽默小说,以1961年《第二十二 条军规》的出版为标志;第二阶段是从1971年《但以理书》的问世至20世纪末,一直延 续到现在。”(注: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2年,第3、75-76、97、4、78、85、89、4、36、47、4、36、138页。)杨教授的观点是 否成立,暂且不论,然而根据他的这一分段说,《路的尽头》并不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之 列。陈世丹将其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主要文本来讨论,是因为他认为巴思在《路的尽头 》中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戏仿”,而戏仿是后现代主义 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法。但第四章第一和第二小节以很大的篇幅评介了《路的尽头》表达 出来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主义”,关于戏仿的论证则不充分,缺乏说服力 。另外,书中对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评介不准确,例如,50年代美国“出现了最 适宜于存在主义这种充满着悲观绝望、颓废情调的哲学生长的良好条件”;(注:陈世 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76、97、 4、78、85、89、4、36、47、4、36、138页。)弗洛伊德的理论“抹杀了意识在人的行 为、活动中的调节作用”;(注: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76、97、4、78、85、89、4、36、47、4、36、138页。) “弗洛伊德的理论不仅给未婚青年男女的乱交提供了理论根据,也引起了婚姻家庭中的 性混乱。”(注: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3、75-76、97、4、78、85、89、4、36、47、4、36、138页。)陈世丹在《美国 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中讨论的《路的尽头》在创作手法上全然属于传统小说,体现 的内涵是存在主义哲学;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则被公认为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 他应该选择更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作为范文。
不过,《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的最大问题还是对后现代主义小说审美特征的 认识。“前言”部分对全书各章要点有一个简短总结,关于第一章“后现代主义小说审 美之维”的概述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从后面剪贴过来的,现摘录如下:
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仅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内部形态和结构,而且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 本身进行反思、解构和颠覆,它不再讲故事,不展开情节,也不塑造人物,形成了元小 说这一奇特的小说形式;反体裁成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主导模式;后现代主义小说 家否认先验的、客观的意义,认为意义仅产生于人造语言符号的差异,因此后现代主义 小说仅仅是无意义的符号组合、能指的延续,表现为不确定的内在游戏,小说的意义靠 读者的解读来实现;后现代主义小说追求的是大众化,而不是高雅,因此,一些后现代 主义小说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倾向,成为读者大众的文学;后现代主义小说在对传统小 说形式与叙事技巧不断消解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艺术手法,如戏仿、拼贴、蒙太奇 、黑色幽默和迷宫等,在叙事模式上表现为语言主体、结构零散、能指滑动、零度写作 等。(注: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 、75-76、97、4、78、85、89、4、36、47、4、36、138页。)
这段提纲挈领式文字有多处值得商榷。首先,“传统小说”这一概念不清楚,它既可 指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也可指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采用线性叙述,拥有完整情节,营造真实幻觉,宣扬、复制、强化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 态;现代主义小说作为对现实主义的反拨,遵循支离破碎美学原则,其主要特征包括共 时性叙述、非理性、意识流、支离破碎、梦幻语言、对现存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的批判性 。那么,后现代主义小说与这些“传统小说”是否如陈世丹所说构成一种“解构、颠覆 ”的关系?至少,巴思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富足的文学》中写道,后现代主义小说应 该是这些对立面的“综合体”(synthesis),“我理想中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对于20世纪 的现代主义父辈或者19世纪前现代主义(即现实主义)的祖父辈,都不会是绝对地排斥或 绝对地模仿。”(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in The Friday Book:Essays on Other Nonfic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205,p.206,p.196,p.203,p.203,p.203,pp.203-204.)巴思相 信:后现代主义小说能“以某种方式超越”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对“传 统小说”兼收并蓄、继承发展,而不是“抛弃和否定”。(注: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 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76、97、4、78、85、89、4 、36、47、4、36、138页。)
其次,所谓“不再讲故事,不展开情节,也不塑造人物”的小说,确切地说,是典型 的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吴尔夫的《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等 意识流小说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缺少完整的情节,作家注重展示主人公内心世界复杂 纷繁的心理活动,而不是简单地塑造一些好人或坏人、高尚的人或卑贱的人。《美国后 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重点讨论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最后一幕》、《五号屠场》 和《路的尽头》等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反倒都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和情节。“元小说 ”作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一个明显特征是自我“反映”:叙述者展示创作的过程 ,时时提醒读者注意作品的虚构性。但现代主义小说形式与“元小说”的形成并无因果 关系。
论点之三:“后现代主义小说仅仅是无意义的符号组合。”《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 术论》第三章讨论《五号屠场》时却赞扬该小说有“深刻的思想”。(注:陈世丹《美 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76、97、4、78 、85、89、4、36、47、4、36、138页。)后现代主义小说一方面是“无意义的符号组合 ”,一方面却又能“表现超验世界的问题,即对人类的抽象思考——人类的局限、人类 的前途、人类的存在和毁灭”,(注: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76、97、4、78、85、89、4、36、47、4、36、138页 。)这里岂非逻辑混乱、前后矛盾?退一步讲,后现代主义小说如果真是“无意义的符号 组合”,它便是一堆乱码,读者根本无法解读。陈世丹的另一个观点是后现代主义小说 具有“通俗化倾向”。从常理推论,这种由乱码组合成的“天书”如何能成为“读者大 众的文学”?
论点之四:“小说的意义靠读者的解读来实现。”这是读者反应批评的观点。根据读 者反应批评理论,莎士比亚的戏剧、弥尔顿的诗歌、狄更斯的小说,其作品意义都要通 过读者的阅读来实现。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并无任何独特之处。
论点之五:“后现代主义小说在对传统小说形式与叙事技巧不断消解的同时,也创造 了自己的艺术手法,如戏仿、拼贴、蒙太奇、黑色幽默和迷宫等。”这与事实不符。如 前所述,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根本任务”并不是对传统小说形式与叙事技巧进行“破坏 、消解和颠覆”,(注: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3、75-76、97、4、78、85、89、4、36、47、4、36、138页。)而戏仿、 拼贴、蒙太奇等手法也早已存在,并非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造”。另外,黑色幽默是 盛行于60年代美国的文学流派或作品,而不仅仅是“艺术手法”。黑色幽默作品对世界 的非理性采用放大、扭曲、变形的艺术手法,掺入喜剧成分,使生存状况显得更加荒诞 不经。
以上讨论可以说明,《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立论不够严谨。该书理论阐述与 文本分析之间缺乏相互照应,有些文学史料也不准确。(注:《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 术论》将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想当然地译为乔 治·路易斯·博吉斯(第75页),将意大利作家、著名学者恩贝托·埃柯(Umberto Eco) 称为“美国文论家厄姆伯图·艾柯”(第67、281页)。)相比之下,胡全生撰写的《英美 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无论在学术水平还是在资料掌握方面都要好得多。该书 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理论探讨有条有理,细密完备;作品分析深入透彻,阐 发允当。胡全生在论述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定义时,引用了麦克黑尔(Brian McHale)在《 后现代主义小说》(Postmodernist Fiction)(注:对于麦克黑尔其人其书,陈世丹的《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未曾提及。)中提出的观点,即现代主义诗学与后现代主 义诗学的整体对立表现在现代主义小说是“认识论的”,而后现代主义小说是“本体论 的”。同时,他也不忘指出麦克黑尔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界定之说的局限:“虽然本体论 与认识论之别似乎在总体上即作为一整体诗学把握住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但是小说分析 总归要就具体作品来分析,而以麦氏的界说来分析某一作品,界定就容易失于宽泛、游 移不定。”(注: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 2年,第6,16,11,132-134,128,110、108、93,272页。)《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 述结构研究》的特点是既有自己的理论思考,又以具体作品分析为基础,不失为研究后 现代主义小说的有益之作。
胡全生在讨论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时,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即不是孤立地研究英 美后现代主义小说,而是将它放在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比较中进行考 察,使三者之间的异同一目了然。他认为,现代主义小说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关系可视 作“父与子关系”。(注: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2年,第6,16,11,132-134,128,110、108、93,272页。)后现代主义小 说源生于现代主义小说,二者是一脉相承。“现代派小说家的一切创作方法,都被后现 代派小说家接受、运用,而且有的用得更广、更多、更极端。”(注:胡全生《英美后 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6,11,132-134,12 8,110、108、93,272页。)同时,后现代主义小说又对现代主义小说有所超越。“理 论篇”在充分论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继承性”和“超越性”之后,逐一分析了后现 代主义小说文本中的现实、语言、人物、情节、读者的作用、滑稽模仿和互文性、拼贴 、意识形态等成分,揭示后现代主义小说“激进”的特征。以讨论滑稽模仿和互文性的 第九章为例,作者对parody一词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详尽阐述了滑稽模仿的现代含 义、后现代含义、表现形式、在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运用。胡全生指出 :“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家都好用滑稽模仿,”但二者在用心、用法、效果、程度上存 在差异。(注: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6,16,11,132-134,128,110、108、93,272页。)现代主义小说家将滑稽模 仿视为一种“形式实验”,注重互文性,“而忽视了它的心理审美效果即滑稽的一面” 。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
滑稽模仿已不是用作形式试验,而是一种调侃方式,读者在被调侃的过程中,感觉到 作者是在玩游戏,感觉到滑稽、可笑,如我们读巴思的《迷失在开心馆》和库弗的《保 姆》时,无不有这样的感觉。但在玩笑之余,我们又可能有一种领悟:啊,原来是说小 说的小说。这里,我们既看到了滑稽模仿的滑稽一面,又看到了其互文的或元小说的一 面。(注: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6,16,11,132-134,128,110、108、93,272页。)
胡全生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说明了滑稽模仿,即戏仿,体现出后现 代主义小说对现代主义小说的继承和超越,这是与陈世丹关于戏仿是由后现代主义小说 家所“创造”的“自己的艺术手法”这一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显而易见,胡全生的论 点有理有据,较为容易让人接受。
《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的“实践篇”点评库弗的《保姆》、福尔斯的 《法国中尉的女人》和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进一步阐发“理论篇”提出的观点, 不乏精当之论。不过,由于三部作品都是带有实验主义成分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作者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理论建构;或者说,作者关于后现代主义 小说的理念影响了他讨论什么具体作品的决定。就小说情节而言,书中的论述仅适用于 有前卫性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胡全生总结后现代主义小说情节的特点为“答滴式”断 裂的情节设置:“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对待情节的态度趋向极端,他们不仅疏远而且背离 情节。”(注: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6,16,11,132-134,128,110、108、93,272页。)陈世丹同样认为后现代主 义小说“不展开情节”,小说家“不再依靠常规性的小说手法——冲突、发展和线性情 节,而是为读者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零碎片段”;后现代主义者“持存于、满足于各种片 段性、零散性、边缘性、分裂性、孤立性之中”。(注: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 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76、97、4、78、85、89、4、36、 47、4、36、138页。)在陈、胡两人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完整的情节似乎是与后现代主 义小说水火不相容的东西。
这里涉及的实质性问题是如何界定后现代主义小说。巴思在《富足的文学》一文中告 诫我们:“如果说现代主义作家教导我们,线性叙述、理性、意识、因果关系、幼稚的 幻觉、透明语言、天真的趣闻以及中产阶级的道德规范等并非构成全部真情,”那么, 从当代批评家的角度所看到的这些东西的对立面,如断裂、共时、非理性、反幻觉、自 身反映、形式即内容、道德多元主义等“也不构成全部真情。”(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in The Friday Book:Essays on Other Nonfic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205,p.206,p.1 96,p.203,p.203,p.203,pp.203-204.)如果后现代主义小说仅仅是指前卫的实验主义小 说,似乎失之偏颇,它同时也应包括情节引人入胜、雅俗共赏的作品。在这方面,埃柯 的《玫瑰之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该小说讲述了14世纪初意大利北部一所修道院 七天里发生的一连串谋杀事件,叙述者阿多索是个见习修士,他的导师威廉是个福尔摩 斯式的人物,能通过表面上相互没有联系的现象推断出事情的真相,从蛛丝马迹中发现 真正的罪犯。小说构思奇妙、悬念丛生,谋篇布局周密完备,情节发展环环相扣,是一 部非常好看的书,曾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
《玫瑰之名》与《迷失在开心馆》等“元小说”显然大不相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更确切地说,是一部侦探小说。将其视作后现代主义小说,有何依据?埃柯在《玫瑰之 名》的“附言”中专门就后现代主义进行论述。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与传统决 裂,并非要埋葬或摧毁过去;相反,它“承认过去”,“重访过去”。但它毕竟经历过 现代主义阶段,不再那么天真,因此采取了一种反讽的态度。
我将后现代态度比作一位男士,他爱上了一位十分有教养的女士,他知道自己无法对 她说:“我爱你爱得发疯,”因为他心里明白她知道(她心里也明白他知道)巴巴拉·卡 特兰已经说过这些话。不过仍然有一个解决办法。他可以说:“正如巴巴拉·卡特兰所 说,我爱你爱得发疯。”在这一点上,他避免了虚假的天真,也明确表明现在已不可能 天真地说话,然而,他还是对那位女士说了他想说的话,即他爱她,但是他是在失去天 真的年代里爱她。如果那位女士合作,她将依然能接受这爱情的表白。两人都不会有天 真的感觉,两人都将接受过去的挑战,都将接受爱情表白已被人用过的挑战,而过去是 无法根除的;两人将有意识地、开心地玩着反讽的游戏。……但是,两人都将成功地再 次谈情说爱。(注:Umberto Eco,The Name of the Rose,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84,p.531,pp.511-512.)
如果将传统小说来替换“巴巴拉·卡特兰”,后现代主义小说则处于生活在“失去天 真的年代里”的那位男士的位置,它可以接受、运用、模仿、重复过去的现实主义小说 和现代主义小说范式。埃柯的比喻揭示了后现代主义小说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双重编 码(double coding)。巴巴拉·卡特兰曾经认真地说过:“我爱你爱得发疯。”在新的 语境下,通过适当改变表达形式,依然可以重复这句话,并且同样能达到表白爱情的目 的。巴思在《枯竭的文学》一文中曾呼吁小说“形式”要出新,做到与时俱进。《玫瑰 之名》“附言”引用了巴思的《富足的文学》,而巴思的《再探后现代主义》又引用了 埃柯的“附言”。巴思与埃柯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实践者,心心相通,所见略同。许 多后现代主义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借用了大众/传统叙述方式,如传奇、侦探、 科幻小说的叙述方式,同时又不止步于此,形式上有革新,意图或态度不同以往,其结 果是成为兼具通俗性和后现代性的作品。《拉格泰姆时代》、《公众的怒火》、《天秤 星座》等后现代主义小说就属于这一类,很受普通读者喜爱,畅销一时。
“双重编码”与互文性紧密相关。互文性是指话语或文本与其他话语或文本的关系。 埃柯发现:“书总是在谈论其他的书。”(注:Umberto Eco,The Name of the Rose,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84,p.531,pp.511-512.)《玫瑰之名》是一部 关系到其他书籍的书,充分体现了互文性。埃柯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手头 积累的关于中世纪教会的资料,虚构出一个故事。“双重编码”解释了不少后现代主义 小说是戏仿之作的现象: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是对传统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 青蛙王子》的戏仿,巴思称他的《烟草商》、《羊孩贾尔斯》为“模仿小说形式的小说 ”。(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in Malcolm Bradbury ed.,The Novel Today:Contemporary Writers on Modern Fic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72,p.70,p.79,p.75.)《戏说乾隆》与满清王朝 的正史、《大话西游》与《西游记》之间也存在显而易见的互文关系,前者从后者衍生 而来,对后者既模仿,又改造,既复制,又替换。
“双重编码”的观点意味着作家和读者是处于新的语境中,都具有后现代意识。福尔 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说:“我生活在罗伯-格里耶和罗兰·巴尔特的时代;如果 这是一部小说,它不可能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注: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 的女人》,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福尔斯作为小说人物闯入 故事当中,并为小说安排了三种不同的结局。读者对此并不反感,而是乐于参与作品的 创作。同样,读者阅读《玫瑰之名》时,一方面并不“天真地”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另 一方面又被其所吸引,依然手不释卷。后现代主义小说依然有真实,依然有意义,虽然 读者意识到这是虚构的真实、虚构的意义,但它依然是一种真实,依然是一种意义。作 者和读者“意识到我们过去的经历和目前的位置”,(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in Malcolm Bradbury ed.,The Novel Today:Contemporary Writers on Modern Fic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72,p.70,p.79,p.75.)彼此心照不宣,共同构建一种新型的“超现实”(hyperreality)。
如果我们承认“双重编码”中的两种编码同样有效,后现代主义小说就不一定都是“ 无意义”、“无深度”的作品,其模仿也不一定必须带有滑稽成分。《法国中尉的女人 》讨论偶然与必然、选择与命运等一系列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很有深度,对狄更斯、哈代文体的模仿,成功营造出维多利亚时代的氛围与情趣。后现代主义小说也不一定必须排斥完整的情节。精巧曲折的情节是产生阅读愉悦的源泉,已被证明是吸引普通读者的有效手段。巴思向来看重小说的愉悦功能,主张后现代主义小说并不是少数醉心于高雅艺术的精英才能欣赏的艺术,而是能够超越纯文学或精英文学与地摊文学之间的对立的艺术;小说家“应该”跳出专家的小圈子,去“接触和愉悦”更多的读者,因为小说的历史根基“植根于中产阶级的通俗文化之中”。(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in The Friday Book:Essays on Other Nonfic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205,p.206,p.196,p.203,p.203,p.203,pp.203-204.)巴思把后现代主义小说比作爵士乐或古典音乐,经得起反复聆听、揣摩玩味,而每听一次,“可以发现许多第一遍听时没有听出来的东西;但是第一遍应该动听迷人,能让听者喜欢回放。”(注: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in The Friday Book:Essays on Other Nonfic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205,p.206,p.196,p.203,p.203,p.203,pp.203-204.)埃柯曾 在“附言”中援引巴思的这些论述,表明他认为自己的《玫瑰之名》符合巴思心目中的 后现代主义小说之标准。
胡全生在《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后记”中说:“我没有面面俱到地 讨论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述结构,而是择其最为突出、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叙述特 征进行讨论。”(注: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6,16,11,132-134,128,110、108、93,272页。)他未能深入讨论的 一面就是具有通俗化倾向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述特征。我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在此 作一些补充,以引起讨论,就教于大方。
“后现代主义”这个词80年代曾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后来因为广为使用,泛滥成灾, 几乎变得“毫无意义”(meaningless)。(注:John Barth,“Postmodernism Revisited ,”in Further Fridays & Essays,Lectures,and Other Nonfiction:1984-94,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5,p.113,p.120.)2002年一年中有两部关于后现代主义 小说的论著问世,这并非表明后现代主义的回归。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 斯图加特就已举办过“后现代主义的终结”的学术研讨会。(注:John Barth,“Postmodernism Revisited,”in Further Fridays & Essays,Lectures,and Other Nonfiction:1984-94,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5,p.113,p.120.)新世纪 伊始,后现代主义小说风头已过,现在尘埃落定,可以对其是非功过予以评说了。不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理解上还存在偏 差。因此,后现代主义小说这一领域还值得我们去继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