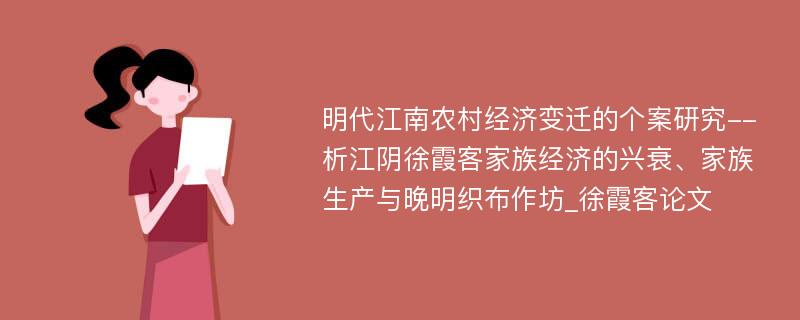
明代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江阴徐霞客家族经济兴衰、分家析产及明末织布作坊诸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家析产论文,江阴论文,经济论文,探析论文,明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6)04-0088-10
据《梧塍徐氏宗谱》所载,[1]江阴梧塍徐氏家族为北宋末年开封府尹徐锢之后,因金兵南侵,于建炎四年(1130)扈驾迁居浙江,其子孙散居荆溪(今江苏宜兴)、云间(今上海松江)、琴川(今江苏常熟)一带。元代时其中一支卜居江阴县西顺乡梧塍里(今江阴县祝塘乡大宅里),称“江阴梧塍徐氏”。有元一代,梧塍徐氏家族出于民族之义,连续几世避世隐居、“乐道不仕”①,以耕读传家、增殖田亩为归,“身修家齐,生业寝广”②。明代时,徐氏家族曾出过解元(如徐泰,第十一世)、经魁(如徐元献,第十二世)之类科场明星,也有过州守、通判、鸿胪寺主簿等官宦,著名的“晴山堂石刻”(见上海古籍版《徐霞客游记》[2]的“附编·石刻”部分)收录了许多反映明代显宦名士与该族往来的文墨,至明末还孕育出了一位杰出的旅游探险家、地理学家、游记文学怪杰徐霞客……这是一个名震江南的明代望族,也是一个显赫一时的土地大族。这样一个家族所经历的历史变迁自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本文选择该家族在明代发生的经济变迁个案为对象,力图作出具有实证意义的微观研究,并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为方便起见,本文在叙述时以徐霞客家族的直系成员为主。
一、一个土地大族的兴衰过程
从元代时的第五世千十一,至明末第十六世徐霞客及至清初其孙徐建极一代,江阴梧塍徐氏家族经济经历了初创、兴盛、中衰、没落多个阶段。如将有元一代徐氏家族经济划为初创阶段,则第九世徐麒(1361-1445)至第十三世徐经(1473年-1507)可称为兴盛阶段;而此后至第十五世徐有勉(1545-1604年)、王孺人(1546-1625)夫妇时可称为中衰阶段;又此后为没落阶段。
从第九世徐麒至第十三世徐经,是徐霞客家族由“身修家齐,生业寝广”之初创,进入到“膏腴连延,货泉流溢”③之兴盛阶段,大致在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十四世纪中至十六世纪初)。徐麒是梧塍徐氏家族家业走向兴盛的关键人物。在明初休养生息、鼓励垦殖的政策之下,徐麒精心“经画家务,赀产日饶裕”。④后以学行获荐、奉诏使蜀,事竣辞归时所提理由就是“家赋浩繁,难于遥理”。辞归后,徐麒被“推长郡赋”,任郡中的粮(赋)长。由此,徐氏家族产业更臻丰盈,“辟畦连阡,原田每每,储橐益广”。⑤据有关传志所记,徐麒时徐氏家族的田产有“若千顷”,⑥即便是虚估,这在人丁较旺、土地不广的江南也是十分惊人的。第十世徐忞(1393-1475)时保持发展增殖之势,“家益裕,族益大,赀累巨万”。⑦人或称其与二弟徐悆“皆称素封”、富类封君,其庶出之三弟徐应经过30年“辟土殖产”,家产亦得“与二兄埒,名行亦相颉颃”。⑧至徐忞之子第十一世徐颐(1422-1483)、徐泰、徐坤兄弟时,徐颐亦曾有辞官归里、治产奉亲故事。他“益勤俭治生业,增产拓地,殆无虚岁”,并为卒于荆门州守任的二弟徐泰治丧教子,为幼弟徐坤理家政、“俾勿堕业”,⑨可见田产又有所拓殖。徐颐生子徐元献(1455-1483)、徐元寿,是为徐霞客家族第十二世。虽因徐元献早卒(仅得年28岁),该世于田产只是维持而已,但从时人对徐衍芳子徐经家产“膏腴连延,货泉流溢”、“大厦千间,金珠委地”⑩的记述看,其时徐氏家族仍不负“世以高赀为江南鼎甲”之名。(11)
然而,正是从第十三世徐经开始(大致在弘治末年至正德初年间),徐氏家族经济进入了中衰阶段。这主要反映在徐经夫人杨氏在他去世7年后(1514)所书分家析产文书中。从文书中可见,徐经家当时分给3个儿子的家产计“官、民田地三百七十七顷九十三亩二分八厘,官山十亩,民山五顷三十三亩七分四厘八毫,又滩八十六亩八分四厘七毫,又芦场四顷四十三亩三厘六毫,草场三十二亩,鱼池大小六所”,并有两个女儿的妆奁田计12顷、祭祀田3顷等,各种田、山、滩、场总计约403.9924顷(合40399.24亩),由于已经过数世财产分割,其内涵远大于明初徐麒时。但是,正如杨氏在文书中所写,“不幸夫故,子女皆幼,门户无人,氏竭力撑持,保守祖业”,以上所列家产均为杨氏竭力撑持“保守”而得,与以往数世增产拓地之势已是不同;而且,文书中还提到“近年门户重大,人口众多,使费烦难,以致揭债,银钱米麦不能积蓄盈余,无以标拨”,一个在初承家业时还是膏腴连延、货泉流溢的大家族,只过了20多年,竟然会“使费烦难,以致揭债”,其中衰迹象已然显露。(12)此后至第十四世徐治、徐洽(1507-1564,徐霞客曾祖父)、徐沾兄弟时,或于举业屡厄屡试,或曾以年幼而受欺侮、一度“产业被乾没过半”,(13)兄弟间幸能协谋共虑,方使家业“赖以不堕”。(14)徐霞客的祖父辈即第十五世共有兄弟5人,其祖父徐衍芳(生卒失考,约当正、嘉、隆、万之时)为长子,诸兄弟有的子女林立,又以“守先世之业足矣”为念,(15)不再增殖土地,传至十六世即徐霞客父辈6兄弟时,一分再分,窘境可知。徐霞客父亲徐有勉(1545-1604)在6兄弟中排名第三,诸兄弟中有多位不是因故只获得“一椽数亩”而“绝无多寡之嫌”,(16)就是虽“以遍蓬对泣,兴构西堂”却“不厌硗瘠”,赖兄长之助得以“业稍起”。(17)而徐有勉分得之产“处东偏之旷土”,人更直称其“家已中落”。(18)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家道已经中落的景况下,这个曾号称“赀拟封君”的大族出了几位以棉纺织业撑持门户的女子。一位就是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1546-1625),她经营的棉布作坊在江阴、苏州一带颇为有名。另一位是徐霞客的五婶苗孺人,她“果尔椎髻,操作纫缉,不少休纾,堂前朝夕谋己”。(19)她们襄助丈夫甚至独力经画家业,一度使家业“竟复旧观”,(20)或“渐殷殷然”。(21)
但是,女子纺织只是昔日这个江南土地大族的回光返照而已,此后就日趋没落了。十七世徐霞客(1587-1641)典地出游,于家族无些介之入,而有持久之耗;至第十九世其孙辈徐建极(1634-1693)兄弟时,更是“家资衰落”、(22)“田庐不及中人之产”(23)了。据宗谱所见及笔者的实地了解,徐霞客家族到清代已混同于一般农户,只有某些分支或可跻入后世所谓之“富农”。
通过对江阴梧塍徐霞客家族盛衰变迁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它随着明王朝的建立而走向兴盛,又随着明王朝的动荡崩溃而走向衰落。
二、人口增殖与分家析产情况
江阴梧塍徐霞客家族的分家析产情况饶有趣味,其中诸如析产原则、分配方式、分家析产概况及其对经济变迁的影响等问题,都值得人们关注。梧塍徐氏宗谱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记载。
要谈徐霞客家族分家析产问题,还是应当先看看对其有直接影响的家族人口情况。按照以徐霞客直系祖先为主的办法,从明初第九世徐麒到明末第十八世即徐霞客子辈之间10代人的人口情况大体是这样的:第九世徐麒,单传;徐麒育有4子,即忞、悆、应、懋,是为第十世;徐忞育3子,即颐、泰、坤,是为第十一世;徐颐育2子2女,2子即元献、元寿,是为第十二世;徐元献育有1子,即徐经,是为第十三世;徐经育有3子2女,3子即治、洽、沾,是为第十四世;徐洽育有5子2女,5子即徐霞客祖父衍芳及衍嘉、衍成、衍禧、衍厚,是为第十五世;徐霞客父亲徐有勉共兄弟6人,即有开、有造、有勉、有及、有登、有敬,是为第十六世;徐有勉育有3子1女,3子即弘祚、弘祖(即徐霞客)、弘禔,是为第十七世;徐霞客育有4子1女,4子即屺、岘、岣、(李)寄(但李寄系霞客妾周氏改嫁李氏后出生),是为第十八世。
从中可见,江阴徐霞客家族自徐麒起不断繁殖扩大,其中第九世徐麒至第十一世、第十三世徐经至第十八世两段发展奇快。前一段(洪武中至天顺年间)连续两代以4、3倍之数扩大;后一段(弘治初年至明末清初)更为惊人,育有3子1女的徐霞客父亲徐有勉算是生育最少的了,徐霞客曾祖父徐洽、祖父徐衍芳竟分别生育5子2女和6子,而且连续5代直系祖的平均生育数在5.4人(生子平均数4.2人)!由于每一代的财产都要经过子女们的共同分割,这种家族人口增长的情况也就必然会成为影响徐霞客家族经济变迁的重要因素。
那么,江阴徐霞客家族是怎样进行财产分割的呢?
根据梧塍徐氏宗谱提供的材料,其家族分家析产主要遵行以下几个原则:
(1)嫡庶有别(若数子同为庶出,则其中长幼亦有别)。比如,第九世徐麒有四子,但在分家析产时,庶出之第四子徐应在二位兄长皆“赀拟封君”的同时,却只能“茕然依母氏居东庄别业,田庐无几”,以至其一度“拮据卒瘏,靡昼靡夜”,生活很窘迫,过了几30年“辟地崇屋”,才得以“殖产与二兄埒”。(24)这里我们看到了析产时的嫡庶之别,也看到了同为庶出时的长幼之别。当然,个别情况下也出现例外。如徐霞客共兄弟三人,幼弟为庶出,徐有勉临终前曾嘱其妻王孺人曰,“季(指第三子弘禔),吾孽也,授产勿埒两儿”,王孺人当时虽表示同意,实际析产时却是“鼎分田庐者三,其平如砥”。(25)很显然,徐有勉“季,吾孽也,授产勿埒两儿”之语反映的是嫡庶有分的一般析产原则,而“鼎分田庐”则是王孺人分家析产时在纲常伦理之下做出礼让的体现。
(2)嫡子均分。即在诸嫡子中实行财产均分。杨氏为其三子分家析产是一个典型事例。杨氏在分家析产文书中一一开列了家中各处庄屋、船坊、池塘、田亩、滩荡、山冈、草场,以及座船、耕牛、农具、轿马、驴骡、书画、家什,乃至各种管账、催账、力农、杂用“家人”,规定一切“俱各三分均分”。还写明“写立拨付,一样三本,各执为照”。又规定:“既分之后,各照受分官、民田地办粮当差,毋得抵捱;及有重大差使,如粮长之役,三分均当协办。”杨氏所称“三子皆吾骨肉,标拨至公,无有偏向”,则明确界定了“三分均分”是在三子均为嫡出时的析产原则。(26)这种嫡子均分原则在有明一代徐霞客家族的分家析产中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分家析产时嫡长子通常规定有优先选择权,徐经3子析产时杨氏便作文字规定,称“祖居一所、房屋基地、船坊、市屋、池塘,无改旧规,理宜长子治分受”,但在明代后期似乎已有所变化,从第十五世、第十六世(约当嘉、隆、万年间)徐氏家族连续两代的析产情况即有所反映。
(3)男女迥异。女儿在财产分配中的继承权利几乎被剥夺。在第十三世徐经夫人杨氏手书的分家析产文书中写得很明白,两个女儿除了办理婚嫁时的妆奁补贴外,不再另有与3个儿子分享各种家产的权利。当时长女因出嫁后“妆奁不敷”,获贴田4顷;次女待嫁,妆奁未办,获贴田八顷,以备日后置办出阁时使用。(27)这数顷之额与徐经3个儿子各分得126顷多的田产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充分表明中国传统社会里男女性别歧视之森严。这些妆奁田是随本人出嫁而转移到夫家的,所以一旦分配,也就不再属于本家族了,这就是财产分配重男轻女的奥秘所在。
综上所述,徐霞客家族的分家析产(或曰财产继承)机制以嫡庶有别、嫡子均分和男女迥异为特点和原则,其中又以嫡子均分为主体。而学术界多为笼统称“战国秦汉以后,诸子均分制度遂成为(我国)家族制度中广为遵循的传统规约”、[3]“各阶层皆采用诸子财产均分”,[4](P151)现在看来,这一提法至少对明代江阴梧塍徐霞客家族而言很值得推敲。当然,强调“嫡庶有别”的存在,在总体上并未改变中国分家析产时的“均分”色彩,与日本及西方国家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仍存在鲜明差别,所不同的在于它还反映了宗法伦理的等级秩序在析产中的存在,正如男女有别一样。
关于徐霞客家族分家析产的方式,前后出现过多种:
第一种方式,由父母事先作好清丈、权衡,然后形成析产方案、付诸实施。上述第九世徐麒、第十三世徐经夫人杨氏、第十四世徐洽等的为子析产即属此情况,又以杨氏析产文书最为典型。这一种析产方式往往具有严厉的权威性,如徐经夫人杨氏在其手书析产文书中就强调:“吾身殁之后,如有言称不均,以起争端者,以不肖论。”(28)这就具有了族规家法式的强制色彩。
另一种方式,事先配定析产份额,以抓阄而不是以父母决定份额归属的方式来析产。如上述第十六世徐有勉兄弟在父亲去世后的“以射覆(抓阄)法析产”。这种析产方式具有与前一种方式不同的特点:不仅注重数量的平均性,还注重机会的公平性。而且,这种析产方式的强制色彩淡化了许多,当徐有勉在“一再得正室”的情况下“牢让于伯兄”时,就显得比前一种方式多一点人情味和弹性。抓阄析产方式多在父母去世后所采用,从时间上看出现在明代后期。
还有一种析产方式是赠(赐)予式的,作为对析产后所出现意外情况的补充。第十六世徐有造原以出继叔父徐衍成而未能获析产份额,但又“雄资先为诸叔父所分析”,结果“于父于叔两无所授”。在此情况下,其祖父徐洽便“怜而赐之一椽半亩”。(29)虽然难与兄弟们相比,却可解决衣食之需。这种赠予方式所得虽非父辈之产,但依然属于家族财产(留给祖辈的赡老之田)。
分家析产方式可以因为情况特殊或时代推移发生变化,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在上文所概括的几个特点方面还是相同的。
在考察了分家析产的特点与方式后,我们不妨来估算一下明中期即十四世徐洽(徐经之次子)至明末十八世即徐霞客之子的财产分割及经济衰变状况。据徐经夫人杨氏手书的分家析产文书,徐洽分得官、民田及山、滩、场共12966.296亩,并畅岐庄屋、鱼池二个等;(30)徐洽育有5子2女,均嫡出,扣去给2个女儿的妆奁田后,按嫡子均分原则,又按家产“赖以不堕”的估数,徐霞客祖父徐衍芳可得官、民田及山、滩、场共约2500亩及若干房产;第十六世有兄弟6人,也均为嫡出,姑且按“守先世之业”的乐观估数5人均分(徐有造因出继未参与析产),徐霞客父亲徐有勉所得连同山、滩、场在内大约是500亩,与乃祖相比,称其“家已中落”一点不为过。虽徐有勉夫妇“拮据修息,竟复旧观”,(31)家业稍得扩充,但家中曾屡遭变故,恐亦有限;徐有勉育有3子1女,虽有嫡庶,但徐霞客母亲王孺人一视同仁,一律均分析产,此时徐霞客分得的家产大抵有200多亩。徐霞客出游时耗资不少,还曾有典地之举,(32)即便其母王孺人随其同居,稍得贴补,其家产仍难有增殖,如果为子析产,其4子1女,其中3子参与均分,每户不足百亩之数。徐霞客侄孙徐升自称“忆昔受分,田逾百亩”,(33)其数大致相合,又因其祖父徐弘祚(徐霞客长兄)不仕不游、常年经理田亩,境况当略优于徐霞客子孙。——这就是徐霞客家族第十八世时“家资衰落”、“田庐不及中人之产”家境的具体写照。
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变迁之影响
为何一个兴盛的土地大族会忽而走向中衰?而且最终又走向没落了呢?似乎有必要考察一下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为在传统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徐霞客家族的经济变迁史上这是一个突出特征。
其一,人口增殖的影响。由于传统宗族传承链作用和分家析产的特点,使人口增殖成为制约徐霞客家族经济变迁的一个直接而基本的因素。从十三世徐经起,徐氏家族中衰时期人口状况的分析看,一个繁荣的家业,终究抗不住连续5代人的爆炸性裂变所造成的财产分割冲击。徐经夫人杨氏关于“近年门户重大、人口众多,使费烦难,以致揭债”的叙述,还只是第十四世分家析产前的情况,其后的析产窘况远较此为甚,从上文的析产估算已可清晰看见。至于第九世徐麒至第十一世徐忞兄弟(洪武中至天顺年间)连续两代以4或3倍之数扩大,却并未造成衰落,其原因除了持续时间不长外,也与分家析产时嫡庶有分、出继者不参与有关。徐麒所育四子忞、悆、应、懋中,应、懋均为庶出,且懋出继他人;而徐忞所育3子颐、泰、坤中,次子泰与幼子坤亦均为庶出,因此使析产造成的影响大为减少。当然,这毕竟只是占析产总体的一小部分,难以改变人口负担造成的巨大影响。此外,从徐霞客家族第十一世徐颐至第十三世徐经两代的析产情况,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反证:徐颐所育2子2女中只有元献是嫡子,徐元献又仅育1子,这样就使其祖孙三代的财产传承十分简明、分割次数与程度很有限,虽然徐元献遭受科场挫折、29岁即病逝,于财产并无增殖,却也并无大影响,以致徐颐与其兄弟所继承的“赀拟素封”的家业传到徐经时仍是“膏腴连延,货泉流溢”,可见人口生育数量多寡、嫡庶比例及性别差异等因素对分家析产及经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
其二,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江阴徐霞客家族经济的变迁来看,影响其盛衰的政治因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官府政策。有一点是明显的,明初休养生息政策给了徐氏家族经济发展的机遇。在徐麒辞荣归里时,曾获朝廷“足国于家,是亦为政”的允准与鼓励,(34)还曾因其义行获蠲免徭役的特许,都是十分典型的事例。但是,国家以及地方官府的政策也会产生相反的作用,比如徐经夫人杨氏在分家析产文书中提及“数十年来水旱荒歉,每每匮乏”的同时,又提到多项“府县差使”,诸如修学、修城等,把它列为令其“多端劳心劳力,不得一日安寝”的困扰因素之一。(35)无疑,当开国初期的宽松政策被繁重加派所取代时,这种困扰就会给乡村经济、甚至一个土地大族造成巨大的伤害。
(2)不测讼狱。从明代徐霞客家族的变迁过程来看,曾经历了一系列不测讼狱的打击,对其家族衰落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其中徐经所遭遇的科场之狱影响最为深远。这就是徐经与江南名士唐寅的“科场行贿案”。弘治十二年(1499),徐经与唐寅同船赴京参加会试,二人或富而有文,或才名显赫,均踌躇满志、意在必得。不料三场考试甫终,户科给事中华昶即参劾主考官程敏政鬻卖试题,事涉徐经、唐寅,结果二人均被收狱拘审。经查,事有出入,二人实并不在录取名单中,但他们曾分别携礼物拜访主考官程敏政为实。最终被告、原告各挨五十大板,程敏政革职,华昶贬官,徐、唐二人也遭削除仕籍、废锢终身、发充县衙书吏的严厉处罚。遭此打击后,三个被告均不服,程敏政疽发而卒;唐寅耻不就吏;徐经作《贲感集》以自明,最后抑郁而死,仅得年三十有五。据此,笔者以为,徐经成为其家族走向中衰的转折点主要应归因此狱,而其后的家族人口剧增则使家族经济的衰落成为不可逆转、并急转直下。而清初徐氏家族被“挂误”于江南“奏销之祸”,(36)以致其愈加衰落、“不及中人之产”,也是突出之例。除此类重大讼狱外,还有各种乡里官司,或“费及百金”以解决风水纠纷,(37)或“讼縻岁月”以清涤恶意中伤,(38)等等,均耗去徐氏家族许多财力,加速了衰变过程。
(3)社会治乱。家族和国家一样,其经济发展需要安定有序的内外环境。明初徐霞客家族经济得以走向兴盛,曾得益于此,而明后期的社会动乱则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宗谱记录了徐氏家族当时遭遇的一系列“盗劫”、“奴变”,其中徐霞客父亲徐有勉便经历过两次。第一次,徐有勉夫妇规复家业、稍见起色,但“未几中盗,避之梁溪”,归家时又因坐骑堕河而致跛一足,此次变故对于徐有勉规复家业的雄心打击颇大。另一次,竟导致徐有勉丧命。他当时正在幼子弘禔所居之田舍,不料竟“为盗困”,致中风而卒,得年六十。(39)王孺人不得不与徐经夫人杨氏时一样独力撑持门户,历时20年之久,然当时家景已远非昔比,其艰难可想而知。此外,徐霞客长子徐屺、徐霞客侄子徐亮工家中于明清鼎革、清兵南进之际亦先后遭“奴变”(指佃户骚乱),徐屺即死于“诸逆奴”之手,(40)徐亮工及其孀居的大嫂家中更是遭到“围基惨杀,焚劫殆尽;一十六人,骨肉灰烬”!(41)这些“奴变”均乘明清鼎革、清兵南下之时发生,内外交攻,其对徐霞客家族伤害之大,足以解释该家族在明末走向衰落以后未能重振的原因。
其三,观念意识与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影响经济发展与变迁的各种非经济因素中,观念意识与社会风气虽然不如人口、政治因素引人注目,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起作用的。这在明代徐霞客家族的经济变迁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在这里我们也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1)传统伦理与习俗。这方面例子俯拾即是。如析产时无论是通常的嫡庶有分,还是王孺人破例的嫡庶同一,其实体现的都是传统伦理,只不过前者重尊卑、后者讲礼让而已。又如徐霞客伯父徐有造因故在析产后只得“一椽半亩”、家境萧然,但他却为了“族有异疾者死,越埋其墓道”、“恐伤先灵”而寝不宁席,不惜“费及百金”开讼打官司,(42)结果维护了虚幻的先灵,却加快了现实的衰变。
(2)非利取向与行为。这与前一点彼此相关,却更直接地影响到经济行为的评价与抉择。不妨以涉及到徐家织布作坊及所代表生产方式属性评价的徐霞客母子为例。徐霞客虽然生活于一个拥有一定规模之织布作坊的大家庭,在其游记中对民间商业活动也多有记述,但本人却并不对工商经营感兴趣,在云南考察时,他见到一位“向以贾游于外”的吴姓商人归而结庐于深山之中,竟感叹“可谓得所讬矣”。(43)商贾非所归,而山水为所绸,其价值取向十分了然。其母亲王孺人虽经营着一个棉布作坊,其实也是个非利之人。有一次,她与长孙徐建极前往青阳(江阴地名)张氏家交涉(当为债务问题),见其家无长物,而夫自拭榻、妇躬纺织,连进茶也不劳仆婢,不由大喜而赞叹之,“竟忘所白事归”。(44)在这里,勤俭美德与经济利益亦取弃立判。
(3)消费观念与风气。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明清江南的奢靡性消费风气研究颇多,[5]其实还有一种消费观念与风气也十分值得关注,即中国传统的“人情消费”。恰恰是这种消费对于徐霞客家族的经济变迁产生了很大影响。徐经之罹祸和王孺人之获誉即为典型之例。徐经作为徐氏家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导致此转折的主因是“科场行贿”之狱。然而宗谱却称因其“富而不施,内外嫉忌”,才导致“竟以场屋飞语,系诏狱落籍”。(45)此语颇耐人寻味,徐经本是因涉嫌“行贿”(即行不当之“施”)入狱的,缘何还称其“不施”呢?言下之意似乎只有一解:“人情消费”不能只对主考官一人,只有广施才能消灾。“人情消费”风气如此之烈令人震惊,而修传作者分析之实在令人服膺。王孺人的例子则与之恰好形成对比,她经营棉布作坊被称为是“积得金钱供布施”,“即家有好布,无与民争利之嫌”。(46)经营棉织作坊不图利益而广作布施,王孺人大得称誉,而其经济行为则因布施消费(一种道德义举,也是一种特殊“人情消费”)而几乎成了伦理行为。徐霞客家族因“富而不施”走向中衰,又以“积钱布施”难以为继,徐氏家族经济在一个必须抉择的时刻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其衰变之势最终未能挽回,王孺人去世后其棉织作坊亦不复见载了。
在种种传统观念及相关风气习俗的影响下,经济行为抹上了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这成为徐霞客家族经济衰变的诱因,而且也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徐霞客家族的经济变迁几乎时时处处被非经济因素牵着鼻子,由其摆布。而分析这些非经济因素,却都属于传统的范畴,能阻滞却不可能推进经济的变革。一个典型的乡村土地大族,处在当时最具活力的江南地区,却无法找到自我突破的路径。
四、徐霞客母亲织布作坊研究
数十年来,在有关徐霞客的研究中,一向有一个“资本主义萌芽”情结。(47)分析起来,这大致涉及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徐霞客母亲织布作坊的性质问题,二是《徐霞客游记》有无“萌芽”记载的问题,三是与时代关系问题。笔者以为,游记中有无“萌芽”记载比较好判断,因为其概念和地域都有边界,难以无中生有;与时代关系问题则主要是一种推论,结论是否成立有赖于相关研究进程。三个层面中,对徐霞客母亲织布作坊性质的探讨才是最关键的,而这也是考察徐霞客家族经济及其结构变迁不可回避的重点。
考论徐霞客母亲织布作坊之性质,必须分析其产生原因。上文已进行了多方面论证,表明徐霞客家族经济衰变主要是由一系列传统的非经济因素导致并加深的。徐霞客母亲的织布作坊正是这种背景的产物,是在徐有勉去世后“久支门户,课夕以继日,缩入以待出”(48)的窘境中被迫产生的,而不是在“拮据修息,竟复旧观”时的主动抉择,徐霞客五婶苗孺人的躬事棉纺织也大抵如此。当然许多人还称赞这是王孺人性勤朴而“故好艺植,好纺织”,(49)归因于道德因素,等等。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应当是货币经济排挤人身依附关系,应当是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决定其产生时机、方向与性质,而导致徐霞客母亲的织布作坊产生的动因却是诸多传统的非经济因素,这二者似乎难以联系到一起。歪打有时能够正着,南辕却似乎是不可能北辙的。
再从徐霞客母亲织布作坊中劳动者的身份和生产管理方式来进行考察。关于徐家织布作坊的劳动者身份,我们找到的记载大致有以下一些:“王孺人久支门户,课夕以继日,缩入以待出,凡饘酡、酒醴、塗茨、朴斲以及鸡埘、牛宫之类,诸僮婢皆凛凛受成于母。母无他好,好习田妇织,又好植篱豆……”;(50)“机声轧轧频呼婢,篱下离离欲曙天”;(51)“母(王孺人)性恭俭,好率婢子鸣机杼,及广艺秋藤,架棚而引之,令绿荫满堂”;(52)“孺人织布精好,轻弱如蝉翼,市者辄能辨识之。手植篱豆,秋实累累,日课卯孙、诸婢于绿荫中,命曰‘碧云龛’”;(53)“余尝观《秋圃晨机图》,问机上人,仲子(徐霞客)母也。卯孙在侧。卯孙,仲子子也。亡何登堂寿母,篱豆未花,是若母织于斯而子读于斯,呼长命藤非耶?”(54)
这些资料均见于《秋圃晨机图》诗文序记,为徐霞客亲自请人题写、镌刻的(著名的“晴山堂石刻”),当属可信。从中可见,徐霞客母亲本人是“机上人”;其他参与织布者是“婢子”、“诸婢”;在各种家务中,劳动者身份都是“诸僮婢”。还可见到,徐霞客母亲与“诸僮婢”、“婢子”的关系是“率”、“呼”与“凛凛受成”的关系,也就是家内役使关系。学术界有称战国、汉代存在“萌芽”的,虽然因其不考虑相关条件而受到质疑,但还是能在“雇佣劳动”上找到一些材料,而在徐霞客母亲的织布作坊中,显然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任何痕迹。在徐霞客家族的传统南辕之下,并无新兴“萌芽”之北辙。
根据上面所引述的资料及考证,徐霞客母亲织布作坊的技术、分工与规模问题也大致可以获得解决。关于织布技术,资料称是“鸣机杼”、“机声轧轧”,还有资料进一步称是“弄杼轧轧”,(55)可以判断出徐霞客母亲和“婢子”们所用的还是原始的手工织机。这种手工织机的特点是产品质量高但生产效率不高,符合家庭手工作坊技术水平的特点。关于分工,徐氏织布作坊内的分工情况也很简单,一是徐霞客母亲“率婢子”、“频呼婢”、“课诸婢”,即徐霞客母亲在躬织之外又管理、督促“婢子”;同时,按常理生产中总有上下手之分,即织布和辅助之分;此外,织出之布除去自用外,要“持向吴门货吴侬”,(56)到苏州一带去卖,通常这出头露面的事是由男仆担当的。归结起来也就是管理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中的上手与下手、生产者与外销者三种最简单的分工,而且分工未必是清晰的,比如徐霞客母亲就是一身二任,既是管理者,又是生产者。关于规模问题,既然上文已考明织布作坊中劳动者身份是家内成员与婢仆,则根据当时家中女性成员有徐霞客母亲及四媳(三子中仅徐霞客有侧室,一为金氏,另一为周氏,后者方孕即被出,故只计1人。其原配许氏早逝,后续娶罗氏,计1人。女儿出嫁早,不计)、一些婢女(由于当时“家已中落”,徐霞客母亲又性喜俭朴,还要剔去男仆数,每家也就2~3人,合计起来当不超过10人),再计及儿媳中或须哺育子女、织布亦有一定分工等因素,其织机数当不可能超过10架。从技术、分工和规模来看,徐霞客母亲的家庭织布业还是称“作坊”为宜,尚称不上曾有学者提出过的“织布工场”。
判断徐霞客母亲织布作坊是属于具有近代意义的商品生产、有“萌芽”性质,或是仍为自然经济范畴的小商品生产,我们还必须从产品流通与消费的角度进行考察。上文曾经分析了徐霞客母亲及其织布作坊因“积得金钱供布施”而广受赞誉,可以看出“布施”是其产品消费的一个方面。但是必须指出,这并不是其消费最基本的方面,可以通过对描绘徐霞客母亲的《秋圃晨机图》及其相关题记诗文来分析。这幅图中有“圃”有“机”,“圃”指豆棚,“机”指织机。对于徐霞客母亲植豆事圃,根据当时人的描绘,是典型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画面:“好植篱豆,雍溉疏剪,绞绳插架,……每当藩实累累,则采集盈筐,分饷诸亲族,余即以啖卯孙”(57),事实很清楚。但对其织布经济,因其“持向吴门货吴侬”并在市场上受欢迎之故,人们往往会将它与植豆事圃区别开来,以为已经属于新的经济范畴。笔者认为,产品的流通还是要与消费视为整体,徐霞客母亲曾自称:“吾贸布以易糈,摘豆以佐酒,卯孙从旁覆诵句读以挑汝欢:吾母子复何求哉?”(58)既然布匹到市场上主要是被用作换口粮的,是被用作维持大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其积余利润(“积得金钱”)又是供“布施”之用,那么只能说它依然属于自给自足性质,在商品经济发展史上依然是处于传统的小商品经济范畴。也就是说,“贸布以易糈”和“摘豆以佐酒”被并提非出偶然,乃属同样性质。
没有逐利动机、由非经济因素导致发生,又不具备雇佣关系特征和相应物质生产力条件,而且产品的流通消费也具有鲜明的小商品经济色彩,要从这样的织布经济中得出“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显然难以成立。对于这样的认定还是以谨慎为妥。事实上,虽然太湖流域在明清时期确实存在着零星的“萌芽”,但阻力重重、程度微弱,影响是很小的。[6](P.392)而且,有研究认为棉纺织业并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7]
综上所述,徐霞客家族作为明代江南乡村一个望族和典型的土地大族,其经济变迁特点颇值得关注。其一,它的兴衰变迁与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密切相关,曾经得益于此,其后又更多地受其伤害并致衰落。其二,它的经济变迁陷于传统伦理与经济功利的两难之境,难以形成变革突破的主观动力。徐经的“富而不施”罹祸与徐霞客母亲的“积得金钱供布施”得誉反差鲜明,不能仅用简单的道德哲思去解释。其三,它的人口增殖以及传统分家析产规则造成的财产不胜分割不容忽视。不仅是人口生育的数量,而且是嫡庶之比也影响着家族产业的分割与衰变进程。究竟如何概括中国传统分家析产原则的演变,有可能要做些进一步的考订和分析。其四,徐霞客母亲织布作坊本质上仍属于小商品经济范畴,是妇女涉入商品经济活动的尝试。与其说这是一种自觉的经济行为,还不如说这是一种勤劳俭朴的伦理道德行为。这对于评价明清棉纺织业的水平与性质具有参考意义。
[收稿日期]2005-10-23
注释:
①《亨一小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3《先世小传》。
②《伯三小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3《先世小传》。
③(明)文璧:《〈贲感集〉序》,《梧塍徐氏宗谱》卷57《题赠序记》。
④(明)曹鼐:《本中征君墓表》,《宗谱》卷54《墓表》。
⑤(明)陈敬宗:《明故徐征君墓志铭》,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13页。
⑥《征君心远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3《旧传辑略》。
⑦(明)胡濙:《送义士徐景南、景州谢恩还乡序》,《梧塍徐氏宗谱》卷57《题赠序记》。
⑧《处士松雪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3《旧传辑略》。
⑨(明)李东阳:《明故中书舍人徐君墓铭》,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26页。
⑩《春元西坞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3《旧传辑略》。
(11)(明)文璧:《〈贲感集〉序》,《梧塍徐氏宗谱》卷57《题赠序记》。
(12)《杨氏夫人手书分拨》,《梧塍徐氏宗谱》卷56《内行传序》。
(13)《隐君南塍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3《旧传辑略》。
(14)(明)徐材:《鸿胪云岐公行状》,《梧塍徐氏宗谱》卷54《行述》。
(15)《上舍璜拙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3《旧传辑略》。
(16)佚名:《提举养庵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5《传文》。
(17)(明)叶茂才:《渐庵徐公墓志铭》,《宗谱》卷54《墓志铭》。
(18)(明)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53页。
(19)(明)叶茂才:《渐庵徐公墓志铭》,《宗谱》卷54《墓志铭》。
(20)(明)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53页。
(21)(明)缪诜:《廪彦范中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5《传文》。
(22)(明)缪诜:《廪彦范中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5《传文》。
(23)(清)薛云蒸:《庠士君铨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5《传文》。
(24)(明)薛章宪:《徐母包太孺人墓志铭》,《梧塍徐氏宗谱》卷54《墓志铭》。
(25)(明)陈继儒:《豫庵徐公暨配王孺人传》,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57页。
(26)《杨氏夫人手书分拨》,《梧塍徐氏宗谱》卷56《内行传序》。
(27)《杨氏夫人手书分拨》,《梧塍徐氏宗谱》卷56《内行传序》。
(28)《杨氏夫人手书分拨》,《梧塍徐氏宗谱》卷56《内行传序》。
(29)佚名:《提举养庵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5《传文》。
(30)《杨氏夫人手书分拨》,《梧塍徐氏宗谱》卷56《内行传序》。
(31)(明)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53页。
(32)(明)徐霞客:《楚游日记》,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205页。
(33)(清)徐升:《君铨公豫止自述》,《梧塍徐氏宗谱》卷58《家集》。
(34)(明)陈敬宗:《明故徐征君墓志铭》,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14页。
(35)《杨氏夫人手书分拨》,《梧塍徐氏宗谱》卷56《内行传序》。
(36)(清)缪诜:《廪彦范中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5《传文》。
(37)佚名:《提举养庵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5《传文》。
(38)(明)叶茂才:《渐庵徐公墓志铭》,《宗谱》卷54《墓志铭》。
(39)(明)陈继儒:《豫庵徐公暨配王孺人传》,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57页。
(40)(清)缪诜:《廪彦范中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5《传文》。
(41)(清)徐升:《君铨公豫止自述》,《梧塍徐氏宗谱》卷58《家集》。
(42)佚名:《提举养庵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5《传文》。
(43)(明)徐霞客:《滇游日记四》,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772页。
(44)(明)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54页。
(45)《春元西坞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3《旧传辑略》。
(46)(明)黄克缵:《秋圃晨机为徐霞客母太孺人赋》,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46页。
(47)参见拙作:《“徐霞客与资本主义萌芽有关”说质疑——关于徐霞客家世研究的一点商榷》,载于《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又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1年第9期。
(48)(明)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35页。
(49)(明)李维桢:《秋圃晨机图引》,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39页。
(50)(明)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35页。
(51)(明)姜逢元:《秋圃晨机为徐太君赋》,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44页。
(52)(明)张大复:《秋圃晨机图记》,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37页。
(53)(明)陈继儒:《豫庵徐公暨配王孺人传》,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57页。
(54)(明)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63页。
(55)(明)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35、1236页。
(56)(明)何乔远:《题秋圃晨机图》,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47页。
(57)(明)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35页。
(58)(明)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褚、吴本《徐霞客游记》第1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