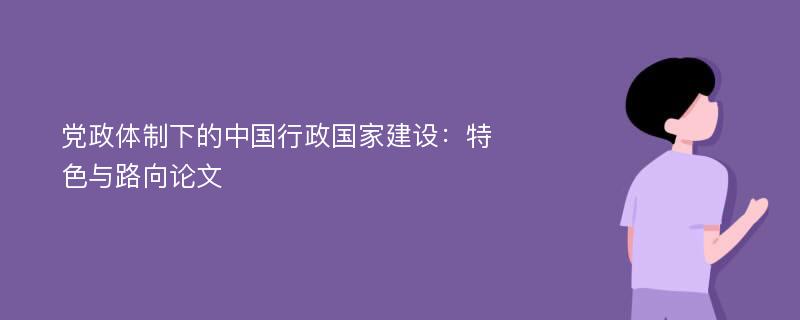
党政体制下的中国行政国家建设: 特色与路向
颜昌武
[摘 要] 党政体制作为理解中国行政生态的一个框架性概念,对中国行政国家建设具有关键性的情景预设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核心,内嵌于国家权力体系中,并与之形成“两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形态。党政体制下的中国行政国家建设以公共权力的制度化为基本路径,以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为组织载体,充分彰显了使命型政党的政治担当与政治智慧,也充分展现了理性官僚制的科层特色与专业优势。
[关键词] 党政体制; 行政国家; 制度建设; 理性官僚制
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保持了长期的总体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携手前行,创造了现代化发展的中国奇迹,这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提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注]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的著名论断形成了强烈对比。一些学者惊叹于中国的现代化奇迹,提出种种理论解释,以期破解“中国发展之谜”或“中国成功之谜”;[注] 参见俞可平等:《中国的治理变迁(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有人惊呼“中国威胁论”;[注] 参见吴飞:《流动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威胁论”的缘起与演变》,《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也有人高喊“中国崩溃论”。[注] 参见刘杉:《2015年以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两个热点——“中国崩溃论”和对华政策反思》,《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在各种声音中,凸显出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二是中国崛起超出了西方既有理论的解释范围,简单套用西方话语体系,不足以理解中国崛起。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引入“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概念,通过将其置于党政体制这一独特的制度框架内,梳理中国行政体系的发展路径与组织特征,透视中国奇迹所蕴藏的行政逻辑及其制度优势。
所谓行政国家,是与立法国家或司法国家相对应的一种国家形态,本质上是关于国家角色的一种积极与能动的定位,具体表现为“公共部门使用了庞大的社会资源;公共行政管理者在当代政府运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总体上处于政治的核心地位;国家通过行政行为来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并达成目标”。[注] [美]罗森布鲁姆等著,张成福等译:《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在现代社会,行政是“行动中的政府”,凸显为“政府中最显眼的部分”,[注] Wilson Woodrow,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2, No.2, 1887. 国家必须有效“行”政方能显示其力量,这就有了对行政国家的呼唤。[注] 本文用“行政国家”这样的字眼来表述一种国家形态时,主要是想强调其国家行为的重心落在行政系统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立法或司法等其他系统的重要性就可以被忽略。
就其基本蕴涵而言,行政国家首先是一种“政府国家”,相对于市场和社会,国家的力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能影响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得失安危。行政国家也是一种“执行国家”,相对于国家权力机构的其他组成部分,行政权力不断扩充,屡屡入侵传统上属于立法或司法的领地,行政分支凸显为“现代政府的核心”。[注] [美]沃尔多著:《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颜昌武、马骏编译:《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行政国家还是一种“官僚国家”,相对于选任官员或委任官员,以专业性著称的技术官僚体系在政府中占据支配性地位。[注] 更多对行政国家内涵的探讨,参见颜昌武:《行政国家: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蕴涵》,《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3期;颜昌武、林木子:《行政国家的兴起及其合法性危机》,《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2期。
实践民俗学是面向生活实践和交流实践的民俗学,而不仅是将民俗学知识用于指导实践,或者民俗学者主动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实践民俗学首先要承认,民俗是民众的生活实践,民众的生活实践又经常表现为琐碎的生活事件。正如费特曼所言,“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事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个具体社会价值观的隐喻”[注][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9页。。当代民俗学“朝向当下”和迈向日常生活的学术实践,需要从过去的强调民俗事象研究还原到民俗事件研究,再由民俗事件研究还原到生活实践研究。
对照行政国家的基本蕴涵,可以发现,今天的中国同样是一种行政国家的国家形态。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行政国家不仅呈现出一般意义上现代行政国家的基本面貌,更凸显出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制度优势。
二、党政体制:理解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一个框架性概念
党政体制是分析中国行政体系的出发点,作为我们理解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一个框架性概念,[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关系,学术界目前有多种不同的表述,如郑永年的“以党领政”体制,任剑涛的“政党国家”,陈明明的“政党—国家”或“党—国体制”,唐亚林的“党治国体制”和“党兴国体制”,虽然表述各异,但都明确了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突出特点,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本文采用景跃进等人的表述——“党政体制”。参见景跃进等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郑永年:《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陈明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唐亚林:《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 意指中国共产党按照自身意志设计和构造当代中国的行政体系,行政体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运作;党不仅是行政体系的领导核心,对其实施包括动员、组织、管理、引导等在内的全面领导,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动主体,与其领导的行政体系等公共权力组织共同构成中国所特有的“广义政府”。[注] 政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等同于国家,狭义的政府限指行政机关。参见杨立华:《建设强政府与强社会组成的强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目标》,《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本文主要是从广义上来使用“政府”这个概念的,包括所有党政军群等公权力组织;当本文使用“行政机关”或“行政体系”这样的表述时,则限指狭义的政府。2017年两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参见《王岐山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体制 提高执政能力 完善治理体系》,《人民日报》,2017年3月6日,第4版。 这种党政体制的鲜明特点在于: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嵌入国家权力体系中,并与之形成“两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形态。党政体制对于中国行政国家建设具有关键性的情景预设的作用和意义,如果不理解党政体制,就不可能触及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实质;不了解党的领导,不了解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规律,就难以真正把握中国的行政体制和行政行为。[注] 任晓:《中国行政改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党政体制是在中国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党政体制是在低组织化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启动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选择。实现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但现代化并非坦途,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路上沦为了失败国家。这些失败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缺乏一个有能力的、非人格化的、组织良好的、自主的国家机器,说到底是“国家行政部门的失败”[注] [美]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正是由于行政力量的软弱,失败国家被牢牢地锁进了冲突、暴力和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注] [美]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
其次,中国共产党天生具有理性官僚制的特性,具体表现为组织严密、权力集中、纪律严明、指挥统一、运转高效。[注] 景跃进等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党的组织体系严密且完备,延伸到了车间、村社、学校和社团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呈现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特征。党的这种组织特征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盘散沙的状态,也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结构,即个体被纳入某一基层组织中,基层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所有党的组织,在民主集中制下形成科层形的组织网络体系”。[注]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这个网络体系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其之所以能够高效运转,恰恰受益于党自身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注] 景跃进等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49页。
实践证明,对党的行为的制度规约不仅不会弱化党的领导,反而会使党的领导更加规范,有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积累更加牢固的合法性基础。[注] 陈毅:《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研究: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为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求是》2004年第19期。
第三层面体现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关系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国家权力机关体系内的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人民政府)一委(国家监察委)两院(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有着明确的分工关系。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监察委行使监察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只要我们承认这种分工关系的存在,我们就得承认这种分工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分权的关系”,但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往往是行政权优先,形成了一种“法理上的人大集权和实际上的政府主导”格局。[注] 何俊志:《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较高的制度化运作水平是衡量政党现代性的关键性指标。[注] 唐皇凤:《使命型政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基础》,《武汉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作为一个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具有“强烈的制度化诉求”[注] 林尚立等:《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注]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如何在恰当地处理好党政关系的前提下,推进公共权力的理性化生长,进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是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主要挑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注]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过),“共产党员网”之“党章党规”专栏,http:∥fuwu.12371.cn/2014/12/24/ARTI1419388285737423.shtml。 这项规定为理顺党与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通过制度化建设,党同人大的关系、党同政府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相对规范的运作框架,即党统揽全局,合理区分党与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间的不同职能,保障各权力主体依法行使法定职权。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注]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0月30日,第3版。 这就意味着党把领导整个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使党和国家呈现出“两位一体”的关系,即党和国家在结构、功能与活动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党政体制“既是20世纪中国克服组织资源匮乏以建设现代国家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人们观察和理解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价值的解释性概念”。[注] 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复旦政治学评论》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三、公共权力制度化: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基本路径
直到今天,当提及行政国家的时候,仍然会有人将其理解为警察国家甚至法西斯国家。[注] 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增订新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它们之间的共同特点都是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性位置。如果只强调政府权力的集中,专制国家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行政国家”。因而,我们今天所讲的行政国家,根本不同于专制国家,而是在人民民主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创生的概念,基于法治的民主政治是行政国家赖以发展的母体。在现代社会,无论行政权力多么强大,它都要受到宪法与法律的约束,要受到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关的监督,还要受到公共舆论的监督,因而现代行政权力是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品格的国家权力,这种公共权力的规范化和理性化,是现代行政国家建设的基本路径。
制度构成了现代行政国家理性化的基础。所谓制度,就是一种稳定的、经久不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长期规则,它能够塑造、限制和调整国家权力主体的行为,决定国家发展的空间与活力。现代国家成熟的基本标志,就体现为支撑现代国家成长的制度体系的成熟度。因而,唯有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牢固地确立起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从传统型权威和卡里斯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化。传统型权威通常以“君权神授”为理论基础,卡里斯玛型权威则建立在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基础上,而法理型权威是以正式制定的规则和法令之正当性为基础的,如韦伯(Max Weber)所言:“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注] [德]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在法理型权威下,人民不再服从于个体的神圣性或超凡魅力,而是服从于理性的法律;他选择服从,是因为相信他所服从的法律具有正当性。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也是施政党,党在运用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也展示了其解决公共问题的施政功能。[注] 罗晓俊、孔繁斌:《执政与施政:执政党双重功能的一个理解框架》,《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从各组织体系的分工看,总体上是党负责路线、方针、政策制定,政府负责贯彻实施,“负责行政管理的政府与负责决策、协调,以及监督的政党一起形成了一种有区别但是密不可分的组织层次体系”。[注] [美]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执政党作为广义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使着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的政府职能,“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组织而又超越了国家组织”。[注] 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公共权力的制度化首先表现为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党的制度化建设,是党自身建设和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不断完善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制度,成为推动党的制度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为了使党的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注]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过),“共产党员网”之“党章党规”专栏,http:∥fuwu.12371.cn/2014/12/24/ARTI1419388285737423.shtml。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再次明确了这一规定。党给自身活动范围划定边界,其自我约束的意义不言而喻。党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表明党的行为的规范化“是一种从制度方面负责任的承诺”,[注] [美]汤森、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这也意味着国家政治生活发展出了一种具有确定性的且可预期的治理模式。
旧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一方面,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的政府,都饱受腐败、无能、低效的困扰,特别是民国政府,始终无法有效解决“军阀割据”的困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散且低组织化的社会,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一盘散沙”。[注] 孙中山:《建国方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中国的现代转型并非内生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势侵入的产物,这就注定了转型必然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动荡过程。要顺利实现转型,首先出场的一定不是现代国家体系本身,而是一个具有强大组织性的、现代化取向的权威力量——政党或军队。[注]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 面对一盘散沙、分崩离析的旧中国,不少仁人志士意识到,“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新问题,克服全面危机”。[注] [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要言之,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对具有高度统一的现代政党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政党体制的形成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做出应急反应的必然产物。[注] [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其次,公共权力的制度化表现为党领导下的公共权力配置的规范化。这一规范化配置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第一层面体现在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鉴于现代国家建设可被宽泛地定义为国家为提高治理能力而与社会各利益主体进行建设性互动以获取支持和资源进而实现其公共目标的过程,[注] [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等主编,卢军坪、毛道根译:《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与国家构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页。 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因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就是政党—政府—社会—市场关系调整与优化的过程,[注] 更多讨论,参见颜昌武:《机构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建国以来的中国》,《学海》2019年第2期。 是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关系的合理化构建过程,是“公共权力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注] 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949年后,我们建立起党政合一的治理模式,党因其权力集中而形成了一个强组织,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在这样的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积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样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为权力高度集中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注]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1978年以后,社会和市场急剧变化,促使国家不断革新和优化治理机制,这就需要合理配置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党与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可以被概括为“党自我限制它对后者的权力”,[注] [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即要进一步明晰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边界,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通过激活地方、激活市场、激活社会,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治理机制。
第二层面体现在党政关系上。建政之初,党沿袭革命年代的成功经验,通过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实现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元化领导。与此同时,党也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建构一种规范、合理且制度化水平高的党政关系,以使党和政能在职能和载体上进行合理分工。虽然党的领导人早就意识到党政职能要适度分工,但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实践仍然总体上呈现出党政一体化的特征,忽视了公共权力的横向结构建设。政党组织的行政化和政府组织的政党化,不利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具体来说,党组织承担过多具体行政事务,容易使政党本应具备的利益表达、沟通信息、联系群众等传统的政治功能被日趋强化的行政功能所消解;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与活动的泛政治化,则容易使政府本应具备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的优势不能得到充分体现。[注] 周光辉:《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DSA检查30例患者的阳性检出率为96.6%,三维磁共振静脉成像检验患者的阳性检出率为86.6%,两组检查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于表。
孙中山最早开启了“以党建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历程,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上,他希望将国民党打造成有组织、有纪律的“列宁式的政党”,认为“本党以前的失败,是各位党员有自由,全党无自由,各位党员有能力,全党无能力”。[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但中国国民党的涣散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观,最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究其原因,在于组织严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将分散的社会个体有机地聚合起来,将“一盘散沙”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满足了现代国家对于集中各种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要求,从而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依靠和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中国共产党主动选择了这种党政体制,而是中国这样多民族的超大型国家的现代化内在地需要这种党政体制。[注] 林尚立:《政党与国家建设:理解中国政治的维度(代丛书序)》,王海峰:《干部国家:一种支撑和维系中国党建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制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进水口布置有清污机抓斗导槽、拦污栅槽、检修闸门槽和事故闸门槽各1道,检修、事故门的启闭、拦污栅启闭和清污均利用进水口顶部独立桥机进行。
四、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组织载体
理性官僚制在一国的确立与否,是评判该国行政国家发展状况的“根本性的尺度”,[注] [英]毕瑟姆著,徐鸿宾等译:《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第65页。 美国行政法学家马肖(Jerry Mashaw)甚至断言:“除非具有充分发展的官僚机构,否则就不存在充分发展的行政国家。”[注] [美]马肖著,宋华琳、张力译:《创设行政宪制:被遗忘的美国行政法百年史(1787—1887)》,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韦伯也将理性官僚制视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志,认为官僚体系对于国家政治生活至关重要,现代国家真正的统治权“既非在议会的演说中,也非在君主的告示里”[注] [德]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6页。 ,而是体现在职业官僚日常的行政工作中。后发国家要顺利实现国家的现代转型,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专业化的、有效率的现代官僚体系。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面临如何打造一个高效政府的紧迫任务。建政之初,我们确立起一个身份制的干部制度,这些干部主要来源于革命年代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整体上并不具有专业性的理性官僚的特点。如邹谠所言,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新官僚机构”的下层、中层乃至高层人士,很大一部分“几乎没受过任何教育,除了从实践经验、政治训练与意识形态灌输中得到的知识外不具备任何知识”,因而,虽然这一新的官僚机器“在意识形态与组织上是强大的,但其人员缺乏专业技能与现代知识”。[注] [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致力于在党政体制的框架内建设一个理性化的现代官僚体系,[注] 景跃进等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一任务显得尤为迫切。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改革不合时宜的干部人事制度,认为改革的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注]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并明确提出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注]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
随着计算机领域的再次崛起,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人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从对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把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和使用上.这恰好对于热舒适的研究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加上ZigBee无线网络控制技术的整合,便能更加方便快捷地调节空调系统,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热环境需求.
在党政体制框架内,我们党建立起一个双重层级的现代官僚体系。首先,除政府体系外,执政党自身也构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科层组织。党作为嵌入政府体系的组织,具有与政府体系相对应的科层制结构。从横向来看,不仅中国政权组织的各个层级都有一整套党政机构,政府机构内部也都设有党的组织(如党组等);从纵向来看,执政党“把党和政府的正式的官僚机构的影响扩展到乡村一级”[注] [美]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页。 ,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纵横叠加,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双重官僚体系。这套官僚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党的领导的特色,即上级党组织领导下级党组织,上级政府领导下级政府,同级党组织领导同级政府。[注] 熊易寒:《解释好中国奇迹 理解透中国崛起》,《文汇报》,2017年5月30日,第6版。
2)中小学作为我们学习英语的基础阶段,为我们以后的英语学习提供了基本知识条件,如果能够针对中小学英语词汇学习做出更多的研究,提高中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和教学质量,这无疑会对我们的英语学习提供更好的方法。
中国官僚体系全面走向理性化,标志性的事件当属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我们党引入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以期打造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队伍,这不仅意味着干部队伍的组织结构和操作程序开始走向理性化,也意味着“意识形态和组织取向占统治地位的官僚政治”[注] [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开始大规模地向理性化方向发展。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并实施。这部建国以来关于干部人事制度的第一部法律规范,是干部人事管理规范化的重要标志,表明我国理性化的公务员制度开始进入实操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作为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第一部具有总章程性质的综合性法律,其2006年的正式生效是“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注] 胡威、蓝志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十年回顾、思考与展望》,《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标志着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整体进入专业化、制度化发展阶段,为中国行政国家的建设确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其理性化建设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严格控制编制总量、严禁超编进人、严格财政预算,确立了“编制就是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二是严把用人入口关,确立了主任科员以下公务员“凡进必考”的基本原则。这些刚性的制度约束,为我国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提升官僚体系的专业素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注] 颜昌武:《刚性约束与自主性扩张——乡镇政府编外用工的一个解释性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4期。
2.1 川木瓜醇提取物对3T3-L1前脂肪细胞活力的影响 与空白组比较,川木瓜醇提取物能显著降低3T3-L1前脂肪细胞的活力,且随着剂量的增加,作用更为明显,川木瓜醇提取物浓度为25.0 ng/L时,细胞活力为空白组的85.1%;200.0 ng/L时,细胞活力仅为空白组的41.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在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公务员的外延相对狭窄,限定于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在2006年开始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公务员的内涵被规定为“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其外延不再限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而是涵括了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工作人员。[注] 原国家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并没有直接列举七类机关的名称,是因为“从立法角度讲,在国家法律里直接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机关的事务,不太符合我国的立法习惯”。参见侯建良:《我国公务员范围的几次变化》,《中共党史资料》2009 年第3 期。 这一调整,不只是意味着公务员的范畴从狭义的政府工作人员扩大到广义的政府工作人员,更意味着党对整个官僚体系集中统一领导的强化,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广义政府”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从理性官僚制的角度看,国家行政体系是以专业分工、职责法定和非人格化等作为显著特征和优势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正是以功绩制(merits system)为基本前提,假定通过专门入职考试的人能够胜任未来专业技术岗位的工作需要。这同时也使得国家行政体系更关注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法定的边界与程序,即特别强调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行为的结果则不太关心,也不太关注行政对象的个体感受。其负面效应体现在:严格依法办事的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容易给公众一种僵硬的、缺乏回应的和没有人情味的印象,甚至招致公众的不满、批评和指责。
与照章办事、非人格化的行政体系相比,使命驱动型的执政党更具有回应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党通过其强大的渗透能力,在行政活动中注入政治因素,能够将官僚体系的注意力集中于某项特定的任务上,如波齐(Gianfranco Poggi)所描述的那样,“成千上万的党员,在领导者的指挥和命令下,在党提倡的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的鼓舞下,日复一日地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献给党要求他们去做的事,这些事情集中于公共生活中的政治活动”,[注] [美]波齐著,陈尧译:《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凸显了“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党通过自身的组织体系开展政治动员,通过归口管理的领导方式调动各方资源,能够打破理性官僚制专业分割和部门本位的痼疾,达到“整体政府”治理的良好效果。这样一种兼具使命驱动与依法行政特征的双重官僚体系,将日常性的专业事务或常规性的行政事务交由国家行政体系来完成,而将那些单个行政部门难以完成或事关百姓疾苦、社会稳定与政权合法性的重大事项交由党内官僚体系来处理,有助于促进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和政府体系的行政执行权的相得益彰。毋庸讳言,过度依赖党内官僚体系来提升执政合法性与治理绩效,也可能延滞行政国家的理性化发展。[注] 杨华:《县域治理中的党政体制:结构与功能》,《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5期。
五、结束语
一个国家实行怎样的行政体制,取决于该国的国家性质、人民需求和社会发展阶段。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行政国家建设通常以其内生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社会组织为历史起点,后发国家的行政国家建设则通常起步于现代国家权威力量的构筑。世界各国行政国家建设的不同路径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在党政体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核心,内嵌于国家治理结构当中,与国家权力体系形成了“两位一体”的关系。党政两位一体,既超越了传统政党组织的逻辑,也超越了传统政府组织的逻辑,本质上是能够有效实现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和政府体系的行政执行权和谐统一的现代政体。
“a gesture of withdrawal”是“a small offended laugh”的同位语,即这种略显恼怒的微笑本身就是一种离开的姿态。原译却将二者处理成并列结构。
基底节及脑白质多发腔梗还需与其它低密度病变如肝豆状核变性、病毒性脑炎、中毒性脑病等鉴别,这些病变往往基底节对称发病,肝豆状核变性为铜代谢障碍及肝硬化史,病毒性脑炎临床中毒症状,中毒性脑病有毒气吸入及药物过度使用及体内代谢中毒等以鉴别[4]。
中国行政国家建设曾走过一段艰难的探索历程。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国家建设走上了快速的理性化、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发展道路,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积蓄了能量。中国行政国家的建设路径,不是西方主流的行政国家模式在中国的复制,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出的一条自主之路,其最鲜明的特点,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推进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制度化建设,彰显了使命型政党与理性官僚制的双重优越性——既充分彰显了使命型政党的政治担当与政治智慧,又充分展现了理性官僚制的科层特色与专业优势。要言之,中国共产党主导行政体系的发展,行政体系的发展内在地需要党的领导,构成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Administrative State under the Party -State System
YAN Changwu
Abstract: The Party-state system has been formed and developed during China’s long-term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ractice, and it has played a presupposed role in China’s administrative state construct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for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in the core leadership pos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state, and it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forming a “two-in-on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state power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state under the Party-state system takes the Party’s leadership as the prerequisi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ublic power as the basic path,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bureaucratic system as the carrier. This construction not only fully demonstrates the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political wisdom of a 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 but also shows the bureaucr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of the rational bureaucracy.
Key Words: Party-state system;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ureaucratic system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19)07-0037-09
作者简介: 颜昌武,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政府改革与建设:能力、法治与监督”(批准号:16JJD630010);江苏省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决策过程中的县委书记权力运行优化研究”(批准号:18ZZB004)。
责任编辑 王治国
责任校对 王景周
标签:党政体制论文; 行政国家论文; 制度建设论文; 理性官僚制论文;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