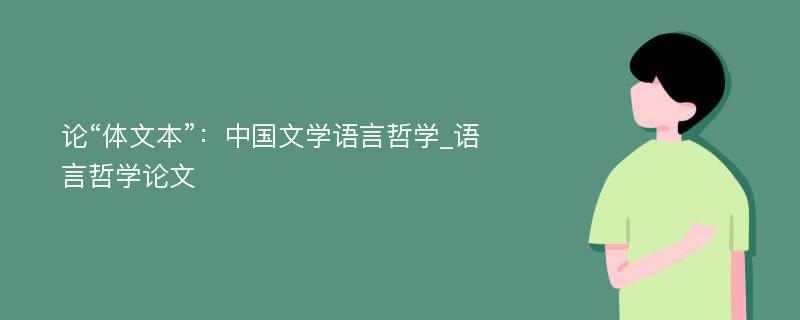
“身文”辨:汉语文学语言哲学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语言论文,汉语论文,哲学论文,身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5)02-0121-07 DOI:10.13967/j.cnki.nhxb.2015.0045 刘勰《文心雕龙》多次用“身文”论诗文,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即身性”语言哲学观。仅从字面上来看:“身文”之“身”指身体,“文”指纹饰、文采等,与“美”相关,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身体美学”范畴;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言,身之文”,“身文”主要是用来描述“言”的,是个语言学或语言哲学范畴,并且是个能反映中国古人基本文学观乃至文化观的语言哲学范畴。中西对话,古今贯通,首先要在哲学层面展开,才能有效地进行下去,研究“身文”这一语言哲学范畴,对此将有所启发。 当然,不管怎么说,即使用来描述“言”的“身文”,也与“身”相关。身与心或灵与肉的关系,是各民族文化中关乎生命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作为“两希”文明的西方文明来看,无论是在古希腊(如柏拉图等)那里还是在希伯来宗教传统中,身与心、灵与肉之间的张力都比较大,或者说,紧张度都比较高,并且都试图使肉、身服从于灵、心——但其对立面即放纵身体肉欲的想法和做法,也在西方文明史中时隐时现,而这对立的两面其实又是相互加强的:压制身体肉欲的文化力量越强大,放纵身体肉欲的愿望越强烈;反之,身体肉欲的极端放纵(如西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恰恰从反面展示着禁欲力量的强大,欲望放纵中有禁欲力量在作祟。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对西方文明作本质主义的理解,它其实也处于不断的历史变化中,西方当代理论中身体哲学、身体美学的兴起,就展示出一定的新的趋向。倡导身体美学的美国当代学者舒斯特曼坦言:虽然西方哲学提供了其对身体美学的最初思考,但是东亚思想,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成为其研究身体美学的持续灵感来源,他论及儒家的“修身”、道家的“守身”,对书画中的身体动作、书画理论中“气”“胃”“肉”等概念有所分析。而如果舒氏愿意深入到中国古代文献中,就会发现:“身文”或许可以成为其所倡导的“身体美学”的基本范畴乃至“元范畴”,比如他认识到:“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基础,而我们古人有云“礼乐二事以为身文”、“礼容全备于身文”、“身文而德备”(详述见后),“身文”与“礼”“乐”“德”等相关,既是个美学范畴,也是个伦理学范畴。如果说西方传统文化中身与心关系显得过度紧张的话,那么,“身文”范畴理论则昭示:身心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显得并不那么紧张——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并且主要是从文化理念上来说的,禁欲与纵欲的相互加强现象在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中当然也是存在的,兹不多论。 生命哲学与语言哲学又是相互贯通的:西方传统中的人之身与心的紧张关系,又表现为言之音与义的紧张关系;中国传统中的身心不离的生命哲学观,又表现为言、文与身不离的语言哲学观。对于试图解构西方传统的德里达的“语音中心论”说,笔者始终有保留意见,或许把西方相关思想传统概括为“语义(观念)中心论”才更妥帖。此外,为解构“语音中心论”,德里达又强调书写(文字、书面语)比口谈(语音、口语)更重要,口谈具有“即身性”,而文字书面语则可以离“身”而在。由此来看,试图解构西方传统的德里达,是否却更深地陷入西方传统窠臼或更深“结构”中,亦未可知。附带强调的是:“象形”只是汉字“六义”之一,不通汉语及中国语言哲学的德里达对汉语文字象形性之想象性的过度夸张,甚不靠谱,而汉语学界对洋大师在这方面的随声附和,尤不可解。从西方当代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来看,总体上也具有离“身”论“言”的“语义(观念)中心论”色彩,其中,“语言能否传达情感”,是其涉及的问题之一——对此,分析语言哲学大家维特根斯坦有直接的分析: 我们是否也能想象这样一种语言,一个人可以用这种语言来写下或说出他的内心经验——他的感情、情绪以及其它——以供他个人使用?——我们就不能用日常的语言来这样做吗?——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这个。这种语言的单词所指的应该是只有说话的人知道的东西,是他直接的私有感觉。因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懂得这种语言的[1]。 在维氏看来,人的感觉、情感等是不可以作为语言的“意义”或“语义”传达给别人的,比如我收到一张写有“我很痛”的字条,我是无法判断这种“痛”在写这字条的人身上是否真的存在及“痛”的程度究竟如何的——但是,“语音”呢?尤其“声成文”之后的和谐语音结构,能不能传达人的“内心经验——他的感情、情绪以及其它”呢?我们古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论诗的“声情”范畴、论文的“声气”范畴理论,就充分表达了古人这方面的认识(当然语言和谐形式结构所传达之“情”已确非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直接的私有感觉”了,详见拙著《声情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 结合生命哲学,即使从书面文本来看,相比较而言,语义结构具有更强的“离身性”,而语音结构具有相对较强的“即身性”,因为语音是与人的身体的发声器官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当代语言哲学的“离身性”,与其身心关系紧张的生命哲学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与身心不离生命哲学传统相关的“即身性”,可谓汉语哲学的基本特点,并且也是汉语文学理论的基本特点——这由“身文”这一范畴理论集中体现出来了。 考虑到“身文”范畴及其相关理论即使在汉语学界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下面对涉及“身文”的相关原始文献略作梳理。 一 关于“身文”的文献梳理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文”本指纹身之“纹”,与身体相关。古代工具性类书如《佩文韵府》卷十二、《渊鉴类函》卷二百六十六皆列有“身文”条;而“身”与“文”连缀在一起的最早文献,似是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引介之推语: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2] 《国语·晋语》也有“言,身之文也”的记载: 阳处父如卫,反,过甯,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谓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举而从之,阳子道与之语,及山而还。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从之,何其怀也!”曰:“五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以外易矣。若内外类,而言反之,渎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机,历时而发之,胡可渎也!今阳子之情譓矣,以济盖也,且刚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惧未获其利而及其难,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贾季之难,阳子死之[3]376-377。 “情(身)—貌(华)—言(文)”,约略可见与“身文”相关的汉语—生命哲学的基本结构。又,《国语·鲁语》载有“服,心之文也”说: 虢之会,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蔡公孙归生与郑罕虎见叔孙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郑子皮曰:“有执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国也;公子围,其令尹也。有执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大夫有贰车,备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设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无其心,而敢设服以见诸侯之大夫乎?将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为君,必死,不合诸侯矣。”公子围反,杀郏敖而代之[3]186-187。 当然,作为“心之文”的“服”,也是“身之文”,身心关系隐现其中。左丘明所记载的与“身之文”相关的故事,竟然皆与死亡有关,作为“身文”的“言”乃是关乎人命之“枢机”,兹事非小。 此后,魏晋至李唐文献中,“身文”使用频率比较高。陈蕃《让封高阳侯疏》:“臣闻,让,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盗以为名。”(《全后汉文》卷六十三)[4]819。这里实际上以“让”等德行为“身文”。孙绰《颖州府君碑》有曰:“君天纵杰迈,奇逸卓荦,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远鉴之识,礼乐饰身之具,固以足之于天仞,冠之于搢绅,出匡南位,功深于爵,金龟三曜,冲壤再发,道光古贤,风改雕伪,允可谓明德宏猷,赞世之伟器者矣”(《金晋文》卷六十二)[4]1814,“礼乐饰身之具”也可谓对“身文”的描述,礼乐是“文”身之具。梁简文帝《谢敕赉方诸剑等启》云:“才发紫函,雕奇溢目;始开泥检,丽饰交陈;已匹丹霞之晖,乍比青云之制;身文自贵,器用惟宜,寒暑兼华,左右相照。”(《全梁文》卷十)[4]3005所谓“身文”非指言语;而梁元帝《加王僧辩太尉、车骑大将军诏》所谓“行为士则,言表身文”(《全梁文》卷十六)[4]3040则直接以言为身文。又僧顺《释三破论》有云:“《左传》云:言者身之文。《庄周》云:言不广不足以明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虽言出于口,终不以长舌犯人。则子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为累,伤人之深哉”(《全梁文》卷七十四)[4]3399。而刘师知《侍中沈府君集序》:“至如敦厚之词,足以吟咏情性,身之文也;贞固之节,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全陈文》卷十五)[4]3488,则是直接以“身文”论诗文了。 庾信《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少保豆卢公神道碑》有云,“公资忠履孝,蕴义怀仁,直干百寻,澄波千顷,留心职仕,爱玩图籍,官曹案牍,未尝烦拥”,“宝珪世胄,雕戈旧勋,名称实宾,言谓身文”(《全后周文》卷十五)[4]3959;后周武帝《答李充信诏(五年十一月)》云:“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豳国公广,藩屏令望,宗室表仪,言著身文,行成士则,方凭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蓼,便致毁灭,启手归全,无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间才藻,追叙于中蔚,东海谦约,见称于身后,可斟酌前典,率由旧章,使易箦之言,得申遗志,黜殡之请,无亏令终。”(《全后周文》卷二)[4]3891常爽《六经略注序》可谓六经“身文”论: 《传》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宁越庸夫也,讲艺以全高尚之节。盖所由者习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焉。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莫不导以《诗》《书》,教以《礼》《乐》,移其风俗,和其人民。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秋》也。夫《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其几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顷因暇日,属意艺林,略撰所闻,讨论其本,名曰《六经略注》以训门徒焉(《全后魏文》卷三十二)[4]3673。 “经典者,身之文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焉”,身之文也是道之文,而六经的功能之一就是“文身”——这其实也正是刘勰《文心雕龙》开篇《原道》、《征圣》、《宗经》三文的基本思路,两者可对读。 李唐文献中,“身文”使用频率就更高了,其中一些文献是直接论诗文的。以下是《全唐文》载录的相关文献,先罗列泛论身文的文献:武宗《册李德裕太尉文》:“修德刑为战器,阅礼乐为身文”(卷七十七)[5]811。宣宗《授郑涯山南东道节度使制》“礼容全备于身文,和易雅彰于心术”(卷七十九)[5]829,《授夏侯孜集贤殿大学士制》:“以孝友为家行,以礼乐为身文”(卷八十)[5]838。苏颋《授游子骞屯田员外郎制》:“言用身谋(一作‘言曰身文’),智为心计”(卷二百五十一)[5]2537。张九龄《故韶州司马韦府君墓志铭(并序)》:“言炳身文,礼充物检”(卷二百九十三)[5]2971。常裒《授李琬宗正卿制》:“饬礼乐于身文,详典刑之政体”(卷四百十二)[5]4220。于邵《送房判官巡南海序》:“以公忠为已任,以学行为身文,蹈和以全真,修睦以合义”(卷四百二十七)[5]4356。李观《上陆相公书》:“《传》曰言身之文也,在乎身,非言不见也”(卷五百三十三)[5]5417。令狐楚《谢赐春衣牙尺状》:“臣伏以衣服者身之文章,尺寸者王之律度。被于四体,不衷则灾。考以二分,无差为贵”(卷五百四十一)[5]5495。李德裕《赠崔珙左仆射制》:“礼乐二事,以为身文”(卷六百九十八)[5]7168。 再看与诗文相关的文献:李峤《上巡察覆囚使历城张明府书》:“至于组织身文,筌蹄意象,照神交于千载,得奥旨于三复”(卷二百四十七)[5]2501,“组织身文,筌蹄意象”用于描述诗文创作亦无不可,与此相近的表述是萧颖士《登临河城赋(并序)》:“备润身之黼藻,闻染翰之蹄筌”(卷三百二十二)[5]3262。“润身”也可谓“文身”、“饰身”或“藻身”,李德裕《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内侍省事刘公神道碑铭》有“藻身文囿”(卷七百十一)[5]7297说;吕温《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都督秦州诸军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义军节度陇西经略军等使上柱国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尚书右仆射中山刘公神道碑铭》有“周旋经训,斧藻身文”(卷六百三十)[5]6362之论。宋暠《獬廌赋》:“诗美乎思无邪,道贵乎解其纷,得道之实,为身之文”(卷九百五十七)[5]9935。而权德舆《贞元二十一年礼部策问五道》更是直接以身文论诗文:“言,身之文也。又曰:‘灼于中必文于外。’司马相如、扬雄,藉甚汉廷,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涤器,或赞符命以投阁,其于溺情败度,又奚事于文章耶?至若孔融、祢衡,夸傲于代,祸不旋踵,何可胜言?两汉亦有质朴敦厚之科,廉清孝顺之举,皆本于行而遗其文,复何如哉?为辨其说”(卷四百八十三)[5]4937。 又,言之“身文”论又与“枢机”论相关(《文心雕龙·声律》就有“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语),张宪《砚铭》:“言出乎身,文以行之。噫嗟君子,慎尔枢机”(《唐文拾遗》卷四十七)[5]10913;阙名《大唐故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开国公樊府君碑铭[并序]》:“言表身文,慎机枢于自远。行成士则,总枝叶于昌年”(《唐文拾遗》卷六十二)[5]11073。徐彦伯长篇《枢机论》(卷二百六十七)也是论语言的: 《书》曰:“唯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又云“齐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语,节饮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出其言不善,千里违之;”《礼》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呜呼!先圣知言之为大也,知言之为急也!精微以劝之,典谟以告之,礼经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修其诂训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动则物应,物应则得失之兆见也。得之者江海比邻,失之者肝胆楚越,然后知否泰荣辱系于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济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镂其心,右阶铭其背,南容三复于白圭,箕子九畴于洪范,良有以也。是以掎摭瑕玷,详黜躁竞,审无恒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利生于口,森然覆邦之说;道不由衷,变彼如簧之刺:可不惧之哉?……孔子曰:“予欲无言。”又云:“终身为善,一言败之,惜乎!”老子亦云:“多言数穷。”又云:“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议人者也。”何圣人之深思伟虑,杜渐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隐。钳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怀?括囊而处,孰启谟明之训?……大雅之言,犹钟鼓也,人考击而乐焉。作以黾镜,周公之言也;出为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国侨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孙之言也。是为德音,谐我宗极,满于天下,贻厥复昆。殷宗甘之于酒醴,孙卿谕之以琴瑟,阙里重于四时,郢郡轻其千乘:岂不韪哉?岂不体哉?但懋探大猷,克念丕训,审思而应,精虑而动,谋其心以后发,定其交以后谈,不蹙趋于非党,不屏营于诡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累累之绪,扑其炎炎之势,自然介尔景福,锡兹纯嘏,则悔吝何由而生,怨恶何由而至哉?[5]2718-2719 主旨是“慎言”,而“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济身,亦可以覆身”,大抵可见古人的基本语言观。 李唐后,“身文”也偶或出现在相关文献中,兹不赘录。 二 “身文”与“人化批评”及其理论意义 以“身文”论诗文最多者,是汉语文学理论经典《文心雕龙》:“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明诗》)[6]66,今人范文澜于此注引介之推语“言,身之文也”云云;再如“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表》)[6]408,《程器》有相近的说法“岂无华身,亦有光国”[6]720;“言既身文,信亦邦瑞”(《书记》)[6]460;其中两篇重要篇章《原道》、《情采》中其实也间接含有“身之文”论。若说“文”是其关键词,则“身文”论乃是其“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且可以说“身文”语言哲学观构成了刘勰文学观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一。 其实,《原道》也可谓《原“文”》,“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天之文、地之文为道之文,“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在“天地—心—言—文”这一结构中,“言”处于重要地位。“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动物之“身之文”;“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此所论其实就是《情采》篇所谓“形文”,而以下则论及“声文”:“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形文’也),声发则文生矣(‘声文’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有心之器”之“器”是指人相对于“心”的“身”,所以,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身文”。“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6]1-2——这是六朝人在儒学传统中为言之“文”辩护的重要着眼点。 在此基础上,刘勰描述了“爰自凤姓,暨于孔氏”的言之文的发展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圣人“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6]2-3——今人论及《易传》“言不尽意”论,每每妄言古圣人轻视外在之“言”,而重视内在之心、情、意,未免厚诬古人:作为“道之文”的“辞(言)”岂容小觑!此其一。其二,今天解读《原道》,往往懒于细读,当然更主要是囿于很大程度受西人影响的文学语言观的影响,只抓住所谓“道之文”,且以后世宋儒鄙薄文采的“文以载道”为据释之,尤不足为训。 如果说《原道》可谓《原“文”》,那么,《情采》也可谓《情“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里像《原道》所讲一样,讲的实际上也是动物之“身之文”,接下来的“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可以说讲的是人的“身之文”。“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此处三“文”说理论意义重大,关乎诗文之体用,即以“情”为“体”,而以“形文”“声文”为“用”。“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文”既指身之文,也指心(情志)之文,“心定而后结音(‘声文’也),理正而后攡藻(‘形文’也),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6]537-539——要强调的是:今人以西人之内容—形式论来分析情—文关系,虽非方枘圆凿,却也不尽和合《情采》虽然还是以质—文论情—采,但其三“文”说则是以“体—用”论之。 理解“身文”语言哲学论的意义,首先当结合《文心雕龙》中大量的“类身(体)性”表述。如《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6]513,“形”与“体”互文,也指人的身体;《体性》:“辞为肌肤,志实骨髓”[6]506,《附会》:“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6]650——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有极相近之表述:“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7]267——这其中实际上:以“情志”、“理致”为“体”,而以“事义”“辞采(华丽)”“宫商(气调)”为“用”——这种“一‘体’三‘用’”之说,后来在晚唐诗格中被大量征引①。这种类身性表述与魏晋前后的人物品藻密切相关。 汉代以来的人物品藻,首先可谓是一种政治人体学,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观相”学,通过观察人的体貌特征(形(面相、骨相等)、神、气等等),来探寻人的才性、品德,如此,人之身可谓“才之文”、“德之文”,反过来说,“才”、“德”也可谓人之“身之文”。刘邵《人物志》总结了人物品藻经验,得出了九征系统:神、精、筋、骨、色、仪、容、气、言,其中蕴含着神、骨、肉三层结构或形(身)、神(气)两层结构。到了魏晋,人物品藻的主潮,由政治上的裁量人物,转为美学上的欣赏人物,转为审美人体学或审美观相学,由探察面相、骨相后面的才性、品德,转为品鉴面相、骨相背后的才情、神韵:如此,人之身可谓“情之文”、“神之文”,而反过来说,“美(神)”也可谓人之“身之文”,审美化的人物品藻可以说就是一种“身文”美学——这集中体现在《世说新语》的相关记载中,而在审美的人物品藻中产生了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当时人物品藻虽然重“神”、“骨”,但也不排斥“肉(肥)”之美。由人物品藻形成的审美结构,被运用到一切审美对象之中,类身性表述在诸类艺术理论中被广泛运用,成为中国美学把握审美对象理论的基本结构。 由气、阴阳、五行而来的人体结构进而形成中国型审美对象结构,并从审美的人物品藻,扩展到其他审美领域,标志着中国美学的成熟。从文化上看,中国文化中作为宇宙根本观念的“气”,从哲学(先秦)到人体学(两汉)再到政治人才学(两汉三国),最后进入美学,从审美人物品藻(魏晋)扩衍到其他审美领域。从美学自身看,从先秦孔子的“文质彬彬”“有德有言”,到汉代扬雄的“事辞相称”“丽以则”,重视的是文艺作品内容中实的一面,与气的理论不相干。到魏晋曹丕《典论·论文》以气论文,强调文之气来源于人之气,人之气又来源于天之气。审美对象理论的发展上升到了文化高度。钱钟书先生将中国“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同类的活人”的独特做法称为“人化文评”[8]——这是一种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思维方式影响的审美把握方式。 当然,所谓“类身性”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艺术形式结构与身体结构作类比,两者就并无直接关系。所以,“类身性”的“人化批评”还当结合“即身性”来理解,而所谓“即身性”强调了艺术形式结构与人的身体的相互作用——而这跟礼乐交融及诗(歌)乐舞交融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古代作为宫廷礼仪的歌乐舞表演,既是“礼”,也是“歌”、“乐”、“舞”,其中,“歌”、“舞”与人的身体相关,而《礼记·郊特牲》有“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之说——这在魏晋以后演变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流行说法,在诗(歌)乐交融活动中,重“肉声”甚于“器声”,乃是古人主导性传统;而今人在讨论古代诗歌与音乐关系时,每每从诗歌从属于音乐(器乐)上立论,可谓差异之毫厘,谬以千里。 在宫廷礼仪中,与身体相关的“声(人声、歌等)”与“容(舞容、色、肢体动作等)”之有“节”非常重要;反过来说,礼乐的重要文化功能之一,也就是使人的包括发声在内的身体动作有“节”,并由“节”身而“节”心。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乃君子“修身”之法,同时也是“修德”之法,而修“德”不仅要修“心”,而且要修“身”——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古人所讲道德修养具有较强的“即身性”,绝非只重视内在的心性修炼(宋儒或有此倾向),而这种“即身性”也绝非仅仅指在实际的社会行为中践行某种道德善念,即通常所谓的“身体力行”,而且也包括身体动作之有“节”:比如士人、女子之玉佩等饰物,就有“节”身即使行走有节奏的功能。而“修”身,同时也是“文”身,言语有节,既有节奏,又富文采,乃是君子“修”身或“文”身之法宝——此即:言,身之文也。 再从“言”本身来看,古人又有“直言”与“文言”之分,而言之文又主要分“形文”与“声文”,而“形文”尤其“声文”具有更强的“文”身作用。直言主要是用语义或概念来表达,从与身体的关系来看,“即身性”最弱;刘勰所谓“形文”在诗文创作中主要表现为用情景交融的“意象”来表达,而“声文”则主要表现为用声情交融的和谐“声情”结构来表达——这其中“声情”结构表达方式具有更强的“即身性”,《文心雕龙·声律》有云: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非声学器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6]552。 以上对“即身性”的强调,也是理解刘勰言语“身文”论的关键、枢机所在。进一步深入理解“身文”语言论的理论意义,还当结合对《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及《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等表述的语言哲学思想的理解:“书—言—象(卦)—辞”是个关乎“意”之表达方式的连续性的结构:“书”指语言之书面的表达方式,“言”指口头言语,“书不尽言”所强调的其实是:“即身性”较强的口语在“意”之表达功能上也相对较强(尽管未能“尽”意)。 “辞”何尝不也是一种“言”?当然“辞(卦辞)”从表达主体来看是圣人之言,从表达流程来看是依卦象而生之言;但是,不管怎么说,由“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表述可知:《系辞传》绝未在绝对的意义上强调任何语言都绝对不能表达“意”——对此的误读其实从魏晋以《庄》释《易》的玄学就已开始,如荀粲就倡导绝对意义上的“言不尽意”说,但今人误读尤深。同样,《诗大序》也含有“言—嗟叹—咏歌—舞蹈”这样的关乎“志”、“情”之表达方式的连续性的结构:“咏歌”依然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但已是一种“声成文”的语言表达结构。其实,“言之不足”之“言”主要指“直言”,而“声成文”的“咏歌”可谓“文言”,语义、概念性的“直言”之所以不足以表达情志,是因为其“离身性”,而情志离不开“身”;咏歌、舞蹈之所以足以表达不离身的情志,正是因为其与身体的和谐有节的发声动作(咏歌)、肢体动作(舞蹈)密切相关,即具有极强的“即身性”。 还可以从语言艺术与其它艺术体裁的关系来看:西人舒斯特曼从古代书法、绘画艺术中觉察到了创作者的“身体动作”(这与高建平先生的重要研究成果相关),从接受的角度来看,欣赏者主要是通过对书画作品的心理学所谓的“意动”去感受创作者的“身体动作”的,一般来说,不需要欣赏者直接的身体动作的介入;而在对诗文这些语言艺术作品的接受,清桐城派所强调的“因声求气”之接受方法,则需要身体的“发声”动作即大声朗读的介入,默读等方法相对而言不能充分“求”索到经典古文及其创作者之“气”。从语词上来看,“文”本诉诸视觉,而古人艺术论却多言诉诸听觉的“声文(声成文)”,听觉与身体的发声动作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说,对于语言艺术的接受方式具有更强的“即身性”——这或许也是语言艺术在古代中国整个艺术体裁体系中之所以处于相对显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果说《诗大序》所谓“言之不足”之“意”主要关乎诗人之“情”的话,那么,《易·系辞传》所谓“言不尽意”之“意”则主要关乎天地之“道”。《文心雕龙》强调文艺既是道之文、心之文(《原道》),又是气之文(《风骨》《养气》等)和身之文,是道、气、身、心之贯通,是宇宙、身体、文艺同构,所以,赏文、鉴艺之道与观物、相人(人物品藻)之道相通,对身体结构的强调使审美对象结构更富于生命意味,对自然结构的强调使审美对象又更富本体意味——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一“气”贯通而身道互动、身物不隔、身心不二、形神相融、灵肉不离等特点,或者说,中国文化这些特点,施之于把握审美对象的方式,就表现为体用不二、感性与理性相融、形式与功能(内容)不离等特点。 最后,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谓“即身性”,主要是从相对的价值中立的角度所描述的中国文化、汉语文艺创作及其理论的“特点”,而非价值判断上的“优点”或“缺点”。而我们今天要判断古人文艺创作及其理论的优点或缺点,恐怕首先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其特点——如果不如此,对其优缺点的价值判断恐怕很难准确、到位。比如,“文以载道”是今人所熟知的也确实是古人的重要文艺观之一,今人往往从西人建基于语言工具论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种强调思想控制的文艺观念——这种判断不能说绝对的错,但是,如果说古人强调在文艺活动对人的控制的话(这仅仅是一种假设,是否准确,尚需研究),那么,他们所强调的就绝非仅仅是思想观念控制,同时也是一种“身体控制”——这种阐释,较之单纯的观念意识形态控制论,至少要更为深刻,兹不多论。以“西”裁“中”,固然不对,但拒绝与“西”对话,恐怕也很难将“中”说清:如何在中西互释、互通中推进对中国传统文化、文艺更深入的研究,看来尚需时日。 [收稿日期]2015-01-22 注释: ①参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M].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刘方喜.声情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达[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之第1章及与“体与用”初辩.